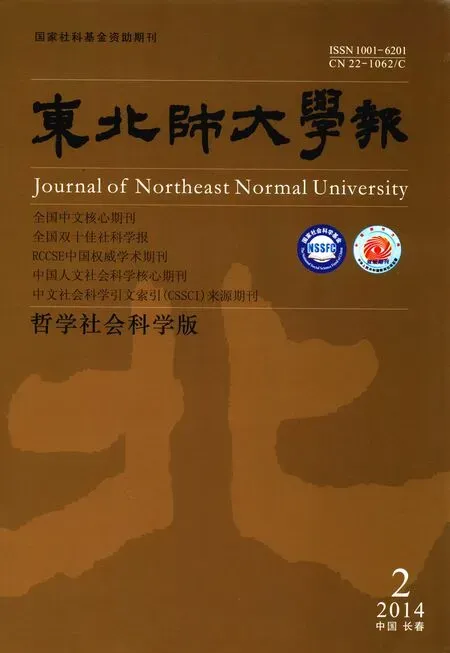民俗学视阙下近代甘青藏区的“男逸女劳”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男逸女劳”,并非广西土著民族聚居区的独有现象[1],在甘青藏区也长期存在。它有悖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男耕女织”,与人们普遍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原则恰恰相反,“诚异闻也”,因此很早就引起了汉地旅行者的广泛关注。藏族妇女“凡普通男子所为,概为之……并不以为劳”。如果说藏族妇女如此任劳任怨是藏区的传统美德,那么这种传统美德在藏族男子身上为何几乎没有体现?如果说男逸女劳,“殆习惯使然”,那么这种习惯又缘何而成?虽然,诸如刘正刚、范玉春等许多学者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但对其深究者甚少。为此,笔者试图以民国时期游记等资料为中心,对甘青藏区“男逸女劳”这一民俗产生的原因进行探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近代甘青藏区的“男逸女劳”
青藏高原长期为藏人所居,“平时操作,男逸女劳,稼墙耕褥外,妇女之力居多”[3]。甘南藏区,“实以女子为中心,凡一切生产事业及劳苦操作……均由女子任之,男子则反是……常饮酒谈天,或负枪带刀,骑马闲游”[4]341。西藏“男子怠惰,女子强健。普通男子所操之业,在藏中大抵为妇女之职务……凡普通男子所为,概为之”[5]。男逸女劳在藏区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传统社会也可能缘此在文献中鲜有记载,至近代引起了进入藏区的旅行者们的广泛关注,在他们的考察记中才多有体现。
(一)近代甘青藏区男子的安逸
在藏区,“家有二男,则一男为僧。有男女各一,则男子为僧……虽有一家数男,皆不为僧者,则寥寥无几”[6]97。“男番惟一出路,是离开帐篷,进入寺院,充任喇嘛,整日拜佛诵经。既有金屋可居,又不忧衣食”[7]357。“男子除当喇嘛……安坐而食,除缝衣、守、户、嗅、鼻、烟、谈天外,几无所事”[8]14,即使不当喇嘛僧,也是“终日骑马荷枪外出打猎,和结群游荡”[9]245,或者以“藉备兵差为名,整日骑马驰骋,学射逞雄”[10]257。
藏族男子只是做些诸如捻线、缝衣、画像等较轻的工作。在玉树,西番“男子多腰小包藏针,补绽时则捻羊毛为线”[11]。在拉卜楞,“他们的皮袄、皮裤,不论男女老少的,完全由男子来缝制”[12]96。在青海保安,“男子长年出外谋生,每年阴历十月始归,正月十五日后又出外。据云:男子在外之职业,大半为画佛像,少数为铜匠铁匠,或经营商业,即喇嘛亦多出外画像。于是男子在家之日甚短,即在家中,亦不任一切劳动工作。”[13]185这些是藏族男子日常生活中仅有的几项工作,尽管其捻线、缝衣、画像的技艺可能也很熟练,但是其工作强度始终无法与妇女的户外劳作相提并论。
(二)近代甘青藏区女子的劳苦
藏族大部分家庭以游牧为业,放牧是女子的日常工作,“一家养着几百只牛羊,都是番妇很留心的看守着,他们每天早上,驱使牛羊上山吃草,每天晚上照例邀着一群一群的牲畜进了帐篷前面的木栏,而且喃喃的数着,倘使牛羊掉了,或者是被抢掉,总晓得是那一只,因为每一只牛羊,都有一个名字”[7]357。即便在新年,女性的放牧工作也不间断,“(新年这一天)大概有十点钟的样子了,牲口才开始在草地上出现了。藏女们喜色盈盈地一边唱着,一边儿牧着,也是修饰的焕然一新”[14]。除了放牧,管理牲口,挤牛乳,做酥油都是番妇们所专心从事的工作,也是她们主要的职务[12]96。藏族民众的游牧地时常变动,牧群迁移也以女子为主要劳动力,“在甲地时草食尽则迁徙乙地,三日以前公议启程日期及欲赴之目的地与路线,全部人畜分为三队,第一妇女,骑马持枪穿着美丽之服饰,第二用品家俱,第三牛羊。妇女先行达目的地,即预备,后队粮秣,有时妇女竟早到三四日。”[15]在青海同仁,“帐房亦是女人下苦将牛毛帐房撑于避水之地”[8]40。女性在游牧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牧场迁移及日常畜牧都由她们来完成。
在农牧交错地区,藏民也从事农业耕作,耕作者以女性为主。甘南从土门关至拉卜楞寺中间的夏河两岸,适宜农耕,“据任承宪君调查,夏河县农户四百五十家,占总户数百分之五。已耕地一万四千九百余亩,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二。藏民体质强健,尤以女子为然,故农家每户人口虽少,但经营三四十亩之地,尚不感人工缺乏”[16]125。“五月底正是锄草时节,只见三三两两的番妇们,有的赤着右臂,有的整个裸着上身,裹着腰,很勤苦的在地里刈草”;“山堂对河,有一个寺院,庙下面是一片较大的田地,地里有三四十个番妇结队成排的在那里弯腰锄草”[17]310-311。在青海,“途径白马寺,乍见藏女二人,在马铃薯地中耘草”[18]142。藏区的农业耕作只在部分地区存在,女性是主要从业者。
其实,无论是游牧区还是农牧交错地带,藏族妇女都是家庭的脊梁,几乎包揽了家庭的所有劳务,生儿育女仅仅是其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倘使生育了儿女,都是妇女的抚育……所以很多的番民,只知有母,不知有父”[7]370。西藏妇女还要“耕作田野,或登山采樵,或负重致远,或修缮墙壁,建造房屋……且在家自庖厨、纺绩、裁缝,及老幼之亦梳发等亦为之”[5]。青海都兰妇人还要主持家务,“每日操作甚为辛苦,甚至耕作、修葺、纺织……每日黎明即起,作饭、挤奶、牧放牲畜、汲水、磨炒面制酥油及奶饼,客至烹茶作饭招待极为殷勤。日暮将牲畜一一用绳系上,复挤奶子作晚饭,老小一起就寝后,伊始于牲畜附近处寝”。在“拉卜楞……街上背着大水桶往河边汲水的妇女,尤为醒目”[17]340。高原地区山高水深,“女子则跋山越岭,行不喘气,能背负百斤,徒步长涉,面不改色,为汉人妇女者望尘所不及。犹有超人奇术者,盛水一桶,重可八十斤,一绳捆之,负于背上,水在桶中周旋,点滴不溢”[10]257。她们“每日早晚,榨取马牛羊乳、作饭、牲畜、汲水、磨面以及客至之招待,皆萃集妻女之身,极为劳苦。”[18]150实际上,藏族妇女的劳苦岂止于此,她们还要从事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在商业贸易方面,在汉地,贩夫走卒执业者多为男子,而在藏区,“妇女尤多”[19],屡见不鲜。藏族妇女中不但有坐贾行商,而且充当中介牙人,“货物辐辏,交易街市,女人充牙僧,经纪其间”[20]。在康藏,“打箭炉番女,年十五以上即受雇于茶客,名曰沙鸨。凡茶客贸易听沙鸨定价。直人不敢校,茶客受成而已。”[21]在拉卜楞,“急遣人购草,数小时后,有藏妇数人,负草来售”[16]124。
外出佣工方面,也以女性为主,如甘南夏河,“藏民体质强健,工作效率颇大,尤以女子为然。本县各种劳动工作,雇用藏民妇女,固时有闲忙,价无一定,现在每日工价约有二角有奇”[22]。拉卜楞,“有一处垒墙的工程正在进行,在版筑架子上用力榨压松土,使为坚固的一概是女人。但是这一般女人仿佛是由某部落来拉卜楞专以卖力气为业的”[17]340。青海保安,“城系土城,须时时修理,时当农隙,正修理城墙,劳动者全为妇女或儿童,男子全袖手旁观……妇女运土,或以肩背,或用驴驮,小儿运土,用柳筐悬于胸前,其合作精神,颇可佩服。”[13]185外出佣工挣钱的女性,从事着繁重的体力活,其劳苦之状毋庸多言。
在服役当差方面,藏民女性也一马当先,“一遇调遣,则备马裹粮,奔走效命”。在青海巴戎,“沿途各村庄,大半为藏族,行十余里,遇藏妇十余人,仆仆道上,据云:往扎什巴军营当差者,犹昔时‘汤役’之风也(向例官长或军队至番地时,番民妇女侍候,供给茶汤,谓之汤役)。”[13]177在玉树,“内地委员兵弁,至番酋派人供役,名曰汤役,多用女子充当,汲水执爨耐苦过于男子”[11]151。在这方面,马鹤天对此亦有记载,“又有所谓汤役(司粪水之役),由藏民妇女执役,结古附近札武等族,均派人来轮流服务”[16]444。藏区女子所服差役,大多是又脏又累的服务性工作。
据考察,在藏区“一切劳苦操作之役,皆女子任之”[22],而且其劳作“自十五岁以下”既已开始,“多拾马粪苦工”,直至年老,其辛苦程度无与伦比,是西北地区较为少见的女性生存方式,也是藏族妇女生存状况和社会角色的真实写照。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凡普通男子所为,概为之……并不以为劳”[5]。如果说藏族妇女任劳任怨是藏区的传统美德,那么这种传统美德在藏族男子身上为何几乎没有体现?如果说是习以为常,那么这种习惯又缘何积淀而成,的确有必要予以探究。
二、甘青藏区“男逸女劳”的成因
从前文不难看出,藏族妇女不仅主内,而且主外,藏族男子“不过为妇女之辅助”,她们这种内外无别的角色意识与内地妇女迥然不同。藏族妇女几乎承担了所有琐碎的家务劳动之后,还要到户外从事更加繁重的户外劳作,她们几乎独自撑起一片蓝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男逸女劳的劳动格局“殆习惯使然”,在其产生之初必然存在适合其生长的条件,在其传承过程中一定存在赖以维系的原始观念和新生观念。
(一)藏传佛教影响下的藏族女性观念
在妇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不同区域先后都经历了女神、女奴到女性三个阶段,但深受区域地理环境和区域社会历史人文史环境的影响,区域社会对女性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甘青藏区。藏族妇女处于相对于汉族主流文化和男性主流文化的边缘,佛教传入西藏后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关于藏族起源的著名神话《猕猴岩魔女》。萨迦·索南尖赞在其历史著作《王统世系明鉴》中通过比较作了最具代表性的描述,藏族女性承袭岩妖魔女的性格特征,即“岩妖魔女传出来的一类,贪欲好怒,经商谋利,好盘算,喜争执,嬉笑无度,身强勇敢,行无恒毅,动作敏捷,五毒炽盛,喜闻人过,愤怒暴急,这是魔女的遗种也”[23]。岩妖魔女是苯教中的罗刹女,本无性别之分,佛教传入后被披上女性的外衣,代表了女性的形象。后来,随着藏民对藏传佛教的皈依和信仰,佛教塑造的女性思想也成了社会大众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女性被称为“劣生”,被打上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强烈烙印。尽管在密宗金刚乘中,女性被重新提到了一个平等甚至是崇高的位置。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密宗金刚乘仅在小范围内发展较好,没有形成对广大藏族地区的广泛影响[24],结果造成藏族社会对女性本质的认识和理解表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局面,其中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这也导致了妇女在藏族社会地位具有两重性、复杂性和矛盾[25]。藏族女性与周围邻边的亚洲社会相比,没有汉族士大夫们对女性所设定的种种行为规范,过去有着强大的自决权和自由度,有着更大的生活和生存选择权。然而社会和宗教权力却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26]。于是,在社会分工中就逐渐形成了“男逸女劳”这样一个格局。由此可见,男逸女劳是佛教影响下的藏族女性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这种女性观的长期存在,藏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很难提到一个与男子平等的高度,男逸女劳这一习俗就会一直沿袭下去。
(二)藏传佛教信仰影响下的男女比例失衡
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藏族男子乐于做喇嘛,他们认为做喇嘛是光荣的,受人尊崇。“卓尼汉藏回三族杂居,但大多数是藏民,迷信佛教,人民都愿当喇嘛。只有喇嘛才能念书,其衣食皆取于民,不事生产,且为人所崇拜,像汉人的拜崇官吏。”[27]185藏族男子除了做喇嘛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过上令人向往的优裕生活外,而且为僧能养老,“顾番俗虐老,兽心,其子僧者老有所养……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于是宁为不祀之馁鬼,不愿为有子之独夫矣,或此信教者所以多也。”[11]126在藏区,喇嘛是收入丰厚的职业,所得收入也可供奉老人,也正因为这,藏民热衷送子为僧。在玉树,“盖番俗家有二男,则一男为僧,或一男一女,则男子为僧,女子继产,生齿不繁,职此之由。”[11]126拉卜楞,“番俗最信佛教,家有二男,则一男为僧。有男女各一,则男子为僧,女子继产”[6]97。藏传佛教寺院如此吸收大量人口入寺为僧,是边地人口减少的一大主要原因[22],当然也是造成藏区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原因之一,正如俞湘文所言:“藏族社会的性比例本来是平衡的,惟因一部分男子是喇嘛,取消了结婚生育的权利,所以可婚男女的比例是女多于男,失去了平衡”[30]。再加上,藏区受“普通生男不如生女喜”这种生育观念的影响,导致男女人口的比例严重失衡。
民国时期拉卜楞寺所在夏河县,“据县政府报告有34 200余人,其中男13 700余,女20 500余,性比例为150。县治所在居民有2 600人(喇嘛寺除外),其中男1 320余,女1 270余”[31]。此时拉卜楞寺的僧侣数额问题,徐近之认为“有大喇嘛500人,普通喇嘛3 600,习经者亦四五千”。李安宅认为“有3 600名喇嘛,一般少于此数”[16]43。1936年马鹤天至拉卜楞寺,“坐谈半小时,得悉此寺原有喇嘛三四千人,与宁海军冲突时,减至1 700人,近年始渐渐增加,现约2 500余人。”[32]邹志伟认为,“尽管拉卜楞寺附属寺院的僧侣数额无法考证,但我们仍可保守推断民国拉卜楞寺寺院群落的僧侣人数应在3 600之上。”据邹志伟统计,除拉卜楞寺外,夏河县还有黄教寺院58座,它们虽规模不及拉卜楞寺,但喇嘛的数量应不在少数,若按每寺20人计,也在千余人以上[18]155。夏河还有红教喇嘛,据于式玉统计,约有三十余人。综合来看,民国时期夏河县总喇嘛人数在5 000人左右,占夏河男性人口近40%。
青海依然如此,“青海143处之寺院,常年豢养数十万众,不事生产,有闲阶级式的藏僧”[11]126。玉树,“25族男女3万余口,壮丁不过万余,而僧徒至9千余人,几居三分之二”[33]71。虽然民国时期进行的人口调查数据未必精准,但从中我们可看到藏区喇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据估算,此时喇嘛占藏地的男性人口的比例至少在30%以上。
藏族家庭出现这样的人口结构,女子面对家庭重担责无旁贷,妇女从事重体力劳动常态化之后,也就凸显了男逸女劳这一现象。所以说,参与社会经济生产的男女比例失衡,也是“男逸女劳”产生和传承的原因之一。
(三)人口增长缓慢
尽管影响藏区人口增长的原因很多,但直接原因正如文献中所说,“生齿不繁”、“枉死者众”。前者与生育率有关,后者除了与发病率有关,还与相对滞后的医疗条件有关。
1.“生齿不繁”
藏族偏居极边之地,物质与文化相对短缺,尤其是青藏高原,藏民生活极为窘迫,佛教是其精神信仰。然而,信仰范围最为广泛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其教规却禁止僧人婚娶,“喇嘛一生不准讨女人,讨女人是他们唯一的戒条,不管你是活佛或俗僧,一旦讨了女人,共认为有犯清规群起而攻之”[33]73。尽管佛教有此清规戒律,但藏族男子并没有因此望而却步,他们大多还是做了喇嘛[27]185。这样一来,“对藏区的人口繁衍必然带来影响,因为他们不娶妻,不能生育,人口只有减少,不能增加,所以拉卜楞一带那么大的一片土地,都是草原,人口稀少”[34]。象甘南卓尼,“卓尼汉藏回三族杂居,但大多数是藏民,迷信佛教,人民都愿意当喇嘛……因此喇嘛甚多,人口不能繁殖”[35]。正如顾执中所言:“他们男子都当喇嘛,种族的生殖力比较薄弱得多”[24]。藏区1/3以上的男性做了喇嘛,一方面直接导致婚育男子人口直线下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藏区“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物资的匮乏程度,自然也就抑制了低生育率的回升。
藏民“大半为游牧之生活,逐水草而转徙于四方”,这种生活方式常年居无定所,使生育年龄阶段的女性,无法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护理,对生育的影响也是普遍存在的。据“察之,兼农耕生活之区,繁殖力较纯畜牧生活之区,增加数倍,盖以生活安定,资养较优,适于人口繁殖之故也”[17]342。佛教夸大生育的痛苦,就使藏族女性产生了恐惧心理。再加上,藏族传统的观念视女性生育为“污秽”,不允许女性在帐篷里或屋里分娩,而孩子出生时也常由产妇自己处理,接生工具既简单又不清洁,对女性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加之缺医少药,藏区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全国其他地区[11]126。可见,藏民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同样也是造成生妇女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原因导致社会低生育率外,当地流行的疾病、藏族妇女的衣着习惯及其劳动强度等都可能影响到生育率的提高。“藏民生殖率甚低。大批的青年去当喇嘛,自然就造成了怨女旷夫的局面,而即是结婚的夫妇,后裔亦不繁昌,流行的性病及杂交当然是主要原因。还有人说藏妇久不穿裤,所以不易受妊”[4]343。梅贻宝在此所言与现代医学所述一致,女子久不穿裤生殖系统的发病率就大为增加,当然也就直接影响到了女性的受孕率。
总的来看,藏区常期以来一直维持着一个较低的生育率,导致藏区人口不升反降,随着藏族男性出家做喇嘛的人数持续走高,劳动力相对缺乏,使“女劳”这一现象凸显。
2.“枉死者众”
藏区位居气候恶劣的极边之地,本身发病率就相对较高,“藏民普通疾病约有三种,一为皮肤病,二为肠胃病,因食物大都生冷不洁,第三为花柳病。”[10]258这些致病原因和疾病普遍存在,长期威胁着藏民的健康。
多数藏民随水草而游牧,在地广人稀的草原生活,民众对于环境卫生极少关注,而这种习惯的危害在定居之后开始凸显,“拉地商民于卫生俗不注重,臭气熏蒸甚于鲍肆”[9]245。在班禅驻锡拉卜楞寺期间,各地信徒纷至沓来,“次行小巷,沿途湿痕斑斑,皆尿迹也,左右成行,间有大便点缀其间……此间各僧院无一厕所,便溺多在门外……”[16]443在遍地污秽的环境中定居,发病率就会大幅度提高,对藏民的生命健康极为不利。
虽说藏民身体抵抗力较强,但其陋习恶化了本身就极为严酷的生存环境,患病在所难免,枉死者众。尽管也有人意识到“蒙、藏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种牛痘,不预防传染病,劝其清洁,种痘、防疫,有病后,请医吃药,以期人口增加。”[16]72可是,藏医所用“药物大部为草根树皮以及珠玉宝石等,概不炮制,更无分量,研为细末,以茶匙酌给,或搓为小丸,用水吞服……较轻之疾病,多不服药,普通有二法治之,一为熏烟……第二种方法以酥油炒糌粑,用布包扎,熨病人之脑盖,手心,耳门,足心,胸膛,丹田等处,冷后再熨……至小孩患病,概不服药,家炒小麦数升……藏民对于近代医药,均不信仰”[16]445,更甚者“患病不需用医药,只求番僧诵经”[6]94。偶尔即使有“富者请喇嘛治病”,“尝试其功效而求之者”[4]341,还要“视其病情”,最终还是因“此地药品多半陈滓,且亦不全,服之未能生效”[8]78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在藏区,不仅普通民众有病不愿医治,就连班禅大师也如此。九世班禅在内地游历多年,“有汉、藏出使,身体亦健,故疾病甚少。仅携有藏医一人,所谓大夫堪布,并无中西医随行。”[13]188他“自拉休寺归玉树后,因种种感触,心中不快,竟罹病。初仅乳下疼痛,继而腿足浮肿,照宗教例,忌生人往视,仅诵经而不医治,以故病势如何,外人莫知”[36]。
总的来看,藏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惯以及妇女的长期操劳等,使其发病的几率大增,疾病常常威胁着他们的健康。藏区医疗科技相对滞后,再加上信仰的原因,枉死者众。这样一来,也就大大限制了藏区人口的繁衍速度。随着藏族男性出家做喇嘛的人数持续增加,劳动力相对缺乏,也使“女劳”这一现象逐渐显现。
(四)婚育观念
在藏区,“盖以女子为中心至藏族社会,往往视男子为女子之附属品,而婚后至行为,亦一随女子之主动”。女子“不拘女诫”,有着相对较大的自决权和自由度,可与男“逃避山中野合数日回家后始由媒妁言定,婚娶乃成”,还具有更大的生活和生存选择权,“盛行赘婿”,且不论尊卑间有二男。藏族女子体质强健及其在婚姻、家庭中的核心地位,使藏民在生育方面有了异于汉族社会的性别选择。在青海隆务寺,普通生男不如生女喜,因生男多入寺为僧,而生女可赘婿养老也。因而藏民偏爱生女子,他们有了女子,不愿叫她出门,生了男子,千方百计,总叫他脱离家门,免得惹祸招灾。青海盛行赘婿,全是这个原因。这种基于以女性为中心群体的社会文化建构、重体力劳动多倚女性、家庭养老等现实人生需求的生男生女优势选择,是一种观念意识形态的反映,也是一股潜流涌动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藏民不同层次的生存和繁衍需要,然而却降低了男女性别的比例,致使社会经济领域呈现出男逸女劳现象。而且在这一种现象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影响下的女性观的社会实践途径,为女性争得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又进一步通过赘婿、生女养老等多种具体形式使其自身固定成俗。
“男逸女劳”,令人闻之而愕然。它作为藏传佛教影响下的女性观的社会实践途径,不是近代这一历史阶段藏区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传承已久的习俗。其中的“女劳”,虽然没有什么使藏族妇女提到一个与男子平等的高度,但为其争得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体位,也为其争得了较大的自决权和自由度,还为其争得了更大的生活和生存选择权,同时也给藏区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更是一种文明行为。其中的“男逸”,有其历史根源,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地方,但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种文化,体现着社会历史的文明程度。它们的产生和传承不仅受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且受卫生习惯、医疗条件的影响,同时还受地域社会诸如佛教、原始的女性观、婚姻观、生育观等诸多方面人文因素的影响。它们显然也是这些综合因素共同作用在男女社会分工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形象地刻画出藏族男、女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成为窥探历史时期藏族儿女开发西部的镜像,对于研究西部历史、开发西部经济极具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助于适当调整广大女性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充分调动她们的主人翁精神,而且有助于切实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使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同步。
[1]张磊.论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中“女劳男逸”现象及其原因[J].岭南文史,2008(1).
[2]刘正刚.清代西部开发中的藏族女性.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代康区藏族妇女生活探析[J].中国藏学,2005(4).
[3]李之珂.光绪:炉霍屯志略[M].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中国民族史地丛刊之十四:13.
[4]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5册.
[5]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十[M].西藏:中州古籍出版社据1936年大达图书供应社本影印,1990.
[6]张丁阳.拉卜楞设治记[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99册.
[7]张文郁.拉卜楞视察记[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4册.
[8]佚名.青海省各县风土概况调查记[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5册.
[9]李孤帆.西行杂记[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5册.
[10]陈宝全.甘肃的一角[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41册.
[11]周希武.玉树调查记[M].民国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
[12]唐蔦.拉卜楞番民的经济生活[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40册.
[13]马鹤天.青海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4]唐蔦.新年在拉卜楞[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40册:18.
[15]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中国西北文献丛,32册:192.
[16]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17]梅贻宝.拉卜楞之行[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9册.
[18]陈赓雅.西北视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9]黄沛翘.西藏图考·物产类[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98.
[20]曹抡彬,曹抡翰.乾隆.雅州府志:卷12[M].熹庆至光绪递补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322.
[21]周霭联.西藏纪游[M].嘉庆刻本.
[22]张其昀.夏河县志:卷7[M].民国抄本.
[23]萨迦·索南尖赞.王统世系明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43.
[24]陈果,胡冰霜.论藏传佛教对藏族女性性别角色的影响[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25]诺布旺丹,巴桑卓玛.藏传佛教的两种女性观[J].中国藏学,1995(3).
[26]Rita M.Gross.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Delh:Isri Satguru,1995:85.
[27]风玄.卓尼归来[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39册.
[28]张汉光.我国边疆人口问题之提出[J].边政公论,1941,1(3/4):126-132.
[29]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56.
[30]徐近之.西宁松潘间之草地旅行[J].地理学报,1934,1(1).
[31]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2]邹志伟.民国时期拉卜楞寺僧侣制度与甘南藏区环境初探[J].西北人口,2012(2).
[33]潘凌云.拉卜楞寺与喇嘛生活[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40册.
[34]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6册:108.
[35]张德善.青海种族分布概况[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7册:146.
[36]杨希尧.青海风土记[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5册: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