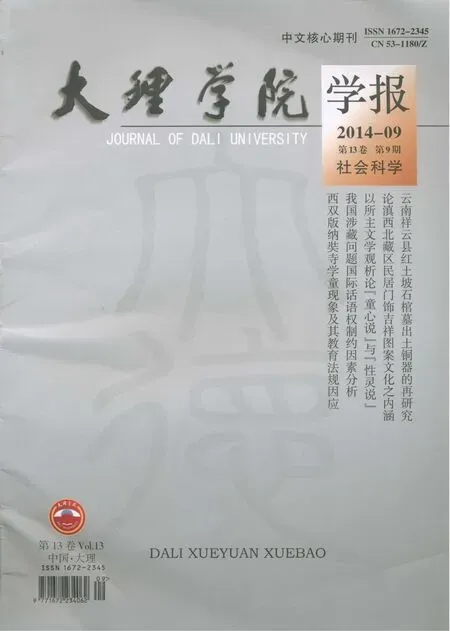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制约因素分析
——以宗教为考察维度
曾晓阳,李冬莲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制约因素分析
——以宗教为考察维度
曾晓阳,李冬莲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后,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但藏传佛教的复兴不仅未能促进涉藏问题的有利解决,反而成为制约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负资产”。将这种战略“负资产”转化为“正能量”的一种可行思路是,重视藏传佛教信众的心理认同,加强藏传佛教统战工作,争取宗教文化认同,占领道德制高点。
涉藏问题;藏传佛教;话语权;制约因素
尽管西藏的发展有目共睹,但这种发展并没有产生普遍的国际认同。在涉藏问题上,西方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在当代涉藏问题上,还没有建构起能够使世人理解和接受的较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
话语权问题归根结底是认同问题,是服人心的问题。西藏分裂集团之所以能在国际上颠倒黑白、扰乱国际视听,乃至占据道德制高点,是因为它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这些力量之所以会对分裂集团产生“认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西方由来已久的“西藏情结”以及藏传佛教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现实影响,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个体宗教心理认同;其二,基于现实政治利益而产生的认同,把涉藏问题作为敲打中国的一张牌〔1〕。本文旨在从宗教心理认同方面对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在厘清藏传佛教的发展现状、分析信众群体与现实影响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具有操作性的策略与建议。
一、藏传佛教发展现状
(一)藏传佛教在藏区发展迅速
从国内来看,与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无神论中国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国正日益成为新兴的“宗教大国”。传统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商品提供者〔2〕。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宗教政策的调整,宗教氛围的宽松,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将西藏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色拉寺、萨迦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西藏共有1 7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僧尼约4.6万人,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萨噶达瓦节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传统活动,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次以上”〔3〕。最能反映我国藏传佛教发展的典型例子是四川甘孜州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1980年,晋美彭措上师在喇荣沟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创办了该道场,当时只有32名学员。时至今日,该道场已发展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修习场所,鼎盛时期信众过万人。“在此出家的人,有名校教授、医生、律师、4A广告公司的部门总监、富二代、海归博士,也有十几岁就远离红尘的少年,还有先后看破红尘,来此寻求人生终极答案的三口之家”〔4〕。
(二)藏传佛教是西方的新兴宗教
从国际上来看,“西藏情结”与西藏热正方兴未艾。对于西方人而言,西藏具有地理与精神上的双重意义。雪域高原壮美神奇的自然景观给人以震撼:雪山高耸巍峨;天空宁静深邃。不仅如此,西方人也视西藏为地球上最后一片精神的净土与人性的绿洲、最后一块杜绝物质侵占精神世界的土地。“数百年来,我们认为西藏人是富有道德感、心地善良而单纯的民族,他们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污染,远离任何邪恶的玷污”〔5〕。被物质文明侵蚀的西方世界,失却了精神家园,他们需要寻找心灵的寄托、灵魂的归宿,希望得到活佛高僧的拯救,而为了获得这一拯救,西方人认为他们责无旁贷地要“拯救”流亡藏人以及藏传佛教。西方人的“拯救梦”与流亡藏人的“藏独梦”不禁暗合。因此,喇嘛、活佛、袈裟等藏传佛教符号在西方成了某种神圣性的文化表征。活佛高僧成为众多西方人顶礼膜拜的对象;香格里拉的幻想充斥着西方的各类媒介、扎根于西方的大众文化,《西藏度亡经》《西藏生死书》《第三只眼》《西藏七年》等,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藏传佛教在西方获得了很大发展,尤其在美国,发展势头最为迅猛。达赖喇嘛在美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他主持的法会,参与者动辄超过二十几万。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忠实信徒遍布各个阶层,其中不乏优秀学子、好莱坞明星、政界要人、专家学者。
二、藏传佛教的信众群体分析
藏传佛教的信众大体可分为三个板块。
(一)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信众
这是中国政治版图内的信众,构成了藏传佛教信众的主体。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后,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佛教的中心,西藏自治区则是该信仰板块的核心。这里信众数量庞大、宗教发展态势积极、宗教经济繁荣。在港澳台地区,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各种信仰更是普遍、持久。
(二)海外华人信众
这部分信众与中国存在着民族、语言、血缘、历史等诸多联系,同时,他们又融入了所在国的社会。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他们能较好地充当藏传佛教传播的互译者:既能把中国佛教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增进所在国民众的中国认知,也能对所在国的对华政策施以某种影响。
海外华人信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流亡藏胞。这个群体构成了“藏独”最坚实的群众基础。1959年,由于“藏独”势力的裹胁、欺骗,少数藏胞追随伪政府进入印度,辗转漂泊异乡。目前,流亡藏胞总数约17万,主要分布于印度(11万多),在尼泊尔、锡金、欧美等地也有少量藏胞散居〔6〕。印度法律规定流亡藏胞不能入印度国籍、不能拥有财产、土地,只能租借。在欧美虽没有这种歧视性限制,但流亡藏胞总体上是社会边缘人群。
(三)外国信众
藏传佛教的外国信众分布于各个阶层,其中不乏社会精英。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总统学者奖章得主格西罗兹。他曾于印度出家,佛学素养深厚。他花了12年时间研究出藏文输入法,将藏文《大藏经》输入电脑,并刻录成光盘免费赠送10余万张。好莱坞明星竞相以皈依活佛为时髦,影星李察·基尔即是典型。他每年都前往印度达兰萨拉(伪政府所在地)求法,也曾闭关静修。他控制的基金会支助了许多境外涉藏机构。美国著名大学中的一些涉藏学术研究机构中,许多重要的犹太裔藏学家具有特殊的“西藏情结”,他们是美国涉藏政策与“藏独”活动的重要智库。他们都曾皈依某著名活佛,学习藏语、研究佛法。这些人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西藏通”,在涉藏问题上往往扮演意见领袖的作用。代表人物有印第安纳大学的Sperling、哥伦比亚大学的Barnett、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戈尔斯坦等。
应该看到,这些人同情或支持“藏独”,更多地是出于个体的宗教心理认知与体验,而非政治因素。厘清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们对症下药、开展有针对性工作的认识前提〔1〕。
三、藏传佛教或已成为我国的战略“负资产”
(一)藏传佛教已成维稳的不确定因素
藏传佛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允许它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健康发展。但是,“藏独”势力却别有用心地借机向国内进行渗透,其黑手已伸向少数寺庙。在其煽动教唆胁迫下,境内少数信徒公然对抗国家法律、破坏社会安定。2009年以来,在藏区发生的僧尼系列自焚事件即是明证。自焚事件是伪政府在政治上黔驴技穷的表现。其意图无非是通过这种“悲剧性表演”,吸引国际舆论关注,迫使中央接受伪政府为接谈对象,从而在事实上为“藏独”制造政治合法性依据。
“藏独”分子除了在少数寺庙进行非法活动外,还处心积虑地利用各种民间佛教组织发展其势力。这类民间组织往往以“学会”“协会”等面目出现。一些接受过境外间谍训练、披着袈裟的“藏独”分子渗透其中。其惯用手法是请某个颇有影响的高僧大德开展法会,吸收善男信女,并从中物色为其效力的人选。这类法会还借助互联网传播,影响甚大。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学会”“协会”已发展为分裂势力的外围组织,而参与法会的一些高僧大德与善男信女往往被他们的宗教外衣所蒙蔽,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这些现象似乎印证了释迦牟尼当年所言:末法时代,毁我佛法者,穿我衣者!
(二)西方炒作“宗教迫害”问题抹黑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国际上大肆炒作所谓的西藏宗教信仰、人权等议题,制造中西之间的结构性认知分歧,强化西方“无神论中国”的制度偏见。这些国际反华势力将涉藏问题进行政治化运作,如在国会通过涉藏法案、各类政要“接见”达赖喇嘛、“藏独”分子在各种国际场合游说公关等等,不一而足。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的炒作,这些反华反共势力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
藏传佛教的西渐,客观上为“藏独”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藏独”势力充分地利用了西方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并将其转化成政治资源,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在其同情者眼中,“藏独”分子这股分裂祖国的政治势力俨然成为因受“宗教迫害”而出走的政治流亡者。
中国是儒佛道与许多民间信仰的中心,拥有众多的信众、繁荣的宗教经济、宽松多元的宗教氛围。然而这一切不仅未能成为增进国家利益的有利因素,反而在国际背负上了沉重的“无神论中国”的骂名。这恰恰反映出我国宗教海外辐射力的不足。客观而言,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涉藏问题确已成为21世纪中国的“软肋”。如何将这种战略“负资产”转化为“正能量”,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建设性力量?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战略选择。
四、加强藏传佛教统战工作,争取宗教文化认同
(一)藏传佛教统战的重要性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的盛况。一方面,中国积极接纳域外宗教并合和共生;另一方面,中国真诚地向域外传播宗教文化。这种频繁的宗教互动,不仅成就了中国自身,也建构了周边世界。“每当中国试图在东西、海陆两个方向的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而传统东亚世界就不仅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朝贡圈、贸易圈,亦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信仰圈”〔7〕。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有经济、政治、军事层面的涵义,也包括文化层面的输出与认同。儒佛道与民间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能够在世界上起到对中国文化传统体系的培土固根的维系作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生态基地及草根植被〔7〕。
“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8〕。通过宗教领域的统战,争取信众的宗教认同,并进而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取话语权,这一“被遗忘的治国术”在今天已日益突显出现实意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藏传佛教这一精神纽带,凝聚海内外信众的民心与力量,改变国际上“无神论中国”的刻板印象,塑造一个更为包容、多元、积极的国际形象。这不仅可在一定程度抵消各种反华反共势力的负面炒作,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应然之意。通过藏传佛教的统战工作,我们可在宗教领域构筑起一条捍卫国家利益的隐性文化防线。
(二)具体策略和建议
1.打造朝觐中心
中国境内拥有许多佛教圣地、圣迹、圣物,如布达拉宫、大昭寺、佛教圣湖与神山、佛指与佛牙舍利子等。要充分利用好这些宝贵资源,将中国打造成藏传佛教的朝觐中心。吸引海内外的信众来中国,通过他们的亲身感受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反击国际舆论对我国宗教状况的无端攻击。
2.“请进来”
境外有不少影响广泛的活佛,在他们周围凝聚了众多虔诚的信众。考虑到这些活佛大都年事已高,应作为今后统战的重点。通过做他们的工作,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我们可创造条件将其“请进来”,与我国境内佛教界开展互动交流,并且通过这些有影响力的活佛将真实的中国人权、宗教情况介绍给国际社会。
流亡印度的藏胞在印度只具有“难民”身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生活窘迫,其中不乏思念故土的藏胞。对于这部分藏胞,我们要积极地创造条件,让他们返回故土,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如果这种形式的统战能形成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效应,则可收到统战的奇效。
3.“走出去”
鼓励中国的高僧大德、活佛“走出去”,与境外的活佛开展对话、交流,与境外的信众建立联系。境内的活佛对宗教国情有长时间的体察,通过他们以身说“法”,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中国佛协、学术界继续大步走出去;继续办好藏文化交流团、世界宗教领袖会议、世界佛教论坛、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佛教界开展的人道主义援助等活动,以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树立“信仰中国”的宗教形象。
4.要做好部分“藏独”分子的宗教统战,实现争取一批、孤立一批、打击一批的目标
“藏独”集团内部并非整齐划一、铁板一块,他们由于教派与地域而存在尖锐的矛盾。大体上可分为“元老派”与“少壮派”。“元老派”是那些早年追随伪政府流亡印度的人,有些已过世,在世的也年事已高。他们对西藏的历史有较多了解,并且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他们中的多数已看清了大势,明白分裂没有出路。对于这批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包括宗教统战在内的各种方法争取过来,壮大爱国力量,削弱“藏独”的群众基础。考虑到这些人已至暮年,故此事宜尽早开展,以争取主动。“藏独”中的“少壮派”往往是那些在海外出生且接受西式教育的新生代。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方式均已西化,加之对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所知甚少,所以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都很激进,是“藏独”的中坚力量。对于这批人,我们要继续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
5.在“西藏情结”与“西藏热”的背景下,做好外国信众的统战工作,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以藏传佛教为精神纽带,改善其对华认知,将其纳入中华文化大认同的框架,这不仅对“藏独”势力的外国同情力量可以釜底抽薪,而且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6.继续努力营造多元宗教共生共荣的氛围,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容纳世界多元信仰的气度与自信
现代社会的英明领导,不仅在于他能迎接现代科学技术、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冲击,而且还在于他能够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能够以一种平常心、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来理解、欣赏宗教。如果只突出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如果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理解不够,对宗教的认识太肤浅,那这个文明要变成世界重大文明中间的一部分,就会有很大困难〔9〕。如果海内外各种宗教信众群体在中国文化这个大熔炉中都能找到精神依归,那么就可对国际上炒作中国人权与宗教问题的势力进行有力的反击。
此外,还应注意,我们在做藏传佛教统战工作时,应偏重于民间路径,改变以往重官方轻民间、重精英轻草根的倾向。实践表明,官办宗教往往下力甚多,收效甚微。
〔1〕曾晓阳,李冬莲.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刍议〔J〕.大理学院学报,2014,13(5):50-53.
〔2〕徐以骅,邹磊.“信仰中国”: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和两岸关系〔J〕.公共外交季刊,2012(9):46-47.
〔3〕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西藏和平解放60年〔EB∕OL〕.(2011-07-11)〔2014-01-23〕.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07∕11∕c_121652459.htm.
〔4〕易立竞.索达吉堪布下山〔J〕.人物周刊,2014(15):32-42.
〔5〕ORVILLE Schell.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M〕.New York:Henry Holt&Company, 2000:226.
〔6〕伍懿雯.移居印度藏胞价值观变化探析:以婚姻家庭、信仰价值观为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11):14-19.
〔7〕卓新平,徐以骅,刘金光,等.对话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及公共外交〔J〕.世界宗教文化,2012(4):33-38.
〔8〕SCOTT 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16.
〔9〕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1):42-43.
(责任编辑 张 成)
Analysis of Restrictive Factor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or the Tibetan Matter: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ZENG Xiaoyang,LI Donglian
(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After Buddhism declining in India,China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world Buddhists.However,the resurgence of Tibetan Buddhism fails to turn into an advantage to solve the Tibetan matter;instead,it is a constraint to discourse power of Tibetan matter as a kind of"negative asset".Transforming this strategic"negative asset"into"positive energy"can be a feasible way to value Buddhist′s psychology identity,reinforce united front work of Tibetan Buddhism,strive for the religious cultural identity,and occupy the high point of moral.
Tibetan matter;Tibetan Buddhism;discourse power;restrictive factors
G647
A
1672-2345(2014)09-0059-05
10.3969∕j.issn.1672-2345.2014.09.013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4XMZ02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13XJC850004)
2014-06-25
2014-07-01
曾晓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涉藏问题、民族地区教育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