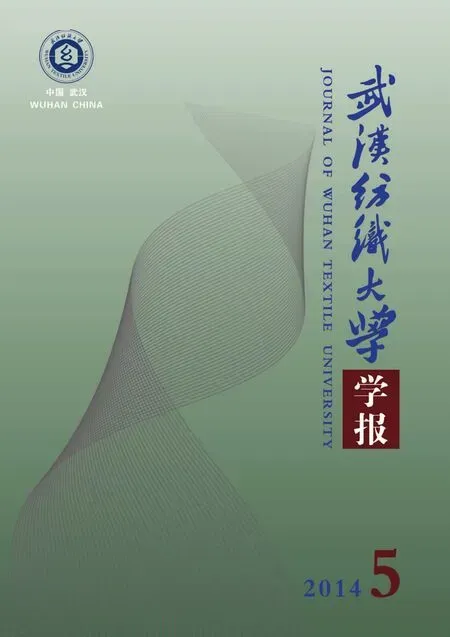古诗英译之描写性翻译研究——以许渊冲英译《无题》为例
陈奇敏
古诗英译之描写性翻译研究——以许渊冲英译《无题》为例
陈奇敏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
本文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观照,以许渊冲的英译唐诗《无题》为研究案例,力图重构译诗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规范,探索古诗英译的描写性研究途径。文章认为,描写性研究途径纳入了对翻译过程中文化层面的考察,重视对翻译的文本、过程及功能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有利于加强古诗英译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古诗英译;描写性研究;翻译规范
在文化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汉语古诗英译更加蓬勃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古诗英译的质量和效果,有效地推介中国文化经典、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近年来学者们展开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在以语言层面为基础的本体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同时,古诗英译的研究视角已经不再囿于传统的文本、语言层面分析,而是倾向于与美学、语言学、文化、哲学等多元视角和多学科的融合(杨秀梅、包通法,2009)。
然而,在古诗英译研究的繁盛外表之下,依然存在着研究角度失衡、研究方法主观、评价标准单薄等局限性,以原文为绝对标准的规定性翻译研究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而关注翻译选择过程、翻译目的和译文接受效果的描写性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箝制了研究的深度和效度。谢天振(2003a:14)认为,“目前中国的描写性翻译研究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令人信服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因为经验之谈难以自成体系”。有鉴于此,本文试以许渊冲英译的一首唐诗为研究样本,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指向层面探索描写性研究范式在古诗英译领域的应用途径,以求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翻译作品、过程和功能,提供一个从双重文化角度去描写分析古诗英译作品的个案,为古诗英译的实践和理论发展提供些微有益的观照。
一、描写性翻译研究:理论基础
(一) 源流及内容
描写性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而此前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侧重于以微观文本为中心、以忠于原作为标准、以价值评价和行为指导为目标的规定性研究。具体而言,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事先设定原文意义的固定不变性,追求文本的微观语言层面的对等,忽视历史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力图寻找一种对应于原作的“超越时空的理想译文和理想的翻译模式”(申连云,2004),并以之作为衡量所有译文质量的标准,从而指导一切翻译实践。
规定性翻译研究对于翻译领域的发展有过一定的贡献,然而翻译的“绝对标准”无法解释形形色色的翻译实例,针对这种局限性,霍姆斯(Holmes)最早提出了“描写性翻译研究”这一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霍姆斯将翻译研究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其中描写翻译研究又可细分为面向产品、面向过程和面向功能的研究。
霍姆斯的翻译理论框架在范畴与方法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现代翻译学的发展与完善,而图里(Toury)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描写翻译学的理论依据和研究内容。图里通过系统考察1930-1945年间希伯来文化背景下的英语及德语小说译本,提出:翻译不仅仅是文字转换的过程,而且是文化交流的过程,翻译总是受制于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因素”,亦即,受到“规范”的制约(Toury, 1995: 54)。同时,图里指出,翻译活动源于目标语文化的需求而非原文本的内在特性,译文跟原文的关系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因而翻译研究应跳出狭隘的文本视角,进入宏观的文化视野,对文本、语境和文化因素的全面描写分析遂成为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必要内容。著名学者蒂默兹科(Tymoczko)认为:“描写性翻译研究是在研究产品、过程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到时代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去研究。”(转引自林克难,2001:43)
(二) 研究方法
描写性研究“运用那些产生于直观对象本身之中的概念来表征直观对象”,它是一种“本质直观的描述分析”,“从变化多样的意识中直觉到其不变的本质结构”(曾利沙,2004)。因此,描写性翻译研究遵循观察、描述、解释、推论的步骤,通过对翻译现象(包括翻译行为和翻译作品)的客观描写,找寻译作特征和译者的决策倾向,并结合具体的翻译语境,重现翻译选择过程,为翻译实例提供合理的解释,进而追溯某一历史文化语境中制约翻译活动的内外因素和本质规律。这些规律汇聚为动态开放的翻译理论,随着历史文化因素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对相关的翻译研究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
图里根据自己的实地研究经验,简要概述了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Toury,1999:70-86)。首先,研究者需确立翻译研究的文本对象,而任何被目标语文化认同为翻译的文本都可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研究者可以把这些翻译文本放置于目标语文化系统内检验其语言特性和可接受性,尤其是关注翻译文本与目标语文化原创文本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研究者需要找出译本所对应的原语文本,分析文本之间的翻译对应关系。如果现成的数据与例证已清晰显示了译文所选用的原语文本,这个确定过程会十分很简单,否则研究者还需做大量的查证工作。然后进入重要的对比分析阶段:研究者对比分析译文和原文,确立文本平行对,识别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发现翻译问题和常规解决方案,进而分析规约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重构翻译规范,并归纳能够阐释各翻译规范变量内在关系的法则。
在此过程中,翻译问题并非根据原文单方面来确定,而是从对比分析中凸显出来。这种“回顾性”(retrospective)研究视角十分必要,即:并不以原文为出发点预先假定翻译问题,而是通过回顾分析译文和原文的异同,确定实际翻译问题。同时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翻译迁移现象,但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判断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对等程度,而是为了识别译文中的特殊选择和规律性差异,以探寻制约翻译活动的翻译规范因素。
二、描写性翻译研究:案例分析
笔者将以许渊冲英译唐诗《无题》为例,描写分析译作的文本特征及译者的翻译策略,并结合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制约因素,解释译作生成形态,同时根据目标读者的反应,客观评价译作质量。
(一) 研究对象的确立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位大家,其作品清丽感人、寄情深微,富有朦胧婉曲之美,而最能代表其风格特色的作品,是他的《无题》诸作。李商隐的《无题》诗一共有十七首,包括古诗、律诗、绝句等不同体裁,其中的一首七言律绝(“相见时难别亦难”),迷离悱恻、深挚沉郁,为唐代抒情诗歌之经典之作,传咏至今。而许渊冲先生曾将此诗译为英文并在多个场合引用,足见译者对此译诗的满意程度,换言之,这首译作可以较好地体现译者的风格和水平。同时,有学者(马红军,2006)曾抽出六首许渊冲的英译古诗,在英美读者群中调查其接受情况,发现英美读者对这首《无题》诗的译文比较认同、接受。因而笔者认为这首译作完全可以进入描写性翻译研究的视野,是研究译者翻译风格和翻译规范的理想对象。
国内的古诗译集大多都提供中英文对照,现将李商隐的原诗和许渊冲的译诗摘录于下:
《无题》 “To One Unnamed”
相见时难别亦难,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东风无力百花残。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
春蚕到死丝方尽, Spring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蜡炬成灰泪始干。 A candle but when burned out has no tears to shed.
晓镜但愁云鬓改, At dawn I’m grieved to think your mirrored hair turns grey;
夜吟应觉月光寒。 At night you would feel cold while I croon by moonlight.
蓬山此去无多路, To the three fairy hills it is not a long way.
青鸟殷勤为探看。 Would the blue birds oft fly to see you on the height?
——(许渊冲,2007:213)
(二) 描写分析的途径
翻译文本是译者翻译目的、策略及倾向的最直接的体现,接下来笔者将对比分析译诗和原诗之异同,观察翻译中的迁移现象及对应现象。这些现象呈现了各种翻译难题,而析出译者解决各种翻译问题时的策略倾向,是溯求译者所遵循的翻译操作规范的有效依据。
1. 翻译问题的发现
译诗为原诗的全译,逐行对应,笔者遂以自然句为对比单位,观察分析原诗与译诗在题目、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各部分行文表达的异同,并据此确定了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列举如下:如何处理含蓄的标题含义?如何处理原诗中的主语及人称缺失现象?如何表现原诗的重复、双关等修辞手段的文学效果?如何处理原诗的隐含逻辑与意合句式?如何处理原诗的关键意象词汇?如何处理原诗中的数字词汇?如何处理原诗中的专有名词?如何选用标点符号?
此外,综观全诗,原诗与译诗在文体方面的关联性也十分引人注目,对于原诗的形式和韵律特征,译者既有所保留又有所变更,因而如何表现原诗的外形特点和押韵特征也是译者必然面对的问题。
2. 翻译策略的描写
(1)建行形式
建行形式是指诗句的外观排列。《无题》原诗一共八行,每行七个字,排列整齐,具有工整对称的外观视象美;而译诗诗句长度明显大于原诗,排列参差不齐,这说明译者在成文构句时考虑到了汉英语言的固有文字结构与句法规则的差异,因而力求译诗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而不强求译诗和原诗的外形相似性。但在此基础上,译者又努力加强原诗和译诗的外形特征联系,如:译者以相同的行数对应原作,采用左对齐的方式排列诗行,且以每行六音步为固定韵律,从而间接表现原作排列整齐、字数固定的形式特征,显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诗外观特征的关注。
(2)韵律节奏
《无题》原诗于偶数行押韵,且一韵到底、严谨整齐,各联诗句平仄相向、抑扬顿挫,极富回环叠荡的音乐节奏感,那么译者是如何传达原诗在韵律节奏上的美感呢?作为韵体译诗的倡导者,许渊冲在唐诗英译中非常注重音韵之美的重现。为了表现原诗音韵整齐的文体效果,许渊冲的译诗也力求句末押韵,但他不拘求于对原诗押韵方式的模仿,而是充分巧妙地利用英诗的多种韵式和语音修辞手段,尽可能达到音韵优美的效果。
首先,英语格律诗虽然也讲究押韵,但由于构词方式的限制,很少能够一韵到底,其尾韵模式也随之灵活多变。英诗常见的韵法包括:aabb联韵、abcb隔行韵、abab交叉韵、abba交错韵、aaaa同韵和aaba韵,而许渊冲的《无题》即选用了交叉韵的模式,表现为ababcdcd的隔行尾音押韵。此外,译诗还运用了头韵(如:第二句“wind”和“weak”;)、元韵(如:首句中“hard”和“part”)和辅音韵(如:首句中“meet”和“part”)等语音修辞方法,读来音律和谐,节奏鲜明,间接地反映了原作的韵律格。
其次,许渊冲选用了“抑扬格”音律来安排译诗的轻重音节奏,这既符合英文表达的自然规律(虚词在前,实词在后),又类似于唐诗原文的诵读节拍(唐诗中每个双音步的第二个音和单音步都是音节的节奏点)。同时译者选用了近似的音步数目(六音步)来对应原诗的音节数目(七言),协调了重音计时语言和音节计时语言在歌诵读节拍上的差异。
(3)标题的改译
对比此诗的中英文标题,可以发现原诗和译诗标题存在语义范围偏差,字面并不对应。中国古诗经常以“无题”为名,既可指诗歌的某些所指(如倾诉对象、作品意图)不便明言,又可指不待命题的感遇即兴之作。这种题目符合含蓄朦胧的中诗传统,也能激起中国读者的审美联想,因而李商隐用“无题”为题,隐晦表达相思的情怀。而英译标题“To One Unnamed” 意为诗歌是为某个不便提及姓名的人而作,无疑缩小了诗歌的描写范围,尽管英语读者无法知道诗歌的具体言说对象,但比较容易揣测出诗歌的爱情主题。可以看出,译者采用了一种兼顾原题风格和读者趣味的折中做法,对题目的表述方式稍作改动,既保留了一些原诗题的含蓄意味,又缩小了原诗题的意义范围,靠近英诗表述清晰的总体倾向。
(4)主语及人称的添加
原诗虽为一首寄托相思的情诗,但从头至尾都未交代人称主语,造就了一种形式简约、语义含蓄的美感,同时增加了读者理解及翻译的难度和灵活性。对此,译者运用了添加的翻译技巧,使译文语法成分齐备,晓畅易懂,其中颈联二句的翻译尤为引人注目。颈联两句原文没有明言“镜、愁、吟、觉”等动作的主体为谁,带来了理解的多义性。一般的解读为:女方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渐改、朱颜憔悴而感伤,于是揣想男方夜吟遣怀时,觉得月光寒冷、心境凄清。但许渊冲的译诗别出心裁,其主语和人称的添加带来独特的诗意阐释——(我)想到(你)早晨对镜梳妆发现头发变白,(我)不禁忧伤难耐;(你)设想(我)晚上在月下吟诗看书,(你)也会感到寒冷凄凉。译者认为这样的译文更能表现两位恋人心心相印的深情,能更好地衬托出诗歌的主题和意境(许渊冲,2003)。
(5)修辞的转换
原诗中第三句“丝”与“思”字谐音双关,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清晰的画面:思念仿如春蚕吐丝、无尽无休,传达出刻骨铭心、生死不渝的相思之情。而许渊冲翻译为“Spring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增补了动词“spin”及状语“from lovesick heart”,将原文中的双关词“丝”一分为二,用英语表述为蚕丝的“丝(silk)”和思念的“思(love-sick)”。囿于英汉语言的固有差异,尽管译者没有再现原文的双关手法,但寻求了巧妙的变通手段,其拟人和头韵方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诗歌的修辞效果。
(6)衔接方式的多重性
中国古诗以含蓄朦胧为美学特征,往往跳过字面的衔接手,采取意合的表达方式,以突显意象鲜明和体验。而英语的诗学传统注重结构的完整、词句的精当、意义的张显和逻辑的明晰,尽管英美现代诗也经常打破语法常规,但未能彻底改变英美读者的传统诗学理念和审美模式。而许渊冲在翻译古诗时,兼顾了两种诗学传统的特征,灵活地运用了形合与意合的衔接方式,力求译诗易于被英语读者理解接受,同时又能表现中国古诗的部分创作特点。
首先,在处理两句之间的表达关系时,译者不用任何连词,主要运用意合手段,使译诗具有中国古诗的意合特征,表现内在连贯。而在表达单句之内的逻辑关系时,译者常用形合的手段清晰阐述。例如,原诗第二句将两个意象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省略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陈述,那么,究竟是“东风无力”伴随着“百花残”,还是“东风无力”致使“百花残”,需由读者自己解读。许渊冲则采用了英文中逻辑明晰的“too…to”结构,指明了“东风无力”和“百花残”的因果关系,原诗意象的多向性罗列随即转换为单向的动态过程。
(7)意象的翻译
诗歌通过呈现具体的意象传达象征意义,激发读者的情感体验。很多意象词由于历代诗人的反复使用而具有固定的联想意义,反映了一定的文化特殊性。《无题》原诗中包含很多鲜明的意象词汇,如用“东风”、“百花”代表盎然的春意,用“蜡炬”、“春蚕”象征无怨无悔的恋人。除了“百花”之外,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其余的三个意象词汇在英语环境中都没有类似的联想意义,但译者对这几个富含中国文化内涵的意象词汇都采取了直译的方式,其跨文化交流的愿望十分明显。
(8)典故的翻译
尾联中的“蓬山”和“青鸟”分别为中国文化色彩浓厚的地理名称和动物名称,都是典故性的专有名词。“蓬山”,本来是指传说中的海上蓬莱仙山,这里借指恋人住处,而“青鸟”是神话中王母娘娘的神鸟信使,诗人借此含蓄简洁地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之情。对这两个典故性的专有名词,许渊冲没有使用常见的音译方法,而是选择了带有实在意义的词汇“three fairy hills”和“blue-bird”。同时,为了进一步向英语读者揭示以上两词的文化内涵,译者还在译诗末尾附上了简短的说明:“The poet writes this poem for his unnamed lover compared to a fairy living in the three mountains on the sea where only the mythical blue birds could bring messages.”意译加注的方式比较成功地传达了词汇的指称意义,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方式。
三、 描写性翻译研究:翻译规范的重构
《无题》译诗所呈现的翻译问题虽然性质繁杂、纷乱无序,却都可以反映译者在形美、音美、意美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通过描写译者在此过程中解决问题的策略倾向,我们可以大致析出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
首先,译诗较好地表现了原作的诗学外貌特征。译诗为英汉对照全译,与原诗结构一致,外形相似,同时译者借鉴利用英语格律诗的体裁,间接却鲜明地表现了唐诗格律严整、节奏匀称、音韵优美的古典诗歌特征。其次,在表述诗歌的意象和含义方面,译者兼顾了译诗的可读性和跨文化交流的效果。译者通过意译、添词、加注、修辞转换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作的含蓄内敛风格,使译者更易于被目标读者理解接受。在此基础上,译者又尽量直接表现原诗中的重点意象和意合句式,以传达唐诗的意美表达方式。
总之,译者的总体翻译倾向更贴近源语文化规范,但在具体操作策略中又兼顾了译语文化规范,在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受到了两种文化规范的制约作用。在表现唐诗的基本形式特质、整体意义和文化意象方面,许渊冲更靠近源语文化规范,体现出“充分性”的整体翻译倾向;在此前提之下,许渊冲也充分认识到目标语文化规范对读者的巨大影响力,尽量结合目标语的语言特点、减轻译诗的陌生化程度,在句式、衔接、标题、选词、语法等有助于主题理解的细节方面尽量遵从目标语行文规范,选用可接受性较强的译文表达。
译者尽量在古诗翻译中寻求两种语言和文化在音美、意美、形美三方面的统一,他认为,“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统一,还应该是两种文化的统一”(许渊冲,2003:73),这个观点正是对其英译唐诗所遵循的初始规范的恰当注解。而相关调查显示,对于许渊冲的这首英译唐诗,多数英语读者认为其音韵效果和整体质量属于中等偏上(马红军,2006),可见,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具有较好的文化交流效果。
四、结语
通过描写分析英译《无题》的翻译策略和重构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笔者试图跳出狭隘的以原文为中心的价值评判模式,结合译作产生的文化背景因素,更好地解释译作的表现形态与社会功能。笔者认为,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是在特殊时代背景、文化交流现状、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主流诗学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唐诗英译理念,译者藉此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目的。
图里所倡导的描写性研究途径重视对翻译的文本、过程及功能的全面考察,促使古诗英译研究进入了具体的历史文化空间,为古诗英译研究拓展了新的思路,有利于加强古诗英译领域的研究深度和效度。然而,图里的研究源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目的,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后来者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尚需对其理论的实际应用方式加以调整和完善。例如,图里从希伯来翻译文学的实情出发,认为本质上翻译是由目标语文化发起的活动,强调目标语文学系统对翻译的巨大影响,但当今世界的翻译活动类型多样、目的各异,由源语文化发起的翻译活动屡见不鲜,源语文化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实力、原作文学地位和译者个人经历等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翻译研究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总之,描写性翻译研究路径为古诗英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观照,但研究者应注意扬长避短,使相关的翻译研究理论与方法切合具体的研究情景,兼顾翻译研究中科学性和人文性、文本性和文化性。
[1] 丛滋杭.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2] 林克难.翻译研究: 从规范走向描写[J].中国翻译,2001,( 6):43-45.
[3] 马红军. 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4] 申连云,翻译单位的描写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381-386
[5] 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3.
[6] 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7] 许渊冲(译). 唐诗三百首[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8] 杨秀梅,包通法.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历史与现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12):57-60.
[9] 曾利沙. 论文本的缺省性、增生性与阐释性——兼论描写翻译学理论研究方法论[J]. 外语学刊,2004,(5):77-112.
[10]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1995.
[11] Toury, G. A Handful of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and “Norms” [A]. C.Schaffner (ed.)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9.
A Descrip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Taking Xu Yuanchong’s Translation of the Tang poem “” as an example
CHEN Q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00, China)
Enlightened by Toury’s theory on translational norms, this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n the poem “Wuti” 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 trying to reconstruct the strategies and norms embedded in the translation, hence exploring the descriptive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t is concluded that by integrating cultural aspects to the translation study and evaluating the text, process and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re objectively, the descriptive approach could deepen and validate the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in a good sens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Descriptive Study; Translational Norms
陈奇敏(1975-),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3g272).
H315.9
A
2095-414X(2014)05-005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