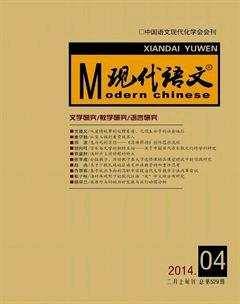从曹七巧看张爱玲的女性叙述
摘 要:张爱玲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完成了她对女性的书写。在作品《金锁记》中确立了曹七巧的疯女形象。通过曹七巧对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的反叛,张爱玲强调了女性被男性扭曲的心路历程。通过压抑处境的书写,张爱玲叙述了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下所承载的性别、经济、人格上的剥削和压制。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家长身份在男性家长缺席的情况下得到了确认,张爱玲把处于从属压抑位置上的女性纳入叙述主体。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压抑 宗法父权 疯女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生活在细碎的阴影与缝隙中,她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变得越来越疏离。张爱玲在上海艳极一时,而后一路不断跌落,最后只剩下苍白的碎片。但是,张爱玲的生命并未因此而终结,她通过作品写出了“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她以敏锐的笔触直面人性的卑陋和扭曲,深入描绘了那个时代在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命运的凄怆和悲凉,揭示了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和戕害。张爱玲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代表,捕捉了女性的复杂心理。并对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人物进行了潜意识的挖掘和心理分析,展示了在宗法父权体制下女性被剥削和被压抑的历史,完成了张爱玲对女性压抑的阐述。在权力与欲望的角逐中,曹七巧的身体和精神人格发生了分裂,走入了疯狂。这表现在她极力去破坏自己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正常而幸福的生活,她视儿子为“驻在敌国的代表”,对女儿则扮演了一位复仇的母亲。这反叛了传统社会中的贤妻良母形象,其中隐藏着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曹七巧的疯女形象也是一种对父亲权威的模仿,这突出表现在她的女性家长身份上。张爱玲让曹七巧处于从属压抑的位置上,同时又赋予某种程度上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把压抑中的弱势女性纳入叙述主体,在此复杂矛盾的内涵中隐含着潜在的颠覆能力,张爱玲借此主体的置换对宗法父权提出了反抗。张爱玲就是通过对具有典范意义的曹七巧的疯女形象的确立完成了她独特的女性叙述。以下文章就此内容作了探析。
一、压抑处境的独特书写
张爱玲,一生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她以女性的角度直接书写女性,完成了其独特的女性叙述方式。“在生活和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当一位妇女着手写一部小说时,她始终希望去改变那已经确立的价值观念”。张爱玲的书写就是这样,她通过《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疯女形象的确立,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书写了父权体制下的女性,即写了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下的压抑处境,并以此从反面控诉了宗法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这种书写方式的内容和角度就不同于五四之后的女作家的书写。冰心是歌颂母爱的哲学,白薇是控诉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丁玲是以中性的叛逆话语大胆地暴露社会问题,张爱玲则以“放大的女性化进行叛逆书写,一反革命型女性的虚构神话,使转型时代中受扭曲,受凌辱和毁灭的女性真相获得了具体化的历史面貌”。张爱玲通过曹七巧的疯女形象的确立写出了女人过去沉重的负荷,写出了女人在现实中的种种压抑与痛楚,写出了以曹七巧为代表的被压抑和被沉默的女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叙述隐隐传出了父权文化结构下遗落的女性呼声,深入挖掘了女性阴暗的深层潜意识。《金锁记》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是张爱玲书写模式中的一个典型的女性叙述,具有女性典范意义。作品以曹七巧为叙述中心,并确立了她的疯女形象。曹七巧出身低贱,是“麻油店的活招牌”,嫁给了身患骨痨的姜二爷并因此在大家庭中倍受排挤和欺侮,这种幻灭的婚姻给曹七巧带上了“黄金的枷”,并使她变得扭曲,阴沉而千疮百孔。金枷压制了情爱,其结果是曹七巧对小叔姜季泽的畸形的爱欲被泯灭之后,她成了一个疯狂报复的女人。逝去的东西可以残忍或温柔的复活,带给我们幻觉中的痛苦和幸福。别人毁了曹七巧的一生,她又毁了自己儿女的幸福。曹七巧就像一头困兽,一生都在权力和欲望中挣扎。“三十年来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就这样《金锁记》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这是一段无回报的爱和不幸的婚姻岁月。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一文中谈到,女性小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女性与她们的小说,一是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我们在谈到张爱玲的写作时,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即女性和她们的写作,在此就是张爱玲和她的写作。通过阅读我们看到张爱玲是一个女性压抑的阐述者。在以《金锁记》为代表的女性文本中,其女性人物往往在宗法父权中被边缘化为他者,即“第二性”。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概念,以女性主义视角而言,男性是主体,是绝对完整体,而女性是他者,是处于非本质论的现实中。在父权文化社会中,女性被界定为“他者”,为男性所观照,女性在“天”“乾”“君”“父”等宗法象征主体下,被定义为附属于男性的他者概念。那些长久以来被压抑在历史和转型时代中的女性问题,在张爱玲的笔下展开了她们巨大的内在压抑领域: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大部分女性群体的非正统身份,在此以一种畸形、歇斯底里、病态等征候表达了她们的被歧视和被压抑。因为姜二爷的无能,曹七巧在姜家没有任何尊严和地位,连家里下人也对她说三道四。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对姜季泽的一点爱恋也被限制在压抑的欲望中,这种女性主题的书写,表现了张爱玲对于女性遭受贬压的一种抗衡。在此,张爱玲把有关女性的卑微沉默都力图写成承载着文化层面的愤怒的荒凉。所以说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压抑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压抑不仅是与各种生活能量相对立的消极力量。同时,压抑还寄生在各种生活能量之上”。女性主义认为,压抑有压迫和抑制两个层次,主要强调心理和性欲层次的压抑,女性压抑是父权文化社会对女性身体、人格、精神和性欲的普遍监控下的产物。曹七巧的疯狂就是在此层面之上诠释了女性断裂的历史镜像。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害怕用一生换来的财产,再次落入男人或其他人的手中。曹七巧对长安的那一段告白,最能表达她对于男性的怀疑和对金钱的信仰:
一阵风过,窗帘上的绒球与绒球之间露出白色的寒天,屋子里暖热的黑暗给打上了一排小洞。烟灯的火焰往下一挫,七巧脸上的影子仿佛更深了一层。她突然坐起身来低声到: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的。endprint
姜季泽虽是七巧最后一个怀有幻想的男人,但这爱慕情意也被姜季泽破坏。自揭穿姜季泽的虚情假意和谋财意图之后,七巧就再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男人。上文中曹七巧脸上的黑影,暗中写出了她内心的黑影,把她害怕丧失钱财的恐惧心理勾勒了出来。此内心的黑影揭示出了曹七巧所遭受的压抑处境和内心的恐惧。曹七巧在道德上的破产和人性上的丧失殆尽代表了女性人物的悲剧,这种悲剧包括她们的言行,在表面上是为钱财而疯狂,其实却含藏着文化上的性别政治以及人格遭受扭曲的心理因素。因此对曹七巧的疯狂等类似的描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不安全感来自宗法父权在经济、人格和性别上的多重压制和剥削,而不只是钱财上的问题。宗法父权体制是男性通过他们所建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组织,对女性进行宰割的一种体系。父权的权力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机制,也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约束能力,即道德观对女性精神的迫害。在父权文化中,男性是父权宰制社会的基本原则,女性被放逐于社会结构的底层和历史的边缘。宗法父权长久对女性的歧视和压抑,构成了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的病变。女人在父权社会里,其作用被充当成交易的媒介,在自身作用剥夺之后,女人最终变成贡品被牺牲掉。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就是在这种被充当为交易媒介的历史中,被传统社会压榨成血淋淋的一堆碎尸,彻底而几乎疯狂:“她睁着眼直钩钩地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这里蝴蝶标本在寓意上成为了曹七巧压抑性质的女性图像。在《半生缘》中还用“红粉骷髅”意象描绘了曼璐,恐怖凄冷。在《茉莉香片》中有“屏风白鸟”的意象写了冯碧落,“年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这些图像暗示了儒家宗法对女性的不同形式的道德迫害。表面上,这类女性在经济的金锁下度过其悲惨的一生,实际上,在此经济层面的背后可以窥探到父权对女性在经济与人格上的控制。这就是张爱玲独特的女性书写,书写了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下所承载的性别、经济和人格上的剥削压制以及她们的压抑处境。
二、贤妻良母形象的反叛
贝克尔在《拒斥死亡》中提到,母亲对于儿童来说代表了两件事情。一是说母亲是快感和满足的纯粹来源,是可信赖的保护性力量,她必然表现为美、善、胜利和力量的女神。一是说母亲代表着可靠的生物性依赖对象,儿童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呵护。传统社会中的母亲形象也是按照这样的图式存在的,但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对自身家产、权力和地位的维护,直接导致了她对于他人的伤害和压迫。在权力与欲望的角逐中,曹七巧扼杀了爱与天伦,完全反叛了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的形象。没有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角色去让她的儿女感到可“信赖”,可“依赖”,更没有受到母亲意义上的“呵护”。相反的是,她的儿女在爱的不断缺失中疼痛的成长,这突出表现在她和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紧张复杂的关系上。曹七巧畸形的婚姻,内心的空虚无助,使她对人生感到绝望,精神和肉体发生了裂变,形成了她的双重人格特征及其多重身份。如《金锁记》文中所描绘的:
起坐间的帘子撤下送去洗濯了。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的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天是无底洞的深青色。
具有花旦气息的曹七巧渗透在“戏剧化的脸谱”中,“一搭黑,一搭白”的夜空在此揭示了曹七巧双重人格的象征写照。在曹七巧彻底的疯狂中,聚集了各种压抑能量,在荒野中呈现了一幅女性精神崩溃的历史面貌。这种双重人格的分裂集中表现在曹七巧的多重身份及其对自身角色的反叛中。曹七巧既是有名无实的妻子,又是有名无实的母亲。在妻子的角色上,她表现出不忠于丈夫,甚至公开谩骂唾弃自己的丈夫。在母亲的角色上,她把儿子导向堕落糜烂,视其为“驻在敌国的代表”,更加破坏了女儿的恋爱和婚姻生活。曹七巧在此双重人格的作祟下,最终导致她在攻击他人和自我的宣泄中,走入自己的心理地狱,躯体转化为疯狂的代替物。
1.与儿子的关系——“驻在敌国的代表”
在《金锁记》中,长白的形象隐含着姜季泽和姜二爷的影子,他兼有父亲和叔叔的某些负面特质。而曹七巧对待长白的方式,其实也和她对待丈夫和姜季泽的方式有些共通的地方,这似乎是曹七巧借此对姜季泽和残废的丈夫的一种报复。一方面,她把长白留在家里抽鸦片,但长白到了窑子里“玩得比大爷三爷精明,强爷胜祖”。另一方面,长白又是她“驻在敌国的代表”。一生卧病在床的丈夫和姜季泽的嫖赌成性与窝囊无能,照理曹七巧会把独子调养成人中麒麟,事实却相反。这现象反映出曹七巧内在复杂矛盾的心理。长白在文中的身份由始至终都是曹七巧的傀儡,毫无主体意识,他的堕落都在曹七巧的教导、诱惑和安排下完成。作为母亲的曹七巧没有把他带离堕落的道路,反而把她生命里两个重要男人的命运交织在长白身上,重复着两种她最痛恨的现实:在家之内把长白变成残废丈夫的替身,在家之外把长白变成另一个姜季泽。长白作为宗法父权的承传者的悲剧无疑正是曹七巧命运的一种讽刺。曹七巧在长白的毁灭中看到了丈夫和玩弄她情感的姜季泽的毁灭。不同的是,她在长白的堕落中始终是个主宰者,不象当年嫁给姜二爷和年轻时迷恋姜季泽时候的孤独无助。长白的堕落毁灭,确立了曹七巧和儿子,以及曹七巧和她生命中两个男人的关系。长白在曹七巧的授意下走向了毁灭,这种在精神上“谋杀亲儿”的现象背后,可以看到曹七巧的绝望和病态。借由这种毁灭的家长宰割仪式,曹七巧成功地把女儿留在身边,儿子不被儿媳霸占,女儿也不被女婿带走。其中,曹七巧对女儿长安的压制和摆弄也是值得注意和分析的。
2.与女儿的关系——复仇的母亲
对于儿媳芝寿,曹七巧扮演着复仇的婆婆,对于女儿长安,她又扮演着一个病态的母亲角色。曹七巧对儿媳的疯狂言行,表述着她对欲望的一种诠释,对女儿的言行则可以探察到她对爱情婚姻的恐惧、反感和罪恶感。曹七巧把女儿视为他者,深恐另一个他者掉进父权婚姻的陷阱之中。曹七巧设宴宴请童世舫,她有“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在席间,她轻描淡写地说到长安“她再抽两筒就下来”,因而长安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最后还是由曹七巧加上了“不堪的尾巴”。从曹七巧对长安的言行而言,她其实是以“受害者”或“过来者”的身份去对待长安的婚嫁问题,而不仅仅是扮演了一个逼害女儿和害怕失去财产的母亲而已。在母亲的身份上,由于遭到长安的抗衡,曹七巧的言行更被激化为疯狂的他者,由此从疯狂的婆婆转为疯狂的母亲。这也缘于曹七巧在情感与人生信仰上的混乱。一方面她要把女儿留在身边,甚至在歇斯底里的言语中多次表露她阻止长安出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长安,为长安着想,以免长安重蹈当年她所遭受的折磨。另一方面,曹七巧通过扮演男性家长身份的压迫角色,去达到她想要阻止长安出嫁的目的,而不惜千方百计地对长安进行各种阻挠折磨的行径。曹七巧一方面无情的刺伤、打击着身边的亲人,一方面又倍感愧疚,自哀自怜。“她知道女儿、儿子恨毒了她,她婆家人也恨她,她娘家人也恨她……曹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小洋枕头,凑上脸去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擦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地自己干了”。曹七巧的这些言行我们看到她在精神人格双重性之外的另一种精神面貌:在友人之间,她的人格往往丧失理性;在独处时,她又无法面对自己,甚至否定自己。当童世舫走后,爱情(男性)的幻想和亲情(母爱)的慈爱,都在长安身上正式幻灭。曹七巧在对身旁亲人的报复和惩罚中,正好也暴露了她被禁忌、被剥削的人生历程。endprint
作为疯狂的母亲,曹七巧的病态表现在把女儿的终身幸福视为一种罪恶,使尽手段破坏长安和童世舫的恋爱。她不时地警告自己“我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可不能糊里糊涂地断送了她的终身,我自己可是吃过媒人苦的”。在婚姻的选择上曹七巧无形中强逼着长安回到她以前所走过的道路:不要被男人所欺骗。因为在曹七巧的眼里,男人和姜季泽一样,绝非善类。在接下来,长安终于在曹七巧的强逼欺哄下一步步地重写着上一代留下的悲剧。然而,从长安愿意牺牲终身幸福的抉择去迎合母亲的行为来看,她又深爱母亲而又怜悯母亲,不仅仅是她性格上的软弱使之。所以说长安是姜家黑暗世界里的善者,一方面为了安抚母亲的无常冷酷;另一方面,她更为童世舫着想,不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因她母女的关系而毁了一生。“她知道她母亲会使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长安明知道要后悔,最后还是把戒指退给了童世舫。在这行为上,长安虽然把自己定位在母亲的法则中,但是由于母亲的法则是遵从父权秩序的,因此母女两人在无形中还是落入了父权体制中,并以宗法父权对于她们二人的要求去对待对方,这使得母女冲突的悲剧,在曹七巧的人格精神分裂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因此《金锁记》中母女两人的对话,使她们各自在彼此的认同对象中,重写了女性作为他者的事实,她们母女两人在彼此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长安的矛盾与哀伤缘于母亲的情感创伤,同时它源自母亲所属的宗法制度的宰割。在母女冲突上,曹七巧并没有视自己为人母亲,而长安也不敢以母亲女儿的身份自居,最终导致了长安婚姻上更为尖锐而深刻的悲剧。曹七巧把长安留在身边,其实也像她把长白留在烟榻上的行为一样,始终无法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去体会女儿的矛盾和创伤,长安的一生幸福只能像“腐烂的水果一样坠落”,她的牺牲只能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也就是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通过剥夺女儿的幸福,造成自身作为母亲的离位。曹七巧混乱了她自己、姜季泽、童世舫和长安四角之间的位置。曹七巧沉浸在疯狂的世界里,把女儿的欲望、身体和精神充当成压抑的媒介,充当了自我净化的工具,完成了另一个替身的再造。
在曹七巧与其儿子和女儿紧张、复杂关系中具体体现了她的疯女形象。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疯女形象被视为一种微妙的女性文学策略,是女性自我的化身或复写,这里显示了含有作家的焦虑和疯狂的意涵。在父权文化的性别角色规范中,女性的疯狂,实际上表现了女性在生理、性别、或文化方面的阉割意涵,隐含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暗涌,成为抗衡宗法父权的一种颠覆书写。《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疯女形象也是具有典范和开放意义的,她既是宗法父权对于女性压抑处境的具体反映,也是她双重人格及其人格分裂中多重身份角色的一种集中体现。张爱玲以曹七巧为代表透彻而清晰地描绘了边陲女性的真实内在的精神面貌,强调了女性身体与精神人格在宗法社会文化中所承受的重量,并以女性荒凉的面貌去叙写了女性被男性扭曲的心路历程,隐含了儒家宗法社会中广大女性的人生悲剧。
三、家长身份的女性主体
在女性主义看来,性别是一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范畴,是社会现实被组织、被表明和被检验的方式。性别首先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人们对性别有着不同的理解;性别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男女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性别角色归根到底是由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性别还是一个政治范畴,它包括权力机关,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一个缩影;性别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有不同的塑造和表现。女性用性别写作就是用社会时代和历史所赋予她的身体、价值观和情感体验来写作。她们应当写自己“被体验着”的生活。性别寓意,性别体验不同,作品的内涵和形式就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写自己就是要写自己的性别,反抗父权体制下的压迫,以特有的性别感受创造出新的女性文化”。张爱玲就是通过曹七巧书写了特别的女性文化,如前文所说的不同于五四之后的女作家对于女性的书写。以曹七巧为代表,张爱玲文本承载着女性在现实中所承受的历史和文化体验,并在此基础上把压抑中的弱势女性纳入叙述的主体。其女性人物处于从属的位置上,却又同时被赋予某种程度上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曹七巧就是这样的例子,表现在她对儿子和女儿人生幸福的宰割,如上文所述,在疯狂中确立了她的女性家长身份。类似的还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小艾》中的席老太太。她们之中虽然不完全脱离从属色彩,但其一家之长的特殊身份却提供了某种微妙的复杂的主体身份。一方面,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家长虽为一家之主,但是她们的主体性在文化意义上却并非决然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她们在文化中虽然能够以女性家长身份去表现主体,但在实际上却不能完全脱离宗法父权体制的象征秩序。原因在于女性家长的主体身份是出自她们在家庭中“资力”基础。一如《红楼梦》中的贾母。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家长是在男性家长缺席的情况下,才得以占有主体地位和权威性,而这种主体性最后将被男性(儿子)所取回,无法在文化意义上直接承续给下一代的女性。所以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主体地位是建立在其丈夫有身体残障和长白和长安子嗣传承的基础上的,这些也就是曹七巧具有女性家长身份的“资力”基础。她的女性家长身份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宗法父权的象征秩序。
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人物身上具有从属与主体兼备的矛盾内涵,这在其中隐含着某种颠覆能力,文本中男性家长的缺席和死亡,意味着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除了《金锁记》中姜二爷的残障,类似的还有《花凋》中“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郑先生,《留情》里“整个地像个婴孩,小鼻子,小眼睛,不能决定自己是不是应当要哭,就像个打了包的婴孩”的米尧晶,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父亲也缺席。这些男性家长图像的残缺破碎,甚至病态肌理,就使他们在传统社会中丧失了传统家长原有的地位,从故事的开始到结束,都隐逸在文本之外,成为文本中的缺席者和沉默者,完全丧失说话的地位,丧失了传统宗法父权社会下的权威和精神人格。在男性家长缺席下,女性家长的涌现构成了以女性叙述为主体的文本。张爱玲借助这种女性家长的确立,让女性在她笔下能有更大的空间去表现涌自压抑底层的主体意识。但是这种主体地位是在男性传统权威、身份、或地位被陈述者否定之后才得以确立的,所以说这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的主体意义。总之,张爱玲这种借主体置换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宗法父权秩序提出了反抗,因此,女性家长的主体身份具有了颠覆意义。张爱玲在文本中对于男女两性家长关系的书写,也是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有关女性主体意识和男性主体身份的关系的思考。在此基础上,男女两性之间不再单纯地遵守主从尊卑的秩序,而是男女两性主体并位的关系。这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主体现象:女性不再被简化为“父亲的女儿”,而是有着“我是我自己”的一种宣示。女性家长对于确立“我”和“自己”的关系,事实上正是确立了“主体”和“自我”的关系以及有关女性身份和她们主体意识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3]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4][美]厄内斯特·贝克尔著,林和生译.拒斥死亡[M].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肖巍.为谁 用什么 以什么话语写作——也谈女性写作[J].粤海风,2000,(6).
[6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钱理群.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姜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8300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