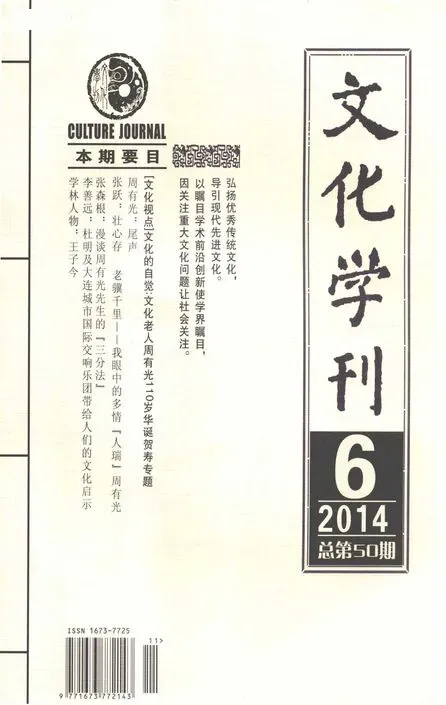任璧莲小说中的通婚与种族身份建构
李红燕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当今美国是个移民大国,异族通婚日益增加,然而,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观念严重的国家,反对异族通婚几乎从殖民地时期就已开始。反异族通婚法从法律上严格划定了种族和社会界限,在形成种族认同和种族等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至2000 年,美国才陆续废除了各州的反异族通婚法。法律上允许通婚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观念上的种族阶梯论并未消失,华裔在美国的地位一直在低位徘徊,于是被视为同化最后阶段的跨族通婚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向上流动、改变种族身份地位的功能。以亚裔为例,除日裔,基本上是学历越高,跨族婚姻比例就越高,尤其是女性。另外,亚裔的联姻对象基本上是白人。[1]
通婚是否真的可以帮助华裔改变种族身份地位?一些具有通婚经历的作家从文学角度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颇具代表性,她的作品通过表现通婚家庭成员关系来揭示种族身份地位问题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下文将以小说《谁是爱尔兰人》 (下文简称《谁》)和《妾》为例,借助身份理论来分析通婚重构种族身份的政治功能及其有限性,以及通婚所造成的社会性别身份错位和基因传承的不确定性等问题,表明通婚不能帮助华裔个体以改变自我角色身份的方式达成改变华裔群体的种族身份地位,任璧莲的作品通过对通婚问题的呈现审视了华裔在当代美国的种族身份地位和政治诉求。
一、社会性别身份错位
任璧莲小说表明,美国华人移民个人身份与自我的角色身份和社会群体身份密切相关。角色位置可以定义和建构一个人的身份,而社会分类所形成的社会群体身份往往比角色身份更能彰显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根据社会群体身份理论,将自我和他人进行分类从而形成“内群体”或“外群体”的方式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个体的言行总趋于与群体内成员的特征相一致,以此来区分与群体外成员身份的不同。[2]自觉选择哪个群体为“内群体”体现了社会认同。在美国,由基因所决定的肤色和血统标出了华裔的外群体身份,华裔遭受偏见和歧视,因此华裔想获得白人主流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并成为白人内群体成员。就群体之间关系的变量而言,他们无疑相信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因而采取社会流动策略,以白人的妻子或丈夫的角色身份进入白人家庭,以角色身份渗透群体身份,进而改变后代的遗传基因,使后代逐渐白化,进入白人群体,获得等同于白人的种族群体身份。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通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在《谁》和《妾》这两部小说中,从夫妻关系层面看,通婚家庭中华裔一方的社会性别突破了常规的角色形象和功能作用,尤其是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的家庭分工模式和话语权分配,在存在种族阶梯的历史背景下,传统的社会性别身份产生了错位,女性担当男性化的角色,男性处于女性化的地位。从混血后代的基因层面看,或是华裔的基因被吞没,混血儿身上的华人特征基本消失;或因为继承较多的华人特征而将继续边缘化的待遇,遭受更多身份的困惑。
(一)女性的男性化角色
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内部,男性具有话语权并处于支配地位。父权文化的性别体系为两性规定了不同的性别角色,即“男主外女主内”。即使在当今社会,女性也还完全没有摆脱对传统社会性别的认同,一方面是基于生理差异,另一方面是对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同。不过,性别身份与族裔/种族相关联时情况却可能发生变异。作为丈夫的白人男性即使经济不能独立,作为妻子的华裔女性仍愿意给他家庭主宰者的地位。
《谁》中的通婚家庭就存在这样的性别身份错位关系,但也不是“女主外男主内,”而是“女主外女主内。”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68 岁的华人移民老太太,老伴已经过世。女儿娜塔莉与爱尔兰裔男子约翰·希结婚,有个混血女儿叫索菲娅。孩子的保姆走后,老太太来到女儿家带孩子,在她看来,这个家庭是个颠倒的世界。娜塔莉是一家银行的副总裁,连婆婆都认为她“真是和白人一样出色。”[3]虽然娜塔莉嫁的是白人,但是老太太否认高攀,这不仅因为美国的爱尔兰人移民社会地位不高,还因为希家四个男人能力都很差,没有一个工作的,且有各种诸如懒惰和酗酒等坏习惯。老太太完全有理由相信希家男人没有男性气质,没有养家的责任感。依据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男主外女主内不仅成为男女之间的界限,也把男性作为以社会为主的人,女人则以家庭为主。当然,现代女性同样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较好的工作,但是男性也还是被认为需要工作,有时也要帮助照顾小孩或做点家务。娜塔莉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职位和不菲的收入,这个家可以“女主外”,她对此没有表示过不满。然而,女婿既不能主外也不愿主内,“他既没有工作,也不照顾索菲娅。因为他是个男人……”[4]娜塔莉必须独自支撑这个家,因为她不想离婚。
华裔女性与白人通婚的结果是让自己充当了传统的男性化角色。娜塔莉却没有抱怨过丈夫,丈夫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保险员的工作,她就恭维道:“很高兴看到你又执政了。”[5]她在家里自我弱化,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认同,同时也顺应了种族身份地位的从属性。不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华裔,她的自我角色和群体身份归类都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她对待婚姻的方式体现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思想,有失必有得。她也因此获得希家人的尊重,并维持了婚姻。从这个通婚家庭结构的表面上来看,华裔女性是拉近了自己与白人的“社会距离”。
(二)男性的女性化地位
任璧莲小说显示,在家庭中占支配地位的一方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和种族身份密切相关,社会性别更像是一种权力系统,而不只是一套刻板化的模式或是一些男女之间可见的差异。在《妾》里华裔男性卡内基·黄与欧裔女性简妮·贝利的通婚家庭中,话语权的分布状况显出种族身份的高低,性别身份错位表现在华裔男性的女性化地位。
当初黄母对儿子要娶白人表示坚决反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儿子婚后没地位。但是卡内基坚持要娶简妮,白人对他的诱惑力很大。黄母于是悄悄给了简妮一百万美元现金让她不要嫁给卡内基。简妮虽收下“贿赂”,却照嫁不误,于是黄母更加不喜欢这个白人。正如黄母所料,卡内基婚后的家庭地位确实低于简妮。简妮居于传统家庭中的男性地位,并以此规定自己的言行。[6]当她的支配性地位受到挑战时,她就立刻给自己打气,“在这个家里,我只让别人疑惑。”[7]尽管卡内基有接近白人社会的倾向,但是他的思想多数时候是朴实的,他的善良没有被等级观念所限制。例如,当初兰兰从中国来美国是以保姆的身份进入这个家,卡内基并没有以主仆的姿态对待她,而是认为应该让兰兰住楼下的独立成套客房。然而简妮借口说兰兰肯定想要私密性,让兰兰住外面马棚上面的小房间。卡内基觉得自己要表达点想法都“需要聚集自己微不足道的男人的勇气…… 得先考虑自己的染色体”。[8]在这个家里,白人太太才是主人。后来,卡内基为了帮兰兰排遣工作之外的无聊,翻出旧电视和VCR 给兰兰用,还想让兰兰上大学、拿学位,简妮知道后感到很吃惊、很不舒服,因为卡内基产生这种想法居然没有先和她商量。很明显,在这部小说里,华裔男性在美国社会处于女性化、边缘化的地位是以一个家庭内部的华裔男性被支配的性别身份展示出来,他处于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显示出种族地位的边缘性。
人的性别角色行为受到环境的强烈影响,不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人们想象的社会环境,都对性别身份及其发挥的功能产生很大作用。美国主流白人社会,或出于错误的认知,或为了保护利益集团的权力,对华裔男性的气质做了歪曲的认定,否认他们应该拥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同时,白人男性或女性为自己构建了高于其他种族的气质和品质,将自己置于支配性的地位。
二、基因传承的不确定性
通婚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后代族性特征的不确定性。或许以跨族婚姻进入白人家庭并“制造”混血后代是当初华裔重构种族身份的一个目标,但是结果仍然出乎他们意料。《妾》中坚持通婚的卡内基明显对混血儿子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看到自己“新出厂的”儿子时非常吃惊:
他不是你最近你可以在周围看见的那种褐色头发、居于两者之间的孩子。这个孩子——我的孩子——他是白肤金发的孩子……还有他的眼睛:圣母玛利亚蓝色。能亲眼目睹孩子的接生真好。如果搁在50 年代,我很可能跌跌撞撞地跑去找律师,语音不清地告诉他,孩子出生时被掉包了![9]
与卡内基的不安相对比,简妮对儿子的样貌则比较满意,“我对我的基因没被卡内基的吞没而感到高兴……我的血统,我这一边,我自己没有被淹没。”[10]血统是一个民族、家族或者说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沉淀下来的血缘关系,通常用来指代某种优秀的品质,无疑,在简妮心目中,她的血统代表更优秀的品质。小贝利像贝利家人使得简妮非常高兴,因为贝利家的基因显出了压倒性的强势力量,但是卡内基对混合基因儿子的感受可谓五味杂陈:
多数人都没注意到贝利是个杂烩汤。即使有人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反应迟钝。思考他意味着什么。然而是什么呢? 多数人会说,是未来,很可能——这是他们最善良的表达。只有我会说,是正在消逝的过去。[11]
多种族人可能被视为美国的未来,但是卡内基却表现出对华裔作为一个族裔的显著特征突然消失的震惊,表现出对生物同化的忧虑。在同化的过程中,少数派或其文化有可能消失在更大的或占更多支配地位的群体或文化中。
第一代移民往往反对通婚,也不喜欢混血后代,因为华人的基因被吞噬了,如在《谁》中,老太太对混血儿外孙女的不满:“她跟我曾见到的其他中国姑娘可不一样。我们去公园的时候,她是这么做的。她站在婴儿车上,把衣服脱掉,然后扔到泉水里。索菲娅!我说,别扔!但她却只是笑,像个疯子。”[12]老太太认为中国女孩应该文雅端庄,她最不能忍受外孙女在公共场合光着身子乱跑,她天天教育索菲娅不要脱衣服,口头教育不行,她就改为打屁股。在用体罚方式帮助外孙女不在公共场所脱衣服后,索菲娅的麻烦更多了,她学会了踢人,后来索性向老太太身上扔起沙子, “中国有成百上千万的孩子,没人这么做的……她跟所有的中国女孩儿都不一样。”[13]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华人的基因没有得到良好的复制。她认为自己能帮索菲娅,“让她用很中国的一面去跟她很野性的一面搏斗”。[14]
混血儿最不能让华人接受的首先是外貌,其次是言谈举止、思维习惯等,很多混血儿完全不像中国人,华人一方的基因或文化基因得到的遗传不多,像美国孩子一样,他们全无中国人推崇的孝顺概念,血缘和文化的纽带在他们心中变得十分脆弱。不论华裔与白人的混血后代传承哪一方的基因更明显,都存在一个被社会接受的问题。混血儿遗传白人基因多常被“理解”为白种人,遗传华裔基因多就会被“理解”为亚裔美国人,他仍将遭遇华裔的种族身份问题。
结语
美国通婚的合法化本身反映了美国社会的进步,法律上种族隔离和歧视逐渐消除,但是社会观念中的种族优劣区分依然存在,并对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任璧莲通过通婚家庭里的成员间关系揭示了美国存在的种族阶梯,暴露了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里的弱势地位,表达了对种族歧视的“理性的愤怒”,同时用选择通婚表达了少数族裔个体对社会的自我调适和对于社会上种族观念的妥协,既体现了向白人种族的靠拢,又表达了华人族裔希望分享平等权利的政治诉求。但是,华裔选择与白人通婚并不能立刻改变种族阶梯的秩序,从而帮助华裔和白人社会实现无缝对接或重构种族身份。在文化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种族群体有优劣之论的当下,华裔不可避免地遭遇身体、性别身份和基因的等级化,靠一代人的通婚不仅不能消除华裔个体的身份焦虑,更不能解决华裔整个族群的种族身份问题。
[1]Qian,Zhenchao,et al. Asian American Interracial and Interethnic Marriages: Differences by Education and Nativit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35.2(2001) : 557-586.
[2]Goldberg,Caren B. Applicant Reactions to the Employment Interview: A Look at Demographic Similarit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56. 8( 2003) : 561-571.
[3][4][5][12][13][14]吉什·任. 谁是爱尔兰人[J]. 郭英剑,译. 外国文学,2002,( 4) :27.30.29.28.29.29.
[6][7][8][9][10][11]Jen,Gish. The Love Wife[M]. New York: Knopf,2004. 83. 247.22.184.155.156.
——读《卡内基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