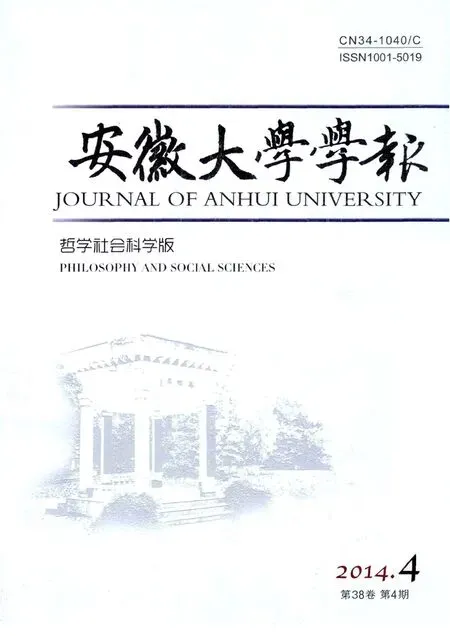1935年保学在婺源的推行及其折射的社会变迁
——以《徽光》杂志的记述为中心
邹 怡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11月,由蒋介石得力干将熊式辉主持的江西省政府便颁布《江西省设立保学暂行办法》,要求依托保甲组织,按保设校,以一保一校为原则,就地筹款,采用政教合一的方式,实施儿童义务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经过在丰城等县为期3个月的试点后,1935年,保学向江西全省推广铺开①程时煃:《十年来之江西教育》,《赣政十年:熊主席治赣十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12月,第3页。。
国民政府在结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后,以教育为“地方秩序”重建之首务,与蒋介石等对多次“围剿”惨败的认识有关。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剿共”会议上提出,“围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苏区民众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故“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重视对民众思想的整顿②《蒋委员长在牯岭训话:这次剿匪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的方法是硬作快作及实作,最要注意的改变心理养成风气》,《教导周刊》第3卷第18期,1932年,第2页。。为此,从1933年开始,国民党着力在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地区,尤其是赣、鄂、豫、皖、闽五省推行政教合一的特种教育,并令江西省率先施行。特种教育实施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山民众学校的设立。江西省于1935年开始全面推行的保学,可以说是随着“围剿”后保甲制度的落实,特种教育的进一步深入展开③关于江西中山民众学校的情况,可参阅肖如平、王彩玲《民国时期江西的特种教育》,《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肖文提到,“1934年江西省共设有中山民校245所,分布在收复区60个县,随后几年略有减少”(第44页)。其实,中山民众学校的减少,是因为其已转化为保学的形式。。
关于保学,在部分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研究中,曾被连带提及④谢增寿:《国民党南京政府保甲制度述论》,《南充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毛园芳:《试析国民党南京政府保甲制度的反动作用》,《湖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江汉学刊》1997年第2期。。一些关于近代教育的通史性著作中,也涉及对保学的介绍①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但是,对保学的专门研究却少有见到。笔者管见所及,2001年,刘燕云开始关注熊式辉督赣时期的江西保学,她从政策规定入手,梳理了1932—1942年江西保学的发展情形,文章着重点明保学推广的思想清剿性质,并指出,因民众反感思想政治教育,地方亦对筹集保学经费怀有抵触,故保学虽得大面积铺开,却有不少形同虚设,教育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但文章亦承认,舆论上对保学的大力宣传,提升了民众的兴学观念,保学的普遍设立也推动了江西教育的发展②刘燕云:《关于熊式辉督赣时期的江西保学》,《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肖如平完成于2003年的《民国时期保学在江西推行的历史考察》及随后的系列论文③肖如平:《民国时期保学在江西推行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李红梅、肖如平:《民国保学与江西乡村教育的近代化》,《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李红梅:《论民国时期保学在江西推行的原因》,《黑河学刊》2011年第12期。李红梅的论文沿袭了肖如平硕士论文的观点。,对保学政策的实施过程和社会影响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分析。与刘燕云的研究有所不同,肖如平对保学的评价更倾向于积极,他认为,保学的推广令江西乡村教育由以私塾为主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小学教育为主的“现代模式”,保学整合了政府、士绅和民众三者间的联系,对乡村民风民俗的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燕云和肖如平对保学评价的差异,缘于学界对近代史认识的变化,他们的观点分别隐含了近代史研究中先后流行的两个思路:对国民党政策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关注。刘和肖的研究,使用的主干史料基本同质,大体是国民政府和江西地方政府编辑出版的报告和杂志。不可否认,在这些文献的记述中,既有对新政实绩的推崇褒扬,也有对政策推行中繁难之处的分析思考,所以,均可为前述两个流行思路张本。但是,政策的落地、教育的推行,涉及实施和接受两方,双方的互动方才构成完整的历史,因此,在借助政府视角认识这段历史之外,有必要透过民众的立场对此再作一检视。在民众看来,保学的设立意味着什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基层对保学推行中的当为与不当为,又有着怎样的判断?进一步,将政府主张与民间因应两相对照观之,近代中国的建设努力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难局?这些问题,均需更多来自非官方背景的史料,方能得一立体的认知。笔者在阅读史料过程中,在一册题为《徽光》的民间团体刊物中读到时人关于保学推行的若干调查和讨论,恰为前述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史料入口,本文的讨论即围绕《徽光》④徽州六邑旅省同学会:《徽光》第2期,1936年,安徽省图书馆藏。而展开。
一、关于《徽光》与徽州六邑旅省同学会
《徽光》是徽州六邑旅省同学会的会刊,创刊于1934年春⑤“本刊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春天诞生的。”《编后记》,《徽光》第2期,第103页。,虽距今并不久远,但存世极少。现知公藏机构中,仅安徽省图书馆收藏有一册,为 1936年出版的第二期,得据以一窥鳞爪。
所谓“徽州六邑”,即自唐代大历五年(770)置立的歙州(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名徽州)开始,徽州长期辖有的六县:歙、休宁、绩溪、黟、祁门和婺源。长久稳定的行政区划,形塑了自成一体的徽州文化,造就了徽州六县民众强烈的自我认同感。明清两代,徽州人以大量旅外经商而蜚声海内。为谋求安全保障、事业发展,离乡流寓的徽州人常以乡谊为纽带结成同乡团体。自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更多乡镇人口步入城市,同乡组织的传统由此得到赓续,并因更为多元的职业分途,组织的业缘色彩渐趋浓厚。徽州六邑旅省同学会便是这一时代趋势的产物,它是在安徽省城安庆求学的徽州青年组织的一个同乡团体。
1933年5月,由吴鸿章等发起组织,经紧密筹备,同年6月4日,徽州六邑旅省同学会在安庆圣保罗中学⑥今安庆市第二中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同学会下设负责处理会务的干事会,内分文书、事务、监察、交际和编辑等股①《本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徽光》第2期,第97页。。从《徽光》杂志所附同学会编辑股出版委员会会员一览表来看,该同学会成员主要包括在安庆就读于安徽大学、安庆初中和安庆高中的学子。因会员姓名后所注“长期通讯处”中的地址并不限于安庆,还包括绩溪、婺源和黟县等原籍住所,甚至还有芜湖,笔者推测同学会会员包括了业已毕业的学生。
同学会成立的时代,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已逐步击败北洋时代以来的各派军阀,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完善加强国家政权建设,提升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综合实力。此时,原本同呼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却因各自政治理念和具体政治利益的不同,自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系发生激变,互相将对方斥为“反革命”②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其中,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并因国民党的挤压和对时局的判断,将自身群众基础转移至农村,尤其是皖、赣、闽、豫、鄂等省的边界地带。与此同时,进入1930年代后,世界性的大萧条开始影响中国,而中国因缺乏强有力的货币财政工具,白银被迫升值,国内通货紧缩,农产品价格大跌,城乡经济遭受沉重打击③参见[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孟凡礼、尚国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95页。。
“最近几年,故乡社会的急剧崩溃——整个中国的社会也是如此——老幼残弱流离失所,我们还可以‘埋首窗下’而忍心不问吗?‘学而优则仕’的幻梦在今日的青年是应该彻底觉悟了!”④《本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徽光》第2期,第94页。求学省城的徽州学子面对时局,发出了这样的呼唤。热血青年们在成立大会上将同学会宗旨设定为“联络感情,切磋学问,改进桑梓教育”。至1935年秋第六届会员大会时,同学们又表示,若纯以改进教育为目标,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进一步将宗旨修正为“联络感情,砥砺学问,发展桑梓文化”。学子们最初认为,改善教育是将新知识传播至桑梓的有效途径,但他们很快又发现,教育的改善有赖于地方的社会基础,即地方文化的全局性改观。学子们提出“发展桑梓文化”,“所谓文化的意义,就是包括社会、政治、文物……等全部的社会生活”⑤《本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徽光》第2期,第95页。。
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发展呢?青年们认为,“虽然我们的知识能力很薄弱,但是比着故乡里一般终日劳动的民众,已经是应该站在智识的前线上了。……我们总应该利用我们的智识工具来指导他们,把他们没有地方告诉的隐痛向全社会来宣布,向保护他们的政府来陈述;同时我们还可以唤着‘人类互助’的口号来激动一般青年和智识阶级对于桑梓建设的注意和从事于实际的工作”⑥《本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徽光》第2期,第95页。。同学会会刊《徽光》,就是作为这一桑梓改造途经的载体而存在的。《徽光》第二期的“发刊词”中点明了该刊承担的三个使命:“第一,就想把故乡实际状况,如教育,政治,经济,农村,商业,忠实地描写出来,使旅外同乡都知道一个大概。第二,就想把现代思潮,新的学说,以及各种新的学术传达给父老乡亲。第三,就想把我们的意见,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一一报告给与全徽州的民众。”⑦杰谋:《发刊词》,《徽光》第2期,第1~2页。所以,《徽光》杂志的内容,包含着很大一部分社会调查。从现存第二期的目录看,除发刊词、编后记与附录外,全册包括文章15篇、诗词10首。15篇文章中,理论性的论说文有4篇:王炳森的《本然社会与社会理想》、际唐的《朱子的教育学说》、汝黛的《谈谈人生观》、荣译美国心理学家William James的《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小说1篇:江知凡译英国小说家Charles Dickens的《囚徒归来》;其余10篇均为社会调查,此处不避烦琐,胪列于下:啸菲才《徽州“中学教育”的两大问题》、汪登鳌《由普及教育谈到祁门不识字的民众们》、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隽如《婺源小学教育的近况及其危机》、吴志会《改进农村的我见》、程延津《徽州农村问题的研究》、适安《徽茶之研究》、心纯《婺源妇女生活的写实》、余心明《谈谈故乡》、碧《家乡》。社会调查中有近半是对地方教育问题的专门探讨,其实,4篇论说文和1篇译文也均与教育有关,这一内容倾向正体现了青年们对改变桑梓基本路径的最初设想——教育。
徽州的婺源与江西省的保学推行发生关系,缘于一次行政区划的调整。1934年,出于“剿共”的需要,婺源划归江西。婺源民众为此曾掀起声势浩大的“回皖运动”①参见唐立宗《省区改划与省籍情结——1934至1945年婺源改隶事件的个案分析》,胡春惠、薛化元主编:《中国知识分子与近代社会变迁》,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5年,第519~546页。,徽州人亦仍视婺源为徽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个徽州因为政治的关系而破碎了,但是整个徽州的精神还是存在的,还是团结一致的。……同学会不但无分离的现象,更能加紧组织,团结坚固起来;而本学会的会刊之问世,则属这种团结精神的表现。”②杰谋:《发刊词》,《徽光》第2期,第1页。这期1936年出版的《徽光》中,有关婺源的内容明显多于其他五县,当与此原因有关。
二、1935年保学在婺源的推行
1935年,保学开始在江西省全面铺开,甫入江西的婺源亦在推广之列。《江西省设立保学暂行办法》是保学推行的指导性规定,《徽光》撰稿人碧深根据实际操作体验,将其内容概括为四个要点:“A.保学制度采政教合一原则,全县教育由行政人员管理。B.保学制以保甲为设施学校单位——每保必须设保学一所。C.除新设立的保学外,其他的教育(包括公私立小学及私塾等)完全停止。D.保学经费完全由地方自筹。”③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37~38页。这些要求固然经过了丰城等县的试点,但在婺源的推广中,还是出现了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
784 “和谐使命―2017”非洲七国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临床疗效分析 宋 平,杜改萍,易 岚,叶 霞,吴晋晖
保学制要求依托保甲设立学校,每保务必设立一所。该规定的初衷是保证保学在乡村的均匀分布,并且,依托保甲,与政府力推的基层行政单位相同步,也便于政府管理及贯彻政治宣教。1935年上半年政令下达时,政府以整齐划一之气势,要求全县现有小学悉数停办,普设保学。经过半年的磨合运行,碧深认为,婺源境内的小学教育出现了五种类型。
第一种为“县立中心学校”,就是旧有的完全小学。当时,婺源全县在行政上共分五个区,每区设一中心学校。在保学制度推行后,县立中心学校内部实际分为两个部分:高级部和保学部。高级部,负责推进本区教育事业、便利保学毕业儿童升等,经费由县政府承担。保学部,其实为初等小学部分,经费由所在保自筹。
第二种为“私立中心学校”,此种学校的组织和功能与“县立中心学校”相同,差别之处在于高级部的经费亦由地方自筹。这一种学校,全县其实仅庆源一所。
第三种为“代用学校”,此种学校与“私立中心学校”相仿佛,不过经费上不如后者宽裕。
第四种为“联立保学”。这种学校设于规模较大,即包含不止一保的村庄中,经县政府核准,得联合两保以上、五保以下共同设立一保学。此种学校的教育内容基本上为初等小学水平。这一种学校的数量很多。
第五种为“保学和巡回班”。凡户满一保的村庄,设立保学一所。户不满一保的村庄,无法独力举办,得与邻村合办一保学。偏远的村庄还可采用巡回班的方式,即由保学每日或每周派人前往教导。这种学校的数量也不少。
细究之,这五种类型的学校其实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高级小学,存在于县立中心学校、私立中心学校和代用学校的高级部中,但该层次的学校数量极少。第二层次为初级小学,存在于前三种学校的保学部和后两种学校中。相较此前的地方教育,保学推广的实质性工作在于依托保甲,在村落的层次上推广初级小学。
经过半年多的办理,全县的保学“不下一百几十所”。但是,其中不乏空壳学校,“县府把某保保学校长的委任令填就发出后,便是创办了一个保学,那校长把县府每次发下的表格,很起劲的捏造填来,便可以象征他把保学办得成绩斐然了,事业究竟如何了,他却不管”①隽如:《婺源小学教育的近况及其危机》,《徽光》第2期,第50页。。另外,婺源地处山乡,村落分散,多村合为一保所设立的保学不少,这表面上照顾到了教育机会的均等,实际上却因为交通的限制,民众前往邻村学习极为不便。“六足岁到十二足岁的儿童,和终日勤劳的农夫农妇,在风霜雨雪,和黑夜更深的时候(保学教育的时间,儿童班以日间为原则,成人班以夜间为原则),跑几里路来接受教育,恐怕不是容易的事。”②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40页。
政府取缔私塾,有更新师资力量的考虑,因为保学的推行,连带着政治宣教的目的。所以,政府要求,“无论公私立的中心学校,和地方设立的保学,校长、教员、职员一律由县府委任”④隽如:《婺源小学教育的近况及其危机》,《徽光》第2期,第51页。。私塾教师虽怀有地方教育的热情,但其知识结构多基于旧学根底,通过县政府组织的区督办员考试和保学教师登记颇多困难,故对此强烈抵触而罢考。而政府指派的督办员和保学教师,缺乏乡民基础,得不到大家的信任⑤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39页。。为弥补保学教师的不足,政府在鄱阳专员公署设立了保学工作人员征训所,但富有学养的塾师拒绝受训,接受培训的多为失业的店伙和不得升学的小学毕业生,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他们将担任保学教员作为一个职业出路。“拿小学生来教小学生,小学教育怎不江河日下?”⑥隽如:《婺源小学教育的近况及其危机》,《徽光》第2期,第51~52页。撰稿人隽如对此不禁忧心忡忡。
保学推行中更多的难局源于经费的筹集。根据《江西省设立保学暂行办法》,保学经费由各保自筹,“尽先以各保原有学款公款公产拨充之,不足时按照保甲经费住户分等负担比例摊足”⑦《江西省设立保学暂行办法》第十五条,《江西省政府公报》第236期,1935年,第3页上。。公产是民间为应付家族或村落公共开支而集体置办的盈利资产,其中,专用于子弟教育支出的谓之学款。但是,因此时国共两党力量在江西的拉锯对抗,公产多被移作地方自卫开支,难有盈余用于保学⑧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40页。。公产、祠产,本质上还是民间财富的积累,与地方经济情势密切相关,而保学开始在江西各县铺开的1935年,是中国农村经济正经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的一年,经费筹措更形艰难。就婺源而言,除生存所需的一般粮食作物外,农家的日常开支多仰赖茶业。而当地茶叶生产多属零散粗放经营,在国际市场上遭受日本、印度和锡兰工业化茶业产品的冲击,加之地方局势动荡,商人裹足不前,更加剧了婺源茶业的不景气⑨适安:《徽茶之研究》,《徽光》第2期,第64~65页、69页。。地方事业各种经费,为此更是无从获取。
基层公产不足以应付保学开支,“保学经费的来源,无疑的是要压在老百姓的户口捐来了”,“故往往教育经费愈增加,愈使贫民感受其疾苦,结果,不但人民不欢迎教育,甚至发生仇恨之心……盖教育之效,原期其能助人增加经济之能力,今其效未见,而负担已先在身,此仇恨之心所由生耳”⑩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41页。。
更令民众对保学经费摊派产生抗拒心理的是经费筹集过程中的贪腐。原本作为保学经费第一选择的公产,管理中不乏侵吞现象。“侵吞公产的份子,至少是在乡村里有点势力的人,他们把公产侵吞了去,当然是不愿意再拿出来的;他们看到没有人能够在最短期间把公产清理起来,便趁此帮助办教育的人把保学经费从别方面——摊派户口——确定了下去,将来或许不至于再清理到他们家里的公产上去。”而摊派在具体操作中更是成为“污吏剥削乡民的一种工具”,“负地方行政及保学长官的区长保长——区长是全区的教育长官,保长是保学经费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他们为便利从中取利计,当然是赞成摊派户口来得方便”。户口实数只有区署知道,每户应摊派到的经费由区署说了算,上下其手是极为便利的事。婺源某区在摊派自卫经费时,按户口实数计算每户每月应负担经费6分5厘,但在区内保长联席会议上,区长以便于征收为由,提出每月每户缴纳1角,此提议居然也获得了通过。集腋成裘,多征收的费用,据悉全区每年达1000多元。“这一千多元的额外征收,到底做了什吗事,老百姓是不能问的。”①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41页。保学经费的摊派,在经手者看来,又是一个敛财的时机,自然难逃此套路。
以行政力量为后盾,私塾在婺源被保学所取代,但是囿于按保设立,在村落分布稀疏、交通不便的环境下,保学在空间分布上的灵活性便不如民间自发组织的私塾,一部分乡民只能跨村上学,反不便利。加之保学推行过程中,追求按保设校政策目标的短期达成,出现了一些并无实质教育力量的空壳保学,导致初等教育实际供应量的减少。保学推行中,对教师资格的行政认定,又遭到乡村旧有塾师的抵制,而新培训的师资得不到民众的信任,教育质量下滑。加上保学经费完全摊派至村民,更兼征收过程中基层官吏的贪腐,令民众对集资办学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所以,在《徽光》的撰稿人看来,婺源保学推行中发生的种种流弊缘于实施方法过于呆硬,“把固有的教育历史和背景完全推翻,而硬性的要把保学制从根本上立刻建筑起来”②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38页。。从《徽光》中的记述来看,民众对保学的抵触情绪并不来自政教合一。以《徽光》撰稿人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固然意识到“县政府要不要有教育行政权,那是教育应不应该有独立精神的教育哲学问题”,但他们并不反对把政教联系在一起,“过去中国教育同政治脱离了关系,在教育设施上确发生了很多非教育本身所能解决的困难”,所以,教育的推广倚赖行政力量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的要害在于行政组织是否健全,地方行政力量是否具有发展教育的眼光和能力③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44~45页。。
三、保学问题折射的社会变迁
《徽光》撰稿人将婺源保学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归结为“把固有的教育历史和背景完全推翻,而硬性的要把保学制从根本上立刻建筑起来”。那么,“固有的教育历史和背景”是指什么呢?在《徽光》讨论婺源保学的文章中,主要指婺源旧有且受民众信赖的私塾教育。其实,若放大观察的视野,关注婺源保学推行的上下左右,将其置于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能看到更为丰富的社会背景,并透过保学问题捕捉到近代社会变迁的若干脉络。
保学,是政府利用保甲组织在基层推行的基础教育。在婺源推行保学的30年前,即1905年,始于隋代、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正式废除。“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即士子永无实在之学问,则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④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84页,见《民国丛书》第2编第7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废除科举的直接原因,是清末中西竞争中,政府意识到人才的短缺。列强精湛的工业文明令清政府瞠目,而中国的科举取士只能筛选出应制之才。废科举、兴学堂,反映了近代中国在人力资源问题上一次根本性的思路转变:政府不再依靠考试被动选择人才,而将利用学堂主动培养人才。但是,在此之前,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并未被纳入政府基本职责范围①以清代为例,除顺天府外,政府一般不提供办学经费。《礼部则例》要求州县设立社学和义学,但办学经费完全依靠州县官自己,往往是由仁厚的州县官自己捐款或向士绅募集资金来建立社学和义学。不过,绝大多数州县官并不热心,也不情愿捐资建学校。由于缺乏经费,维持学校十分困难。许多由先前的州县官捐资建起的学校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中国教育史上的核心内容——科举——只是一种考试制度,而不是一种教育制度。民众的基础教育长期依靠民间自行组织的私塾,政府本身并无多少工作经验和财政基础。所以,在政府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开始将民众教育揽入自身职责范围,并亟待成效尽快兑现时,只能寄希望于利用民间力量,采用官督绅办的路径。
就1934年以前婺源所属之安徽省而言,清末在省城设立的学务处,办事职员便是官绅并用,有“地方自治”之性质②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523页。。而清末的地方自治,其定位乃是对官治的一种补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总纲第一条便明言:“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按照定章,由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③《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北洋法政学报》第91期,1909年,第1页。当时,县级的教育行政机构名为劝学所,劝学员“由总董遴选本区绅衿呈请地方官札派……劝令各村董事切实举办,此项学堂经费均责成村董就地筹款,官不经手”④安徽通志馆编纂:《安徽通志教育考稿》卷5,1934年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29号第8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影印本,第2714页。。安徽省级的学务处,后改为学务公所,进入民国后渐次演变为教育司、教育科、教育厅。县级的劝学所,在1923年后改组为教育局,但改组进展并不顺利,教育方面的行政力量仍然有限⑤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第527页。。《徽光》中的《谈谈故乡》一文,描述了1935年前后祁门的教育状况:“统计全县县立完全小学只有二所,公立完全小学也只有二所,私立完全小学三所,私立初级小学二十四所,中等学校更谈不到,所以失学的儿童很多。”⑥余心明:《谈谈故乡》,《徽光》第2期,第77页。此段记述中的“公立完全小学”,可能指区立完全小学。另有一份史料统计了1933年祁门县的小学数量,计有县立完全小学2所、区立完全小学1所、私立初级小学9所、私立完全小学4所,共计16所(安徽省统计年鉴委员会编:《安徽省统计年鉴》,1934年,第273页)。该统计资料中祁门的小学数量比《徽光》中的记述更少。江西省的情况更不如人意,“江西之教育,在十年前之今日(引者按:指1931年前后),尚未发动至县以下,故只有‘省的教育’而无‘县以下的教育’,复以省教育基金,连年被移作他用者,达八十余万元,省教育机关经费,积欠不发至半年以上,因此‘省的教育’亦陷于不能维持之境”⑦程时煃:《十年来之江西教育》,《赣政十年:熊主席治赣十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12月,第1页。。可见,当时政府虽有心发展教育,但限于能力,在基础教育方面,很大程度上仍依靠民间办学。此时,政府在塑造健全国民的大方针下,对学校中思想教育的管理也比较宽松。1920年代,徽州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甚至将佛学作为学生修身课的主要内容。省教育厅虽然认为此举“似与部令未合”,但最终也容许了二师校长坚持己见⑧方光禄、许向峰、章慧敏等:《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7页、101页。。省立学校犹如此,私立学校可想而知。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力量响应政府号召兴办新学时,一些地方出现了师德败坏、教学质量低下、纯为敛钱的现象。1920年代,曾有论者批评徽州当地的办学者“是为饭碗而办的,是为分赃而办的,是为占一个位置而办的”⑨舍我:《歙县师范讲习所的“人”的问题》,《微音》月刊第26期,1926年1月,第17页上。。教师队伍中,“居教职者,或为前清老学究,或为失业商人,更有学文不就习贾未成者,亦忝然而为人师”⑩孙之杰:《黟县教育进行之计划》,《黟山青年》夏秋二季合刊,1923年9月。转引自张小坡《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与改造徽州社会的舆论动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53页。此期出现师德低下、贻误子弟的现象,与科举废除后,乡间读书人社会地位下降、经济上没有出路有关。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清末将自治视为对官治的补充,学堂教育的推行亦旨在适应时代需求,培养多样的人才为政府服务①参见周振鹤《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而至民国时期,在孙中山的设想中,自治是达成民主的准备,孙中山理想中的自治甚至不是日本那种官治主导下的自治,而是欧美式自下而上的民权②孙中山:《在上海与李宗黄的谈话(一九一八年七月)》,《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1页。另可参见李国忠《超越“日本化”——论孙中山对日本近代化的认识及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构想》,李卓主编:《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7页。。为实现此理想,必须先开民智,所以,民国时期的教育,尤其是1928年以后“训政”时期的教育,就政府用意而言,与清末大相径庭。为民权作准备的教育思想,也为当时的知识阶层所赞同。《徽光》中诸篇谈及教育的论说文,均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啸菲才《徽州“中学教育”的两大问题》认为,当时徽州的中学教育不重视体育和表达,所以难以培养出体格强健、能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社会公民。译文《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指出,教育能给予民众判断好坏美丑的能力,选出能领导大众的好人。际唐《朱子的教育学说》则从乡贤传统中寻找根据,论证人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变。王炳森《本然社会与社会理想》援引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更是推崇社会本然具有的组织能力。
而乡闾大众对教育的理解并没有达到这一程度。汪登鳌《由普及教育谈到祁门不识字的民众们》一文所谈到的情况便颇有代表性。作者在1935年暑假回祁门老家,劝村民送小孩入私塾读书,村民答道:“我父没有读书,我也没有读过书,到了现在的今日我依然能够生活在世上;现在我的小孩子,用不着令他入学。”在一般大众看来,社会管理的责任由一小部分读书人承担即可,“有一个子弟入学校读书识字,一切责任都可委给他去做,别人就可以不必识字了”③汪登鳌:《由普及教育谈到祁门不识字的民众们》,《徽光》第2期,第34页。。可见,大众对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于科举时代:读书主要是为了成为管理者,也就是做官,若这条路堵上,读书便无多大意义,能简单识算、懂些人情道理便足够了,甚至认为不识字照样也能过活。所以,大众并未从自身权利出发,萌生迫切的教育需求。在国民政府的计划中,训政于1934年结束,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不得不坦言:“回顾过去成绩,全国一千九百余县中在此训政将告结束之际,欲求一一达到《建国大纲》之自治程度,能成为一完全自治县者,犹杳不可得,更遑言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工作。”④《五全大会通过〈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决议》(1935年11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10页。《徽光》中显示的民众状态,也显然还未达到民权主义、全民政治的要求。
前人研究已经揭示,推行保学的直接原因是国民政府发现在民众宣教方面远逊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新近的研究更加证实了这一点⑤参见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0~145页。。受国民党挤压,在有限空间内生存的共产党,审时度势,放弃了共产国际指导的城市斗争路线,转向农村深入动员,根据地宣教工作的成功便与此革命路线互为表里。而国民政府在基层的行政力量依然孱弱,因此,保学只能更加依靠地方力量,匆忙推开。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前人研究中所说的政府、士绅和民众三方的一种整合,但也令前文所述部分民间办学者唯利是图的弊窦加剧放大。据《徽光》中的调查观之,基层的区长、保长利用政府对保学的支持,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其视为敛财的工具。此时的区长、保长虽为地方有力者,但与传统士绅有着不小的差别。对于这批人,撰稿人碧深分析道:“婺源因为兵匪的骚扰,地方上热心办事的士绅都逃住在城里或大镇市上去了,所以一般保长都由无知识的游民充任。(其原因是忠厚的农民,应付不了军队和土匪的骚扰。)他们担任保长的使命是帮助区公所和军队施行命令,——命令对不对,他们是不问;目的是借此可以得点生活费。——保长是不给薪的。农民的利益是他们不能代表的。”①碧深:《商讨婺源推行保学的实际问题》,《徽光》第2期,第44页。对于民众来说,“乡绅”已不可依靠,自然便将改变这一局面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所以,前揭《徽光》中的撰稿人并不反对保学教育政教合一,而是期望政府能甄选可靠的办事人员,在政策推进中更加照顾到当地的具体情况。
四、结 语
以上,笔者利用徽州六邑旅省同学会会刊《徽光》,对1935年保学在婺源县的推行进行了研究。这册出版于1936年的民间自办刊物,保留了当地人眼中保学推行的具体情形,为研究者留存了一个不同于政府报告和官办刊物的观察视角。据《徽光》记述,保学在婺源快速推广的过程中,出现了上学不便、师资短缺、经费摊派等问题。民众对保学推行最为反感之处是经费的摊派,以及经费筹集过程中经手者的侵吞。对于政教合一,民众并非如前人研究所示持反对态度,而是希望政府在推行工作中甄选可靠人员,尊重当地文教传统。
1935年保学在婺源的推行,只是历史中短暂的一瞬,但将其置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保学推行中显露的问题也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若干脉络。自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在中西竞争的刺激下,政府开始意识到主动培养各种人才的重要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更是将教育视为民权实现的前期基础工作。政府开始将学校教育纳入自身职责之内,但行政力量有限,尤其在基层初级教育领域,只得依靠地方力量缓慢推进,其间也出现了部分民间办学者唯利是图的现象。国共竞争中,共产党强大的宣教动员能力刺激国民党迅速在“收复区”用行政力量普及基础教育,保学便是此背景下的产物,可谓政府普及基础教育的仓促展开。因行政力量不足,故仍只能依靠地方力量。此前民间办学中的弊窦,这次因地方势力承担政府任务,趁势贪敛而放大加剧,保学推行中民众最为抵触的经费问题,便是这一时代积弊的反映。民众期待着以政府力量来革除此弊端。类似的现象同样发生于教育领域之外,即近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绅”问题,民众的期待也与保学个案中所见相近似②参见魏光奇《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国民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收于氏著《清代民国县制和财政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中国现代史上持续的“国进民退”,或许正是源于这一现象表征的结构性动力。当然,这一点还需更多领域的史实来加以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