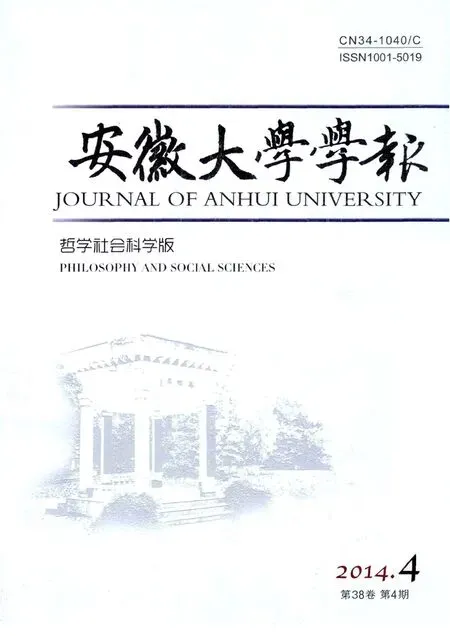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艺术自律思想的批判性考察
韩清玉
作为西方现代美学的基本命题,艺术自律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基于艺术本性的美学原则。它是以审美自律为基础,以审美无利害观念为源头的理论命题。艺术自律的基本含义是艺术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强调艺术的自我立法和独立自足性。当然,对这一命题的共时性建构是建立在对美学史的历时性考察中。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康德谈起。
康德在美学史上的意义非同一般,无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主体性转向,抑或为审美划定独立的疆域,都是革命性的。虽然康德的审美自律思想有着明确的道德指向,但是恰恰是审美本身的自律特质成就了其道德自由的象征潜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自律思想与康德美学的关联。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艺术自律理论是对康德审美自律思想在其价值论视角的发展;但大不相同的是,康德是以审美为本位的,而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则是以艺术自律性来达成社会批判的革命性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艺术自律性本身又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而被利用的,有一个激进的政治目的以他律的姿态出现在理论架构的前提中。因此,艺术自律思想从康德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
那么,以社会批判和政治干预为重要理论表征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艺术自律思想的深层动因是什么?这一思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它自身的复杂性彰显了批判理论的哪些特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仍然没有重视起来,究其原因,是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指向遮蔽了其美学理论的价值;另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理论谱系中,我们倾向于关注从黑格尔到阿多诺等人的理论线索,对康德美学的影响观照不够。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自律思想及其理论溯源的深度考察存在很大空间。
一、批判理论与美学价值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被贴上的标签,但是其成员们(特别是阿多诺)并不排斥这一称谓。“一开始,这个名称指一种批判社会学,它将社会视为一种对抗的总体性,那时这种社会学还没有将黑格尔和马克思排除在它的思想之外,而是相反自视为他们的继承者。”①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批判理论家对黑格尔、马克思的继承视角,本身就决定了其批判理论的对象、方法和理想建构,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以社会批判为自觉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什么会如此倾心于美学和艺术。
工业社会出现之后,“异化”越来越成为西方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思想家着重思考的问题。如果说黑格尔的“异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人之社会性存在的探讨的话,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则将其置于生产劳动的结构叙述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经济政治体制的调整,“异化”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了。异化程度的加深“在霍克海默那里也存在着这两种相互矛盾的预期。一方面他观察到,服从阶级缺乏独立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得到的食物很少’,而且因为他们被限制在虚假的思想精神状况之中,还因为‘他们是他们的监禁者的拙劣的模仿者,他们崇拜他们囚牢的象征,不是准备着去攻击他们的看守者,相反,谁要试着把他们从看守那里解救出来,他们就会把谁撕得粉碎’”②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册),第147页。。这一点也曾得到马尔科维奇的积极呼应,他认为现代人感到自己已经拥有自由,而这时却往往正在遭受奴役。对于这一情形马尔库塞也很清醒,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将人异化到全然不知的程度,异化对象“与狼共舞”却自得其乐。这种反抗意识的钝化是资产阶级文明的结果,这种文明所指向的,更多的是大工业背景下的物质生产,所造就的,正是失却自主意识和精神自由的“单向度的人”。如果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思想是一种技术社会中的特定产物的话,那么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也概莫能外,他是在打造一种理论思维的方法论工具以抗议社会依仗“同一性”的理论权威对人的精神自由的压抑和控制,纵然“否定的辩证法”仍然是一种哲学化思考方式,但已然不同于传统的哲学理性的先在性逻辑。可以说,阿多诺冒着走向绝对否定的理论漩涡的风险来反抗压抑性的社会,也反抗着哲学理性本身。
虽然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生长有其哲学基点,但是,由于他们以社会批判立论,这就决定了其对哲学理性的态度必然是进行一种合法化的“驱逐”,这在阿多诺的观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自17世纪以来,伟大的哲学把自由确定为它最特有的兴趣。哲学有一种来自资产阶级的未明说的使命,即为自由找到显而易见的基础。哲学这种兴趣本身是对抗性的:它反对旧的压迫,却助长了新的压迫,而这种新的压迫就隐藏在合理性原则本身中。人们为自由和压迫寻找一个共同的公式:把自由割让给那种限制自由的合理性,把自由从经验中清除掉,人们甚至不想看到自由在经验中得以实现。”③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相对于康德对自由的意志性规定,阿多诺更乐于把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也许自由的人们也要从意志中解放出来,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个人才会是自由的。”④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262页。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批判,连其哲学理性基础也在他们的横扫之列,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他们走向感性审美之路的理论选择。
除了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和传统哲学理性之外,技术理性也进入批判理论的视野。在他们看来,“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⑤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马尔库塞也认清了技术理性对人的思想意识的钳制和束缚,马尔库塞对理性的拯救充满了失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尔库塞放弃了理性,而是说马尔库塞把理性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与当下的现实存在之间有一个鸿沟,这鸿沟只能借助感性来弥补和填充。我们不难看出,马尔库塞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是感性的存在物”的观点中受到启发,而对自身观点进行了某种修正。把过程和努力的路径寄予感性,“并不是要放弃理性和排斥理性,它的作用就是纠正理性过度畸形发展所造成的人性失衡”⑥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4页。。马尔库塞试图实现理性与感性的和解,基于这一思考,他创立了新感性思想。这种力图在技术理性压制下获取解放的新感性,其本质就是审美。
总之,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主要从“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精神控制”等视角进行社会批判,并在针砭资本主义时代之弊病的同时力图寻求人之自由解放之路。在他们对社会流弊的痛陈中也充分流露出对艺术寄予的厚望,这样,“破”和“立”结合在一起,美学价值问题在批判理论的视野中被推向了前端。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言:“批判理论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把‘审美领域’列为关于批判超越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⑦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4页。
在批判理论的语境中考察美学的价值问题,更为侧重的是艺术性以外的社会意义,着重挖掘审美对于人的救赎能量。即是说,面对如此不堪的社会现实,批判理论家们的出路选择集中于审美领域。社会批判的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们对艺术的思考始终站立在社会历史的高度。阿多诺寄希望于艺术形式的破坏力量,而这种力量并非如他所幻想的那般具有颠覆性,——这一点阿多诺是清醒的。这种状态被魏格豪斯描述为“绝望的希望”①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下册),第854页。。无独有偶,马尔库塞曾经明确表示:“在悲惨的现实只能通过激烈的政治实践加以变革的情况下,从事美学研究是需要辩解一下的。这样来从事美学研究,即退却到一个虚构的世界,现有环境只能在一个想象的领域加以变革和克服,其中必然包含令人绝望的因素,否认这一点是愚蠢的。”②马尔库塞:《美学方面》,陆梅林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254页。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整体的理论倾向而言,走入艺术的王国并非批判理论家的最终目的,对社会的批判才是他们根本的理论意图。工业文明对人的压抑性存在是批判理论产生的根由,而如何改变异化和技术理性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控制和戕害则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思索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说,转向艺术自律观念的探讨是批判理论本身的需要。
二、艺术自律与人的自由
虽然在康德那里即已确立了审美自律的价值向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自律思想是对康德的照本宣科,恰恰相反,由于批判理论的参与,与康德相比,这一思想已经成为某种变相,甚至可以说是对康德审美自律思想的某种反叛。如果说康德的自由思想同时具有“上升”和“下降”两方面的张力的话③参见张盾《“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那么与审美自律性紧密关联的道德自由肯定是“上升”思路,其“下降”思路主要应该体现为政治哲学。席勒的自由路线较之于康德则更为生动,经由席勒,法兰克福学派对自由的追求更为具体化了。因此,正是在批判理论的背景下,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艺术自律思想在具体的自由追求指向上更为明晰,甚至即使在如此具体的美学命题上都显现出革命性或政治美学的特征。
艺术自律性与人的自由问题的探讨在康德美学中已趋向深入,后世美学大致是沿着康德的思路前进的,即以主体的自由感为纽带。如果说艺术自律性能够承载人之自由的话,那么在具体的实现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二是艺术形式。作为法兰克福学派艺术自律思想的两大核心问题,“艺术与现实”指涉的仍是艺术自律性命题的外部关系;而艺术形式则是艺术自律性本身的自我关联,甚至可以说,艺术形式与艺术自律性本就是一个问题,在多个层面上两者都可以实现话语转换,这一转换的根本意义在于赋予形式以革命性力量,更好地实现社会批判和承载人之自由追求的社会性价值。虽然“艺术与现实”问题是艺术与外部的关系,但是它并不外在于艺术,用阿多诺的话来说,艺术与社会的聚合是实质性的,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也是艺术自律思想要解决的问题。
在批判理论家那里,艺术认识现实的方式不应该是照相式的或者透视的描写,“而是通过其自律的构造(法则)来表现的,这些构造被现实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形式隐藏着。”④Theodor W.Adorno,Notes to Literature(VolumeⅠ).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227.相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实反映论,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艺术与现实”问题上的观点更为复杂。首先,艺术是与现实对立的,是对现实的否定。艺术对现实的否定性在阿多诺那里是否定辩证法的具体展现,也是建立在整个批判理论对社会的否定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构成了艺术否定现实的合法性所在。正是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所以艺术只能是对过去的追忆抑或对未来的梦幻,“在世界历史上,它是一种对灾难的想象性补偿,是一种在必然性魔力下不曾实现的、或许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由”⑤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Kegan Paul,1984,p.196.。
但是,否定性也只是艺术与现实关系的一个方面,艺术还有对现实肯定的一面。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必须是现实的,必须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就是对现存生活的刻意否定——否定他的全部不合理的内容。从这一思维逻辑出发,在艺术中出现了两重现实,即那种人们对它抱以“否定”的现实(历史现实),和人们向它表示“肯定”的现实(艺术现实)。这两个“现实”之间是对立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与超越。否定与超越是同时进行的,“破”和“立”结合在一起。只有分辨出两个现实的不同意义,才能准确地理解马尔库塞的这句话:“艺术作品在谴责现实的同时,再现着现实。”⑥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句中的第一个“现实”是不合理的既存现实;第二个现实则是艺术所力图构建的理想世界。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再现现实”,被阿多诺看作是艺术所具有的约定性(promissory)。而艺术构建理想世界,也是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积极呼应。
结合“社会批判”这一价值指向,细察法兰克福学派的形式概念,就会发现其带有的革命性色彩。这一点阿多诺讲得非常明确:“虽然艺术中的形式特征不应该从直接的政治条件角度来解释,但它们的本质含义就包括政治方面。所有真正的现代艺术都追求形式的解放。……艺术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会(从另一种意义上)参与到政治中去。当然,在当前社会结构已经完全一体化的语境下,形式本身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抗议。”①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p.361 -362.这就是说,形式承担了艺术自律性的价值诉求,成为社会批判的武器。形式被阿多诺规定为改变经验存在(empirical being)的法则,这经验存在就是艺术所要否定的现实,而形式则表征着艺术所要肯定的自由。马尔库塞也认为,作为艺术自律性本身的内在构成,审美形式使艺术与“给定的东西”区别开来,这“给定的东西”正是阿多诺意义上的“经验存在”,因此,是形式产生了美学的“异在效应”,这也就意味着,艺术的批判实践是通过形式进行的。阿多诺在这一问题上是与艺术否定现实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就其一般意义上来讲,压抑性的社会现实是作为艺术的内容(或质料)出现的,虽然艺术是一种形式化的展示,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现实的清除,艺术形式包含经验存在物的本质要素。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细微差别:马尔库塞一直在强调内容如何被淹没在形式中;阿多诺却要努力表明这样一种理论倾向:作为内容之积淀的形式并非只求其本身的独立自足,内容应该在其中得以艺术化地展现。“当形式成功地恢复了积淀在其中的内容的生命力之后,才能判断其在审美意义上完成。”②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202.即使这样,阿多诺意义上的艺术还是形式,因为艺术作品对于现实内容的表达不是直接的,而是采取迂回间接的方式,并且越是以自我组织的形式来表达,其否定性力量则愈为强大。
可见,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艺术自律思想既出乎艺术之外,又是入乎艺术之中的。所谓“出乎艺术之外”是指他们从压抑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人的不自由出发,用艺术自律性印证着人的自由;“入乎艺术之中”则是指他们把艺术自律性与艺术形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艺术自律性与艺术形式凝结成为一个问题,在阐扬形式专制、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中,艺术自律得以完满实现,艺术在形式铺就的光明大道中抵达“自由王国”。可以说,艺术在自律性问题上的纠结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美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他们认为实现社会批判的他律性目的必须内化于形式专制的艺术自律性中方能更好地实现;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艺术自律性的异质契机(heterogeneous moment),这一异质性因素在否定艺术自律性的同时也成就了艺术的自律性。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艺术自律性作为一个美学命题的复杂性。
三、现代艺术与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对艺术史的观照和对社会文化现象和趋势的审视是其艺术自律思想的一大理论特色,具体而言,这一理论特征呈现为“一个肯定和一个否定”。“一个肯定”指的是对现代艺术的推崇,把这种艺术风格作为自身美学价值诉求的承载。自然,这种艺术史的对应是建立在对古典、现代及后现代艺术的纵向参照中完成的。“一个否定”即对文化工业生产下文化产品的责难,这一批判的视角是双重的:一是就大众文化的制造目的和生产流程来说,较之于精英艺术,其艺术趣味的通俗化伴随的是艺术性的大打折扣;二是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把文化工业看作是资产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精神控制的一种手段,从价值维度的自由追求来考察,进而把其当作文化批判的靶子。
可以说,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现代艺术的推崇是对其艺术自律思想的一种赋形实践。这首先在于,他们认为现代艺术所要表达的正是对既存现实的否定,是对社会的抵抗和颠覆。这就与他们在艺术与现实的否定性关系方面相互印证。甚至于在阿多诺看来,先锋派是当代世界的仅有可能的真诚表现。因为对于他来说,“先锋主义艺术是一种彻底的抗议,它反对与现存一切的任何妥协,因此是仅有的一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艺术形式”③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8页。。超现实主义艺术对外在文明所建现实的否定和对艺术再造另一现实这一伟大力量的肯定,正是马尔库塞艺术功能论的考察依据;而处于现代社会中的现代艺术,如何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出现于这一虚假的、不合理的现实之中,又如何能揭示社会历史的真理性内容,业已成为阿多诺全部艺术哲学的核心问题④See Lambert Zuidevaart,Adorno’s Aesthetic Theory:The Redemption of Illusion,Cambridge:Mass.& London:The MIT Press,1991,p.xx.。这不仅是对现代艺术的发问,更是对艺术自律价值指向如何实现问题的探索,并且,其对现代艺术的形式批评回答了这一问题。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借用一种隐蔽的形式让社会进入了自己的境域,这样就保留了艺术的固有禀性。但是阿多诺同时又指出:“超现实主义概念必须回到它的艺术技巧,而不是回到心理学。”①Theodor W.Adorno,Notes to Literature(VolumeⅠ),p.87.
总体来看,现代艺术虽然已经脱离“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旨趣,但仍然是一种艺术自律性的实践。理查德·沃林将先锋派艺术的本质特点描述为“去审美化自律艺术”,这本身即已彰显了现代艺术作为新的艺术自律维度之表征所迥异于以往艺术自律传统的地方,也更鲜活地体现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性。只是,需要对“去审美化自律艺术”作出进一步阐释的是,“去审美化”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姿态;而艺术的自律性仍然会促成审美的达成。再用更为折中的说法就是,虽然先锋派艺术对艺术形式具有破坏性,它却仍然没有越出马尔库塞或阿多诺对艺术所做出的界定范围,“因为它的激进的或‘进步的’影响依然取决于它能够使业已建立的艺术形式去熟悉化。与此同时,这种艺术‘坚持它的激进的自律’,因此对生活保持一种批判的、‘意识形态上充分的’距离”②理查德·墨菲:《先锋派散论——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后现代问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因此,现代艺术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艺术自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某种契合。
当然,无论是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所代表的批判美学的艺术自律思想,还是现代艺术所体现出的艺术自律观念,所抵抗的不仅仅是压抑性的社会现实,还有艺术的商品化。这突出表现在其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文化工业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是技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和人与时代的精神状况密切相关,特别是当文化作为一种工业领域被政治资本家控制之后,文化工业的控制力已成为批判理论家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
坚持艺术自律性本身就是对艺术的尊重,没有了这种尊重,艺术性也无从谈起。艺术作品的不可复制性是传统艺术的主要特征,而机械复制时代则打破了这一艺术惯例,同时也就打破了艺术的灵韵,当千千万万个艺术品以同样的面目出现于千家万户的时候,艺术的光晕会因为普及而变得廉价。这种艺术精英主义的姿态不仅是批判美学家所独有的情结,也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接受传统。如果文化消费成为文化工业的基本环节,商品逻辑必将成为文化生产的第一准则。虽然文化工业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但是这种需求不是以提升自身为目的的真正需求,而是一种虚假需求。因此,商品市场下的文化生产在导致艺术庸俗化的同时更导致了对人的压抑,这两者是相关的——庸俗化的大众文化不具备自律性艺术带来的审美升华,因为“审美升华的秘密就在于,它所代表的是背弃的诺言。文化工业没有得到升华;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压抑”③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126页。。
应该说,文化工业与艺术自律性之间的冲突还是艺术制作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对立。一直以来,艺术性的展现是一种个人才能的施展,艺术创作过程是自由而个性化的过程;而在文化工业中,“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社会劳动越是客观的和有组织的,对艺术作品而言就越显得空洞和格格不入”④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147.。此外,就大众对文化工业的迎合心态进行分析,固然是一种“虚假”的需求,却成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文化消费对象。正是在这种“必要性”上,阿多诺发现了问题所在。在他看来,艺术属于自由王国,“假如用必要性表示艺术的特征,那就会使交换原则超出其经济领域得以扩展,屈服于市侩从艺术中获得什么实惠的愿望”⑤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356.。想从艺术中得到什么实惠的要求,自然不是艺术自律性的表现,而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消费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赋予艺术或经济创收或消遣娱乐的他律目的。
总之,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现代艺术的肯定和对文化工业的否定,使其社会批判这一激进的美学锋芒毕露无遗,更使其艺术自律思想有了艺术史的依托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参照,本身也是对其艺术自律观念的一种充实和丰富。只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免质疑的是,在阿多诺的理论中,具有自律性的现代艺术在张扬批判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分化”的后果。现代艺术的精英主义特征,实质上催生了它所不屑的大众文化工业,这正是现代艺术在理论追求与实践效用上的悖论之处,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在艺术自律性主张上的尴尬,这一尴尬使得先锋艺术羞于自身的批判效果。
从康德经由席勒,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自律思想,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艺术自律观念价值论维度的理论线索。如果说“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可以精准地概括这一理论轨迹的话,那么必须重申的一点是:“革命的美学”必然以“美学的革命”所确立的艺术自律规范为前提才能彰显其革命性。具体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自律思想,虽然以社会批判为理论背景,以人的自由解放为价值诉求,但是并没有湮灭康德以来的艺术自律准则,而是以此为前提来展开其革命性诉求。他们并没有摆脱康德审美自律的理论框架,即道德自由的价值是以审美自律为基础的,前者的实现乃是后者的一种事后效应。这一坚持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康德对道德自由的价值寄托,还是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鲜明的自由解放追求,说到底是艺术的他律因素。如果没有自律性的前提,这些价值诉求本身就会成为对艺术自律性的否定。
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批判视角形成的审美理论模式,并没有以牺牲艺术本身为代价,相反,正是艺术自律思想这根红线贯穿始终。对这一问题的厘清和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通过以艺术自律思想为中心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体系的批判性考察,一改批判理论在艺术批评问题上他律论的单一面相,康德和席勒的美学传统在此有了承续。其次,当我们回到美学发展的中国语境,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美学转型,不难发现这其中存在追随并迷失于西方美学思潮的弊病。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地面对审美的诸多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并没有及时彻底地消化吸收中西美学理论遗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具有时代感的美学理论建构,可以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走出康德,而不是否定康德。“走出康德”是因为自律性思想也只是艺术理论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内容;而作为审美标准的自律性在艺术世界中仍然会有它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当下西方审美主义传统再次萌生的缘由,因此,艺术自律性只会被超越而不应被否定。无论是作为背景还是被推向前台,关切人之自由这一深沉主题的艺术自律问题的讨论势必会成为当下中国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部分,时下关于艺术语言研究的风行就是很好的例证。对此,我们充满了期待。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艺术自律性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