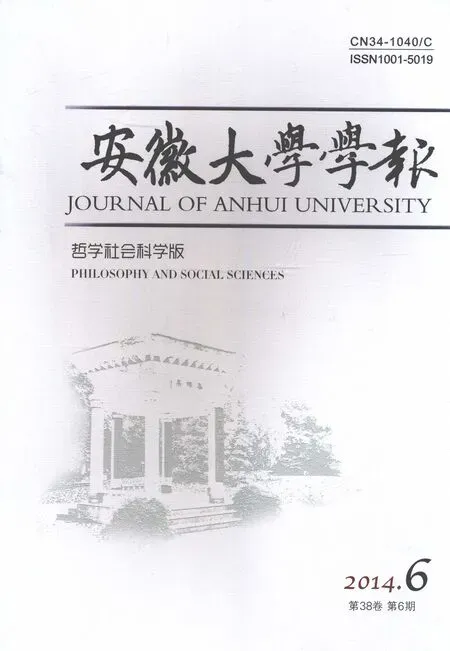以古文为时文: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时文改良
师雅惠
谈论桐城派的文学活动与文章理念,“时文”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一直以来,学界对桐城派时文的关注,集中在时文创作是否拉低了桐城派古文的水准,也即“以时文为古文”的方面,而对桐城派作家“以古文为时文”的努力,却缺乏客观的论述及评价。与姚鼐等桐城派后期作家不同,戴名世、方苞等桐城派早期作家大多在时文界享有盛誉,写作、评选时文,贯穿了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段,而时文也成为他们宣扬自身文学主张的重要阵地。本文即试图通过对桐城派早期作家从事时文改良的文学史背景、思想立场与具体方法的论述,揭出他们的时文活动中所蕴含的“文人”与“文章”因素,以期对桐城派兴起时期的文学史细节进行补充描画。
一、晚明文坛的“以古文为时文”
时文向古文学习,自有“时文”之时即已开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0页。可见有宋一代,“古文”一直是科举文体的重要取法对象。明代的“以古文为时文”,则有前后两个兴盛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正德、嘉靖年间,以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文人为代表。归、唐将古文家的手眼代入时文,所作文章,能“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显隐曲畅”②方苞:《进四书文选表》,《方苞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80页。,向被视为“以古文为时文”的典范。第二个时期则是在万历以后。隆庆、万历年间,时文在义理阐释与行文风格两方面均发生变化。义理方面,以隆庆二年会试,《论语》程文阑入王学为始,时文文义须遵从朱熹《章句》及官修《大全》的科场定规渐为人所忽视,所谓“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③转引自顾炎武《科场禁约》,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59页。,时文中朱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在文辞方面,以万历十四年会试主考王锡爵喜好“新奇”之文为始,时文写作逐渐出现“文胜于质”的局面,吕留良描述这一现象是“杜撰恶俗之调,影响之理,剔弄之法,曰圆熟,曰机锋,皆自古文章之所无”①吕留良:《东皋遗选前集论文一则》,《吕晚村先生文集》卷5,第36页,清雍正三年吕氏天盖楼刻本。。这种义理和文辞两方面的乱象,虽曾引起朝廷的重视,万历年间,礼部关于科场之文应“纯雅合式”、“平正通达”的申饬,即有十余次之多②参见吴柏森等编《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296、299、302、309、320、324、333页。,但其成效并不理想。崇祯六年,凌义渠上《正文体疏》,认为当日时文,仍多“纵横险轧之言”、“危苦酸伤之词”、“妖浮纤眇之音”、“欺己欺人之语”③凌义渠:《正文体疏》,凌义渠《奏牍》卷2第10页,明崇祯刻本。,远离平和质朴的文章正轨。庙堂之上不能转移廓清,于是一些草野人士开始谋求以一己之力维挽风气。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启、崇祯年间的复社二张兄弟与江西豫章社艾南英、陈继泰等人。他们所采取的救弊之方,也是从古文寻找资源,即艾南英所说的“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④艾南英:《金正希稿序》,《天佣子集》卷3,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年影印本,第329页。。
尽管张氏兄弟与艾南英在论文主张上有分歧,但对“通经学古”的大前提,双方并无异议。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学什么样的“古”的问题。复社、几社诸人以秦汉古文为文章正宗,故其论时文,亦要求从秦汉文入手,“日取《五经》摹而书之,左右周接,无非钜人之名,大雅之字,趋而之善也疾焉”⑤张溥:《房稿表经序》,《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5,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1034页。。艾南英则推崇唐宋文,尤其是寓法于平淡质朴之中的宋人文字,论及时文时,亦要求士子“刊除枝叶”⑥艾南英:《王承周制义序》,《天佣子集》卷3,第369页。,“以朴为高,以淡为老”⑦艾南英:《金正希稿序》,《天佣子集》卷3,第331页。,写作平实、简劲之文。因此这两派的分歧,只能算是“以古文为时文”阵营之内的矛盾。较之复社诸人,豫章社对当时时文文坛的影响要大得多,艾南英曾说自己编选的《今文定》、《今文待》刊行七年后,士子作文,“一禀程朱”,且开始学习“宋元及国初以来作者之意”与“秦唐汉宋文章相沿之法”,文坛气象为之一变⑧艾南英:《增补今文定今文待序》,《天佣子集》卷1,第137~140页。。然而艾氏恢复成、弘时期浑朴之文的理想,并未实现。他所极力称赏的“朴淡”的金声文,在后人眼中,却是“鹜八极,游万仞,使题之表里皆精神所发越也”⑨何焯:《两浙训士条约(代)》,《义门先生集》卷10,第7页,清道光三十年姑苏刻本。,走的仍是奇矫一派说理曲畅刻露的路子。又如他的豫章社同仁陈继泰之文,亦被后人描述为“抉其髓而去其肤,摹其神而尽其变”,“纵横排荡,时轶出先辈之法之外”⑩戴名世:《陈大士稿序》,《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4页。。时文的“先正之体”,并未恢复,后来者仍任重而道远。
二、文人与文章的独立性:桐城早期诸家时文改革的基本立场与主要活动
对于时文,桐城早期诸家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并非纯粹的时文家,写作时文以求取功名,并不是他们的初心。如戴名世自幼留心前朝史籍,二十以后,“家贫无以养亲,不得已开门授徒,而诸生非科举之文不学,于是始从事于制义”⑪戴名世:《意园制义自序》,《戴名世集》,第123页。。方舟少时喜好兵学、史学,十四岁后,自叹“吾向所学,无所施用”,于是学作时文,以求获得“课蒙童”的资格,来贴补家用⑫方苞:《兄百川墓志铭》,《方苞集》(下),第496页。。方苞幼承父兄之教,“诵经书”,“治古文”,后亦因“家累渐迫”,而走上了教馆、作时文的道路⑬方苞:《与韩慕庐学士书》,《方苞集》(下),第671页。。戴、方的友人汪份,为古文家汪琬之从侄,“古文辞深得司马、欧阳家法”,从事时文写作,亦是“抑郁不得志”的无奈之举○13戴名世:《汪武曹稿序》,《戴名世集》,第100~101页。。这种“非其所习,强而为之”①方苞:《与韩慕庐学士书》,《方苞集》(下),第671页。的不愉快经历,使得他们多不愿提及自己在时文方面的成就,如戴名世说自己的时文“无得于己,亦无用于世”②戴名世:《自订时文全集序》,《戴名世集》,第118页,,方舟“自课试之外未尝为时文”③方苞:《刻百川先生遗文书后》,《方苞集》(下),第631页,,方苞少年时亦常欲舍弃时文之业,“以一其耳目心思于幼所治古文之学”④方苞:《与韩慕庐学士书》,《方苞集》(下),第672页。,而另一方面,出于生存的需要以及对文事的责任感,他们又未能完全放弃时文,而是试图将他们少年时的学问抱负投射到时文活动中来,对现有的时文进行改良与提升。
在戴名世、方苞等人看来,当日时文的弊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文章写作目的的功利性。如方苞曾言:“夫时文者,科举之士所用以牟荣利者也。”⑤方苞:《储礼执文稿序》,《方苞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6页。戴名世也说:“今夫士之从事于场屋,不以得失撄其念者,自非上智不能,其余大抵皆欲得当于考官也。”⑥戴名世:《孙芑山制义序》,原文见《南山文集外编》清钞本,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2页。以“得中”为写作的目的,于是时文完全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这可以说是时文品质败坏的根源。
二是文章个性的缺乏,即戴名世所言的“雷同剿袭”⑦戴名世:《己卯科乡试墨卷序》,《戴名世集》,第95页。。文辞的“雷同”,源于作者没有坚定的见解与独立的人格。如戴名世《忧庵集》中记述,当日时文有一种“为吉祥冠冕之辞,不必与题相切”的颂圣套子。时文乃代言体,而“以百世之前之圣贤,预颂百世之后帝王之功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套路,并不合时文体制。但因近日考官欣赏此种体式,“会试往往以此为定元魁之格”,众人便纷纷从而学之。这种“趋同”,正是时文作者在功名面前,“丧失其所以为心”,不复考虑文辞本身尊严的结果⑧参见戴名世《忧庵集》第66条,《戴名世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6页。。
三是文章法度的卑陋。戴名世认为,世俗之徒以“以古文为时文”为过高之论,而他们所推崇的时文之法,不过是“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与“根柢乎圣人之六经,而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的古文之法,“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此种世俗文法的盛行,使得时文、古文两道均萎靡不振:“吾谓古文之亡亡于时文,而时文之亡亡于竖儒老生。”⑨参见戴名世《甲戌房书序》,《戴名世集》,第88~89页。
针对上述弊病,桐城早期作家们继承了前人“以古文救时文”的思路,如戴名世《汪武曹稿序》所言:“顷者余与武曹执以古文为时文之说,正告天下。”⑩戴名世:《汪武曹稿序》,《戴名世集》,第101页。而他们“以古文为时文”的改良,并不仅仅停留在文章技法上,而是涉及从人心到文辞的多个层面。在作者人格的层面,他们提倡时文作者不慕世俗功名的品格:“夫读书之有成者,不必其得当于制科,虽以布衣诸生,萧然蓬户,而功名固已莫大乎是焉。”⑪戴名世:《蔡瞻岷文集序》,《戴名世集》,第79页。不以世俗功名为意,则作文时“必不肯鲁莽灭裂以从事,而得失之数不以介于心”⑫戴名世:《李潮进稿序》,《戴名世集》,第105页。。在文体价值的层面,他们认为时文同古文一样,具有明道的功用,所谓“时文之是非关人心之邪正”⑬戴名世:《汪武曹稿序》,《戴名世集》,第100页。,并希望士子能够“由举业而上之为古文辞,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圣人之大经大法”○13戴名世:《己卯科乡试墨卷序》,《戴名世集》,第96页。。在文章作法的层面,则提出古文之法可用于时文:“夫所谓时文者,以其体而言之,则各有一时之所尚者,而非谓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为之也。”⑮戴名世:《甲戌房书序》,《戴名世集》,第88页。可以看到,这三个层面,均指向对时文“功利”属性的剥除,与对时文“文章”属性的凸显,这一点,可以说是桐城早期诸家时文改良活动的基本立场。
对时文的“文章”属性的强调,体现在桐城早期诸家的时文创作中,即是坚持以古人之文、先辈之文为标杆,不作世俗之文。戴名世友人刘捷回忆说:“方壬子、癸丑(即康熙十一、十二年——作者注)间,海内溺于时文之学,而鸷骜自强不肯仿效者,独吾乡人为多。吾兄北固与戴子褐夫辈,发愤于故里,而余与百川兄弟,淹滞金陵,穷愁无聊,刻意相勖以古人之文,一时时文之士,讪侮百出。”①刘捷:《方百川遗文序》,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第43页。可知桐城早期诸家在甫接触时文之时,即立场鲜明地站到了“古人之文”的一面。此后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朱书、汪份、何焯、刘岩、刘齐等以拔贡生的身份入太学。康熙三十年,方苞亦入太学。在风景与江淮殊异的京师,戴名世“以其平日所窥探于经史及诸子者,条融贯释,自辟一径以行”②戴名世:《自订时文全集序》,《戴名世集》,第117页。的时文,得到了诸位友人的赞赏,据戴氏回忆说:“余自入太学,居京师及游四方,与诸君子讨论文事,多能辅余之不逮…同县方百川、灵皋、刘北固,长洲汪武曹,无锡刘言洁,江浦刘大山,德州孙子未,同郡朱字绿,此数人者,好予文特甚。”③戴名世:《自订时文全集序》,《戴名世集》,第118页。之后,戴名世、方舟、方苞分别于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三十四年、康熙三十八年刊刻自己的时文集,并受到时任礼部尚书的时文名家韩菼的推重。韩菼认为戴名世之文,“视一第如以瓦注”④韩菼:《戴田有文序》,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第402页。,又极力推崇方氏兄弟的时文,认为方苞文乃“近世无有”,方舟文则是“融液经史,纵横贯串而造微入细,无一字不归于谨”⑤韩菼:《方百川文序》,《有怀堂文稿》卷5,第14页。。而以如此声望,他们的科场之路却并不顺利,戴名世、方苞分别于康熙四十四年、康熙三十八年中举,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四十五年方得以中进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文字的不趋时,如韩菼在方苞会试落第后的赠诗所言:“春衫底泥萋萋色,只欠新来时世妆。”⑥韩菼:《方灵皋解元落第二首》,《有怀堂诗集》卷5,第10页,清康熙刊本。
作者身份之外,桐城早期诸家又大多身兼时文评选者的角色。据萧奭《永宪录》记载,戴名世及其友人汪份、何焯,均是康熙一朝的著名选家⑦萧奭:《永宪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9页。。作为选家,诸人亦表现出对时文“文章”质素的特别关注。在《九科大题文序》中,戴名世赞扬晚明选家艾南英能在“文妖叠起”之时,“昌言正论,崇雅点浮”,清初选家吕留良亦能“为学者分别邪正,讲求指归”,“摧陷廓清,实有与艾氏相为颃颉者”。而他自己则意欲继承前人“正文体”的事业:“余为编次是集,以补吕氏之所未及……而艾、吕两家之绪言,犹可于此书得之也。”⑧参见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戴名世集》,第101~102页。而选家如何“正文体”?一是提倡“古之辞”,如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戴名世强调士子作文,应沉酣于包括“《左》、《国》、庄、屈、马、班及唐宋大家之为之者”在内的“古之辞”,而尽去“怀利禄之心胸之为之”的“今之辞”⑨戴名世:《己卯行书小题序》,《戴名世集》,第109页。。二是提倡“先正之文”。戴名世认为,时文虽然风尚屡变,但“屡变之时,辄有不变者存”。此“不变”者,包括“理取其精深”、“法取其谨严”、“辞取其雅驯而正大”等,而这些因素,均能在“先正之文”中找到⑩参见戴名世《宋嵩南制义序》,《戴名世集》,第113页。。因此,在“新科利器”之外,诸人还注重前代大家之文的编选,如戴名世曾选康熙乙卯到庚辰间会试墨卷为《九科大题文选》与《九科墨卷》,又选有明一代小题文为《有明小题文选》,汪份曾选明隆庆、万历间文为《庆历文读本》。在《庆历文读本序》中,戴名世指出,隆庆、万历两朝文章,“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此后虽亦有作者兴起,而“其源流旨归,未有不出于先辈者”,因此,“为文而不本之于前辈,则必破坏其体,灭裂其法”⑪戴名世:《庆历文读本序》,《戴名世集》,第106页。。艾南英曾认为时文中亦有时、古之分,“以出于近科,纤俊软腐者为时文,而出于先辈,能根据经史理学,高伟朴拙、杰然自名一家者为古文”①艾南英:《王承周制艺序》,《天佣子集》卷3,第367~368页。。戴名世对先辈时文的推崇,与艾氏的观点类似,可看作是艾氏向“古之辞”学习的思路的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与戴名世所推崇的前代选家艾南英、吕留良相较,桐城早期诸家的时文评选,更多只是一种“文字事业”,而无深刻的附加意义。如在对待时文文献的态度上,艾南英说自己《今文定》、《今文待》的编选,是为了“存一代之文”②艾南英:《再与周介生论文书》,《天佣子集》卷5,第515页。。吕留良晚年留心搜集有明三百年之程墨、大家文稿及“布衣社稿”,准备编一部《知言集》,亦是要以时文存一代之史③参见《吕晚村先生文集》卷1《与施愚山书》、《与钱湘灵书》,卷2《与某书》、卷3《与董方白书》诸篇。。而戴名世虽曾编选《有明小题文选》与《九科大题文选》等时文总集,但其选文目的,只是给士子提供写作参考,希望士子“一意讽诵研穷于此书,则人人皆顾、陆也”④戴名世:《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戴名世集》,第100页。,并无沉重的史家意识。又如在对时文义理的阐释上,吕留良在清初以时文讲理学,“在彼之意,实欲拔赵帜,立汉帜,借讲章之途径,正儒学之趋向”⑤钱穆:《吕晚村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143页。。而戴名世虽亦推尊程朱,认为宋儒对四子书的阐发“无不达之旨”⑥戴名世:《己卯科乡试墨卷序》,《戴名世集》,第95页。,但其关注点,并不在朱学、王学之辨,现存戴氏文集中所收多篇时文选本序,着力辨析的主要是“古文之法”。这种对“文事”的侧重,固然使得他们的议论缺少一些厚度与深度,但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能从时文的政治与学理背景中跳脱出来,专一精细地展开对文章本身的探讨。
三、表现性情:桐城早期诸家“以古文为时文”的具体操作方法之一
桐城早期诸家的“以古文为时文”,在具体操作方法上,主要有将作者性情代入时文与提倡文章“活法”两个方面。以下分别论述之。
乾隆间学者焦循认为,表意功能的差异,是时文与古文的重要区别:“古文以意,时文以形,舍意而论形则无古文,舍形而讲意则无时文。”⑦焦循:《时文说二》,《雕菰集》卷10,第20页,清道光岭南节署刻本。而桐城诸家则试图打通时文与古文在表意上的界限。他们极为强调文辞与作者情怀的关系,如戴名世认为:“人之心之明暗、善恶、厚薄,其著之于辞者,皆不能掩,是故观其文可以知其人焉。”⑧戴名世:《忧庵集》第160条,《戴名世遗文集》,第137页。方苞也认为:“自明以四书文设科,用此发名者凡数十家,其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⑨方苞:《杨黄在时文序》,《方苞集》(上),第100页。作者有希圣希贤的品格心胸,代圣人立言,才能“修辞立其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时文可以表现作者的志向与性情。
在用时文表达性情这一点上,桐城早期诸家中成就最高者,当属方苞之胞兄方舟。方舟曾言自己作时文,只求“自知”:“凡吾为文,非求悦于今之人也。吾有得于天地万物之理,古圣人贤人之心,吾自知而已。”⑩《自知集》刘捷序,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第308页。因此,他的文章,多能借题发抒己意。夫子之世,夫子不得行其所学,方舟平生留意经世之学,“以万物之不被其功泽为忧”⑪参见方苞《与慕庐先生书》,《方苞集》(下),第674页。,然亦无机缘实施,因此其文凡涉及圣人心事,便极为深情绵邈。如《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一文中、后比:
视其上则无国而不乱,视其下则无人而不矜,长与之共处于域中,非目见其人,即耳闻其事,跔蹐者自顾岂有穷期耶?
视其国则皆有可以清明之理,视其民则皆有可以仁寿之形,第惄然坐观于局外而于此焉,嵩目于彼焉,怆心栖皇者,岂能越于人境耶?
夫事之无可奈何者,徒转以自苦无为也。而情之不能自决者,非以计断之不可也。
使吾身而犹在人群之中,虽百虑其无成,终接时而心动,儳然将以终身。
使吾身而已在遐荒之外,则怀忧而莫致,虽欲拯而无从,此中亦庶几少释。①方舟:《道不行,乘槎浮于海》,方观承辑评《方百川先生经义》上册论语卷第12、13页,清乾隆刊本。
《集注》于此题,引程子语:“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此文则并不限于感叹无贤君赏识,而是着力描绘夫子对不可挽回之时势与身处此时势中之民众的悲悯。夫子逃世之想,看似超脱,实则无可奈何,方舟将此一层款曲,揭示得十分动人。
又如《子路宿于石门章》中两大比:
盖其心知世不可为,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而又未尝不顾滔滔者,而心恻也。以己之不复能忍,而愈知吾子所为之难,故一旦与吾徒邂逅风尘,而不禁于局外发伤心之语,盖其声销而志无穷矣。
抑其心知世不可为,度不能以幽人之贞,逮三代之英,而又未尝不愿斯世有斯人也。以己之绝意于斯,而愈望吾子为之之切,故不能自隐其平生之心迹,而殷然以一言志相属之诚,盖其自计审而其忧世愈深矣。②方舟:《子路宿于石门章》,《方百川先生经义》上册论语卷第48页,清乾隆刊本。
与《集注》取胡安国语,认为晨门“以是讥孔子”的意见不同,方舟此文着力抉发晨门与夫子心事的相通处,晨门虽隐,但不能忘情世事,亦欣见世上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之人。此种体察,正源自方舟心中所有,如檀吉甫所评:“悃款如知己,亦缘百川夙抱忧世心肠,不觉体贴到此。”③转引自梁章矩《制义丛话 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
方舟之外,桐城早期诸家的时文文风大多能肖其性情。方苞为人不偕于俗,其文亦深刻峭劲,有耿介绝俗之风调,如《子曰岁寒章》起讲:“且人世何知,受知之分,惟吾自决耳。吾急欲人知而人竟知矣,吾不欲受人不足轻重之知,而人亦不知矣,而亦非终不知也。其藏德深者,其收名也远,旦暮之间,嚣然自炫,虽不为一时所困,亦必无千古之荣也。”④方苞:《子曰岁寒》,《桐城方氏时文全稿·抗希堂稿》,第13页,清光绪十四年会友书局刊本。松柏不争“雨润而日喧”之时,不为“朝华而夕秀”者所动,无论世人知与不知,其坚贞之质均无毁无伤。这种阐释,较之朱注对“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的强调,更深入一层,也更合于松柏高洁之身份。又如朱书,性情豪放,与朋友交游,可以“酣嬉终日,解衣盤礴”⑤方苞:《朱字绿墓表》,《方苞集》,第346页。。因此其文亦平实通脱,较少凌厉之气,如《子使漆雕开仕》中二小比:“吾夫子忧世之切,虽莫宗而犹欲大行其道,即为兆而亦且小试其端,此意固在仕也。吾夫子乐天之深,虽王天下而不与存,即遁世不见知而亦不悔,此其意又并不关仕也。”⑥朱书:《子使漆雕开仕》,《朱书集》,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93页。写夫子在出处问题上平和安详的心态,与二方兄弟笔下常见的凄怨之音不同。上述诸例,虽在唱叹委婉、“寄情遥深”⑦参见孔庆茂《八股文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25页。的方面,不及方舟,但都能以明畅之笔抒发个人心得,不为雷同之语,可称得上是具有真性情的文字。
四、文成法立:桐城早期诸家“以古文为时文”的具体操作方法之二
“文成法立”,首先是桐城早期诸家所认可的古文写作之法。如戴名世认为,文章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运用之妙成乎一心,变化之机莫可窥测”⑧戴名世:《史论》,《戴名世集》第405页。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中,既对“两两相映”、“隐括”、“以虚为实”、“以实为虚”等具体笔法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讲解,又告诫读者应从整体着眼,感受文辞的“千岩万壑,风云变现,不可端倪”⑨《鄢陵之战》总批,王兆符、程崟传述《左传义法举要》,见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73页。处。其《史记评点》,既讨论“侧入逆叙”、“夹叙”、“牵连以书”、“虚实之法”等具体章法,又强调“纵横如意”、“义法所当然”。其《古文约选》诸评,在严格辨析不同文体的独特作法的同时,又多次论及文章之“气”、“气象”、“文境”,表现出对文章整体美感的关注。可见戴、方等人,对古文法度,有极为灵活通脱的阐释。对初学者、中才之人,注重讲明文章基本的写作技巧,即“死法”,而对已有一定基础者,以及天才之人,则提醒他们注意神妙变化的“活法”。
与对古文作法的理解类似,在现存桐城早期诸家关于时文文法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强调时文写作的具体技术,如戴名世、刘岩都注重小题文。小题文之题,皆割裂经文而成,虽不能阐发大义,但这种文题,在写法上限制颇多,对士子熟练掌握时文法度极有裨益。因此戴名世建议士子在初学时文时,多作小题文,“惟久而熟焉于小题,而大题已举之矣”①戴名世:《甲戌房书小题文序》,《戴名世集》,第90页。。刘岩也认为,小题文可以开作者混沌之心,使其“披豁呈露”,下笔为文,则能变化多端,引人入胜②刘岩:《小题立诚集序》,《匪莪堂文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70页。。另一方面,他们又好谈论“文气”与“文境”,如戴名世多次谈到“自然成文”:“今夫文之为道,虽其辞章格制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此自左、庄、马、班以来,诸家之旨未之有异也,何独于制举之文而弃之。”③戴名世:《李潮进稿序》,《戴名世集》,第105页。他曾描述自己作文的情景说:“每一题入手,静坐屏气,默诵章句者往复数十过,用以寻讨其意思神理脉络之所在,其于《集注》亦如之。于是喉吻之际略费经营,振笔而书,不加点窜。”④戴名世:《意园制义自序》,《戴名世集》,第123页。这正是“率其自然而行其无所事”的状态。又如方苞在乾隆初年奉敕编选的《钦定四书文》中,亦大力表彰流畅、浑整之文,如评王鳌《桃应问曰章》:“化累叙问答之板局而以大气包举。”⑤《钦定四书文·化治文》卷6,第20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评归有光《多闻阙疑 二节》:“显白透亮,而灏气顿折,使人忘题绪之堆垛。”⑥《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2,第13页。评唐顺之《牛山之木尝美矣 二节》:“依题立格,裁对处融炼自然,有行云流水之趣。”⑦《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6,第28页。诸评均从文章整体气息着眼。
对时文整体气息的关注,明代正、嘉之时即已出现,茅坤在专门论述时文作法的《论文四则》中即特别列出“布势”一条,认为“势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得其势则相题、言情如风之掣云,泉之出峡,苏文忠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⑧茅坤:《论文四则》,转引自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334~335页。。此“势”也即桐城诸家所说的“文气”。但茅坤并没有详述得“文气”的方法。规制严格的八股时文,如何能做到浑灏自然?对此一问题,戴名世在《丁丑房书序》中,认为文章写作不应有文法上的预设:“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循题位置”的“铺叙”与“相题之要而提挈之”的“凌驾”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文章采取哪种叙述结构,应根据题意而定,能“扼题之要而尽题之趣,极题之变,反复洞悉乎题之理”⑨戴名世:《丁丑房书序》,《戴名世集》,第93~94页。。即可算得上好文章。方苞在《钦定四书文》中,同样强调题目之“义”对“法”的决定性作用,如评唐顺之《此之谓絜矩之道 合下十六节》:“法由义起,气以神行,有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之乐…循题腠理,随手自成剪裁。后人好讲串插之法者,此其药石也。”⑩《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1,第11、12页。又如评瞿景淳《天子一位 六节》:“以义制法,文成而法立,整练中有苍浑之气,稿中所罕见者。”⑪《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6,第17页。瞿景淳是明代时文机法派的代表人物,方苞对瞿氏文章整体评价并不高,认为其“殊不远时文家数”,此处特别表彰其“以义制法”的篇目,亦可以见出方苞对不顾题意、一味调弄法度的做法的贬斥。总之,在戴、方看来,“法以义起”、“文成法立”,不仅是古文写作准则,而且同样适用于时文,惟其如此,时文才不再是拼凑字词的文字游戏,而是具有内在气韵的“文章”。
五、结 语
“以古文为时文”,虽非桐城早期作家的首创,但在这一口号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上,桐城诸家的贡献却不可忽视。虽然由于《南山集》案的影响,戴名世、朱书、刘岩等人的文章,在康熙五十年以后被禁止刊行,逐渐湮没不彰,但从这场文字狱中侥幸逃脱的方苞,以及方苞早逝的兄长方舟,终清之世,都被认为是“以古文为时文”的代表作家。二方富含文学意味的时文,不仅受到桐城派内部人士的称赞,如吴敏树于时文“独高明之震川归氏,及我朝方舟百川,以为超绝,真得古人文章之意”①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吴敏树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75页。,曾国藩认为方苞得“八股文之雄厚”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读书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368页。;而且得到桐城派之外的文人的推尊,如翁方纲说:“桐城两方子,喻彼马与指。时文即古文,使我心翘跂。”③翁方纲:《次东墅纪梦韵叙述江南当代人文之盛用志鄙怀》,《复初斋外集》诗卷13,第17、18页,民国嘉业堂从书本。梁章钜也认为方苞时文“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故集中篇篇可读”④梁章钜:《退庵随笔》,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502页。。而经由戴名世、方苞等人的时文评选而得以细致、深入的“以古文为时文”的方法与理念,在士子中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戴名世、方苞之后,文坛上的“时文古文一体论”仍不绝如缕,如吴玉纶认为,在“有物有序”方面,“古文与时文异源同流”⑤吴玉纶:《试谕一则》,《香亭文稿》卷12,清乾隆六十年滋德堂刊本。;张文虎认为“志古人之志以为时文,即亦何异于诗古文词”⑥张文虎:《妙香斋集序》,《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第57页,清光绪刊本。;俞樾也认为:“以古文为时文,其时文必佳矣。”⑦俞樾:《孙丱庵试帖诗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9,第7页,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春在堂全书本。这些意见,都可以视为桐城早期诸家“以古文为时文”的回声。
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看,桐城早期诸家“以古文为时文”的时文改良,对他们的古文事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的一面,首先是诸人“以古文为时文”理念在创作中的成功实践,以及在此理念指导下编纂的诸种时文选本的流布,有助于提升他们在文坛的知名度,对他们古文理论的传播亦不无裨益。其次,对时文取法古文的具体方法的探究,促使他们对古文文体功用及写作方法进行深入思考,有助于他们古文理论的形成与完善。而消极的一面,主要在于时文篇幅窄小,在义理上又限制颇多,长期致力于这种以说理为主的拘谨文字,在面对叙事性体裁时,便显得力不从心。方苞文集中多篇墓志铭,剪裁皆极有分寸,却不免失之单薄,其原因即在于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能大”的格局,除需尽力淡化时文文法的影响外,恐怕还需要来自外部思想界的变革与冲击。当时文所依附的思想条框得以松动时,文人才能够较彻底地摆脱“时文思维”与“时文语感”,桐城古文在晚清的自我蜕变,即从历史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