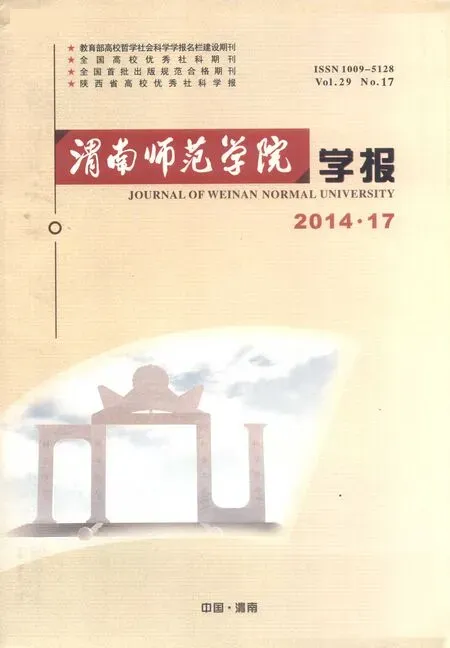“边地”与“腹里”之间:乾隆朝君臣的陕甘印象
杨军民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张掖 734000)
【历史研究】
“边地”与“腹里”之间:乾隆朝君臣的陕甘印象
杨军民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张掖 734000)
乾隆帝及西北督抚以不同的视角,对于清代陕甘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作出了较为一致的描述及评价。在专制制度之下,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的陕甘印象及由此影响下的治理政策对于陕甘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要正确认识清代陕甘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进程以及作为边地行省在全国的地位,乾隆帝及其西北督抚对于陕甘社会的认识和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在乾隆一朝六十年的时间内,甘肃虽然已由康熙时代的“边陲”变成了“内地”,但陕甘的边疆印象在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的陕甘认识中从未消除,只是在与新疆伊犁等处比较时,“内地”或“腹地”概念才出现在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的陕甘印象当中。
乾隆朝;西北督抚;甘肃;印象
在《清高宗实录》中,记载有大量与陕甘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颇有价值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来自皇帝的上谕和西北督抚的奏折。这些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从军事政治角度,论述陕甘地区在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地位,其中又包括了关于陕甘地区民族关系的内容,这一类内容较多;第二类是从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角度,对陕甘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及文化教育水平的评价,这一类内容相对较少;第三类是以农业社会的视角,在重农思想的指导下,对于陕甘社会发展农业的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看法,第二、三类内容相比于政治军事类又较为丰富;第四类是关于陕甘地域社会的风土民情、社会风尚的内容。这一类内容虽然较少,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对于陕甘社会风土民情的认识。
通过对上述上谕及奏折的分析,大体上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乾隆帝及乾隆朝西北督抚对于陕甘社会的认识及陕甘两行省在清帝国的地位。另外,为了从清代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认识陕甘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部分上谕及奏折内容也涉及到了乾隆之前的康熙、雍正及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诸帝时期。
在清代专制政治体制之下,清代诸帝和历任西北督抚对于陕甘社会的认识及由此而产生的陕甘社会印象,必然影响到清廷和陕甘督抚治理陕甘社会的政策,从而对于陕甘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了解清代诸帝及历任西北督抚的陕甘印象,对于正确认识清代陕甘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西北地区在清帝国的地位及对全国的影响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清代陕甘总督所辖之陕西、甘肃(包括今天的宁夏、青海、新疆乌鲁木齐以东至哈密的天山北路地区),几乎包括了整个西北地区,而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又是清代比较落后的地区。这种观念甚至延续到了近现代,成书于民国时期的《甘肃乡土志稿》也认为甘肃“僻处边陲,交通梗阻,土广人稀,地瘠民贫”[1]106。因此,了解清代诸帝及西北督抚的甘肃印象及由此影响下的治理政策及成效,对于了解今天陕甘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促进陕甘社会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地区在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地位
“甘肃北达蒙古,南杂番、回,西接新疆、宁夏,以河套为屏藩,西宁与撒拉相错处,为西陲奥区。”[2]4066有清一代,甘肃作为西北边疆省份,在西北边防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不特为边陲之孔道,且为中原与外番来往之枢纽”[3]12-20,军事政治地位极为重要。在乾隆帝的上谕和西北督抚的奏折中,有关陕甘地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地位的内容是最多的。从这些上谕和奏折来看,乾隆帝及西北督抚都认识到了陕甘地区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其在西北边防体系中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陕甘地区,特别是甘肃是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基地。作为新疆门户,甘肃又是经营新疆的战略通道。因此,甘肃行省在西北边防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陕甘在清代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从边防前沿到边防基地的演变,自顺治时代到康熙三十年,甘肃长期处于清廷西北边防的前沿地带,担负着防范准噶尔扩张、保卫西北边疆线的重要任务。从康熙三十年起,随着康熙帝对准噶尔军政战略的变化,甘肃作为对准噶尔作战的前沿,陕西作为对西北用兵的战略基地,陕甘地区在清帝国的战略地位陡然提升。在整个康熙时代,因为西北准噶尔问题,清帝国的西北边界只能延伸到安西、哈密一线,在这种情况下,甘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边疆要地。而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后,随着西域新疆的拓展,清廷西北边疆线已经推进到伊塔、叶儿羌一线,甘肃行省作为西北边防体系的战略支撑和军事基地,重要性更为加强。
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因为受到准噶尔的威胁和牵制,清帝国西部边疆线只能延伸到安西、肃州一线。[4]10367在这种情况下,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就成为清廷的西北边界,甘肃作为抵御准噶尔扩张的边疆前沿,受到康熙帝及雍正帝的高度重视。乾隆二十年以后,因为西域新疆的拓展,清廷西北边疆线推进到巴尔喀什湖一线。随着边疆的西扩,甘肃从康雍时期的边疆变成了内地,成为清廷经营西疆的战略基地和内地通往新疆的战略通道,在整个西北边防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在谈到甘肃在西北边防中的重要地位时,分别用了两个层次的概念。在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上,君臣一致认为甘肃地处“边地”[5]800“边荒”[6]1018“边要”[7]792“边隅”[8]961“边陲”[9]419。虽然自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广阔的新疆地区已完全纳入清帝国的版图,甘肃已从边疆区域变成了内地省份,但在乾隆帝及其西北督抚的印象中,甘肃的“边疆印象”亦未削弱。即使到了同光时代,在同治帝及湘系西北督抚的西北印象当中,甘肃仍然是“地方瘠苦”[10]36“地瘠民贫”[11]981的“边陲”[12]280之地。
在其重要性上,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经常用“隆陲要区”[13]406“边陲要区”[9]419“边陲重地”[14]675“边防重地”[15]995等语来强调陕甘地区,特别是甘肃省在西北边疆地区和西北边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但说明了陕甘地区的边疆属性,而且更强调甘肃行省作为“边陲要区”,在西北边防中的重要地位。
与边疆空间上的拓展相适应,与康熙朝相比,乾隆朝君臣的甘肃印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随着甘肃建省和西域新疆的拓展,甘肃由康熙朝的“边地”[16]842变成了“僻近边陲”[17]4的内地。随着清帝国在空间上的发展,西部边疆的延伸,甘肃由康熙时代的边疆变成了乾隆时代的内地,从地处边陲变成了切近边陲,完成了由“极边”到“内地”[18]723的转换。随着西域新疆的拓展,陕甘由边疆而成为内地,两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逐渐表现出重大差异。随着内地化向边疆地区的推进,清廷也逐步调整了陕甘地区的军政结构和治理政策。
首先是调整陕甘军政架构,以川陕总督改陕甘总督,裁撤甘肃巡抚,陕甘总督移驻兰州兼甘肃巡抚,西北军政中心前移兰州。其次是加强向新疆地区,特别是天山北路地区的移民屯垦,解决内地居民,特别是甘肃贫民生计。这一措施首先是为了解决被灾严重的甘肃贫民的生计问题。乾隆二十九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甘肃皋兰等32州县被灾,乾隆帝明令杨应琚设法开导邻近新疆之甘肃安西、肃州、甘州、凉州等地贫民,并提供车马口粮,资助其赴新疆屯种,以达“腹地资生既广,而边隅旷土愈开”之功效[19]986。再次是开始区分陕西与甘肃,在比较中强调陕西与甘肃在西北边防体系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别。
但是,在边疆与内地的概念上,终乾隆一朝,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并未就陕甘的“内地”“边疆”与“边地”“腹里”属性作出严格的界定。在乾隆帝的上谕及西北督抚的奏折当中,内地与边疆,腹里与边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的语境下交替出现,并未表现出本质上的区别。在道咸同光诸朝,新疆已入版图将近百年以后,道咸同光诸帝仍然将陕甘称作“边陲”之地。以甘肃为例,在新疆已入版图将近二三十年的情况下,乾隆帝及西北督抚仍然将甘肃称为“边地”或“边陲”。
由此看来,在乾隆朝君臣的思想中,“边疆”并非纯粹地理概念,“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是构建起来的。真正的边疆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生成的”[20]86-91,在不同时期相异语境下,边疆的定义、内涵呈现动态变化的特点。因此,终清一世,边疆与内地始终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乾隆、嘉庆、道光及至晚近时期的同治、光绪诸帝,都在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着“内地”与“边疆”概念。如与陕西相比,则甘肃为“边地”;而与新疆相比,则甘肃又为“腹内”。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甲戌上谕来看[21]748,在准噶尔及回部问题解决以后,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将自北疆伊犁、南疆叶儿羌以东原为边陲的区域均划入“内地”,而此时的边陲概念则延伸到伊犁、叶儿羌以西至巴尔喀什湖、葱岭一线。但在新疆拓展二十余年以后的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乾隆五十年二月的上谕中,则又认为甘肃“地处边陲”[22]569,系“隆陲要区”[9]406,其中所反映的边疆与内地概念呈现出较强的相对性。
终乾隆一朝,乾隆帝分别在乾隆十二年正月[23]689、乾隆十二年五月[24]800、乾隆十四年二月[25]820、乾隆三十八年正月[26]368、乾隆五十年二月[13]406历次上谕中将陕甘称之为边疆属性的“极边”“边地”“边疆”“西陲”“边陲”“隆陲”;而在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乾隆三十八年八月的上谕中则又将陕甘称之为内地属性的“腹地”[27]862“腹里”[28]71“内地”[29]723。由此来看,在乾隆一朝六十年的时间内,陕甘虽然已由康熙时代的“边陲”变成了“内地”,但甘肃的边疆印象在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的陕甘认识中从未消除,只是在与新疆伊犁等处比较时,“内地”或“腹地”概念才出现在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的陕甘印象当中。
即使到了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帝时期,陕甘的边疆印象仍然顽固地存在于嘉道咸同诸帝及同时期的西北督抚的陕甘认识当中。嘉庆十四年年十月、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同治五年八月的上谕在谈到陕甘时,仍然使用了“地接边隅”[30]960“地处边陲”[31]506“边陲重镇”[32]280等概念。可见,在开拓西域新疆将近百年以后,在乾隆以后的嘉道咸同诸帝及西北督抚的认识当中,陕甘地区,特别是甘肃的边疆印象仍然是长期存在的。实际上,即使到民国时期,甘肃地处边疆,经济文化落后之印象亦未曾改变,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仍然将甘肃一省归于边疆省份。成书于民国时期的《甘肃乡土志稿》也认为甘肃省“僻处边陲,交通梗阻,土广人稀,地瘠民贫”[1]106-107,甘肃的边疆印象依旧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
二、乾隆朝陕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是区分边疆与内地的重要指标。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性差异,边疆往往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和民族聚居地区。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一个动态变量,呈现过渡性特征,因此,边疆与内地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地带,甘肃可以视为由边疆到内地的过渡地带,既因经济文化落后和民族众多而呈现边疆特征,又因西接新疆、东临陕西腹内地区而带有过渡性地带特点。
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来看,甘肃与其他行省相比,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是比较低下的,即使与邻近的陕西省比较,两省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在《清实录》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经常使用两个方法,从比较中阐明对甘肃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的看法。其一是将甘肃作为边疆行省与内地行省比较,其二是以同为边疆行省的陕西与甘肃进行比较。
“甘肃地处高原,气候变化悬殊,旱雹风霜虫害及洪水诸灾迭有发生”[1]133,同时“甘肃实为西北区中地震最多且最烈之省份”[33]172,自然灾害频仍,自然条件艰苦。甘肃瘠苦的印象终有清一代未改变,从同治帝和同治时期湘系西北督抚的上谕和奏折来看,在同治帝和西北督抚的印象中,甘肃仍然是高寒瘠苦的贫寒之区。
在农业社会中,在以农为本的为政理念下,农业的发展既是地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是评价地域社会在整个帝国系统当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满洲虽以骑射起家,恃弓马而定天下,但是在取得对全国的统治以后,也如同历代入主中原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迅速放弃了其游牧传统。在治国理念上,以农业为根本,视农事为要政,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乾隆帝在给西北督抚的上谕中,屡次谆谆告诫其必以农事为本,重视民生疾苦。乾隆帝曾两次在上谕中特意表扬甘肃巡抚德沛和陕西巡抚崔纪,称赞二人在陕甘兴水利,裕仓储,凿井修渠的养民举措[34]807,要求继任川陕总督查郎阿和新任甘肃巡抚元展成要认真学习德沛重视农事,兴办水利的治甘措施,并特意叮嘱查郎阿和元展成加意留意后续工程,勿使前功尽弃[35]867。西北督抚虽以八旗为主,以满洲居多,劝课农桑与民生吏治本非其所长,但是,在乾隆帝的屡屡告诫下,西北督抚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重视农业发展,在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方面卓有建树的大吏,从而推动了甘肃社会的农业发展。
从上谕和奏折所反映的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对于甘肃农业发展的认识来看,首先,乾隆帝及西北督抚一致认为甘肃农业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非常艰苦,河西四府一州多风少雨,河东四府二州苦于亢旱[36]575,而且“地土高燥”[37]25且“瘠薄”[38]94,“地方苦寒”[39]843,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非常艰苦,因而“农事草率,收获有限”[40]742,农业发展水平低下。
从社会财富指标来看,与其他腹内省份相比,甘肃社会仍然非常贫穷,“户鲜盖藏”[41]1258,“每岁额征,除兵粮外,所余无几”[42]905,“民衣食不充”[43]616。甘肃“近在内地亦荒僻与他省不同”[44]1181,虽与陕甘同处西疆,但“甘肃地处边荒,土瘠歉收,商贩不到”[45]1018,而陕西则“殷实商人甚多”[46]274,陕甘两省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终清一世,包括乾隆帝在内的清代诸帝及西北督抚几乎一致认为甘肃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社会经济水平不高,一般民众生活水平均较低下,实物形式的财富,包括粮食和货币均较贫乏。“地瘠民贫,户鲜盖藏”[41]1258,以至“民力拮据”[47]6,社会经济非常落后。因为自然条件恶劣,甘肃发展传统农业的条件非常艰苦,加之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乾隆一朝对甘肃采取经常性的蠲免赈济[48]225措施,几达“殆无虚岁”[49]718。这些蠲赈缓贷措施对于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稳定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三、陕甘社会风土民情
从地域社会的风土民情来看,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对于陕甘社会风土民情有两个深刻印象。首先,康雍乾诸帝都认为甘肃地处边地,民风淳朴[50]859。甘肃风俗淳朴,民性刚强,康雍乾诸帝对此多有论及。乾隆帝多次在诏谕中提到,“向来甘省民风,尚称淳朴”[51]255。而且急公近义,“虽连年办理军需,毫无派累。而一切受雇挽运,罔不踊跃急公”[52]369,于西陲军事成功作用重大。康雍乾以来历次西疆军事行动,均以甘肃为粮草兵员供应基地,甘肃社会为此贡献巨大。
其次,陕甘社会人才健壮,“兵多精壮”[53]102,而“陕甘之人,长于武事。其人材之壮健,弓马娴熟,较他省为优”[54]558。这在平准战役和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与其他行省相比,甘肃民风刚强,兵皆土著的陕甘绿营战斗力较强,而甘凉兵尤为“天下劲卒”[55]29。因此,陕甘兵马在西北用兵准噶尔、回部及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中,作为绿营劲旅,被大量征调出省作战,特备是甘肃兵以比陕西兵更为强悍的战力,给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清帝国的开疆拓土和平定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乾隆皇帝就说过:“西陲自军兴以来,陕甘兵丁,备极勤奋。而甘省兵丁尤为出力。”[56]941大小金川之役,因川陕甘三省地界相连,而且“陕甘兵多精壮,距川省亦不甚远”[53]102,陕甘兵多有调遣。清军攻打金川曾头沟时,由于番兵据险守死,久攻不下,乾隆皇帝曾感叹,“若甘肃兵四千全到,军声自当更壮”[57]258。可见,在乾隆帝的印象中,与湖广滇黔绿营相比,陕甘绿营战斗力较强,而甘肃兵丁最为骁勇善战,乾隆帝对甘肃绿营依赖与期望甚高。
从文化教育状况来看,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几乎一致认为陕甘社会文化教育水平是非常低下的,这一认识不但表现在上谕和奏折中关于甘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判断,而且也表现在对陕甘社会的文教政策上,其集中表现就是乾隆帝对陕甘分闱的态度。另外,乾隆帝关于陕甘之人长于武事的论断和增加甘肃武乡试解额的举措进一步表明了其对甘肃文教发展水平低下的评价。从积极方面来讲,这一政策有意识地调动了甘肃地域社会的优势和特色,有利于陕甘社会的发展;从消极方面来讲,这一论断及举措也表明了乾隆帝对于陕甘社会文教落后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四、结语
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在对甘肃的自然地理条件、农业发展状况、陕甘社会的民族关系、地域社会风土民情、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甘肃在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作出了较为一致的判断,由此决定甘肃社会治理政策也基本符合甘肃社会的实际状况,从而是有利于甘肃社会发展的。但是,由于乾隆帝从未亲临甘肃,其对甘肃社会的印象和认识完全是基于西北督抚的奏折和书本知识,因此,这种认识及其基于此所制定的政策的合理程度也必然是有限的。西北督抚作为封疆大吏,主政陕甘军事民政,对于甘肃社会的印象和认识相比于乾隆帝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自康熙七年以后,甘陕督抚的满缺制使得乾隆朝西北督抚绝大部分为八旗满洲,因此,西北督抚长于征战弓马而弱于经世治民的民族性格影响到其对甘肃社会的认识和判断更多是基于政治军事层面的,经济及社会的认识在以陕甘总督为代表的西北督抚群体中,被习惯性地忽视了。
因此,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对于甘肃社会的认识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乾隆帝及其西北督抚对于甘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判断是以重农思想为标准的,但是甘肃经济的特点是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甘肃省主要生业,次于耕者即推牧业”[58]166,因此,基于地理条件的区域特点及区域优势,畜牧业也应当是评价甘肃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从乾隆帝上谕及西北督抚的奏折来看,对于甘肃畜牧业之发展,显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二,在陕甘分闱问题上,乾隆帝及其西北督抚对于甘肃文教发展水平的判断有失偏颇,对于清代甘肃文教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由于乾隆帝两次否定陕甘分闱,使得甘肃成为内地行省(吉林、奉天、黑龙江、西藏除外)中唯一至光绪元年之前未分闱乡试的省份,此举必然影响清代甘肃文教事业的发展及甘肃在全国之地位。
甘肃作为西北之中枢,在清帝国保卫西北边防,经营西疆的战略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终乾隆一朝,无论是在西北边疆的开疆拓土,还是在西南地区平定大小金川,甘肃行省及甘肃绿营都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乾隆帝及西北督抚对于甘肃在清帝国政治军事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是一致的。
康雍乾时期及此后的同光时期持续的西北用兵,对陕甘地区,特别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康熙三十年开始反击噶尔丹,中经雍正朝打击青海噶尔丹策零,到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西部用兵前后历三朝70余年。如果下延到道咸时期对回疆小规模叛乱的作战及同光时期平定阿古柏叛乱和陕甘回民起义,那么,自康熙三十年至光绪五年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西北社会长期处于战乱的影响之下。长期的内外战争对于甘肃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甘肃作为战乱波及省份和西疆用兵的战略基地,人力、物力消耗牺牲极大。清廷虽以“协饷”形式长期对甘肃给予援助,但是解决不了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甘肃社会的发展一方面须依赖于西疆的稳定与安宁,依赖于西北民族关系的和谐,以便为经济及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内外环境。另一方面,甘肃社会也须通过农业及畜牧业的均衡发展解决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
在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上,自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准噶尔的彻底失败及南疆回部的平定,广阔的新疆区域已纳入清帝国的版图,甘肃从昔日的边疆变成了腹地,但是,终清一世,甘肃作为“边隅之地”的偏见长期存在于统治阶层的西北印象当中,乾隆帝两次否定陕甘分闱,其内心对于甘肃人文发展水平的判断和偏见是不言自明的。
[1]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2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2]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转送之西北农业、畜牧业和社会经济考察报告(上)[J].民国档案.2001,(3):12-20.
[4]赵尔巽.清史稿·岳钟琪传:卷296[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清高宗实录(四):卷290[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清高宗实录(五):卷36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清高宗实录(十五):卷1178[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8]清仁宗实录(三):卷21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清高宗实录(十六):卷1224[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0]清穆宗实录(五):卷167[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清德宗实录(四):卷301[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清穆宗实录(五):卷18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清高宗实录(十六):卷1224[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4]清高宗实录(十五):卷1169[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5]清高宗实录(五):卷36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清圣祖实录(二):卷170[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清高宗实录(十二):卷974[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8]清高宗实录(十):卷79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清高宗实录(九):卷716[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周平.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86-91.
[21]清高宗实录(八):卷601[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2]清高宗实录(十四):卷1084[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3]清高宗实录(四):卷28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清高宗实录(四):卷290[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5]清高宗实录(五):卷34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清高宗实录(九):卷922[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7]清高宗实录(九):卷70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8]清高宗实录(九):卷63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9]清高宗实录(十):卷79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清仁宗实录(三):卷21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1]清宣宗实录(六):卷360[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2]清穆宗实录(五):卷18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3]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30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34]清高宗实录(二):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5]清高宗实录(二):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6]清世宗实录(二):卷11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7]清高宗实录(十四):卷1049[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8]清圣祖实录(三):卷206[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9]清圣祖实录(二):卷170[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0]清高宗实录(三):卷21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1]清高宗实录(十二):卷971[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42]清高宗实录(二):卷5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3]清高宗实录(六):卷42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4]清高宗实录(二):卷153[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5]清高宗实录(五):卷36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6]清高宗实录(十):卷144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7]清高宗实录(六):卷380[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8]清高宗实录(十六):卷1220[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49]清高宗实录(十三):卷1024[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0]清世宗实录(二):卷150[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1]清高宗实录(九):卷648[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2]清高宗实录(八):卷578[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3]清高宗实录(十二):卷905[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4]清高宗实录(一):卷25[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5]昭梿.啸亭杂录:卷四[M].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56]清高宗实录(二):卷134[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7]清高宗实录(十二):卷914[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8]甘肃省志[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33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责任编辑 朱正平】
The Concept between“Frontier Region”and“Interior Area”to Reveal Emperor Qianlong and Shangan Local Offical's Evaluation on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YANG Jun-min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Hexi University,Zhangye 734000,China)
Qianlong emperor and localofficial had the same evaluation about the Gansu province,such as the socialand economy developing level,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eople of Shan-xi and Gan-su,the importance of Gansu province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Defence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etc.Although,Gansu province had fin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rontier region to the interior area From the Shunzhi period to the Qianlong period,in some extent,Qianlong emperor and the local officials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had never changed their evaluation about the Gansu province.
frontier region;interior area;Gansu province;evaluation
K249
A
1009-5128(2014)17-0059-06
2014-06-14
杨军民(1970—),男,甘肃庆阳人,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