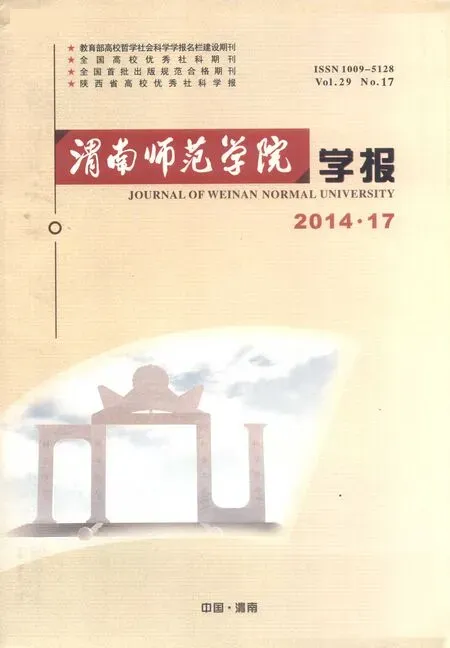论杨逵小说中的底层民众形象
宋颖慧
(1.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论杨逵小说中的底层民众形象
宋颖慧1,2
(1.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底层民众是杨逵小说叙述的重点,以1942年杨逵复出后发表小说为界,他小说中的底层民众形象出现了嬗变,1942年之前是被苦难残噬,被同情与待拯救的无知、无助者,此后则变为被仰赞的勤劳、勇毅者。1942年之前的底层民众形象是杨逵表达人道情感和进行社会批判的工具,折射出他早期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精英意识;1942年以后理想化的底层民众形象则是他表达庶民价值认同的载体,体现了他对劳动及劳动者价值的肯定,寄寓他的劳动美学想象。
杨逵小说;底层民众形象;嬗变;劳动美学
自2004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底层叙述”成为作家的“热门叙述”,引发读者的注意和批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而“底层叙述”或者“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探讨左翼代表作家杨逵的“底层叙述”的主要内容和创作得失,有助于深入认识其思想和创作特点,也能给当代作家的底层写作提供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以杨逵小说中的底层民众形象为研究对象,历时地探讨其小说中底层民众形象的嬗变,分析其成因和深层意蕴,进而指出杨逵底层叙述的特点及价值、局限。
一、1927—1937年:被同情与待拯救的无知、无助者
杨逵1927—1937年间的小说,叙写了底层民众内部的分层现象和阶层身份的流动,构建了深陷苦难泥淖,无知、无助的“失土”农民和“失业”工人等底层民众形象。
农民是底层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逵注重从农民内部经济地位的不同来塑造不同阶层的农民形象。当时农民的经济地位以土地所有权的状况来分:有自耕农、佃农、长工、短工等。[1]129他在1927—1937年间的小说中叙述的重点是佃农,且对农民从自耕农向佃农的阶层流动着墨较多,但这种流动并非自然进行,而是带有极大的强迫性,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和佃农租赁土地的权利频频被政府和地主剥夺,这也是农民苦难生活的根源所在。那些“失土”的自耕农和被压榨、盘剥的佃农境遇极为惨烈悲凄,甚至堕入死亡的深渊。《送报夫》中以名为杨君的知识者“我”的视角叙写了村民面对官方的土地强购通知,惊恐忧虑却无计可施,自耕农家庭出身的“我”有三次发现了父亲躲着流泪,后来“我”的父亲勇于公开拒售土地,但因势单力薄,惨遭蛮横警察的殴打、关押,最终无语离逝;而“我”的母亲则在得知父亲被巡查拖走的消息后人事不知、悲恸憔悴,后苦于病痛和家计而绝决自戕。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不仅要面对殖民政府和资本家的土地掠夺,还要遭受地主的压榨、剥削。由于“本地的封建势力是借着日益巩固的外来政权以维持其尊荣”[2]175,所以在日本政治势力的庇护下,本土封建地主就更加放纵恣肆,他们贪婪、跋扈、残酷地迫使农民陷入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贫农的变死》中佃农阿达叔卧轨自杀、江龙伯被殴致死,罗汉叔上吊自尽……此外,《水牛》和《模范村》两部小说也触及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水牛》里的佃农阿玉之父,为缴佃租续承租地而不得不让女儿辍学,之后又卖掉赖以为生的水牛,最后无路可走,只能将亲生女儿卖给地主做丫环。《模范村》中的佃农憨金福,费尽心血开垦的土地被勾结殖民者的地主阮固收回,他乞求阮固续租土地,不仅被拒更遭其无情虐打,只得靠打短工饥饿度日,最终死在了溪边岩洞里。总之,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农民命运凄惨、喑哑无力,是杨逵悲悯同情的对象,也是他暴露封建地主和殖民者丑恶嘴脸的鲜活明证。
除丧失土地的农民外,失业工人也是杨逵着力叙写的对象,他侧重于通过底层民众的身份下移来揭示失业等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在社会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之下,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变本加厉、冷酷无情的面目暴露无遗,劳工失业的现象普遍发生,导致他们的物质生活更加穷窘困苦。杨逵小说反复摹写了失业佣工在苦难生活面前的茫然无措、痛楚无助。《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中的失业劳工们,因下雨而无工可做,生活饥贫交迫,只能强忍辘辘饥肠苦盼老天放晴。《送报夫》中工读留学生“我”眼中的那个懵懂无知、被欺骗被辞工却只能无语饮泣的失业少年,是底层劳工命运悲苦无告的普遍写照。《毒》里因被老板强暴而感染性病、此后又多次被骗的无知女工和免费娶到女工但却身染病苦、忧怯来“我”处就诊的失业劳工,他们如无良医“我”的义诊恐怕只能坐等死神的到来。《新神符》中失土继而又失业的邻村老翁,因无力筹措保险金续保而在血本无归的苦痛无助中发狂。另外《收获》里却避罢工之劝、渴望归农之乐的失业老工人“我”,面对艰辛务农却收获无果的残酷现实,不得不幻灭了以从农安度晚年的希望。这些因失业而致生活无着、未来无望的底层劳工,他们面对苦难时薄力寡言、懵懂无措、被动无助,有待于启蒙和拯救。
二、1942—1958年:被认同与被仰赞的勤劳、勇毅者
杨逵战前诸多叙写底层生活的小说,如《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送报夫》《灵谶》《死》《模范村》等,都注重表现劳动的社会学意涵,通过塑造一系列勤勉劳动却依旧不得温饱甚至日益贫困的底层劳动者形象,揭示出劳动者自身价值的被压榨、被剥夺,控诉社会的黑暗不公。而杨逵1942年后(包括绿岛时期)建构的底层民众形象,不论是底层劳动女性,如《萌芽》中作者仿拟的女性“我”(从信末署名可见其名为素香)、《增产之背后》中的女矿工金兰、《犬猴邻居》中的林坚之母、《种地瓜》里的林清辉之母、《才八十五岁的女人》里的85岁老太太和林秋生的妻子等,还是底层男性劳动者,如《蚂蚁盖房子》中的短工金池爷爷、《增产之背后》中的佣工老张、《宝贵的种籽》里的勤儿等,他们作为生产劳动的主体,共有的行为特点便是勤劳。劳动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他们创造价值的重要途径。《萌芽》中的素香在丈夫生病疗养时独撑家计,对从农后劳作的艰辛和肤色的变黑不以为意,反觉活力焕发、愉悦爽快。劳动不仅充实了她之前做酒家女的疲乏空虚的心灵,而且劳动的成果——亲手栽种的满畦的蔬菜和花木萌芽时,给她带来无限的希望和鼓励。小说“表面上以‘国语运动'‘增产报国'‘灭私奉公'呼应皇民化运动,若再深一层看,素香透过劳动重获新生一事歌颂了劳动的神圣”[3]201,并流露出对底层劳动女性自立、达观、坚忍品格的赞美。应总督府情报科要求而创作的《增产之背后》虽有鼓吹日台融合、增产报国以及颂扬大和精神的皇民化意味,但结合杨逵当时抒发考察心得的散文——《劳动礼赞》中写到的:“他们借着劳动接受千锤百炼,就像被雨水浇淋的煤炭一样,散发出暗沉的光辉。”[4]164联系小说中那个身姿矫健、坚毅果敢、充满劳动的活力和热情,不畏恶劣的工作环境,且在同伴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女矿工形象以及叙述者“我”的声音:“我……就像一般的劳动者那样……我也努力地去吸取他们那种强韧与不畏缩的精神。”不难看出作者对劳动的歌赞以及对底层劳动者的称扬。《犬猴邻居》中的林坚之母,在瞎眼、丧夫后昼夜劳作、强韧自立,含辛茹苦抚育独子长大成人。劳动是她生存的方式,同时也是她保有个体尊严,体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作者在字里行间渗透了对这位底层劳动女性的誉赞。《归农之日》里作者借作品人物李清亮及其妻之口赞赏了匪贼一样的农人的“健全的身体”和舍身救人之勇。另外,绿岛时期杨逵的小说创作虽然是“以个人的生活体验为范围,缺少对时代和社会脉动敏锐的反应”[2]83,但他歌咏劳动,书写劳动者强韧精神的创作倾向依旧。《才八十五岁的女人》中的老太太,坚守勤劳度日、自食其力的人生信仰,不仅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而且乐观坚强,作者借叙述者“我”及小说中的人物林秋生之口,对其表示了由衷的佩服。在杨逵1942年后的小说中,苦难成为远景,作者旨在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结实硬朗的身体、坚忍不屈的灵魂和自食其力的精神,并对此表达了温热的仰赞之情。
三、底层民众形象嬗变的成因
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杨逵,从1905年出生至1937年归农之前,已历经从“庶民”到“知识青年”——“社会运动家”——“左翼作家”的身份转换。他出生于台南乡下的农民家庭,童年目睹噍吧哖抗日事件被血腥镇压的惨景,少年因不满包办婚姻出逃日本半工半读,留日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参加日本的劳工运动、政治运动,1927年回台后又积极投入农民组合运动并担任领导要职。但随着日本在台湾实施的殖民资本主义的急速成长和台湾被动殖民化程度的加深,台湾的社会运动逐渐朝向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到了1931年前后,历经10多年发动与组织而形成的文化政治运动高潮陡然低落,台湾的左翼政治运动急速萎缩,但却反而导致本土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更加快速发展起来。[5]在社会运动受挫后,杨逵精心致力于“以笔代伐”,由于“自30年代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台湾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以推行文艺大众化为主体的发展时期”[6]434,在“文艺大众化”推进的过程中,台湾文坛上的左、右翼知识分子及新传统主义者通过各种路径“争取‘大众'作为自己的读者,企图透过文学来教育‘大众',使之服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以便扩展自身立场与路线之影响力,成为台湾文化生产场域的主导力量”[7]8。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杨逵,冀望以文学“启蒙大众、教化大众、唤起大众反动的潜能”[8]22,“以便让其觉醒、团结,继而去对抗来自资本主义的世界压迫”[8]11。所以,庶民出身且在早年便与底层民众有过“亲密”接触,亲历了他们苦难生活的杨逵,怀揣着对大众的期待和美好愿望,在早期小说中建构了无知、无助的底层民众形象,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1937年后的台湾社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而进入战时状态,总督府为配合日本侵略战争对台湾人民进行严密控制,不仅支持在台的日本右翼团体打压、恫吓台湾民众,更广泛实行皇民化运动,采取废止报纸汉文栏、强力推行日语、实施皇民奉公运动等多种“同化”措施,妄图使台湾民众成为日本统治下的“皇民”。在这一背景之下,台湾的知识分子原有的对于争取台湾殖民地人民权益的热情开始消退和转变;日据末期的知识分子一部分被收编进入殖民地的行政体系,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高压政策之下,选择逃亡他乡,来到大陆祖国。[9]23-24而颇具自主意识和抗议精神的杨逵,面对政府的思想钳制,从1937年开始便逐渐淡出喧嚣的政治中心,再加上此后他又经历了好友入田春彦自杀等一连串人生打击,所以创作之笔日辍,于农园埋首近四年之后,直至1941年10月才正式复出文坛。在1937年得好友入田春彦之助创办了首阳农场后,杨逵开启了长久的园丁生活,不仅在复出后发表的散文中屡次以“园丁”自居,而且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曾表示:“在东京,我送过报,做过土木零工;台湾的运动瓦解后,我又干过各种活,最后进入园丁生活。我写文章,但不把自己说成是作家,而自称为‘园丁'。”[10]288“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11]426,由于战争的特殊时代背景和总督府皇民化运动的“同化”政策的影响,再加上杨逵创办首阳农园后“园丁”身份的转变以及他与农民日益亲密的接触,他主动调整了自己原初的知识分子心态,在1942年后所建构的底层民众形象,以底层劳动女性为构成主体,普遍摆脱了被苦难摧残、吞噬的“弱者”命运,倾向于以勤恳务实、坚韧豁达的人生态度来积极应对生活苦难,成为作者由衷仰赞的对象。
四、底层民众形象的深层意蕴
农民、劳工等苦难寡语、无智无助的底层民众形象,是满怀人道情感和阶级体悟的杨逵在1927年至1937年间将关切的目光投向社会底层时获得的最初、也是最为震惊的印象,也是他抨击丑陋社会现实,确证自我主体的工具和筹码。
杨逵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压迫阶级,一种是被压迫阶级。”[10]33-34对于底层民众,杨逵因日益了解而生同情,他说我回台后积极参与当时已有的农民团体、工人团体、以及文化团体的种种实际行动,而在实际参与的过程里,更使他得以深入到一般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现实生活里头,得以理解在殖民统治者高压和剥削底下求生存的劳苦民众的挣扎与悲苦,加深了抗日的决心,也加深了体恤底层低阶层民众的情感。正因如此,杨逵对底层民众的叙写产生了真切感人的共鸣力量,而且具有立场鲜明的社会批判价值。
不过,早年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杨逵,对自己的精英身份有着潜在的认同。他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一九二七年九月。当年我才二十二岁,……几乎跑过三分之一的南台湾乡村,参加演讲有10多次。这个时候,豪气十足,好像此鞭一挥便可以把整个江山易色,十分可笑。那时是患了英雄主义的毛病。”[10]227从1927年发表处女作《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伊始,到1937年淡出文坛,这期间杨逵小说中塑造的底层民众形象面对苦难无知、无助,有待于启蒙、拯救,有形无形地烙上了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印迹,成为杨逵文学话语表述中建构自我主体身份的“他者”。如《送报夫》中虽然作者借叙述者“我”之言肯定了杨母的志气和决断,但依然遗憾于杨母的寡闻少知和先前的被动软弱:“现在想起来,如果有机会让母亲读……的话,也许能够做柴特金女史那样的工作罢,当父亲因为拒绝卖田而被捉起来了的时候,她不会晕倒而会采取什么行动罢。”[12]94叙述者“我”的假设和想象流露出作者“俯视”底层民众时的尚知倾向。而且,“若观察杨逵惯用的叙事结构,可以发现杨逵小说的进行除了暴露工人/农人被剥削而造成生活的困境外,结局往往会安排一名‘启蒙者'的出现,用来启蒙、指导工人/农人的反抗意识”[13]143,典型的如《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中的金子君、《送报夫》中的伊藤、《贫农的变死》中的王铁等。这些力图通过政治思想的启蒙来拯救底层民众脱离苦难泥淖的启蒙者,是黑暗社会光明和希望的引导者,也是杨逵接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先锋主义”和阶级意识灌输论思想的体现,他通过可靠的叙述者的声音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同情以及对启蒙者的仰望与崇拜,折射出杨逵早期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精英意识。
庶民家庭出身的杨逵经常接触底层,更在正式“归农”后切身体验劳动,更加深入地了解、融入了底层,所以杨逵在1942年后建构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底层民众形象,对底层庶民经验进行了描述、展示,并站在底层庶民的立场上对知识分子的弱点展开批评,逸出了传统的精英规范,除却了战前的精英意识,部分地传达出底层民众作为主体、有着自我认知的声音。如《蚂蚁盖房子》中归农的知识分子“我”的临时佣工金池爷爷,勤劳而务实,虚心且健谈,虽无书本知识,但人生经验丰富,常出“拜蚂蚁为师”的惊人之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无知”的金池爷爷丝毫不惧读书人“我”,单刀直入地对知识分子发出批评之声,责骂读书人优越感强、虚浮、挑剔、虚荣,让“我”羞愧却无辩驳。《增产之背后》中归农的小说家“我”眼中的佣工老张,虽大字不识但在“我”面前不卑不亢,他敏锐感性、经验丰富、豪爽直言,“不光是我的小说的上好鉴赏家,还是我为人处事的痛切批评家”。他直指“我”胆怯的性格弱点,并告诉我农民式的质朴生活哲理,“不折不扣地是我的良师”。可见,归农后处于社会权力秩序边缘的杨逵,不仅认同底层庶民身份,而且其庶民意识日益鲜明。
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14]180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亲身经历劳动并获得切身体验的杨逵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是创造一切的源泉”[15]18。1942年后的杨逵肯定劳动及劳动者自身的价值,并潜心挖掘劳动的美学意蕴。从他1942年后在《萌芽》《增产之背后》《蚂蚁盖房子》《犬猴邻居》《才八十五岁的女人》等小说中建构的勤劳坚忍且能自食其力的底层民众形象,我们可以窥见他的劳动美学观——积极投身劳动,劳动能锻造强健的身体,磨砺勤恳务实、坚忍顽韧的精神品格,通过劳动还能充实自我心灵,满足生存需要,抵抗物质生活苦难,彰表自身价值和尊严。而且劳动内蕴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等精神品格也是中华民族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民族文化和民族品格是被殖民国家对抗殖民化、他者化、实行民族重建的有效手段。[16]94因而,对于庶民劳动的美学想象是饱有疾病经验的杨逵,在战时殖民体制和国民政府统治压力下,投射自我疗救理想,转移内心压抑和焦虑,抗击苦难现实,抗议殖民压迫,表达庶民价值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依托力量,也是他躲避政治高压检阅,曲折表达自我心声的书写策略。
综上所述,底层民众是杨逵小说叙述的重点,以1942年杨逵复出后发表小说为界,他小说中的底层民众形象出现了嬗变,1942年之前是被苦难残噬,被同情与待拯救的无知、无助者,此后则变为被仰赞的勤劳、勇毅者。1942年之前的底层民众形象是杨逵表达人道情感和进行社会批判的工具,折射出他早期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精英意识; 1942年以后理想化的底层民众形象则是他表达庶民价值认同的载体,体现了他对劳动及劳动者价值的肯定,寄寓他的劳动美学想象。
参考文献:
[1]吴素芬.杨逵及其小说作品研究[M].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5.
[2]黄惠祯.杨逵小说中的土地与生活[M]//江宝钗,施懿琳,曾珍珍.台湾的文学与环境.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3]黄惠祯.左翼批判精神的锻接:四十年代杨逵文学与思想的历史研究[M].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4]杨逵.劳动礼赞[M]//彭小妍.杨逵全集:第九卷.台南:文化保存筹备处,2001.
[5]崔末顺.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文学运动的形成与发展[J].台湾文学学报,2005,(7).
[6]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等.台湾文学史:上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7]赵勋达.“文艺大众化”的三线纠葛:一九三○年代台湾左、右翼知识分子与新传统主义者的文化思维及其角力[D].台南:成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8]陈培丰.大众的争夺:《送报夫》·“国王”·《水浒传》[C]//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邱若山,译.2004.
[9]胡海凤.日据末期台湾政治与文化生态视野下的知识分子研究(1937—1945)[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0]彭小妍.杨逵全集:第十四卷[M].台南:文化保存筹备处,2001.
[11][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2]杨逵.送报夫[M]//彭小妍.杨逵全集:第四卷.台南:文化保存筹备处,2001.
[13]赵勋达.狂飙时刻——日治时代台湾新文学的高峰期(1930—1937)[M].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1.
[14]孙云英.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探讨[M]//冯文华,薛忠义,苑世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1辑.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9.
[15]杨逵.绿岛时期家书[M]//彭小妍.杨逵全集:第十二卷.台南:文化保存筹备处,2001.
[16]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责任编辑 朱正平】
Study on the Im ages of the Lowest Classes in Yang Qui's Novels
SONG Ying-hui1,2
(1.Chinese Department,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China; 2.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The lowest classes had always been the objects and emphasis in Yang Kui's works.Demarcated by his return of publishing novels in 1942,the images of the lowest classes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his former works.The images of the lowest classes he created before 1942 referred to people who were ravaged by theirmisery.They were ignorant and helpless,needing for enlightenmentand salvation.However,the images of the lowest classes he created after1942 were industrious and brave peoplewho were appreciated by the author.Those images he created before 1942 are the objects that he expressed humanitarian feelings and social criticism,and could reflect his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elitist as a LeftWing intellectual in his early life.The ideal images of the lowest classes he created after 1942 are the vehicle for expressing Yang Kui's valu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lebs,which could show Yang Kui's affirmation on the value of labor and laborers,and his imagination on labor aesthetics.
Yang Kui's novel;images of the lowest classes;changes;labor aesthetics
I206
A
1009-5128(2014)17-0041-05
2014-06-24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女佣形象研究(11JK0259)
宋颖慧(1982—),女,山东枣庄人,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