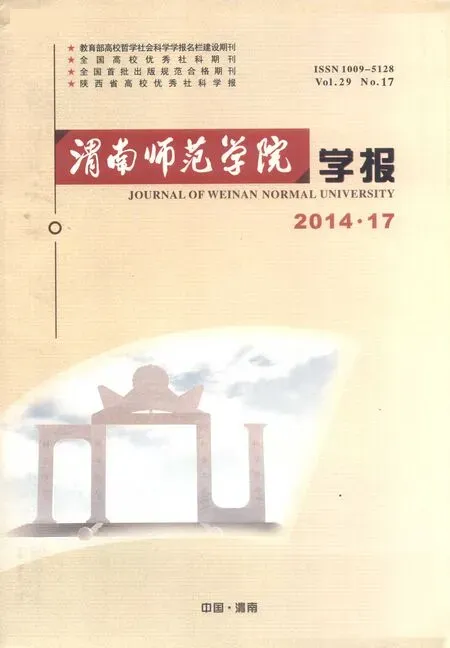坚守与抗争
——左联时期茅盾为延续五四传统所作的贡献
田 丰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 250100)
坚守与抗争
——左联时期茅盾为延续五四传统所作的贡献
田 丰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 250100)
革命文学倡导者为完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文学范式转变,采取的是与“五四”断然决裂的态度,对五四话语及五四传统形成巨大的冲击。“五四”一代成名作家纷纷受到贬斥和攻击,作为“五四”之后诞生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也未能幸免。在革命文学倡导者咄咄逼人、四面出击的强大攻势面前,茅盾虽然也曾作过有力的回应,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开始自觉接受规训,以便能够重新回归到左翼阵营之中。然而作为“五四”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却并未彻底放弃对五四话语的坚守和阐扬,从而在左联时期为延续五四传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茅盾;五四话语;革命话语;左联时期
太阳社、创造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采取的是与“五四”断然决裂的态度。在他们眼中,五四话语早已失去昔日的光环和魅力,只配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腐烂变质,而与革命相形而生的革命话语却备受推崇。革命文学倡导者借着革命话语对“五四”以来渐渐形成的文坛固有格局进行重新裁定,使得五四时期成名的一代文人纷纷受到清剿,摇身一变成为三代以上的古人。
当此文学范式转换之际,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等革命文学倡导者围绕革命文学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在此之后,茅盾逐渐开始自觉接受革命文学思想的规训,以期重新回归左翼文学阵营。因而,左联时期茅盾在对五四话语的评定方面也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一开始他受制于左倾观念的束缚和自身认识上的局限,对于五四话语持着贬抑、否定的态度;而当外界束缚有所松动之时,他又与鲁迅一道致力于恢复五四话语,为延续五四传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初,太阳社、创造社等革命文学倡导者并未把矛头指向茅盾,相反钱杏邨等人还把茅盾视为同道中人。但自从1928年10月《从牯岭到东京》一文公开发表之后,因其暴露出茅盾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革命文学观念的巨大差异和裂隙,由此导致两派一道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1]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已脱离党组织,加入左联后,他也曾向瞿秋白提出过想要重新回归党组织,但因瞿秋白本人此时正遭到党内的排挤而作罢。革命文学倡导者的集体围攻和党的拒绝接纳,使茅盾在文学和革命道路上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以至于在加入左联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都谨小慎微地自觉接受规训,唯恐再次受到革命文学倡导者的攻击。但茅盾毕竟是在“五四”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佼佼者,五四文化的精神早已渗透到血脉之中,他对于“五四”的信仰并没有彻底湮没。
1929年,在遭受到革命文学倡导者激烈的批判后,茅盾在所作的《读〈倪焕之〉》一文中仍然指出,“五卅”前后活跃着的人物虽然在精神上已经超越“五四”而前进了,但其佼佼者却是经由“五四”培育方能茁壮成长起来的,因此他提出“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2]198;同时,他在该文中还特意提醒革命文学倡导者尤其是“五四”感召下成长起来的创造社不要忘记历史,割断历史。然而,当1930年5月茅盾自日本回国加入左联以后,他对于“五四”的评价却开始发生了较大的转变。1931年,茅盾奉瞿秋白的指示先后撰写了《“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两篇文章,其目的是要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在写作之前,茅盾首先征求了瞿秋白的意见,特别是对于五四文学运动评价方面的观点,基本出自瞿秋白。受限于当时的时代语境和明确的现实功利意图,茅盾通篇采用的都是其时流行的革命话语,完全顺应了极“左”思想的规训,对于“五四”的评价非常之低,即便如此,在当时仍“被认为是温和的,保守的”[3]76。
茅盾在《“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中认为,“五四”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文学革命,因而五四文学除了鲁迅的《呐喊》之外都是“惨淡贫乏”的,对于当前的革命文学而言几无可取之处。在他看来,整个“五四”早已被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此后不断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只能是日趋没落,直到“五卅”时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巨人将“五四”彻底地送入到坟墓中去。茅盾认为“五四”的口号虽然在破除封建思想方面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在当前却阻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只能起到反革命的作用,这与创造社、太阳社对于“五四”的评价几乎如出一辙。
《关于“创作”》一文却另有一番深意,茅盾借助该文对太阳社、创造社的观念予以反驳和贬斥。他认为正是由于创造社的错误打压,才使得文学研究会“被侮辱者与被践踏者”的“血泪”文学的主张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太阳社创作出的所谓革命文学作品,也充斥着概念化、脸谱化的弊病,其中“最拙劣者,简直等于一篇宣传大纲”[4]。茅盾在该文中称太阳社、创造社为“小集团”,意在抨击和清理两派在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以及延伸到左联时期的宗派意识和关门主义,同时借着对文学研究会观念的褒扬,显现出文学研究会所秉持的五四话语与革命话语内在的脉络传承。
由此不难看出此时茅盾在对待“五四”评价态度上的前后不一。一方面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语境和左联特殊的政治氛围的拘囿,他对于五四话语不得不极力贬斥和否定;另一方面却又在批判太阳社、创造社等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过程中,不时标举出五四话语以便与两派所推崇的革命话语相抗衡。然而总体而言,茅盾对于“五四”的评价仍然较低,基本未能走出贬抑“五四”的圈框。
茅盾在1932年《“五四”与民族革命文学》一文中仍然认为:“‘五四'运动并未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反封建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虽然以‘反封建'为号召,但旋即与封建势力为各种方式的妥协,对封建势力为各种方式的屈服!至如反帝国主义,则‘五四'始终不曾有过明显的表示!”[5]311显然,这与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的历史定位和事实真相并不相符。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偏差,主要在于茅盾将“后五四”与“五四”运动本身混为一谈,因而误将“五四”之后衰落期的种种表现视为“五四”自身的弊病和缺陷。首先,茅盾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和领导阶层的认定都有明显的错误。茅盾立论的主旨是为了说明在不健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运动必然要走上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相妥协的道路,因此五四时期的文学不可能完成反封建与反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然而,五四运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市民群众、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并非茅盾所认为的那样单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其次,茅盾之所以贬抑“五四”,无非是为了通过对比凸显出“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到了五卅时期,“民族革命运动的大旗转入到全国最大多数被压迫民众的手里而作坚决英勇的斗争”,因而“‘五卅'就是这个全然新阶段的民族革命运动的第一声”[5]312。然而茅盾的这一论断与他在《读〈倪焕之〉》一文中所提出的“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的观点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由此也充分显示出左联前期茅盾在对“五四”认识上的倒退。
二
茅盾在瞿秋白、鲁迅等人的信任和支持下,不仅很快在左联占得一席之地,而且还被委任为左联行政书记,显然这有助于稳固他在左联的地位,他也尚想借此机会积极参与到左联活动中。但是,他的一番“苦心孤诣”却并未得到完全的肯定和回应,党也并未因此重新接纳他。除了在瞿秋白参与领导左联期间之外,茅盾的态度基本难以称得上是积极主动,而始终与左联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1933年1月,《子夜》出版后在文坛上引起轰动,使得茅盾一跃成为左翼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在左联内部无人能够望其项背。茅盾在艺术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开辟自己的言说空间。然而,早在1932年间,左联机关刊物全部遭到国民党查禁,并且从此左联再无法公开出版刊物。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左联转而鼓励其成员联络中间势力,开辟新的阵地。茅盾与郑振铎一起创办了类似于《小说月报》那样的大型文艺刊物《文学》,其编委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包括历任主编在内均为原文学研究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小说月报》的延续。正是依托这一阵地,茅盾开始尝试着重新反思和恢复五四话语,对以前在革命话语拘囿下作出的错误评价和批判进行修复和改正。
在《文学》创刊号上,原文学研究会的名家巨头如陈望道、叶圣陶、朱自清、王统照、丰子恺、夏丏尊、俞平伯、陈子展、顾颉刚、曹靖华、朱湘等都荟萃其中,占据大半版面,自《小说月报》停刊后,尚属首次。而这些作家无一不是吸吮着“五四”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创刊号还专门设有“五四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专栏,刊登郁达夫、金兆梓、适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人撰写的文章进行比照讨论。茅盾还在《文学》上发表了诸如《文坛往何处去》(1卷2号)、《从“五四”说起》(2卷4号)、《我们有什么遗产?》(2卷4号)等等一系列五四新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在《文坛往何处去》一文中,茅盾申明“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的重要性,强调有必要就该问题继续扩大讨论,他期待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还在《“从五四”说起》一文中明确指出,新文学是肇始于“五四”的,无论如何“不把西洋文学作品当作‘闲书'来消遣而当作文学来研究学习,是始于‘五四'的”[6]165。但在该文中也可以看出,茅盾尚未完全摆脱革命话语的束缚,他在对“五四”的价值定位上仍然比较谨慎,因而才会认为“五卅”以后五四时期的文艺理论已经无法得到青年人的共鸣,到了20世纪30年代更是毫无价值。在同期刊另一篇文章《我们有什么遗产?》中,茅盾认为,虽然五四新文学运动起初是一场“解放运动”,但在整个五四时期却没能提出坚实的系统的新文学运动的主张,这与新文学运动的事实并不相符。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茅盾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和约束,对于革命话语生硬割裂五四传统的弊病的反思和批驳不够彻底,但他毕竟已经开始纠正以往的错误观念,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来再度审视五四传统。而且,茅盾是在曾经否定了“五四”之后,转而重新发现和肯定其价值,这便越发显得难得和宝贵。茅盾对于五四文学观念上的改变,在此后的文艺论争和文学活动中愈加明显,他越来越倾向于给予五四传统正面的、肯定的评价了。
三
前文已经论及,太阳社、创造社为树立起革命文学的旗帜,曾经极力贬斥“五四”一代成名作家,除了郭沫若本人之外,其他的五四作家都被否定和贬斥,而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却是与创造社素来不睦的文学研究会。[7]曾经拥有多达170余名会员的文学研究会,仅仅只有茅盾、王任叔、彭家煌等少数几个得以加入左联。曾经被太阳社、创造社视为论敌的茅盾对此是感同身受、颇为不平的,他对冰心、庐隐、叶圣陶等“五四”一代成名作家秉持着团结、帮助和鼓励的态度,他相信这些作家经过一番思索会转变思想,紧跟时代步伐。到了左联后期,茅盾已然认识到要想革除“革命话语”的流弊,就必须对五四文学传统重新加以检视,进而推动五四作家及五四文学的经典化。唯有恢复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文学地位,方能彻底纠正革命文学倡导以来的种种弊端和缺陷,扭转文坛久已存在的不平衡状态。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茅盾有意加强对原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评论和总结,重新估定他们为新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从而最终恢复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左联时期,为了对五四新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和梳理,茅盾又对冰心、庐隐和许地山等作家进行了专门研究,在《文学》上先后发表了《冰心论》《庐隐论》《落花生论》等三篇作家论。在他的引领和带动下,评论界掀起了研究五四作家的热潮。穆木天、许杰、苏雪林等分别对徐志摩、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等五四作家展开专门研究,并与茅盾的作家论一道于1936年结集出版。作家论的批量化生产,有力地推动了五四作家的研究,开启了系统化、规模化研究五四作家作品的先河,使得新文学研究进入到深入总结和对五四作家作品进行经典化定位的崭新阶段。
不仅如此,在茅盾的影响和支持下,赵家璧开始组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在回忆文章中曾经说过,茅盾实际上是这套《大系》的真正主编。在《从“五四”说起》一文,茅盾就曾明确指出:“现在要是来编一本《近代中国文学史》,无论如何得从‘五四'运动说起。”[6]164同时在该文中,他还设定了现代文学的分期时段,提出:“从‘五四'到‘五卅'是一个时期;从‘五卅'到‘一九二八',又是一个时期;以后直到现在,又是一个时期。”[6]164而在赵家璧向茅盾请教《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选稿起讫年限时,茅盾的“五四”分期观点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给赵家璧的回信中说:“‘五四'是一九一九年,‘五卅'是一九二五年,前后六年,这六年虽然在新文学史上好象热闹得很,其实作品并不多。……不如定自‘五四'到‘北伐',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七年……本来‘五四'到‘五卅'不过表示了‘里程碑'……从1917到1927,十年断代是并没有毛病的。”[8]178由此,不仅确定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限范围,而且对以后的文学史撰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茅盾在为《小说一集》所做的导言中,对文学研究会的人员组成、文学观念、文艺刊物都作了详细说明,对文学研究会以及代表作家们的功过得失也给予了较为客观准确的评价。《小说一集》自1935年出版以来至今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但它仍是五四作家研究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因而不仅在当时有力地纠正了自革命文学倡导以来所导致的文坛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对于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经典化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从对五四传统的继承还是五四作家的经典化来说,茅盾在左翼文学家中都是开风气之先者。在党的权威话语描述中,直到抗战以后才重新对“五四”给予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一二·九”运动讲话中指出:“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9]由此可见,茅盾对五四话语的肯定和高扬是极其难得的,也是极富前瞻性的,为延续五四传统作出了巨大贡献。
[1]田丰.“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190-198.
[2]茅盾.读《倪焕之》[M]//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朱璟(茅盾).关于“创作”[J].北斗,1931,(1):75-87.
[5]茅盾.“五四”与民族革命文学[M]//茅盾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茅盾.从“五四“说起[M]//话匣子.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7]田丰.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论争缘起及观念罅隙[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88-92.
[8]赵家璧.编辑忆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9]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N].人民日报, 1985-12-01.
【责任编辑 朱正平】
Maodun'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Words of the“May 4th Movem en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eft League
TIAN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dvocators fo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had the views of being out of the“May 4th Movement”completely,in order to make the transition of literature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literature,which gave the great impact on the tradition of the“May 4th Movement”.Maodun was involved in the debate.Maodun hasmade strong response and back to the opponent's aggressive offensive,but inspectof this the impact of the debate to him is extremely profound.Although Maodun isnot comp letely agree with the opponent's views,but in fact he has largely began to voluntarily accept discipline of revolutionary thought,and completed the“magnificent”turn around,back to the Left.But as the first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by the nourishment of the“May 4th Movement”,he did not thoroughly abandon the reflection and struggle,and persisting in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words of the“May 4th Movement”can prove it.
Maodun;“May 4th”discourse;revolutionary discourse;period of Left League
I207
A
1009-5128(2014)17-0031-04
2014-06-26
田丰(1981—),男,河南新乡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茅盾研究。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