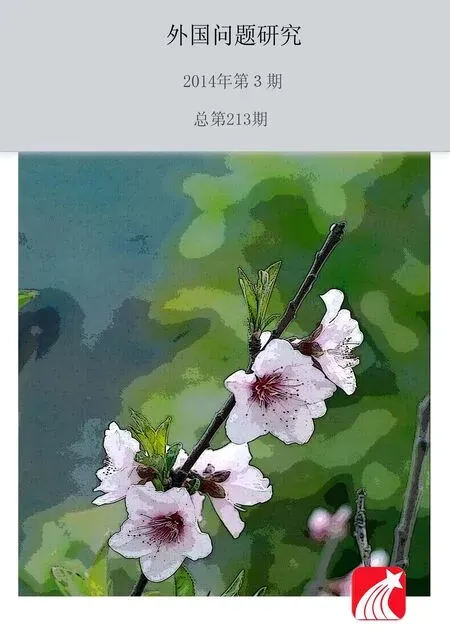伪满洲国的广播剧
代 珂
(首都大学东京 人文科学研究院,日本 东京)
一、伪满广播剧的概况
(一)“双重放送”广播系统和广播内容的分类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位于哈尔滨和沈阳的广播电台。1933年4月,关东军在长春建“新京中央放送局”,并于6月由日方出资五千万日元成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以下简称“电电”),统一运营伪满无线电广播事业。自电电成立之时起,历代总裁均由关东军司令官担任,并与日本放送协会签订指导合作协议,以表面独立,实质受日本管理的形式完成对伪满广播事业的垄断控制。其主要目的除运营“关东州”和伪满的电信电话业务之外,就是扩展伪满的广播事业,通过广播在传媒层面实现“各民族间的文化整合”[1],以期通过控制媒体强化统治体制。
电电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广播内容上同时兼顾中日两种语言。移居至伪满的日本人构成初期广播听众的主体,但同时当地还有大量中国人,他们是伪满广播的潜在听众,如果无法满足其收听需求,伪满广播事业便无法发展,广播传媒层面的“跨民族整合”也将成为空谈。
“双重放送”(当时称作二重放送)广播系统在这样的前提下登上伪满广播史的舞台。1934年10月,100千瓦大功率广播塔在长春宽城子设置成功并完成实验播音,正式开始投入使用。在被作为“第一放送”使用并足以覆盖伪满全域的这一大功率设备的支持之下,各地方广播站得以抽出设备构建“第二放送”播音网,从硬件上解决了两套网络同时广播且内容各异的播音系统的问题。由此,伪满的广播形成了“第一放送”日语播音,“第二放送”中文播音的格局。
当时的广播内容沿袭日本模式,主要分为“娱乐放送”、“教养放送”和“报道放送”三类。娱乐放送包括各种音乐、戏曲以及后来的广播剧等,教养放送包括中日文讲座、时政讲演等教育性节目,而报道放送则为各种新闻节目。两种语言播音节目的编辑制作方式也各不相同,日语播音中,来自日本的转播占其内容比重的一半以上,而在伪满编辑制作的节目多为一些新闻和教育类节目。中文播音除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实况转播之外,完全由隶属于电电的各地方广播站制作播出。本文的研究对象广播剧同时出现于中文和日文两套广播节目中,但是由于日文节目中的广播剧大部分为转播节目,因此实际上将范围设定为完全独立制作,最能体现伪满广播传播实际状态的中文广播剧。
(二)广播剧在伪满诞生和发展的背景
伪满广播剧在内容分类上属于“娱乐放送”,始现于1937年后期,同当时的文化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时期,伪满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政策调整,尤其在文化层面,全面掌控伪满电影事业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和当时最大规模的文人团体“文话会”的相继成立使得伪满文艺界甚为活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伪满的话剧界也迎来了一次相对的繁荣。长春、沈阳、哈尔滨相继出现较大规模的职业话剧团,在相互竞争公演的同时引领着伪满话剧界的发展[2]。
话剧公演的兴盛以及民众喜好度的提高也引起了广播媒体的关注。笔者调查《大同报》广播节目表发现,自1938年后期起,每晚七点之后的节目内容中频繁出现“放送话剧”(即广播剧)这一节目,而之前则很少出现。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这个问题可以从当时电电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找到答案。1938年12月,电电以“中国人喜好的播音节目”为课题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三大主要播音分类中,最关注娱乐内容的听众占总调查人数的51.6%,成为“最近最为关注的播音内容”第一位的话剧(26.0%)则超越传统戏剧(21.8%)[3]97-99。从这一结果中可知,当时的听众收听广播的主要动机是为寻求娱乐消遣,而由于话剧的兴盛,广播剧这一新兴目种打败传统戏剧,成为听众最为喜爱的播音节目,并且听众的这一反馈得到了广播媒体的及时关注,由此成就了1938年伪满广播剧黄金时期的到来。
各种跟话剧和广播剧密切相关的社会团体及机关团体的相继出现从侧面印证了广播剧受到重视、进入发展期这一事实。除文话会之外,成立于1939年12月的文艺协进会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跟伪满广播剧最为密切相关的社会团体。它由电电组织成立,主要目的是对中文节目作内容上的充实,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广播剧的剧本创作和节目制作,在伪满较为活跃的作家山丁、吴郎等都是这一团体的成员。文艺协进会的出现,从内容上和政策上都帮助广播剧巩固了在当时广播传媒中的地位。而1940年3月成立的,通过加强电电、满映和满洲弘报协会相互间的合作关系来推动新剧发展的满洲演艺协会,则在文化政策上一定程度地推动了广播剧的繁荣。
当然,话剧和广播剧受到如此重视并不单纯只出于文化层面的考虑。据笔者调查所知,电电通过实况转播的方式播出的《建国史断片》(1937年8月29日)或可称作伪满广播剧的雏形。该剧政治色彩强烈,讲述的是伪满建国的相关故事,宣传目的明确。而从满洲演艺协会公布的“指导统制满洲演艺界,在促进其正常发展的同时给国民大众传输健全的娱乐精神,通过演艺进行建国精神的彻底普及并谋求文化的向上”[4]这一要纲主旨中可以看出,广播剧之所以受到传播方的如此关注,最大原因是伪满政府背后的日本统治者注意到其受众程度之广泛,欲将其作为思想统制和政策宣传利器之目的,而这一目的也造成伪满广播剧在后期发展上的畸形和最终的没落。但是,政策上的关注在侧面推动了广播剧的发展也确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三)伪满广播剧在内容上的分类
为把握大致情况,笔者通过查阅1937年至1943年间的《大同报》和《盛京时报》,获得相当一部分关于广播剧的内容简介。在报纸上刊载的这些广播剧,可以理解为是传播方较为认可并重点宣传的,同时也是相对更为受到听众关注的剧目,而对这些作为文献资料遗留下来的广播剧的内容简介进行分析整理,也是在第一手声音资料流失的情况下最为直接和可能的观察方法。结果显示,1938年共刊登广播剧内容简介8篇(8月至12月),1939年共刊登33篇(1月至12月),1940年共刊登15篇(1月至12月),而1938年8月之前和1940年之后关于广播剧的介绍则寥寥无几。这一结果同前文提及的话剧繁荣时期的文化背景相吻合,再次从数量上证明了1938年至1940年这一期间的确为伪满广播剧的黄金时期。
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可以将当时播出的广播剧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各话剧团进行剧本创作并编排播演的原创广播剧;第二类是对已有的文学作品进行适当的改编后进行播出的改编广播剧,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赛珍珠的《大地》等,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少数伪满作家的作品,形式类似于广播小说;第三类较为特殊,是借用满映即将上映或已上映的电影剧本,将其进行适当的改编后进行播出。这类作品为数稀少,调查已知的分别为1938年11月5日播出的《国法无私》、1939年1月31日《冤魂复仇》、1939年2月6日《四潘金莲》、1938年12月2日《田园春光》、1939年9月9日《黎明曙光》共5部。这类作品并不是由专业话剧团而是由满映的演员直接参与播音演出,笔者认为其意图在对满映的电影进行宣传的同时,兼顾丰富广播节目,是一种满映和电电在业务上的合作方式。该类型的作品在现有的满映研究中亦未被提及过,可谓是一片仍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广播剧之所以得到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被视作思想统制和政策宣传甚为有效的媒体手段。伪满的殖民地属性决定了其政策决定内容的简单传播模式。在这一前提下,广播剧从剧本创作到制作再到播出被听众收听的这一传播过程中,担任传播者角色的话剧团成员的立场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难。他们通常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在制作广播剧时为电电工作,另一方面又是作家文人、话剧团成员。因此他们不得不在保证创作质量的同时,迎合来自政策的需求。这一境遇又必然地决定了伪满广播剧的局限性。
二、进退维谷的广播剧
(一)广播剧的两种创作形态
将各话剧团的原创剧目进行编排后播出是当时伪满广播剧的主要创作形态之一。话剧团的创作素材多来源于剧作家们的日常生活,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了当时的伪满社会。1938年10月15日播出的《乡间的苹果》便通过讲述青年男女的感情故事,勾勒出农村和城市之间质朴与奢华的巨大差异。守正和二英自小青梅竹马,二英有一副好歌喉,于是守正劝其去戏班学戏,而他则默默守候对方,时不时送去几颗家乡的苹果。二英的戏越唱越好,最终在大都市一举成名,成为炙手可热的名伶。然而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却让二英忘却了故乡,疏远了守正。几年后,当守正再次带着家乡的苹果去见二英时,和一群男女嬉笑欢乐的二英终于对其视而不见。最终,面对二英的冷漠,守正放下苹果,独自回到了乡间。
以小人物为题材,讲述日常生活和感情故事,是当时广播剧的一个重要特征。除《乡间的苹果》之外,还有如以文人韩明和妓女雪铃之间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欢乐之门》(1939年1月5日);描绘母亲、儿女和养父之间情感纠葛的《养育之恩》(1939年2月11日);以一张借据为线索而引出两家人尘封已久的恩怨情仇的《一张借据》(1939年8月13日)等。这些作品均以贴近生活为切入点,勾勒出人生百态,其文学水准暂且不论,但由于他们贴近生活、讲述生活,引起了听众的关注。纵览当时报纸的评论栏,也时常可以发现一些听后感和评论文章。署名“聂明”的听众对《养育之恩》一剧大加赞赏,评价其“达成功之域,角色的分配极其相宜,这是导演用心之功”[5]。同时也有听众对致力于广播剧创作的话剧团抱以厚望:“总之奉天放送话剧团一切都在向前迈进着。我们希望要更努力下去。当事者也应该提出更多的演出机会来——这些我们都是急于期待的。”[6]这些声音反映了伪满广播剧在迎来繁荣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来自听众的赞赏和期冀。
同时,对现有文学作品进行重新编排和改写,是伪满广播剧的另一种创作形态。以1939年11月10日播出的《少小离家》为例,该剧基于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的改编。作品名称及剧中人物姓名均被替换。如女主角卡捷琳娜改为高玲、季洪改成马鸿起、鲍里斯则变成了鲍姓青年等,故事的舞台也从伏尔加河畔搬到了哈尔滨。《大雷雨》是一部从女性视角出发,以爱情为题材表现反抗体制主题的剧本,在创作之初受到较高的评价。这一剧目进入伪满广播剧作家的视野并被改编播出,除从类型和内容上丰富了广播剧的创作之外,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更为隐蔽和重要的原因——对文化统治政策的规避。李文湘曾在《四一年放送话剧再检讨》一文中如此评价当时的广播剧创作:“此刻满洲放送话剧的第一个缺点是其题材狭隘与陈腐。可是大家都以‘无事可写’来解释。(中略)有人说也是因为由于种种的约束在目前摆着的,故事是不能尽收在放送话剧的题材范围里的。这当然也是个困难之点。补救的办法是翻开国外的作品改译或改编一下。”[7]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伪满广播剧面临的两个困境,一是题材的单一和枯竭,而另一个则是创作所受到的制约。改编作品,则是剧作家们所提供的解决之道。
(二)广播剧与政治的结合——“国策剧”
不难想象,题材的单一和枯竭归根结底是创作受到制约的显现,伪满广播剧所面对的真正困境是“由于种种约束在目前摆着”。广播剧的创作虽是文学的过程,但在伪满它受到来自殖民主义文化政策的控制。前文所提及的和剧作家息息相关的文艺协进会和满洲演艺协会,无一不受到政治力量,即来自日本的统治思想的直接约束。那么,当时的日本统治者是如何看待伪满的戏剧创作的呢?
满洲演艺协会会长三浦义臣曾如下评论中文播音剧种的选择问题:
国民戏剧的定义对满洲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蒙、鲜、俄系,任取其一都不可视其为国民化的戏剧,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现存的民族戏剧而已。(中略)传统戏剧中有很多赞美忠孝节义的因素,这些当然无可厚非,但这些戏剧同小说一样,大量融入了对中国社会中阶级意识的暴露。(中略)这些对于怀抱着新理念而日渐繁盛的满洲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所以必须注意剧目选择。而关于新剧,如果是民国之后创作的,那么在思想问题上要严加注意,这一点更是毋庸置疑[8]。(笔者译)
三浦义臣关于剧种选择问题的论述中可以提取两个观点。首先他否定了现存的传统戏剧和新剧,因为前者所包含的阶级意识不符合伪满的“国家”理念,而后者则因为民国后的剧目中所包含的“思想问题”需严加筛选。从这两个理由中可以看出伪满对于剧作本身所传递的思想信息的控制十分严格,而其标准之一亦可说是最重要的标准是弱化阶级意识,强调所谓的国家理念,即所谓“民族协和”。另外他还提到了“国民戏剧”这一概念,这才是他对伪满剧作的真正要求。
“国民戏剧”是1937年在日本被提倡的戏剧创作理念,它可以描述为四个方面:针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针对自由主义的统治主义、针对艺术至上主义的目的主义、针对欧化主义的日本主义[9]。简而言之,它是一个以强调日本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标准、目的性明确的戏剧创作规范。这一概念被三浦义臣所借用并加入“多民族性”这一要求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应呢?上原笃在《国民演剧的构想和规划》[10]一文中理解为:在超越各自的民族身份、作为相同的国民而怀抱着爱国热情的前提下所达成的创作;笠雪间雄又进一步提出了戏剧应和政治结为一体,和国家结为一体的要求[11]。
综合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日本对伪满戏剧创作的一厢情愿。首先,对阶级意识的视而不见已经触犯了戏剧创作作为文学行为的底限,使其脱离了最基本的社会实际。其次,在殖民统治的大环境下,破除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日本人和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国人之间身份认同的差异更无实现的可能。因此,从国民戏剧这一理念出发对伪满戏剧的创作操控,实质是戏剧和政治的强制结合,这在当时被视作文学戏剧创作的“国策”,同时也造就了束缚广播剧健康发展的巨大枷锁。
从1939年8月21日播出的《聚散》一剧中,可以看出如此的政策压力下伪满广播剧在内容和表达上的失真。该剧的主人公是飞行员李志毅,七月十日在诺门罕战役与苏蒙军队的战斗中,因身负轻伤回长春疗养。返家后的李志毅同久违的妹妹、妻子以及邻居们谈起了战场生活。《聚散》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剧情,主要内容为人物对话。
若说苏联的飞机多确是真多,也正像乌鸦一样黑押押的满天飞。不过因为他多,飞到一块转不开身,我们在飞机上放的机关枪,碰不着这架,还许打那架上,所以就像用砂枪打家雀似的,那才好打呢。(中略)至于他们的陆军也有不少,但是不勇敢,都怕死,所以只用装甲车来攻。我们这边呢,除了用大炮集中射击而外,还有不怕死的肉弹勇士,突入车阵里边,去活捉他们的战车[12]。
诺门罕战役在这名虚构的角色口中被如此呈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媒体对真实战况的封锁和虚报,另一方面更是出于统治政策的需求。首先,这场战役的实际参战双方是日本和苏联,所谓“满洲国军”几乎没有正面介入战争,更不可能出现李志毅这样的飞行员。然而,由于这场战役的导火索是所谓“满蒙国境问题”,所以日本对这次战役的报道宣传几乎完全站在伪满的立场,将其描述成一场为全体“国民”而打的正义之战,如李志毅般的虚构角色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以陆续登上广播剧的舞台。其次,该剧于8月21日播出,这正是日苏双方在诺门罕正面战场胶着之时期,并且随着苏联方面的兵力投入,日军已显露颓势,但实际战况却由于日本对媒体的统治而被隐瞒。相反,关于日“满”联军的捷报却在报纸上被大肆报道。而《聚散》则可以看做是这种信息统治在广播媒体上的体现,也就是戏剧“国策”下的广播剧和政治结合的产物。
类似《聚散》这样的剧本在当时被称作“国策剧”,它在原创广播剧里占据相当比重。1941年,随着对伪满文化统治影响巨大的《艺文指导要纲》的公布,戏剧为政治服务的呼声更为高涨,广播剧也几乎完全政治化,沦为单纯的宣传工具。“如果将职业剧团演出的成绩夸张来说,‘缺乏艺术性’,但是他们的理由非常充足:这是‘国策剧’。”[13]可以看出对于国策剧的强调给伪满戏剧造成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剥夺了戏剧原有的艺术性。
三、伪满广播剧的局限和没落
(一)严密审查下的广播剧
为确保播音内容体现“国策”要求,伪满广播从节目内容的制作到播出有着一套严密的审查制度。电电每月举行一次“弘报联络会议”,由关东军、伪满政府、协和会以及电电代表构成该会议的主要成员,目的是制定每个月广播播音的指导方针。各广播站则根据方针在每月十号之前向电电提交下月的节目编制议案。这些议案在电电审查之后,还需提交“放送参与会”进行最终审议,“放送参与会”的主要成员为关东军、弘报处、交通部、协和会和电电代表。只有在该会议上审查通过的议案才有可能制作成节目播出,但同时仍有专员实时监听[14]。这套节目审查制度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关东军、弘报处和协和会,它从方针控制和实时监听两方面确保了对伪满广播传媒的完全控制,所有政策上的需求都在这一体制的作用下在广播传媒中得以实施和体现。
这套制度的存在和运行,使得上述对广播剧的“国策”需求得以实现,同时过滤掉所有不符合或者违反方针需求的作品。透过1944年7月25日播出的《新天地》一剧的审查事件,可以看出伪满广播剧在这一制度下的艰难处境。该剧的创作背景是协和会创建纪念日,为起到宣传效果电电决定在当天播出一部以“协和”为题材的广播剧。然而,当时的编剧却出于暴露伪满“五族协和”虚伪本质的目的,创作了一部看似顺应,实则讽刺的闹剧:某山村居住着中、日、朝、俄各族村民。某天身为村长的日本人宣布洪水即将到来,要求大家集中到石头房子里避难。此时俄国人开始忏悔起卖牛奶兑水的罪过。受他影响,朝鲜人和日本人也相继坦白曾贩卖大烟和收受贿赂。一夜之后,因房间里实在气闷便有人搬开砂袋推开窗户,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洪水。这时村长才坦白洪水只是他散布的谣言。该剧在村民们围着村长大笑道“原来你才是最大的骗子”中结束。《新天地》由于负责人的疏忽未经审稿便被播出,但在播出的同时被监听人员注意,出于有辱日本人的原因被要求上交剧本接受审查。这一事件最终由于负责人害怕被追究责任而上交假剧本后不了了之[15]。虽然跳过审查制度得以播出,但却被实时监听后要求二次审阅。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伪满广播监控体制的严密,以及广播剧几乎不可能跳脱束缚获得突破的状态。
《新天地》只是一个特例,伪满的广播剧实际上完全处于由于创作被控制而导致的内容无法接近社会实际的困境之中。避免作品中出现对日本人的负面描写,是伪满文学的普遍特征。这是身处伪满的作家在实际境遇下的无奈之举,也是出于自保的目的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伪满的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的日本作家眼中被贴上了“阴暗”、“消极”等标签,原因是很多有一定质量的作品均以社会问题为素材,以描写社会底层大众的困苦为主题,不符合政府强调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理念。在这样的作品中如果出现对日本人负面描写,很容易受到审查甚至危害到自身安全。因此,作家们大多采取了避免日本人的角色在作品中出现这一规避措施。
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描述伪满广播剧。在笔者调查所得的所有剧本中,不论是原创作品还是改编作品,不论题材是积极还是消极,包括政治性最为强烈的“国策剧”中,都几乎没有日本人作为角色登场。广播传媒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所接受的审查之频繁和制度之严密要远远高于文学创作,因此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然而,这一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伪满的广播剧实际上所表现的只是虚假的或片面的现实,是对政策需求的被动迎合,它展现给听众的,仅仅是一抹难以获得认同的浮华景象。
(二)广播剧在伪满的没落
对伪满广播剧的政治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大。《艺文指导要纲》公布之后,包括文艺协进会等在内的团体均遭强制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在戏剧及相关领域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剧团协会。剧团协会受当时政府的直接管辖,这一变动最直接的影响是加剧了戏剧创作的政治化进程,而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国策剧”的大量泛滥。
最近在所听到的放送剧里,总括说来,有如下的感想两端:一是对话的混乱,一是内容的公式化。(中略)其次,所谓“内容公式化”,我是指最近听到的一些雷同作品。这些作品都好似一个窑烧出来的陶器。增产也好,归农也好,储蓄也好,纵然都是由一个“国策”窑烧出来的,但至少也涂上一点不同样式的釉彩,听了头,便知道了尾的东西,这岂不是“靡劲之至”[16]?
以上言词大胆地指出并概括了在政策需求下伪满广播剧的变质及原因。以中途岛战役为转折日本开始深陷战争泥潭,对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日益加剧,而伪满作为其重要的资源供给站亦受到这一变化的巨大影响。对增产、归农、储蓄等的鼓吹便是应日本的资源需求而生的政策,从1942年后期开始在伪满被大肆宣传和强调。伪满的广播剧在这样的宣传需求下,如以上材料中所述,出现了大量以这些政策内容为主题的广播剧,几乎占据所有篇幅。然而如此的政治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内容上的单薄和公式化,剧本的创作受到严格的限制后数量骤减,广播剧的娱乐功能消耗殆尽,成为伪满广播剧步入没落的根本原因。同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广播政策进行了以新闻为中心的方针转变,战况报道被作为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可以随时中断正常播音进行插播,这也从侧面导致包括广播剧在内的娱乐播音内容的萎缩。至此,广播剧几乎淡出了伪满的广播传媒,失去了听众的关注,在数量大幅减少的同时成为可有可无的存在。
四、结 语
伪满广播剧自1938年伴随着兴起的话剧运动而登上广播的舞台至1942年失去文艺精髓沦为单纯的宣传道具,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兴衰。它的兴起,是多重因素下的结果。电电成立之初,伪满的广播听众人数仅为7 995人,并且几乎都是日本人。1939年随着电电对双重放送的推广以及廉价型收音机的普及,总听众人数达到22万,其中中日双方的听众大约各占一半,而次年的听众人数中,中国人的数量以大约2万的优势首次完成超越[3]。这在受众需求的层面上奠定了中文广播节目多元化的基础,加之话剧在同一时期的伪满文艺界得到繁荣,受到大众的关注,将其引入广播传媒以广播剧的形式呈现给听众可以说是必然的演变。同时,统治势力出于政治宣传的需求对大众传媒加以利用又从侧面推动了这一演变的进程。
然而,广播在伪满可以说是单向的线性传播方式,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几乎没有反馈这一过程,听众对传播内容的实质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代表政治需求的电电和介于电电和听众之间的剧作家是广播剧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因素,因此,伪满的广播剧自诞生之初就处于不得不在文艺性和政治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尴尬境地。回顾广播剧在伪满的兴衰历程就可发现,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文化统治的束缚。它的两种创作模式,剧团原创和改编再创作,都分别受到来自文化政策的影响。剧团原创剧目看似是自由创作的结果,但实际上剧作家的创作过程被约束在殖民文化政策的框架之内,有着诸多限制,才造就了只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感情故事这一局限性。而从已有的文学作品中选取素材,加以改编制作,与其说是为了丰富广播剧的类型,倒不如说是因创作束缚而面对题材单一枯燥这一问题时的无奈之举。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政治政策的影响力一直处于膨胀状态,严密的审查制度和一味的“国策”化近乎完全扼杀了广播剧的艺术性和大众性,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将广播剧塑造为思想统治的教科书。
或许可以认为,伪满的广播剧从未真正反映过社会现实。它从未描绘出一副日本人和中国人共存时的真实场景,从未摆脱日本统治思想的控制,只是统治者通过电波完成的一次思想改造。但是同时,它也是伪满十四年历史中的一次文艺实验,在短暂的四年里它刻画过大众生活,也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夹缝中寻求着存活之道。由于声音资料的不可溯性,当时的广播剧在制作上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几乎已经无法了解,但是从这些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当时民众的生活断片和社会侧面,同时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一时期广播传媒的实际状态。东北沦陷十四年的历史在研究的积累中已经开始浮出水面,这一时期的媒体研究,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填补空白的工程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定欵案[N].满洲日报,1933-06-04.
[2] 大久保明男.从社会文化层面看中国的都市——关于伪满城市中的戏剧活动的考察[C]//2003年度东京都立短期大学特定研究报告,2004.
[3]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满洲放送年鉴复刻版第1卷 [M].东京:绿荫书房,1997.
[4] 满洲国通信社.满洲国现势1941年版[M].1941:51.
[5] 聂明.听了养育之恩[N].盛京时报,1939-02-27~28.
[6] 凡郎.记大年初一[N].盛京时报,1939-03-27.
[7] 李文湘.四一年放送话剧再检讨[N].盛京时报,1942-02-04.
[8] 三浦义臣.国民演剧和放送事业[N].宣抚月报,1939-09.
[9] 饭塚友一郎.国民演剧和农村演剧[M].札幌:清水书房,1941.
[10] 上原笃.国民演剧的构想和企画[J].满洲文艺通信,1942,1(11).
[11] 笠间雪雄.在满洲中央剧团新的出发之际[J].满洲文艺通信,1943,2(7).
[12] 文才.放送脚本 聚散(一)[N].大同报,1939-08-18.
[13] 白萍.职业剧团战时下的责任和生存问题[N].大同报,1942-10-23.
[14] 山根忠治.我国放送业务概况(二)[N].宣抚月报,1941-09.
[15] 尔泰·丛林.哈尔滨电台史话[M].哈尔滨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86.
[16] 荘也平.闲话放送剧[J].青年文化,194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