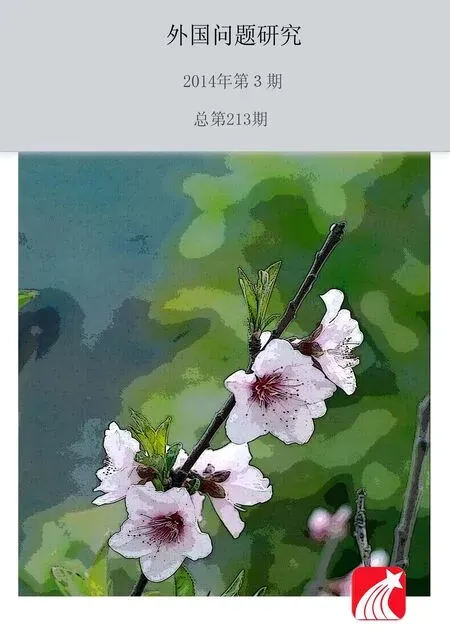日本武士信仰的特征
许译兮
(天津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7)
武士曾经在日本历史上长期占有统治者的地位。虽然武士阶级和他们的统治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武家社会所造就的日本人的感受方式、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等对于日本人的国民性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日本向近代过渡以及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的日本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学者说:“日本武士阶级,在长达大约7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涌流中,创立和发展了包括武士道在内的日本新文化——武家文化。它在以后的历史流向中又不断经过来自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制约和批判地继承、改造而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近年来人们开始议论武士道至今仍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的根本缘由所在。”[1]事实正是如此。
在武士伦理中,信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信仰可以定义为“人对人生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起源存在、性质、意义、归宿等的认定和确信,并以此形成最高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2],这样的信仰落实在社会生活中必然成为决定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武士的信仰是在武士阶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了武士的宗教观、人生观、社会观,表现出新兴权力阶级与以往的贵族统治阶级的差别,影响了日本信仰文化发展。那么,武士的信仰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本文拟以武家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真实反映武士思想状态的武家家训为主要资料,对武士信仰的特征略作探讨。
一、现世为本
在武士刚刚开始建立政权的镰仓时代,留下家训的多是与贵族阶级联系较为密切的上层武士。他们虽然也会向佛神祈祷后世冥福,但是已经开始注重请求神佛保佑自己本人乃至家族在现实世界的利益。镰仓幕府初期北条重时的《极乐寺殿御消息》中有:“得神眷顾,人保其运。……纵然主上粗疏,不识忠良,佛神必来护佑。一心仕宦,便是修行。”[3]61体现了寻求现实利益的目的。作者还认为,神佛对现实利益的影响会延续到后代子孙。“比如父有德,子任高官,非一己之力,乃神佛护佑也。……人不以佛法为本,则祸及子孙。”[3]72室町幕府初期的《竹马抄》中说“又有身陷忧虑时方求神者,何其愚也。”[4]230“有身陷忧虑时方求神者”,印证出当时已经有人为自己在现实世界所受的困扰向神佛祈祷。这说明在武家政权刚刚起步的时期,在信仰上已经出现了现世主义的苗头。
随着武家社会的发展,武士信仰中的现世主义的因素愈发体现出来。室町时代,应仁之乱前夕的《伊势贞亲教训》要求在日常生活中礼敬神佛,按时参拜。“清晨早起,洗净身体,着三衣*三衣:指僧尼所穿之衣。于肩衣之上,捻珠礼拜佛神三宝,尤其氏神,要诚心布施”,而这一切的目的是“祈愿武命长久,家门相继。”[5]80这时伊势贞亲向神佛祈求的已经不再是死后世界的幸福,而是现实世界武士家的长久延续,祈祷的重心明显向现世、特别是向武士家存亡攸关的“武运”倾斜。
应仁之乱之后的战国时代,战国大名向神佛祈祷的内容更加现实。战国大名礼拜神佛,一是为了镇护国家,维护统治地区内部的稳定,二是为了攻占得胜,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如果祈祷之后如愿以偿,就要以向寺社进献的方式对神佛表示感谢。一度称雄日本东部的武田信玄曾于1542年攻克诹访后致书诹访上社神长守矢赖真,感谢他的祈祷使战争获得胜利,同时请其继续为自己祈祷“当国静谧”,即领地内政局的稳定。信玄还曾向信浓的开善寺承诺,今后如能继续保佑武田家武运长久、分国平安,就会一如既往地寄进寺领[6]。中国地区大名毛利元就在1557年给三个儿子的《毛利元就遗诫》中嘱咐,“汝等信奉严岛明神,心志要坚”[4]318,因为他认为严岛大明神保佑毛利家获得了严岛之战的胜利。严岛之战发生在两年前的濑户内海,毛利家在这场战争中以少胜多,奠定了称霸中国地区的基础,因此这一战对毛利家具有重要意义。在你死我活的杀戮征伐中,战国大名不关心教义、教派,他们直接将宗教与武士的现实利益,即统治的稳定和战争的胜利挂上了钩。
不仅如此,战国大名在与神佛打交道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人的主体性。这是因为武士在建筑城堡、开发新田、开采矿山、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体会到自己的力量。虽然卜筮和祈祷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已经不仅仅被动地依赖神佛。战国初期的《朝仓敏景十七条》中有:“可胜之战,可下之城,却因选吉日,虑方角,迁延时日,贻误战机,何其可惜。仗是吉日,便飓风中使船,或独骑敌千军,亦必无功。纵为凶日,如能详察虚实,密整军力,善用权谋,临机应变,亦必获胜。”[7]98当时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对超自然神力的崇拜,战国大名能够指出实力和努力比迷信的吉凶之说更加可靠,是因为他们在组织武装力量与敌对势力进行战斗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对人力的信心。他们清楚地知道,神佛的保佑不能代替现实社会中人的实力和谋略。有时候,战国大名甚至会借助神佛传达自己的意志。1564年,武田信玄曾就一事分别于诹访神社的上社和下社求取神签,得到的结果却不相同。于是信玄致书两社,声称自己多年神前礼奠,从无怠慢,上下两宫果然真正用心祈祷,结果理应相同。这显然是把祈祷不成的原因归结为神官的过失。信玄还命令两社在神前重新求签,并许愿,如果祈念成功,将予布施[6]。所谓祈祷成功,自然是指得出信玄想要的结果。想来两社的神官接到这样的书信,对于该如何进行卜筮也是心知肚明了。可以看出,战国大名已经开始在政治统治中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神佛信仰了。
中世社会中,禅宗对于武士的影响也是不能不提的。作为佛教的一支,禅宗之所以受到武士的青睐,原因在于与武士的精神世界十分契合。禅的修行注重直觉,适合精神世界比较单纯的武士;注重意志的磨炼,有利于培养武士推崇无畏而死、视死如归的精神。“禅关心的,不是同武士们讨论什么灵魂不灭,神道的正义以及伦理行为,而是要告诉他们,不管结果是合理的还是荒谬的,只要别人能达到的,你就要一往直前去奔向它。哲学可以借助理性去躲进安全港,禅则直接诉诸行动,而最有效的行动就是一旦决心已下,就要勇往直前、绝不回头。”[8]对于武士来说,禅的意义主要在于指导在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现实的、行动的宗教。武士的禅同样体现了现世主义精神。
江户时代,日本由分裂走向统一,神佛也被纳入了现实世界的统治体系。16世纪后半期,织田信长弹压一向宗之后,丰臣秀吉的全国检地举措深入到了寺社。17世纪初,江户幕府继承了织丰政权的宗教政策,进一步对宗教实行严格的统治。幕府对佛教各宗相继颁下寺院法度,确立本山和末寺之间的主从关系,在各宗派内建立阶层秩序。正规宗教秩序之外的民间信仰则成为取缔对象。僧人在严格的本山末寺组织体系中失去创立新教派、新学说的可能和自由,佛教教义的发展陷于停滞,原有佛教各宗派学理上的差异逐渐淡化。在一般民众看来,寺社主要是满足人的现世利益的场所。人们到寺社祈祷以求治病除灾、开运招福、家族和睦、生意兴隆,为此向寺社进献金钱财物。寺社与共同体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经营性倾向日趋加强。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延续了现世为重的传统。安房国胜山藩主的《酒井隼人(忠胤)家训》说礼敬鬼神和祖先可以振兴武道,“日常敬鬼神,崇祖考。此乃古人之教。……凡有崇敬之心,便可止邪志,兴武道”[5]294;熊本藩主的《肥后侯训诫书》说向神佛祈愿可以消灾免难,“贵贱皆须祈神佛,非是念后世,乃为避今世之灾。比如农夫虽出力劳作,然若不承天惠,亦是五谷无收。自身消灾免难尽在祈祷,朝暮要敬神佛”[3]226。振兴武道,消灾免祸,都属于现实利益的范畴。
同时,近世武士在实际生活中信奉入世的儒家思想。儒学自5世纪初传入日本,在武家政权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为武士所学习,随着文化由京都向地方传播,儒学日益普及并实用化。室町、战国时期的武家家训中不乏引用儒家经典的例子。而儒学思想真正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是在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开创江户幕府之后,日本社会进入和平稳定的时期。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有利于武士阶级政治统治的现世本位、武士本位的御用思想”[9]。朱子学以一套精密的理论形态论证了现世封建秩序的合理性,把君臣父子的上下尊卑关系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天理”的高度,令人们恪守现存秩序以“存天理”。出于维护现世统治秩序的需要,武士采用了朱子学。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在任时,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应用于统治。江户中期儒学者室鸠巢所作、被武家家训广为借鉴的《明君家训》教导武士要礼让谦退、贞信孝悌、亲亲睦族,按照丧礼的规矩为亲人服丧,亲族中有人犯法为之隐瞒,这些都来自儒家道德规范。同为江户中期的武家典制学者伊势贞丈所作《贞丈家训》,以儒家思想的“五伦”、“五常”作为对武士的基本要求,教导武士要具备“心”和“操行”。“武士之心”即“五常之心”,“五常乃仁义礼智信”。“武士之操行”则“以五伦之法为首”,“五伦者,为五类,乃人之五品。一曰父子,二曰君臣,三曰夫妇,四曰兄弟,五曰朋友是也。”[10]89儒家思想被武士作为指导行为的准则,规定了在现实世界中的思想行为,肯定和维护了现实世界的封建秩序、封建统治,构成了武士现世主义信仰的一部分。
通过武家社会发展历程中武士对信仰的态度可以看出,现世主义是武士信仰中的重要因素。武士的信仰主要不是为了拯救灵魂在死后得到一个安宁的去处,而是为了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获得利益。武士在宗教与现实之间毫无障碍地取得了协调,宗教的意义即在于服务于现世。武士在信仰方面的现实性与武士伦理中现世主义、注重实际的因素也是相吻合的[11]。
二、兼容并包
武士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在整个中世社会,佛教都居于社会文化体系的中心地位。佛教自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平安时期已有天台宗、真言宗出现。平安后期以来,佛教势力强大,不仅在思想文化界有重大影响,而且拥有众多的庄园、寺院,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僧兵,与公家、武家相对应,史称寺家。至中世时期,佛教又产生净土宗、真宗、日莲宗、禅宗等许多宗派,拥有众多的信徒。幕府期望获得宗教这一政治势力的支持,很注意恢复和修建寺院,保护佛寺领地。当时佛教文化十分普及,武士往往会在晚年出家修行,或成为在家佛教徒。最早的武家家训作者北条重时即在五十九岁时辞官出家。今川了俊、北条早云、武田信玄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武将名字都是法号或戒名。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中世武家家训体现出浓厚的佛教色彩。室町初期武将的《今川了俊制词》结尾一段论述治国的基本理念:“要人为己所用,临国当如日月普照草木,近侍远臣,隔海隔山,至被官*被官:指中世社会从属于上级武士的、作为家臣的下级武士,他们分得部分屋宅田地,自己经营耕作,同时为主家的军事、家政以及农耕效力。以下,昼夜以慈悲心恩庇纠罚,深思熟虑,量才为用。既为诸武之首,若无智慧才学,处事失当,必受上下非难。行往坐卧,当如佛祖说法普度众生,殚精竭虑,以励文武两道。治国安邦,仁义礼智信,缺一则危。凭正道治罪行无人怨恨,构非仪令死科为叹殊深,且难逃因果之数。”[12]这些论述以佛祖说法的慈悲心比拟临国施政的心态,以因果报应作为对施政者的约束。战国初期的《朝仓敏景十七条》这样讲述领主应有的施政心态:“如某高僧所喻,为人主者,应似不动、爱染两位明王。不动提剑,爱染持弓,其心却不在刺射,但在降伏,慈悲深重。为人主应扬善惩恶,明辨曲直,除一恶救百善,方可称慈悲之杀。”[7]104将武家领主治国的政治行为定位为“扬善惩恶”、“除一恶救百善”、“慈悲之杀”,可以看出深厚的佛教思想底蕴。
尽管佛教居于中心地位,却并没有排斥本土神道信仰的存在。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通过为共同体繁荣的祈祷、祭政一致的体制以及崇神敬祖的教育,为行为准则更具约束力提供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源于自然崇拜的神道形成了日本人心灵深处的文化积淀,使他们本能地看重自发的、本源的、自然的东西。武士最看重的是发自本源的正直之心。《极乐寺殿御消息》有多处强调“心正”、“持心正直”,“以弓箭之道为首,诸事上扬名显德,莫不以持心正直为要。”“我邦为神国,如持心不正,何以报神明。”[3]72,80《竹马抄》、《早云寺殿二十一条》等许多家训都把“居心正直”作为最关键的因素反复强调。内在的、本源的心意重过所有虔诚礼佛、拜殿参社的外在形式,这一点来自于本土神道无教义无仪典的自然崇拜信仰。
在中世武士的信仰世界里,神和佛是相融合的。神道没有固定的组织、教义和仪典形式,就连“神道”这一概念也是在接触到佛教之后比照本国传统信仰进行反思后才形成的,对自身界定的模糊和淡漠为融合异种宗教提供了可能。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宗教并无西方国家常见的排异性,甚至不同宗教神明之间的界限也可以是模糊的。产生于平安时期、流行中世的宗教解释有“神佛习合说”、“本地垂迹说”,都是将神和佛以某种特定形式联系起来。进入中世以后新产生的以神道为主体、佛儒为附属的“伊势神道”、“吉田神道”,虽然在侧重倾向上不同于之前的佛主神从说,但同样反映出对异种信仰的吸收,与传统的宗教思想是相通的。当时,日本神社和佛寺往往同在一处,从组织形式来看,寺院的镇守神社、各地的神宫寺以及其他很多神社往往都由僧人管理,僧众和神官一起从事社会活动。一般大众更加无意将佛和神截然分开。神作为佛的化身被包容在佛教中。
作为其表现,武家家训中经常“佛神”或“神佛”并称。由于当时的佛教中心思想,从两者次序来说,先佛后神的还要多一些。镰仓时代的《极乐寺殿御消息》中有:“神明如镜照人心,无所不见,因其唯愿人心正直故也。……欺世瞒人,必受加倍果报,惜愚者不知也。”[3]80“神明”是神道的神,“果报”的说法却来源于佛教。室町初期的《竹马抄》中有:“所以佛不导人行恶事,为人常保心灵清静……便是从不拜殿参社,只要居心正直,慈悲为怀,神佛亦有眷顾。尤其伊势大神宫,八幡大菩萨,北野天神,只宿于居心正直清静之人头脑之中。”[4]230将外来的佛与日本的神并提,认为佛的眷顾和神的护佑是可以同时获得的。战国大名的《早云寺殿二十一条》中有:“虔诚礼佛,固然当行,然正直和平之心,尤为紧要。敬上怜下,去伪存真,有便是有,无便是无,方合佛意。即便不求,但凭是心,必有神明护佑。存心不正,天道所抛,拜也无用。”[4]262同样是说可以得到神、佛共同的保佑。神道和佛教这样的异种宗教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求神和拜佛在武士的意识里是没有分别的。
中世武士也同时接受儒家思想。儒学自5世纪初传入日本,即为统治阶级所学习。镰仓时代,朱子学与禅宗一起传入日本。应仁之乱以前,朱子学主要流播于五山禅僧和京都的贵族、博士之间。武家社会的上层武士由于接触贵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室町初期的《竹马抄》、《今川了俊制词》中已经出现“仁义理智信”的表述。应仁之乱以后,群雄割据,战乱频仍,贵族、禅僧、博士为逃避战乱纷纷离开京都去依附地方大名,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也开始大规模流传到地方。战国大名纷纷招募儒学者作为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为其统治和扩张服务,儒学在此过程中日益普及化、实用化。当时阅读中国典籍是武士学习文化的重要途径,很多武将家训都显示出作者的儒学教养。多胡辰敬家训中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语,朝仓敏景引《论语》“君子不重不威”,《早云寺殿二十一条》也出现撷自论语的“三人行,必有吾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尤其是《武田信繁家训》,每一条都是引经据典,引文出自《论语》、《尚书》、《史记》、《汉书》、《帝范》、《臣轨》、《孙子》、《吴子》、《三略》、《碧岩录》、《禅林集句》等许多典籍,可以说是中世家训运用儒家经典的典型例子。武士的儒学修养与他们敬神礼佛并不发生抵触。朝仓敏景为巩固统治一度联合宗教势力,今川了俊、北条早云都是晚年出家,具有丰富儒学修养的武田信繁在家训中鼓励参禅,教导要尊重僧人。在武士心中,儒家思想与神佛信仰是和平共处的。
到了江户时代,由于武士从“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角色转换的需要,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代替佛教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许多家训基于儒学原理向武士提出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儒学者室鸠巢所作的《明君家训》。家训共二十条,以一藩主君的口吻对家臣提出了行为上的规范。家训要求武士读圣贤书效仿古人行止,注重个人操守,要做到忠信孝悌、固守节操、礼让谦退、生活简朴等等。针对丧失战斗职能以后武士中出现的困惑与堕落的现象,最后一条集中阐释了武士应该承担的职责——守“义理”。士农工商四民中,其他三民都有具体的职业,“农事耕作,产出米谷,工或为匠人营造屋室,或为陶冶制造器物,商营商卖以通有无,此三民皆致用于天下”,而武士不事生产,职责即在于司掌义理。“只将义理一事定作士之职也。”义理虽然无形无色,却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社会如果丧失了义理,则“人无廉耻之心,相欺相掠,无所忌惮,终致子不以父为父,臣不以君为君。”“士使其守义理之规,故置于三民之上。”[10]81可以看出义理的根本意义在于既定的统治体制、社会秩序。武士在个人操守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符合作为士的规范,才有资格作为统治者履行维护义理的职责。《明君家训》针对新形势下武士面临的如何将个人的价值实现纳入国家统治体系的问题,基于儒家理念为武士实现人生目标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由于适应了形势的需要,该训自1715年出版以来在武士中广为传播,影响极大,以至于有“登城之士,人人怀揣一册”之说[13]。这说明《明君家训》绝非被束之高阁的空谈之论,而是在武士的实际生活中切实发挥着指导作用。
推崇儒教并不等于排斥神佛。江户中期著名典制学者伊势贞丈的《贞丈家训》中论述了儒家思想与神、佛的关系。“日本国中之人皆为神之子孙,要敬仰神明,不可亵渎毁伤。只要居心正直,不需祈求,神明自佑。所谓正直头脑中有神灵是也。心如不正,则失五常五伦之法,纵使祈求亦不得护佑,反受其罚。”“佛为天竺国之神。虽非日本之神,然自古得本邦敬仰,应随世间风习。人云,佛者,可护佑死后之世。此世持正直心,不失五常五伦之法,善守为人之操行,来世必成佛。此世悖五常五伦之法,肆意妄为,操行如畜牲,则来世必沦为畜牲。如何祈求后世,供养佛祖,建立寺堂,若以恶心操恶行,必堕地狱无疑。”[10]95也就是说,神明、佛法都应该敬仰尊重,具体表现都是“心正”,即在现实生活中遵守儒家的“五伦”、“五常”之法。儒家道德作为行为实践准则,与信仰神佛仍然是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伊势贞丈的神、佛、儒相结合的理论阐释。江户时代,尊崇儒学的武士依然信仰神佛,这样的观点在家训中十分普遍。很多具体的制度规定能够体现出武士日常生活中神佛的影响力。有的基于佛家思想的影响禁止随意捕鱼捉鸟,无益杀生;有的规定每年都要派人前往日本最大的神宫——伊势神宫参拜;有的训诫各种神佛法事仪典均要依照执行,不可违背错失……神和佛仍然保持着相容的状态,在信仰世界中占据着自己的位置,与儒家思想和平共处。社会上也依然是寺社不分,直至江户时代结束。
纵观武家社会发展历程,在武士信仰中,异种的信仰是融合的。自武士阶级出现以来,神、佛、儒一直并存于武士的信仰之中,作为外来信仰的佛、儒与传统的神道之间表现为兼容并包的状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武士信仰的重心是有所不同的。中世武士信仰的重心在佛教,近世武士信仰的重心在儒学。而神道作为本土的信仰,作为内化了的最核心的精神力量始终浸润着日本人心灵的深处。武士看重内在的“正直”、“清净”、“心正”超过外在的形式,这一点在武家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贯的继承。
三、结 语
可以说,现世为本和兼容并包是武士信仰的两个特点。
一方面,武士信仰一直保持着现世主义特色,信仰的重心不在“彼世”而在“此世”,信仰与现实世界的利益挂钩。这与武士的社会存在密切相关。武士是以武艺为家业的职业军人,要关心军事技术,应付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同时又是组织农业生产、掌握财政收支的管理者,要关心生产技术、财用分配。这就决定了武士的行动既不能以兴趣为出发点,也不会以思想上的道德完善为标准,他们信奉的是现实的利益。今天的日本人为了家族平安、入学晋升、交通安全等现实问题去参拜神社,仍然是以现实利益诉求为根本的。在日本人看来,信仰并不是人的心灵归宿和本源需求,而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为现实中的人的需要服务的。他们让宗教为现实服务的时候丝毫不会感到心理上的羁绊,这一点与将信仰内化为心灵永恒归宿的宗教信徒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武士的信仰世界不是单一的,而是在保持了本土信仰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信仰文化。在武家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神、佛、儒都为武士提供了精神食粮,并在武士的精神世界里和平共处。武士道源于神道、佛教、儒家思想的看法已经成为共识。没有具体的教义和规范的神道在融合佛、儒时表现出了灵活性和柔软度,社会上普遍的思想状态是三教一致,认为这样才能保障共同体的安宁和幸福。可以说,武士一旦发现外来信仰在现实世界的用处,就能够把它融合在自己原有的信仰中加以利用,这一点也体现了注重实际的传统。今天的日本人仍然生活在神、佛、儒兼容的世界里,每逢新年等重大节日或有所祈愿时都会到神社参拜、祈祷,也不妨碍他们死后举行佛教法事归葬于寺院,而经过日本风土过滤的儒家文化更是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人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不会感到任何的不协调。
武士信仰的特征反映了日本人普遍的信仰特征,而且在当今日本人的信仰中仍然有所体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士伦理对于日本社会的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 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评介林景渊著《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J].世界历史,1994(3):106.
[2] 赵建国.终极关怀:信仰及其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6.
[3] 山本真功.家訓集[M].東京:平凡社,2001.
[4] 小澤富夫.家訓[M].東京:講談社,1985.
[5] 小澤富夫.武家家訓·遺訓集成[M].東京:ぺりかん社,1998.
[6] 武田信玄致书等事[M]//笹本正治.戦国大名の日常生活.東京:講談社,2000.
[7] 吉田豊.武家の家訓[M].東京:徳間書店,1972.
[8]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陶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2.
[9]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01.
[10] 石井紫郎.日本思想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M].東京:岩波書店,1974.
[11] 许译兮.日本武家家训所见之伦理[J].日本研究论集,2007.
[12] 第一勧銀経営センター.家訓[M].東京:中経出版,1979:60.
[13] 近藤斉.近世以降武家家訓の研究[M].東京:風間書房,197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