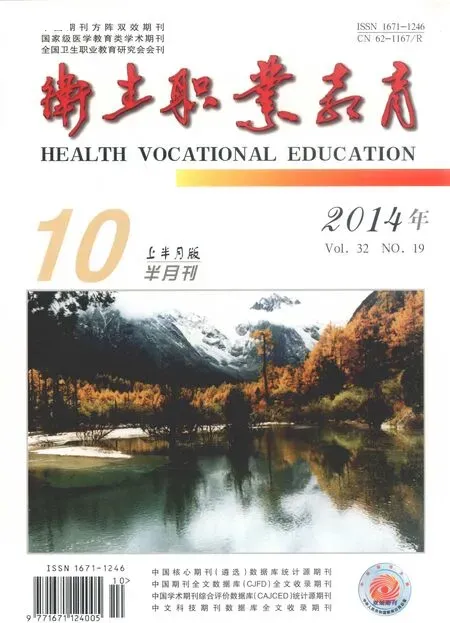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学关系新探
张宝石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都匀 558000)
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学关系新探
张宝石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都匀 558000)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呈现新的态势。本文重点探讨两者的关系,为医学发展提供参考。
生命伦理学;医学人文学;关系
2012年6月,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主要用于约束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行为。中国医师协会的《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平均每家医院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病人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师5人,医患矛盾有激化趋势。而在频发的医疗纠纷中,因技术原因引起的约为20%,其他80%均源于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医德医风问题。在21世纪初,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出台《全球医学教育基本要求》,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沟通技能培养列为医学教育重要的教学目标,认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当代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主要通过医学人文学和生命伦理学教学、实践展开,然而,在教学和实践过程中,并没有理清二者的关系,甚至有学者将其彼此孤立。为此,本文重点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旨在为医学发展提供参考。
1 体悟生命——生命伦理学的现实起点和归宿
生命伦理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纽约海斯汀中心。生命伦理学由医学伦理学演变而来,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它利用伦理学理论、原则、规范和范畴探讨生命的终极问题,对人的生命状态、本质、价值和意义进行道德追问,对医学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不在于对某一种或几种道德理论的应用,而是研究和创制适应于生命本体或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哲学理论;它不仅限于解释与论证生命行为和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合道德性,而且必须帮助人们努力认识生命的所有问题或难题。生命现象、生命技术、医药卫生等的伦理问题,仅仅是它十分表浅的研究内容之一,对灵性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哲学化注释,是其重要的使命。”[1]历史上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从未中断,无论是将其作为元伦理学还是规范伦理学。在宗教神学控制的中世纪,神的视角将人的欲望、自由和意志贴上原罪的标签,人的降生过程就是承负罪孽与赎罪的过程,他的幸福在于对上帝的信仰、希望和爱,在于进入天堂的刹那。因此,生命伦理实践就是按照神的信仰进行宗教道德实践。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生命伦理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医学领域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对传统伦理道德提出新的挑战。如心脏起搏器可以让垂死的病人继续存活;可以在产前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可以依靠新技术对器官衰竭的病人进行器官移植,但这引起医疗资源分配公正问题;安乐死可以结束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病人的生命,但这又与行善原则、不伤害原则相冲突。再如阻止有缺陷新生儿的诞生是否违背人道主义?结束无脑儿的生命是不是伤害病人?生命伦理学就是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
2 直观生命——医学人文学责任与窘境
医学人文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20世纪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勇气面对那些曾经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如急性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等,现代医学从预防疾病、减轻病人痛苦、恢复健康发展成为包括探索生命奥秘在内的复杂体系。现代医学技术为人们提供的保健服务日益增多的同时,人们对医学的批评也日益增加,因此,不得不反思医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是什么。
医学人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追问人以何种方式生存,人的生命如何存在,医学人文学不仅肩负着使医生人性化的使命,更肩负着使医学人性化的使命。中国明代医家孙志宏认为,“古之良医,不敢逞臆见而务博学,又不敢泥俗谛而求诸阅历,又不执一二证验而求圆变无穷之心悟。至老手不释卷,虚习常广咨询,诚以人命为重,自存德行也”[2]。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从东方到西方,医学人文学始终作为一种活的灵魂鞭策着医生的职业精神,强调一种人性化的诊疗艺术。纵然医患矛盾愈演愈烈,但只要医生具有专业知识与技术、理性的判断力和自信心、诚挚的态度和良好的交际能力,医生和病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损伤、信任的缺失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进入20世纪以后,“技术至善”论占主流。该理论认为,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器官可以效仿机器的零件,只要损坏或功能减退就可以随意更换。这一理论也对医生产生了消极影响,他们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实验室,以不断更新医疗诊断技术,而聆听病人倾诉的时间急剧减少,只关注病人的躯体忽视其情感。与日俱增的医疗事故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生物医学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意识到现代医生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和平衡。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普朗克所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3 敬畏生命——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
医学人文和生命伦理有其自身的精神谱系,既具有守护传统、呵护心灵的一面;又促使人具有爱智、批评、反思和创新,将理想、人格、命运、信仰等聚合在一起,构建个性十足的精神共同体。但是,它们作为特殊历史境况的产物,与政治气候、经济现状和文化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直接影响人们的态度和决断。面对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们不再是书斋里的谈资,也不是博物馆里的亡灵,而是具有历史气魄、充满责任和担当的人文斗士,将自身化作时代的精神地标,指引着公众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
从严格意义上讲,医学人文学迄今为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定义,但学者们有一共识,即它不是单纯的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作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它涉及人文学科,也涉及社会学科;它探讨生命、痛苦、快乐等形而上的领域,也关注健康医疗、卫生保健等形而下的现实。因此,我们回首医学人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会发现推动其前进的直接动因无疑是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伦理问题。正是当代医学科学的许多成果需要各种人体实验来检验,才引起人们对人体实验伦理道德的关注,《纽伦堡法典》等伦理学法规的问世就是佐证。正是医学人文学独特的学科属性,促使其成为生命伦理学重要的理论基石。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生命、死亡、疾病、健康、病人权利、医疗资源分配等现实问题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生命伦理学家致力于生命伦理基本理论研究,力图为生命伦理学的实际应用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撑。其中,恩格尔哈特就是杰出代表之一。他认为道德哲学应“既认真地看待道德多样性,也认真地看待其信仰,并且为生命伦理学和保健政策提出了共同的俗世道德观。它为宽容辩护,但并不否认道德内容可以相互分离并可以进行谴责”[3]。严格意义上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是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他对“道德主体”的论述虽然更接近于生命伦理实践,但他的生命观也存在理论缺陷,如他认为婴儿、严重智力障碍者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生命伦理学作为“显学”,根本目的是为行为主体提供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为身处道德困境的行为者提供合理的价值取舍。然而,生命伦理学的德性与价值智慧需要通过医学人文学来完成,生命伦理学既要汲取道德哲学的理论营养,也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将文学、艺术等学科作为交叉研究。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人文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呈现新的态势,两者的融合不但能守住生命的疆界,而且能展示生命绽放的炫美。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所有的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分支。他们都是为了升华人的生命,把人的生命从物质世界提升出来,并把人类引向自由王国。”
[1]张大庆.医学人文学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孙志宏.简明医彀[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3]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G420
A
1671-1246(2014)19-0025-02
贵州省卫生厅、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联合基金项目“生命伦理视域下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实践途径研究”(Gzwkj2012-2-016);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基金项目“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伦理精神的实践途径研究”(QNYZ20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