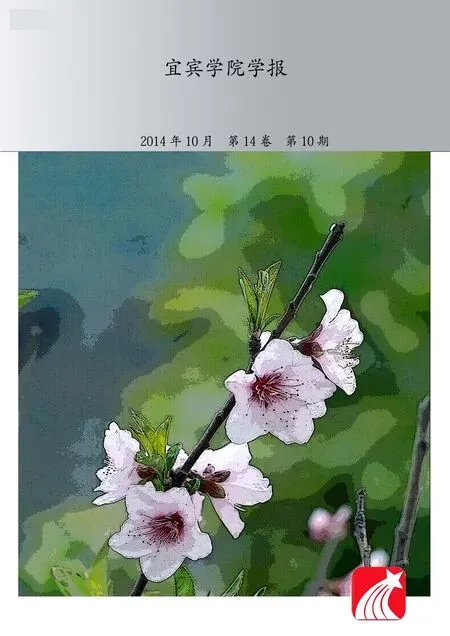冷静批判下的浪漫书写
——评叶弥长篇小说《美哉少年》
李姝铮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美哉少年》是叶弥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位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江苏女作家,亲身经历了文革带来的动荡和不安,由富庶温润的江南名都苏州辗转流离到偏僻贫穷的苏北农村。生活差异、文化差异、社会地位的差异都给当时年仅6岁的叶弥留下不可弥灭的印象。而这样的经历也深刻影响了叶弥的文学创作。叶弥在她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多部的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如《粮站的故事》《明月寺》《成长如蜕》《去吧,变成紫色》等。这些创作都得益于其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叶弥笔下的文革题材小说,都可以拿捏得当,厚重又不失飘逸,显示出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较高的文学价值。《美哉少年》就是以文革为背景,展现少年在政治运动冲击下的成长历程。在叶弥的小说中,少年成长是一个重要的叙述视角和叙述主题,对这一主题的解读不仅益于理解叶弥的小说创作,也益于通过评析特殊时期少年成长而获得对现实的关照与反思。在《美哉少年》的创作中,作者采用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超越特定时空的人性思索,为读者展现了文革对人性的异化和少年对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浪漫的书写方式使小说在严厉中不失温情,表现出独特的创作和审美风格。
一 旁观视角下的冷静批判
《美哉少年》讲述的是文革背景下,遭遇生活颠覆,父权崩塌,丧失母爱后的十一岁少年李不安以反抗的姿态出走,追寻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归属的成长故事。[1]主人公在他的出走路程中经历了欺骗、饥饿、偷盗等人性丑陋的一面,也在这一路程中学会了责任、感恩并最终成长。小说的时间跨度并不大,从李不安出走到回归不过短短数月。而在这样的时间跨度里,李不安从一个叛逆的、受到文革冲击而异化了的孩子,通过在出走路上的所见所闻所做,逐渐成长为心智成熟,学会感恩,学会发现生活的美好的少年。作者的写作重心并不在文革带来的伤害,而是以一种理想浪漫的的方式,对青少年的理智与情感的成长展现出审美的关照,因此,小说的叙事动力也不仅仅来自对历史的批判,也是来自人性的美好与特定时代发生冲突矛盾后,并最终由异化转为回归的历程。叶弥的创作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旁观的姿态最大化地给予小说叙述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消除生理心理等因素对小说的影响,从而能够灵活自然而又冷静客观地反映社会,完成现实书写。小说中的李不安最初的形象正是当时社会大部分孩子的缩影,文革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挥之不去的伤害,不安和恐惧始终伴随着他们。虽然李不安的父母亲一直努力维系着看似安稳体面的生活,却无奈地被政治运动打破。父亲李梦安因为被怀疑在县城写反动标语被捕入狱,母亲朱雪琴性情软弱,无法独自承受动荡社会和艰辛生活带来的压力,同时也为了打听丈夫的情况,不得不委身于大队书记孙二爷。而这一幕,恰巧被李不安亲眼目睹。这个少年崩溃了,没有人知道他这种隐秘的感受,也没有人能明白他被击垮到何种地步,他的“母亲”没有了,他赖以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突然消失无踪。母爱的丧失,父亲又因为知道了妻子与孙二爷的奸情而负气出走,李不安的家庭终于崩塌。在这样的崩塌之下,李不安学会了恨,他恨父亲的自私绝情,恨母亲的失贞软弱,恨孙二爷仗势欺人。在动荡的政治背景下,单纯的少年被扭曲异化,固执地走上一条出走之路。然而,受到政治运动影响而异化扭曲的人又何止李不安一个?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李不安的童年玩伴,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小翠子家庭贫困无力上学,每天都要做繁重的家务,切藤喂猪洗衣服作晚饭,甚至没有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与李不安从“敌人”到朋友的张小明,十几岁就开始代替母亲作售票员工作。他的母亲为了挽回在外面风流的父亲,在张小明14岁的时候就给他定了亲。作为村里小学校长的孙大舅读过三年私塾,数学上只会加减法,不会乘除法。他毕生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把课文念得听上去有点像普通话。“杀杀燕子五只枪。”他就这么念“飒爽英姿五尺枪。”人文缺失和政治运动的内外挤压,让这些孩子承担起了孩子不该承担的责任,又让他们接受不到应有的教育。社会让这些少年拥有了超越年龄阶段的成熟和强烈的独立性意识,然而却没有给他们提供接受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的教育,这使得本就自控能力不强的少年出现自相矛盾的行为,甚至畸形成长。文革给予整个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恐怕是对于孩子成长所造成了挥之不去的灾难,并使他们始终游离与人类美好精神家园之外。[2]叶弥的小说表面往往不起波澜,却能够在平静的叙述之下,借助于形象精确的细节描写,展现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活动,透露出残酷的真相,给读者带来深刻的思索。[3]如小说中李梦安到小学校长孙大舅家的情景:“长板凳放在孙大舅的屁股后面,两碗茶一碗放在长板凳上,一碗端给李梦安。她(孙大舅的女人)说:‘李老师,坐。’李梦安闻声坐到板凳上,又端着水认真地想了一想,离开板凳蹲到一边去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却包含了巨大的信息。叶弥用这一坐一蹲的动作,形象地展现了文革时期受到批斗的知识分子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面前,人生来拥有的平等权荡然无存。这样鲜活生动、充满“即视感”的细节画面,拉近了小说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更深入地走进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在小说中,面对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和对少年成长的消极作用,作者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竭力地细致展现人物形象的真实生活,并对这种生活保持尊重,极少妄加指责评论。作者这种“作壁上观”的写作方式,使得小说所有的是非对错都由读者自行判断,作者成了单纯的叙述者和引路人,留给读者更大的思索空间。《美哉少年》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之下,将批判不动声色地融于人物不经意间的言行与毫无造作的情景之中,尽可能保持了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人物心态,借助于人物自身的行为来还原历史的真实。[2]
二 超越时空的理性思索
《美哉少年》虽然以文革时代为故事发生发展的背景,但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革题材小说以反映文革本身为主题不同。《美哉少年》并不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一般,把小说的思想主题、情节结构,甚至小说人物的命运都交由文革这一先行主题来决定,而是大大减少小说中文革内容的分量和地位,把文革作为小说叙事的背景,仅仅是小说主人公成长经历的大环境。[4]在这样的文本叙述方法下,文革的权威被淡化,甚至成了一种回忆,一种想象,一个故事的起因。这样的写作方式,给了小说更大的自由度,使得小说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表现手法都更趋于多元化。在《美哉少年》中,文革成了李不安最初性格形成的外部环境,是李不安出走的主要因素。但在李不安的成长过程中,文革的因素被淡化了,具有更普遍性更广泛的影响力和批判意义。如李不安在火车上遇到了叫做章四瓦的女人,这个女人看似像母亲一样关心着李不安,给他食物,给他“抓虱子”,却借机猥亵了这个十一岁的少年,给李不安的身心成长带来巨大伤害。在性意识还处于懵懵懂懂的年纪,李不安以一种被迫的姿态接受了“性启蒙”,这样的故事不仅关注了少年的身体成长,也对那些即将达到青春期的少年,在面对身体变化时产生的敏感、畏惧、好奇、自我防卫等情绪给予了关注。除了李不安,作者还塑造了人生导师一般的人物形象老刺猬。老刺猬年轻时有个显达响亮的名字叫于光达,却在三十岁时把名字改成了卑贱的名字:老刺猬。只有当人处在极端卑微绝望的境地时,才会觉得连响亮一点的名字都成了侮辱。老刺猬甚至后悔没有给自己起一个更轻一点的绰号,当认定自己生来就卑贱时,才能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活下去。虽然轻贱自己,老刺猬却分外爱惜纸墨。煤渣化在水里自制成“墨汁”还要时不时用筷子搅动它,不然水里尽是化不开的小煤渣,“写在纸上面,对不起纸。”在老刺猬眼里,自己可以被社会轻贱鄙夷,但纸不可以,文化不可以,知识不可以。即便生活贫困不堪,他也要尽最大努力维护他心中的圣地。一个重视知识、尊重文化的人,却要不断轻贱自己,尊严成了生活的最大痛苦。小说没有介绍老刺猬的生平,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只能从他曾经的“于光达”这样的名字中看到父辈曾对他给予的厚望。在作者的描述中,读者了解到这个人虽然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却愿意收养小瞎子平安,愿意收留流浪的不安,愿意省下自己的口粮接济生活更加困苦的唐寡妇……老刺猬这个形象在《美哉少年》中是近乎完美的,也是矛盾的。他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却坚定地教导孩子们融入社会,他坚持教平安写字,因为坚信“会写字了就不会造反”。老刺猬在贫困卑贱中隐忍,却对下一代充满希望;他可以放弃尊严,却绝不放弃道德;他忍受着社会的不公,却始终怀抱感恩之心……这样一个善良坚韧的人,为了满足母亲想吃鱼的愿望,在初冬下河捕鱼而得了感冒,无钱医治死于肺炎。老刺猬的人生引起读者的好奇与思索,这样的思索就是作者的最终意图。在叶弥冷静的叙述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人的尊严被践踏,文化被轻贱,生活变得愚昧而麻木。这样的批判,显示出作者的思索已经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以高屋建瓴的姿态表现出对人类社会中残缺人性、病态文明的强烈控诉。
三 理想审美下的浪漫书写
在阅读《美哉少年》时,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作者不动声色的批判,也可以感受浪漫的诗化书写。李不安的遭遇,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作者用一种浪漫的方式讲述一个现实的故事。小说中随处可见那些充满爱意的画面。如李不安在出走时与玩伴小翠子约定,在“春天,飘絮的时候”回来,和小翠子一起解救那些被顽皮孩子捞出来仍在土地上的小蝌蚪;李不安和与他年龄相仿的张小明,因为彼此的母亲不和得缘故而结成“死敌”,却在打了一架之后成了无话不谈的“结拜兄弟”,张小明甚至冒着被父母责骂的危险给李不安偷了车票,促成了李不安的出走……孩子的这些童心并没有被残酷的社会所磨灭,而是以一种原谅的姿态,展现着人性美好的一面。除了这些充满浪漫气息的画面,叶弥对整部小说的构造也具有浪漫的审美色彩。叶弥在小说中的创作思路非常清晰并且理想化,主人公经历着“出场——遭遇成长困惑——出走——经历社会磨砺——引路人指导——成熟”这样一个大部分成长小说主人公都延续的一条道路。[5]在遇到老刺猬之后,不安的人生走上了一条向着真、善、美而去的光明之路。这是一条“单行道”,在这条路上作者有意忽略了成长期人性的自我矛盾,强化人物更自觉的道德行为,削弱成长过程的片面性与主观性。这样的设定,不能不说是充满着浪漫与理想化。小说在批判的同时也带有希望的积极乐观情绪。这样的成长小说充满了浪漫化的理想色彩。在《美哉少年》中,除了人生导师老刺猬的循循善诱外,每一个人性的闪光点,几乎都会出现一位起着“模范”作用的人物出现,通过言传身授,带给李不安美好的教育。如善良的王彪叔,明知李不安偷了他家的鸡,却为了维护李不安的尊严而没有点破,让李不安学会了知错而改;总是来老刺猬家“蹭吃蹭喝”的唐寡妇,总是拿走老刺猬的一半口粮,给老刺猬纳着永远也纳不好的鞋底,缝着永远缝不好的棉衣。然而这个女人却在动荡的生活中独立抚养四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哥嫂和姐姐的孩子。唐寡妇的存在让李不安学会包容与怜悯;老刺猬死后,不安承担起照顾平安的任务。他要给平安做饭,督促平安练字,承担起家庭的担子。他不能丢下平安不管,平安让他学会了责任……这样的浪漫与理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但也深刻表现出作者对生活,对少年的殷切希望,以一种母亲般的姿态温暖关照着他们。值得一提的是,叶弥并没有在这样的温暖浪漫中迷失方向。与大多数成长小说最终以融入社会的和谐姿态作为结尾不同,《美哉少年》中李不安虽然人格得到了完善并最终回归了家庭,但大的社会格局并未改变,除了小翠子的死亡,一切与李不安离开前别无两样:李不安仍然不愿上学,父亲继续看他的美女图,母亲仍在看她的菜谱,学生们还在学着“杀杀燕子五只枪”……这样的回归是无奈的,讽刺的,是对社会环境影响少年成长的深刻反思。
叶弥曾说“每个女人都是诗人”[6]。在叶弥的小说中诗思与诗的语言随处可见。如小瞎子平安,看不见东西,却坚信镇长女儿月香送给他的糖纸“会化成水,就是化成太阳那样的颜色。或者化成一道烟走了……烟也是太阳那样的颜色”。这样纯真可爱的想象让读者怜惜之意油然而生。如李不安回家后去看小翠子的坟,作者这样描写:“解冻的土壤里有什么?有小翠子好看的头发。小翠子又长又黑的头发给严寒冰在土壤里,拉都拉不开来。现在解冻了,她从土里拉出她长长的黑发,不知对谁露出甜甜的微笑。”“蚂蚁成群结队地从草根里爬出来,苍蝇栖在枯草的顶端,在风中惬意地飘荡。第一只蝴蝶是不是早就从它的窝里爬出来,在太阳下面晒它麻木的翅膀?鹅和鸭子在没有冰块的河里欢快地嬉闹……生命极端膨胀的地方,就是生命大量消亡的地方。”这样充满诗性的话语在叶弥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浪漫话语让原本充满矛盾与批判的文章瞬间变得活泼明亮起来。舒缓的节奏、梦幻般的描写、形象的比喻和拟人,显示了叶弥深厚扎实的语言功底。这样的诗性语言,也消弭了小说中剑拔弩张的对抗色彩,让读者在沉痛的反省与思索中又不失对未来的希望。
结语
叶弥对李不安成长历程的描写,表现了这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注与思考。在她冷静的批判与浪漫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人性关怀。面对对荡社会给人性所带来的异化,叶弥毫不客气地揭露并批判,但叶弥并未对这样的人性失去希望,她渴望着每个少年都能够在成长中学会真善美,而这样的愿景,需要社会中的每一员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春红.追寻成长的精神轨迹:从叶弥小说看其创作心态[J].山花,2012(7):123-124.
[2] 张蕙.理智与情感的审美关照:评叶弥小说《美哉少年》[J].枣庄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4(6):28-30.
[3] 刘新锁.生活像藏在棉花里的针:读叶弥的《猛虎》[J].当代作家评论,2005(2):140-143.
[4] 余涛.另类的成长[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9.
[5] 易立君,刘彬.《看不见的人》: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7):43-45.
[6] 叶弥,姜广平.我太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了[J].西湖,2008(6):9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