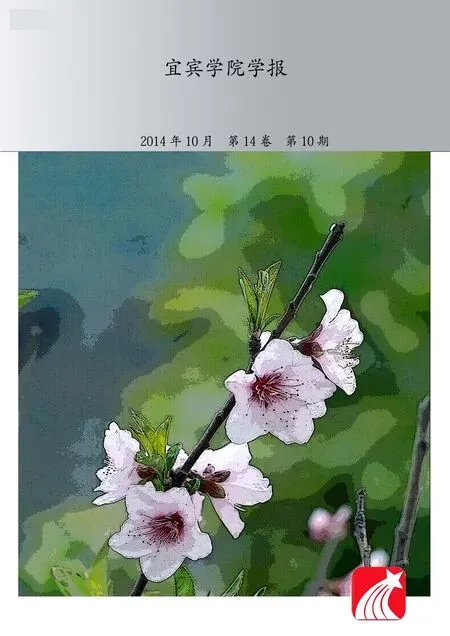唐君毅先生诠释二程学“性理”义之方法探源(下)①
邓秀梅
(环球科技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五)伊川之“心主性情”论
唐氏特别标明伊川学的基础在性情论,理气论乃后来之派生。明标此论点用意即在不使伊川学流于悬空之思辨哲学,盖伊川的性情之论为源于人对其道德生活之省察,自然引出对其心之性情二面之省察,顺此再推拓至天地万物之理气之省察。性情与心原是一体,不可分离,即便伊川严分性情之异,然不碍心为整个之一心。
1.心、性、情之关系
关于性、情二者,伊川的解说十分清晰,即“性为情之体,情为性之用”。诸如仁与恻隐之情、孝弟之用等,伊川说: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1]182
论“孝弟为仁之本”则分辨道:
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1]183
以“体用”模式论仁与恻隐、孝弟,则仁是体,恻隐、孝弟是用;以“性情”论,则仁是性,恻隐、孝弟是情。性和情截然划分为二,伊川之意相当清楚。然则性、情与心之关连又如何?
问:“仁与心何异?”曰:“心是所主处,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则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说仁者心之用,则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谓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未可便谓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榖之种,必待阳气而生。”曰:“非是。阳气发处,却是情也。心譬如榖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183-184
唐先生区别二程小异,其中之一即是伊川于种种名义有分别肯断之论述,此处分辨心、性与情即为显著之一例。此引文最引人再三致思的地方就是言“仁是心之用”可,言“仁者心之用”则不可,其次“仁是就事言”一句也须仔细推敲方能得其意。依唐氏之解,所谓“仁是就事言”者,
此就事言者,言就心之事而见也。由仁必由心之事而见,而此心之事,即心之用,故可说仁是心之用。此所谓仁是心之用,乃谓于心之用中,见有此仁性之显,亦见心之依其仁性,以成此心之用。此即如心之自用其仁,以有其心之事,而此仁自在此心之用中。[2]171
仁若为性、为体,岂可为他物之用?伊川直说“仁是心之用”实有不通处;然唐氏却能从此处转而表达伊川之重要义理。伊川所著《颜子所好何学论》有云:
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3]577
最后一句“性其情”,意谓此情之发非感物而动、随物而流转之情,乃是依仁义礼智信之性而生之情,换言之,此情为仁义礼智信之性之表现。情之表现性体有全、有不全,大约唯有圣人方能将性之全体朗现无余,一般人仅能表现一、二分,而夹杂其他不善之情欲。人固可使情为其仁义礼智信之表现,但未必可以使其情将性之全体加以表现,由此处看,则见情与性之有分。即使不夹杂其他不善之情欲,而纯粹表现仁义礼智信之性,唐氏依然认为此至纯粹之情也未必能同时表现此五性,一情恒只表现一性,纵使其人表现五性一如仁时,亦不能穷此一性之可能有之表现,而表现此性之全。[2]170亦即当人表现其对人物之恻隐之爱时,此固能表现其人之仁性,但仍不足以尽此仁性所可能有之表现,此人纵至博爱而无所不爱,也只是自己有之博爱事上言,此能博爱之仁性固仍有未表现于此一切已有之博爱之事者在。此即伊川说“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以及反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的原因,孝弟非仁之本,乃为行仁之本,伊川之意亦在此。
此义若明,则“仁是就事言”便可了然无碍。盖性必由情得见,而诸情之发必然由心,每一情之发露即是心之事也,是以唐先生解释道:“由仁必由心之事而见,而此心之事即心之用,故可说仁是心之用。”但不可说“仁者心之用”的缘故在加一“者”字,乃表示将仁单独提示别出,以说其为心所用,此无异视仁为心所用之一物,此则大不可。伊川取四支和身体譬喻心与性之关系,心如身、四支若四端,四支属于身,然不同于身所用之物;同样的,仁固是心之性,而属于此心,但非心所用之物。伊川之种种解释为的“是要在一心中分性情,更由四端之情,以见性之是在此心之用中,然同时亦绝不许视此性为心外之物,而为心所用者。”[2]172由此以证性、情俱属于心,心便如一榖种,生之性即是仁,阳气发处是情,榖种阳气所发处,即其有生发之事处。榖种本身自是一整体,以喻心乃一整个之心,生之性就在其中,以为其生发之情之所依。伊川所言“心是所主处”,“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1]204性、情之绾合就落在“心”处,性之寂然感通也在此。
2.心为一整个之心
唐氏定位二程学之时,曾明言:“自明道言‘天人不二’‘天人无间’,则更无此天人之内外,而只有一心之内外之两面。”[2]164言下之意自是明道以前,例如张载,便是先于天人关系分内外,而后再求合天人以一内外。伊川继明道之后,故无再返回张载之思路之道理,自然是唯就一心而分内外。是故,伊川分性情之为二,与缘此而有之理气为二,皆不同于横渠之以天人分内外之说,“乃只是于此一整个之心自身,姑分内外两面而更观人对此内外两面,当有之工夫。”[2]165
不论伊川如何分别各项名词义理,在唐氏的理解下,皆是统在一心,整体而言仍是一。以性情寂感为论,性理是当有而未有之情之根据,若吾人欲实有此情,在客观世界中是寻求不到的,唯赖吾人自己创生之。而我之创生之,也是以我此心之感其为义所当有、理所当为,为唯一之根据。此义理初呈于心,而未见于情,亦只为人之性之见于心。至其实见于情时,则此情乃不得不说为唯依此心之性而生,此情之气,亦不得不说唯依此性之理而生。[2]176由此义,唐先生续申论性情之动静与心之寂感。当情气未生时,于此性理可说之为静;然性理本身是一生理,具有“向于与之相应之情之生、气之生”的本质意义,故即此性理以观其向于相应之情气之生,则此性理非只是静,而是静中隐含着动义;依此性理之有此动义,而实表现一动,遂显此性理于情气。唐先生将这些动静俱纳于心之寂然感通:当性理显于情气时,为此心之“感而遂通”;若自此心未实表现一动,只有此具动义之性理之存于心说,则为此心之寂然不动。[2]177
如是,一整个之心可分成两面以观,一面是性理,为心之寂然不动之一面;另一面则是情气,为心之感而遂通之一面。依此,又可推述至“心之寂然不动一面,为隐微,为心之体;心之感而遂通一面,为彰显,为心之用。”[2]177这样的结论。性情统于一心,既是二,而又非二。所以为二者,以其名义各不相同而相对之故;然此二中同时具有相向以成不二之义,盖以性情二者俱属于心,性情原是一心之性情;由之以言理气,初亦是一心之理气,寂感也是一心之寂感。总言之,
此性、理、寂,是心之内层或上层;情、气、感,则是其外层与下层。其由内而外,由上而下之整个道路,即名为心之生道。此心之生道之两端,即此性与情、寂与感、理与气。两端在此整个之生道中,亦即在一整个之心也。[2]178
因为分属一心之两端,性情、理气便不能截然分为二物,彼此的关系乃是“相对而又相向”,相对是就分属一心之“两端”言,相向则是就统属于一心而论。不同于其他学者只见到伊川之分性情、理气之为二,唐先生另提出“性情、理气统于一心”的论点,由此保住伊川仍符应明道“合天人、一内外”之学。
唐先生再引用伊川一言“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②厘清如何由性而心、而情之层层落实的过程。
盖意谓“形”为性之初显于心内,而“动”则为性之更见于外之情气。当然之性理未形,为静为隐,形于心而见为一当然之性理,与心为一,即由隐而显,则在动静之交。见于情气、即是显。显即其由隐中自动出,由寂以通感于外。[2]179
从“性”而见于情,须经过“形”与“动”两个步骤,性理之初显是显于心,心觉一当然之理,此时心与性为一,心再依性理而动生相应之情,性不能直接显发于情,其间必须经过心之动方能显于情气。“心性为一”是此中从隐至显的中枢,心性若不为一,等于性理尚未形于心,自然也谈不上动于情。然则心性欲为一,是从心觉晓性理开始?或是性理自身即有能形、能动、能感之能,而主动显于心?③此处唐先生便不细究了。他要人“不必更问:未形者如何能形,静者如何会动;心即具生道,自是能显其所隐,而见性于情,通寂于感。”[2]179不过,综观唐氏全部的解析,他应是倾向性理能动、能显,能寂、能感,由是心方能觉性理而生情,只是性理之动、显、寂、感没有动静之形迹可见,唯暗中默默潜运密行,是以本文才以“潜在的吸引力”形容性理之活动型态。
唐君毅先生对伊川学之诠释,确实颠覆一般学者之认伊川为“性情、理气截然二分”与“性只是理”的印象,他提出性理具有“向于与之相应之情之生、气之生”的本质意义,因之性理为一“生理”,有着生情、生气的感通之动义,并非仅存有而不活动之理。至于性情、理气之二分,也是就着一整个之心相对而言,分属心之上、下层或内、外层,在心之实际活动中,性、心、情三者合为一体不可分。此二义若续延至唐先生对朱子学的诠释,影响所及,朱子的“理乘气”之说不再是曹端所讽喻的“死人骑活马”,而是具有活动性的万物的存有之理。
二 唐先生诠释理路之疏理
(一)以“道德义务之感”为起点
唐先生为当代受人景仰之鸿儒巨擘,其学融贯中西、陶铸古今,鲜有人能出其右,大约唯有另一位宗师——牟宗三先生堪与比肩齐论,学界也多有取两位先生之学相较以观④;对于宋明理学,两位宗师俱有精辟详尽的论释,皆足以影响后代学子研究宋明理学之方向与方法。有关明道、伊川与朱子三人之学术,唐、牟二位先生所关注的义理重点也相差无几,然而所诠解的内容却是大相径庭,这一点值得后人细心研究。
以牟氏而言,其论释二程之学的主轴定在三人是否有无“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的洞见,有此洞见者,自能保有道体、性体之超越存有之身份,以及鼓舞万物生发的创生力与作用力;此有活动性之性体透过主观之“心”朗现自己,心、性的差别在于一是主观的意志,一是客观的超越根据,两者其实是一,性即是心,心被升举为“心体”。无此见地者,会不自觉地将“即存有即活动”的道体、性体渐渐抽象提练成一“即存有而不活动”的理,而心仅能是“心气”之身份,心和性不即是一,心和理也保持平行不相交的关系。二程中唯有明道有此洞见,故其所论之道、理、易或性均保有活动性不失,而伊川则渐丧失本体的活动性,其见解实已歧出原始儒家的本质,所疏解的内容与古典文献多半不合。
然而唐先生全然不取“道体、性体是否有活动性”之观点,他的观点十分简易——二程乃是从内在生命开始,从人性论上升至天道论,由此思路进入,则所谓人之性乃是一生命上升而扩大之性,是一充实其生之性。此中即已决定二程必从道德意识进入,以达尽性知天之境;不能径从“存在之所以然”之存有论的入路以思理、气之关系。而后者却是牟先生解析伊川学的大纲。
从道德意识进入以思考理、气之关系,会得到何种结论,吾人可以从唐氏申论朱子“理先气后”之义时所采用的方法获得证明。他采用两种论证以证明“理先气后”为真:其一是以“形而上先后”解释之,其二是以“道德义务之感”论证之。前者主要说明一件事:“在宇宙根本真实之意义上,理为超乎形以上之更根本之真实,而气则根据理之真实性而有其形以内之真实性。”[4]448于兹,一般学者多取“存在之理先于存在者”之进路释理先气后义。此思维并没有错,可是径以存在之理与一切存在解理、气之关系,照唐氏看来,亦未得朱子理先气后之实蕴。问题出在朱子非泛泛之思想家,他是两宋集大成之理学家,其思想必定承袭宋代理学之一贯问题,以及理学家对于“理”之见解共识。溯源宋明理学家之根本问题,唯是一如何成圣之问题。成圣之道在乎以理导行,故其所求之理,初重在“应如何”之当然之理,而不重在宇宙“是如何”之存在之理。[4]454由此推述,朱子心中“理先气后”之言,必先对当然之理与气之关系有意义,而非先对一般存在之理与其气之关系有意义。此即第二种论证方式——以“道德义务之感”论证理先气后。⑤唐氏这种推述理先气后的理由和强调伊川之必由性情论而至理气论的道理是相呼应的,显见得此为唐先生对宋明理学诠释入路之大旨。
从此意义分辨理、气之先后,则必发现当然之理首先呈现于我之前,且是以命令之姿态呈现,命令我应当遵此理而行,此与前文所云性恒显为一在前为导之理、之道一致,只是唐先生诠释二程学时的文气语势没有如是强烈。自此而观唐先生的诠解思路,是不会出现伊川将理视为“只是静态的存有之理”的质疑。
(二)有关“性”之内涵论述
对于人物之“性”之意义,道德是非之理在其中,由内心真诚发出的各种理想也是出自“性”这一源头,此在前文已说明过。扼要简述“性”之意义,唐先生之《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有一段精辟的解释:
性只是一生的灵觉,或灵觉的生。此生之欲有所向往,欲有所实现,即此生的灵觉或灵觉的生之性。实则此欲有所向往,欲有所实现,即是去创生。故生即是性。[5]194
只是有所倾向,倾向于美好理想的事物、境界,想要有所实现,单单这一倾向就是去“创生”了,因为唐先生肯认“欲有所向往,有所实现,即是一自命,自令,故性即是命。”[5]194而这些意涵早蕴于二程学中,在唐先生看来,二程言性理绝非仅存有而不活动,即使性理的活动性不显明,但此性依然要向于相应之情气使彼情气生发出来,即便实际生发者在心而不在性,但若无此性,心亦无法生发此情、此气。
若道性理不能担任实际生发相应之情气的动源者,仅仰赖心之遵此性理而发,这就不能保证性理必然外显化为实际之情气,它依然只是存藏于内心的当然之理罢了。此处唐先生亦有其强而有力的反证理论,即针对“当然之理”之涵义作充分的解析,以凸显当然之理“必然”显化于外,不然当然之理不成其为“当然”之义。
首先,吾人应知所谓“当然之理”者是在义务意识中呈显,而不是悬空想象一当然之理。
在义务意识中,吾人认识一当然之理,然此当然之理,即我当如何行为之理。吾真对此理有认识时,乃在感此理对吾人下命令时,亦即在此命令之贯彻于我时。如吾人不感此理之命令之贯彻于我,则不能认识之为我所当如何行为之理。我之能认识之,唯在其对我有所命令,我之有所感动上。故我之能认识其有,肯定其有,唯在其对我呈现一种作用,而显露其真实性时。[4]462
其次,“当然之理即当实现之理,其为当实现,乃对一能实现之者而言。当实现而无一能实现之者,则当实现之辞无意义。吾固可泛指此理普遍为任何人或任何存在者所当实现,不指定其为某某特殊人所当实现。然任何人非无人,任何存在者非无存在者。”[4]474当然之理是基于道德意识而生起的一种应当如是如是行为之理,此种理想往往与当下之现实差隔甚远,然不碍此理必然实现,原因即如唐先生所示,若当实现却无存在者可以实现,则此所谓“当实现”便无意义。从当实现至于实际已实现自然有差距,这就是理和气之间的差距,伊川、朱子特别感受这一点,是以特强调理、气之间的悬殊差异。
唐氏自然也知悉当然与实然常常不能合一的现象,因为人对于其所视为当然者之是否必能实现,常有一根本之怀疑,怀疑来自当然者非实然,即涵可不实现之义。既是如此,人便常念其不实现,而一味陷溺在实然者之执持,而不求当然者之实现了。于兹,唐氏提出一突破之道,以坚定人之信心:
此须知真为当然之理想,无论属人之主观之道德理想,与客观之社会文化之理想,以及对自然宇宙之理想,皆无不必然能实现。然以此当然之理想,为无穷之广大高明,故其实现,亦为在一无穷之历程次序实现。然亦不能越序而皆一齐实现。人之越序而望其一齐实现,则为贪欲。然此次序实现之历程之无穷,并不碍其必能实现。此无穷之理想,在无穷之历程中,必能实现,则可为吾人当下之一信心。[5]492
这种信心是人之天生之性情所必有,无需借助任何哲学思维才能形成,然哲学之思维确是有助于开启此信心,因为
在人可由哲学的思想以知理想之有一必然趣向于实现之动力。此动力,乃通主观与客观世界之一形而上之生命存在与心灵,自求一切合理之理想之实现之动力。此动力,是一能、一用;其如何去除不合此理想者,以有理想之实现,是其相。而由此能此用之相续不断,即见其有原。[5]493
求真实之理想必于现实世界中实现出来,这样的动力不是外铄于我,乃是来自我之本性。至此,性之于人,不只是一理而已,此理带着命令、动力要求我必然实现之,如是陈论当然无有牟先生所忧虑的实践动力减杀之问题存在。
(三)有关“心”之内涵论述
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意思是心不仅止于知觉作用,同时也是道德法则的来源,道德法则乃是吾心自立自发、自我命令的;于此义之下,心、性之关系必然合而为一,客观之性藉由主观之心形着朗现,性不仅是理,同时也发而为意志、情感。牟先生以为道德实践之至其极,必然导致这样的理论。对唐氏来说,他不否认此结论⑥,也不会把伊川所言之心强转成即理、即道之心,他依然保持伊川论心之原貌,把心视为心气之心,而非即性、即理之心。
不过,这样的心对唐氏而言,并不会减低道德实践的动力,原因之一,天命之性本就会自命、自令,当我认识某一当然之理时,我即感受此理对我下命令,此自命、自令之感即为履仁践义的动力来源。原因之二,伊川言心乃是“一整个之心”,如前文所述,一整个之心可分成两面以观,一面是性理,为心之寂然不动;另一面则是情气,为心之感而遂通。性情统于一心,虽是为二,却又非二,盖以其名义各不相同而相对之故,同时具有相向以成不二之义,最终性情二者俱属于心,性情原是一心之性情。此处,情原是心之表现,而性又不在心外,自然性理一动(在唐氏的理解下,性理乃静中隐含着动义),遂显此性理于情气。这些都是心之寂然感通的活动。
这是就着伊川“心主性情”之说来证明纵使心为气之属,与性、理不即是一,也无碍显性理于情气。若再加上朱子“心者气之灵”之说,则更能增强心之有感于性理之能力。所谓“气之灵”是专属于人的,其他万物无福领受气之灵,所禀受的均是粗驳之气,此气之灵之义不同于泛泛之气的地方在于:
此所谓气之灵,亦即其气之清,气之中正,而恒能运行不滞,无昏暗,无偏倚,故能动能静,能寂能感,而使此天理性理,直接呈现于心,而人乃得有尽心知性等事。然所谓气之灵者,当即不外就气之依理而生,复能回头反照其所依之理而立名。[6]481
源于人有此气之灵之心,故能寂然具理以为性,复又能感性理之动而发为相应之情,是故心为绾合理气之枢机,一方面内具理而上通天道,另一方面又为气之灵,以与此身之气和万物之气相感而相通。如是之心虽仍为气之属,一样容易受性之感动而遵理以行,实践动力依然不减。
其实,唐先生对于气实有特别的独到见解,他不会把气局限在材质义,在他眼中,
吾人不能谓宋明儒所谓物,即西方唯物论哲学中之无生命心灵意义之纯形体之物,而此气,亦非只此形体抽去其形式形相所余之质料或底质。此物,乃自始为兼具生命心灵意义之具体的物。此气,乃一自能或自知依理,以成一切具体物之变化,或一切存在者之变化,以合为一宇宙之存在的流行,或大化流行之气者。气之依理而变化,即见气之灵、气之明、与气之伸、气之神、气之生生不息。故气自具神明义、心义、与生命义。[5]251
宋明儒眼中之世界当然不会是纯粹的物理意义的世界,其中必然带着道德价值之意义,以此观物,物即是具生命心灵意义之具体物,气也是理、神、气合一的大化流行之气,而全宇宙即是一道德宇宙,然客观之世界能成为一道德意涵之宇宙,其源头何在?唐先生认为源头即在气之中,气自身即能依理之所命以流行,因为气本有其虚灵之一面,气之虚灵即是气之灵、气之明、气之神,人心之所以为人心,亦在此神明,故人心为气之灵。[5]250
从唐氏对心之内涵的种种陈述,即便心为隶属于气之心,但它是气之虚灵、神明的那一部分,气之灵、气之神本即通着道、通着理的,心为气之灵自然也一端通着道、通着理,故心认知理而遵理以行,实非难事。
结语
唐先生卓著超群的研究成果,堪为接引后人研读中国哲学之桥梁,启发人处甚多,单以唐氏之学为研究专题,或取他人与唐先生对照比较之学术论文,比比皆是,但能够专研唐先生为何如此思维,其中之来龙去脉又是如何形成者,毕竟不多;然本文认为以唐氏这般宏伟丰富之学术内容,若能握其纲领,顺其宗旨条理一贯而下,则对于他所诠释之宋明理学的各项、各层义理内涵,当更可了然于胸,明白何以会有如是之论说。
唐先生疏释二程之学,“道德义务之感”绝对是首要之前提,二程所讲述的任何内容,均须系在此前提之下,唐先生乃是基于“道德义务之感”所蕴涵之义理来解述二程的心性论与天道论,遂有如上之义理解说。其次,唐氏于“心气”之见解也是左右他对二程之学的诠释与评价,从他对朱子之“心为气之灵”的解析、疏释之过程,可以见出唐先生是一步步抬升“心”的地位。⑦自然他所诠解的二程之心性论是颇与众不同的。
注释:
①此文为本刊2014年第9期所载文章《唐君毅先生诠释二程学“性理”义之方法探源(上)》的续篇。
②伊川云:“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见《程氏遗书》第二十五卷,第31页。
③朱子是继承伊川“心主性情”说的,伊川没有解释的,或者可以从朱子的解释中获得一答案。朱子曾说道:“若以谷喻之,谷便是心,那为粟,为菽,为禾,为稻底,便是性……包裹底是心,发出不同底是性。心是个没思量底,只会生。”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第一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第91页。有学者根据此条文来分辨心、性之关系乃是“性作为心之为心的意义承担者,犹如今天的基因、DNA等,最终决定着生之实现。性虽不‘灵’,但又不是沉寂的质料,而是必然‘发出不同底’生之根据。”又说:“性或理并不是一个可以捉摸的特定对象,而只是必然会发散出来的内在性能。”见向世陵的《论朱熹的“心之本体”与未发已发说》,收于陈来主编的《哲学与时代 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依此学者的讲法,性本来即是会发散出来的,因为它是各种道德之情的发生根据,于此而说性有能形、能动、能感之能,而主动显于心,应是可允许的讲法。
④学者多有取唐、牟两位先生的思想互作比较者,如张晓芬:《试论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道德内在论”的异同》,载于鹅湖月刊总号第413号(2009年11月),20-40页。邓秀梅:《唐、牟二氏对张载哲学的诠释比较》,载于鹅湖月刊总号第411号(2009年9月),25-39页。陈荣灼:《论唐君毅与牟宗三对刘蕺山之解释》,载于鹅湖学志第43期(2009年12月),71-94页。林月惠:《唐君毅、牟宗三的阳明后学研究》,载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卷1期(2010年1月),22-33页。
⑤当代学者杨祖汉先生曾大力赞誉唐先生之疏释朱子的理先气后论颇多精义,唐先生给出了一很有意义的诠释方向,此一诠释方向,实可与牟先生之朱子学诠释并立,而与朝鲜李朝之朱子学,有主理派与主气派之对峙相似。见杨祖汉《唐君毅先生对朱子哲学的诠释》,载于刘笑敢主编的《中国哲学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⑥唐氏曾言道:“纯从心性论之观点,以看此中之心与理之俱呈俱现,则亦可不说心为能觉、理为所觉;而尽可以满心而发者皆是理,或心即天理之昭明灵觉,而言心即理。此即可成陆王之义。然朱子于此盖亦有意焉,而未能及。”参见唐君毅所著《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382页。此外,唐氏在分辩朱子对“天命流行”之分疏、及其以理气分三命之论时说道:“此中之真正问题,在朱子之由摄取横渠重气之意,或偏在即气之灵以言心,未特重即心之理与道以言心,遂未能同时重此心之超越义,以贯通于具超越义之天道天理,进以见此人之心,与天命天道之直接相贯。”见唐君毅所著《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596页。心、性、理至其极应是“为一”之状态,但朱子于此稍有欠缺,此点唐先生也看出来了。
⑦唐先生在《原太极》中对“气之灵”的理解是重在“气”字上,故批评此说乃以气之观点看心;待至《朱陆异同探源》一文,则确立朱子亦有“未发之心体”一概念,因此说朱子言“心”存在着心性论和宇宙论的不一致;直至《原教篇》唐氏对“气之灵”提出另一新诠,一再由气之灵而上指,以见心之具理。此中之详尽内容,参见游腾达的《唐君毅先生的朱子学诠释之省察——以心性论为焦点》,鹅湖学志第42期(2009年6月),第31-94页。
参考文献:
[1] 程颢,程颐.程氏遗书: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上[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3] 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M]//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8.
[5]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册[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6]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