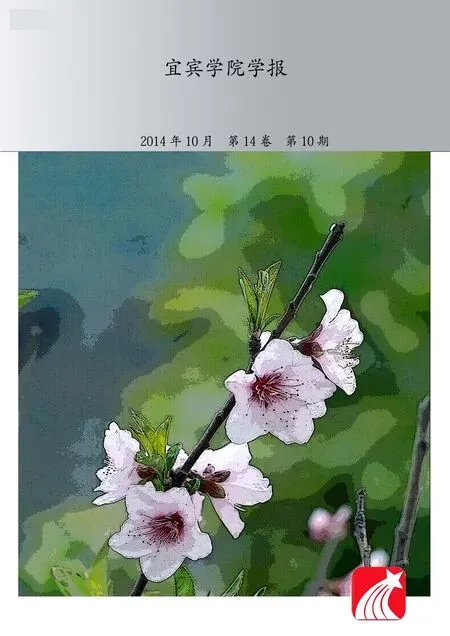以和为体
——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音乐本体论
杨 杰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在《声无哀乐论》(以下简称《声论》)中,嵇康通过秦客与东野主人的八番答难,表达了一种倾向于音乐自身艺术性与规律性的音乐美学,而不是以一种外在目的论的方式定义音声。这一点现在已经为多数美学史或音乐理论研究者所认同。如张法认为,《声论》提出的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背后是“艺术的自主性问题”[1]89;叶朗认为,嵇康“认为音乐(艺术)和社会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其积极意义是“人们对于艺术的审美形象的认识的深化”[2]198。因此,虽然《声论》的第八回问难大谈音乐的“移风易俗”问题而让人疑惑此论的真正目的①,但《声论》所包含的乐理思想及审美思想也是应当独立进行考察的。
在嵇康看来,儒家以乐的功用性价值作为评价其好坏的标准,乃至将之作为乐的本质意义,强调乐在“和人心、和伦理、和政治”中的根本性作用,其弊端是在音乐实践上无视乃至曲解音乐自身的本体存在及其规定性,忽视音乐本身的艺术性,追求音乐的外在需求与工具价值,从而将音乐变为一种附属性的存在,否定了音乐的艺术性及创新可能。而道家从其“少私寡欲”的原则出发,站在“道”或“天籁”的高度上,批评、超越儒家的功利主义音乐观,同样反对音乐的形式美,注重一种稀疏平淡的音声,也否定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音乐艺术。在以和论乐中,儒家关注的是“和”的道德性标准,雅正之乐才是“和声”;道家的“和”则是要以平淡的音声乃至“无声”达到“道”的混沌境界。二者都是否定音乐的艺术价值的。嵇康对音乐的思考是深入音乐自身,而不是从外在为音乐寻找依据的。他重视音乐的表现形式,在《琴赋》中他对音乐进行的不厌其烦的描写铺陈,就是一反儒道对音乐形式的忽视,强调音乐自身的美。因此《声论》中的音乐美学,即是以音乐本体之和为中心来展开的。笔者将之称为“以和为体”的音乐美学。
一 音声有自然之和
在《声论》中,嵇康指出“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3]426。这是说音声(纯音乐)源于金石管弦等乐器,因此只包含和谐的音律节奏而与人的感情没有牵涉。所谓“音声有自然之和”,是就音声的本体性而讲的,指音乐作为自然界中万物之一种,遵循着天地自然和谐之理。嵇康具体说到: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3]432
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钥纳气而鸣耶?[3]438
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损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耶?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3]437
这里嵇康把音声看作同嗅味一样的客观的自然物,这种自然物有其不随人的意志变化的本体。因为音声的产生首要是风(气)作用于“籁钥”或“口”的结果,而风(气)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触地而发”的,因此音声也就有着自然万物所遵循的特征;即便是“律吕”“五声”这些人为设定的声律规则,也只是依照“四时之气”的规则所制定的,人并没有改变这种音声自身的性质,也没有赋予其制作者的思想意图。音声所具有的只有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性质,也就是“和”的性质。
《太师箴》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3]544,《明胆论》说“五才存体,各有所生。明以阳曜,胆以阴凝。岂可为有阳而生阴,可无阳耶?虽相须以合德,要自异气也”[3]485。嵇康所持的是汉代所通行的自然元气论的宇宙观。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氤氲相合构成,阴阳合德,其本性就是一种物质内部各元素之间以及不同物质之间的和谐性,嵇康称之为“天地之理”或者“自然之和”,这就是天地万物所遵循的规则道理,其内容就是“和”。音声作为阴阳和合之产物,其根本性也在此。
而《乐记》讲“乐由天作”[4]1090,阮籍《乐论》也提到“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都将乐的来源或依据归于天地之道。他们与嵇康的不同之处有两点:其一,嵇康所论的“音声”是纯音乐,是不包含任何“象”的艺术性作品,而儒家和阮籍所谓的“乐”是“圣人之乐”或用于教化民众的“雅乐正声”,是诗乐舞合一的整体性的乐。其二,儒家和阮籍把乐归源于天地,只是为乐寻找一种神秘性与权威性,从而论证乐教的合法性;嵇康则是论述音声的生成性原因,从而得出与儒家和阮籍不同的结论:音声其体自若而不变。此外,嵇康同儒家和阮籍也都讲音声或乐效法天地自然之和,这个“和”,他们的理解仍然是不同的:嵇康认为音声即作为一种自然物自有其和谐的本体;《乐记》和阮籍则主要把乐作为天地和谐的表现以教化民众,
事实上,“音声有自然之和”更多的与庄子的音乐思想有着一致性。庄子认为天地万物是由气构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音声也是一样,是由“大块噫气”“作”于“万窍”而产生的,无论是地籁、天籁或者众窍、比竹,其发出的声音都是这些空窍因其自性而发出的。嵇康在《声论》中两次引用“吹万不同”的例子,就是要进一步说明音声是客观事物自然发出的,与欣赏者主观的情感无关。
二 声音以平和为体
“音声有自然之和”讲的是音声所具有的自然主义来源,是乐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显现于音声,就是体现在音声本身上的平和的特征。关于音乐的本体,李泽厚、刘纲纪、冯友兰等认为是“和”[5]214-216,蔡仲德认为是“道”[6]508,也有人认为是“无”[7]。笔者认为能够称为“本体”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遵循嵇康文本的“和”,“道”与“无”只是与“和”性质一致的引申说法。因此所谓“以和为体”的乐论,就本体论而言是指音乐以自然之和为本体,就现象层面而言指音乐形式是平和的,这才是完整的乐的本体论。
关于“平”“和”,《国语·周语下》说“声音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8]15。“和”是指五声之间相互应和协调;“平”是指小声和大声不相互逾越。“平和”在《声论》中出现四次,其中三次指心境之平和,一次指音乐形式的平和:
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3]439
音乐本身只有善恶即和谐平正与否之别,因此其对人心的感染也没有常态。这种善恶只取决于音律节奏的组织形式,而与作曲者、制作乐器者、弹奏者或者欣赏者没有关系。不同的乐器、不同地方的音乐,其风格都有不同,但其根本上是乐律节奏的简繁、高低、好坏而已:
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而钟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则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体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役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譬犹游观于都肆,则目滥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3]439
琵琶、筝、笛,它们的发音区间距离较短、声调高、音阶变化频繁而音节急促,因而会使人体态躁动心志激越;琴、瑟的发音区间距离较大、声调低,音阶变化舒缓而声音清正,人要虚心静听才能感受到清和之声的极致,所以人会体态安静心情闲适。曲调不同,也如同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一样。比如齐楚之曲,其音调大都深沉凝重、音阶变化少因而让人坚贞专注;柔美的小曲则聚集了众声的美妙之处,综合了五音的和谐平正,形式丰富变化多样。因而让人愉悦舒畅。但这些不同都只是音律节奏的不同,在形式上它们都是和谐平正的,是遵循着“自然之和”的规则的。
以平和为本体的音乐,具体表现为或猛烈或恬静等不同的音乐形式,从而使人有或躁动或安静等不同的体态反映,这就是“躁静者声之功也”[3]439。“躁静”只是人的体态反应,而非情感表现,情感的哀乐是人心不和的表现,这成为人接受音乐影响的前提。
三 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
嵇康在《声论》的第七番论难中对哀乐这两种情感做了区分:“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愉,乐之理也”。②轻微的悲哀面色难看,大的悲哀则会哭泣;轻微的快乐面色和悦,最高的快乐则只是心里愉悦,却没有激烈的体态表现出来;而大笑这种表现则不是在音乐欣赏中出现的自然反应,而是由别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人是无法通过外在表情体态的变化探知内心情感的哀乐的,同样也是无法通过音乐形式的和谐与否探知人内心情感的。
事实上在嵇康看来,音乐活动中心境平和才是根本的,嵇康在这里再一次显示了其与儒家音乐观的不同。在儒家看来,乐的来源与人心有关。《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4]1074,秦客也说“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3]433,人心受外界的刺激而产生一定的声音反应,这些声音经过一定的有组织的排列组合而形成音乐。在这个过程中音乐被赋予了哀乐等情感属性。而嵇康认为音乐形成过程中心的情感情绪并不附着在音声之上,但人心的平和与否则会显现于外,人心的平和与否也就通过音律形式的和谐与否显现出来。
在《声论》的最后一个辩难中,他说在“古之王者”统治的时代,人们:
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儛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3]411
内在遵守道的自然清净的特性,心境平和,外在则显现为和谐之气,由此和谐之气才会发出平和之声。但是人心并不总是和谐的,特别是在“衰弊之后”,主体的性情之和总表现为一定的哀乐倾向,即人总是“哀乐不等”的。因此“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3]432的现象就出现了。这是说作曲者在作曲之前已经有了悲痛之情,于是排列言辞组成诗歌、排列五声组成音乐;演奏者和欣赏者被这些诗歌和音乐共同打动。但是音乐形式本身仍是和谐的。并且和谐的音乐是“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的。因此为了协调人们的心境不使哀乐失去节度,圣人就制作和谐的音乐以协调人心。这种协调、引导实际上只是培养、涵育、宣导人心本就含有的和谐之境。这就是音乐能“感动”人心的本质。
四 和声感人
嵇康认为“心之与声,明为两物”,因而不能“因声以知心”。这是说心与声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实),具有不同的属性(名),二者名实不同,即其外显的表现不同,因此不能通过音声的性质(和)探知人心的状况(哀乐与否)。但这并不是说音声与人心没有关系。一方面,形式和谐的音声是人心发出的,另一方面,形式和谐的音声对人心也有感发作用:
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谓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3]435
哀乐是人在听乐之前就已具有的情感,和谐的音声则把哀乐之情引发出来,这如同酒醴激发出人的感情一样。嵇康多次谈及音声感化人心的作用,又如音声“发滞导情”(《声论》)、“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琴赋》)等。这种“感化”,嵇康意指音乐引导出人心本有的哀乐之情;这种哀乐之情不能毫无节制,因此圣人制作出形式平和的音乐,使听者的心情得到感染、培育,从而回复到心境平和的本来状况。
音乐之所以能够对人心产生作用,或者说人心之所以对音乐有所“反应”,现代的音乐理论有很多种解释。比如有人认为音声与人心是“异质同构”③的,有人认为是“音心对映”④的等。嵇康则站在道家的立场上,以“天地之和”作为“和声感人”的根源。在他看来,主体的性情之和显现为主体在听乐之前就有的哀乐之情,音声本体所具有的自然之和显现为音声自身所有的形式之和,二者皆源于天地之和。正是由于音乐与人心都分享了天地之和,二者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可能。
结语
嵇康对音乐的分析,完全是就音乐自身而讲的。“天地之和”“人心之和”作为音乐自身的依据,赋予音乐以平和之体,反过来平和的音乐有对人心有着感发、宣导作用。因此,要想使音乐真正起到“移风易俗”的目的,需要人心平和,平和的人心与平和的音乐相互作用,才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而只有实行无为政治才能使人心平和。在此意义上,嵇康又指出所谓的“郑声”或者“流俗浅近”,都不是使人心荒淫的原因,而是结果;二者并不能与平和的人心发生正面的契合,因此应当舍弃。但是他指出,无论“郑声”还是“小曲”,其自身只有“善恶”即韵律音阶平和与否的区别,而没有淫正之别。淫正同哀乐一样是属于人心的,对其的纠治只能是由平和之政引发平和之心,而不能寄托于音乐。因此,为政首先要使人们“心感于和”,就是实行“简易之教”,使没有产生“郑声”的社会基础,平和之乐大行其道,如此音乐的教化功能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在嵇康看来,儒家乐论以政治功用为音乐的根本、以音乐为政治功用的手段,既没有理清音乐理论的问题,也没有明白政治治理的根本。几百年来儒者纠缠在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上,都没有使音乐对政治产生实质作用。他强调“和为乐体”的音乐美学,其根本的目的是深入音乐自身的本质与艺术性,试图对音乐做出新的解读,以此实现无为而治的道家式政治理想。而事实上,嵇康的政治理想从未实现,但其对音乐自身的分析则有利于音乐脱离政治而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这也是嵇康乐论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比如冯友兰就认为《声论》的主题是讲“音声之理”的,“作为一篇美学论文,这就够了。讲‘礼乐之情’是画蛇添足”,甚至认为第八个回应讲“礼和乐的配合”,与其反对“名教”“礼法”的观念不符,因此“这也是他(嵇康)的思想中的一个内部矛盾”。见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第九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版,第398-399页。
②“至乐心愉”,吴抄本改作“至乐而笑”,这种修改实际上没有懂得嵇康有意区别哀乐两种情感。《答难养生论》云“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则忧喜并用矣。由此言之,不若无喜可知也。然则无乐岂非至乐耶?”因此“至乐”即“无乐”,“至乐”的表现是无形无相的。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嵇康指出亲人转危为安自己就会手舞足蹈显现出来,亲人一直安豫无恙自己内心就会安适自得而外在并不表现出快乐的情绪动作。在嵇康看来,后者的情感是更深的。因此在嵇康那里“至乐”只能是“心愉”的。
③格式塔学派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包含物理性(非表现性)和表现性两种属性,审美体验就是对象的表现性及其力的结构(外在世界)与人的神经系统中相同的力的结构(内在世界)的同型契合。在音乐欣赏中,音乐和欣赏者内心的力的结构是一致的,二者的沟通使得物我同一的和谐境界得以产生。苏珊·朗格认为音乐与人的情感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是这种说法的进一步发展。参见童强著200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嵇康评传》,第403-409页。
④李曙明在1984年发表《音心对映论》一文,认为《乐记》《老子》、嵇康的《声论》等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和律论”的音乐美学,是“将音乐艺术看成是物质(乐音运动)与精神(心灵运动)的动态对映系统”。从而引发了音乐美学、音乐理论界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争论,直到《音心对映论证明与研究》一书的出版才暂告一段落。参见由韩锺恩、李槐子主编的2008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音心对映论”争鸣与研究》,第3-16页。
参考文献:
[1] 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2]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4]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6]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7] 黄毓任.和声无象哀心有主: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J].南通大学学报,2012,21(4).
[8]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