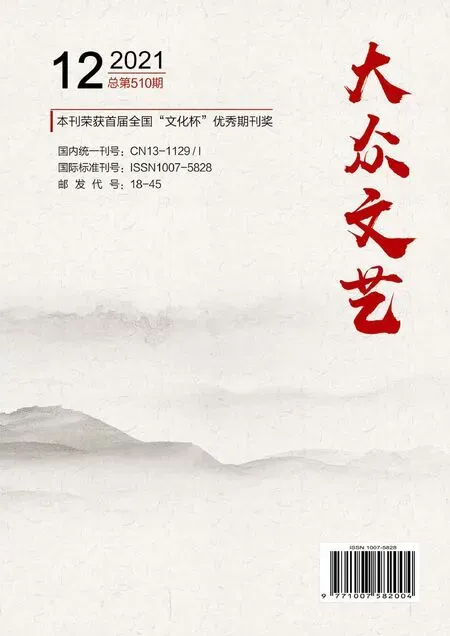电影《悲惨世界》中的悲剧美
曹昕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200240)
电影《悲惨世界》中的悲剧美
曹昕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200240)
2012年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将原著的悲剧色彩以视觉听觉双管道的方式更直观地呈现出来。从康德对美感的定义角度来看,电影中的悲剧美具体表现为对优美感的破碎和重构以及面对为战胜苦难的心灵经过中对崇高感的塑造。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双重挖掘人物优美以及崇高的一面,制造以及拔高戏剧冲突和高潮。
《悲惨世界》;悲剧;美学
2012年改编自雨果的鸿篇巨作《悲惨世界》的同名音乐电影上映之后,票房口碑双丰收,并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3项大奖。电影继承了原著文本的情感广度和深度,创造性地采用了现场演唱的录音形式和场面调度,将原著的悲剧色彩以视觉听觉双管道的方式更直观地呈现出来。该版本继承原著的故事,着重体现了这样几对凄美壮烈的冲突:冉阿让与沙威警官一生对信仰与生命认识的斗争;芳汀在梦想与现实中挣扎堕落的绝望;马吕斯等青年对革命的希望与彷徨、质疑与牺牲……一件件的悲剧中却闪耀着人性中美好的光辉。
康德将美感分为优美感与崇高感,崇高令人产生畏惧,而优美带来欢乐和微笑女性身上具备更多优美的品质,男性的品质则趋于崇高。笔者尝试以康德对美感的定义为基础,从电影《悲惨世界》的文本、音乐及画面三方面分析影片中所的悲剧美。
一、优美感与悲剧
巴尔塔萨曾说过:“美”从来不是作为和谐完满的存在而出现。电影中,对这种不完整的美的直观表现就是人物的造型:除了珂赛特在成年之后有着完整美丽的衣着之外,全片的女性的服饰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旧感。最典型的莫过于因爱一再沦落,被现实摧毁的芳汀。当她第一次被蹂躏之后,剪短了头发衣衫褴褛的芳汀躺在如棺材一般的箱子中,唱起了《我曾有一个梦》 :她身上最女性的气质刚刚被无情的夺去,那些可以被称之为优美的特征遭到了严重的毁坏。而当她开始吟唱那些她曾经的梦想,一个长达4分钟的定机位长镜头特写将她置身于背景模糊的大光圈中,那些女性的气质因为污秽背景的隐去,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上。我们意识到这种优美曾经在她的身上带给人多少欢愉,也意识到它当下的缺席,因而扼腕叹息。景别和光圈的设定很好地将幻想与现实集中在了一个画面之中。
二、崇高感与悲剧
康德认为美就是道德之美,而真正的德行只能植根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越是普遍,则它们也就越崇高和越高贵。要坚持这个原则决不永远是轻松愉快的,更多时候它意味着给自身带来不便和困难,甚至是灾难。因此为了完成它,人性中的软弱总会经历一番挣扎,如果说悲剧是通过摧毁挤压优美感而形成,那么崇高感则是在悲剧的痛苦中被深化。
冉阿让在片中有三段唱段渐进地表现了心中“崇高感”的激发与升华。第一段是冉阿让在教堂的长走廊中经过一场心灵的洗礼而悔悟。教堂的走廊的场景设置以及长镜头的推拉调度与歌词紧密配合,完整的从视觉观感上表现了这种心里的触动和挣扎。从冉阿让对自身的质问“我为何变成黑暗中的窃贼?”“我为何让这个人触动我灵魂,教会我爱?”机位及人物移动节奏缓慢;最后冉阿让突破心灵捆绑,激发“善”的品质,机位移动迅速方向一致,从爆发的节奏上宣泄出了主角新生的欲望。
随后冉阿让得知有人因自己无辜被捕后内心自责:“难道我要这样躲避一生?我的灵魂已属上帝,我知道。”高尚的正义品质在此时再次深化,完成了一次从自我救赎到拯救他人的转换。这一组叙事镜头通过画面的摇摆与烛光的运用,去表现冉阿让内心的痛苦。这种将自我陷于水火的痛楚与挣扎越大,当他站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逃犯的坚毅就显得越发崇高。
最后在革命前夜,冉阿让为马吕斯的生命祈求上帝:“如果该死,就让我死。求让他活着,让他平安回来。”画面多次切换冉阿让观望马吕斯的主观镜头,这一次冉阿让彻底地抛弃自私的想法转化为真诚的利他行为,在生死前的大无私祈祷如光环一般笼罩在冉阿让周围,这一次冉阿让已如圣人一般崇高。每一次冉阿让将自己陷于险境,经历身心的痛楚,以实现爱人与救人,每一次他心中的那份道德律的作用就越来越强,其形象也就愈趋于高大完整,愈接近于“美”。
三、优美感与崇高感的冲突
崇高感与优美感是对立统一的,然而崇高与优美有时也会是一对矛盾。黑格尔认为悲剧的产生是因为悲剧冲突的双方都有自己合理的辩护理由,就是说每一方都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但是这两方却不能同时存在,必然有一方要灭亡,要失败,这样悲剧的产生就是必然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对罪人的不同态度往往导致不同的行为,而爱情与忠义的两难也是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常客。
影片中一曲《到明天》可谓剧中所有矛盾的镜子:这是在革命的前一夜,所有人的命运被推向一个巨大的未知。在交叉蒙太奇的画面下,歌曲频繁切换前半部电影中所出现的人物的主旋律,冉阿让的避世之心、马吕斯与珂赛特在爱情与对父亲友人的忠诚间的挣扎、艾潘妮为爱牺牲的决心、沙威坚守信仰的固执、德纳迪夫妇利欲熏心的算盘、青年起义军为革命献身的信念。音乐和画面的切换这些信念存在的合理理由和冲突,他们是如此的相违背,以至于无论是什么结果,哪一方胜利,都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也就是在此时,电影的戏剧冲突被推到了最高潮。
四、悲剧,因距离而美
距离产生美,这个美学上的著名命题在悲剧中同样适用。《悲惨世界》中的人物性格与经历与我们有一定的心理距离固然是我们欣赏这种美的一个因素。但宏大而且早已远去的历史背景也为这种悲剧美增添了更多壮丽的色彩。康德认为“悠久的年代是崇高的。假如它是属于过去的时代的,那么它就是高贵的;如果它是展望着无法窥见的未来的,那么它就具有某些令人畏惧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意义在今天已经受到了历史的肯定,在定义这段历史时,我们是以仰视的态度在观望。因此青年革命领袖们在街道上带领人民高唱《你们听到人民的歌声了吗》,我们知道心中那份震撼是高尚的正义的。因为我们离那个时代有着距离,也不会产生同马吕斯在看见同伴全部牺牲后的质疑:“不要问我你们的牺牲有没有意义。”从这样的距离去观望,我们摆脱了世俗的忧虑,才能单单为人性之美之壮丽而感叹。
[1](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商务印书馆,2001.
[2](瑞士)巴尔塔萨,刘小枫编,曹卫东,刁承俊译.《神学美学导论》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曹昕悦,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