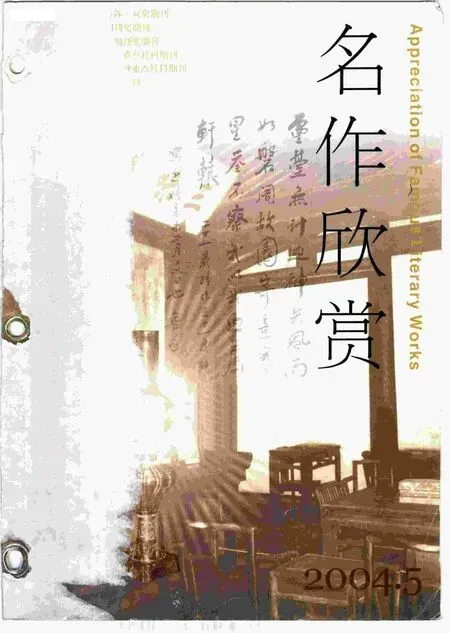浅析川端康成的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理论与创作
⊙韩春红[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浅析川端康成的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理论与创作
⊙韩春红[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川端康成是世界级别的文学大师,其文学创作生涯达五十年之久。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新感觉派文学”的创作虽然短暂,但其文学创作手法、表现技巧等却影响他终生。鉴于此,笔者着重从新感觉派的“文学理论”和“实践作品——《感情装饰》”两大方面来探讨作为新感觉派文学旗手的川端康成,解析他的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理论与创作。
川端康成 日本新感觉派 文学理论 《感情装饰》
川端康成(1899—1972)是日本知名小说家,出生于大阪,毕业于东京大学,是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代表作家。1968年,凭借《雪国》《古都》和《千只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继印度泰戈尔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一、日本新感觉派简述
日本新感觉派(大正末—明治初)、形成于1924年,由日本知名评论家千叶龟雄(1878—1935)命名而来,顾名思义就是“批判自然主义式的写实手法,试图运用感觉上的新颖方法来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学”。其同人杂志为《文艺时代》(1924—1927,金星堂发行),代表作家有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中河与一、今东光、佐佐木茂索、十一谷义三郎、池谷信三郎、稻垣足穗等。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家毫无疑问当属横光与川端。
横光利一在《文艺时代》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头与腹》(『头ならびに腹』,1924),作为新锐作家而崭露头角,被视为“新感觉派的天才”。随后,又先后发表了《拿破仑与顽癣》(『ナポレオンと田虫』,1926)、代表作之一的《春天乘着马车来》(『春は馬車に乘って』,1926)以及集大成之作的长篇小说《上海》(『上海』,1928)等,均充分表现出了新感觉派的文学创作风格,亦巩固了他在新感觉派文学中的领军地位。与此同时,横光还写作了《感觉活动》(『感觉活动』,1925)等文章,从理论层面对新感觉派的文学进行了探究。但是,遗憾的是,《上海》是其最后一部新感觉派文学作品,此后他转入了新心理主义小说的创作。
与横光利一相比,川端康成虽不似横光利一那样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大放光彩,但他却是新感觉派同仁的支柱,绝对不容忽视。那么,川端的“支柱”之说又缘起何处呢?下面,笔者将重点从“文学理论”和“实践作品的创作”来探讨作为新感觉派文学旗手的川端康成。
二、日本新感觉派文学旗手——川端康成的文学理论
纵观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先后出现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新现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以及“艺术派(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等文艺思潮。其中,新感觉派虽占有一席之地,但却可谓是“昙花一现”。原因当然是有诸多方面的,但是笔者认为有一点绝对不可否认,那就是代表作家纷纷放弃新感觉派式的文学创作。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新感觉”这一文学创作方法始终贯穿于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生涯,曾有学者说过:“川端康成的文体的最大特色就在于简洁而又含蓄的表现、诉诸感觉的比喻,以及执拗地聚焦于它们的反复运用和甄选出的特定事物并由此而带来的一种全新的飞跃。”对于“执拗”地聚焦于“诉诸感觉的比喻”这一点,笔者亦有同感。举例说来,《雪国》(1937)开头的“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拔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夜の底が白くなった。信号所に汽車が止まった”这段话,被公认为带有新感觉派的表现技巧。那么,对于“新感觉派”,川端又是如何释义的呢?
早在1924年6月川端康成在一篇文艺评论中就曾说过“我好像被文坛上的一部分人看作是既成文坛破坏运动的勇士”。关于这种说法,川端自己的解释是:“作为新进作家,要抛开既成文坛走另一条道路,并努力朝着那个方面前进。所以,既成作家与新进作家并不是势不两立的。(中略)何谓新进作家的新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并且,通过这种新事物的性质、价值等,也将决定在明天的文坛上既成作家所占的位置。(中略)我们并不希望这些人(既成作家——笔者注)没落,只是想走不同的道路而已。”在此,川端反复强调了新的文学创作道路。那么,川端的新的文学创作道路到底是什么呢?
随后在1924年10月,川端康成与横光利一、片冈铁兵、中河与一、今东光等十三人创办了《文艺时代》。该杂志的题名是由川端命名而来的,卷首的创刊词亦是他写的。创刊当时,其同人均书写了创刊词,但是其中川端的创刊词最具有明确的创刊意识。在创刊词中,川端主张“新文学的创造即是新文艺的创造”“革新文坛上的文艺”“把人生中的文艺或者艺术意识从根本上进行革新”等观点,以及追求“艺术革命与生活革命一体化”的境地。可以说,在创刊之际,川端即为新感觉派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他的新的文学创作就是指新感觉派文学吧。
如上所述,新感觉派文学打破了以往既有的文学传统,日本文坛对此持批判态度的人不在少数,继而引发了文坛上的激烈的论争。在这种背景下,川端康成于1924年12月发表了文艺评论《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宣扬新感觉派的理论根据,阐述了“新文艺的兴起、新感觉的内涵、表现主义的认识论以及达达主义的思维方式等”,从正面回应了各种批判,从而为新感觉派同仁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持。
此外,对于新感觉派的文学理论论述,川端康成还有《新感觉派之辩》(1925)、《回答诸家之诡辩》(1925)、《短篇小说的新倾向》(1925)、《文坛的文学论》(1925)、《关于表现》(1926)、《文坛波动调》(1926)、《文坛现状论》(1926)等。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川端康成在理论层面为日本新感觉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川端康成的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实践作品——《感情装饰》
众所周知,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生涯是极其复杂的。如果按照他的文学创作时期来划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分别是:“文学形成时期(13岁—19岁)”、“第六次《新思潮》时期(20岁—25岁)”、“《文艺时代》时期(25岁—29岁)”、“浅草物时期(30岁—34岁)”、“《雪国》时期(34岁—46岁)”以及“战后活跃时期(47岁以后)”。
其中,在“《文艺时代》时期”,作为一名新锐作家,川端康成凭借在新感觉派文学的同人杂志《文艺时代》上发表的《伊豆的舞女》(1926)而备受瞩目,得到普遍认可。《伊豆的舞女》起笔于1922年,是以1918年川端在伊豆旅行的一段经历为素材创作而成的,因此,普遍认为该小说采用的不是新感觉派手法而是传统手法。但是,随后他发表的《感情装饰》毫无疑问被公认为新感觉派文学的实践之作。下面笔者将着重解析一下《感情装饰》这部小说集。
《感情装饰》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掌篇小说”作品集,亦是他新感觉派文学的实践作品。该作品集发表于1926年6月,由金星堂出版。其中收录了1921年至1926年间川端发表在各种文学杂志上的三十五篇短篇小说。笔者在此仅对《川端康成作品精粹》①中的“掌篇小说”《脆弱的器皿》(1924)、《蝗虫与铃虫》(1924)、《月》(1924)和《自杀》(1926)做以简单分析。
《脆弱的器皿》讲的是,“我”因古董店旁立着的一尊瓷的观音像而做的一个梦。“观世音冰冷的肌肤便同玻璃门一起轻轻地颤悠”“观世音直挺挺朝我倒了下来”“一双低垂而修长的皓腕,突然伸出,搂住我的脖子”,本来观世音瓷像是一个死物,但是在川端康成的笔下却变成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不言而喻,这便是“拟人”修辞法,而这种文本表现手法对于当时文坛上的人来说是非常新奇少见的。
在《蝗虫与铃虫》中,有一段关于“绿光”和“红光”的描述:
可是,映在女孩胸前的绿色的微光,使我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二夫”三个字。(中略)从这只灯笼映在男孩腰间的字形虽然不如“不二夫”三字那样明显,但我还是能辨认出那晃动的红光是“喜代子”这个名字。
女孩胸前的红光映出“不二夫”、男孩腰间的绿光映出“喜代子”,这一男一女、一绿一红、一“不二夫”一“喜代子”的对比(对照)描写是那么鲜明、那么富有立体感,就好似坐在电影院里看到的特写镜头似的。从中我们也似乎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纯纯的喜爱。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终会被忘却;也许随着喜爱的升华,转化为爱恋。但是不管怎样,那种童年时代的少男少女间的美好回忆是值得我们追忆与缅怀的吧。
接下来,在《月》中,关于“童贞”有这样的描述:“童贞——这东西实在是讨厌的累赘”“那时,他会仍然提着‘童贞’这件唯一的行李出门行乞吧”,可以明显看出在此川端康成运用了“拟物”修辞法,即把“童贞”物化了。此外,“既然心情沉重地把它携至此地,光凭这一点,恐怕也不愿拿它喂路旁的狗吧”,有观点指出这是说“并非是女人谁都可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觉得此种表现手法应归类为“隐喻”吧。与此相对,“啊!明月!让我将这感情赐予你吧!”这句话中又把月亮这个“物”比拟成“人”,即“拟人”修辞法。可以说,通过这些表现手法,更加强烈地表达了文中的“他”对于女人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世间似乎是找不到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女子了。”
最后,关于《自杀》一文,日文题目为“心中”。该词语根据《大辞林》的解释是“相爱的男女商量好一起自杀,即殉情;两人以上一起自杀”。而小说的结局是,“母女俩竟双双死去了。说来也怪,她丈夫也并枕死在身旁。”这也恰恰印证了该题目。但是,在结局之前,小说的内容可谓扑朔迷离、充满悬疑,阅读起来多少有些拗口难解吧。比如说,开篇即说:“因嫌弃她而出走的丈夫,写来一信。是两年后,寄自一个遥远的地方。”通读全篇小说便可知道“她”共收到了丈夫从不同地方寄来的四封信,信的内容分别是:
——不要叫孩子拍皮球。我听到皮球声了。那声音叩击我的心。
——不要叫孩子穿皮鞋上学。我听到皮鞋声了。那声音践踏我的心。
——不要叫孩子用瓷碗吃饭。我听到碗响了。那声音割碎我的心。
——你们不要弄出一点声响来。也不要开门关门。不要喘气。家里的时钟也不许响。
令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在遥远地方的丈夫是如何听到那些声音的呢?话里话外就好像是在“她”和女儿身边似的。其实不然,丈夫已经离家出走两年了,至于为何给“她”寄信呢,也许正如著名小说家井基次郎(1901—1932)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父亲的他在看到跟女儿同龄的孩子唱歌、踢毽球、幸福地上学时,不期然地就会想起因自己的出走而失去父爱的女儿;与其他孩子的幸福相比,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一种不幸的存在,这又使他感到痛苦。或许是因为内心承受的痛苦严重到心脏已承受不住脑海中所想象出的女儿的皮球声、皮鞋声、碗响,他最终给妻子的“她”寄来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吧。
概括说来,像上述的“拟人”“对比(对照)”“拟物”“隐喻”等的表现手法、“奇特的故事情节”构思等,旨在说明《感情装饰》这部作品集中的一些作品是凝练了川端康成的创作技巧的。换言之,川端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对“新感觉派”的文学题旨与艺术手法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因为,新感觉派文学的文章构成特点就在于“欧文派②、大胆的拟人手法、隐喻”等。
概言之,通过川端康成的新感觉派文学理论的论述、《感情装饰》的文本解读,可以阐明川端为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① 高慧勤选编:《川端康成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页。
② 直译西洋文字来表达日语中前后文的逻辑性。
[1] 稻贺敬二,竹盛天雄,森野繁夫.新订合国语便览[M].第一学习社,2001:199(.本论文中的日文参考文献引用内容的译文皆为笔者试译)
[2] 长谷川泉.川端文学の机构[M].教育出版センタ—,1984: 291.
[3]李在圣.川端康成の文体の魅力—『雪国』『千羽鹤』を中心に—[J].国文学解と鉴赏:川端康成特集(62卷).至文堂,1997(4):79.
[4]川端康成.敌ではない·川端康成全集第三十卷[M].新潮社,1982:121-122.
[5] 川端康成.新进作家の新倾向解说·川端康成全集第三十卷[M].新潮社,1982:172-183.
[6] 第一学习社编辑部.新编日本文学史の研究[M].第一学习社,1992:126-127.
[7] 森晴雄.川端康成『第一短篇集』—「月」を中心に—[J].国文学解と鉴赏:横光利一と川端康成特集(75卷).至文堂,2010(6):56.
作 者:韩春红,文学硕士,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面上项目“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日本作家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启示”(编号:12512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