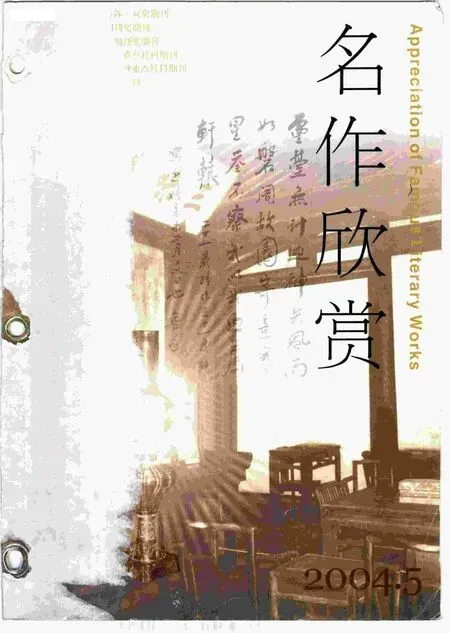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秋歌》情怀
印度古代有一则寓言:牧人仗着牧犬在旁守卫,在树荫下安然大睡。毒蛇从草丛中亮着毒牙爬来,眼看这牧人便要受害,好心的蚊子连忙前来营救,它狠狠地叮了牧人一口。牧人被叮醒了,打死了毒蛇免了灾。朦胧中他还拍了蚊子一掌,可怜的蚊子便丧命身亡。弱者对强者可别去刺伤,否则难免这蚊子般的下场。这样的事情世上多有,休说什么你是好心帮忙。每次读到这则简单的寓言,都让我产生丰富的联想,它让我想起我的青春激情年代,让我想起20世纪50-70年代的知识分子,让我想起常让我的心隐隐作痛的郭小川及他的《秋歌》。
据当时知情者说,写此诗时诗人在农场是以极其虔诚、配合的态度面对管理人员的批评训斥的。在农场干校相对封闭的惩罚空间里,异常令人疲惫的田间劳动在诗人看来是改造世界观的必要途径,他坚信“大好形势”“一片光明”,绝不能绝望放弃,即使生命“化烟”,也是“火药味很浓很浓”。所以,他忍受着身体的多种疾病,顽强地坚持着,他相信阳光一定会照射到他的身上。因而,他不停地谴责、否定自己的“昏睡”“迷茫”,他要把自己滚烫的心掬捧到天地之间,让祖国、人民、“同志”、“亲人”看看,这是不是一颗真诚、执着的赤子之心?想至此处,心总是酸酸的,但又欲哭无泪。究竟为什么?为诗人心碎?诗人不值得?还是觉得诗人明月之心为沟渠时代所误是人生遗憾?难以言传。
记得在1978年,我读到这首诗时,心中陡然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震撼,肺腑之中似有汹涌澎湃的海水在奔腾撞击。啊!“战士”!“革命”!“人民”!“斗争”!这是那时极被人们认同的话语。况且,由于这首诗是“新辞赋体”,音韵铿锵,节奏鲜明,读之朗朗上口,是诗歌朗诵的最佳稿本。因此,我很快就把它背了下来,且不止一次在大学晚会上表演。我站在舞台上,严肃庄重,昂首挺胸,慷慨激昂,丁字步站开,屏息凝神做缅怀沉思状:“一年一度的强劲秋风啊,把我从昏睡中吹醒;一年一次的节日礼花啊,点燃起我心中的火种……”我俨然,不,我就是内心洋溢着革命、理想、忠诚、激情的“不懂政治”的诗人郭小川!我就是“心明眼亮”,随时准备向“鬼蜮横行”,向“修正谬种”发起冲锋,铭记“斗争哲学”的“战士”郭小川!
今天,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过去,我还有这种情怀吗?读者还有这种情怀吗?这种表情与姿态只能在叙述那个时代的作品中才能找到,离今天越来越远,几近陌生了。
郭小川虽也可称为知识分子,但按专家的看法属体制内知识分子。遵守政治规范与服从召唤是一种责任义务,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自觉的道德自我约束。反观诗人一生,即使是极度地皈依时代政治,却也难以掩盖其精神深处闪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光亮,那就是他具有超越自身的利益而关怀具有一般性、普遍性问题的特质和品格。只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他的这种超越依然是在权威话语统摄之下,这也就愈见其悲哀。犹如寓言中的极想帮助猎人的蚊子。“蚊子”的结局是“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结果”(黄平博士语)。我模仿此句式说一句:有信仰之激情与不知荒谬之结果。
这组论文作者除徐志伟博士外,皆是研二学生。徐志伟是王晓明先生的博士,是我邀来助阵的。
文章以郭小川的《秋歌》为批评对象,是因为在讲当代文学思潮时总觉得一些定论不确切,很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锻炼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
读者可以看出,诸多论文表述还很幼稚,乃至偏激,但确实是这些研究生用心思考的结果。如果回归历史本真场景,须有许多考证才是,这些论文皆有此短。其长是以文本解读为主,识见为主,但历史的因素或多或少已渗透其中。至少,可以看作是他们锻炼批评能力的辛苦尝试。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