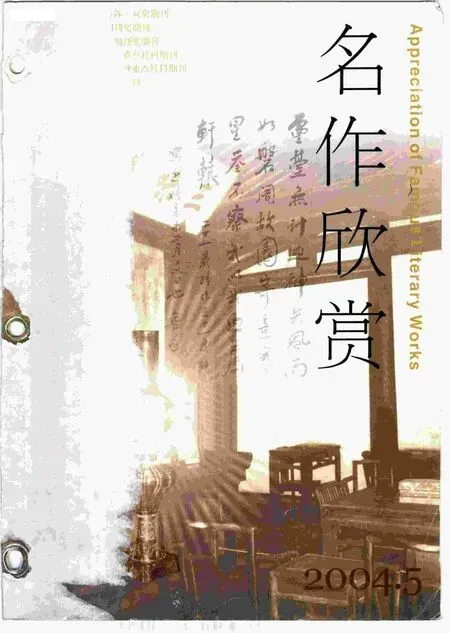雷平阳:乡愁是诗歌永远的来路
⊙牛殿庆[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作 者:牛殿庆,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学报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
雷平阳的诗歌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呼唤,是一种回归,回归故乡、回归母亲、回归琐碎的生活、回归尘埃。能让读者感动和震撼的诗在当代新诗中很少见了,读雷平阳的诗却满足了我们这种欲望。这种感动和震撼是诗人植根于故乡,植根于泥土,“一头扑进亲人怀”的和谐相融的眷恋。他的诗在智性的启迪中有了更多忧伤和温暖,以至于让我们流泪,在他的诗后面站着一个对家乡情深义重、胸有大爱的诗人,所以他的乡愁不是肤浅的表白,而是睿智的呈现。雷平阳以乡愁为核心的诗大致是沿着三个向度来创作的。
一是对家乡草木的依恋,对亲情的依恋。这里包含了和谐维度的人与自然、人与人融汇的情感。这种依恋近乎“偏执”,他在《亲人》中这样表达:“我只爱我极速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是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蜜蜂”。这种一咏三叹的申述,不仅表达的是对故乡固执的专一,更是对家园的坚守。因为家乡山川草木不仅是视觉上的美丽与壮阔,更是给他以丰沛的精神想象,是他诗情才智的不竭之源。
那首备受争议《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把他对家乡山水之恋写到了极致:“澜沧江由维西县向南流入兰坪县北甸乡/向南流一公里,东纳通甸河/又南流六公里,西纳德庆河/又南流四公里,东纳克卓河”。这类似于一幅澜沧江的水系图,有景无情,几乎接近于地理资料,这被称作的“零度写作”不管受到多大质疑,诗人确有自己的坚持,“我至今依然偏爱这首诗,尽管它确定是一份地理资料,只是每读这份资料,我的灵魂都会由衷的颤栗。三十三条支流,都通向一个世界,我以笨拙藏下了无尽的想象。”经过诗人这样诗意的解读,我们再回头去读这首诗时,确实感到了澜沧江三十三条支流恣意奔跑的壮观和伸向世界不可知的神秘。在雷平阳的笔下,故乡的山水草木因宏阔而宽容,因苍凉而悲悯。
我们来读《背着母亲上高山》:“背着母亲上高山/她困顿一生的地盘。真的,那只是/一块弹丸之地,在几株白杨树之间/河是小河,路是小路,屋是小屋/命是小命。……”整首诗里洋溢着低对高的敬仰,高对低的俯瞰,小对大的依赖,而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和所有故乡一样高大并且超乎所有高大之外的亲情,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最无私的感情。诗人用自己的诗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伟大而平凡的母亲的伟岸。在《母亲》一诗中,诗人是这样来报答母亲的:“母亲,就在昨夜,我看见你/坐在老式电视机前/歪着头,睡着了/样子像我那个九月大的儿子/我祈盼这是一次轮回,让我也能用一生的/爱和苦,把你养大成人”。雷平阳的诗怎么说也走不出母亲的怀抱,走不出家乡的《望乡台》,他是一个永远为着母亲、亲情、乡情而歌唱的诗人。这是对母亲的敬畏,也是对家乡故土的敬畏,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的一切苦难在自然面前都变得轻而小。雷平阳对山川的书写不是简单复制,更看重的是人在家乡故土面前的位置关系:“用一条江的鱼养家/用一条江的水洗脸/劈开的山,掩埋一生的梦”(《怒江》)。诗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是骨肉相融:“我们一起观看山上的火、缅甸的落日/我们谁也说不清,辽阔的世界/究竟存在多少类似的角落——/用玉温丙的话说/影子会变成草,悄悄地蹿进骨肉的缝隙”(《布朗山之巅》)。这种人与自然相融之境大概是天人合一的最理想的追求。这种人与家乡、自然浑然一体的追求,或许在下面的文字里可以找到一些缘由:“和大象回家不同,人往往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那些大地的孩子,神的孩子们,他们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旷绝古今的魂路图。谁也不例外,人一死,就得踏上这条路,返回祖先的原生地。”(雷平阳荣获“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6年度诗人”获奖感言)读了这些肺腑之文,就应该理解诗人为什么在他的诗里写满了乡愁,这源于对家乡的敬畏,对自然生灵草木的敬畏,人的一生剔除不了生之罪,就不会魂归故里。
二是对那片土地上人心苦难的观照。这是雷平阳的诗最感人的一部分。诗人用冷静、朴素的语言记叙着生活中被人熟视无睹的片段和故事,几乎是对本真生活场景的还原,没有抒情,没有评论,但站在不动声色的诗句后面的,是诗人抑制不住的愤怒、悲哀与忧伤,而在悲哀的后面,没有颓丧,是对人生苦难的温暖的悲悯与关怀。下面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个过去的故事,也是让人感动的故事:“张天寿,一个乡下放映员/他养了八只八哥。在夜晚人生鼎沸的/……/张天寿和他的八哥/走遍了莽莽苍苍的哀牢山/八哥总是在前面飞,碰到人就说/‘今晚放电影,张天寿来啦!’/……/八哥对影片的名字倒背如流/边飞边喊《地道战》《红灯记》/……/有一天,走在八哥后面的张天寿/一脚踏空,与放映机一起/落入了万丈深渊,/……/一直有一只八哥在飞来飞去/它总是逢人就问:‘你可见到张天寿?’……”(《存文学讲的故事》)八哥喊着《地道战》《红灯记》,喊着一个时代的符号。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自身在这个时代的存在和不要轻易遗忘这个世界。在这里,人和八哥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亲情关系,昭示了人与物的和谐。诗人用灰色笔调描绘了一个“与己无关”的画面:哈尼寨、大雾弥漫的山脉、会说话的八哥,诗人始终没有现身在画面上,这个创造的意境本身就体现了诗人的和谐维度的诗意追求。一贯自诩富于情感的人类在一只单纯的八哥面前退缩了,一只八哥的飞来飞去轻易超越了人类间所有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
诗人让见惯不奇的生命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重新焕发出人性的温暖,如《地上的阳光》中那个山中贫穷的农村夫妇:“我的母亲对着斜坡大喊:‘嗨,卖水人/我没有钱,但可以煮顿饭给你吃’……卖水人/坐在我父亲的旁边,始终很少说话……他走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他对父亲说/我的村庄是一个开裂的村庄,然后/挑着两桶月光消失得一干二净”。贫困没有让善良消失,也没有让苦难而清贫的小山村的温暖消失。诗人不仅挽留温暖,还对自然界生灵的被屠杀表示极大的痛惜:“把这么多胸膛都剖开了/把这么多的飞行和叫鸣终止了/……/死亡的香味不分等级/可以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我没有劝戒什么,反而觉得/麻雀堆里,或许藏着/我们共同的,共有的杀鸟技艺”(《卖麻雀的人》)。诗人不仅对卖麻雀人的冷漠表示愤怒,诗的最后两句上升到人类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批判高度,在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杀戮中,也许每个人都是参与其中的刽子手,这种清醒的自我反省和忏悔,向世人提出了犀利的追问。
三是对即将消逝的原生态家乡的忧虑,这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的忧虑。万物都是有规律的,这是自然的法则。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不和谐,不和谐生态就会遭到破坏,上天就会惩罚人类。在一个生硬的现代化的背后讲诗歌的“乡愁”,难免有无病呻吟和附庸风雅的怀疑。毕竟现实中大量的耕地、山林、绿地,乡土的资源已日近枯竭,被重新编排、整合的村庄夹杂在现代化生产机器隆隆的轰鸣声中,生冷的钢筋水泥的建筑不断地耸立,不断翻新吞吐出陌生的产品。那些胆怯、弱小的乡亲,注定将离开昭通、苍山、怒江,被抛进一座座冷漠的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向着山村蔓延和侵略,人们在享受着商业化带来的财富快乐的同时,却没有顾忌到乡村生活的破坏。那令人梦魂牵绕的乡村正被现代工业侵蚀和毁灭,这让以家乡为生命背景的诗人怎能不焦心忧虑:“我想说,我爱这个村庄/可我涨红了双颊,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像传说中的一朵花,长到一尺高/花朵像玫瑰,长到三尺/花朵就成了猪脸,催促它渐变的/绝不是有情有义的泥土”(《我的家乡已面目皆非》)。乡村的异化,破败不堪,“像被大火烧毁的古代建筑群”(《在会泽迤车看风景》),“春风的双重之火,蔓延在冶炼厂的上空”(《春天》),“樱花在哪?眼睛里全是黑色的空气”(《圆通街的樱花》),诗人再也感觉不到家乡的青山绿水,乡村土地消失后的悲凉,让诗人的乡愁变得浓重而抑郁,“都碎了,完整的只有时间的尘埃”(《凉山在响》),“数不清的裂口,一直向上/停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的地方”,“黑铁一样的水,依旧不为所动顽固的结成一块”(《类比的哀痛》),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我们在诗人的悲哀中开始警醒,开始反思,开始回望人类的乡愁。
“他站在故乡经验的针尖上,怀想世界天真的童年,也领会了个人生命的灿烂与悲情。”①正是雷平阳诗歌对故乡的怀想,让我们对乡愁有了明确的方向感,让现代人空虚焦躁的心灵有了诗意栖息的可能。
① 《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度诗人授奖词》,《南方都市报》,200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