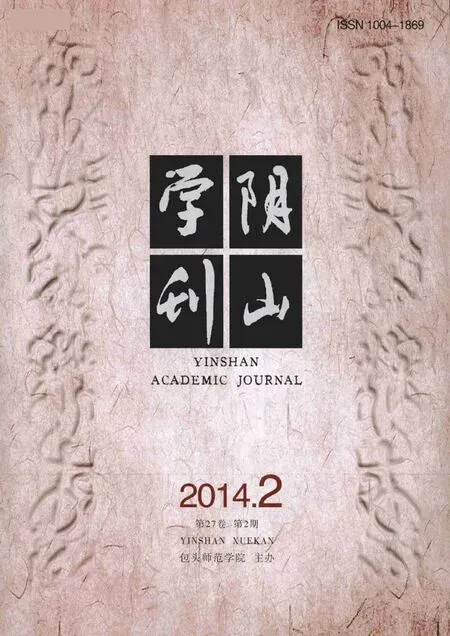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看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涵
罗 璇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在南宋以及整个中国诗歌史中都显得独树一帜,被严羽称为“诚斋体”,并且在南宋以及其后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对其诗歌的各种评述也屡见不鲜。但是,杨万里诗歌的独特之处并不仅仅表现为诗歌体式或语言的创新,而更体现在其诗意的创新上。这种诗意的创新,其背后其实有着理学思想的深深浸染。作为理学重要奠基人之一的程颢所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一理学命题与杨万里诗歌的内蕴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值得我们仔细检索和体味。
程颢《识仁篇》有云:“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1](P16~17)
在程颢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一哲学命题中,包含着几层非常重要的意思:第一,程颢在定义“仁”的内涵和特点时,认为达到“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是成为“仁者”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成为“仁者”所应达到的境界;第二,“浑然与物同体”境界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与物无对”,二是“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这就指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不是一种“以己合彼”的状态,而是两者完全浑融为一个整体,在这种浑融一体的状态下,进而达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也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我”就成为了一个与天地万物浑融一体的“大我”;第三,当真正实现这种“与物无对”的“大我”境界时,再来反观自己,便会感到一种至大之乐,也就是实现了这种“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境界时的至大之乐。从这三个层面对杨万里诗歌试作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蕴。
一、 “生生之仁”与杨万里诗歌中的盎然生意
杨万里诗歌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在于充满字里行间的盎然生意。他的诗作最为擅长表现自然万物的生命活力,尤其富于特色的就是他能够将各种本是静态的景观或是常见的现象描写的生意盎然,富有十足的生命力和动态美。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1](P118)陆游诗歌更多地是把景物当作一种欣赏或外在于自己的对象进行静态的描写,而杨万里所要描绘和展现的却不是自然事物的外在形貌,而是要更深一层,进入事物的生命层面,来充分展现他所体察到的内在于万物之中的活泼泼的盎然生意。杨万里将自然万物都看作生生不息、充满生命活力的灵性生命,并在他的诗歌中反复加以表现,这种以动态生命的方式观照自然万物的眼光与程颢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程颢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1](P120)他又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1](P29)天地化生万物,赋予万物以生意,这是最高的“善”,最大的“仁”。可见,生生之理乃是程颢哲学中“仁”的第一层重要内蕴。程颢的这一思想显然来自于他对易学以及周敦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生”是《易传》的核心观念之一,《易传》中将天地化生万物看作天地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3](P349),“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3](P318~319)易学作为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极大重视,也是先秦道德儒学在宋代能够转化为学理深刻、体系周详的新儒学的重要理论根据。因而,易学在宋代理学家的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也非常重视对易学思想的研究和阐发。“生”这一易学核心观念在宋代得到理学家的大力阐扬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周敦颐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4](P498)程颢也说:“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1](P60)可见,周敦颐将《易传》“生生之谓易”的思想又进一步发挥了,他在认识到“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这一天地间的道理之后,便在实践中通过周身细小的一草一木来仔细体察天地万物的这种生意。程颢、程颐兄弟都曾问学于周敦颐,尤其是大程子对周敦颐的思想有更多的领会和继承,万物生生之理,程颢也颇受周敦颐的影响。
程颢云:“观天地生物气象”[1](P83)。他又置盆池养小鱼:“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唯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4](P578)程颢的这些思想和行为显然是受到周敦颐启发之后对万物之生意的体察。更为值得重视的是,周敦颐和程颢对万物生意的体察不是以一种理性认知方式进行的,而是重在心灵层面的体认和观照,“‘观天地生物气象’,无疑指的是从整体上体认天地造化万物所涵具并彰显出的一派浩然盛大、沛然莫之能御的盎然生机、生意。这种‘观’或‘看’,不是西方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二元分际甚明格局下的经验感知,主要不是以作为感官的目之‘观’或‘看’,毋宁更是一种生命全副投入其中而与之无隔的心灵、精神的观照、体认。”[5]
周敦颐和程颢在对《易传》“生生之为易”这一思想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发展:第一,由周敦颐开始将《易传》这一抽象理念落实到对周身细小的自然万物的具体体察中,从而使得这一理念有了可以在日常心性修养中领会的可能性;第二,程颢在继承周敦颐体察身边细小事物生意这一理念的同时,更进一步去体察万物生意中所体现出来的“自得”之意,这种“自得”之意显然是对万物之“生意”的进一步阐发,展现出万物生命力的自由舒展;第三,周敦颐和程颢是以体认感知的方式来观照万物之生意和自得之意,在这种全心投入的体认观照之中,人与万物之间有了融为一体的可能。周敦颐和程颢对《易传》这一哲学思想的阐发显然带有鲜明的感性直观特征。
杨万里是南宋理学修养非常深厚的诗人,他在其哲学著作《庸言》中表达了自己对儒家六经的独到见解,可以见出其儒学修养的深厚功力,同时,在其退居南溪之后,耗费十七年时间,完成了体系精详的《诚斋易传》一书。这部书后来与程颐的《程氏易传》并行于世,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也足可见出杨万里的理学修养是得到理学界人士承认的。
正因如此,杨万里诗歌中的山水景物才会展现出完全不同于前人山水诗中的面貌。对于同样的景物,他看到的并不限于外形,对于前人不太注意的细小事物或景象,他则更能从中挖掘到常人体察不到的生意。正如周敦颐和程颢能在窗前小草和池中小鱼这些极为常见却不被人重视的细小事物中体察到作为“天地之大德”的“生”,杨万里在他所看到的一草一木中也不断地体察到了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意,从而产生“万物毕来,献予诗材”的感受,因为这些似乎常被人道的日常景物在他的眼中已经富有了不一样的意蕴,它们不再是外在于诗人存在的客观物体,而是与诗人一样领受了来自于天地之大德的生生之意的有生命、有灵性的存在,它们的生命与诗人一样在这充满着生生之大德的宇宙天地间自由舒展、盎然挺立,自得自适。因而,当杨万里用这样的眼光去观照这些似乎再平常不过的自然万象时,他的笔下就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却又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一个充满着蓬勃而自得的生命力的世界:
《雨后晚步郡囿》:
画舫鸣钲野寺钟,暮声惊破翠烟重。
好风不解藏天巧,雕碎孤云作数峰。[6](P112)
《春草》:
天欲游人不踏尘,一年一换翠茸茵。
东风犹自嫌萧索,更遣飞花绣好春。[6](P209)
风吹散云层,山峰逐渐展露出来,这一极为常见的自然现象在诗人眼里却是因为“好风不解藏天巧”,想要展示自己精湛的雕刻技艺,故而要“雕碎”云层幻化出秀美的山峰。这一本来极为自然常见的自然现象在诗人看来却是缘于风的主观意态,它要让这些蕴藏着天巧的山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将风写成了具有生命意态的存在,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诗人更是将春季春草复苏,铺满大地以及花开遍野这些本来是季节更替最为平凡的自然景象看作是天对游人的体贴以及东风在此之上的锦上添花之举。在杨万里的诗中,天地万物不再是外在于诗人而存在的静止的客体,而是带着挡不住的生意向诗人走来,涌现到诗人笔下,它们都带着各自的灵性生命,与诗人对话,在这浩大的宇宙天地间自由挥洒着自己的生命力,“世界在他的眼里并非是一个冷漠的客体,而是活泼泼的生灵,他能与之产生情感的交流、心灵的默契”[7]。因而,我们在他的诗作中能够感受到程颢所说的“万物皆有春意”,一切天地万物在他的笔下都展现出领受于宇宙天地的勃勃生机。
杨万里不仅充分展现出自然万物自发的勃勃生意,更在这生意中展现出自然万物的“自得”之意,他的诗句如“雨为梅花遣尽尘,柳勾日影自传神”[6](P464),(《雨霁》)“春禽处处讲新声,细草欣欣贺嫩晴”[6](P446),(《春暖郡圃散策三首》)“柳丝自为春风舞,竹尾如何也学渠”[6](P487)(《寒食相将诸子有翟园诗》)显示的不仅是自然万物的自然生命,更把自然万物当作一种有主观情态的生命体来展现它们在天地所赋予的生意之中所展现出来的自由自适之感,对万物客观展现出来的生意以及它们的主观情态的充分展示才构成了杨万里诗歌中对“万物生意”的完整表现。
杨万里在《庸言》中解释“中”与“和”时说:“不观之天地乎?阳气潜萌、万物归根之谓中,分至启闲、序则不愆之谓和。观吾心,见天地,观天地,见吾心”[6](P1461),“中”与“和”这组概念本是最早由《中庸》提出用来解释“性”之“未发”与“已发”的。杨万里在这里用“天地”来解释“中”与“和”,正显示出他将“吾心”与“天地”看作是息息相通、互为一体的,天地与人心之间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天地与人心也正是理学家所最为注重的两个层面,他们用“天理”将两者密切联系起来,使两者通过“天理”而成为可以互相贯通的整体,因为理学家大多认为天地与人心都是“天理”的具体体现,只是呈现方式不同,两者都分别显现着“天理”所赋予的属性。杨万里将天地与人心看作紧密相联,息息相通的整体,正体现出他对理学这种将天地万物与人之心性密切联系起来看待的观念的认同。杨万里的这种将人心与天地贯通起来看待的理念与程颢正有相通之处:“不当以体会为非心,以体会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说。圣人之神,与天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在此。此心即与天地无异,不可小了佗,不可将心滞在知识上,故反以心为小。”[1](P23)程颢也将人心与天地看作互为一体的存在,两者之间是互相贯通的甚至互为一体的。尤其是,程颢认为“人心”与“天地”互为一体的主要方式正在于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为特点的“体会”,充分体现出其思想中的感性直觉特征,这也与他所说的“观”的内涵是相符的。
杨万里以人心和天地互相阐发的思想,使得他对自然万物的把握方式与以往的山水诗人有了很大不同,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使得自然万物在他的眼中不再是外在于诗人的事物,而具有了内在的相通性,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他是以“观天地”这种更具有直觉感知特色的方式来体会天地万物的生命力的存在,天地生物之气象在杨万里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程颢在对万物生意的体察中,感受到了天地化生万物的生生之“仁”,也体察到这一生生之“仁”乃是蕴藏于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之中的共同的天理。正是对这一共同天理的体认,成为“仁者”实现“浑然与物同体”的前提。程颢云:
“‘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著。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来依旧。”[1](P34)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1](P33~34)
从这两段话来看,程颢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以及“万物一体”,其内涵并非是指人拥有了天地万物的各种功用特征,而是指人与天地万物都同样内在地蕴藏并体现着天理这一天地间的终极性存在。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并不是说,自然界的现象都是‘我’所作为,如自然界刮风下雨,就能‘呼风唤雨’。这种境界的哲学意义是打破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中国哲学称为‘合内外之道’。”[8](P112)正是因为人与天地万物都共同内在地具有了这一天理,人与天地万物才能够具有内在地成为一体的可能。这一天理的内涵正如程颢所说“天只是以生为道”,也就是《易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3](P315),正是天地化生万物的生生之理。
正如叶嘉莹所说:“在宇宙间,冥冥中常似有一‘大生命’之存在……它的存在、它的运行不息与生生不已的力量,却是每个人都可以体认得到的事实。生命界之中的鸟鸣、花放、草长、莺飞,固然是生命的表现; 即使非生命界之中的云行、水流、露凝、霜陨,也莫不予人一种生命的感觉……‘我’之中有此生命的存在,‘物’之中亦有此生命之存在。因此我们常可自此纷纭歧异的“物”之中,获致一种生命的共感。”[9](P266)她所说的宇宙间之“大生命”其实正是理学家所说的“天地化生万物”之“理”,而“生命的共感”的获致其实也来自于对这一“大生命”也就是“生生之理”的体会。
因而,通过对这一彰显着最高“天理”的“生生之仁”的体会,“天地”与“人心”、“万物”与“我”才有了在根本意义上融为一体的可能性。杨万里的“观吾心,见天地,观天地,见吾心”以及程颢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其根本意义都在于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打破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使“天地”与“人心”、“万物”与“我”内在地融合在一起,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障碍,成为不分彼此、不分内外的整体,而这种融合不是物质层面的合并而是精神层面彼此界限和对立状态的彻底消除。
在杨万里所体察到的这个充满生意、流布着天地生生之仁的世界中,诗人与天地万物都自由舒展着自己的生命力,各适其性,怡然自得。诗人仿佛在这些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之中窥见了蕴藏其中的深意,他不仅仅只是在与这些自然现象对话,而是更进一步在与隐藏在这些生意盎然的万物之后的天地造化对话,怀着欣喜的目光在揣测着天地造化生化出这些自然景象的深意所在。他的诗歌所要表现的不只是简单复制所见到的自然景象,而是试图去寻找这些自然景象之后所内蕴的造化之生意,张镃称道杨万里的诗说“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我们在杨万里的诗歌中看到的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的描摹,而是那种充溢于天地间的造化之生意在天地万物间的自然流动的生动图景。
二、 “浑然与物同体”与杨万里诗歌的仁者情怀
杨万里在《庸言》中曾对程颢关于“仁”的看法作过解释:“或问:“程子谓‘仁者,觉也’。觉何以为仁?”杨子曰:“觉则爱心生,不觉则爱心息。觉一身之痛痒者,爱及乎一身,故孝子发不毁;觉万民之痛痒者,爱及乎万民,故文王视民如伤;觉万物之痛痒者,爱及乎万物,故君子远庖厨。”[6](P1451)程颢认为“觉”是成为“仁者”的必要因素,而杨万里将程颢所说的“觉”的内涵理解为对“万物之痛痒”所表现出来的“爱心”,应该说这里面包涵着两重内涵,第一,首先要有“觉”的意识,能够觉察到万物之“痛痒”;第二,是在觉察到的基础上要能够以“爱心”去关怀万物之“痛痒”。
杨万里关于“仁”与“万物之痛痒”之间关系的看法其实也来自于程颢:
“‘刚毅木讷’,质之近乎仁也;‘力行’,学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以为仁之方也。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1](P74)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痒,谓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犹是也。盖不知仁道之在己也。”[1](P366)
“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它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1](P33~34)
可见,上文论述的“生生之仁”只是程颢在“仁者与物同体”这一命题下对“仁”的涵义的第一层解读。“生生之仁”来自于“天理”,而对于人来说,“仁”的境界则表现为“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在这一境界中,“人”从与万物同样作为天理的具体体现的存在转化成一个能将天地万物都囊入胸怀之中的“大我”。这一“大我”并非在物质形态和功用上具有了万物的一切形态和功能,而是内在地具有一种与天理同样的囊括宇宙的宏大气象,即是一种将天地万物看作一身,品物万形视为四肢百体的境界。更为重要的是,以这样一种境界去体察品物万形的痛痒,以关怀己身的态度去关怀天地万物。这就是程颢在体会“天理”所彰显的“生生之仁”的基础上,认为人应该具有的“仁”的境界,而这一境界也正来自于对“生生之仁”的体察和领会。显然,这比上文所说的人与万物因共同领受来自于“天理”的“生生之仁”而具有了内在共性,从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境界更进一步,程颢所提出的这种以圣人为代表的“至仁”境界则要求人不能将万物与人看作独立的个体,不只是内在地具有共性,更要直接将万物看作自己的一部分,完完全全地与自己融为一体。“万物之痛痒”的提出显然比体察“万物之生意”又更进一步,因为对“万物之痛痒”体察的可能性建立在真正意义上将其看作自己的一部分的基础上,就如同体察自身的痛痒一般,因而,程颢提出对“万物之痛痒”的体察是对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的要求,也是对这一境界的准确描述,而他对这一境界的追求也充分体现出其哲学思想的感性直观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程颢这种‘万物一体’境界的获得,不是通过逻辑分析而达成的,而是本体体验的结果。它在形式上表现为感性的观照,或曰感性形态的直观,是一种当下的、直接的、整体性的把握”[10]。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浑然与物同体”,达到一种浑然一体的境界,而不是彼此相合这种仍有隔阂的状态。由此可见,杨万里将程颢“仁者,觉也”中的“觉”的内涵解释为“万物之痛痒”也是深深契合于程颢思想本身的。
杨万里在《跋丰城府君刘滋十咏》中说到:“丰城府君爱山成癖,不知身之化为山欤,山之化为身欤?”[6](P1577)山与人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体现出一种内在的“与物同体”的状态。他的诗歌中也有很多展示诗人对自然万物之“痛痒”的体察,如“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6](P164)(《暮热游荷池上五首(其三)》),本是诗人自己感到夏季傍晚酷热难耐而去荷池边寻找可以纳凉之地,但是当诗人看到池中荷花都藏在大大的荷叶之下,就开始关心荷花是否也因为难耐酷暑才纷纷躲在荷叶之下;还有像“桃花爱作春寒信,只恐桃花也自寒”[6](P255~256)(《二月一日晓渡太和江三首(其二)》),诗人虽然觉得在春寒料峭时就悄然绽放的桃花固然很美,却不禁开始担心桃花在这种初春时节也难免会感到丝丝寒意。诗人正是在以体察“一身之痛痒”的心境在体察、关切着荷花的不耐酷暑以及桃花可能经受的寒冷。“万物之痛痒”此刻也成为诗人“一身之痛痒”的一部分,在这种感同身受之中,诗人与万物成了不分彼此的整体。
在这种状态中,诗人不仅将自然万物当作与自己的一部分来体察“万物之痛痒”,更从万物自身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地为它们着想,细心地体察着它们的喜怒哀乐,如“蜘蛛政苦空庭阔,风为将丝度别檐”(《晚兴》),从对蜘蛛苦恼的体察来看待蛛丝被风吹到别檐这一无意之举,使得这一无意之举瞬间成为使蜘蛛由忧转喜的过程,诗人通过自己的这一细致体察将蜘蛛细小的喜怒哀乐展现了出来;又如《观鱼》一首描写小池中鱼儿们的情态也殊为细腻动人,“鱼儿殊畏人,欲度不敢度。一鱼试行前,似报无他故。众鱼初欲随,幡然竟回去”,诗人显然不满足于只是描写鱼儿的动作行为,而是兴趣盎然地将鱼儿们的内心情态都形神必现地展现出来,仿佛诗人与鱼儿之间是完全相通的一般。
正因为杨万里以“与万物同体”的心态去体察万物之情态,他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一种息息相通的亲昵和温情。在杨万里的诗中,自然万物与诗人之间没有隔阂、关系亲密,互相之间可以称兄道弟,“梅兄冲雪来相见,雪片满须仍满面”[6](P626)(《烛下和雪折梅》),或携手同行、共饮美酒,“我行山欣随,我住山乐伴。有酒唤山饮,有蔌分山馔”[6](P259)(《轿中看山》),还会为诗人殷勤效劳,“风亦恐吾愁寺远,殷勤隔雨送钟声”[6](P356)(《彦通叔祖约游云水寺二首(其二)》),诗人与自然万物之间这种亲昵而密切的关系体现出诗人与万物之间的内在相通的存在。
杨万里诗歌之所以能在如此丰富的古代山水诗中显得独树一帜、极为富有个性色彩,其关键点正在于杨万里用完全不同于其他山水诗人的眼光看待物、我关系。自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人,在他们的山水诗中展现出了丰富多彩、富有生意的大自然景象,但是仔细体会,便会发现,他们仍然是用一种对待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界中的一切,将自然万物仍然看作外在于人的审美客体,诗人通过对他们的欣赏和描写从中获得心灵和审美的愉悦。但是到了杨万里这里,他不再以物、我两分的方式来看待万物。在他的眼里,自然界的万物不再是简单的作为客体的事物,他们与人一样拥有自己的灵性生命,尤其是,当诗人运用一种“大我”的视野来看待万物时,这一遍布于宇宙天地间的“生生之仁”便成为了连接人与万物的纽带,使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终而成为浑然一体的生命整体,正如张瑞君在《杨万里评传》中所指出的“杨万里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用新的思维方式建立一种自我与自然的新关系……这种新思维认为外物与人心可以相通”[11](P112),“杨万里把万物视为亲友,直接进行交流对话,注入满腔情爱,融自己于万物之中,同时在对外物的观照中表现自我的性格。”[11](P113)因而,我们会发现杨万里的山水诗总是频繁地出现诗人自己的身影,在他的诗歌中,自然万物与诗人之间总是充满了亲切的互动。将自然万物看作是能够感觉到“痛痒”的像人一样的生命性存在,这不得不说是杨万里从程颢那里得到的重要启示,因而,他的诗中比比皆是的对这些常见以致于不起眼的自然现象如此丰富多彩而又富有新意的描绘,就显然不只是对“拟人化”手法的简单运用,更是其思想中“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一观念在深层次上的展现。
从以上“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一角度再来重新理解杨万里诗歌的“活法”,我们也会得出进一步的看法。“活法”诗学作为一种诗学理论最早由吕本中提出,主要为了解决江西诗派后学过分拘泥于法度而不知变通的问题,他在黄庭坚所提出的“不烦绳削而自合”的理想诗歌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活法”诗学,追求一种对法度的超越,达到对法度的灵活运用,以求诗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杨万里作为出入江西诗派的南宋大家,自然对江西诗学也有深入研究,并且在其《诚斋诗话》中对江西诗学的法度理论也多有继承,并且被刘克庄认为是真正体现了吕本中“活法”诗学的诗人,“后来诚斋出,真得所谓活法,所谓流转圆美如弹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见耳”[12](P108)。但是我们仔细品读杨万里的诗歌就会发现,他的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活法”显然不仅仅停留在诗歌法度层面的圆融流转,而更具有诗歌本体论上的创变,也就是清代赵翼所指出的“诗意”的创新,而其诗意创新的内涵,其核心则表现为上文所论述的对传统物、我关系的超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诗歌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重大突破。其诗歌之所展现出一种“活”,正在于他所要表现的是具有“活”的特质的灵性生命以及人与万物这两种灵性生命之间充满情感的交流,因而,表现的内容的“活”就必然决定其表现方式也必须出之以“活”,由此形成杨万里诗歌表里如一的“活法”特质。
三、“吾与点也”之意与杨万里诗歌中的“乐”
杨万里的诗歌不仅将天地万物盎然的生意充分展现在人们眼前,还处处流露出一种“乐”意。杨万里诗歌中洋溢着的这种发自肺腑的自得之乐,其实包含着三个重要的层面:
首先,用“观天地生物气象”的眼光去体察那蕴藏于天地万物之间随处可见的盎然生意,由此,也将诗人自身作为天地万物一员的那份生命力重新激发出来,诗人也从万物的生意盎然之中体会到了自身所蕴藏的深厚的生命活力,在生命力的互相激发以及自身生命力的重新焕发之中,自然会感到由衷的喜悦和快乐在:
《南溪早春》
还家五度见春容,长被春容恼病翁。
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末梢红。
卷帘亭馆酣酣日,放杖溪山款款风。
更入新年足新雨,去年未当好时丰。[6](P689)
诗人年事已高,更被病痛困扰,但在灿烂的春光面前,诗人仍然重新体会到了那种生命力盎然的状态,仿佛自身的衰老与病痛在这新鲜的春光面前也变得生机焕然,不再有衰颓之感,而是倍感身心愉悦,重新收获了一份来自于春天的快乐。春季虽然万物欣欣向荣,却也是最容易引起诗人感伤的季节,所谓“伤春悲秋”,正是传统诗文的一个重要主题。自然界的万物能够在年年的春季重新迎回崭新的生命,其生命的旅程因为四节的轮回不会有真正的结束,但是人的生命却只能直线地走向衰老,而面对衰老和病痛,春季的万物复苏无疑是容易引起人的感慨和惆怅的,但是在同样被疾病与衰颓缠扰的杨万里看来,春容固然恼人,却又何尝不是重新激发起人的生命力呢?万物复苏并勃然绽放的生命力仿佛也给诗人已经不那么完满的生命重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使诗人感受到生命力的重新焕发。
二是因为诗人将自然万物看作与自己互为一体的生命整体,在这种“浑然与物同体”的浑融无碍的境界中,诗人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洒落,仿佛天地间不再有什么阻碍和隔阂,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与诗人之间都是一种可以互相交流沟通,互相有情的状态。因此,诗人在与天地万物相处时就像与自己的四肢手足相处一样,毫无滞碍,潇洒自然,自然会感受到一种非常自由畅快的快乐之情。正如程颢所说“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放身在天地万物中一般或一例看,这实际上是要求:作为一个生物种类,人应该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想法;作为一个个体,人应当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而一旦放弃了这些中心倾向,人就不会再感到他物与自己对立,也就不必再费尽心思去对付这些东西,如此则全身轻松、快乐异常。”[13]如:
《泊平江百花洲》
吴中好处是苏州,却为王程得胜游。
半世三江五湖棹,十年四泊百花洲。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6](P514)
在通常容易引起诗人们感伤的宦游漂泊之中,杨万里却写出了一种不同流俗的潇洒与愉悦,“半世三江五湖棹,十年四泊百花洲”,诗人似乎并不以此为累,反以此为乐,颇有一种自豪的心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诗人所到之处不仅美景众多,更因为这些美景对诗人充满情谊,与诗人早已是一种老友的关系,不论是杨柳还是云山都对诗人依依不舍、苦苦相留。这使得在宦游漂泊之中的诗人一扫孤寂无依之感,而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找到了自身的依傍,在“与物无对”的状态中,漂泊宦游不仅没有成为诗人孤寂感的来源,反而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潇洒与自由,“乐”意也就油然而生。
三是来源于诗人对“仁者”情怀的体察。前面提到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及“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些问题,其实都指出了一点,就是当人能体认到自己与万物是浑然一体,个人便超越了作为个体的小我,而成为与万物息息相通,“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我”或者说达到了“至仁”的境界。这个“大我”贯通着天理所蕴涵的“生生之仁”,与天理一样以化生万物,使万物在这生意之中自得自适,获得各自生命力的舒展与实现为最大的“善”和最大的“乐”,因而,万物生命力的自由舒展和充分实现,在诗人眼里就是对这种“大我”所代表的“生生之仁”的最好体现,是“大我”最大的快乐,
《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P124)
对于小池周边一系列可爱的小小景致,诗人充满了融融的爱意,从其描写的笔触,就可以感受到诗人充满柔情的目光。诗人关心着这些自然界中无人在意的小小生灵们,在它们虽然细小却自由自适的生命情态之中感受到一种由“万物之生意”而引发的“仁者”之乐,正如朱良志所说“能在‘生意’之物中亲证‘仁’的道德境界”[14]。
“乐”是儒家哲学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宋代理学家对“乐”的境界也非常重视,并且对其内涵作了进一步阐发和扩展。程颢云:“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1](P59)所谓“吾与点也”,就是曾点在孔子让学生们各言其志的时候所说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5](P474)(《论语·先进篇》)的人生理想。曾点所形容的这种人生理想其实是一种人生境界,在这样的人生境界之中,能够体会到一种融入自然万物之中,胸中无事、洒落自然的精神愉悦,程颢所说的“有‘吾与点也’之意”,正是在受到周敦颐的启发之后对这种与万物融为一体从而感受到的自然无碍的精神愉悦的一种体察,正如他对曾点之志的解读“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此勇于义者。观其志,岂可以势利拘之哉?盖亚于浴沂者也。颜渊‘愿无伐善,无施劳’,此仁矣,然尚未免过于有为,盖滞迹于此,不得不尔也。”[1](P107)子路和颜渊的志向非不高远,只是与曾点比起来,却不免显得过于滞于行迹了,至少在程颢看来,少了一种儒者的洒落与从容,“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谓狂矣,子路等所见者小”,这里的“狂”其实不失为一种赞美,直接将其与圣人之气象联系起来,表示了高度的认同,因为,在程颢的眼里,圣人气象是拥有能够囊括整个天地万物的胸襟气度的,子路、颜渊所着眼的毕竟还只是人事的层面,这与程颢所追求的“至仁”的境界相比则不免显得狭隘了。程颢自己常为人所提及的两首诗作所表达的也正是这一层意思:
《秋日偶成二首》: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1](P482)
《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
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1](P476)
在“静观万物”之中却展现出一种雄豪之气,显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欣赏风景这么简单,而是在这“静观”之中,通过“风云变态”来体察能“通天地有形外”的“道”,也就是“天理”。正因所体察到的实质如此不同,才会有“旁人不识予心乐”之误会,而旁人所不识之“乐”其实是他在“望花随柳”之中所收获的足以使其“富贵不淫贫贱乐”的圣贤境界以及“四时佳兴与人同”的万物一体之境界。
处于“与物同体”的境界之中,便能够充分体会到万物内在的充满的生命活力,并且因为处于这种“大我”境界中的人灌注了来自于天理的“生生之仁”的精神,因而,万物之生意盎然并在这种盎然生意之中各适其性,生命获得自由舒展和完满实现就是这种“大我”境界之中的人最大的愿望,也是其最大的愉悦。正如程颢所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1](P59)这正是对“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进一步阐释,当人真的进入了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时,他所感受到的是万物活泼泼的生意,是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所,处于它本真状态下的生意盎然,与之融为一体的人由此也感受到自我生命力的空前自由和广阔,并为万物生命力的自适自得而感到由衷的喜悦。杨万里诗歌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生机活力便是他在与万物同体的境界中感受到的万物各适其性的活泼生意,而在这生意盎然的诗歌世界中所处处流露出来的“乐”即来自于对天地万物生命力自由舒展以及诗人由此而感受到的自我生命所获得的洒落和自由所带来的欣喜之情。
[1](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魏)王弼注.周易正义[M].(唐)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清)黄宗羲原著.宋元学案[M].全祖望补修.北京:中华书局,1982.
[5]王新春.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J].周易研究,2006,(6).
[6](宋)杨万里著.杨万里诗文集[M].王琦珍整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7]黄宝华.从“透脱”看诚斋诗学的理学义蕴[J].文学遗产,2008,(4).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9]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付长珍.试论程颢境界进路中的直觉性特征[J].上海大学学报,2008,(4).
[11]张瑞君.杨万里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湛之.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4.
[13]方旭东.他人的痛——对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沉思[J].学术月刊,2005,(2).
[14]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15](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M].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