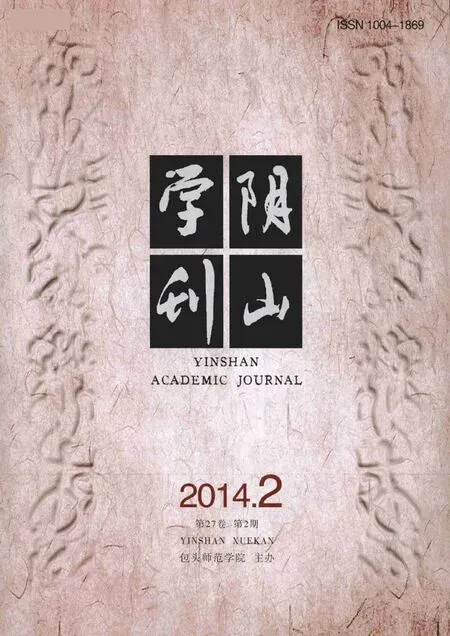试析土默特文化对北方民族多元文化传承的历史作用
王 泽 民
(右玉县文联,山西 朔州 037200)
土默特,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特殊的历史文化系统。土默特文化,是以土默特部文化为基础并融入了汉、藏、满、回等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研究土默特文化,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内涵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土默特文化具有丰富的包容性,它不仅具有一般文化的社会属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它是历经北方各民族的艰辛开拓、传承积蓄和不断创造而形成的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地域性文化。开展土默特文化研究,推动土默特文化发展,是我们应该担当的历史重任。
近几年,土默特文化已经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丰硕研究成果,把土默特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土默特文化的内涵、类型、特征和基本精神,挖掘了土默特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揭示了土默特文化在北方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土默特文化是北方民族文化建设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精神资源,这对于土默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在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游牧民族在土默特地区成长壮大,他们与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尽管这些游牧民族由于种种原因相互嬗递比较频繁,有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与其他民族互融,但他们各具特色的历史足迹却深深地镶嵌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春秋战国时期前后,活动在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一般被称为“胡”,史书中有代表性的是林胡和楼烦。他们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是今天的土默特地区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等地。赵国在武灵王统治时期,势力范围达到今呼和浩特一带。赵武灵王在原阳设置“骑邑”,学习林胡、楼烦的骑射技术,增强了军队的实战能力。史学界以“胡服骑射”来赞誉赵武灵王向林胡、楼烦学习的进步举措。骑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能力,使赵国在云中一带的统治日益巩固,林胡、楼烦被迫西迁。
进入秦汉时期,匈奴人成为活动在今天土默特地区的一个强大的民族,河套、阴山一带是其发祥地。战国时代的燕、赵、秦政权的边界都与匈奴人活动的地区相邻。秦灭六国以后,曾派大将蒙恬与匈奴大战于北边,“悉收河南地”,修筑了几十座城池并派兵戍守;又修九原至云阳的直道,加强对匈奴的防备。
匈奴人频繁地、大规模地出入和进驻今天的土默特地区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内容。一般来讲,成百上千甚至几千骑进入云中(今托克托县)、定襄(今和林格尔县)、雁门(今右玉县)的情况甚多,较大规模的可达3万骑左右。所以,在匈奴与中原的关系中,这一地区显得十分重要。直到公元前33年的“昭君出塞”以及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的和亲,则表明了相当一部分匈奴人强烈的和平愿望,50年以后,双方基本处于无战事状态,友好交往成为主流。民族关系的融洽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最明显的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诸领域相互交流的机会增多,历史呈现多元化发展也就成为必然。
东汉后期,北方各地战乱不已。南匈奴的许多人口被迁入今山西省境内,对今天土默特地区古代历史的影响减弱。随着曹魏政权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的乔迁以及南匈奴的内徙,鲜卑人取代匈奴人成为在这一地区历史上又一个影响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5世纪,敕勒人居此,人称敕勒川。蒙古土默特部勃兴,此间又以土默川著称于世。16世纪土默特部的领地,以土默川为中心,西至乌拉山前后,东达宣化以北一带。鼎盛时期,其领地甚至扩展到青海一带。17世纪中叶以后直至1949年,土默特两翼辖境为通常所谓的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包头七县及归绥地区。
土默特地区向称富庶。先前畜牧业发达,马驼牛羊繁殖每以数十万计,后来,牧场垦为农田,农产品又为大宗。自然资源丰富,地下蕴藏极富开发前景,地上动植物及水利、气候资源亦颇为可观。全境山水掩映,景观甚佳。
14世纪以前,汉、回等族曾在土默特地区生息。到16世纪中叶,内地汉族农民相继徙来,人数达5万至10万,土默川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农业和手工业。入清以来,随着清廷对土默特牧场的开垦,汉族人大批迁来,同时也有部分回族人定居于此,本地区遂形成蒙、汉、回、满等各民族杂居局面。与土默特地区相邻的杀虎口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土默特地区的历代各民族正是通过这一地带南下中原,这个地区又是他们的重要基地和后方,这不但推动了北方文化的发展,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剧烈变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南北民族间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社会习俗、观念形态、宗教信仰等各个领域的全面交往与交流,从而使这个地区得以成为中国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也就是说,在民族大融合,社会大转轨的时期,北方草原民族不仅带来了极富生气、极其活跃的文化品格,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活力与生命,而且更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民族文化和各种信息,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更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拓跋鲜卑改革旧俗,倡导汉文化,积极仿制和推行中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土默特首领俺答汗在隆庆年间被明王朝册封为顺义王,其妾三娘子被明廷封为忠顺夫人,先后为黄台吉、扯力克收继,历事三王,左右土默特政局达40年。《明史》卷327《鞑靼传》称,三娘子佐历代顺义王主贡时,“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三娘子为蒙汉友好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
明隆庆年间,杀虎口便是通贡互市之要地。“大同方面,后来增设守口堡马市,以待原与黄台吉同在新平堡互市的兀慎、摆腰诸部。又在助马堡、保安堡、宁虏堡、杀胡堡、云石堡、迎恩堡、灭胡堡等处设小市场。”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3《险隘考》、杨时宁《三镇图说》,玄览堂丛书本)[1](P332)清代时,杀虎口又成为朝贡、商贸、移民、税关之要道。随着清政府对内蒙古地区移民政策的转变,那些长期饱受灾荒、重税之苦的山西人,尤其是晋西北地区的流民,开始纷纷涌向边关险塞,徙居口外长城以北土默特地区,从事农耕和行商活动,这种特殊的人口迁移现象,从清朝前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近三个世纪。杀虎口作为“直北之要冲”自然成为移民运动的重要口岸,山西移民,尤其是晋西北的移民主力军便穿越此口,浩浩荡荡地奔赴土地肥沃的土默特地区,也有人把这一社会现象称为“走西口”。在“走西口”移民运动中,晋蒙两地在文化上出现的大碰撞、大交流,发生了明显的吸收融合与共铸新质现象。以《走西口》为代表的民歌圈的生成和“二人台”戏曲的出现,就是这种融合共铸的重要成果。
从杀虎口“吉盛堂”发展成为称雄塞外的巨商“大盛魁”,二百余年频繁往来草原与内地之间,杀虎口作为连接草原和内地的纽带,自然成为晋商旅蒙的主要渠道。有清一代长达300年之久,土默特地区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经过长期互通有无贸易往来,带动了游牧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二
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生活在土默特地区的各民族从不自我封闭、固步不前,而是在游牧和农耕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铸就了该地区民族开放的心态、豪放的性格和进取的精神。他们以开放豁达的心态互相弥补各自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各民族之间不断进行全面的、多领域的、大规模的联系与交往。而且这种联系和交往在特点、方式、机遇等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指向性和内聚性。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格局从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北方民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格局。
由于游牧地区缺少对自身经济产品转化的机制,维系自身生命的某些产品必须从中原农耕地区获得,这就演化为对外产品的交换、军事的对抗甚至文化的碰撞是游牧地区人民繁衍发展的必然。明王朝在隆庆五年(1571年)与俺答汗达成和议,恢复通贡关系,并在大同得胜堡和大同右卫杀胡(虎)堡开设边贸互市场所。边贸互市场所使蒙汉人民的生活、生产有了相应的改善和提高,尤其是通过相互交往增进了民族间的友谊。明正德以来在一段时间内,明朝统治者同蒙古封建主的关系日趋紧张,统治阶级彼此敌视,封禁、攻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关系,致使民族矛盾一度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蒙汉劳动人民仍然相互友好往来,说明蒙汉人民之间的友谊,以及彼此间的历时久远的经济联系,绝不是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墩哨军丁为避免摩擦“全不坐哨”,民族间的摩擦少了,和平与友好往来必然就成为当时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同样,蒙古族进入长城,也渐渐由攻掠转向“与我买卖”,寻求以贸易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在边贸市场的影响下,边镇一些高级军官“希求苟安”,遂以布缎等物“买和”,[2](《禁通虏酌边哨以惩夙玩疏》)甚至结交蒙古族的首领。如隆庆四年(1570年)大同参将杨缙就以红布、梭布六百匹及改机缎、水獭皮等物送俺答求和,同时以梭布二百匹赎回十余名被掳人口。[3](《俺答列传中》)就是向以敢战著称的周尚文也不能逆转这种希望和平的趋势,他在嘉靖中期任大同总兵时,也不免“私使其部与虏市”[3](《俺答列传上》),在明廷屡次拒绝俺答求贡,俺答每次兴兵南下的情况下,他藉此同俺答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俺答封贡后宣大等七镇皆开马市。这次马市除官市外,还增设民市、小市,听任商民军兵与牧民交易,私市贸易终于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从隆庆五年起,民间贸易一直没有间断,持续了几十年之久,这是明代蒙汉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通过私市贸易,蒙汉人民间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故当沿边人民的反抗遭到失败后,他们便纷纷逃往塞外,“北走俺答诸部”[4](《俺答封贡》)。此外,由于生活无着,或不堪压榨而零星逃出边塞的农民,为数更多。对于这些逃来塞外求生路的汉族,蒙古族尽可能地予以救助,依照当时蒙古社会实行的一种赡养法,即“有穷夷来投,别夷来降,此部中人必给以牛羊牧之,至于孳生已广,其人已富,则还其所给”[5](《牧养》)。据有关资料记载,来自内地的一些汉族人沿大小黑河,“开良田数千顷”,并建造了许多村庄。因汉人自称百姓,蒙古人也以此称呼他们,译写谐音作“板升”。汉族聚居的村庄,也随之被称为板升。在蒙、汉人民共同努力下,土默川的农业迅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促使蒙古封建主进一步改变他们的政策。原来在蒙古封建主同明朝的战争中,从内地俘获了许多汉人。这些人多数沦为牧奴,“男子放牧、挑水、打柴,妇女揉皮、挤奶”[2]王崇古《核功实更赏格以开归民向化疏》。
当土默川的开发具有一定规模,蒙汉关系有了改善,俺答便适时地采取一些措施,把一部分被掠被俘而沦为牧奴的汉人,从家庭奴隶的地位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参加到农业生产中去。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俺答开始从汉人牧奴中择选儒生,给以自由民身份,使他们参加垦殖。以后,俺答又进一步从被俘为奴的汉人中,将“有智勇艺能之人”解脱出来,“令之管事”[5](《听讼》)。至于有些“艺能”的人,还被封作达儿汉,如丰州川著名的三十二板升的首领中,就有“东打儿汉”、“打儿汉”等。从畜牧业家庭奴隶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汉人为数不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对蒙汉共同建设家园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农业大规模的发展,这个地区手工业也有了可喜的进步。在逃亡草地汉人中,有一些工匠是极其宝贵的手工艺人,蒙古族对他们颇为器重。随同丘富来到草地的丘仝,是位“习梓人艺”的木匠。他一来便施展了才干,为俺答“造起楼房三区”,又造船,还制作了不少农耕器具,因而被俺答倚为亲信。随同吕老祖(即吕鹤)来的弓匠贺彦英,一次就为俺答“治弓数十张”,[3](《俺答列传中》)受到青睐。
在板升首领中,也有许多名噪一时的工匠,如“王绣匠”、“杨木匠”、“土骨赤”(即铁匠)等等。这些工匠,在土默川“造室力农”、“筑城建墩”中大显身手,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他们将汉族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带进草地,所以蒙古族的手工业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求贡时送给明朝的贡品中,手工艺品就有“金银锅各一口”,至隆庆四年俺答封贡时,贡品中则有镀银鞍辔、镀金撒袋(即箭囊)。
在农业手工业得到发展的基础上,营造规模较大的城池的条件日臻成熟。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板升汉人在赵全等带领下,于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村附近,建造了范围约十里的“大板升城”。第二年,他们“采大木十围以上”,又在城内建了七重宫殿和三重仓房,修建五重城楼。该城的修建,标志着土默川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水平又有了显著的提高。
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促进畜牧经济的发展。嘉靖初当俺答驻牧开平一带时,他们尚处于“最贫”的境地,拥有的牲畜数量很少。而到嘉靖末,俺答部已拥有“马四十万,驼牛羊百万”[3](《俺答列传上》)。这个巨大的变化,除畜牧经济本身的发展外,应主要归结于对土默川的全面开发和建设,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对畜牧业所起的促进作用。俺答封贡时,王崇古曾说过,“今板升农业,亦虏中食物所资”[6](王崇古《散逆党说》),这里数万汉人所生产的谷物,除自己食用外,基本上也能满足数万蒙古牧民的需要。这个地区所存在的严重食物不足的社会问题,至此基本得到了解决。这对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另外,板升汉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普遍经营畜牧业,饲养了大量牲畜,如赵全的板升就拥有数万马牛,对发展土默川畜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蒙汉人民共同开发与建设土默川的过程中,蒙汉人民在文化、语言乃至生活习俗上日益接近,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已经越来越大。在土默特地区汉人中,使用蒙古族语言的人非常普遍,有些还会书写蒙古文字,如李自馨、周元和王孟秋等人就不仅会说蒙语也会写蒙文。在汉族文化影响下,一些牧民也由游牧转向定居,逐渐学会从事农业生产,在土默川板升中就有“夷二千余人”。[3](《俺答列传下》)
在板升的汉人中,起蒙古名字的也不足为奇,如汉族人赵龙在塞外生了几个小孩,起了蒙古名字火泥计、窝兔等。到了万历年间,板升地方的汉族人也被明朝官员统称作“夷人”,与蒙古族不加区别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兵科给事中陈亮条陈说,“板升夷人,众至十万,宜令通事及亲识者密谕得意,许其率所部来降,照宣抚宣慰事例授以世官。”[7](卷一四一)由于长期居住在板升的很多汉族人语言和生活习惯均与蒙古人相同,所以也就成了“夷人”。因为板升的汉族人已经渐渐融合于蒙古族,他们也一扫“思乡归正”,*郑洛《慎招纳》曰:“议款之初,华人被虏,家有父母妻子,思乡归正者其人固多”。反变成了明廷宣抚宣慰的对象。蒙古民族恳切期望同中原地区友好相处,通过俺答一再向明朝请求通贡,这种恳切的心情已经强烈地表现出来。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俺答向明朝提出入贡以来,在十七年中俺答又十余次提出类似的要求。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遣石天爵等通贡,申明“北部素通中国,进贡不绝,后因小失乖异。今愿入贡献马驼,贡道通则两不猜忌,中国可出二边垦田,北部自于碛外畜牧,请饮血为盟”[8](卷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俺答又向明朝进一步提出“请为外臣,朝请瓯脱,给耕具食力”[9](冯时可《俺答前志》)的要求。为顺利实现上述要求,俺答曾告诫诸部:“若等过塞上,敢犯塞上秋毫者,听若等夺其穹庐及马牛羊”[3](《俺答列传上》),严禁属部攻扰明边。嘉靖期间,俺答为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是作过积极努力的。他的通贡主张和行动,不仅代表着蒙古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中原汉族人民来说,也利害攸关,故广大边民深表赞同。
蒙汉人民共同对土默川的开发与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贫困面貌,但生活中所需的布缎、铁器及农耕器具,仍是塞外无法解决的。长期以来塞外的困难,正如俺答在贡表中所说的,“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缎布难得。每次因奸人赵全等诱引,入边作歹,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10]。
隆庆年间,方逢时、王崇古先后调任大同巡抚和宣大总督,他们一到任所,就尽量撤去大边的墩军,严饬诸将不得擅自出兵,要求各边要遍插红旗招纳降者,这一变化为蒙汉民族友好开创了广阔的前景。无论俺答,还是明朝,都在伺机行事。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俺答的爱孙把汉那吉携妻子及奶公阿力哥等,投奔大同败胡堡这一事件立即成为双方改善关系的契机。
把汉那吉是因内讧出走的。他所以投奔明朝,也是受了招降的影响。把汉那吉一行受到边关的热情接待,方逢时对他们厚加宴赏,并妥善安置在大同城馆驿内。方逢时想趁此时机,与俺答和好,开放马市。方逢时在九月底给王崇古的信说:“两据平边中路探报,俺答走了此孙,刻期聚兵来抢左右卫地方,索要孙儿,其言甚真。而刘廷玉所报要甚么即与甚么之说不虚。则弟昨所言与之为市之计,似有可行,惟在公主张,选择得人行之。”[11](《与王军门论降夷书》)明朝以诚相待,使俺答深受感动。明廷于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封俺答为顺义王,受到明廷封授的俺答所部大小酋长共63名,都颁给敕书。五月二十一日,在大同得胜堡外蒙汉聚集一堂举行了隆重的封授典礼。至此明朝与俺答间的封贡关系顺利实现。
由于政治上的统一,俺答、三娘子和历代顺义王,同历任宣大总督王崇古、方逢时、吴兑、郑洛等,都保持了十分友好的情谊。三娘子深明大义,先后辅佐三代顺义王与明朝友好相处。她三十余年致力维护民族友好关系,因此深受蒙汉人民的爱戴。
三
土默特文化是蒙汉民族长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生存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地域文化。正如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12](P85)。土默特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文化、精神方面的文化还是行为方面的文化,既有多样性又有活跃性;无论是在生产中的交通用具还是日常生活里的饮食习俗,既有浪漫色调又有实用价值;无论是文学力作还是艺术精品,既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又有对英雄人物的赞美和讴歌。诸如流行于晋蒙陕冀的二人台,是集歌舞、曲艺、戏曲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它是伴随晋陕冀人民走西口到塞外谋生的移民史而形成的,是历经悠悠岁月的时空磨砺,历经热爱它的芸芸百姓千锤百炼发展而成的综合性民间艺术。
在这些艺术表演形式中,既有汉族的民歌、曲艺、舞蹈、丝竹乐、戏曲等成分,也有蒙古族音乐成分,如唱腔《海莲花》、《阿拉奔花》、《四季花》、《盼五更》、《小牧牛》、《栽柳树》等,牌子曲《森吉德玛》、《四公主》、《巴音杭盖》等就是其中的例子。歌唱和道白就用蒙汉两种语言混合起来表演。如《亲家翁相会》的表演中,台词里就有:
玛奈(蒙语,“我的”意思)到了塔奈(蒙语,“您”的意思)家,黄油烙饼奶子茶。正赶上塔奈念经“巴雅尔拉”(蒙语,“喜庆”的意思)!中午饭更排场,玛奈安在首座上,众人敬酒我紧喝,放下筷子吃“五叉”(蒙古族最好的宴席食品,又称“羊背子”)。你看玛奈多喜色?/塔奈到了玛奈家,正遇玛奈不在家。玛奈的脑亥(蒙语,“狗”的意思)咬塔奈,塔奈掏出大烟袋,狠狠地打了它的“讨劳盖”(蒙语,“头”的意思)。
在塞外土默川上,蒙汉通婚,结成儿女亲家,因为言语互相不通,亲家们很少来往。《亲家翁相遇》反映的故事情节,主要描述汉族亲家翁向蒙族亲家翁道出没有很好款待他的话。再如蒙古族民间艺人老双羊在演唱走西口时,其蒙汉语混合道白:
从家出口外,盲目来到妥妥岱(托克托县),面向青山往北迈,走五申,过陕盖,胡游乱闯到大岱。道路生,紧问讯,晚上住在大板升。蒙老乡,真厚诚,莫把咱们当外人,滚奶茶,吃肉粥,暖炕睡得热呼呼。进了土默川,不愁吃与穿。乌拉(蒙语“山”的意思)高,岗勒(蒙语是“河川”的意思)湾,海海漫漫的米粮川。牛羊肥,庄稼宽,逃难人见了心喜欢。
一走走到山湖湾,碰见两个鞑老板(是指蒙民老妇人),她们说话我不懂,只好比划问安宁。有水请你给一碗,我要解渴把路赶,塔奈(蒙语“您”的意思)勿圪(蒙语“话”的意思)米德贵(蒙语“不知道”的意思)“忽尔登雅步”(蒙语是“快走”的意思)指向西,手指口渴嗓子干,她却给了一碗酸酪旦(蒙民制成的乳制品——干酪)。
流传在土默川一带的山曲民歌也吸收了“脑包”(蒙古语,即隆起的高地)、“灰塌二胡”(蒙古语,冷落凄凉的意思)、“哈苜尔”(蒙古语,即白圪针)等蒙古族惯用语,如“山药皮皮盖脑包,谁给俺们管媒天火烧”;“远远瞭见他家的门,灰塌二胡死下个人”;“哈蟆口炉炉烧哈苜尔,活到哪影儿算哪影儿”;“哥哥走在那些高山疙瘩瘩唰哩唰朗割莜麦,妹妹走在那些半山坡坡蛤蟆蟆戒指指珊红珠珠银手镯镯唰铃铃唰啦啦刨山药”。后句里的“蛤蟆戒指”、“珊红珠珠”、“银手镯镯”及象声词实际上是对塞外妇女首饰特征的生动描绘。“十月里狐子冰滩上卧,扔下了妹妹无人理”;“你走在口外只管了你,提起你走口外我心难过”;“人家回来你不回,你在那口外刮野鬼”;“西包头红火人又多,顾了你红火忘了我”;“大青山山上卧白云,难活不过人想人”;“上畔畔葫芦下畔畔瓜,娶下了媳妇守不成家”;“你在东来我走西,天河水隔两头起”;“万般出在无其奈,扔下小妹妹走口外”。[13](P344~394)民歌、二人台这种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流传在土默川这个蒙汉杂居地区,起了蒙汉文化交流的作用。为扩大与中原地区联系,进一步促进蒙汉文化交流,草原民族还非常注重医学、建筑、音乐、舞蹈、剪纸、绘画、工艺美术、礼仪祭祀、时令节日、民俗风情、天文历法等,而且成果卓著。
土默特地区是历史上中原农耕经济文化与塞外游牧经济文化交流、交融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有了进一步联系、碰撞、融汇、贯通,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形成以贸易交往为纽带的密切关系。在客观上起到了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之间理解和团结的作用,进而增强了北方兄弟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凝聚力。
旅蒙商在将中原的茶叶、粮食、布匹等输入蒙古各地的同时,还把草原上的土特产品运到中原各地,从而为中原各地农耕、运输业提供大量畜力,为军事用途提供了畜力,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另外,旅蒙商在走屯串营流动贸易时,还把中原的中草药和针炙等医药知识,带往缺医少药的蒙古草原,他们在与蒙古牧民做买卖的同时,遇到蒙古人生病和牲畜疾疫时,还用针炙、中药为牧民治疗一些常见病,为病畜提供医疗,这样不仅有利于人畜的健康保护,同时也加深了蒙汉民族间的感情沟通。商贩还将中原地区的书籍带到草原牧区,传播了中原文化。同时,旅蒙商为便于与蒙古人做生意,必须不断学习蒙语和蒙古文字,通晓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学习了与畜牧业有关的经验和技术,然后又带回内地交流,从而促进蒙、汉诸民族之间文化、经济交流发展。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委派兵部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开始了大规模官办垦务。贻谷坐镇归绥,设立办理河东河西十二台站土地垦务的杀虎口台站地垦务总局、分局和垦务公司等机关,逐步清丈放垦了察哈尔八旗和归化土默特旗的土地。杀虎口台站地垦务总局的设立,不但使土默特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引起了放垦区的蒙古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随着放垦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许多蒙古族人民逐渐放弃以牧为主的经营方式,转向以农业为主或半农半牧的生产经营方式。蒙汉族人民在共同的生产劳动中,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高了农牧业生产的技能。在蒙汉杂居地区多种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改变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在居住方面,出现了土木结构的蒙古包和汉式平房;在饮食方面,多以谷物蔬菜为主,辅以肉食与乳制品,并逐渐习惯饮红茶,喝粮食酒;在服饰方面,逐渐吸收当地汉族农民的习惯,开始穿布鞋、布衫,甚至连以前最讲究的发式也不大讲究了。
放垦区蒙古族人民生活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古族人民风俗习惯的变化。首先是节日与祭祀的变化,放垦前的蒙古族人民有祭天、祭风、祭雨、祭雷、祭神、祭星、祭火、祭敖包等祭礼。放垦后接受了汉族人民的习惯,祭龙王、祭土地庙、祭孔庙、过端午节、中秋节、小孩过生日、老人过六十大寿、过年时贴门神、供财神等;其次就是婚姻制度的变化,放垦前的蒙古族人民一般在同族之间远娶远嫁,不能与其他民族通婚。放垦后的蒙古族人民打破了民族界限,蒙汉通婚的家庭开始出现了。此外,在丧葬礼仪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风葬、树葬、天葬,改变为土葬”[14]。
杀虎口台站地垦务总局的设立,尽管解决了大批汉族饥民的生计问题,也方便了蒙古牧民的粮食供应,但是,台站地的放垦也付出了很高的生态成本,带来严重的生态后果。由于大面积的放垦开荒,导致整个土默特地区生态系统的失调:水土流失面积逐年增加,降雨量普遍减少,各种自然灾害周期缩短,灾情越来越严重,沙尘暴爆发的次数、强度以及袭击的范围有逐年上升和扩大之势。
文化的开放和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古往今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吸收从来没有停止过。保持完全“原汁原味”、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是发展不起来的,更无从去谈现代化。民族要发展,社会要发展,就必须与外界建立广泛的联系与交往,看到差距,明确历史方位,寻找与时代的契合点,这样的文化其内涵会更丰富,内容将更优秀,更加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更富有生命力,更易于被其他民族所接纳,文化整合能力更强,从而形成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对其他民族文化中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要努力学习、借鉴并吸收,从而建立健康合理的文化机制,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理性思维能力。
结 语
土默特文化是土默川地域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是北方民族文化宝库的瑰宝。其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是祖国文化的一颗璀灿的明珠。明清时期土默特地区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是蒙汉长期交往,两种文化融合之必然。该地区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有浓厚蒙古族特色,新型地域文化的形成,突出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汇聚,一体化发展的总趋势。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土默特文化对于人们充分了解和认识北方民族文化特色,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蒙汉民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创造文化的活动和过程其实是体现北方民族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的量变,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质变。文化继承也叫文化积累,通过对民族内部文化和外来优秀文化的积累,推动人类文化活动从有限向无限发展”[15](P11)。土默特文化是蒙汉民族的多元并存价值观在自然环境中的外化形式,在土默特文化生态体系中,土默特文化生态观创新发展的关键就是在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实现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创新。当前我们面临着多元并存的时代,要使土默特文化生态永远充满生机活力,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土默特文化生态价值观的创新理念。
[1]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崔九思.万历武功录[M].四库禁毁书丛刊表.
[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萧大亨.夷俗记[M].山东:齐鲁书社,1997.
[6]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三十七)[M].清(1644-1911)木活字印本.
[7]明神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王士奇.三云筹俎考[M].台北:台北广文书局,1963.
[9]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三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明)俺答.北狄顺义王俺答等臣贡表文[M].景明刊本.
[11]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12]大地的引力[A].巴·布林贝赫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3]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4]刘海源.内蒙古垦务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15]郑海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文化创新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