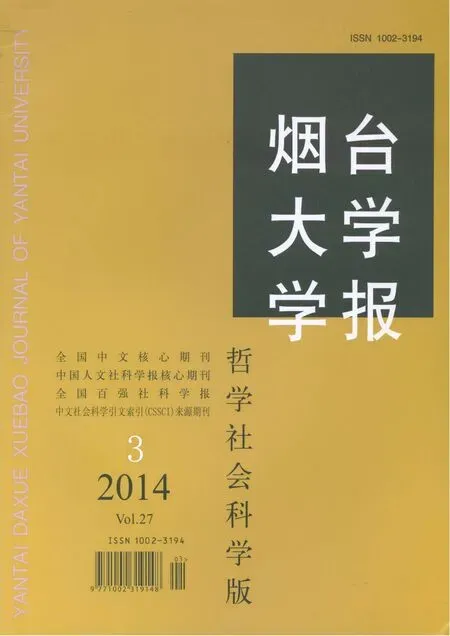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绞缬及其文化内涵
金少萍,王 璐
(1.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2.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绞缬及绞缬的各种名称
(一)何谓绞缬
绞缬是中国古代传统染色工艺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文献《一切经音义》中就有关于绞缬的记载,“以丝缚缯染之,解丝成文曰缬”。元代《韵会》中也有“缬,系也,谓系缯染成文也”①转引自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4页。的相关描述。两者所述之意均阐明了绞缬工艺就是利用捆扎等方式达到防染目的,进而在布帛上形成有色晕的纹样。此外,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对什么是绞缬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缬,撮采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色斑斓谓之缬。”②转引自罗钰、钟秋:《云南物质文化纺织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由此可见,上述关于绞缬的解释完全是基于绞缬工艺的制作流程,进而对绞缬技艺作出的概括和释义,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和概括了古代绞缬技艺的要点和技术特征。首先,古代的绞缬是一种纯手工技法,除了依靠简单的针和线之外,全凭手工制作。其次,绞缬也是一种特殊的防染技术,将纺织面料按照预先的设计,借助缝、扎、结等方式抽紧处理使染液不能完全渗透,以达到防染的目的,染色后除去线结呈现出独特的纹样。最后,唐代盛行的所谓“三缬”中,虽然绞缬、夹缬、蜡缬其原理相近,但却是手法完全不同的防染技艺。蜡缬是指以蜂蜡加热在织物上绘制图形以达到防染效果的技法,而夹缬是指运用两块相互对称的精致镂空花板用力夹住织物以达到防染效果的技法。而绞缬则是通过或缝、或捆、或扎以达到防染效果的技法,其缝扎技法因人而异,捆扎或松、或紧,针脚或长、或短都会影响纹样的成形和色晕,其独特性在于绞缬技法本身的不可复制性,这是绞缬区分于夹缬和蜡缬最为突出的特征。从考古实物资料中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由绞缬防染成花的技艺所形成的花纹一般比较简单,多半染成单色织物本色花的样式。绞缬也存在复杂的加工样式,主要是利用套染的技术呈现多彩纹样。再者,由于防染和染液渗润的效果,花纹表现为自然形成的色晕,图案则呈现出层次感。
《辞海》中也有关于绞缬的定义:“丝织品的染色方法之一,属于机械性防染法。将织品用缝、扎等方法加以绞结,保留其底色,染色后解去结子,即可出现几何形的花纹。最适于染制简单的点花或条格纹。我国民间很早发明,唐代宫廷广泛使用,花纹精美。”①《辞海》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3074页。《辞海》的释义也突出了绞缬防染技法的主要特点,显示出古代文献中关于绞缬名称的解释沿袭至今。
(二)绞缬的各种名称
历史上关于绞缬名称的记载很多,首先,绞缬也称“染缬”、“撮缬”、“撮晕缬”等。其中,染缬除了特指绞缬之外,还包括夹缬、蜡缬在内,是一种泛指。而其余的名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具体的工艺特征,如“撮”是绞缬工艺中较为典型的成花手法,丝绸或是布帛局部经过设计纹样,加以针缝抽紧成“撮”状,再施以线捆扎,最终染色后使其局部因为机械性防染作用不能够完全着色,形成预期的防白花纹,并在花纹周围呈现不同层次的色晕效果。因此,选取绞缬工艺不同阶段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绞缬名称,是各种绞缬名称的共通之处。
其次,除了当时民间或是文献中记载的普通称谓外,绞缬在诗歌中还存在不同的叫法。例如唐代诗人李贺的诗中有“醉缬抛红网”,②李贺:《恼公》,《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77页。这里的“醉缬”既是对绞缬色晕的描述,也是关于绞缬的一种雅称。此外,源于对绞缬起源的猜测,当时文献中也出现了“襭”和“撷”字近似作为“缬”字的使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一段话,“襭,以衣衽扱物谓之缬,从衣,颉声。”③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简本),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虽然在《说文解字》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于“缬”的释义,但单就“襭”的解释而言,与我们所说的“缬”是基本一致的,现在国内的多数学者也都认同缬应为此意。此外,在现代版的《说文解字》中,又增添了“襭,或从手”的解释。④许慎撰,徐铉校订,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现代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55页。据此有学者推论,绞缬可能正是因为古人据衣缝折角处的染色得到启示所产生的一种防染技术,⑤王予予:《中国古代绞缬工艺》,《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那么,此处的“缬”与“襭”“撷”是可以相互通用的。
最后,从制作流程与成花技术特点来看,绞缬也与现代“扎染”同出一脉。现代扎染在秉承古代绞缬技法的基础上,其制作手法更加丰富。在古代文献中多有“缬”、“绞缬”、“染缬”之说,并未出现“扎染”一词,可见扎染这一手工印染技法的名称并非古代已有的称谓,但可以肯定的是,扎染就是古代文献或考古资料中的“绞缬”技艺在现代的称谓。
(三)对绞缬名称的解读
缬字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作为古代防染印花织物的统称,前而加上定语则有绞缬、夹缬、蜡缬、灰缬诸多防染工艺;二是就缬字本义,实际上是指绞缬。
从广义上来说,所谓“缬”,意即斑斓之色彩,后来也泛指染色显花的织物和染色显花的方法。⑥余涛:《现代扎染艺术》,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可见,“缬”既是指防染印花的技法,又指防染印花织物之意,系古代丝绸防染印花织物的总称。此外,唐代就有“三缬”之名,绞缬与蜡缬及夹缬并举,统称为“染缬”,而绞缬、蜡缬、夹缬之分则是指不同的防染工艺。
从狭义上看,“缬”实际上特指“绞缬”。前文中提到的唐代《一切经音义》、元代《韵会》和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都有有关“缬”记述,这些文献中的“缬”在此特指绞缬。在绞缬技艺盛行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之时,“缬”特指绞缬的意义仍然被保留了下来,绞缬技艺传入日本之后,在《倭名类聚抄》卷12中有“缬,结帛为文彩也”的记载。另外,据日本学者的考证,在《法隆寺献物帐》中,古代染织物分别为夹缬、臈缬、缬三类,其中缬就是专指绞缬。①河上繁樹、藤井健三:《織りと染めの歴史·日本編》,东京:日本昭和堂,2004年,第23页。
在古代文献对于“缬”的描述中能够看出,通过结扎、捆绑丝绸染色的防染方式制作出的成品即为绞缬。虽然在这些文献中没有特别提到针具的使用,但毋庸置疑,明显呈现了线缝、打结、扎制的防染技法的运用,而线缝则是必须使用针具的。1959年阿斯塔纳304号墓出土的匣紫、绛紫两色“叠胜纹”绞缬绢裙上,每个防白色晕斑点的中心都有一个明显的针眼,是利用针具引线达到绞缬防染效果的极好证明。在胡三省的描绘中,我们也能够体味出“缬”专指绞缬时的染色特点,根据扎结部位的松紧不同,缬的成色深浅也不同。这种呈现多层次色彩效果的特征正是绞缬工艺自身所独有的,因此这里所说的缬应当指绞缬。
二、绞缬纹样的类别及名称
(一)绞缬纹样的类别
一方面,从古代文献、考古资料以及相关图像资料的记载看,古代的绞缬纹样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花的纹样,二是点状纹样,三是几何纹样。另一方面,就整个染缬技艺来说,其最终在织物上形成的图案有抽象与具象、规则与不规则之分。由于古代绞缬具有的工艺局限性,难以更多表现具象的图案,抽象图案就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绞缬纹样。古代绞缬形成的抽象图案可分为规则与不规则两类。花的纹样和点状纹样就属于抽象的不规则纹样,而几何纹样则属于抽象的规则纹样。
1.花的纹样
其一,在考古文物中出土实物较多的是四瓣花纹样,印有四瓣花纹样的绞缬绢一般被称作“朵花绞缬罗”。这种四瓣花纹样的典型即是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朵花绞缬罗,实物现藏于新疆博物馆。根据实物来看,被防染的四瓣花呈散点分布,应为纹罗织物原色防染,是接近白色的效果,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朵花已成米黄色偏浅褐色。就单个朵花而言,四瓣花呈十字型对称,而且每个朵花中央及每片花瓣的中央均有明显的浅棕色晕染线条。朵花的外轮廓近似正方形,其边长约为5cm左右,每个正方形的对角线恰好与织物的经线和纬线相互重合或平行。就这件朵花绞缬罗来说,其中一组花瓣只有浅褐色的晕染痕迹,相对另一组的形状色彩来说较为模糊和浅淡。而另外一组则在浅褐色的基础之上还施以浓重的蓝色,即最终表现为墨绿色花瓣中心聚染。这种四瓣花的形状和色彩的特点反映了织物折叠和双色套染的特征。相关实验表明,这种正方形四瓣墨绿地棕色晕染的团花,是先将纹罗地折叠绞扎成四瓣花型,入棕黄色染液染色,干后再次密扎原绞扎口,入蓝色染液套染而成。②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社,2001年,第87-88页。
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一件唐代“黄地甃纹绞缬”属于同类花式。织物通体被染为土黄色斜条格子,交叉点染作墨绿色,格中有朵花式缝绞法染花。③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8页。朵花的中间印染有明显的十字型,也是四边折叠在一起所形成的染色效果。
上述这两件古代藏品所展示的四瓣花纹均是绞缬工艺的展现,并且这种花纹属于抽象的,我们只能从中看出是朵花的纹样,但却说不出其具体的花样品种,这种绞缬的抽象性也是古代绞缬技艺所呈现花的纹样的一大特征。
其二,另外一种绞缬花的纹样类型即是在古籍图像资料中屡屡出现的团花纹样,这种团花纹样多以大圆圈纹出现,也存在少数花型稍微复杂的团花纹样,两者的花型都比较大。
对于前者,绞缬大圆圈纹往往与刺绣相结合,即先绞染出大圆圈的防白图案,再于防白处施以刺绣点缀,展现出整个团花的形态。而这种形式的大圆圈团花纹多出现在古籍图像资料的服饰运用上。如盛唐画家张萱绘制的《捣练图》中,一名手拿绢扇蹲在炭火旁煽火的宫女服饰,其裙身呈墨绿色地,均匀分布有花型较大的大圆圈防白,每个大圆圈纹的形状都是较为规则的椭圆形,单个椭圆形并没有明确的外围轮廓,墨绿地和防白的交界十分模糊,出现了颜色较淡的墨绿晕染,显然是绞缬所产生的染色效果。而大圆圈纹的内部则有一朵形状规则的淡褐色六瓣花,花瓣较为抽象,近似于云朵似的纹样,外围呈等腰三角形。花蕊也十分清晰,由八段相同的圆弧组成。由于绞缬大圆圈纹内部的团花十分清晰精致,瓣蕊分离,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大圆圈纹内部的团花极有可能是先绞染后施以刺绣所呈现的纹样效果。①杨建军:《扎染艺术设计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类别基本相同的大圆圈刺绣团花纹还出现在唐代周昉绘制的《簪花仕女图》中三名女供养人的开襟轻纱外衣上和山西汾阳圣母庙圣母殿北壁的《乐伎弹奏图》壁画中四名乐伎所着衣裙的衣袖及领口上。此外,这种与刺绣技法相结合的大圆圈团花纹样也可以与刺绣技术分离单独出现,仅显现绞缬的大圆圈纹,这种纹样是前一种纹样的变形,一些大圆圈纹中心还会出现绞缬染料的色晕斑点,呈现出朵花的姿态,这些也属于同一种类的大圆圈纹。如《韩熙载夜宴图》中坐榻上几名女子的开襟上衣、床围、帐幔和枕套上、《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一名身着淡青色地的女骑马者的上衣、敦煌莫高窟五代第98窟东壁北侧“回鹘公主供养像”中公主的长裙。对于这些古籍图像资料中的大圆圈团花纹的具体形态,笔者将在绞缬的功用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此外,前文提到花型较为复杂的另一种团花类型,这种类型的团花纹样既是不对称的,也是不规则的,并没有固定花瓣的数量或是整体形态,甚至是同一织物上的团花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捣练图》中有一名拽拉白色布料的宫女,其身着湖蓝色地的齐胸长裙,黄色团花纹样交错排列于长裙之上。每个团花纹并不比此图中的煽火宫女裙身的大圆圈团花纹明显,可能是直接使用黄色织物进行湖蓝色团花绞缬的结果,而前者可能是使用白色织物经过绞缬扎花,再浸入墨绿色染液中浸染而成。这些黄色团花的外围呈不规则的圆形,花瓣之间极为模糊,数量也难以分辨,只呈现出大致团花的形状,并且每个单独的团花都不尽相同,各种形态均有,应为绞缬捆扎而成,这种朵花的不规则性正符合绞缬技艺的特征。花型类似的团花图案还出现在唐代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女性缬衣俑的长衫上、陕西咸阳底张湾唐墓出土的骑马俑的长衣上、敦煌壁画《张议潮出行图》中骑士的衣着上,各个图画中的具体纹样将在绞缬的功用中详尽阐述。
其三,梅花也属于绞缬图案中花的纹样,一般来说,梅花的花型较小,多呈五瓣对称的规则样式,这一特征能够在古籍图像资料中得到印证。如唐代周昉的《内人双陆图》中,有一名扎双发髻的年轻女子,其身着浅褐色地的圆领连体裙衫,裙衫上细密地印有墨绿色的树干和枝叶,其间有为数不多的白色梅花,单个花型较小,稀疏地穿插在枝叶中。每朵梅花明显呈五瓣,花瓣围绕着中心的白色圆点依次排开,花型规则且对称。白色的梅花瓣周围忽明忽暗,轮廓并不十分明显,能够看出绞缬晕染的效果。
同一类型梅花纹样的变形还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初唐第217窟东壁北侧的《观音经变图》中,左侧的一名女菩萨所着的长裙下摆稀疏地分布有白色的梅花纹样,这种纹样与前述的五瓣梅花有所不同,主要是由四片花瓣组成,呈现十字对称构型,花瓣之间紧紧相连,中心并没有明显的花蕊,整体以交错的形式排列开来。虽然花型同样较小,但在深色的佛衣上能够清晰地看到白色梅花周围的晕染现象,可以推测菩萨所着的服饰应是绞缬织物。
其四,花的纹样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即网状花的纹样。这种纹样在古籍和出土文物中并不多见,仅有少量的网状花纹样出现在卷轴画中,这是对当时绞缬花纹样的间接反映。比较典型的是《内人双陆图》中,有一下白棋的女子,其下身着齐胸浅褐色长裙,长裙上的白色正六边形网状纹样正是网状花的外部轮廓,整体没有空隙间隔,呈蜂窝状紧密排列。在单个正六边形的中心有各不相同的青色绞缬花样,不均匀不对称,边缘与浅褐色地有晕染痕迹,显然是利用绞缬的捆缝技法所形成的花纹。与这种纹样的形制几乎完全相同,还有另一则例证,在《捣练图》中手持小火盆熨烫布料的女子衣裙外搭着一条披巾,披巾呈浅青色地,白色正六边形防白均匀分布于披巾上呈网状,在六边形内部有明显晕染的浅褐色绞缬花样。而《内人双陆图》中另一观棋女子的连衣外衫上呈现上述网状花纹样的变形,长外衫同样是浅褐色地,白框防白的正六边形围绕小团花所形成的图形依然是网状花纹的单位纹样。但是就整体布局而言,每个单位纹样的间隔较大,正六边形呈等距分布于外衫之上。
总之,在绞缬工艺中,花的纹样大多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四瓣花、朵花、团花和网状花纹都只能大致展示花的姿态,无法具体辨明花的种类,而梅花纹样也是经过抽象之后被归于绞缬花的纹样之中的。尽管花的纹样是简单抽象的,但是由于呈现绞缬晕染的效果,依然展现出不同花型的微妙变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绞缬花纹样特有的艺术风格。
2.点状纹样
点状纹样也是古代绞缬纹样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有大小、方形和圆形之分。有学者曾经指出,从出土的古代丝织品到现代存留的民间染缬作品,点状纹样以方和圆的构图格式最为常见,而且结合用品的外部造型,多以方形为主,圆形为次。①蔡光洁:《格律与自由——从染缬艺术看中国民间图案之美》,《丝绸》2005年第3期。
就方点纹样而言,出土的绞缬实物和古籍中有关方点纹样的图像资料较多,一般说来,这种单位方形点纹的花型较小,都控制在边长2cm以内,其形状能够看出棱角似方形,单位方形纹中心存在着与深色染料颜色相同的方形斑点,并明显带有晕染的效果。
方点纹样存在几种不同表现形式,依照单位方点纹的面积大小或是方点纹之间的排列间距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比较典型的一种是单位方点边长约1cm左右,单位纹样之间的间隔保持在一到两个单位方点边长的距离,横向间距与斜向间距基本相同,也有单位间距会稍微扩大或缩小的情况,但总体变化不大,具体方点纹样的细节将会在下文中根据不同的出土实物做详细解说。有的学者将此种方形纹样约在1cm范围左右且单位方点间距适中的方点纹都概称作“方胜纹”。②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21页。如阿斯塔纳305号墓出土的大红色绞缬绢,而同一实物,有的学者则将之视为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醉眼缬”。此外,有资料表明,若是将方点纹样缩小至0.2-0.4cm左右,且将间距缩小,使得小方点在织物上密密麻麻地排列,这样的方点纹就是古代文献中屡屡提到的“鱼子缬”。③王予予:《中国古代绞缬工艺》,《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再说圆点纹样,根据相关实验可知,若是撮起织物的长度扩大至2cm之上,那么按照制作方点纹样相同的捆扎方式得到的绞缬纹样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状,即圆点形纹样。④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91-92页。这类圆点状纹样虽然出土实物较少,但是在史籍或是图像资料中都有出现,是点状纹样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类型。如《内人双陆图》中一位下黑棋的女子的裙衣上就有防白花的圆点纹样。而有的圆点其边缘不规则,形成晕染自然的曲线,中间呈现深色斑点,纹样类似于鹿皮上的纹样,也就是古籍中多次提到的“鹿胎缬”,这种纹样与前面提到的较为复杂的团花纹略有相似之处。若是采用全捆扎法将这种鹿胎缬中心的深色斑点去除,再适当地扩大单位纹样的轮廓至一定程度,那么这种实心防白的圆形纹就是上述花的纹样中提到的变形大圆圈纹。下面具体针对不同的方形、圆形点纹的出土实物和图像资料做详细论述。
首先是方点状纹样的出土绞缬实物较多,可以1959年吐鲁番阿斯塔纳305号墓出土的“大红绞缬绢”为代表。①参见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91 页。整个绞缬绢的方点纹呈散点布局,其纹样是典型的平列“方胜纹”,周围有色晕,是捆扎留下的痕迹,也是绞缬技法的重要标志。这条大红花绞缬绢残片长14.5cm,宽7.5cm,单个点状纹样呈方形,方形中央呈现缩小的红色方形,其染色部分的四周有晕染效果,外周边则是方框形的防白花纹,外边边长约为1cm。单个方形的对角线完全与织物的经线和纬线重叠或平行。
此外,1959年在于阗出土了北朝时期的“绯红色绞缬绢”以及1967年阿斯塔纳85号墓出土的大红、绛紫色两件绞缬绢都是方点状纹样,与305号墓出土的绞缬绢的纹样十分相似,只是点状纹样散点的间隔有所不同,分布的稀疏程度不一致。阿斯塔纳85号墓出土的“红色绞缬绢”长17.8cm,宽5.5cm,②杨建军:《扎染艺术设计教程》,第14页。其方点花纹绞缬相较305号墓出土的绞缬绢略小,边长约为0.5cm到0.6cm左右,③图详见杨建军:《扎染艺术设计教程》,第139页。每个方点的防白面积较大,中心晕染较小,防白几乎形成了方形的绝大部分,根据一些学者对方点纹样捆扎手法因素的分析,形成较大的防白方框很可能是由于在绞缬捆扎的过程中反复缠绕或是用线较粗形成的染色效果。④王蔚:《扎染艺术微探——扎染史话·特点与工艺随笔》,《艺术探索》1996年第4期;余涛:《绞缬技艺琐谈》,《丝绸》1991年第1期;陈健:《有松扎染及其技法初探》,《丝绸技术·第二卷》1994年第1期。红色绞缬绢上的方形白花纹较为不规则,有的呈现菱形式样,交错排列。85号墓出土的另一件“绛紫绞缬绢”,长11.5cm,宽3.5cm,呈稍微规则的方形白花纹,花心有方点,纵横平列。另外,还有1963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西凉墓室中的缬染幡和1965年甘肃敦煌莫高窟130窟主室出土的缬染幡,两者的绞缬纹也属于此类方点纹样。此外,一些珍藏于海外的方点绞缬绢,如印度新德里博物馆藏的六朝中期的丝地绞缬残片、4-5世纪的新疆阿斯塔纳6区1号墓出土的绞缬残片,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的8世纪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大红绞缬残片都属此类纹样。⑤图详见杨建军:《扎染艺术设计教程》,第140-141页。
以上均是不同时期出土的方点散布状纹样的绞缬,这些绞缬绢基本是古代丝绸布料上方形点状纹样的典型或变形。因为这类纹样单体大都在1cm左右,且绞缬的色晕效果朦胧感较强,因此在古代诗文中曾被称作“醉眼缬”。根据相关学者的论证和实验表明,正是因为以上出土的织物均为较薄的丝绸面料,是典型经纬构造的织物,并且产生的方点纹样并不大,基本都在每边2cm以内,这样通过捆扎的绞缬技法所形成的点纹呈现方形就成了一条定则。如果要制出圆点型的纹样则需要扩大撮起点的长度或是采取特殊措施,如更换织物的材料为棉纸等非经纬构造织物。⑥王予予:《中国古代绞缬工艺》,《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另外,这种方形纹单个方形点状纹样中间的晕染呈现出绞缬最为突出的特征,也是绞缬工艺中最简单而且最具有代表性的纹样。
二是除了以上同类型的典型方点平列的绞缬绢以外,还有这种方点纹样的变形实例,变形主要体现在方点花纹的整体布局和单个纹样的面积大小方面。如现藏于日本东大寺的变格醉眼缬,被称作“缥地目交绞缬絁”,⑦图详见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94页图29。这件藏品的方点纹样呈现半明半暗,并且整个纹样的布局并非前面几件的交叉平列,横向单位纹样间距与上述几件绞缬类似,斜向间距明显拉大至三到四个单位方形边长的长度,每条方点形成的行距间隔较大。据相关实验表明,形成这样的状况是由于折叠配合环扎所形成的,折叠的效果除了使得行间距扩大以外,还会使每层折叠上的捆扎点处于半遮蔽的状况,使得最终形成的花纹半明半暗。①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93页。另外一件收藏于日本法隆寺的目纹绞缬,称作“赤地目绞文缬”,②图详见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95页。这是一种方点型纹样的组合形式,一个单位纹样是由一个较大的方点与六个较小的方点对称分布所构成。与典型的方点纹不同的是,这件藏品中心的大方点由于采用上下两层环扎,因此并非只有一层防白和中心晕染,而是呈现双层的“回”字形,这也是方点纹样复杂变形的特例。
三是一种经过特殊夹板防染绞缬处理的全白方点纹样,也是典型方点纹样的一种变形。可以敦煌莫高窟出土的编号为K130:12的“夹缬绢幡”为例。此绢幡湖蓝色地,全白方框纹样,长约8cm,宽约7cm,方块边长约1.2cm,属盛唐开元天宝时期的染缬。虽然名称看似是夹缬所制,但此绢幡与传统意义上使用精致具象镂空花板制作的夹缬并不同。据相关实验表明,这件藏品明显是使用典型绞缬叠坯的加工方式制作,最终由印有方块突起的夹板防染而成,方点边缘略有晕染,但其中心全部呈现织物原色,并未出现晕染的状况。③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9-90页。因而也将其归入绞缬之中。
圆点状纹样也能够在古代的卷轴画中找到例证。如《簪花仕女图》中一名手持长杆绢扇的侍女,内着红色齐胸长裙,外披浅朱砂绸缎开襟长衫,长衫外系有一条手掌宽的浅褐色腰带,腰带上交错分布有均匀的圆点纹,单个圆点纹是由一圈较细的防白圆环和圆点内部的褐色圆斑构成,圆斑相对较大,几乎与圆点纹大小相差无几。且浅褐色圆斑存在晕染状况,以至于外圈的防白圆圈边缘并不十分规整。
这种圆环套圆斑的圆点纹也有其变形,即完全实心的绞缬圆点纹。在《韩熙载夜宴图》中,画卷左轴有两名正在交谈的年轻女子,其中一名身着白色长裙的女子其上衣上跨有一条青色飘带,绕过肩头一直垂于裙摆外侧,这条飘带上交错分布有枣红色的实心圆点纹,圆点外部轮廓有明显的晕染痕迹,且单位圆点之间的距离比较紧密。显然是选用了大红色的丝绸并在其上进行青色实心环扎的绞缬飘带。
3.几何纹样
规则的几何纹样以四方连续的网状纹最为常见,这种网纹缬又被称为“叠胜纹”。其典型实例是1969年新疆阿斯塔纳117号墓出土的棕色地“叠胜纹绞缬绢”,长约16cm,宽约5cm,棕色地的网状纹样呈规则的四方连续。网格呈现规则的菱形,菱形的每边长约1.5cm左右,并且在每个菱形的交点和对角线处都有横向穿过的平行折痕,凸凹有秩,相互间隔。绞缬面料之所以有这样的平行凸凹折痕,据相关实验资料,正是由于网纹绞缬在加工前要将绢以同样的宽度折叠而成,再使用针线反向斜角来回缝制,使每条折好织物的侧面缝纹呈“M”型,之后抽紧扎好入棕色染液,晾干后拆去缝线就显现出棕地网格防白纹样。④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3-84页。此外,每个单位菱形网状纹样的边上会有三四个织物本色的晕染斑点,每个斑点中心都有一个明显的针眼,这正是绞缬工艺平缝技法防染的突出特征。
另外,同样形式的菱格网纹的藏品还有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304号墓出土的匣紫、绛紫两色的“叠胜纹绞缬绢裙”,是唐代垂拱年间的绞缬。这件规则网纹的绞缬并非是一块整体织物,是用几块约8cm宽的窄长绢条染花拼缝而成。⑤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3页。其每个单位网纹的晕染效果和晕染斑点数量均与前一种类似。
此外,这种菱格网状的叠胜纹还有一种典型的变格纹样,此种纹样依然呈现规则四方连续的样式,只是在以上典型叠胜纹呈现白色晕斑处被浸染成染料之色,而围绕原先菱格直线四边形成了八条弧形的防白花纹,较之前的两件防白弧线较为细瘦,这些防白弧线依然是由单个依次排列的小晕斑组成。较为典型的实例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黄地七宝文绞缬绢”,①图详见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4页图3。织物质地轻薄,呈淡藕荷色。虽然此种纹样与典型的叠胜纹有细微不同,但是其折叠制作的方式类似,只是在制作绞缬过程中以叠胜纹的缝线为对称轴,代之为两侧的两道弧线。实验资料证明,正是由于要呈现这种纹样的效果,可能缝制就会比较细密并且线要抽扎得更为紧密一些。②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3页图2。这件藏品的晕染并没有前两件那么明显,但其依然体现了绞缬工艺常用且变化较为丰富的几何纹样的特征。
《捣练图》中还存在菱格网状的变格纹样与大圆圈纹样相结合的情况,但无法确定两种绞缬纹样的制作是否是同时进行的。图中一名手拉绸缎身着湖蓝齐胸长裙的女子所穿的红色绞缬开衫就属于这种式样,菱格网状的变格纹样与“黄地七宝文绞缬绢”基本相同,弧形的防白网格相较前者略长,网格内部中心有一块防白大圆圈纹,所有白色防染的部位都稍微显现出晕染迹象。并且弧形防白花纹的内部存在墨绿梭形和小珠状点缀,防白圆圈内部施以小珠状的密集点缀,看上去类似于团花,因为花纹精致清晰,很可能是先由红色染料在白色织物上进行网纹和圈纹的绞缬,后在防白处施以墨绿刺绣的结果。
总的来说,几何纹样整体单纯严谨,具有明显的几何规范,四面展开产生多样化的晕染效果。而不规则的散点和团花纹样则相对自由活泼,图案的审美表现力和技术适应性都较强,艺术创造空间更广,花纹柔和含蓄具有独特的美感,层次和虚实变化更加丰富多样。
(二)绞缬纹样的名称
绞缬纹样在历史上种类颇多,名称各异,不同的绞缬纹样名称都是绞缬工艺不同应用和创造发展的体现。在古籍中最集中的反映是,元代的一本名曰《碎金》的通俗读物,记载了当时的九种染缬名目,其中不少是关于绞缬纹样的记述,分别是檀缬、蜀缬、撮缬、锦缬、茧儿缬、浆水缬、三套缬、哲缬和鹿胎缬。这些染缬名称中有的明显与绞缬纹样的形态相关。唐代是绞缬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具体绞缬纹样的名称也大多能够在唐诗中加以印证。此外,唐宋之际还有鱼子缬、玛瑙缬、团窠缬等著名的绞缬纹样的名称。
撮缬,即大撮晕缬,是绞缬工艺中比较复杂的一种。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唐代宋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吴皇后将合祔肃宗陵,启旧堂衣服,缯綵如撮染,成花鸟之状。”③转引自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5页。此处的撮染极有可能指的就是撮缬。还有《宋史·舆服志》中也有关于撮缬的记载,仁宗天圣三年(1025)诏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月断绝。”④《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75页。诏令中所说的黑褐色地白花衣服和蓝黄紫地衣应该都属于“撮晕花样”的绞缬,这种撮晕花样极有可能指的就是大撮晕缬。
锦缬,有学者认为可能指方胜格子式样的绞缬。⑤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6页。
檀缬,中檀意为淡褐色,且古代妇女眉毛旁的晕色在古书上被称作“檀晕”,历史上有“檀晕妆成雪明月”的句子。因此,这种被称作檀缬的染缬很可能就是淡褐色的带有色晕效果的绞缬。⑥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5页。
蜀缬,即蜀中染缬。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蜀缬就是绞缬,应当是包括绞缬在内的川蜀地区的染缬。白居易所提及的“成都新夹缬”①白居易:《翫半开花赠皇甫郎中》,《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48页。指的是染缬中的夹缬。唐代成都女诗人薛涛在歌咏海棠之时,有“竟将红缬染轻纱”②薛涛:《海棠溪》,《全唐诗》,第1970页。的诗句,用娇艳的海棠花比作红缬,此红缬即是蜀中染缬的一种。还有《新唐书》中的记载,“帝尝幸其院,韦妃从,会绶方寝,学士郑絪欲驰告之,帝不许,时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③《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韦贯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7页。虽然在此提到的“蜀襭袍”是何物现已无法考证,但是能够确定的是这种袍子是蜀缬的重要代表。
茧儿缬,有学者认为是几何纹样有些象蚕茧的染缬。④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6页。但其他学者则认为茧儿缬是用蚕茧剪成两片相同的茧花,前后相对缝缀在织物上,其排列则多是等距离的散点,染色后除去茧花,即呈现蓝地或其他色地的白色花纹。⑤余涛:《现代扎染艺术》,第2页。
鹿胎缬,传到日本后又称作“鹿子绞”,从文献资料看,是一种紫地白花或是红地白花的绞缬,也就是花纹效果类似梅花鹿的毛皮斑纹,即前文提到的放大的不规则的圆点纹样,点中有染色斑,这种染缬可能多为绞缬。此类纹样在隋末舞俑的着装中就有较为具体的呈现。⑥李雪玫、迟海波:《扎染制作技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3页。晋代陶潜《搜神后记》中载“淮南陈氏于田中种豆,忽见二美女着紫缬襦(上衣),青裙……”⑦转引自赵翰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5页。,称穿着缬衣的女子远看如梅花鹿一样的美丽。可以推断,这两位女子穿着的大概是“鹿胎缬”纹样的服饰。因此紫地白花或是红地白花的不规则的圆点纹样的绞缬便以“鹿胎缬”或“鹿子缬”命名。此外,我们还能够从文献中看出鹿胎缬纹样在当时盛行的程度,甚至影响到花卉的命名。如《洛阳牡丹记》中有“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⑧欧阳修:《牡丹谱》一卷花释名第二,《宋史》卷二百五《艺文四》,第5206页。再有,宋人在《洛阳花木记》和《芍药谱》中称芍药为“黄缬子、红缬子、紫缬子、白缬子”。⑨转引自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6页。
鱼子缬和醉眼缬,其绞缬的制作方式与鹿胎缬完全相同,只是纹样缩小之后就由原先近似圆形变成了小的方形,两者均是鹿胎缬纹样变形的特殊名目。醉眼缬是鹿胎缬缩小至1cm左右,经折叠捆扎之后形成半明半暗的纹样,细碎而朦胧,类似人醉后微张的双眼,故而称之为“醉眼缬”,由于形状近似方形,也称作“方胜缬”。而鱼子缬则是指斑点更小的方点纹样,大小在0.2-0.4cm之间,而且整体方点密集程度较高,密集到地、纹相当的程度。布帛上最终呈现密密麻麻的立体小方点,犹如鱼子般,因此得名,是最简便的一种绞缬,但十分费工。唐代诗人段成式诗中有“醉袂几侵鱼子缬”“厌裁鱼子深红缬”。⑩段成式:《嘲飞卿七首》、《戏高侍御七首》,《全唐诗》,第2166页。
玛瑙缬,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撮晕缬中最为繁复者,为了制造出这样的缬绢应是使用了绞缬之法,套染出像玛瑙色彩的美丽纹理。⑪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6页。还有学者推测,玛瑙缬可能是色彩纷呈的多色绞缬,主要表现其色彩多样。⑫余涛:《现代扎染艺术》,第2页。
叠胜缬,指的就是呈四方连续网状纹样的绞缬。李贺诗中的“醉眼抛红网”所说的网纹绞缬就是叠胜缬的一种。
团窠缬,又称团宫缬,是一种圆形或近似圆形的丝织纹样。有学者认为这种团宫缬可能是类似宝相花之类的团花,团花的外轮廓有连珠纹样作为装饰。⑬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6页。但是目前尚无法确定这种所谓的团宫缬是染缬之中的哪一种。
青碧缬,即被染制成青绿色的绞缬。据《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彩帛缦成履。”①《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第532页。这便是当时妇女流行的服饰和色彩。
此外,《碎金》中记载的其他几种染缬、浆水缬,系指用糊料进行防染的工艺,类似于蜡染,不属于绞缬。而有学者认为三套缬是采用三套花版,并用三种颜色染制而成。②余涛:《现代扎染艺术》,第2页。若是这样,三套缬则属于夹缬的一种。史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另一种“哲缬”,也作“折缬”,很可能是画缬,即用笔直接画出,或是使用蜡染。因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哲匠”就是指画匠。③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6页。而有学者则称哲缬就是使用了折叠方式制作并绞染的。④余涛:《历代缬名及其扎染方法》,《丝绸》1994年第3期。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哲缬应当属于绞缬工艺的范畴。但由于各学者众说纷纭,目前难以准确地考证其真实性。
(三)绞缬纹样名称的命名方法
关于绞缬纹样的名称,历朝历代各有不同的称谓,经过对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认为大约有如下若干种命名方法。
一是以纹样的形状命名,如鹿胎缬、鱼子缬、醉眼缬、方胜缬、团宫缬,等等。所谓的鹿胎缬,据学者的考证,当为模拟鹿胎纹样、紫地白花的一种绞缬产品。⑤沈从文:《龙凤艺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32页。当然,实际上鹿胎缬不一定都是紫地白花或是红地白花,这只是指染色的效果而已。只要是防白花纹中心有类似鹿胎的染料色晕斑点即可。日本也有类似的纹样,日语的汉字写作“鹿子绞”。但日本的“鹿子绞”显然比中国古代的“鹿胎缬”要小得多,呈鱼子缬般大小。另外,早在10年前笔者在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调查时,曾收集到蓝地白花的鹿胎缬纹样的绞染布料。⑥金少萍:《白族扎染——从传统到现代》,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而鱼子缬也是类似鱼子的纹样,其密集程度像鱼卵一般;醉眼缬纹样的效果呈半明半暗,似人的醉眼;方胜缬是方胜形的绞缬,以平列交错的方点得名;而团宫缬大致是指宝相花团花状的绞缬;茧儿缬其中一种推测含义也是因其花纹酷似蚕茧形状得名;锦缬之名也可能是因为其花纹与织锦或是方胜纹相近而来。由此可见,以上几种绞缬都是取其纹样形似得名。
二是以地名命名的,如蜀缬指的是川蜀地区的染缬,在唐代十分有名,包括了绞缬、夹缬、蜡缬,这是与蜀锦齐名的染色织物。据笔者的田野调查,云南大理周城白族老人曾称当地的扎染系从四川传来。唐代的文献记载,由于战争,四川的纺织工匠曾经进入南诏大理地区,推动了当地的纺织工艺文化。⑦樊绰:《云南志校释》,赵吕甫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9页。
三是以染色工艺技法命名的,如玛瑙缬就是指绞缬的色彩灿烂如同玛瑙一般,这充分说明了古代染色工艺的高超技艺。实际上古代绞缬染色技法中已采用多次染、套染等诸多技法,染制的织物色彩绚丽、层次饱满。
四是直接以绞缝技法命名的,如哲缬,“哲”同“折”,取其推测之意,就是采用折缝技法缝扎之后再进行染色的绞缬。此外还有撮缬,因为撮也是绞缬的一种捆扎技法,撮缬、大撮晕缬由此得名。
五是以绞缬染色的色彩命名的,如青缬和紫缬就是一种泛称,显然是以染色的色彩来称呼的,也可视为一种命名类型。其中青缬泛指蓝色或绿色的绞缬,紫缬则是指紫色的绞缬,檀缬指淡褐色的带有色晕效果的绞缬。⑧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5页。
三、绞缬的功用
古代绞缬工艺的产生及其发展,与当时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既是绞缬技法的生产者和创造者,同时也是绞缬成品的使用者。所以,利用绞缬技法染制的丝绸和布帛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功用,服务于当时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日常生活、宗教信仰、商品交易等。
(一)服饰
用于制作绞缬的丝绸和布帛本身就是服饰的主要材料,而带有绞染花纹的彩色织物因为其独特的晕染效果,深受历朝历代民众的青睐。特别是在唐代,不仅妇女的服饰,甚至男人的服饰上也有团花类纹样的绞缬作为装饰,并且这一服饰习惯在开元年间(713-741年)被定为礼仪制度,并沿袭至宋代。①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24页;《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第3575页、第3576页。绞缬服饰曾用作男子的军服,在《张议潮出行图》中,骑士和卫兵的着装明显能够看出大团花纹或是不规则的圆圈纹样,有的还能清楚地看出色晕效果,显然就是绞缬之作。再有,绞缬用于服饰的装饰在宫廷中深受重视,前文所提及的《事物纪原》中花鸟之状的撮缬也见于服饰上。
1.绞缬纹样用于衣衫的装饰
辽宁吉安舞俑冢壁画中,舞俑的上身扎腰长袖衣服上布满了方形的点状纹样,这些方形纹样大小不一,排列较为疏松,方点颜色相较衣服地色深。并且这些方形纹样有的能看出中心为地色,而有的则看似是实心的深色方点纹,显然是绞缬在当时生活中的应用,但也不排除属于夹板防染绞缬的可能。
唐永泰公主墓出土一件女性缬衣俑,身着深地的长裙外套衫,没过膝盖。长衫上有较大的防白团花纹,虽然是泥塑俑,但是团花中心的深色晕染效果处理较好,能够看出是绞缬染制的效果。
陕西咸阳底张湾唐墓出土的骑马俑所着的齐膝扎腰长衣呈现大团花纹样,每个单位团花不规则,且纹样较大,分布散乱,团花中心有色晕大斑点,显然是绞缬染色的效果。这件骑马俑明显为男性,因此,团宫缬也可以用于男性的日常服饰点缀,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的裙衫。
在敦煌壁画《张议潮出行图》中,除了黑色着装的骑士外,有的骑兵身上的衣服穿红着绿,并且能够看出有深色或黄色团花的图案,这显然是包括绞缬在内的染缬服装。
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座榻上的三名女子开襟上衣上缀有大圆圈纹,尤其是左侧女子的暗蓝色地的黄色圆圈纹十分明显就是染缬之作,基于有晕染的大圆圈纹样来看,多为绞缬所制,因此这三名女子上衣上的纹样应当是绞缬技艺的展现。
在《簪花仕女图》中,图中心三名女供养人的开襟轻纱外衣均是浅褐色地上缀有白色方点的防染图案。此图中的几件外衫质地轻薄,能够清晰地看到衣内长裙的纹样和外衫上的防白花纹,这些花纹相互交错排列。女供养人衣内长裙上的纹样白色防染处有晕染渗透的痕迹,应是上述所提到的大圆圈团花图案,大圆圈的防染花纹内部的团花纹样精致清晰,可能是结合刺绣所产生的效果。这些女供养人外衫下的长裙所点缀的大圆圈团花纹样较为复杂,也有可能属于绞缬中的“撮晕缬”。
《捣练图》中,有一名手拿绢扇在火炉旁煽火的宫女,其所着的湖蓝色地的上衣十分精美,以黄色团花纹作为装饰,每个团花纹样交错排开,且与湖蓝色地相互渗透,可能是在黄色绸缎上进行青色绞缬捆扎染色的效果。这件湖蓝色绞缬上衣的纹样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一名身着淡青色地的女骑马者的上衣纹样也极为相似。图中另外两名女子所着的齐胸长裙,一呈深青色,一呈墨兰色,都是团花绞缬的例证。
除以上图像信息中所反映的绞缬在衣衫制作上的应用外,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述,如《宋史·舆服志》中载政和二年(1112)诏令:“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②《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第3576页。如果此文中所指的缬帛是包含绞缬在内的染缬的话,则绞缬也被用于制作卫士之衣,甚至是行军的旗号。
2.绞缬的纹样用于裤子的点缀
辽宁吉安舞俑冢壁画中的舞俑除了上衣外,其裤子与上衣的纹样和色彩完全一致,方胜纹的绞缬也用于裤子的点缀。虽然无法确定此壁画上的舞俑所穿的服装是特殊的表演服饰还是日常着装,但可以肯定方胜纹绞缬在上衣和裤子上的点缀作用。此外,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旧藏稿水陆画《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图》中,左下角的一名身材矮小的侏儒杂耍艺人所穿的灯笼短裤,也是红地黄方胜纹样,且有黄色花边点缀。
3.绞缬花纹装饰裙身
在各地出土的唐三彩的陶俑中,女俑的长裙都有类似的特点,即碧绿色地白点花纹,不论是歌伎、贵妇还是舞女都能够找出类似的实体。这种碧绿色地白点花纹的长裙想必就是《唐书》中所提到的“青碧缬”衣饰,两者都是使用绞缬技法制作的裙饰。正如前文所提到的,1959年在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匣紫和绛紫两色的叠胜纹绞缬绢本身就是一件绢裙,属于墓主人生前的穿着物。
在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内,舜帝的二妃身着一蓝一红两件类似的连身长裙,长裙腰身以下的百褶上布满了较为密集的白色方胜纹样,虽然板画年代已久,上身是否有白色防染的方胜纹不得而知,但是裙摆上的方框防白花纹清晰可见。
喀喇和卓出土的木芯泥俑,泥俑所着的齐肋长裙是深地白方点的缬纹裙,白色方点呈实心,纵向成行排列,上密下疏,也是方点纹绞缬纹样应用于裙身的实证。
在敦煌莫高窟五代第98窟东壁北侧《回鹘公主供养像》中,公主的长裙拖地飘逸,深色披肩垂于肩部,肩部以下从手臂部位开始均装饰有大圆圈团花纹样,纹样边缘稍有晕染效果,可推测为绞缬服饰的应用。
4.绞缬作为披肩和披袍的装饰
1973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泥头木身女佣,①图详见杨建军:《扎染艺术设计教程》,第142页。上身有一披巾,地为豆绿偏草黄色,披巾上有很小的绞缬方点图案,每个白色方点内部还有很小的绿色斑点,边长不到0.2cm。整个披巾上的小方点三个一组呈三角形排开构成一个单位图案,单位图案的间隔较远,花组显得稀疏错落。花组稀疏显然不能称之为鱼子缬,但是其单个小方点的大小和形状与鱼子缬极为相近。有学者认为这条披巾是考古出土物中花纹最小的绞缬实物。②王予予:《中国古代绞缬工艺》,《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前文提到《新唐书》中的“蜀缬袍”,这种“蜀缬袍”是否是绞缬制成现已无法考证,但是如果能够证明是绞缬,那么这种缬袍也是绞缬技艺在当时日常服饰中的应用。
5.绞缬用于服饰的其他方面
一是帽子的装饰。《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画》画作的下部,有写实的社会下层杂技人十一名,多以“方胜”纹样的绞缬作为衣饰。其中两名主要人物头戴蓝地方点白花绞缬帽,两帽带垂于脑后,帽带上有同样款式的绞缬纹样,只是颜色有所不同,一红一蓝。还有宋代《大理国画卷》所绘跟随国王礼佛的文臣武将中,有两位武士头上戴的布冠套与传统蓝地小团白花绞染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大理扎染近千年前用于服饰的直观记录。③杨雪果:《传扬生活妙韵的巧技——云南民族工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二是腰带的装饰。《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图》十一人中,有五人都系有红地黄方点的“方胜纹”腰带,还有一人系有蓝地同样纹饰的腰带,腰带的宽度和式样并不相同,但是可以明显看出方胜纹的轮廓,花纹较大的蓝色腰带甚至能够看出画中纹样晕染的效果。
三是围腰的点缀。《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图》中系有蓝色腰带的杂耍艺人赤裸上身,腰带缠绕在一块红色团花的围腰之下,以起到束紧围腰的作用。这块红地黄花的绞缬腰带宽度较大,图中的花样并不清晰,稍有晕染效果,无法辨认团花的种类,是抽象的绞缬团花,可以理解为上述所介绍的团宫缬。
四是衣衫的肩部和扣带加固处都使用了绞缬纹样。《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图》中上方有两人所着衣衫的肩部有两块长方形的方胜纹绞缬式样的装饰,且纵向的扣带长条也是同类的纹样,两人一红一绿,起到点缀并加固衣衫的作用。
五是手带、脚带、头带上也能够寻觅到绞缬的纹饰。《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图》中的杂耍艺人几乎每人的腕间都缠有红地黄方胜纹的绞缬带。有一人的头部也缠绕了此种样式的绞缬带,以束紧黑色的帽子。另外,《捣练图》中也有用绞缬作为发带装饰的图像。
六是衣领、袖口和衣衫的前摆也有绞缬纹样。《往古九流百家诸士艺术众图》中左下方一男子的衣领一周均为红地黄方胜纹,而其扎于腰带之下的衣衫单片前摆则是蓝地白方胜纹样的绞缬制作而成,周边还缝扎有黄色的外围。
在宋人画《杂剧人物》中①郑振铎:《文物精华第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彩图。,有两名女扮男装的杂剧演员相互作揖,两人所穿对襟衫的衣领、围腰以及围在腰上的锦囊都明显是染缬作品。其腰间插有油纸扇的艺人围腰上能够明显看出团花纹样,但又不像是绞缬技法所能达到的复杂程度,可能采用的是其他染缬技法。而衣领饰有白色凤纹,并间以金色的“回”纹,凤纹显然超出了古代绞缬能够制作的复杂程度,但回纹则是另外加工上去的。②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37页。虽然宋代时期绞缬技艺已经在浆水缬和印花布的冲击下有所衰退,但是上文也提到了一般的回纹极有可能是方点纹样的双层捆扎的变形,并不能排除其衣领上的回纹就是绞缬所致。图画左边艺人腰间的锦囊则是白地蓝色网状纹,呈明显的四方连续,网格交点之间有晕染,显然是使用绞缬技法制成。
还有山西汾阳圣母庙中圣母殿北壁的《乐伎弹奏图壁画》中,图中四名乐伎所着的衣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复杂,其衣袖和领口处都有一圈团花图案,团花外侧有由深及浅的色晕,团花的花蕊极为明显,没有出现晕染效果,因此推测这些领口和袖口处的团花是先绞缬后刺绣的结果,刺绣装饰于花蕊处。
七是飘带上也存在绞缬纹样。在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内,妇女所着衣衫的飘带也是防白的方胜纹样。除了女性日常服饰的飘带之外,在敦煌莫高窟唐第154窟南壁西侧的天王像上,天王盔甲前紧扎的带子也应是绞缬之物,上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白色的方点纹样,近似于鱼子缬。
(二)生活用品
绞缬除广泛用于服饰外,还用于屏风、帐幔、床单等,这些常见的生活用品上多用绞缬技法染色,是当时社会生活时尚和审美情趣的一种折射。
1.绞缬在帐幔中的使用
陶榖《清异录》中载:“显德中创‘尊重缬’,淡墨体,花深黄。二部郎陈昌达,好缘饰,家贫,货琴剑作缬帐一具。”说的是五代时一个穷书生为了赶时髦,不惜卖掉琴和剑去换一顶缬帐。虽然文中的“尊重缬”为何物现已不得而知,但许多学者均推测这顶缬帐是包括绞缬在内的染缬技艺的体现,极有可能就是绞缬之物。③余涛:《历代缬名及其扎染方法》,《丝绸》1994年第3期;蔡光洁:《民间染缬技艺的综合运用》,《四川戏剧》2006年第2期;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37页。
有学者提到,徐兢高丽图经“二十八:缬幕,非古也,先儒谓系绘染为文者谓之缬。丽俗今治缬尤工,其质本文罗,花色即黄白相间,烂然可观。其花上为火珠,四垂宝网,下有莲台花座,如释氏所谓浮屠状。然犹非贵人所用,惟江亭客馆于属官位设之”。④转引自沈从文:《谈染缬——蓝底白印花布的历史发展》,《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可见唐代的染缬技艺流传范围较广,当时的朝鲜半岛已经开始使用缬帐。虽然目前无法判定图经所提及的缬幕具体为染缬的何种技法,但是使用绞缬制作帐幔也是极有可能的。
除了文献的记载,在《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两处画有床榻,床榻上方都罩有帐幔,分别是一红一棕黑,红色帐幔上缀有黄色的大圆形花纹,棕黑色的帐幔上则是白色的大圆圈纹,两处幔帐上的纹样色晕朦胧,显然是采用绞缬技法作为装饰,以团宫缬纹样晕染后的效果。
2.绞缬在屏风上的应用
很多学者的著述中都提到,古代的绞缬技法在屏风的制作中有所使用,尤其是敦煌壁画中佛、天王、菩萨以及供养人的屏风上都有染缬技艺的痕迹。但是古籍、图像材料或是实物却极为少见。我国隋唐时期赠送给日本的许多礼品中,有巨幅的“花树对鹿”“花树对鸟”等夹缬屏风,现在日本奈良正仓院馆藏物中就有唐代的多种染缬屏风,①刘咏清:《略论染缬》,《丝绸》2005年第12期。这些屏风虽然大多是采用夹缬技法制作,但也不排除有绞缬屏风的可能性,只是目前尚未找到实物资料。
3.床围、枕套、坐垫上也出现不同式样的绞缬纹样
在《韩熙载夜宴图》中,红色绞缬帐幔下的床围为湖蓝色地,上面均匀排列有大圆点纹样,与帐幔上的纹样相似,只是总体排列不同,这种纹样与古籍中提到的团宫缬相似,很可能就是绞缬捆扎技法所制。再有,湖蓝色绞缬床围的上方放有一个暗蓝色地的枕头,上面交错排列着与床围纹样相似的黄色大圆圈团花纹,此枕套显然也是由绞缬技艺制作的。另外《宫乐图》②《宫乐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人物的发式或着装为中晚唐女子服饰的典型样式。中,除了女子的服饰上有明显的绞缬纹样外,其坐垫上也呈现出红地白花的绞缬纹样。
(三)宗教用品
绞缬技艺除了在日常生活中有较为广泛的装饰和点缀作用外,还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
首先,用于宗教的绞缬绢幡较为普遍,故而在敦煌等佛教盛地有诸多绞缬绢幡出土的报告。据有的学者对相关考古发掘报告资料的整理,1965年于敦煌莫高窟130主室南壁岩孔中和122窟、123窟的窟前地下,分别发现60多件各类彩幡,其中就包括多件染缬绢幡,也不乏绞缬幡。③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31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并且保存比较完整的是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多色花鸟纹缬染幡,这件藏品于1965年在敦煌莫高窟130窟主室南壁岩孔内发现,颜色艳丽,纹样精美,是唐代时期制作的绞缬作品。幡身主要分为六段,除第三段为蜡缬绢,其余各段均为绞缬绢,以绿地或紫地为底,之上有典型的方胜纹样,防白方点中显现出晕染的效果,每个单位方点的排列也是绞缬典型的平列交叉布局。④杨建军:《扎染艺术设计教程》,第143页,图14。除了这件典型的绞缬绢幡,还同时出土了诸多各式绞缬绢幡和绢带,如前面提到的用夹板防染绞缬工艺制作而成的原编号为K130:12的绞缬绢幡,幡身湖蓝,上缀绞缬全白方块花纹;还有原编号为K122:4的绞缬绢幡,幡身第一段和第三段为褐色地,上缀绞缬白点纹;以及原编号为K130:31的绞缬绢带,是一端打结的双层带,茄紫色地白点纹。⑤张道一:《中国印染史略》,第31页。
其次,直接用绞缬作供祭品,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的开成四年(839)五月二日“……日没之时,于舶上祭天神地祇,亦官私绢,绞缬、镜等奉上”。⑥李鼎霞:《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许德楠校注,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这则资料是用绞缬作供祭品来祭祀天地神的直观表现。此外,据笔者在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过“本主节”时,全村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届时家家户户都要到本主庙去祭祀本主。此时要特别选用扎染方巾衬垫摆放祭品的托盘,直接用扎染布料作为供桌布,这些都是绞缬在宗教祭祀中的运用,表达了祭祀者敬畏虔诚的心境,也是神圣庄严气氛的渲染。
最后,绞缬还用于宗教服饰,在明清时期云南大理地区的寺庙中,曾发现有的菩萨塑像身衣有扎染残片及扎染经书包帕等资料。⑦杨雪果:《传扬生活妙韵的巧技——云南民族工艺》,第86页。在间接图像资料中,敦煌莫高窟初唐第217窟东壁北侧的《观音经变图》中,两名菩萨中的右者就身着点状纹样的深地长裙,每个单位小点以三个为一组呈三角状,分列若干组于全身,这种分布极像1973年阿斯塔纳出土的泥头木俑身上所佩戴的豆绿色的披肩纹样。此外,最为典型的是在敦煌莫高窟第196窟晚唐的《劳度叉斗圣变》图中,莲花座上的菩萨身着湖蓝地的佛衣,佛衣下摆上紧密分布有淡褐色的团花纹样,纹样不十分规则且晕染效果明显,有些甚至看不出单位纹样外部的轮廓曲线。菩萨的佛衣外还罩有一长披风,整件披风呈深褐色地,上面交叉分布有花型较大的浅褐色团花纹样,披风上的团花相较佛衣上的则较为规整,是典型的较为复杂的团花纹样,花样晕染效果明显。由于画工精湛,甚至能够隐约看出团花捆扎的褶皱,因此两件服饰均为绞缬技艺装饰的运用。另外,菩萨的右侧还有五个站立交谈的和尚,和尚所着袈裟的款式和颜色各不相同,颜色有湖蓝色地、棕色地、黑色地等。但不论是那种式样或色彩,袈裟或全身或局部缀满了不规则的团花纹样,纹样相较菩萨的花样更加细长,褐色中心并无白色的晕染斑点,并且浅褐色的花纹分布较密,多在湖蓝色地上。相反湖蓝色在袈裟上显色的面积较小,而褐色斑纹显色比例较大。因此,若是以褐色布帛为原料上绞染湖蓝,不易显色,因此极有可能是在湖蓝色织物上捆扎染淡褐色的绞缬之作。整幅壁画中还有零星分布的披袈裟的罗汉僧徒,袈裟上也同样有制型较长的变形团花纹样,好似抽象的田间山水。以上这些佛衣或是袈裟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绞缬布帛在宗教服饰方面的应用。
(四)商品交易
在古代,绞缬作为商品交易的记述并不多见。制作绞缬的丝绸布帛最初是直接供给皇宫中的皇亲贵族享用,属于上流社会的奢侈用品。后来包括绞缬在内的染缬技艺广泛流传至民间,专门从事染缬的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也为绞缬制品在当时作为商品提供了可能。例如《魏书·封回传》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荥阳郑荣诌事长秋卿刘腾,货腾紫缬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①《魏书》卷三十二《封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1页。可见当时上乘的绞缬已经可以作为“货”用,反映了绞缬绢一定程度上作为商品的社会功用。
四、绞缬的技法
中国古代的绞缬技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往往是多种技法综合使用,延袭至现代又增加了许多先进技术和辅助工具。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古代的绞缬技法进行了研究,有的甚至进行了诸多实验,以分析和测定其技术要领。②探讨古代绞缬技法的文献主要有王蔚:《扎染艺术微探——扎染史话·特点与工艺随笔》,《艺术探索》1996年第4期;余涛:《绞缬技艺琐谈》,《丝绸》1991年第1期;陈健:《有松扎染及其技法初探》,《丝绸技术·第二卷》1994年第1期;王济成、刘凤云:《让古老的扎染艺术重放异彩》,《装饰》1984年第1期;周燕:《扎染艺术的研究》,《辽宁丝绸》2010年第3期;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社,2001年;杨建军:《扎染艺术设计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余涛:《现代扎染艺术》,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其中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一书则记载了诸多复原古代绞缬技法的实验过程及其结果。在前人探讨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试以上述第二部分提到的出土传世绞缬纹样的制作技法为主,进行探讨和分析。因为这些绞缬纹样所运用的技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反映我国古代绞缬技术的面貌和要领。主要的技法大致分为四个类型:平缝技法、捆缝技法、折缝技法和综合缝扎技法。
(一)平缝技法
平缝技法是古代绞缬技法中最主要、最常用以及最基础的一种。主要是借助针线,在织物面料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图案在特定的部位进行缝制并抽紧,从而起到防染作用。平缝在古代是比较基本的花纹缝引,虽然出土文物中多以平缝技法表现抽象纹样,但是单就平缝这种技法而言完全能够用于具象图案的制作。一般情况下,平缝要求每个针眼之间的针距相等,缝制均匀,并且抽线的松紧均匀,按照所需要制成图案的最终效果施以不同的力度。一般而言,一段相同表现效果的绞缬图案会用同一根线缝完,由小到大,自内而外。当然,平缝也有很多变形的方式,制作者可以根据图案的不同要求随意调整典型平缝的针距和力度,进而呈现不同的绞缬效果,也让制作者有一定的创作和发挥的空间。
我们能够看到,在出土文物中,平缝技法是被广泛采用的,但很多情况下都会与其他缝扎技法相结合。如1969年阿斯塔纳出土的棕色叠胜纹绞缬绢上排列着明显对称的平缝针眼,这些都属于平缝技法的延伸。也就是说,在进行平缝的时候,可以使用单层、双层、或是多层织物,后两者是经过一整块织物折叠形成的,这种折叠可以是规则的,也可以是不规则的。后两种平缝方式是折叠缝技法中的一种,简称折缝技法,是下文所要介绍的第三种绞缬技法中的一种情况。此外,其余很多类似的褶缝、包边缝、卷缝和钉缝都是在平缝技法的基础上变化发展出来的,这些缝扎技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不同形式的绞缬纹样。
(二)捆缝技法
捆缝技法,又称作捆扎,是借助线或绳对织物面料的特定部分进行一定力度的捆扎、缠绕,从而在缚线处起到防染作用的缝扎手法。这种捆缝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借助针具的使用,其形成的纹样图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绞缬工艺中最基本、最普遍、最为古老的方胜纹样。根据捆缝织物捆扎的长度和力度不同,会出现色晕层次朦胧、迷离的美妙纹样,因此捆缝技法多用于表现抽象的图案。当然,正如上述所介绍的,经纬织物最终形成的2cm以内的捆扎纹是方形的,或是增大捆缝揪起面料的长度,则形成圆形的圈纹。中国古代的绞缬品大多使用的是丝绸面料,并且大多出土的绞缬文物捆缝的花型都能够保持在2cm以内,因而多形成方点状的方胜纹样。这种由捆缝技法形成的纹样防白外框均匀清晰,又因为制作者每次捆的手法力度不同产生具有细微差异的纹样,整体错落有致,体现着特定时代的审美情趣。
影响捆缝形成绞缬花纹效果的因素很多,如捆扎面料揪起的长度决定了花纹呈现或圆或方的形状;再有,缠线的部位决定着纹样的大小,而缠线的粗细、圈数则决定了防染面积的宽窄;捆缝的力度决定着防白花纹的清晰程度和色晕的效果;所捆扎时揪起的面料在捆扎之后形成的褶皱也会影响花纹的形态;绞缬使用面料的材质、轻薄状况等也都影响着纹样的形成和防染效果。
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多件红色或是绛紫的绞缬绢的方胜纹样均是用捆缝的方法制作而成的,其过程十分简单易操作。在丝绸上选取任意一点为顶点,用针挑起丝绸局部变成一个小的圆锥体,如雨伞合拢状,在顶点下方0.3cm(即整体花型<2cm)处用线环扎一圈或数圈,调整松紧打结,最终浸入染液染色即成。只是在排列方胜纹样时或对齐排列,或交错排列,致使点状纹样呈现出不同的布局和效果。
此外,除了单层捆缝外,双层捆缝和多层捆缝也是一种变形。缠线的方法也有变形,即等距间隔缠线、交叉缠线、平行缠线、螺旋缠线等,这样就会形成大小不同的套状纹样。例如前文提到的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赤地目纹绞缬上的回形纹就是以捆扎的方式在撮起的圆锥体上进行等距或非等距的环扎而形成的纹样。
(三)折缝技法
折缝技法,又叫做折叠缝技法,是先将织物面料进行对折或多次折叠,再按照设计好的图案以折叠形成的最外层的侧面进行多层平缝,然后抽紧线绳。折缝技法多用于对称、局部对称和连续性的绞缬纹样的制作,尤其是制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几何绞缬纹样时必须用到这种技法。折缝技法可以根据绞缬最终产生的纹样效果进行不同方式的折叠,这种折叠可以是规则的也可以是不规则的。规则的则有两角重叠对折和四角重叠对折等方式。通过一般的经纬折叠或是对角线折叠所产生的绞缬图案都是对称的,并且折叠之处正好是单个纹样的对称轴,使整个纹样图案通过折叠相互重合。这样既能够节省工时,又能够获得比较一致和完善的连续对称图案。此外,采用折缝技法制作绞缬时,织物面料折叠的层数还与布料的材质、厚薄因素有关。
折缝技法的典型实物是1969年阿斯塔那117号墓中出土的绞缬菱花纹绢,其缚结时的缝线还没有拆去,可看到折叠缝缀的方法。①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0页。图样见该书图版30。
折缝技法的特殊变形是使用夹板对已经折叠好的织物面料进行防染,是以夹板突起产生的力量代替缝扎抽紧的力量进行防染。这种夹板绞缬与夹缬是不同的技法,并非使用雕刻复杂、纹路精细的镂空印花夹板,而是使用简单图案的防染方式,与绞缬典型的折叠技法相结合,是一种特殊的折缝绞缬技法。前文提到的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湖蓝色地夹板绞缬绢幡所形成的实心方点纹,就是这种夹板折缝的极好例证。据实验资料,此类绢幡首先是使用典型的折缝技法,将其按照需要图案的疏散程度横向或纵向折叠两次,再将折好的丝绸自两边向中心对折成6叠24层,最终的宽度不一定与有方形突出的夹板的宽度一致,因为需要得到菱形的花纹,必须呈45度角斜夹。按照所需角度将折好的丝绸调整松紧用夹板固定,之后染色即成。②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90页。
(四)综合缝扎技法
前面三种绞缬技法一般都不是单独使用的,在绞缬的制作过程中,往往结合两种以上技法,综合缝扎技法的运用可达到防染色晕呈现精致图案的效果。
首先,1969年阿斯塔纳出土的棕色叠胜纹绞缬绢,就是平缝技法和折缝技法相结合的产物,网状纹上的防白斑点中心有清晰可见的针眼以及横向穿过每个菱形网状格眼的凸凹不规则间隔的丝绸直线褶皱,就是两种手法相结合的证明。这件叠胜纹绞缬绢利用的原理依然是针线穿缝与绞扎形成的防染效果,与平缝类似,折缝如果不借助平缝,就无法达到防染效果。据实验资料,这件叠胜纹绞缬绢就是沿着16cm的长的方向纵向叠做五层六折,然后在丝绸条外侧表面,以丝绸条面张开一侧的任意一个顶点为起点,在其表面平缝出“W”形的连续折线,每个折点的夹角约为90度,每个方向的线段上约有3-4个针脚,也就是6-8个针眼,每个针眼对应着叠胜纹上的一个白色晕斑。将这些连续的W形缝好之后抽紧打结固定,最后需要调整紧密的褶皱,使得他们间距适当,不会相互遮挡产生不必要的防染效果。③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3页。
其次,1972年阿斯塔纳出土的墨绿地朵花绞缬罗则是三种技法的结合。据实验资料,首先使用折缝折叠丝绸,折叠的方式是先将长方形丝绸面料纵向对折,再横向对折,沿横向对折的边再呈45度角向后折叠为八层,然后使用平缝技法,沿着横向对折的边,沿这条线段穿缝为弧形,拉到适当的松紧程度,采用捆缝技法最终将需要防染的部分捆住并打结,即成一个单位四瓣朵花。其他的朵花采用相同的方式折叠、平缝、捆扎。最终使丝绸表面结满捆扎的疙瘩,而背面成网状的褶皱楞格,格内丝绸向正面突起。此后需要浸水后染色,此朵花绞缬罗所采用的是特殊的双色套染,先整个放入棕色的染液中,之后正面向下用蓝色染液半浸没套染即成。④图详见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6 页,图6、图7。
总之,关于古代主要的三种绞缬技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对于其单位纹样特点来说,单层织物的平缝可以说是非常自由的绞缬技法,可以用于表现不规则的或是具象的绞缬图形,在理论上能够表现丰富多样的绞缬图案,特别是用于缝制封闭性的图形。但是由于古代绞缬中还没有发展出种类较多的具象图案,因此,这种具象的平缝方式在古代运用不多,主要在现代扎染中使用较多,古代的绞缬多是简单的图案。而折缝技法产生的几乎全是对称的规则图形,纹样类型并不局限于具象或是抽象,多是几何形状。捆缝技法由于其不确定性较高,制作者使用不同的捆缝方式,或是手力的松紧不同,或是捆线的粗细不等,制作出的绞缬花纹都不一致,因此捆缝往往产生不规则和抽象的纹样。
第二,从三种缝绞技艺产生的整体纹样效果来说,平缝技法的针脚主要产生点或是线,由点和线再组合成某一简单图案;捆缝技法会产生一个相对完整的纹样;而折缝技法则是产生位于不同平面的对称图形。
第三,对三种缝绞技艺的操作特点来说,平缝简单易上手,但耗时费力,缝扎方法要重复多次。此外,由于受到当时绞缬工艺本身的局限,只能提炼复杂图案的某些特征来进行表现,并没有绘画等艺术手法的表现力强。捆缝自由随意,能够展现工匠技艺的娴熟程度,专业性较强,也存在耗时费力的问题。折缝则是最节省工时的方式,一次缝扎的图案会显现于各层面料上,但需要一定的设计能力,具有一定立体空间感和设计思路的工匠才能够创造出精致的绞缬连续纹样。
五、绞缬技法及装饰效果的其他应用
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其他门类艺术的借鉴。绞缬技法在古代不仅成为重要的染色技艺得以广泛运用,还深深影响到同时代的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纹样及其审美,如唐三彩、石窟壁画、陶俑或木俑等的装饰。
(一)唐三彩彩釉装饰的应用
在绞缬艺术繁盛的唐代,绞缬工艺精湛的技术、朦胧迷离的色晕效果和丰富的纹样种类在同时代的唐三彩上都有较为相似的展现,尤其是三彩陶俑和三彩陶器的装饰色彩和图案都呈现出绞缬技法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说这是绞缬技艺独特的审美效果在唐三彩制作工艺上的应用和创新。
曾有学者指出:“应用染缬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会不影响到其他工艺部门。显而易见的是它和当时三彩陶器花纹彩色的相互关系。有些三彩陶的宝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于丝绸染缬后来才转用于陶器装饰的。”①沈从文:《谈染缬——蓝底白印花布的历史发展》,《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中国染缬史》一书中明确提出:“唐三彩中常见的花斑,和当时绞缬的技术处理有相通之处”,“在各地出土的唐三彩陶俑中,也可以看到穿碧绿色地小簇白花衣裙的女俑,这就是唐代‘青碧缬衣裙’的基本式样。”②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第162页。还有许多相关的论文对诸多具体的绞缬实物与唐三彩的陶俑和陶器之间的花纹进行了比较,判定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③参见刘素琼、梁惠娥、顾鸣、高卫东:《唐代唐三彩纹样与绞缬纹样比较研究》,《丝绸》2012年第2期;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
因此,综合上述说法,唐三彩的彩釉装饰对于绞缬工艺的应用主要表现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绞缬图案的相似,图案模仿绞缬花纹的视觉效果;二是色彩的相似。关于第一点,绞缬纹样中具有代表性的图案组成,如散点、花的纹样和网状纹样,在唐三彩陶俑的衣裙和器皿上都有所反映。其中,散点纹样和花的纹样中较为抽象的团花纹样具体体现在唐三彩彩釉装饰上,都能够表现为具有特色的“白斑加彩”④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的式样,只是散点与团花的大小与分布各有不同。即分布在唐三彩陶俑或器皿上的白色斑点,或均匀有序或分散随意,十分类似于绞缬工艺中的防染白色斑点的处理方式。而其他四瓣花、梅花或是网状纹的形式比较具体,是比较容易分辨的绞缬花纹,应用于唐三彩上则比白斑加彩的式样更为明确具体,如四瓣花以白色釉彩勾勒出完整的花瓣和花型,梅花以聚集的白斑加以体现,网状纹则以连续环绕呈菱形的白色小晕斑或是直接用白色的直线勾勒而成。二是色彩的相似主要表现在用色的种类以及色彩的组合方面。首先,根据学术界目前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的色谱分析,共发现红、黄、蓝、绿四大色系二十四种颜色,以白色为主形成防白花纹。⑤郑巨新:《中国传统纺织品印花研究》,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43-151页,第158页。唐三彩则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故称三彩,而白色为其主要的色彩过渡配色,这都是与绞缬工艺极为相似的特征。其次,唐三彩缤纷的彩釉组合,不同釉色之间的渗透效果和淋漓斑驳的色彩过渡,特别是围绕着白色斑点的晕散、流动的彩釉效果,与绞缬技艺所产生的富于变幻的色晕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①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
下面试以绞缬和唐三彩陶俑或器皿上图案的单元纹样来进行具体分析,通过点状、团花以及几何图案的纹样三方面,说明两者之间的共性和借鉴性。
1.绞缬点状纹样在唐三彩中的应用
首先,是利用绞缬捆缝技法产生的中心带有色晕的方点纹和圆点纹在唐三彩艺术中的应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绞缬工艺中有几种明确称谓的点状图案,即纹样轮廓相似的“醉眼缬”“鱼子缬”和“鹿胎缬”,它们是绞缬工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纹样。“醉眼缬”和“鱼子缬”的一般形态是白色防白方点中心带有色晕的小方块,外围明显的方点散布于布帛之上,在敦煌阿斯塔纳出土的绞缬绢中有非常丰富的实例。“鹿胎缬”则单位纹样较前两者稍大,且单位纹样边缘较为圆滑,多以外围不规则的圆形呈现出来,属于圆点纹之列。但是三者表现在唐三彩上几乎无法分辨,都是“白斑中加彩”的单元图形,呈散点状布局于陶器表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制作手法和两种技艺本身工艺特征的限制,绞缬纹样相较唐三彩纹样更为精细,正是因为彩釉烧制过程中流动的不可控因素,使得点状纹样与周围相互交融,单位纹样的制型扩大,外轮廓模糊且变化多样,其单位纹样的外围轮廓区分变得较为模糊,无法将某种白斑加彩的点状纹与“鹿胎缬”或“醉眼缬”“鱼子缬”明显的对应起来。以至于唐三彩在表现绞缬团花纹样时,同样也会使用这种白斑加彩的手法来呈现。
白斑中加彩是绞缬的点状纹样运用于唐三彩中的变形,每个单位纹样的面积大小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实物有1972年陕西礼泉县安元寿墓出土的三彩女立俑,该女俑所着服饰细腻写实,身着深蓝色地长裙,是典型的唐装式样,长袖、领口微扎,裙身上稀疏地布满白色斑点,这种白色斑点较大,且每个白斑的中心点有褐彩,②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其褐色与白斑之间、白斑与蓝地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色晕效果。虽然从纹样的比例和大小看,也有点类似于团花纹样,但是这件陶俑身上的白斑完全看不出花的形状,只是不规则的大斑点色晕,我们暂且认为这种纹样是制型扩大了的绞缬点状纹样在唐三彩中的运用。
绞缬点状纹样除了运用于写实性的三彩陶俑类外,也创造性地转用于三彩器皿之上,同样是以“白斑中加彩”的形式加以展现。例如黄冶窑出土的三足炉、三足洗等③图详见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73页图6-8。,在这些三彩器皿的留存残片中,我们能够发现,不仅在三足炉内壁的底部,有以同心圆的形式排列着的密集面积较大的白斑中点有褐彩的纹样,而且在炉外壁罐口的上腹也环绕着这样一圈散点纹样。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些白斑中加褐彩纹样的晕染效果极为突出,明显是先点上褐色釉,在高温焙烧中釉层熔融,白色和褐色彩点集中的地方进行了融合,这是利用铅釉易流动的特性所进行的彩釉装饰。与绞缬技艺防白晕染的制作手法和原理虽然有较大差异,但是其产生的效果却是极为相似的,产生出朦胧迷离,富于变幻的色彩效果。④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
其次,还有利用绞缬夹板防染产生的白色实心的方点纹样在唐三彩艺术中的应用,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实心方点是绞缬技艺捆缝技法中全捆扎产生的纹样。在此我们暂且以前文中提到的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一件夹板绞缬为例,湖蓝色地全白方框纹样,方框周边带有明显的晕染效果,此类纹样我们同样可以在唐三彩中找到实例。如有一件陶罐实物,其外壁上白绿褐三色斑点相互交融,白点周边有晕染痕迹,但是中心并无其他色样的点彩。还有一件无名的唐三彩人物女俑,其开襟上衣以深蓝色为地,上面有较大的白色晕染斑点,整个衣衫只有这两种色彩构成。①图详见刘素琼、梁惠娥、顾鸣、高卫东:《唐代唐三彩纹样与绞缬纹样比较研究》,《丝绸》2012年第2期,图4b、图4c。以上这两件唐三彩实物中的斑点虽然看不出是规则的方点,有些甚至交融看不清白斑的形状,但是确有晕染效果,可以视为绞缬实心方块纹样的变形应用。
2.绞缬花的纹样在唐三彩中的展现
首先是绞缬中对称的四瓣花纹样在唐三彩中的应用。前述1972年阿斯塔那出土的墨绿地朵花绞缬罗,这种四瓣花轮廓为正方形,十字对称。这种十字四瓣花纹在唐三彩的彩釉盘类器皿中出现较多,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瓣纹盘,其盘底为褐色,四瓣花位于盘底中央,几乎布满了整个盘面。花型的四瓣忽略晕染的效果后基本是对称的,白色釉彩勾深蓝边形成四瓣花型,花蕊由浅褐色釉彩点出,在白色花瓣内侧形成晕染的朦胧效果。②图详见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77页图19。色彩和花型之间相互浸渗的效果与绞缬工艺制作的朵花绞缬罗十分相似。还有一件唐三彩四瓣花盘与上一件有所类似,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是一件高足盘,但是其晕染感和色彩之间的渗混效果不如前一件明显。③图详见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77页图21。由此可见白色釉彩的流动性与团花绞缬绢的防染处理十分类似,因此这种三彩四瓣花型就是对于朵花绞缬纹样的模仿。但是,如果使用折叠夹缬工艺也是可能产生四瓣朵花纹样的,因此也不排除这种花纹是借用了夹缬工艺织物中的图形。
其次是绞缬中不规则的抽象散点小簇梅花纹样的应用。仿照《内人双陆图》中的绞缬小梅花纹样,唐三彩中也有抽象的小簇梅花纹样,但并非都是对称的,也并不只限于五瓣花瓣,只是基本呈现了梅花的样式。例如1955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王家坟村唐墓的女坐俑,该女俑身穿碧绿地小白花衣裙,这是当时流行的“青碧缬衣裙”的真实写照。小白花呈四瓣并有明显的晕染效果,晕染还延伸到突起的裙褶皱上,由于彩釉自身的绿色是由蓝黄两色调制,因此晕染的白色与绿色的交融处还有褐色和黄色的色晕。除了陶俑,还有几件唐三彩器皿,如黄冶窑出土的直径为15.5cm的唐三彩盖,深蓝地上饰有白色的五瓣梅花图案;有一件高5.2cm的三彩印花枕的枕面也有类似的绿地白花图案,形似于小梅花,花样中心以褐色点彩花蕊,朵花全部呈竖条状排列,规则整齐;还有黄冶窑出土的一件高6cm的唐三彩水柱和一件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唐三彩罐,一件蓝地一件绿地,白色梅花与上面提到的彩盖上的梅花基本一致,五瓣且中心有褐色点彩。④这三件唐三彩的图详见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74-75页。以上提到的三彩陶器的白色梅花都和周围的彩釉渗混,虽然花型是绞缬纹样中小梅花纹样的变形,但是从效果上讲与绞缬的晕染极其类似,可以视为对绞缬梅花图案的应用和模仿。
3.绞缬几何纹样在唐三彩中的应用
在《中国古代绞缬工艺》一文中,作者将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件唐三彩盖罐上的彩釉网格图案作为套色网纹缬的实例做了说明,并进行了具体的实验,得到了与唐三彩罐上纹样相似的绞缬花纹。⑤王予予:《王予予与纺织考古》,第82-97页。我们也确实能够发现,在唐三彩的彩釉图案中存在着网状纹样。王予予先生提到的1965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的高28.5cm的蓝绿两色菱形纹三彩陶罐,菱形纹的边缘有一周连续性的白色斑点,而且白斑较为均匀规则,在白色斑点的外围还有一周褐色的菱形边框。对比绞缬叠胜纹纹样,如1969年阿斯塔纳117号墓出土的棕色叠胜纹绞缬绢来看,这种出现在陶罐上的连续性的白斑状防染花纹可以通过缝绞技法制得,因此说这种白色联珠纹是对绞缬花纹的模仿就有了现实的根据。另外,在每个菱形纹内部,陶罐上都加有四朵白色小花。其中在绿格内小白花的芯部点出蓝色花蕊;在蓝格内小白花的芯部则点出褐色花蕊。不论是花蕊与绿地、蓝地间,还是花蕊点彩与白花间,都有十分明显的晕染效果。这些四瓣小花可能是对绞缬团花纹样缩小的变形。因此,这件三彩陶器上的网纹与花纹可能就是对绞缬叠胜纹以及花的纹样的借鉴,是一种组合性的借鉴,但在出土实物中,我们并未见到这样组合的绞缬纹样。还有一件唐三彩器皿藏于日本天理参考馆,高18cm,整个罐身为绿地菱形纹,各个菱形纹之间均以白色的宽条纹间隔,且在菱形纹内部装饰若干白色的小圆点,圆点周围施褐彩。①图详见方忆:《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期,第80页图27。这种白色线条状勾边的网格纹与出土绞缬绢实物上白色斑点形成的外围有所不同,有可能是当时制作陶罐的工匠对于绞缬白色斑点的简化,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直接借鉴了夹缬或是蜡缬的网状防白条纹。
综上所述,绞缬工艺与唐三彩的彩釉装饰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关性,而且唐三彩的彩釉图案是研究绞缬图案的参考资料和具体应用。
(二)石窟壁画等对绞缬花纹的应用
从石窟壁画等这些较为写实的艺术记录手法上,也能寻觅到对同时代绞缬花纹的模仿与借鉴。前文对此已经叙述得十分详尽,例如辽宁吉安舞俑冢壁画中舞俑的衣饰上的绞缬方点纹,敦煌壁画《张议潮出行图》中骑士衣着上的团花绞缬纹样,敦煌莫高窟五代第98窟东壁北侧《回鹘公主供养像》的公主裙身上的大团花纹样,敦煌莫高窟初唐第217窟东壁北侧的《观音经变图》中菩萨所穿长裙上的绞缬点状纹样,以及山西汾阳圣母庙圣母殿北壁的《乐伎弹奏图》壁画中乐伎所着的绞缬团花纹样的衣裙等,这些都是石窟壁画艺术对绞缬工艺纹样的借鉴和模仿。
总之,不论是唐三彩,还是石窟壁画,以及其他工艺的何种形式,与绞缬工艺对照比较,它们在图案造型和构图特征上极为相似,其中所展现的审美和色彩效果,可以说是借鉴了绞缬技法的表现形式,这些唐三彩和石窟壁画中人物的服饰纹样或是生活用品上的纹样显然就是当时绞缬服饰纹样的再次体现,是绞缬技法和装饰效果在唐三彩和石窟壁画中的间接反映和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