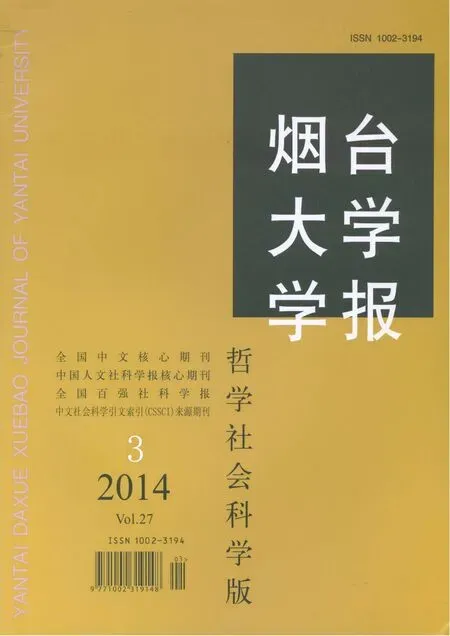真实与虚构的交融
——论布莱德伯里《历史人》的叙述技巧
程淑娟;刘一洁
(1.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91;2.中国农业大学(烟台),山东 烟台 264670)
《历史人》①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历史人》,程淑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以下引自本书的内容只在正文中注明页码。无疑是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基于它的突出地位,国内外学者早已展开研究,并在理解上形成了各持己见的局面。如在作者对霍华德这个人物形象的态度上,托德认为布拉德伯里塑造了一个为人所不耻的反面角色,②Richard Todd,“Malcolm Bradbury’s‘The History Man’,The Novelist as Reluctant Impresario”,in Dutch Quarterly Review of Anglo - American Letter,Vol.11,No.3,1981,pp.162 -182.瞿世镜用“厚颜无耻”对其加以描述,③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戴维·洛奇更是为这样一个打着集体革命口号四处招摇撞骗的人最终没有受到惩罚而鸣不平。④David Lodge,“Lord of Misrule”textit The Guardian,Saturday,January 12th,2008.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8/jan/12/fiction1,2013年5月12日。而与这一论调相反的是,管南异和丁威认为,尽管霍华德行为恶劣,作者却感觉离心目中的霍华德非常近,⑤管南异在《你往何处去——评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长篇小说〈历史人〉》(《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29-34页),以及丁威在《谁是真正的历史人物?——布拉德伯里学院派小说代表作〈历史人物〉解析》(《山花》2011年第5期)中都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同时在小说语言中暗藏着对霍华德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地挣扎的同情。”①管南异:《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
众说纷纭、理解各异,这正是《历史人》的魅力所在。过于简单的情节设计、杂乱无序的内容罗列、超然淡定的书写笔调、有悖常理的故事结尾,让小说自一出版便争论不断。它激怒了传统道德家,更让女权主义者愤愤不平。然而,小说内涵的不可穷尽很大一方面是源自布拉德伯里高超的叙述技巧:他为杂乱的内容套上有序的形式,形式与内容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巧妙地运用多重叙述声音,彰显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他一反常态地运用现在时态叙述,并用停顿、延缓、分流等技巧打破时间的线性运动,丰富了时间的呈现形式;他运用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角度,力图营造摄像机般的真实,然而读者无法进入人物的内心,也就无以安置自己的同情。然而在幕后,作者又通过叙述氛围的营造与艺术形象的选择传递着自己的道德诉求。高超的叙述技巧让原本简单的故事显得杂乱而扑朔迷离,而读者为了挖掘事实真相,不断地游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这种真实与虚构的交融正是小说带给读者的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一、形式上的有序与内容上的无章
无论是情节的设计还是语言的运用,甚至是人物的安排,小说都力求做到规范有序,达到小说形式上的条理,从而获得作品的“文学性”。故事从霍华德家秋天的聚会开始,在他们冬天的聚会中结束,描述了三个月里发生的故事。然而尽管相隔短短一学期,却是物是人非。在这个学期里,激进运动不断、革命思潮迭起。这里有夫妻感情的破裂、师生关系的断绝、学术界的枯燥无聊、机会主义分子的尔虞我诈,更有传统道德家的茫然失措、割腕自杀。尽管事件纷杂,作者却用两个类似的聚会一前一后将它们串联起来。纵观两次聚会,同样的发起方式、类似的人员组成、不变的混乱场景,甚至发生在客卧里不同的人实施的类似的自杀企图,都让原本毫无关联的历时事件具备了一丝规律感。小说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转眼,又是一年的秋天。人们都回来了。夏季里的萧条景象已经结束。在暑假里,报纸内容萎缩,就连时间本身都似乎暂时地萎靡不前了。然而报纸重新变得厚重而充实起来;事情似乎又开始发生。从科夫岛和赛特,波西塔诺和列宁格勒回来的人们在停车场停下轿车和野营车。……天空时阴时晴,电话铃声阵阵。于是,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一对名叫科克的夫妇决定举行一个聚会。(p.1)
而到了结尾的第十三章,作者刻意重复了第一章的叙述方式,首尾呼应,为纷繁复杂的叙述内容制造出形式上的条理性,前后形成张力,使文章自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现在又到了冬天,那些回来的人们又该离开了。那个激情不断上涨、紧张局势加剧、罢工日益累积、报纸里尽是愤慨的秋天,结束了。圣诞节要来了。白鹅变肥了,报纸变薄了,事情似乎不再发生。人们把车停在行车道上,开始装东西。很明显,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在这个节日假期的空档去波西塔诺或者是公共档案局,去莫斯科或者回家找母亲。……电话铃声阵阵,传递着圣诞节的祝福。科克夫妇,那对众所周知的伴侣,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决定举行一个聚会。(p.223)
作者还刻意让芭芭拉的语言在两次聚会上前后重复,而这种重复也犹如一根纽带,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关联感。在准备秋季聚会时,芭芭拉朝楼上喊道:“安妮,我和霍华德在计划聚会的事情。我想你是否能给孩子们洗一下澡?”(p.6)而三个月后,在准备另一场聚会时她用类似的方式喊道:“费利西蒂,霍华德和我正在忙着计划一个聚会,我想你是否介意今天晚上给孩子们洗洗澡?”(p.225)而在两次聚会上,她会用同一个问题作为谈话的开场白:“你是用什么方式避孕的?”(p.84,p.232)
从叙述语言到情节设置再到人物安排,作者都力图营造一种井然有序、首尾呼应的感觉,从而为历时的偶然发生增添一丝规律感和必然性,而在人为的有序背后却是内容上的杂乱无章。《历史人》的故事发生在激进的七十年代,以霍华德家的聚会为主线,讲述了发生在这对夫妇周围的故事,情节简单、叙述琐碎,囊括了那个激进运动迭起、性解放思潮云涌的年代,可谓是那个时期的万象图。小说开始部分就清晰地表明了叙述内容的杂乱无序。作者描述的对象毫无规律与顺序可言,短短几行,囊括了报纸业、旅游业、越战、商业、总统大选、枪战、避孕药等等,更为滑稽的是将政治与避孕器相提并论,而这种内容上的杂乱无章自始至终贯穿着故事的发生。整部作品,犹如霍华德家的聚会,也如那个激进变革的年代,纷繁杂乱、毫无头绪。作品用人为的条理呈现出马克思斗争哲学与“泛性论”两面旗帜保护下的七十年代。人为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强烈的冲突正是作品提供给读者的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二、多重叙述声音与难以捕捉的真实
当代叙事理论普遍认为,叙事只是构筑了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能描述它们的客观真实,《历史人》一书便是这一叙事模式的极佳代表。与宣称作品真实可靠、力求叙述忠实客观的传统作家不同,布拉德伯里自一开始便与读者玩起了文字游戏,通过前后矛盾、似是而非的叙述将读者拉进了亦真亦幻、真假难辨的世界。
在小说开始前的“作者按”中,布拉德伯里提到要将这部书献给毕梅斯,并说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法兰克福机场,当时“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而“他”正在查询行李。毕梅斯本是小说中一个虚构的人物,霍华德的同事,在秋季聚会时曾在客卧中企图自杀,而在这里作者却把这个虚构的人物拽进现实,使“他”游进作者“我”的日常生活,似乎给后面的叙事增加了一丝真实的味道。作者接着写道:“正如历史学本身一样,这本书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完全的虚构。”这也迎合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强调对历史的文本化与对文本的历史化。作者言下之意也就是说,尽管这是一部小说,一个虚构的故事,却有着跟历史学同样的地位。历史文本是对客观事实的主观叙述,这部小说跟历史一样,尽管是对真实的虚构,也具有必要的客观真实性,力求公正地呈现那个激进的年代。到此为止,作者似乎都在宣扬其作品的真实可靠。然而接下来他笔锋一转,说这里的沃特摩斯大学跟现实中的毫无关联,这里的1972年也跟现实中的1972年毫不相干,而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情节安排等等纯属虚构,而“我”那天也不曾去参加什么会议,“即使我去了,飞机上也没有叫毕梅斯的,当然,他也没丢失行李。”(扉页)这段叙述将读者刚刚建立起的对作者的信任感彻底推翻,使他们从假定真实的描述回到虚构的小说世界,一切尽是虚假、谎言,而客观的发生与存在变得那么遥不可及。最后,作者说:“其它在这里说的,当然都是真的。”然而在经历了前面的信任与被骗之后,略显成熟的读者会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是真的?在满纸前后矛盾、出尔反尔中间,还有什么是真的?在故事开始之前,作者似乎就预设了小说真假难辨的氛围,而这种写作方式还贯穿小说整个叙述过程,使读者对真实的把握略显艰难。故事里的人物会把撒谎当家常便饭,而对于他们的谎言,作者在叙述上也有意隐瞒,夸大表象而忽略真实,读者只能凭借明辨是非的“慧眼”来挖掘故事背后的真实。
主人公霍华德经常撒谎,也擅长撒谎,用他臆造的多重叙述声音赋予谎言以真实价值,而作者非但不去拆穿,还在叙述时刻意隐瞒,让事件显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邀请“种族主义者”曼格尔来校讲学是霍华德激进事业的旗帜性胜利,而对曼格尔的邀请过程则是他假借多重叙述声音精心设计的圈套。开学伊始,他走进学院大厅,找到同事莫伊拉,播下了谣言的种子。“霍华德环顾四周,朝莫伊拉靠过去,用很小的声音说:‘人们传言说曼格尔要来这里讲学。’”(p.59)而到了当天中午跟学生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转而对激进的学生说:“‘莫伊拉·米立金今天早晨告诉我说,曼格尔可能来这里讲学。’”(p.69)到了晚上,在霍华德家举办的聚会上,他对同事麦金塔仕继续散播,说曼格尔要来讲学,而在聚会后又借麦金塔仕之口向弗洛拉说:“‘那个新来的麦金塔仕昨天晚上告诉我,据说曼格尔要来讲学。’”(p.112)随着谎言的散布、人员的扩大,谎言产生了三人成虎的效应,在人们的口中变成了一个既定事实,具有了必然性与不可阻挡性,而他散布的谎言也滑稽地流回到了他自己的耳朵:同事罗格·芬迪在课间问他:“霍华德,你听说关于曼格尔的事了吗?”(p.128)而这时的霍华德则显得无知而单纯,并建议罗格制止事情的发生。他转而借罗格的名义对事情再次转述,在课后对摩洛哥学生哈米什说:“罗格·芬迪告诉我说曼格尔要来做讲座,就是那个支持种族歧视的人。”(p.138)在学院会议之前,霍华德将自己的谎言进一步升级,而对于霍华德的这次布谎,作者描述地极为简单,并对重要信息做了刻意的删减。在课前与费利西蒂的谈话过程中,霍华德匆匆走了出去。“霍华德沿着走廊,来到系办公室。恰好是秘书们的咖啡时间,她们都到工会去了。于是他在留言机上口述了一条信息,又沿着走廊回到自己那个长方形的房间。”(p.125)至于他留了什么信息,作者并没有说,只是到学院大会的时候,邀请曼格尔讲学的条款已经写进了会议议程里。对此系主任马文教授很是不解,因为自己压根没批准过这样的议程,而院长助理侯小姐说,信息就在留言机里。通篇作者只讲到了霍华德到系办公室留过信息,具体什么信息读者不得而知,而根据掌握的信息以及霍华德的一贯行径,作者不难推断出事情的真相。至此,霍华德一手炮制的多重叙述声音发挥了它原本没有的功能,将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变成了既定事实。
对于亨利在聚会那晚的遭遇,作者的描述更为隐晦,而这里运用的多重叙述声音模式让真相在不同的人口中演变成不同的版本,从而为读者挖掘客观事实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对于自己那晚的行程,亨利的叙述是他从学校回家去接麦拉,却发现对方已经开车走了,于是不得不步行回城里参加聚会,而刚一到霍华德家就被狗咬了,他去客卧换袜子的时候想去开一下窗户,结果胳膊就伸进了玻璃里。至于他如何把胳膊伸进了玻璃里,他说是他滑了一下,然后拿胳膊去维持平衡,就推到了窗户上面。这个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于是他后面又追加了一句,说地上可能有块儿冰。到了霍华德口中,亨利的遭遇则成了一个意外,一个偶发事件。他刻意地通过“偶发性”来剥夺亨利的心理权利与思维意识。在他看来,亨利生来就与不幸相伴,如果一根树枝烂了要掉下来,它也会等着亨利从下面走的时候掉下来。与他相反,心理学教师弗洛拉则深入研究亨利的行为动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反对自我的过激行为、一个微型的自杀企图。在作者的叙述模式中,亨利那晚的行程、心理和思维变得更为丰富而神秘,而作者又刻意留下几处破绽,为寻找真相的读者透出一丝曙光。霍华德在筹备聚会时并没有准备冰,因此客卧的地上也不可能有冰块出现,而在聚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当亨利与霍华德到酒吧聊天时,酒吧女卡洛伊对亨利评价说:“毕梅斯先生是我最好的顾客之一,……每天晚上都来。身体很棒,我是说昨天晚上。”(p.175)这也就推翻了亨利前面对自己行程的叙述,他到霍华德家之前并非在赶路,而是待在酒吧里。
前后矛盾的“作者按”、让谎言与真实不断转换的多重叙述声音,娴熟的语言技巧为作品增添了分量,也令读者意识到,语言只是一个表象,有很多的虚假成分,而成熟的读者就需要穿过语言表象,挖掘深藏于内的客观真实。
三、形式多样的时间呈现
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别尔加耶夫将时间分成了三种类型: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存在时间。宇宙时间是环形的,日夜之交替、季节之轮换,都具有循环性;历史时间是直线型的,对个人或群体来说,这种直线性可以是向上运动的发展,或者是向下运动的退化。第三种是存在时间,表现为一种垂直线。①谭君强:《叙事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在《历史人》中,作者在刻画历史时间时运用反常的现在时态叙述,加上停顿、延缓、交叉等时间策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时间的呈现形式,同时兼顾宇宙时间,创造出事件发生的循环轮换与不可避免,打破了读者的定向思维,产生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
“我常到这里买菜,回家煮给女儿吃。在这里,我能通过种植者,直接了解到蔬果的情况。”林熙在3年前当了妈妈,如今为女儿准备饭菜,她尤其注重食材的来源是否安全。
一般的叙事大多采用过去时态,因为故事讲述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各种时态的综合运用能让读者建立清晰的时间脉络,叙述也会显得从容不迫、井井有条。然而在《历史人》中,作者在叙述这三个月里的故事时却坚持不懈地使用现在时态,一切的发生都是现在,读者感受到的也只有现在,“叙述者的声音听起来更像足球场上的现场直播。”②管南异:《你往何处去——评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长篇小说〈历史人〉》,《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同时句子结构简短,加上大量动词的运用及过于细致的描述,使时间在这里失去了自然顺畅的流动,而是缓慢的、碎片式的组合。拿霍华德开车为例:“他打开驾驶侧的车门,钻了进去。他点了两次火才发动了引擎。他前后挪动汽车以腾出空间,然后他开出了广场,向下穿过山上拥挤的车流,回到他们那排屋子前。”(p.12)就故事情节而言,这一发生本身意义甚微,大可用“霍华德去停车场把车开了回来”代替,然而作者独特的叙述形式使时间的流动演变为一个个琐碎的动作,而持续的现在时态除了增强描写的生动性外,也传递出了更为深层的信息。正如F.詹姆逊所说:“……我们这整个社会的体系已经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这种变化是会把从前各种社会形态保存下来的传统抹掉的。”③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P.Brooker,Modernism/Postmodernis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2,p179.与过去时态相比,现在时叙述确实产生了“触目”的效果,却失去了“惊心”的功能。它让读者在一系列琐碎的动作中不知所措:尽管一直处于现在,却浮在表面,把握不到其中的内涵。
时间在永恒的“现在”中缓缓流动,读者对时间的判断也只能来自人物动作的交替变化,然而作者还会让时间停顿下来,产生强烈的“静态画”效果。例如作者用肖像画的形式对霍华德与芭芭拉进行刻画,把两个人物恰当地放进了满目疮痍的背景里。
先是霍华德,个子矮小、体型端庄;他那萨帕塔式的小胡子从嘴角垂了下来;头发已经变得稀薄,因此都往前梳着;坚毅的下巴向前伸着,一种气愤而盛气凌人的表情。在他的旁边是好妻子芭芭拉,穿着束腰长袍、个子高大、头发淡黄。她一手拿着热水瓶,一只手微微抬起,紧握成拳头。(p.51)
在文中,这样的叙述不止一处。时间在这里停顿了下来,而时间的静止带给读者的是强烈的画面感。
“延缓”策略的运用又使时间产生逆向流动的趋势,让叙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穿梭。《历史人》共十三章,前十一章的时间跨度只有两天,而在第一章霍华德夫妇就做好了聚会的准备,直到小说的第五章聚会才如期举行。在这一部分的叙述中作者充分运用延缓的策略,回忆了霍华德夫妇的生活变迁以及沃特摩斯大学的发展历程,包括霍华德与芭芭拉的出身、他们的大学生活、霍华德工作后彼此的状态、沉闷的婚姻生活、芭芭拉的出轨、霍华德更换工作以及后来他们的转变。作者毫无征兆地将读者拉回过去,开始长篇大论,时间也从现在一下子倒流回过去,而当读者终于在时间的流动中找到坐标的时候,作者又毫无准备地回到现在的讲述。如第三章在回忆霍华德的发展历程过程中,作者笔锋一转,“‘你害怕她什么?’弗洛拉问道,她整个的体重压在霍华德身上,乳房正对着他的脸。”(p.53)叙述一下子跳到了弗洛拉的床上。“延缓”技巧的运用让读者游荡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通过对不同阶段信息碎片的收集,整理着自己对事实的认识。
不仅如此,作者还让时间在叙述中交叉、分流,力图呈现共时时间中的不同发生。在叙事作品实践中,这本不足为奇,然而作者独树一帜,在场景叙述的线性时间中创造了时间分流的效果。学院大会之前,社会学系的教工们在餐厅里吃午饭,作者对这一场景的叙述主要采用对话的方式,然而通过谈话内容的变化,尤其是麦莉莎·托道夫貌似不着边际的插话,使线性时间呈现出分流的状态,从而提供了同一时间段里的不同发生。当时教员们正你一言我一语、热火朝天地讨论曼格尔来校讲学的事情,然而在这一话题中间夹杂着麦莉莎不着边际的插话。她时而谈到《易经》、时而谈到星座、时而又讲到帕金森定律。她的语言零散地分布在“曼格尔讲学”这一中心话题中间,而同事偶尔的回应也说明在时间上她的谈话是与当时的中心话题共时发生的,只有把她的话从曼格尔问题中挑出来,才能还原其完整性。如“‘耶稣是摩羯座的’,麦莉莎·托道夫说,‘你是什么星座,亲爱的?’”)间隔几行之后,“‘我不相信星座’,麦金塔仕博士说,‘那样的话,如果母亲记忆力好,孩子就有优势了。’”再间隔几行,“‘难道你什么都不相信吗,亲爱的?’麦莉莎·托道夫说。”(p.151麦莉莎的语言零散地分布在中心话题周围,形成两个话题的并行前进,也达到了对叙述时间别具匠心的呈现。
现在时态叙事,停顿、延缓、交叉等策略的有机运用,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时间,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同时作者兼顾宇宙时间,从小说一开始“转眼,又是一年的秋天。”一个“又”字尽显季节之轮回,而到了最后一章的开头,“现在又到了冬天”,更加体现了秋去冬来这一万古不变的时间轮转。宇宙时间是永恒不变的,而故事里的历史时间却时而流动、时而静止、时而交叉,一切都停留在现在,一切也归于现在,读者在感受时间多样的同时,也体味着无从把握的现在。
四、独特的叙述视角与读者无以安置的“同情”
马克·柯里认为,作者通过对叙事视角的把握控制着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同情,并列出了产生同情的两类情况。“(1)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2)当我们发现一些人由于不能像我们一样进入某些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对他们做出严厉的或者错误的判断时,我们就会对那些被误解的人物产生同情。”①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然而布拉德伯里给《历史人》设定的叙述视角让读者难以走进人物的内心,最终导致的是作者在阅读过程中找不到认同感,也就无法安置自己的同情。
作者通篇使用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模式,即我们只能看到主人公在我们面前的表演,作者避免直接的道德评论,更不会带领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漠然的口吻、超然的笔法,给故事一种超脱的叙述氛围,而持续进行的、不加解释的叙述,使读者仿佛跟随一台隐藏的摄像机,追踪着霍华德的行踪。读者获得的是故事对其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却无论如何得不到与小说角色在心灵上的交流。即使是在主人公霍华德独处的时候,作者的叙述也仅仅停留在行为的表面。聚会过后,清晨起床后的霍华德走进了卫生间:
他拉开开关。电灯与剃须刀、光明与噪音同时出现了。他的脸出现在遍布手印的镜子里。在清晨凄冷的城市光线里,他审视着自己作为人的状态。憔悴而消瘦的脸庞、如灯丝般的胡须从镜子里看着他。他说道:“天啊,又是这样的你。”他的手指伸了上来,把这些奇怪的面部肌肉整理成原先的样子。他让剃须刀滑过脸庞,整理着自己面前的这个形象,细心地雕饰着胡子的边际,将侧鬓的线条修剪得干净利落。他关上剃须刀。他能听到楼下孩子们肆无忌惮的大叫声。自己一直修饰的形象苍白而抽象地映照在前面的镜子里。他轻轻拨动着它们,希望给它们输入真正而现实活力的基本光芒。没有回应。他拿起一瓶带有男士标志的剃后乳液,拍打了一些在脸颊上。他关上镜子上方的灯,脸庞消失了。(p.98)
通篇的叙述如上段所示,读者最多能获得人物的视觉、听觉感受,却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更无从知晓他们的想法。这或许是作者为避免道德争议而有意为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外表道貌岸然、内心令人发指的龌龊小人,而马克·柯里也讲到了如若进入一个病态的心灵,或是一种扭曲的动机可能产生的道德危机:
很多当代小说正是通过对道德上令人生厌的人物表示同情而引起对作品的道德之争的。……这些小说就是通过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创造了读者与道德魔鬼间的亲近关系。由于这种亲近关系,读者往往直到发现小说中另一些代表正常心理的人物的判断时,才发现自己由于技术原因而站到了自己道德立场的反面。①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第23-4页。
第三人称外视角的运用很好地避免了对霍华德的内心描写,而“浮在表面”的书写方式让读者只能停留在话语的层面,很难潜入意义的深处,从而避免了读者被带入歧途。曾有学者认为作者感觉自己离笔下的霍华德很近,并在语言上暗含着对其挣扎的同情。布莱德伯里确实说过:“虽说是我创造了霍华德·科克,但没有一个角色能如此自然地进入我的写作。在每一个现代校园里,他是一个熟为人知的形象——如果你像我一样,也在六十年代的英国、欧洲和美国兴起的新型玻璃混凝土大学中执教的话。”而他对霍华德评价说:“他保持激进、保持魅力、保持诱惑,总是站在学生的那边,反对给他发工资的法西斯机构,反对超过三十岁的人,尽管自己已经三十五岁。”②Malcolm Bradbury,"Welcome back to The History Man".http://www.malcolmbradbury.com/fiction_the_history_man.html,2013年4月10日。由此推论,作者所说的“近”应该是“熟悉”的意思,说明他周围不乏这样的人,而并非心理上的亲近与认同。对于作者自己,他评价说:“我是一个绝对的自由派,传统、英国型的自由派。”③Malcolm Bradbury,"Stepping Westward - Unpublished Afterword".http://www.malcolmbradbury.com/fiction_stepping_westward.html,2013 年5 月12 日。作者本人在小说中也隐约出现过:当霍华德到文学院找凯琳妲小姐的时候遇到了“表情犹豫、皮肤黝黑、头发凌乱”的文学系讲师,戴维·洛奇与海瑞特·伍德都将这个作家跟布拉德伯对应在一起,而这样一个崇尚传统伦理道德的角色与霍华德大相径庭,更谈不上对他的认同。
小说中,停留在“现在”的杂乱被有序的书写所呈现,已经令读者不知所措,而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模式对于读者的理解无疑是雪上加霜。它如浮力般将读者推到文字表面,使他们停留在虚构的叙述中,而读者只能通过作者隐约露出的破绽来把握虚构后面的真实。
五、作者的隐形控制与潜在道德指向
布拉德伯里一贯崇尚文学的道德价值,从最初的《吃人是错误的》到后来的《兑换率》再到《克里米纳博士》,无不担负着他沉甸甸的道德关怀,而《历史人》也不例外。戴维·洛奇评价说:“这些小说在一个层面上是对道德和哲学严肃的——实际上是悲观的——反射。”①David Lodge,"Introductory Essay",2010.http://www.malcolmbradbury.com/essay_fiction.html,2013年4 月10日.布莱德伯里本人也对《历史人》评价说:“我一直认为这部小说的特征之一(至少是在英国)就是它有非常‘作者化’的形式,也就是说,在这里伟大的巴特的‘作者之死’并没有真正地发生。”②Malcolm Bradbury,"The Novelist and Television Drama",1992,May 5th.http://www.malcolmbradbury.com/tv_the_novelist_and_television_drama.html,2013年5 月12日.他否认这部小说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个体,而是作者独特视角和立场的体现。然而小说第三人称外视角叙述拉开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打破了读者通过进入人物内心而做出价值判断的传统评判模式,那么作者的道德指向又是如何传递给读者的呢?
故事总能以特有的方式控制着读者,以制造我们的道德人格,而“小说作品是披着精心制造的外衣的论辩”,可以说,“小说是作者的一种口技,而口技表演者自己的论争则在傀儡的假声音中藏了起来”③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第23页。。在《历史人》中,布拉德伯里自己的论争则表现为对叙述氛围的营造和对艺术形象的选择,而他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引导着读者的思维倾向。也就是说读者在跟随作者的摄像头看故事,而在故事发生的时候读者能看到些什么以及看完之后产生什么样的心情是由作者通过叙述技巧所控制的。首先,在氛围的制造上。陪伴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并非艳阳高照、晴空万里,而是阴雨连绵或大雨倾盆。从故事一开始,雨便成了人们生活的陪衬:十月二日开学的时候,“雨水沿着窗户流了下来。整个屋子沉浸在湿湿的昏暗光线里。”(p.9)第二天聚会过的他们从睡梦中醒来,“大雨倾盆,将对面破损房屋的砖瓦结构弄得肮脏、乌黑,也倾泻在科克家那不结实的排水沟里。”(p.98)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发生都有雨的陪伴,而作者也不遗余力地借雨渲染着摧毁一切、打倒一切的气氛:霍华德是在雨中跟凯琳妲搭讪并实施引诱的;霍华德与弗洛拉是在雨中对同事亨利的行为动机反复揣摩的;霍华德也是在雨中把学生卡莫迪赶出了教室。在霍华德看来,装在“历史防腐器”里的凯琳妲、亨利和卡莫迪正是应该被革命的对象,然而革命行动在倾盆大雨的衬托下却失去了应有的正义感与公正性,相反,它让读者产生了对弱者也就是被革命对象的同情。
作者在推进故事发生的同时,也有意地选择进入读者视线的艺术形象,从而巧妙地控制读者的价值判断。霍华德住在城里贫民窟拆迁后留下的房子里,“那原本曾是一个标准而优雅的半圆,然而,一系列的爆破犹如牙医拔牙般将一座座房屋销毁,现在还立着的也已经无人居住,屋顶破碎,窗户空洞。”(p.11)他们附近的购物区,“在灯火通明的通道墙边,四处是人的粪便。”而超市里,“罐头食品与马桶交相呼应。”“一个枯竭了的喷泉里面堆满了垃圾。”(p.13)霍华德去上班的时候要经过一片破败的维多利亚街区,里面肮脏凌乱,到处是拆除的标记,而主干道的沿线有石匠们的屋子,里面有他们制作的“墓碑样品”。(p.106)大学里也不例外,里面有“阴茎般高耸的烟囱”,(p.62)马文教授的办公桌大得足以放下“一口棺材”,(p.208)而学生们“犹如一群有着严肃的、不可猜测的目的的蚂蚁”。(p.65)警车、挖土机、打桩机、喷气机、战斗机伴随着故事的发生不时地出现在读者的视线里,更增强了凌乱、破亡、颓废、瓦解的气氛。
与此相反,作者对过去的描述则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十年之前,这片土地是一个和平、牧歌式的伊甸园。成片的庄稼和成群的奶牛围绕在壮丽的沃特摩斯城堡周围。”(p.63)在这里,孔雀昂首阔步,学生趾高气昂,而那时经常是阳光明媚,到了夏天,他们在通幽的小径里接受辅导,而满怀敬意的园丁在旁边修剪枝叶。然而,十年的历史进程将这里变成了现代的智力工厂,里面尽是破坏一切的热情和学术思想的贫瘠。布拉德伯里曾经说:“《历史人》描述了六十年代解放论者的消亡和学生革命运动时代的凋谢。”①Malcolm Bradbury,"The Novelist and Television Drama",1992,May 5th.http://www.malcolmbradbury.com/tv_the_novelist_and_television_drama.html,2013年5 月12日.确实,文中反面、消极的意象无不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消亡”与“凋谢”,而正反两种意象的对比也流露出了作者对现在的抨击以及对过去的眷恋与渴望。
正如布斯所言:“只有不成熟的读者才会真正与人物打成一片,完全失去距离感,因而也失去所有的艺术经验的机会。”②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200.身为批评家、作家与大学教授的布拉德伯里将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叙述技巧的试验田,娴熟地运用叙述技巧拉开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读者为探究真相便不断地游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这种游荡不仅指出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道德鸿沟,也显示了成熟的叙事审美经验的特征。阅读这部小说时,假如抛开叙述技巧而单方面地探究文本内涵,便失去了小说的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