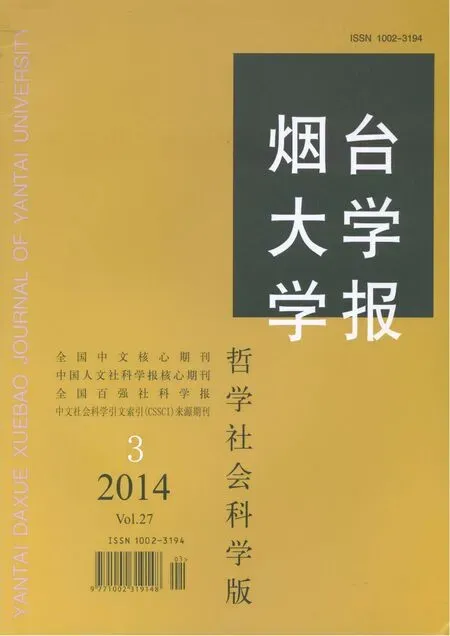再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成立
樊文礼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烟台264003)
再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成立
樊文礼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烟台264003)
“唐末五代代北集团”概念需要进行历史性考察。第一,“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并不影响代北集团的是否成立;第二,代北集团是一个包括沙陀、昭武九姓胡人、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多民族结合体;第三,代北集团与唐朝统治者存在着“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关系,集团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其与唐朝统治者“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过程。
代北集团;多民族结合体;互为作用;资源互利
十几年前,笔者曾提出了一个“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概念,认为“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政治集团,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我们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这一集团在唐末以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为号召,在五代前期则以李唐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是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政治团体。”五代五个中原王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这一集团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这一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并进而指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并进而统一北方乃至全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唐以前的匈奴、羯、鲜卑,唐以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是事例。但是,像沙陀这样其内迁人口不过万余的西域小族,却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地方割据政权(李克用河东割据政权、北汉小朝廷)、三个封建王朝(后唐、后晋、后汉),主宰中国北方或北方局部地区近百年之久(自883年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至979年北宋灭北汉),在历史上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如此,其他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往往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但在沙陀政权中,却看不到这种现象。笔者以为,沙陀人之所以能够以一个基本人口不过万余的小族建立国家乃至统一北方,关键在于组建了一个代北集团。而其所以没有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是因为代北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①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2页。这一概念提出后,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王小甫先生就认为:“唐末沙陀其实并非以外蕃族群征服入主,而是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沙陀固然是其统治集团核心,但未必有什么‘多民族结合体’的代北集团。而且,诸蕃群体间的关系性质也很难用来说明沙陀代兴后统治者和社会群体间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②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载《唐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王小甫是国内知名学者,他的观点在学界颇有一定影响,因此笔者拟就其提出的上述质疑,予以进一步论述,并继续向王先生请教。第一,“并非以外蕃族群征服入主,而是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的势力能否称之为“集团”;第二,以沙陀为“其统治集团核心”的那个集团是不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第三,“沙陀代兴后统治者和社会群体间”存不存在“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
一、“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的势力能否称之为“集团”
所谓“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当是指唐末李克用河东割据政权和五代后唐王朝的兴起和建立。诚然,李克用河东割据政权和后唐沙陀王朝都“并非以外蕃族群征服入主”,而是在沙陀人内迁之后,经过数代人七、八十年的努力经营打拼,不断壮大势力,最终以地方藩镇的身份崛起代兴的。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沙陀人就归附于唐朝,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府州性质的金满、沙陀二州都督府,隶属于北庭都护府。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北庭都护府被吐蕃攻陷后,沙陀人降附吐蕃,被东迁至吐蕃占据的甘州(治今甘肃张掖)一带地区。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由于受到吐蕃的猜忌,沙陀人又举族内迁附唐,先后到达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和代北地区(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到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沙陀首领李克用被唐朝廷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又过了40年,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
王小甫认为,唐末五代的沙陀人“也经历了塞外(外蕃)——代北(内蕃)——雁南(边州)的转移过程”③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3页。。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塞”,指边塞、边界。“塞外”,指边界以外。那么,唐朝的边界以何为标志?王氏曾论及两点:一,“都护为边州的延伸”;二,“都护兼具边州功能”;并说:“唐朝边州官僚体制在北庭府界内是深入有效的。”④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11-13页。“北庭府界内”,当然不仅仅是指北庭都护府治所之内,而应该包括北庭都护府统辖区域之内。也就是说,边州和都护府都是唐朝边界的标志,边州、都护府界内,也就是唐朝边界以内。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如上所述,沙陀人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归附于唐,唐以其部落设置了羁縻府州性质的金满、沙陀二州都督府,隶属于北庭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设置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它的前身为金山都督府,其统辖范围,西北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沙陀州都督府位于距离北庭都护府治所金满县不算远的东北部⑤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3-64页。,金满洲都督府则大约就在金满县一带,“因唐朝的庭州为汉朝的金满,故金满州都督府应即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的北庭古城周围。”⑥雪犁:《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4页。也就是说,沙陀、金满二州都督府都在北庭都护府亦即唐朝边界以内。《旧唐书》卷四○《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下对此也有明确记载:金满州都督府等“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所以,如果以塞内(边界内)和塞外(边界外)作为划分内蕃和外蕃的标志或界限的话,那么至少是从北庭都护府设立以后,沙陀人便不宜再被称为“外蕃”了。
沙陀州都督府存续的时间似乎并不很长,而金满州都督府则长期存在。有据可查较为明确的沙陀人的先祖是沙陀金山。据《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的记载,沙陀金山在唐高宗龙朔(661-663年)中曾跟随薛仁贵讨伐铁勒,以功授墨离军讨击使。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沙陀金山死,其子沙陀辅国继袭。沙陀辅国曾任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①《唐文拾遗》卷六五《大唐银青光禄大夫、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沙陀公故夫人金城县君阿史那氏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6页。笔者考证,此“沙陀公”即沙陀辅国,参见拙著《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24-25页。。墨离军,设置于唐高宗晚期至武则天初期,位置在瓜州(治今甘肃安西东南)界内②按关于墨离军的位置,新、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凉州》条等史籍都记载在瓜州西北千里。钱伯泉则认为在瓜州城郊十里,“千”为“十”之误,参见钱伯泉:《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贺兰军,他书未见记载,位置不详,大约在北庭都护府统辖之内,如先天初年(712年)沙陀辅国就因吐蕃军队的进犯而徙部于北庭都护府躲避。沙陀金山和沙陀辅国担任唐朝地方军使,并不属于个人行为,而是全部落的参与。当时的普遍情况是,部落首领担任某军的将领,部落成员也就成为该军的战士,他们在有事时“应须讨逐探候,量宜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③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652页。。沙陀金山和沙陀辅国也都曾入朝,并且死后葬于长安县居德乡龙首原④上引《阿史那氏墓志铭》云:阿史那氏于开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迁祔于长安县居德乡龙首原先公特府君之茔”。“先公特府君”,即沙陀金山。既然沙陀辅国夫人葬于“先公特府君之茔”,想必其本人去世后也当葬于此。。所以,从沙陀金山与沙陀辅国的这些经历、特别是他们都曾担任过唐朝地方驻军单位的军事将领来看,也很难将他们称之为“外蕃”。
至于“代北(内蕃)”和“雁南(边州)”的划分则更为勉强。代北,即代州或雁门郡以北,在这一区域内还有蔚州(治今山西灵丘)、云州(治今山西大同)、朔州(治今山西朔州)以及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古城)、单于都护府(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土城子)等等,它们都属于边州。沙陀人在进入“雁南”地区之前,其首领都曾分别担任过这些边州的行政、军事长官。而雁南是指雁门郡(代州)或雁门山以南,与上述诸“边州”地区相比,其实这里已经是属于“内地”了。
中国古代的边界远没有今天这样严格和明确,如果必须要将边疆各族以内、外加以区别,那么《唐律疏议》中关于“化外人”和“化内人”的规定和解释,是非常值得参考的。该书卷六《名例》云: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⑤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33页。
同书卷一六《擅兴》云:
……若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
【疏】议曰:……化外人来为间谍者,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私入国内,往来觇候者;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化外书信,知情容止停藏者:并绞。⑥《唐律疏议》卷一六,第307页。
即《唐律》把周边蕃夷各族划分为“化外人”和“化内人”两种。“化外人”,“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显然他们不属于唐朝的“国人”,而是外国人,就如《唐律疏议》中列举的高丽、百济一样;“化内人”,《唐律》没有解释,顾名思义,即“归化”或“归附”唐朝的周边各部族,则应当视为唐国内的少数民族。
对于“化内人”,唐朝一般设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设置的原则是“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119页。。又根据其居住地点的不同,将他们区分为“在蕃”和“入附”两种。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诏书云:“今诸蕃归降,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②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七《诫励诸军州牧将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54页。。所谓“在蕃者”,也就是各部族仍然居住在原地者,随着他们的“归化”和羁縻府州的设置,这些地区也就纳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入附者”则是迁入原唐朝边州境内者,唐一般设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如唐前期关内道灵、庆、银、夏等州界内设置的侨置羁縻府州,都是属于这种性质③樊文礼:《唐代灵、庆、银、夏等州界内的侨置府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对于“入附者”,唐朝廷又根据其入附时间的长短将他们区分为“熟户”(或称“旧户”)和“新降”。开元九年诏书云:“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新降更伫绥怀。……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④《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第11652页。《唐六典》中也明确规定:“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⑤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77页。“内附后所生子”,当然也属于“旧户”、“熟户”,可见至少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成为“章程须依国法”的“王人”、“百姓”了,他们的汉化程度很高,像唐初设置在灵、夏等州界内的“六胡州”胡人,已经“同华夏四乂”⑥《全唐文》卷二八《诛康待宾免从坐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了。
沙陀人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归附唐王朝后,就已经成为“化内人”中的“在蕃者”。但到德宗贞元六年臣属于吐蕃后,则由“化内人”变成了“化外人”。宪宗元和三年内迁后,又成为“化内人”中的“入附者”。李克用及其父亲朱邪赤心(李国昌)都属于“内附后所生子”⑦按李克用出生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九月二十二日,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朱邪赤心(李国昌)的出生年月以及死时年龄,史书都无记载。而对于其卒年,则有中和三年(883年)和光启三年(887年)的不同记载。按朱邪赤心(李国昌)之父朱邪尽忠是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由吐蕃占据的甘州迁到唐朝的灵州的,距离中和三年(883年)和光启三年(887年)分别为75年和79年,故朱邪赤心当出生于朱邪尽忠内附唐朝即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之后。,可见他们早已都是“章程须依国法”的“熟户”、“王人”、“百姓”了,是唐国内的少数民族。所以,尽管沙陀人从内迁以来,仍然保留着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形式,但他们始终是作为唐朝臣民的身份出现的。李克用的祖父朱邪执宜在内附后先后被唐朝任以阴山都督府兵马使、阴山都督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等官职,其父亲朱邪赤心(李国昌)也先后被任以朔州刺史、代北军使、蔚州刺史和云中防御使、振武节度使等职务,李克用本人则相继担任了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雁门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官职。因此,尽管李克用统治的核心和骨干由“沙陀三部落”和代北“五部之众”组成,但李克用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大臣,河东节度使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政权,这与唐朝其他地方政权并无两样。⑧樊文礼:《“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那么,“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的李克用河东割据政权统治者能否称之为“集团”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关于“集团”,《现代汉语词典》作出了如下的解释:“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3页。它可以不分种族、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也可以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不同民族(或族群)中的个人可以组建成同一个集团;同样,同一个民族(或族群)中的人们也可以组建成多个不同的集团。李克用及其追随者们,当然也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这个目的,在乾符年间(874-879年)杀害段文楚的事件中○10按关于李克用杀害段文楚的事件,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年)、乾符元年(874年)、三年(876年)和五年(878年)等多种记载。司马光《资治通鉴》采纳了乾符五年说。,由李克用的叔父、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的李尽忠明确予以表述:“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按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乾符五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95页。即乘“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之际,立功名,求富贵,拥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平定代北,成为一方的霸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李克用河东藩镇势力称之为一个“集团”。事实上,在唐末时期形成或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势力集团,如朱全忠汴州(河南)集团、李茂贞秦岐集团、王建巴蜀集团、杨行密淮南集团以及河北地区的魏博、成德、卢龙藩镇集团等等,李克用组建的集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这些集团有的后来建立了政权,有的则被其他集团势力所兼并或消灭。至于笔者之所以将李克用组建的集团称之为代北集团而不称之为沙陀集团或李克用集团,一则是因为这一集团中包含了沙陀以外的诸如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二则是由于这一集团在李克用之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建立了沙陀三王朝,直至宋初始消失;三则是因为这一集团最早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而且集团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代北地区,故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
二、代北集团是不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
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李克用祖孙三个阶段,到李克用时期,其基本格局最后形成,它是一个以牙军为核心和骨干而组成的军人政治集团。从民族上看,它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了奚、突厥、吐谷浑、鞑靼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从地域上看,它以代北人为核心和基础,包括了河东人和其他外来人员在内。《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云:李克用“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同书《唐庄宗纪》亦云:“武皇起义云中,部下皆北边劲兵。”②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359页;卷二七《庄宗纪一》,第366页。所谓“边部人”、“北边劲兵”,都是指的代北人。
笔者曾对李克用牙军中出身较为清楚的60位军将进行了考察③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88-107页。,其中代北人有40人之多,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这说明,李克用统治集团是以代北人为主的。而在所有60位牙将中,包含了三种成份,即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和代北汉人。
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萨葛(亦称薛葛)、安庆三部落。中外学者早已考订出,萨葛即索葛,均为粟特的不同音译;而安庆部落,从其都督史敬存的出身看,亦当即粟特人部落④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79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后收入《西域史地从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粟特人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作昭武九姓胡人,因此,“沙陀三部落”中,有二部为昭武九姓胡人。
在笔者考察的李克用60位牙将中,明确为沙陀人的有李克用的兄弟李克修、李克恭、李克宁和养子李嗣源,杨光远之父阿登啜、后汉高祖刘知远之父刘琠和郭绍古等7人;明确为沙陀三部落或代北三部落的有安怀盛、康义诚2人;从姓氏看,李存孝(即安敬思)、安金全、安元信、安福迁、康君立、康福、康思立、康延孝、史敬思、史建瑭、史俨、史敬镕以及石敬瑭之父臬捩鸡等13人亦均为昭武九姓胡人。李周,史称其为李抱真之后⑤《旧五代史》卷九一《李周传》,第1203页。,李抱真为“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⑥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按原文作:“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安兴贵为粟特胡人,而李抱真为李抱玉的“从父弟”。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645-3647页。,而安兴贵为粟特即昭武九姓胡人。这样,60人中沙陀及昭武九姓胡人占去了23人。
所谓“五部之众”(亦称“五部之人”),有时是指沙陀三部落和契苾、吐谷浑五部,史籍也多有将这五部相提并论的记载。但在大多数场合,“五部之众”是一种泛称,如在乾符年间李克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康君立谓李克用“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①《旧五代史》卷五五《康君立传》,第737页。;天复元年,李克用致朱全忠的信中,声称自己“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②《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第803页。;以及李友金在代州募兵三万,“皆北边五部之众”③《旧五代史》卷二五《唐武皇纪》,第335页。等等,这里的“五部”、“五部之众”,即是对代北蕃胡部落的泛称,故李友金所募集的“北边五部之众”,《资治通鉴》则作“北方杂胡”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二月,第8247页。。“杂胡”,亦即“杂虏”,胡三省对此解释为:“谓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⑤《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四年三月“陉北沙陀素骁勇”条胡注,第7870页。。故我们将代北地区沙陀三部落以外的蕃胡部落统统称作五部之众。⑥日本学者室永芳三和西村阳子认为,“五部之众”系指沙陀三部落和契苾、吐谷浑五部,与笔者的观点不同。见西村阳子著《唐末五代代北地区沙陀集团内部构造再探讨》,载《文史》2005年第四辑,第213-216页。
在笔者考察的李克用60位牙将中,明确出身于五部之众的有5人,即李克用养子李嗣恩(吐谷浑人)、李存信(即张污落,云中回鹘人)、何怀福(回鹘人)、薛志勤(奉诚军奚人)、张万进(突厥人)等。此外,白奉进,“父名达子,世居朔野,以弋猎为事”⑦《旧五代史》卷九五《白奉进传》,第1263页。,当为吐谷浑人,因为当时吐谷浑白义成部就在云州、蔚州一带地区活动。白文珂,史称其为太原人,从其姓氏情况看,亦当为吐谷浑人。其余15人则大体为汉人,他们为李嗣昭(本姓韩,汾州人)、李嗣本(本姓张,雁门人)、李存进(即孙重进,振武人)、李存璋(云中人)、李存贤(即王贤,许州人)、李存审(即符存,陈州人)、李建及(本姓王,许州人)、盖寓(蔚州人)、张敬询(胜州人)、李德珫(应州人)、周德威(朔州人)、刘彦琮(云中人)、李承嗣(代州人)、张审(代州人)、梁汉顒(太原人)、相里金(并州人)、郑琮(太原人)、刘训(隰州人)、张虔钊(辽州人)。
当然,上述60位军将只是李克用部将中的一部分,如仅据《旧五代史·唐武皇纪》的记载,李克用的部将还有安老、薛可、安金俊、安休休、安知建、安福顺、安福应、石君和、石善友、落落等多人。其中落落为李克用长子,曾任铁林指挥使,其为沙陀人自不待言。其余如安老、薛可、石君和等人从其姓氏看,亦当为昭武九姓胡人,如安福顺和安福应,就与安福迁是三兄弟。此外,“昔从武皇,破黄巢而定紫塞,久权兵柄”的安万金,其曾祖安德昇、祖父安重胤、父亲安进通以及他本人都曾任“索葛府刺史”⑧赵普:《晋故均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安府君(万金)墓志》,参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72-73页。,“索葛”,如上所述,为“粟特”的不同音译,可见其也是昭武九姓胡人;“初自代北与明宗俱事武皇”,后“因负罪奔梁;在梁复以罪奔蜀”的云州人安重霸⑨《旧五代史》卷六一《安重霸传》,第818页。,以及初仕李克用后仕其子李存勖的石金俊○10《千唐志斋藏志》《大周故北京飞胜五军都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赠左骁卫将军石公(金俊)妻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墓志铭并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35页。,也都是昭武九姓胡人。
李克用时期的河东牙将如此,后唐时期的禁军将领亦如此。笔者亦曾考察了后唐部分禁军将领的出身情况○11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154-162页。,共计94人,从地域情况看,出自代北、河东(包括李克用时期旧部将及其子弟)者59人,非代北、河东人者15人,籍贯不明者20人;而从族属情况看,出自沙陀系的有李从璟(明宗李嗣源子)、李从粲(明宗子)、李从璋(明宗侄)、李从敏(明宗侄)、张彦超、药彦稠、刘知远等7人;出自沙陀三部落(昭武九姓胡人)的有安元信、安彦威、安从进、安金全、安审通、安审琦,安审晖、安叔千、安念海、康福、康义诚、康思立、康延孝、史建瑭、史懿、史匡翰、石敬瑭、石敬威、李周、米全等20人;出自突厥的有郭金海、张彦泽2人;出自吐谷浑的有白奉进、白再荣(蕃部人)、白从晖、慕容迁等4人;出自回鹘的有张从训(李存信子)、何福进等2人;其余基本为汉人。后晋和后汉的禁军将领中,汉人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沙陀人、昭武九姓胡人、突厥人、吐谷浑人、回鹘人等各部族仍然占有一定比例,同样可以说明问题。
在李克用河东政权和后唐王朝中,还出现了许多带有“蕃汉”字眼的军事将领,如“蕃汉马步总管”、“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蕃汉马步都虞候”、“蕃汉马步都校”、“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等等。这是我们在其他藩镇即使是河朔三镇中也都不曾看到的。这一官职的出现,无疑反映了李克用河东军和后唐禁军中蕃胡族人的大量存在。史籍也往往将李克用的河东军称作“沙陀军”或“蕃军”,如《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载: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李克用既破邠州后,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莘县,声言欲救兖、郓”。五月,朱全忠“命葛从周统军屯于洹水,以备蕃军”。八月,“李克用自率蕃汉步骑数万以围潞州”,等等。时人甚至将“深目而胡须者”作为河东军的特征,如《新五代史》卷四三《氏叔琮传》云:“晋人复取绛州,攻临汾,叔琮选壮士二人深目而胡须者,牧马襄陵道旁,晋人以为晋兵,杂行道中,伺其怠,擒晋二人而归。”
可见,代北集团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就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
三、关于“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
“诸蕃群体间的关系性质也很难用来说明沙陀代兴后统治者和社会群体间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这是一句不易理解的话。“诸蕃群体”指什么?沙陀代兴后的“统治者”和“社会群体”又何所指?都不明确。如果说“诸蕃群体”和沙陀代兴后的“社会群体”都是指笔者所谓“代北集团”内部各部族,那么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沙陀代兴后”的“统治者”也正是这个群体。如果说其内部有所谓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的话,那也只能是他们之间通过相互联姻、建立义父子关系、特别是通过利用唐王朝的官爵制度建立起来的上下级关系等等手段,不断加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向着族群或民族共同体的方向发展。王小甫在谈到唐末五代沙陀人经历了由“塞外(外蕃)——代北(内蕃)——雁南(边州)的转移过程”(尽管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时也曾说道:“这一转移过程其实就是周边族群主观认同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原社会对这些群体的认知接受过程,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就在这一过程中演进变化。”①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3-4页。所以,说到“统治者和社会群体间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应该主要是唐王朝统治者与代北集团之间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这样才更切合“代北集团”能否成立这样一个主题。
王小甫指出:“在大唐帝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内,处于历史官僚体制不同阶层的各族群共同分享发达的资源,也为帝国提供自由流动资源”。所谓“资源”,即“中央王朝为主体的帝国政治体系,积累起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②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1页。。“内蕃诸群体与唐朝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其实就是酋领以蕃部为军政资源与唐朝统治者交换发达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互利关系。”③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10页。按这段话是作者根据苏航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北方内附蕃部研究》(北京大学2006年)概括出来的。笔者在过去一直将代北集团称作“多民族的结合体”,而没有使用“族群”这一概念。关于“族群”,学界对它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不过它与“民族”密切相连,甚至往往等同。如王明珂认为,“‘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汉族、客家人、华裔美人);‘民族’则是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是最大范畴的单位,特别指近代国族主义下,透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汉族、大和民族、蒙古族或羌族等)。”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页。徐杰舜认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是: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从社会效果上看,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从使用范围上看,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族群与民族的联系是: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②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代北集团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其能否称之为“族群”,且另当别论,不过它与唐王朝统治者之间所结成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代北集团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其与唐朝统治者“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过程,或“就是酋领以蕃部为军政资源与唐朝统治者交换发达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互利关系”过程。
如上所述,代北集团的形成(也可以称作兴起)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李克用祖孙三个阶段。其与唐朝统治者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即“酋领以蕃部为军政资源与唐朝统治者交换发达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互利关系”,从沙陀内迁之初即已开始。《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载:“(范)希朝镇太原,因诏沙陀举军从之。希朝乃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而处余众于定襄川。执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按“阴”当为“陉”之讹)山北沙陀。”范希朝出镇太原,事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即沙陀内迁的第二年。《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的记载有所不同,云:“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无论是“希朝乃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还是“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都说明沙陀人从此时已经开始“为帝国提供自由流动资源”了。
当然,沙陀人在“为帝国提供自由流动资源”的同时,也已经在分享着唐王朝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
有资料表明,沙陀人在内迁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着部落制组织形式,“沙陀三部落”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其保留着部落制组织的情况。朱邪执宜、朱邪赤心都曾担任过部落酋长的职务。部落酋长对于领导、团结和凝聚部落成员有着最具权威的地位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于吸收部落以外人员加入到自己的群体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朱邪执宜在率部归唐后,马上就被唐廷授予阴山府兵马使的职务③关于朱邪执宜最初的任职,史籍有不同记载。《后唐懿祖记年录》以及以此为据的《旧五代史·唐武皇纪》都记载说朱邪执宜内迁后的首任官职即为阴山府都督;《资治通鉴》则记载为阴山府兵马使,葛勒阿波为阴山府都督(《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三年六月“沙陀劲勇冠诸胡”条《考异》,第7652页)。按朱邪执宜为朱邪尽忠之子,史称他在归唐时“年已及冠”,即刚刚20岁出头。而葛勒阿波为朱邪尽忠之弟,史称他在归唐时为部落“大首领”。根据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葛勒阿波当是在朱邪尽忠战死之后,接替其兄长担任部落大首领的。以部落大首领担任阴山府都督,而以前部落大首领之子担任府兵马使,这样的安排,是合于事理的。事实上,到穆宗长庆二年(822年),仍有“阴山府沙陀突厥兵马使朱邪执宜来朝贡”(《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长庆二年九月,第499-500页)的记载。一直到文宗大和四年(830年),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时,才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纪年录》以及以此为据的《旧五代史·唐武皇纪》说朱邪执宜的首任官职即为阴山府都督,恐怕是在有意抬高李克用祖父的地位。,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又被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奏授阴山都督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的职务。阴山都督府虽属于羁縻府州性质的机构,代北行营招抚使也有临时委派的性质,但它们无疑都是大唐帝国政治体系中发达的政治资源的组成部分,这也反应了朱邪执宜所具有的部落酋长和唐朝官员的双重身份。沙陀本来就“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④《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四年三月条,第7870页。,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府都督、并进而担任代北行营招抚使之后,无疑对沙陀征服代北各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朱邪执宜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政治资源,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
在以后的六、七十年里,沙陀人与唐朝统治者继续保持着这种“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关系。如朱邪执宜在世时,曾率部参加了唐朝廷在和元和五年(810年)讨伐成德镇、元和九年至十二年讨伐淮西镇、以及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再次讨伐成德镇的战争,并率军屯守天德军,防备回鹘对唐的侵扰。而作为回报,朱邪执宜被唐朝廷任以蔚州刺史、金吾将军等官职。朱邪执宜死后,其子朱邪赤心继续为唐王朝效力。他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唐朝讨伐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宣宗大中(847-860年)初年收复被吐蕃占领的秦、原、安乐3州和石门、六盘等7关的战争。而作为回报,朱邪赤心相继被唐朝廷任命为朔州刺史、代北军使、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等。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反唐起事爆发后,朱邪赤心又率领沙陀三部落及代北五部之众前往镇压。沙陀军在这次战争中充当了先锋军的角色,为唐王朝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战后,朱邪赤心又从唐王朝那里获取了重要的政治、社会资源,被授予大同军防御使,不久升任振武军节度使,并赐予“李国昌”之名,“预郑王属籍”①《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6页。。这两件事在沙陀及代北集团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前者使沙陀人摆脱了以往被河东节度使制约的局面,作为直属中央的一级地方藩镇,对代北各族更具有了号召力。后者则使沙陀人在中原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使时人乃至宋人对沙陀人后来所建政权的“正统”地位得到了认可②参见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80-82页。。
沙陀人与唐朝统治者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曾因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年)发生的云中防御使段文楚被杀事件而一度终止,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甚至成为唐王朝全力剿灭的对象。不过,到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农民军攻占唐都长安后,随着唐朝廷的“勤王”令下,双方“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关系便马上恢复并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中和元年(881年)二月,沙陀首领李友金奉命率领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及吐谷浑诸部5000人入援京师。随后又返回代北募兵三万,“皆北边五部之众”。李友金建议代北监军使陈景思上奏朝廷,请招李克用南下前往镇压。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到中和二年十一月,李克用率领三、四万代北兵南下,他们在镇压黄巢农民军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杨复光在事后向唐僖宗所上的告捷书中称:“伏自收平京国,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锋,雁门(按即李克用)实居其首。”③《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中和三年四月,第716页。《资治通鉴》在记述此事时亦云:“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④《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五月条,第8295页。当然,李克用也从唐王朝那里获得了更大的社会资源,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进爵陇西郡公,代北集团也在此期间形成了它的最后格局。
李克用在出任河东节度使后,继续维持着与唐朝廷“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关系,所不同的只是,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摆脱了作为沙陀蕃部酋长的角色,而是以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代北集团的首领和唐朝地方大臣的角色出现。光启元年(885年)十二月,宦官田令孜挟持僖宗至山南,邠宁节度使朱玫拥嗣襄王李煴为帝,在凤翔另立朝廷,“诸藩镇受其命者十六七”⑤《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五月条,第8335页。。李煴遣使至河东,李克用“燔伪诏,械其使,驰檄喻诸镇”⑥《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五月戊戌条《考异》引《后唐太祖纪年录》,第8337页。,声称自己已发蕃、汉兵三万“进讨凶逆”。接着又遣使奉表诣山南,云“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⑦《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条,第8338页。。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李克用此次并没有真正出兵,但是他的态度,对稳定僖宗的帝位却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乾宁二年(895年)五月,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和镇国军节度使韩建拥兵入朝,杀宰相韦昭度、李蹊,“同谋废昭宗,立吉王”。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大举蕃、汉兵南下,讨三帅“称兵诣阙之罪”①《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第754页。。三帅闻太原起军,乃停废立之谋。王行瑜和李茂贞又欲挟天子以令诸侯,分别令其兄弟或养子争夺昭宗。昭宗惧为所迫,先后出逃南山、石门镇等地。李克用围华州,韩建登城求饶;战渭桥,李茂贞遣使求和;最后逼死王行瑜。昭宗得以还京,继续“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②《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濬传》,第4659页。。
而李克用从唐王朝那里所获取的,是他本人的一次次加官进爵:从陇西郡公到陇西郡王,再到晋王;从检校左仆射到检校司空、加司徒平章事、太保、太傅、检校太尉、兼侍中、守太师兼中书令;食邑二万户,食实封一千五百户等等,囊括了除皇位外唐王朝几乎所有的高级官爵。尤为重要的,是他长期据有了河东镇这一方土地。后晋时郭威曾对刘知远说:“河东山河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③《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元年八月条,第9275页。李克用正是充分利用了河东镇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唐王朝在这里积累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巧妙地将自己从代北地区带来的三、四万“北边劲兵”纳入到节度使统治体系之中,组建起了一个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集团——代北集团,从而以地方藩镇的面目崛起于唐末政治舞台。
[责任编辑:李国栋]
Rethinking of Foundation of the Daibei Group 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FAN Wen-l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03,China)
The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the Daibei Group(代北集团)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in three folds.Fistly,“rising in the way of local division”does not affect the foundation of Daibei Group;secondly,Daibei Group is a multi-national combination including multi-national components like the Shatuo(沙陀),Hu(胡)troops,Turk,Huihu(回鹘),Tuyuhun(吐谷浑),Xi(奚),Qibi(契苾),Tartar and Han ethnic group etc.;thirdly,there are“mutual interaction and mutual benefit in resources”relationship between Daibei Group and emperors of Tang Dynasty,that is to say,the foundation of the group is the process of“mutual interaction and mutual benefit in resources”with Tang rulers.
Daibei Group;multi-national combination;mutual interaction;mutual benefit in resources
K 242.4
A
1002-3194(2014)03-0090-10
2013-10-25
樊文礼(1955- ),男,内蒙古杭锦后旗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关系史。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代北集团’与唐末五代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研究”(11BZS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