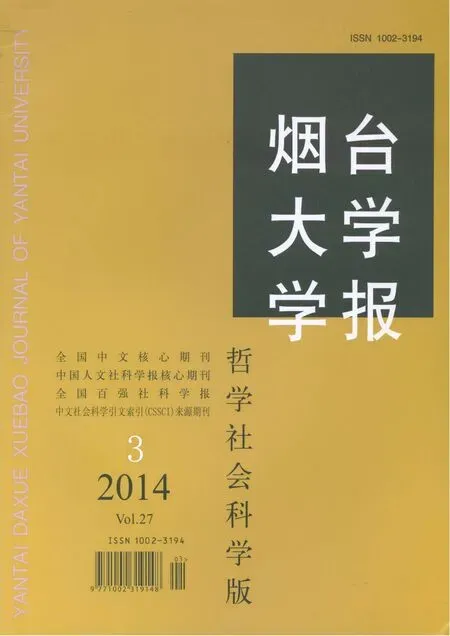对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争的一些问题的评析
陈玉屏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自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被提出以来,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实际上是前些年关于民族问题是否应当“去政治化”论争的继续与延伸,其潜在的影响之大不言自明,故各方面都高度重视,国内外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在这场论争中,许多的专家和学者针对此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我没有立即投入论争的行列,而是经过两年来的观察与思考,迟至今日来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
什么是“民族”?这是一个让韦伯、盖尔纳、安德森、凯杜里、霍布斯鲍姆等著名的学者们都感到头疼的、难以准确描述的问题,而且中国传统话语概念中的“民族”与西方话语中的“民族”,是有很大差异的。《礼记·王制》对“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的描述,讲的不就是因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不同,故而语言文化和心理意识各有特点的不同的“民族”么?这些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其间有许多分分合合,但各自都保持了许多使之堪称为一个“民族”的自身独有的文化特色,直至新中国成立。我们中国人的绝大多数至今就是这样来建立“民族”的概念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的指导,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于是学者们和民族工作者们广泛开展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当时对中国学界和民族工作者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斯大林的有关论述。斯大林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民族”所下的“四要素”定义,中国的学者们普遍接受,因为用“四要素”去衡量中国历史上那些被视作“民族”的各个群体,确实都相当合拍,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开篇几乎就是按“四要素”描述匈奴民族。然而,斯大林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3页。这一句话却把当时中国的学者们都搞懵了,于是学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各种意见后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虽然以“汉民族形成”为议题,但讨论的内容实际上围绕民族形成理论进行的。此书“编者的话”开篇第一句就是:“汉民族形成问题,是我国史学界争议未决的问题之一。”这次大讨论仍未达成共识,根本原因就是许多学者对斯大林的那一句“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不理解,而此种不理解,原因在于斯大林所言的“民族”的概念和当时许多专家头脑中固有的“中国、夷、蛮、戎、狄”这种传统的“民族”概念有很大的差异。
斯大林所讲的“民族”,是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在欧洲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那个国家层面的“民族”,这个“民族”是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相伴而行的,是要求把原处于帝国统治之下的具有共同文化属性的人们群体转变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将群体原来的共同地域固化为新的国家版图、将原来的文化边际转变成为国家疆界的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那个“民族”。对于近代以来经历资本主义上升的欧洲社会产生出来的这个“民族”,不甚了解欧洲历史、也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中国民众,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概念的。就是到了今天,除了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之外,大多数干部和民众心目中的“民族”,仍然还是沿袭着“中国、夷、蛮、戎、狄”那种传统的民族概念,并不清楚中国和西方的“民族”话语有如此明显的差别。
由于“民族”的概念太过复杂而无法准确描述,西方学术界有“政治民族”、“文化民族”、“法律民族”等等诸多提法且并未达成一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5页。,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0页。恩格斯所言的这个“文化民族”显然指的是古代的“民族”,与斯大林所说的近代才逐步形成的、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那个“民族”不是一码事。安东尼·史密斯说西方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将具有前者那种属性的民族称为“族群民族”,将近代发展起来的具有后者那种属性的民族称为“公民民族”④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族群民族”、“公民民族”的这种称谓当然是从西方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西方称谓,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就有点障碍。比如“族群”为何,连西方话语自己都没有统一;“公民民族”,恐怕就没有“国民民族”或“国族”容易理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主张借用恩格斯的说法,将前者那种我们传统概念中的“民族”称为“文化民族”,将后者那种近代以来形成了民族国家后、那个国家层面的“民族”称为“政治民族”。
我所主张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差异在何处呢?本人曾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建构政治民族》⑤陈玉屏:《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建构政治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年第1期。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文化民族’用以维系自身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曰民族‘认同’)的诸要素,比如2005年我国关于‘民族’的新说法的‘6+1’要素”,其基本特点主要体现为文化性,没有特定的政治指向,此种认同具有鲜明的‘文化认同’特征。”“‘政治民族’是在对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人们相互间的‘认同’。此种认同具有对国家体制、制度等认同的鲜明政治指向,基于此种政治认同的人们相互认同,已超过‘文化民族’以传统文化作为主要认同意识而成为第一认同意识,即首先是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其次才是原有‘文化民族’的‘族民’身份认同,而此种‘族民’认同在正常状况下会渐趋弱化。因此,‘政治民族’是与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具有较为紧密的契合关系、这是现代民族的特征。”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在价值判断方面,是把本(文化)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还是把全体国民的根本、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当然是指成员中大多数人的意识),是“文化民族”和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的具有指标意义的差异。国民成员中具有后者自觉意识的比重越大(特别是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个“政治民族”就愈加成熟。
有一点必须指出:“文化民族”是一定历史时代——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是要与时俱进的。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时代,所有“传统的”“文化民族”都是要逐步向着作为“现代民族”的“政治民族”发展的,这是人类最终走向民族大融合的必经过程,尽管需要经历的历史进程极其漫长,对此我们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认为“现代民族”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类。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33页。斯大林的这一论述是很有道理的。“现代民族”这种“政治民族”虽然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伴随“民族国家”率先形成,但并非由资产阶级所独有。“政治民族”只是现代的民族表现形式,“政治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的属性,是与启蒙思想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体制与制度相契合而决定,是由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指导下建构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同样也能够建构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国家体制和制度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民族”。
二、现代国家必须建构“政治民族”
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帝国的羁绊,竭力启发并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将其升华为“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即便是在欧洲崛起的一个个“民族国家”,也很难达到由一个纯粹的“文化民族”构成,这个政治实体和已固化为国家疆界内,总是包含有或多或少的多个“文化民族”,因而需要按照“民族主义”的理论“打造”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即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将各个“文化民族”建构为一个与这个“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政治民族”。比如法国境内原本就生息繁衍着高卢等多个“文化民族”,只不过通过罗马的世界霸权将其“刨削”成“罗马人”之后,经历整个欧洲中世纪,他们原有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被湮没状态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笫145页。,直至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到来后,才开始复苏。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状况都大体如此,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清楚的描述。法国大革命到来时,法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按境内原有的“文化民族”为单位组织人民去为“一族一国”理念而斗争的,而是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动员民众结成一个整体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在面对欧洲封建势力的武装干涉时,又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独立为号召,激发全体民众同仇敌忾的精神,去保卫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体制和制度,通过这些努力去建构起“法兰西民族”的自觉意识。安东尼·史密斯在他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第三章中,开篇就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是如何建构“法兰西民族”的①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48、49页。,史密斯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真正庆祝的究竟是什么?不仅仅是他们取得了权力以及终结了贵族和教士阶级的特权。真正庆祝的是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形式之下,一个新的法兰西民族的诞生……从根本上说,这种有计划的‘民族建构’是一种现代的过程,在1789年之前找不到类似的实例。”②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50页。
需要指出的是,欧美的“民族国家”在建构“政治民族”过程中的方式和手段伴随着不少阴暗、血腥的过程。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都是建立在‘少数民族’被同化、压迫和边缘化的基础之上的……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直至种族灭绝。”③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问题在于欧洲这种在建构“政治民族”过程中出现的丑恶的极不公正的行为,是建立“民族国家”和建构“政治民族”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属性造成的罪恶?
当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由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裹挟着进入中国以后,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下,中国的社会精英们逐步认识到除列强“船坚炮利”之外,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天下观”确实不如西方民族主义经世致用,旧的帝国体制下的国家就是不如西方那些“民族国家”能够凝聚力量,一盘散沙的老大中国甚至斗不过那些只有弹丸之地的民族国家,于是希望按照西方列强建构“民族”那样来建构“中华民族”、建立“民族国家”以救亡图存,于是才有“中华民族”说法的大力传播流行。
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华各民族的先民们在中华大地数千年的生息繁衍中,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吸纳,不仅具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形成了不少具有共性的东西。比如“大一统”的观念,不仅为汉族、同时也为众多少数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传统中的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历史上不少兄弟民族的政权几乎都有志于“一统天下”,都概莫能外地努力“建正朔”、“争正统”。但是,各民族作为“民族”(文化民族)的各种特征依然存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一些民族间因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斗争不仅依然存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20世纪初那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试图师法西方列强,接过民族主义,按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但建构“民族国家”就必须建构“政治民族”——把中华大地上众多的“文化民族”建构为一个“国族”。但是,西方的那个“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而中国社会压根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该如何仿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样子去建构“政治民族”?国民党人在民族的问题上说来说去,或“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④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5页。,或称少数民族为汉族的宗支,而民间的精英人物如顾颉刚等则宣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⑤转引自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尽管这些思想和说法有对抗帝国主义分裂中国阴谋的动机,但对客观存在的各个少数民族采取不承认主义,企图使用民族同化的手段来建构“政治民族”,其结果只能导致民族压迫和民族之间的对立对抗的加剧,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
在未曾经历过“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20世纪初的中国,要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模式去建构国家层面的“政治民族”,不仅水土不服,而且时代已经不同了,国际风云变幻对民族意识的影响已不可低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这种民族政策当然无法取得成功。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选择了建立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发展道路。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中国存在众多的“文化民族”是客观事实,他们不仅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特色,也保留着对“我”者认“同”、对“他”者辨“异”的强烈的意识。历史造成的民族不平等、民族压迫与反抗现象也都客观存在着,这些现象不仅有悖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同时对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而,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承认各兄弟民族的客观存在,制定一系列民族政策,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努力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民族平等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政策中作为基石的最基本的原则,所谓民族平等最实质性的是各民族权利的平等,所谓各民族的权利首先是各民族集体的权利,因而保不保障各民族集体权利就是是否坚持民族平等的要害!中国的各个民族不是因开展了民族识别才被“识别”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如果连身份都不明确或不予承认,又如何保障他们的民族权利,又如何奢谈民族平等!因此,把20世纪后期出现世界性的民族主义张扬形势下,因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对民族关系影响产生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民族识别及以此为基础的一些主要的民族政策,是违反实事求是这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
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我们党从开展民族识别以来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我在《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①陈玉屏:《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已全面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法绕开,必须正面回答,那就是多民族社会主义的中国需不需要建设现代的“民族国家”?近代以来话语中的“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似乎都与资产阶级相连,我个人也认为“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是资产阶级的。但“民族”即“政治民族”是可以建构成社会主义属性的,这一点我在前文已作过论述。那么“民族国家”呢?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使用了“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此后几乎未见有人专门探讨这个问题。“民族国家”这个提法显然是从西方民族主义主张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说法衍生而成,然而“一族一国”实际上很难办到,于是他们才有“建构”之举。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到近现代,“民族国家”是不是一个绕不过的必经阶段?在处于仍然实行实力政策甚至“丛林法则”的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世界环境中,是不是需要一个叫做“国族”的国家层面的民族来应对才能更加有利?多民族的国家的任何一个(文化)民族能否单独地应对国际事务?如果我们回避这个问题,面对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由单一的(文化)民族组成这个现实,我们不把它叫做“民族国家”,而把它叫做“民族的国家”就解决问题了吗?国家对外要代表本国民族的利益?多民族国家代表哪个民族的利益?好不好说我这个国家代表的是“多民族的利益”?似乎不太妥当。如果将其说成“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人民”——people或peoples在西方术语中很多情况下应对的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民族”。那么叫做“代表国民(公民)的利益”?似乎又进入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话语体系中去了。我认为,人类社会自“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到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时期,“天下主义”的到来是遥远的事情。“民族国家”虽然由资产阶级所发明,但它未必一定姓“资”。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能够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民族”,也可以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民族国家”。
诚如一些学者指出,国民党人确有以汉族等同“中华民族”的倾向,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方式来建构“中华民族”。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几千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中华各民族血脉相连,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共性的东西,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基础,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而不能因为国民党人错误地定性“中华民族”,就对“中华民族”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采取一种质疑态度。因此,以“中华民族”作为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民族”,应当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尽管将其建构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政治民族”还需要做长期的、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三、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整合建构“政治民族”
如果我们承认在现代国家(不论姓“资”姓“社”)的建设和发展中,必须形成一个属于国家层面的“政治民族”,那么都有一个由“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的必经过程,多(文化)民族国家尤为如此。这种国家层面的“政治民族”绝对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国家必须努力做好整合建构“政治民族”的工作。
这里使用了“整合”建构的措辞。由于不少人对当年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用行政手段去“促进民族融合”造成的恶果还心有余悸,今天见到“整合”一类的词汇还十分敏感,又鉴于目前社会科学界的许多争议常常是对一个术语无法进行统一的界定造成的,这里有必要先阐明我对民族“整合”的认识。我认为民族“整合”与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是不同的,“整合”属政治范畴,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将一些民族个体“粘合”成一个并非同质化的整体,以产生聚合效应而大大强化其效能。民族“融合”属文化范畴,是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的自然的深度交融而形成一个同质化的整体。民族“同化”也属政治范畴,是用行政、法律等强制手段以求形成一个同质化的整体。
“政治民族”是否靠民族融合来建构?我认为建构“政治民族”与民族融合不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真正的民族融合(我是赞同李维汉同志对民族融合的描述的)是相当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而建构“政治民族”是一个现实性的任务,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有学者主张“我囯现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①金炳镐、毕跃光:《我国现阶段不宜提“促进民族融合”》,《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我是赞同我国现阶段不宜把“促进民族融合”当作口号来渲染,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促进”,否则必然造成民族工作的重大破坏,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但是,也不能因为以往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运动式的“民族融合”搞砸了锅,就连带着将“民族融合”这个术语也要有意无意绕开了。促进民族融合作为我们的一种理念、一种追求则是不能弃之不提的,这同我们当前不能实施共产主义、不能刮共产风,但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将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理想境界和奋斗目标是一个道理。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真正的民族融合虽然是遥远将来才能实现的事,但千里之行,却是始于脚下的。难道,促进“两个共同”,努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正是在为将来的民族融合做实实在在的促进工作吗?!建构现代的“政治民族”,使其不断发育得更加成熟,不也是为将来的民族融合做前期的铺垫工作吗?!
“政治民族”可否通过民族同化来建构?西方民族国家在建构“政治民族”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使用过民族同化的手段,这些都是留下了后遗症的。我始终认为被一些学者认为建构得比较成功的“美利坚民族”,它目前的富裕与强盛掩盖着许多民族问题的后遗症。一旦美国从当前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去,国内各种矛盾凸显之时,谁能保证其潜伏的民族问题会不会躁动起来?尽可以拭目以待!后发国家到了今天这样的现代社会,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下,试图用民族同化的手段去建构“政治民族”,恐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能通过“整合”多个“文化民族”来建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我所描述的民族“整合”尽管可能会被一些学者讥为“大拼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恐怕也只能采用“大拼盘”而非“一锅烩”的方式。关键是你怎么去“拼”,在艺术大师和能工巧匠手中,各色布料不是可以拼出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来么?!惜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虽然在正确地制定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过不少失误,其中一个较为重大的失误就是:不懂得现代国家不论姓“资”姓“社”都要经历一个从“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即保持“文化多元”的同时又要着力推动“政治一体”的过程,并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政治一体”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而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国家采取正确的方式和途径,持之以衡地去做整合建构工作(造成这个失误的原因我曾在其他的文章中阐述过,本文不赘述)。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复杂的问题,都与这个失误有关。
目前民族工作中争议的热点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存异”与“求同”的问题,这恰恰是整合建构的关键。前两年昌言民族问题应当“去政治化”的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从民族识别起的一系列主要的民族政策都是照搬苏联的产物,是造成当前出现诸多复杂的民族问题现象的根源,解决的办法是“去政治化”,其要害是否定民族的集体权利;近两年昌言应当向“第二代民族政策”转型的学者,虽然强调了建构“国族”的问题,但主张的核心仍然是否定民族的集体权利,把否定民族的集体权利作为建构“国族”的必然途径。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些具体内容是需要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适时调整,这个工作实际上一直在做,做得是不是很及时很到位,则是可以不断总结的。但民族平等这个作为民族政策基石的基本原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如果一个民族的集体权利都被否定了,那么哪有民族平等可言呢?当一个民族的集体权利被否定之后,其结果是什么呢?安东尼·史密斯在其所著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1790年克勒蒙特-托内尔(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在法国国民会议上宣称:‘对作为个人的犹太人我们给予所有的一切,对作为犹太民族的犹太人我们什么都不给。’公民的民族主义没有给予少数民族群体以权利,这可能符合自由的个人主义以及个人的人权,但是却实用主义地不计较给予多数(主导)民族以群体权利。这些给予主导民族的群体权利或义务包括公民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法兰西)语言进行学习和处理事务,学习和背颂多数民族(法兰西)的历史和文学,奉行法兰西习俗,承认法兰西的政治象征和制度等等。”①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45页。由此可见,被否定了民族集体权利的少数民族还能够保留住自己的文化么?还能够逃脱被同化的命运么?为什么在西方早已实行过的用民族同化的极不公正的资产阶级建构“国族”的方式,社会主义的中国还要用它来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国族”呢?如果把它视作民族政策的升级换代来推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如何整合建构“政治民族”,如何在保障文化多元的同时推动达成政治一体,实在是个大课题,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精心设计规划、妥善推行。我曾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建构政治民族》一文中指出:“认识清楚‘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过渡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贯彻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识别、民族优惠、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与促进整合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在贯彻体现民族平等(包括努力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时,必须高度重视‘政治民族’的整合建构问题,应当建立战略思维,要有目标、有思路、有具体规划和措施,不能听其‘自然而然’地发展。而和谐的民族关系,只能在妥善地协调‘存异’与‘求同’中才能长期保持和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而不论‘存异’政策过头、‘求同’不足,或‘求同’上操之过急,特别是文化上‘求同’的行政倾向冒头,民族关系都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②陈玉屏:《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建构政治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年第1期。
我们正在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过程中整合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民族”时,难道不可以摒弃西方国家建构“政治民族”的旧模式,闯出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宗旨和中国国情的新路子来吗?对此我是有坚定的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