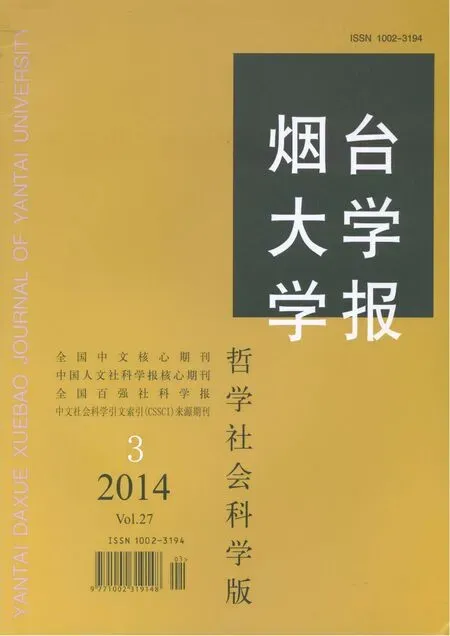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重读《红高粱》
任南南
(1.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2.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作为“青年一代的美学领袖与哲学灵魂”①李藜:《青年一代的美学领袖与哲学灵魂——李泽厚印象》,《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4期。,观点一经提出就被人文知识界高度瞩目,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被视为“五四”启蒙思想的重新开始,这种新启蒙的思路参与了文学研究界整个人文知识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现代性装置”直接作用于创作和批评,《红高粱》就是在这一语境下问世的经典。1986年《人民文学》第3期,莫言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它与随后的几个相关中篇合称为《红高粱家族》,这些小说在打造了当代文学领域中传奇的“高粱地”同时张扬了古老的华夏民族的生命质感,创造性地刷新了战争历史的表述,实现了创作主体身份和小说建构的历史主体身份的双重调整,分别在军旅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和新文学的启蒙主义立场几个向度下有所作为,凭借着救亡压倒启蒙二元对立框架下形成的文学成规,批评界肯定了《红高粱》对革命历史小说叙事经验的突破,对红色经典审美范式的颠覆,在启蒙共识下实现了《红高粱》的经典化。
一、军旅文学序列中的主体身份调整
伊格尔顿一直强调“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每一文本都在自身中内含一个有关它如何、由谁及为谁而生产的意识形态密码。每一文本都隐含地设置了自己的假定读者。”①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就是在伊格尔顿的这样一种理论轨道上规划的。为了文化秩序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以来主流政治要求文艺以意识形态的媒介和载体形象出现,从1949到1966年,作家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和意义植入具有民族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小说里,十七年中出版了约300部长篇小说,其中有110部是战争题材小说。这些小说被新中国纳入新政权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工程,得到了大力推广和重点解读,战争叙事备受关注。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显示,这些战争史诗的出版显示着文学范本的经典化全部症候,昭示着新文艺的整体力量和优势,并隐含着主流政治引导新生代作家向它们学习、模仿和看齐的隐性内涵。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描述中,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民英雄的光辉形象成为小说的重心,参与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具象描述和胜利后的群众教育,成为当代军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军旅文学中的战争书写,国家话语和英雄叙事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本质属性,在几代军旅文学作品中一以贯之。”②朱向前、傅逸尘:《当代军旅文学的精神传统》,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9月24日。
八十年代中期,尽管莫言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步入文坛,但这种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并没有顺理成章地继承。在新时期的两代军旅作家开辟了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两条线索之后,《红高粱》的问世宣布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的开辟。整部小说以儿童视角展开叙事,以儿童的感受方式审视抗战历史,还原了一个充满民间色彩的抗日故事。文学史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经验往往界定为“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③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在这种背景下,《红高粱》显示了创造性的突破,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④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很大程上弱化了历史的政治色彩,还原成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
置身于建国以来的军旅文学序列,《红高粱》的这种写法显示出对于战争历史描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就曾经倡导作家进行战争小说的创作:“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⑤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号,见《周扬文集》(第l卷)。会后,这种战争书写的迫切心理很快被主流政治以文化工程的行政方式推进,并且在选择书写对象的时候格外慎重和微妙——即作者们不约而同地聚焦胜利的战争:“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反映得最多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及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前者相比是有限的”。⑥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对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177篇解放区文艺作品的统计中,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的就达到101篇,而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陕北土地革命的不仅被笼统地列入一般的历史题材之中,而且和其他各种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起也不过7篇。邵荃麟总结这种历史的区别化处理现象时强调:“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⑦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要从历史中获得信心和热情,最直接的方式是对“胜利”的历史的讲述。因此出于现实的需要,叙述者更愿意选择胜利的战争来有所作为。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战争历史的叙述者与战场上的胜利者两者的身份往往是重合的,他们在缔造了崭新的国家历史的同时,也要完成艺术地转述这段历史的革命任务,这一现象在《林海雪原》、《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等作品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①《红旗谱》《林海雪原》等作品的创作者,正是这些传奇历史的在场者,对于自己的政治信仰也具有不可动摇的深厚情感,《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曾有着亲率小分队进入雪原剿匪的经历,以致“这几年来,每到冬天,风刮雪落的季节,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想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作为记者曾经与活跃在鲁南铁道线上的一支游击队生活、战斗在一起,他在小说中写的那些英雄人物,也都有着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原型。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往往决定了这一身份下的战争历史书写,往往是“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做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这种零距离的书写方式明显不适用于缺席战争的莫言,但他对历史的考量却因此有了更多的角度和更大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③莫言:《我为什么写红高粱家族》,《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莫言用新的视角将战争距离化、资源化,进而历史化。在他看来:“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
所以,在《红高粱》的战争书写中,胶东半岛上如火如荼的高粱地既是大敌当前民族自救、硝烟弥漫的战场,又是五四以来个性解放、惊世骇俗的天堂,恢宏的革命历史和豪放的乡野爱情就此缠绕,释放出被战争意识形态特质压抑的生命力。评论界很早就注意到《红高粱》的这一点,它将风云激荡的抗战作为家族历史演绎的壮阔背景,用孙子写爷爷的日常化方式还原了战争的悲壮。《红高粱》中“我”、“后辈”是作为感觉主体存在的,在孩子的眼里战争的英雄主义格调和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壮烈情怀远远不及厮杀的惨烈、敌人的血腥反扑来得印象深刻。“父辈由于这种关系的出现,自然就包括了时间的距离和两代人的差异,因而他们对父辈、前辈所做出的描写,就不像父辈的同代人(如杜鹏程、曲波、吴强等)那样热切,显得冷静多了,字里行间似乎扬出了一般豁达、超脱、飘逸、超功利之气。前辈才是感觉对象和描写主体。这种关系的出现自然就包含了时间的距离和两代人的差距”④王炳根:《审视农民英雄主义》,《莫言研究专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描写的重心不在于再现父辈前辈的功绩,而是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进行更为公允严格的审视。
在这种历史讲述中,家族记忆和个人化历史有效改写了此前的战争叙事,颠覆了革命历史小说自诞生就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特征。莫言对于历史的个人化处理无疑具有新时期启蒙话语的特征——《红高粱》中的国家叙事与家族记忆的置换标志着一种新的革命历史讲述方式的生成,小说不仅重启了江湖草莽土匪抗日民间叙事传统,同样突破了建国以来军旅文学的革命历史观,将革命战争的红色历史演变为携带着个人特征更具丰富性的民间记忆,战争历史的宏大叙事回归为民间野史轶闻,为读者呈现了历史本来就具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海登·怀特认为,任何历史叙事都是创作主体的个人化叙事,任何历史事实都是在想象中重生。《红高粱》中,莫言显然更具备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视角,他主动放弃了“史诗性”的宏观视角,用微观的个人体验,把以往一个连续性、必然性为主导的历史书写改写成了片断的、过程性的人生经验,因此整体政治历史场景被具体化、生命化,甚至于与个人经验遇合,大历史走下神坛成为个人生命的具体流程和生存境遇,在军旅文学的整体创作中,莫言的这种历史书写创造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状态,将抽象的历史重新抟回具体的历史,将历史叙述的判断性、整体性特征修回到其体验性、过程性的起点,为战争书写提供了全新的经验。
二、农民革命书写中的新英雄改写
以“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新文学自诞生始,农民就一直是作为启蒙的对象被纳入到国民性批判的整体框架中,随着民族救亡形势的演变,启蒙救亡的主次关系被改写,农民由革命的受益者转变成革命行为的承担者。抗战的全面爆发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群体大规模迁徙,这一从东到西,从中心到敌后的位移带给新文学很大影响。从都市到乡村,新文艺的新环境导致了现代文学出现了一大变化:“使广大作者一方面亲身感受到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普通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之间的严重脱节与隔膜;另一方面,作家们又实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智慧,特别是他们对新文艺、新思想、新文化的迫切要求,于是,中国农民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地,成了新文艺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以致服务对象。”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序》(第一集),第9-10页。这一变化使得五四时期一直以启蒙对象身份存在的农民成为“有意义的他者”重新进入创作视野,同时与新文学中的农民书写构成了一种有张力的潜在对话,“国民性改造”这一现代文学经典话语被有效置换,农民在文学化政治化的同时,也经历着道德化、革命化的身份质变,因此农民革命书写构成了解放区文学以及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要部分。
这种农民被纳入国家整体文学构想的重要表征在于小说叙事中的政治性角度不断被强化,农民书写和国家政权建设呈现出良好的互动,关于农民革命的“宏大叙事”不断涌现。解放区文学中,《吕梁英雄传》以一群奋起反抗保卫家园的民兵为主角,而且他们只是一群被武装的农民;《新儿女英雄传》里的牛大水和杨小梅最早也是以农民身份进入读者视线的;《林海雪原》中,“杨子荣”革命前的身份是“长工”,革命英雄仍然有着无法忽略的农民血统。“农民”身份,在这里一方面是阶级叙事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则成为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样板,农民英雄的崛起暗示了这样一种美好的结局——每一个田间地头的“平凡的儿女”都有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成长为“英雄”的可能。在《新儿女英雄传》的序言中,郭沫若概括了这种新英雄的逻辑:“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是他们的平凡品质使我们感觉亲热,是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感觉崇敬。这无形之间教育了读者,使读者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最真率的面目。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②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讲话》以来的农民革命书写都有一条相同的轨迹,即农民在人民战争中锤炼成长为群众英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淡化英雄和群众之间的界限,甚至所有的“平凡英雄”本质上就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没有超凡的个人能力,也没有过人的胆识,还时常流露出各种小私有生产条件下长期累积的毛病。这些“毛病”往往在残酷的战争中一点点被修正,另一方面也在组织上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介入和作用中,得到了改造和升华。所以在《讲话》后,我们看到的英雄成长故事,常常是通过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来完成集体主义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的宣讲。在这种个人英雄的冷遇中,农民英雄开始反思个人主义作风,不断提高觉悟领会集体主义思想精髓,实现农民英雄本质化的突破,从个人化到集体化,直到成为人民的英雄。《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就是这类典型成长历史的缩影:当他超越了旧时代农民的境界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时候,农民革命英雄才完成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转型。王一川把这一英雄蜕变进程命名为“原过——改过”模式,前者是中国农民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自私守旧愚昧散漫等不良风气,后者则是接受阶级意识和理性导引走出草莽英雄的在场姿态步入革命英雄行列。这些重新格式化了的农民最终被主流政治命名为新英雄,而新英雄形象判断的核心标准一样来自官方表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就强调了“工农兵群众不是没有缺点的,他们身上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遗留的坏思想和坏习惯。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以及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许多有缺点的人把缺点克服了,本来是落后分子的,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落后意识,成为一个新的英雄人物。”也就是说,有缺点的“工农兵群众”,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下”,克服了“自身缺点”和“落后意识”后,就可以成长为“新的英雄人物”。①周扬:《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第516页
通过周扬的报告不难看出,新英雄的锻造流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但莫言并不是非常接受这种判断英雄的方式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英雄世界观。在《史记》的读后感中,莫言提到项羽“英勇战斗就是他的最高境界、最大乐趣。中国如果要选战神,非他莫属。”在莫言看来,“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英雄,都敢于战胜或是藐视不是一切也是大部分既定的法则。彻底的蔑视和战胜是不可能的,所以彻底的英雄也是不存在的。……一般的人,通体都被链条捆绑,所以敢于蔑视成法就是通往英雄之路的第一步。项羽性格中最宝贵的大概就是童心始终盎然”②莫言:《读书杂感》,《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这里可以看出,作家坚信英雄是一种超越世俗、横行无忌的人生态度,是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性格,甚至是勇武好斗、精神焕发、生命力旺盛的多血质类型气质。而《红高粱》中我爷爷的形象正是作家这种英雄想象的形象化,小说突破了一直以来的农民革命书写的潜在逻辑,在意识形态缺席的背景下实现了对土匪司令余占鳌的英雄命名,用文本标识出八十年代文化关于农民成长历史讲述的民间化倾向和强烈诉求。
《红高粱》以抗日战争作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余占鳌的光荣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莫言的故事材料。与红色经典中众多的平凡英雄一样,余占鳌的个人身份仍然是农民,但也是个“坏事干尽,好事做绝的土匪,和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千百万群众的英雄不同”③莫言:《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前者始终是坚持个人化的本质化的存在方式,后者却成为群众的英雄,以集体主义的精神资源完成了自我蜕变。前者在反抗中始终强化着个人的辐射力量,而后者却在道德的提升中打造平凡的特质。在这种对英雄主体的去政治化和生命还原中,莫言以一种人本主义的方式大气磅礴地完成了农民社会身份溯源,新英雄在红高粱中用不同的形象参与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而作家则在八十年代的特殊语境中完成了民族战争历史背景下的英雄追认。
三、新文学视域内对强者本质的发现
刘再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文中分析了新时期文学的特点:“一是对历史的反思。二是人的重新发现,三是对文学形式的新的探求”。在比较了‘五四’时期与新时期文学对人的发现的异同之后,刘再复强调“‘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是对人的弱者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的文学则是对强者本质的发现,《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其滥觞。”④刘再复:《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雷达、李建军:《百年经典文学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再复这种对于《红高粱》在人的发现层面上的意义肯定,显然是在新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实现的。
在李泽厚的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重新启用五四时期的启蒙视角来挖掘《红高粱》的象征内核,这种土匪传奇对于从农民到新英雄的叙事成规的颠覆,无疑显示出启蒙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于强悍的历史主体的重新建构更是五四文化立场在八十年代的五四回归热潮中的再度复活。《红高粱》里“我爷爷”的经历在这一思潮中被彻底传奇化:余占鳌出身贫寒,十八岁时,杀了跟母亲勾搭的和尚,开始了流浪生涯;二十四岁时刺杀单廷秀父子,在墨水河里杀掉八个土匪后,正式落草。他的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没有成长小说中常见的主导者,也没有始终如一的道德观念,中国农民的一切缺陷与优点都在他身上得以具象化。在最早的新文学中,农民往往作为乡土中国的弱者,承受着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奴役,从而沦为文学革命的启蒙对象和社会革命解放的客体,但“我爷爷”无疑是个异类。
霍布斯鲍姆认为所谓土匪不过是农民对特殊环境做出反应的一种自我拯救方式,“作为个体,他们算不上政治的或社会的叛逆者,更不要说是革命者了;作为农民,他们拒绝服从……一般说来,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社会中的危机和紧张状态的象征……因此土匪活动本身并非是一种改善农民社会的进程。而是在特殊环境下逃避社会的一种自救形式”①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李俊杰等译,序言,第2-3页。。余占鳌波澜壮阔的人生无疑跟这种社会学观点吻合。作为游离于传统乡土中国宗法社会的边缘人,余占鳌用潇洒快意的以暴制暴彰显出极其强悍的人格内涵,刷新了新文学以来的农民形象。生长于乡间的莫言深谙中国农民的反抗轨迹,“多数的土匪都是真正的贫农、下中农,吃不上饭了,要饿死了,没有办法,只有当土匪去;还有很多是大户,日子过得很好的,被土匪糟蹋得没有办法了,索性毁家拉起杆子,也当上了土匪”。农民中的勇敢抗争不甘压迫的反抗者才有会成为土匪。余占鳌从匪前曾是乡绅社会的放逐者,独自一人身无分文,对金钱与物质有着强烈的渴望。作为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由人,余占鳌生于自然了无牵挂,纵情声色,嗜酒如命,爱憎分明,豪爽仗义。《红高粱》中他先后两次率土匪部队与日军作战,凭着性格中的勇猛强悍,余占鳌两次成就壮烈。莫言的描述会给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余占鳌的抗日行为很难提升到理想的政治高度,甚至携带着一种生命本能的明显痕迹,天性上不甘受辱、不受制于人,所以奋起反抗,在他自觉抗日的高尚行为背后往往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与生命力的驱动。所以《红高粱》中“酒色财气”和“英雄气”合二为一,彻底颠覆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卡利斯马形象和一直以来的英雄崇拜。莫言说过,“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被不断地传诵,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提高。在他们的历史传奇故事里,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的故事时,总是使用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总是洋溢着心驰神往的神情”②莫言:《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第189页。。而余占鳌敢爱敢恨、敢生敢死、野性十足、快意恩仇的江湖传奇,在作家这种携带着乡间朴素认知的强人判断中,被赋予一种更为冷硬的底色,更有热度的生命力量和呼之欲出的酒神精神。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黄子平曾经发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展的各个阶段,人们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悲凉沉郁之中缺少一点什么”的浩叹,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弱者承载了国民性改造和民族解放主题的全部历史合法性,因为弱者成为五四以来启蒙主义关注的焦点,“悲凉”的文学史整体面貌避无可避。在《红高粱》中,黄子平的遗憾得到弥补,余占鳌在新文学关于弱者苦难叙述的大格局下强势崛起,在八十年代文学中率先完成了强者的缔造。关于《红高粱》的文学史境遇,莫言自己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如果现在写一篇《红高粱》,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所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运。”①莫言:《莫言文集·小说的气味》,第189页。这种判断彰显出作者对于文本的准确定位和对八十年代文化的种种成规的把握。
作为产生“风景”的装置,八十年代中期的语境格外复杂。由革命到现代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板块置换的大背景下,八十年代文化政治凭借五四话语展开了对于文革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属性的围剿,伴随着“救亡压倒启蒙”历史讲述的深入,延续被救亡和民族战争中断的启蒙进程就成为八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在二十世纪国家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不难看出《红高粱》中创作主体的身份视角的调整、历史主体身份的重构,与新启蒙话语机制的复杂关联;同样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变的整体格局中,《红高粱》在军旅文学的战争书写、农民革命书写以及新文学以来各种人道主义文本的完整序列中,都显示出不同程度上的颠覆和创造,从而成为批评界和文学史长期关注的对象。基于这一点,《红高粱》整个小说甚至可以成为我们回返历史现场的理想入口,在昭示着历史的吊诡与暧昧的同时,为我们勾连起一个无限丰富而复杂的文学场域和一段漫长曲折的文学历程。
——刘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