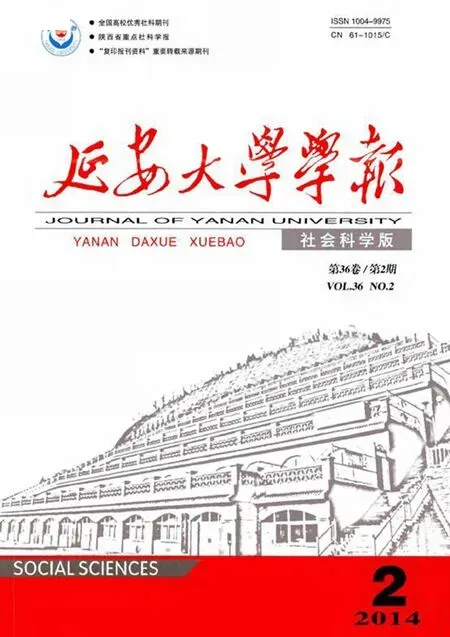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报刊
刘 艳 萍
(延边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世纪之交学界热议的“离散文学”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东方奇葩。随着俄罗斯友谊勋章获得者李延龄教授主编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1]和《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2]的问世,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才浮出历史地表,从“隐学”走向“显学”。而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就是20世纪上半叶在哈尔滨、上海、天津等中国城市先后创办的各种文艺性刊物,它们成为今天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认祖归宗”的历史记录和现实依据。那么,这些刊物是在何种背景下创办起来的?其时生存状况如何?对今天有何启示?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一、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报刊出现的历史背景
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报刊是伴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几次大规模的俄罗斯移民潮出现的。1897年,中俄签订修筑中东铁路的条约,于是俄罗斯移民大批来到中国,他们中既有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也有医生、演员、教师和神甫,还有记者、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以不同身份来到中国东北,而共同的特点就是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在异国他乡的孤寂中,他们迫切需要精神慰藉,这就为中国俄罗斯侨民报刊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和受众群体。根据O.巴基奇的著作《在哈尔滨的俄文报刊:1898-1961年历史书刊简介》所述,从1898年至1917年期间,在哈尔滨共出版了32种俄文杂志和45种俄文报纸。[3]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随之爆发的国内战争,使大批不满于革命“血腥”的人士离开俄国,一批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俄军官和士兵在战败后逃离俄国,还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因支持反革命活动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批判,并被逐出布尔什维克,被迫移民。譬如,1922年,托洛茨基下令把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1 000余名学者用船遣送出国,即有名的“哲学家之船”。[4]其中,一部分人去了欧洲,另一部分人则来到了中国东北。据史料记载:这次移民潮,流亡国外的俄罗斯移民大约在150万-200万人左右,[5]而“在前哥萨克军官谢苗诺夫的领导下,接近20万人越过中俄边界流落到哈尔滨”。[6]这就使哈尔滨的俄罗斯移民数上升为25万人以上。与上次移民潮不同,这次移民以知识分子居多,被称为“白俄侨民”,其中有社会活动家、大学教授、诗人、作家等,如组织成立“青年丘拉耶夫卡”协会的西伯利亚前哥萨克军官、诗人阿·阿恰伊尔以及阿·涅斯梅洛夫、瓦西里·别列列申等。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的存在与活动,直接促成了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报刊的兴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俄罗斯侨民报刊的繁荣时期,仅在哈尔滨的俄文刊物就达到400多种,其中俄文杂志近300种,俄文报纸100多种,数量惊人。
20世纪30年代,苏联实行强制性的农业合作化及肃反扩大化,迫使一批农民和知识分子流亡国外,他们很多人是偷越国境线而潜逃到中国哈尔滨,或者由哈尔滨转道至上海、天津等地。中国俄侨作家鲍里斯·尤利斯基在《米隆·沙巴诺夫的结局》中对此进行过生动的描述:1930年初,一批东正教旧教徒,携带自己的家人和家畜及生活用品,渡过黑龙江来到了中国东北。在渡江过程中,他们不得不与边防人员进行战斗。[7]他们之所以将哈尔滨作为首选地或者中转站,是因为它当时已成为继柏林、巴黎和布拉格等欧洲之外的俄罗斯侨民的第二家园,被称为“东方莫斯科”。19个国家在此设立了领事馆,除俄罗斯移民外,还有来自28个国家的移民。[5]尽管日帝在1931年以后控制了东北地区,实施限制并排挤俄罗斯侨民的政策,但是到1940年在以哈尔滨为主的中国东北地区居住的俄罗斯侨民,还有6万人之多。[7]无论在移民数量,还是保持俄罗斯文化特色方面,哈尔滨都远非其他城市和国家所能比。例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俄侨15 000—20 000人;[8]天津也不过数千人;而同时代的日本俄侨不超过2 000人;[7]可见,作为俄罗斯侨民在东方的中心,哈尔滨当之无愧。
哈尔滨还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发祥地。老辈俄侨作家数量不多,大部分俄侨作家是青少年时代随父母移民到哈尔滨,通过汲取这块土地的营养和文化而获得创作灵感,进而成为作家,如诗人瓦·别列列申、奥·斯阔毕浅克、尤·克鲁森斯滕-别捷列茨、叶·拉钦斯卡娅、拉·安捷尔先等。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哈尔滨,如尼·扎瓦茨卡娅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哈尔滨俄侨诗人和作家中,女性比重较大,有影响的是拉·安捷尔先、莉·哈茵德洛娃、维·扬科夫斯卡娅、玛·科洛索娃、纳·列兹尼科娃和叶·拉钦斯卡娅等。她们以其才华横溢和手法细腻活跃于当时的哈尔滨俄侨文坛。诗人或作家的创作必须借助于出版物,才能为读者所阅读,于是,俄罗斯侨民出版物也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量登载文学作品的哈尔滨俄侨报刊竟有243种之多。
二、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报刊的种类与内容
中国俄罗斯侨民出版业的发展可分成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俄侨出版业处于鼎盛时期,仅哈尔滨就发行了约270家俄侨定期出版物,[9]其中,既有儿童报刊《燕子》、《红日》,也有妇女报刊《女报》、《妇女与生活》,还有《军事简讯》等军事报刊和《满洲里报》等学术报刊。而《亚洲之光》、《叶尼谢伊斯克的哥萨克》、《远东哥萨克》等是俄罗斯哥萨克人创办的杂志,计24种,大大超过欧洲和北美的俄侨此类刊物。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北沦陷后,俄侨出版业受到限制,内容被严格审查,报刊数量明显减少。具有民主倾向的如《前进报》、《曙光》(1920-1940年初)、《祖国之声》、《传声筒》(1921-1940年初)、《戈比》等;黑帮分子的《俄罗斯之声》;法西斯分子的报纸《我们的道路》等。此外,还有文学杂志《边界》(1927-1945年)、《亚洲通报》(1909-1945年)等。
哈尔滨俄侨报刊绝大多数为私人创办,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哈尔滨102家报纸中有72家属于私人所有,杂志也类似,只有少数报刊是官方机构主办的。其中,《传声筒》报和《边界》杂志的创办人是来自阿穆尔边疆区的犹太新闻记者E.C.考夫曼;《曙光》报由M.C.列姆比奇创办,Г.Н.西普科夫担任编辑;《生活新闻》报由З.М.克里奥林和С.Р.切尔尼亚夫斯基创办,И.Ф.布伦克米列尔担任主编。[10]
《边界》是哈尔滨俄侨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文艺周刊,1927年发行,拥有稳定的读者群,发行了18年,出版了862期。《边界》的版面不大,约为20—28个页面不等。从1929年夏开始,《边界》转为周刊,每周六出刊。内容可谓丰富多彩,并配以五颜六色的插图和照片,非常新颖。由于出版商和主编的共同努力,极大地提升了《边界》的威望,订阅者和读者数量显著增加,堪与巴黎俄侨文艺类刊物《带插图的俄罗斯》相媲美。该杂志于1945年8月停刊。[11]
《边界》登载的文章既有政治性论文,也有专门阐述俄罗斯文化各种观点的文章。譬如,有关战争的危险性、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以及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看法。除了当地新闻和可靠的国际消息外,《边界》也介绍俄罗斯历史纪念日,作家、作曲家和艺术家的生活与活动,音乐会或戏剧演出的广告,甚至还有文艺家讲座的摘要、方志学和经济消息等,这些内容无疑丰富了哈尔滨俄侨的业余文化生活。此外,杂志还辟有“妇女之友”、“书讯”等专栏。《边界》繁荣时期(1931—1936年)的印数近25 000册,多数订阅者都是哈尔滨及中东铁路(КВЖД)沿线的俄侨,此外上海、北京、青岛、朝鲜、日本约有200—300册,剩下的是俄侨所在之地,如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其他地方,在波斯、土耳其、南北美洲以及澳大利亚也有订阅者。[12]《边界》杂志的通讯记者遍布世界许多国家和城市。
《曙光》发行于1920年,分早报和晚报,由富有传奇性的天才记者、出版商M.C.列姆巴维奇和西伯利亚人Г.Н西普科夫主持。《曙光》报不仅在哈尔滨,而且在中国乃至俄罗斯域外都是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在俄侨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11]1924年发行量已达到12 000-15 000份。《曙光》报把一大批欧美著名的俄侨作家和记者也吸纳进团队中,从而建立起广泛的通讯网。1920年,《曙光》出版社还发行了幽默文学和戏剧杂志《启明星》、《我们的曙光》和《上海的曙光》。1942年8月20日,《曙光》报被日本傀儡政权满洲的半官方刊物《哈尔滨时代》所取代,被迫停刊。《曙光》发行时间长达22年,版面也由最初的4个版面扩展到1930年以后的8个版面至16个版面,是哈尔滨俄侨定期出版物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报纸。
《传声筒》由《家园》出版社出版,由С.Я.阿雷莫夫、И.И.别杰里内依和И.Л.米列罗姆等先后任主编。该报在报道俄罗斯侨民文化生活事件等政治新闻的同时,还刊登戏剧与音乐剧评论、艺术活动家、俄侨作家和苏联作家的照片。[11]与《边界》和《曙光》一样,它也辟有“妇女之友”专栏,对女性读者充满着真诚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支持。化名为“卡里奥斯托罗”、“公爵夫人”、“当代唐璜”等名家的座谈以及丰富有趣的“满洲里故事”缓解了俄侨生活沉闷的气氛,给人以轻松和愉悦。特别是对一些感觉前途渺茫而失去信心的女性以极大的鼓励,成为其精神支柱。
《亚洲通报》是由俄罗斯东方社会学家学会(ОРО)主办的内部杂志,于1909年7月创刊,1938年停刊,总共发行了54期。И.А.托博罗洛夫斯基、Н.К.诺维科夫等先后担任主编。该杂志发表的基本上是“ОРО”成员的文章,内容多是亚太国家和俄罗斯远东的历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13]
三、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报刊所载文学的题材与主题
综观哈尔滨俄侨报刊上文学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俄罗斯题材;二是中国题材。其中,尤以前者所占比重最大,而且每类题材中又蕴含着不同的主题。
在第一类题材中,抒发对祖国的怀念之情是第一大主题。例如,阿.涅斯梅洛夫的《盖尔·吉茨涅尔》,亚历山德拉·巴尔考的《回忆》和科洛索娃的诗集《先生,摆脱不了的俄罗斯!》等作品都以祖国俄罗斯为题材,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远离祖国的苦闷和身在异国他乡的失落感。维克多里娅·扬科夫斯卡娅的诗《在国界边上》这样写道:“我住在远离湖畔的草房/俄罗斯国界从那里通过/我苦苦地思念/我梦中的家乡……”[4]
由对祖国的怀念生发出坚定地保护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意志,即对东正教的虔诚与膜拜。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失去了故国的根基,视东正教为逝去生活的寄托和精神家园,表达出强烈的宗教情感。他们恪守教规,按时去教堂做礼拜。十字架、圣水、唱诗班、圣诞节、受洗日和复活节不仅是他们尊崇的圣物和节日,而且也被俄侨诗人写进诗中,譬如,E.毕彼科娃的《基督复活》、E.涅杰里斯卡娅的《多样的命运》等。俄侨诗人和作家把崇奉东正教作为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鲜明体现,因此,后来文革中当许多教堂被毁时,女诗人M.维吉在《副本》、《大哭》等诗中表达哀痛之情。
对苏维埃政权、国内战争与革命以及肃反扩大化、强迫农业合作化等给普通人带来的伤害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哈尔滨俄侨文学俄罗斯题材所表达的主题之一。例如,涅斯梅洛夫的《哈尔滨——我的摇篮》:“‘俄罗斯的!’因为又饿又怕,/于是不顾一切铤而走险。/没什么理由感叹和唱歌,/他们祖国已被疾病传染。”[8]在诗中,诗人倾述了自己离开祖国的原因,是祖国俄罗斯染上了疾病,委婉地表达出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和怨恨。
在第二类中国题材中,俄侨诗人把中国特别是哈尔滨作为第二故乡,表达自己对她的亲近之情。瓦.别列列申称中国为“温柔的继母”,涅杰里斯卡娅则称中国哈尔滨为“我的小祖国”。诗人们对哈尔滨比较完整地保持了俄罗斯文化传统心存感激,也视这片热土为自己的重生之地。涅斯梅洛夫的同名诗和小说《老毛子》刊登在1940年《边界》杂志第24期和第30期上,内容都讲述了俄罗斯人逃难到中国时,边防军如何无情地开枪打死父母,而中国人又如何收养俄罗斯孤儿的情景,生动感人。作家将作品命名为《老毛子》,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哈尔滨人对俄罗斯人的印象和观感,在他们的想象中,老毛子就是“长着棕红色胡须的俄罗斯人”。
这种称呼既有哈尔滨等中国东北民众对沙皇时代掠夺中国大片土地的俄国侵略者的历史记忆,又含有对今日与之朝夕相伴、共度苦难的俄罗斯侨民的重新认知和接纳,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同样,俄罗斯侨民对中国人也充满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亲近他们,另一方面又感到这毕竟是异国他乡,是客居之地,不是永久生活之地,因此,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哈尔滨的大批俄罗斯侨民相继离开了哈尔滨。
四、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报刊对中俄文学与文化的巨大贡献
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报刊不仅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载体和生命,也对中俄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扩大了俄罗斯传统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边界》等文艺性刊物每期都登载1-2篇俄罗斯经典作家的原创小说,1-2篇翻译故事,这就为哈尔滨俄侨和懂俄语的中国人打开了了解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视野。例如,1937年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仅在当年头3个月,在《公报》、《朝霞》、《哈尔滨晚报》、《喉舌》、《我们的道路》等俄侨报刊上,分别发表了76篇、60篇、55篇、40篇、35篇、35篇纪念普希金的文章和报道,总数达301篇。[14]可见,哈尔滨俄侨诗人和作家对祖国传统文学的真挚情感。
其次,培养了一大批哈尔滨俄侨诗人与作家。哈尔滨仿佛世外桃源,为远离政治漩涡的俄侨提供了舒适安静的创作环境,A.涅斯梅洛夫、瓦.别列列申、B.H.伊万诺夫、玛·科洛索娃、拉·安捷尔先、维·扬科夫斯卡娅、米哈伊尔·谢尔巴科夫等一批年轻的诗人和作家,伴随着《边界》、《传声筒》、《朝霞》、《丘拉耶夫卡》等刊物的存在而成长。其中,《边界》的贡献尤大,几乎每期都登载7-8篇哈尔滨俄侨诗人和作家的作品、翻译或特写,这对俄侨诗人和作家不啻是施展文学才华的“练兵场”。正如著名诗人和俄侨文学研究者尤里·杰拉比阿诺在诗选《流亡者的诗神》序言中强调指出的:“在中国‘有很多文化和天才之人’”。[15]显然,哈尔滨成为堪与欧洲俄侨相媲美的中国俄侨的基本文学力量之所在。
不仅如此,一些在苏联国内不被认可的文章却可在哈尔滨俄侨报刊上得以刊载,保留了与俄罗斯主流媒体不同的声音。比如,“白银时代”著名诗人K.巴尔蒙特在苏联时期是不被“普罗文学”承认的,作品也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可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为社会服务》是1937年在哈尔滨出版发行的。尽管发行量较小,但是《边界》第48期登载了娜塔莉亚·列茨尼克娃为此撰写的书评,《哈尔滨时报》1937年12月7日也发表过B.阿巴利亚尼诺夫的书评,这些书评在“白银时代”文学得以翻案的今天价值弥贵。
最后,丰富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东北文学。哈尔滨俄侨文学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语言是俄语,却并不意味着其读者群只能是俄罗斯侨民。哈尔滨在当时是多民族融合区,当地的哈尔滨人不可能不受到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拉·安捷尔先在自传中就曾谈到,中学毕业后,她教中国孩子学习俄语。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哈尔滨人有深厚的俄语基础,这为阅读《边界》等俄罗斯侨民报刊扫除了语言障碍,进而从报刊这一媒介再次了解和认识了俄罗斯民族文学与文化,促进了中俄文学与文化的直接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也是中国东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哈尔滨俄侨文学与报刊在20世纪上半叶起到了中俄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作用。正因为有了俄侨报刊与文学,生活在中国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地区的俄侨不再感到被遗忘和被抛弃,报刊与文学给予了他们克服生活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开阔了眼界。同时也为中国人了解俄侨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以及著名俄侨诗人与作家作品创造了条件。从另一方面看,俄侨也从不同民族文化的比照中学会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中国民族特殊性,从而获得了共同生活的经验。
[1] 李延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
[2] 李延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3] [日]泽田和彦,刘丽霞译.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杂志概述[J].俄罗斯文艺,2012,(1):67.
[4] 张坤.论中国俄侨女诗人的群体崛起[J].俄罗斯文艺,2012,(1):42,44.
[5] 张岩,李延龄.论俄侨女诗人莉·哈茵德洛娃诗歌创作[J].俄罗斯文艺,2012,(1):46,48.
[6] Сюй С.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нции в Китае(1920-1940-ое годы)[M].Москва:Изд.ИКАР,2003.
[7] [日]望月恒子,杨雷译.20世纪初期日本对中国俄侨文学的认知[J].俄罗斯文艺,2012,(1):33,31,31.
[8] 李延龄.再论哈尔滨批判现实主义[J].俄罗斯文艺,2012,(1):5,5.
[9]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ГАХК).Ф.28.Оп.1.В1[Z].139.
[10] Весь Харбин на 1924г[N].Харбин,1924.
[11] Мелихов Г.В..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1917-1924гг)[M].М.,1997.78-79,79,79.
[12]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путь(Харбин)[N].1923-01-28.
[13] Русский эмигрант(Харбин)[J].1920,(1):1-3.
[14] [日]生田美智子,何雪梅译.哈尔滨俄罗斯人:东方俄罗斯侨民的同一性问题[J].俄罗斯文艺,2012,(1):60.
[15] Колосова М.В..Отра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ов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я в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й печати[J].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5,(48).
——以美国、爱尔兰和印度为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