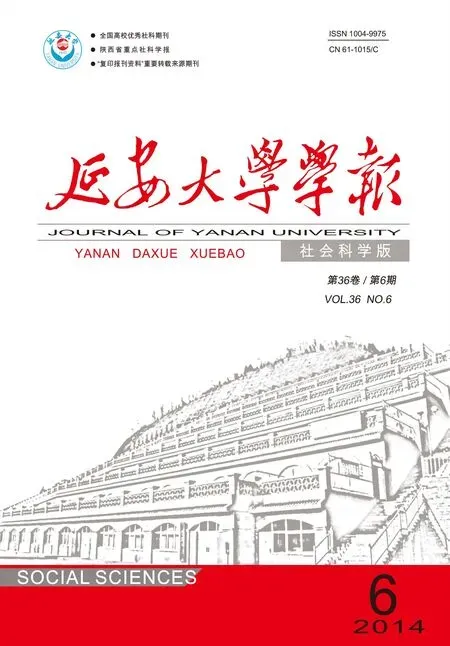马克思幸福观的人民向度
高延春
(1.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延安大学 泽东干部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任何一种幸福观都是基于对“人”的理性思考和终极关照,马克思幸福观与以往西方幸福观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本位。它以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给予人的幸福以科学的阐释,将幸福落脚于人民的现实幸福,进而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劳动异化等一系列现象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深入实际地考察工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寻找到实现人民幸福的领导力量即无产阶级,最后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人民幸福的最高理想。剖析和梳理马克思人民幸福观的逻辑理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幸福观的逻辑起点
人性思辨是西方幸福观的根基,因为幸福始终是“人”的幸福,幸福观的内在逻辑无法缺失人性规定,而不同的人性规定决定着幸福观独特的理论走向。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西方幸福观都把人性或人的本质归结为永恒不变的、超越一切历史条件的人类共性,脱离了实践活动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来探讨人,使人的幸福游离于生活世界之外,成为纯粹的自我意识或生命感受。其中,黑格尔认为人是一个主客统一性的自我意识即精神,幸福是人与自身和谐的自我发现,它并不扎根于历史的土壤。费尔巴哈则认为人的生命本身就是幸福,幸福只是某一生物健康的正常的状态。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深刻地批判了人性的非历史性和非现实性,强调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伟大意义,完成了从抽象人的幸福观到现实人的幸福观的转变。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的首要的观点,也是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7“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2]47说这明了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生产生活是类生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不是超自然的绝对精神和动物的本能使然,而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人的“类生活”是实践生活,人的“类存在”是实践存在,人的“类本质”是生产实践。既然人的生活是实践生活,而人的幸福来自于人的生活,人的幸福必然是对实践性生活现状和生存境遇的表达和反映。实践是人具有的普遍共性,也是人类独特的生存活动,幸福必然在实践活动中展开和实现,它是符合人的实践本质的生活。但这时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的人还处于脱离历史和现实的抽象状态的人,他并不能具体地呈现历史的宏大叙事,这就导致幸福丧失其应有的现实性。由此,马克思继续思考人的现实本质,反对黑格尔把类解读为一种“自我意识”的呓语,同时也反对费尔巴哈把类理解为一种把许多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内在的、无声的普遍性,最终把人的幸福回归于现实生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6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像的东西出发”[2]73。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精神实践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实践,认为二者共同的缺陷是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致使幸福远离人的生活实践。由此,马克思实现了由抽象人的幸福观向现实人的幸福观转变。接着,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79在满足吃喝住穿需要的生产实践中,人能够展示并确证人之为人的本质,感受生活的幸福和快乐,进而创造人类历史。所以,人的幸福就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人的实践本质的实现。可以说,人类社会历史是一部生产实践的历史,也是一部追求并实现幸福的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和幸福生活的创造者、推动者并不是所有人的实践,而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其依据在于,只有现实地从事生产实践的人,才真正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幸福的创造者。马克思把从事生产实践的人称之为“人民”或“人民群众”。这表明了人民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幸福的主体;幸福并不仅局限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每一个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事实并非如此,人民创造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却陷入贫穷、卑贱和不幸当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3]。人民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人,人民的幸福必然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主要体现为阶级关系。马克思认为:“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4]239在阶级社会中,极少数的特权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借此驱使人民群众创造并占有社会财富,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不到快乐和幸福。所以,马克思把幸福落实到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民,这就使马克思幸福观是为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谋求解放的幸福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
二、“劳动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对现实人民幸福的深刻反思
马克思从德国政教合一的事实出发,在反对黑格尔把国家政治制度超越于基督教之上的主张同时,肯定了费尔巴哈将神的本质看成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对宗教信仰的否定引出对现存国家和社会的批判,认为人民在专制制度下生活直接导致经济关系中人的异化,于是将批判的矛头由宗教信仰转向市民社会,再指向异化劳动,最终定位到私有财产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寻找到一条实现人民幸福的道路和途径。
马克思在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鲍威尔把人民幸福归结于天国的错误做法,指出宗教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1由于现存的国家和社会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正是在这种“颠倒了的世界”里,劳动人民过着劳而不获,饥寒交迫和备受屈辱的生活,才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幻想世界。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把神学问题看作是世俗问题的观点,但他发现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指出产生人民不幸的根源不在宗教中,而在产生宗教的社会关系中。对宗教的批判揭示了装饰在“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只是对“苦难世界”批判的“胚芽”,而现存制度的“锁链”给劳动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不幸,这促使马克思的批判由“天国、宗教、神学”转向“尘世、法、政治”。“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2]2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通过政治革命破除了禁锢在人身上的封建专制和基督教蒙昧主义的枷锁,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治自由和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权”,确立了“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价值原则。然而,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它没有彻底摧毁宗教枷锁,也没有消除人民的宗教信奉,只不过是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以“理性的信仰”替代了“神的信仰”而已。然而,这正恰好成了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特权和表征。在伪善的人道话语下造成劳动人民非人性的存在本质和极端的不幸福。马克思开始关注隐藏在政治现象背后的物质关系,进一步思考“劳动异化”。他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5]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实践去考察工人的生存状态,揭示劳动出现了“物的异化”、“活动着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异化”的四大“异化”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2]52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54。马克思对使工人陷于不幸境遇的批判直接指向“劳动异化”,而分工是“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85在这样的社会里,劳动人民不可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享受自身活动的乐趣。
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这决定了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6]45。无产阶级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且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革命阶级,决定了它是变革现实世界的领导力量,它须带领人民群众从事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真正的现实的人民幸福才能得以实现。这个革命实践既批判了黑格尔为现存东西辩护的保守意识,也反对费尔巴哈把现存世界庸俗理解的简单方法,主张革命不是对现实的改良或对弊端的补救,而是以改变现实的斗争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活动。因此,马克思把人民幸福从寄托于神、宗教,到政治、法,再到革命实践,剖析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带来了私有制,私有制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集中体现为阶级关系。这样,马克思幸福观通过对一系列异化的层层批判中挖掘出造成工人不幸的真正原因,找到变革现实世界的领导力量和实现方式,成为无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实现人民幸福的科学理论。
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民幸福的最高理想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后一个阶级社会,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人民群众反对剥削阶级的最后一个形式。由于无产阶级地位、物质需要和锁链的强迫,决定着它是人民群众中最主要、最坚定的革命力量,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摧毁一切奴役制度,消灭一切私有制及其异化现象,建立与无产阶级相适应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人人自由平等而全面发展,真正实现了人民幸福。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统一实现。满足人的需要是人的幸福的本源性依据,因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7]人的需要归纳起来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幸福内容相应地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马克思一方面批判脱离人的生理或物质需要的禁欲主义幸福论,认为一定物质需要的满足是维持人体生命和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8]另一方面也反对远离人的心理或精神需要的纵欲主义幸福论,认为人的幸福更重要地体现于精神需要的追求和满足。吃、喝、性行为等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9]9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需要只是为了拥有他想活下去所必须的需要,工人的需要降低到甚至低于动物的需要,更无法谈及幸福问题。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民的幸福真正实现。“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0]。
其次,人民的创造活动和享受过程统一实现。人的类特性和类生活在于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改变现实世界的活动,这种创造性生产实践使人得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马克思反对禁欲主义所提倡的清教徒式苦行僧生活,认为享受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成果是劳动人民的正当权利,它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也否定纵欲主义所主张的享受就是幸福的全部内容的错误观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使劳动者不是出于自愿的、本质的活动,而是被迫的、外在的强制行为,结果是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越是失去外部的生活资料和生产乐趣;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自己就越贫穷。要使劳动由作为增值资本等外在目的的手段转变为劳动者充分发挥自己劳动能力的过程,必须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那时的“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1]。
最后,人民的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统一实现。现实的人是个体和社会相统一的存在。马克思没有把个体的人孤立于社会而抽象地谈论幸福问题,他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9]122-123个人以社会为存在对象,个人幸福只有在社会集体中才有可能实现。一方面,社会为个人幸福提供制度前提和社会条件。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也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个人幸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4]532。对于阶级对立社会而言,这个集体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的“虚幻的集体”,它只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而不是为了劳动人民。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个人作为个人参加”的“真实的集体”,它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我们决不想破坏那种能满足一切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真正的人的生活;相反地,我们尽一切力量创造这种生活”[6]626。
在马克思哲学中,“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民的主体始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马克思幸福观正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论证人民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幸福的主体,只有无产阶级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推翻使人民陷入不幸福状态的社会制度,建立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幸福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人民”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内涵有所变化,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幸福生活的历史使命,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当前,实现“中国梦”在生活层面上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梦”。由于我国正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之改革开放引发许多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影响人民幸福的一系列民生问题。党和政府必须从“现实的人”的生活需要出发,以“生活”的逻辑替代“资本”的逻辑,以“人民幸福”为本置换“经济增长”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0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
[8]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5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44.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