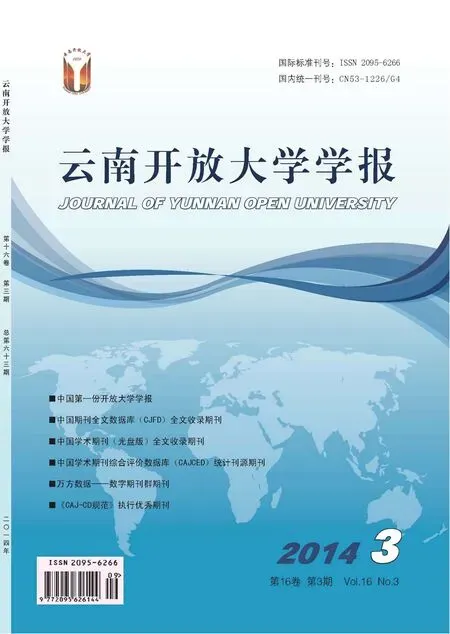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形象与权益公共空间的构建
刘保庆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形象与权益公共空间的构建
刘保庆
(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侵正由“显”到“隐”,维权形象和能力不容乐观,其维权方式的失效同城乡移动所带来的“权益共同体”的中断密切相关。乡民在乡村受到乡村“权益共同体”的保护,走入城市意味着乡村“权益共同体”的失效,而城市又没有为其提供相应的维权方式对接,从而造成维权效果低下。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地方性权益空间建设为基础,以国家法律法规等体制为依据,以新生代农民工人大代表和权益领袖为主体,通过“事件化”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建设社会诚信空间,最终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公共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侵权“隐”向化;权益共同体;权益公共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已经关系到我国城市、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形象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集中体现在维权行动及其成效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侵存在显、隐两个层面。“显”层面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时受到不平等条件——城市户口——的限制;同等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同工不同酬;新生代农民工受工伤,赔偿远低于城市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若想成为市民,在许多城市要买到至少60平方米的房子。此外,还有未签订劳动合同、缺少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差等等侵权现象。
学术界、传媒界对“显”层面关注很多,却对“隐”层面关注甚少。“隐”层面指隐微的、不被公众乃至农民工所认知的侵权现象,也指侵权行为受到招工单位有意遮蔽。据笔者访谈,有些单位严禁工人相互谈论工资待遇,若工人对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提出异议,单位在年终综合考评时会给予极低的评分。个人考评除了参考工作年限、学历等显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个人综合印象分。这种考评的含糊尤其是考评条件的不公开、不透明,致使农民工权益受损时竟茫然无知。还有的单位禁止工人上报工伤情况,若有人上报工伤,实行个人、组长、科长三级连坐制,都要受到批评和记过处分。这种严厉而隐微的惩处制度,再加上工人个体间的隔阂,严重约束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的积极性和可能性。相比于“显”层次的侵权行为,“隐”层面的侵权行为更为隐蔽,限制了农民工组成团体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随着国家出台许多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这种侵权“隐”向化现象可能会更普遍,更难发现。
侵权必然带来维权。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形象并不乐观,可以分为如下四种。其一是逆来顺受型,表现为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只好忍气吞声。据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害怕被报复不敢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占6.5%[1]。尤其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理性上对权益受侵毫无认知,对国家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只有53.9%的新生代农民工仅仅知道有《劳动法》,但对其具体
详细内容几乎一无所知[2]。这带来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把权益受侵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即使感觉到不公平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述。当发生劳动纠纷时,选择“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的比率分别是11.54%和19.23%[3],也就是说30.77%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选择忍气吞声。如果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权益受侵可能毫无认知的情况,这个比率会远远超过30.77%。招工单位侵权行为走向“潜”层化,更加重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的难度。其二是消极反抗型,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可能会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和行为。媒体报道中频现“跳楼秀”、“跳桥秀”等文章固然映射出新闻媒体迎合市民窥视欲望的报道趋向,同样也间接折射出农民工维权时以死相逼的无奈心态。富士康频频发生新生代农民工跳楼事件,折射出问题的严重性。其三是集体协商型。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上,个体维权的力量都是无法和招工单位相抗衡的。阿尔蒙德讲:“利益表达是要付出代价的,坚持持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量很大,靠公民个人无力承担。”[4]当个人无法维权时,新生代农民工会采取联合起来,以集体的方式来和单位进行协商,其手段可能是罢工。集体协商的维权方式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家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这是团结的前提;二是为团体谋利益的代表出头来和招工单位协商。目前看来,这两个条件很难同时出现。一是现代工厂的分工细密,农民工被分割在不相关联的车间。工作的细密分工带来“权益同受侵害”的意识会降低,这种“同受侵害”的共同体感受会影响到团体的人数,直接影响协商的成败。二是“枪打出头鸟”的根深蒂固观念影响了团体代表的出现。招工单位严禁谈论工资待遇的严酷管理制度,使得这种“同受侵害”的共同体更难培养。第四种类型是寻求法律援助。经调查,受访者在问及如何看待法院的裁决时,只有30%表示有信心,60%信心不足,还有10%完全没有信心[5]。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寻求法律维权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法律意识淡薄的自身因素,更有法律维权高成本的代价(为讨薪1000元,要付出最低920元的代价),尤其是“官商勾结”观念的牢不可破。
以往学界有一共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也由被动转向积极。这一共识的形成离不开将其与传统农民工对比的研究模式,其实“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作为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这一研究视野约束了对新生代民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学术界多采用调查法通过数据分析来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和维权行为特点,而对其维权方式及其内在机制甚少关注,没有放在城乡移动背景下传统维权方式的失效上来考察。
二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侵为何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采取集体协商的维权模式,困境在哪里?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真的脱离了农村以及乡村社会那一套生存方式呢?
传统士绅在社会稳定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权力体系分为两个层次:上层有中央政府,下层是由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自治团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和大家庭自然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供给这个团体中的一个人去上学,一直到他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就有了靠山了。”[6]传统士绅虽然没有政治权利,没有行政立法权,但是有行政管理权,有政治免疫性。士绅享受地方乡民所授予的权力,甚至拥有和中央斡旋的力量,成为维护地方权益和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核心阶层。这种有机自治团体在近代被打破了,其标志是近现代知识分子离开了农村,在精神上只能在城乡之间徘徊。
建国至今,传统“士绅”消失了,不过并不代表这一阶层存在的功能及有机结构就消失了。笔者考察了河南省内黄县和武陟县部分村庄,发现传统四民阶层的有机体在当今有了新的变迁。有三类性质的机构和人在维护着农民的权益和安定。一类是买卖“交易员”,这类人在乡村充当商品交易协调的中介功能。交易员一方面为收购人充当本地向导的身份,因为收购人不了解哪户人家打算卖地黄或牛犀;另一方面充当了农户和收购人两方的保护人角色,维护双方的权益,从而使得交易公平、公正。第二类是家族中有名望的人,这类人不仅调解
本家族内部的矛盾,有时还解决乡村中的利益冲突。最后一类是乡村自治团体,如红白理事会、管事会等。管事会管理范围广泛,主要解决乡村事务冲突。红白理事会负责乡村婚嫁、丧葬事宜。在乡村,婚嫁和死亡代表了生、死,是人生大事。两者办理起来都很麻烦,需要专门的人员来负责,否则就会出错“丢面子”。其中,遗产以及丧事任务分配都涉及切身利益,没有中间人的协调,就会出现矛盾冲突。
这三类人仍然具备费孝通所指出的特点:一是有“名望”,在乡村他们办事“公正”、“合理”,虽然这里的“公正”、“合理”未必符合国家法律,但符合乡村的道德伦理规范,符合乡村人对“公正”、“合理”的理解共识。二有“知识”,即乡村遵循的一套社交行为模式和处理矛盾的方法,而非科学知识。三是他们所行使的权力是村民自愿给予的,不具有强制性,而非国家行政权力。四是会写字。
这三类人的权力由于是村民所给予,不具有强制性,其效果依靠的不是外在的法律,而是村民共同遵守的乡村伦理道德及公平感、正义感。其原则有两个:一个是共赢原则;一个是双方伤害最小化原则。其成效不仅取决于村民内心的公平感,而且取决于村民的外在约束机制。这种约束机制体现为乡村权益共同体“看客”的羞辱感。传统学术界关注到鲁迅文学作品中的看客现象,并将之解释为对国民劣根性和麻木的批判。这种解释有其说服力,却忽略了这种看客在维护乡村稳定以及村民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如果有村民不服从上述三类人的调解,精神上将承受整个乡村“看客”的指责和评价。乡村舆论的压力会使得违背乡村道德和公平的村民抬不起头,难以在乡村立足。这种精神上的制裁才是三类人权力的约束性机制。
这三类人和村委会在维护农民权益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共同组成了农民的“权益共同体”。如果这一保护体无法保障农民的权益,最后才会诉诸法律。但是诉诸法律面对的巨额代价违背了共同体的“双赢”与“伤害最小化”原则,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采用的。
农民工离开熟悉的乡土,走向城市,意味着由这四类人组成的“权益共同体”也将消失。乡村空间范围的确定保证了村民之间的熟知,从而有利于形成乡村“权益共同体”,有利于培养乡村“看客”的精神约束机制。农民工对乡村的想象是可能的、具体的、带有情感色彩的,但是对城市的想象是不可能的、抽象的、情感单薄的。城市只能让他们感知到川流不息的人群而非熟知的个人。城市的流动性造成上述四类人以及乡村“权益共同体”的消散,使得农民工找不到乡村保护体。
当权益受侵时,农民工像往常一样希望得到乡村“权益共同体”的保护。经调查,55%新生代农民工向老乡亲友求助[7]。如果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45%这个数据其实传达的只是一种希望,现实中真正诉诸法律的要远低于45%。“权益共同体”的消失,法律意识的淡薄,尤其是个体与招工单位力量对比的悬殊,这不仅包括经济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再加上传统根深蒂固的“官商勾结”的心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选择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消极反抗两种方式。当感到无路可走,诉诸暴力反抗,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消极维权的方式。近几年绑架老板,偷盗工厂东西等事件的频发,已经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农民工犯罪占农民犯罪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30%上升到2005年的85.71%,2006年增至88.94%[8]。随着传统农民工退出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年轻气盛的特点将使得其消极维权的情势更加严峻。新生代农民工维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谐、安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
为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切身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必须将乡村“权益共同体”重新构建起来。在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公共空间”的构建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
(一)利用互联网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公共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带来现实公共空间建构的困难,互联网的出现有助于培养共同体的公共空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论述过民族主义,提出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通过报纸和小说,使素不相识的人们激发出一种“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每位成员的心中[9]”
的身份归属感。以互联网为平台,开设专门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为目标的网站。通过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网站,培养全国各地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感和阶层感,形成一个以新生代农民工为核心的社会团体。互联网有缩短时间和空间的特点,为培养这种权益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
新生代农民工上网人数越来越多,上网能力也有很大提高。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总体文化水平高于传统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人数占54%,高中人数占29.3%,文盲和小学人数占11.6%[10]。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业余时间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比例为46.5%和52.1%[11]。这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公共空间的开创打下了物质条件。不过,通过互联网来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则有待提高。
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公共空间,最终在于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团体意识,即阶层意识。在此公共空间,新生代农民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互联网,使得个人意见形成为阶层意见,使得个人声音升华为阶层声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力量和权益的最大化,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到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
目前,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多关注于外在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等,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改变自身命运的主动性,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只有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意识,让其参与到社会权力结构优化中来,才能实现其权益保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权力的博弈中达到各阶层的权益均衡,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
(二)以农民工人大代表和农民工权益领袖为主体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公共空间的构建脱离不开主体的培养,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大代表,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权益领袖。前者已经成为现实,2011年全国人大代表中有3位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代表,这显示了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不过,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大代表不是由农民工自己选举产生,而是由工厂所推荐,以至于当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当上人大代表时倍感意味,感叹有职无权。新生代农民工人大代表还面临人微言轻,所提问题得不到切实改进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领袖则不同:由于自身知识、声望以及对某一行业的熟知,他们能够并且愿意承担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担,成为得到广大农民工认可和拥戴的权益维护代表。这样的权益领袖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职业类型,其中尤以律师为典型,如河南固始的胡永明律师、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王振宇律师等。当个人无法抗衡一个组织如招工单位时,无数的个人会组织成团体来维护权益,这个团体自然要有团体维权代表。一旦这些维权代表维权成功,会被周围的人视为利益代表,他们如果接受了委托,就成为了维权领袖。维权领袖的力量会随着维权成功案例增多而扩大,从而提高其社会身份、社会资本和社会影响力。胡永明是固始总工会驻盛泽维权中心主任,是固始少数获得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考试的维权者,他的事前不收费、成功后再按比率收取报酬的方式广受农民工的欢迎,成为信阳劳模、固始维权旗帜,被央视等中央媒体广为报道。固始和盛泽,前者为农民工输出地,后者为输入地。大量农民工输出,使得“两地政府产生了劳工服务和维权上的协调需求,更衍生出一条以老乡为纽带的维权产业链,胡永明堪称行业领袖。”以地方性权益领袖为主,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切实维护当地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最后形成全国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团体,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目前这种农民工权益领袖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权益领袖自身权益无从保障,胡永明被扣上“违法收费”的帽子在看守所被拘,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王振宇律师所概括的“大量群众维权代表被定罪现象”值得关注。二是这种权益领袖还有待扩大,数量太少。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领袖需要扩大范围,吸纳各行各业人才。张海超通过开胸验肺来维护自己权益固然让人无奈,但如果得不到医院力量的支持,他可能连举证都很困难。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出身的权益领袖需要培养。社会其他行业权益领袖毕竟和农民工有隔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过法律知识学习,最终成为维护本阶层的权益领袖。
(三)通过“事件化”社会舆论建立监督机制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维权的成效有限,只有团结在一起发挥集体的力量才有维权成功的可能。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不仅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的支持,充分吸收各种人才加入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共同体”中来,而且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力量,最终形成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公共空间。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利用传统报纸,而且要利用互联网视频、微博等来制造“事件化”社会舆论,建立社会诚信监督机制。现实中,个人通过法律打赢官司但权益却无法落实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有些单位改换名字使得法院判决无从落实,有的单位对法院判决不理不问等等很多。如何消除这种现象,不仅需要加强法院判决的执行力度,而且可以借助媒体的舆论压力,来迫使侵权单位执行法院判决。这就需要“事件化”社会舆论的作用。“事件化”社会舆论指,当侵权现象——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权益受侵还是群体权益受侵——发生时,报纸、互联网视频、微博等媒体跟进,加强深度报道和持续报道,让权益受侵行为成为轰动性的社会事件。这种“事件化”社会舆论能够成为约束招工单位等机构的诚信监督机制,形成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诚信舆论空间,并将这种诚信内化为招工单位的内在自身约束机制。
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地方性权益空间建设为基础,以国家法律法规等体制为依据,以新生代农民工人大代表和权益领袖为主体,通过“事件化”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建设社会诚信空间,最终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公共空间,培养成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共同体”,才能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1]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6-21.
[2]严新明,杨海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J].阅江学刊,2011,(1).
[3]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
[4]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陈咏梅.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问题研究[J].天中学刊,2010, (3).
[6]费孝通.中国士绅[M].北京:三联书店,2009.
[7]熊易寒.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力意识[J].文化纵横,2012,(1).
[8]张诺维.构建预防农民工犯罪的长效机制[J].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9,(3).
[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11]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J].数据,2011,(4).
Establishment of Rights Protection Image and Public Spac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U Bao-qing
(School of News and Communication,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1,Hena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infringed from the“obvious” to the“hidden”,and their rights image and ability are not optimistic.The failure of the rights prote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rupt of the“rights and interests community” formed by urban and rural migration.Villagers are protected by the“rights and interests community” in their rural villages,but when they move to the city,the rural“rights and interests community” has lost its effect while the city has no way to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rights for them,resulting in the low effect of the rights protection.By taking the Internet as a plat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public space as the base,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basis,worker representatives and leader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 the main body and by building social credit space through the“events”-based social media supervision,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ew gener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can be established eventually.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hidden infringement,rights and interests community,public spac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G91
A
2095-6266(2014)03-029-05
2014-6-27
郑州市2011年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2PPTG Y 246-10);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3-Q N-619)。
刘保庆(1981-),男,河南安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学和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