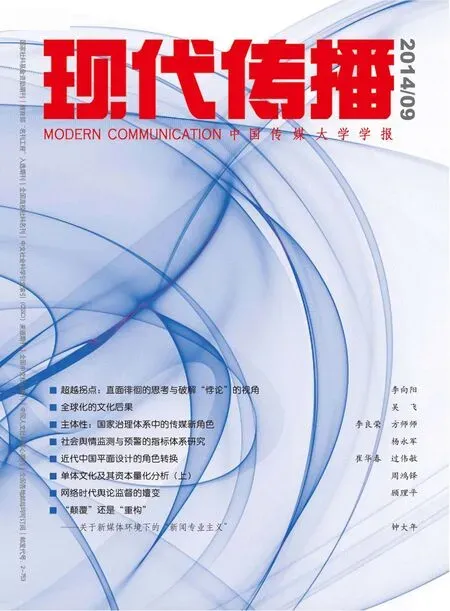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
张昱辰
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
张昱辰
本文从历史语境和学术脉络出发,对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媒介技术思想进行了简要探讨。基特勒深受海德格尔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在学术探索中融合并发展了香农-韦弗的信息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创性地将媒介技术、话语和权力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他的媒介理论批判地检视了媒介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可以被视作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
媒介技术;信息物质主义;话语网络;海德格尔;后结构主义
2014年10月18日,是德国著名传媒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逝世三周年。基特勒的研究远离了德国浓厚的文学研究传统,开创性地将技术、话语和权力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探索。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多部著作被翻译成英语,受到欧美学界的重视,引发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他本人也被誉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然而,在中国大陆,这位学者却鲜有人知。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基特勒的著述多数只有德语版,英语译本只有《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Film,Typewriter)、《文学、媒体和信息系统》(Literature,Media,Information Systems)以及《光学媒体:1999年柏林讲座》(Optical media:Berlin lectures 1999)等。所幸这几部著作是基特勒论述媒介理论的代表作,即使不懂德语的研究者也可通过阅读英语文献一窥基特勒的思想风采。本文试图结合历史语境和学术脉络,对基特勒的媒介思想进行粗浅的概要性解读,期待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学者对这位重要媒介思想家的兴趣与深入研究。
一、人文与技术:基特勒的成长轨迹
基特勒是一位人文思想学者,但他同样纵横于物理学、工程学、光学、光纤科学、计算机编码等领域,这与他的成长轨迹密不可分。基特勒1943年6月16日出生于罗赫利茨,一座邻近德累斯顿的小城。那正是纳粹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败的一天。他早年的记忆就是从远处观看德累斯顿的大火(1945年英国和美国联合发动的大规模空袭使德累斯顿陷入火海)。运用于军事的技术给家乡带来的创伤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巨大冲击。后来基特勒把无线电广播的兴起看成“军队事务的滥用”①,也就不足为奇了。
基特勒幼年时有两位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位在二战中失去许多学生的教师,他花费很多精力来教授儿子古典文学。得益于此,基特勒得到很好的文学训练,在7岁时已经可以背诵《浮士德》中的段落了。另一个是他的哥哥——一位退休的无线电报员,曾凭借在战争中的丰富经验,用废弃战机上拆下的零件组装出无线电设备。两位老师在文学和技术上的熏陶,对基特勒一生的学术生涯有着深刻的影响。
1958年,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基特勒全家搬迁至当时的西德。1963年,基特勒进入弗莱堡大学,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在那里先做学生,学习文学和哲学,后当老师。在当时的弗莱堡,年轻的德国学者致力于引进巴黎的新思想,人数之多,不仅仅是一个巧合②。柏林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19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的温床。相对而言,弗莱堡虽然比较稳定,但思想上受到的冲击还是很大。当时弗莱堡大学教员“成分”复杂,有和平倡导者、环保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激进自由主义者等。多元思潮混杂共存,使那里成为孕育思想的理想场所——出现了一些左翼书店、另类出版社,当然也有法国后结构思潮的传播。学者们聚集起来,努力拓展学科边界,成为第一批研究“法国理论”的德国学者,如特韦莱特致力于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的研究,而基特勒则更钟爱米歇尔·福柯和雅克·拉康的理论。弗莱堡成为当时德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传播的重镇。
1987年,基特勒离开弗莱堡大学。1987年至1993年,他在波鸿鲁尔大学担任现代德国文学教授。1993年,他在柏林的洪堡大学获得媒介美学和媒介史的首席教授职位,这位德国学术传统的“反叛者”正式回到了德国学术场域的中心。在那里,他与其他一些学者共同组建了亥姆霍茨文化技术研究中心。
二、重构“媒介”概念
从最初的文学研究到后期的技术史研究,基特勒的学术生涯通常被认为由三个既连续又断裂的时期组成③。第一个时期主要在70年代,他重点关注的是经典文学文本,不过此时他已经开始创造性地运用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开展文本分析,尤其偏爱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第二个时期主要在80年代,他的关注点转向媒介,尤其是表音符号、电影术、打字机技术带来的书写机械化以及计算机等;第三个时期主要在90年代后,基特勒集中于探讨“文化技术”④,此时他在宽广的路径上开展研究,涉及字母表、数字记号系统、音乐记号系统等媒介系统。
当然,上述划分过于粗略。基特勒的学术生涯,并不是笔直向前延展的线性过程,而是不断深化、拓展的螺旋上升。之前探讨的问题会在之后的探讨中重新出现,不过相似的问题或在概念上有所深化,或在空间、时间上有所拓展。第一个时期,基特勒把大多数精力花在传统文学文本上,时间主要集中于歌德时期(约1770年—1830年),空间上主要在德国境内,重点是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双峰——歌德和席勒;在第二个时期,他的研究开始从文学文本转向广义上的存储媒介,在时间上拓展到1700年至今,空间上溢出德国的范围,关注其他国家;在第三个时期,他进一步拓展了媒介研究的路径,试图通过媒介技术来研究整个西方的历史——从荷马史诗与希腊人对元音字母表的发明开始,直到印刷术的使用、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文明,以及阿兰·图灵的计算机技术。
基特勒从文学研究向媒介技术研究的转向,受到香农-韦弗的信息理论的影响。香农-韦弗把传播描述成由五个环节和噪音构成的过程,让信息概念脱离了原本模糊的意义,成为通信交换的重要对象。信息不仅是谈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交流,更成为通讯领域的传递过程。不过,基特勒认为香农-韦弗的信息理论虽具开创性,却忽视了中介性(mediality)的问题,它仅仅是关于传播的数学理论。
在信息理论的影响下,基特勒对媒介概念进行了拓展和重构。在他看来,传统的符号学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媒介作为一种文化技术,让人能够选择、存储、生产数据和信号。书写和印刷媒介生产符号,而技术媒介生产现实。此种媒介观念要求研究者研究文本时尽力避免提及阐释、理解、意义、所指、表征这些传统文学研究的概念。基特勒试图通过重构媒介概念,超越符号学研究的陈规,打破文本和技术、媒介与信息的对立观念。
三、聚焦媒介技术:信息物质主义
受麦克卢汉的影响,基特勒关注技术及其改变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强大力量。麦克卢汉对媒介的分析游移在人文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和后人文主义(人主体性的消解)之间,一方面他说“媒介是人的延伸”⑤,另一方面也说“所有的媒介”都“完全地作用于我们”⑥。基特勒认为,麦克卢汉走得还不够远,因为他仍然将人放在世界秩序的中心:“麦克卢汉,就职业上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对知觉、观念的了解要多于对电子技术的了解,因此他会倾向于从身体的视角去思考技术而不是相反”⑦。基特勒不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反而认为人体和机器的界限不再清晰,身体更可能沦落为技术的客体。技术不仅仅颠覆了书写,更有吞噬人的主体性的可能性。“人类剩下的仅仅是媒介可以存储和传播的东西。重要的不是组织精神的信息或内容”,而是“感觉的系统性组合”⑧。意义不是先在于技术,而是因为技术才得以可能。
基特勒曾用尼采的打字机作为例子,来说明技术是如何通过书写自动化改变了作家和文本的物理联系。由于长时间看书稿,尼采视力急剧下降,还伴有严重头痛。在他担心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作时,打字机拯救了他。当他可以熟练运用打字机时,他可以闭上眼睛,只靠手指写作。词语再次从他的大脑流向纸张。写作隶属于眼睛,一个超越距离工作的感觉,而打字机促成了不需要视力、仅通过肢体接触即可书写的能力。打字机使写作自动化了,将自身影响带进作者的写作中。不仅如此,它还通过组织书写空间(从原先手写符号的连续性到机械化书写的非连续性——每个字母都同样大小,相互间隔也被标准化),改变了文本的物质性。“写作工具参与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⑨,它不仅改变了文本的物质形式,也改变了人类理解的可能性。
在基特勒这里,信息成为一个物质性的事物。他将这个路径定义为“信息物质主义”:“信息和传播系统融合为一:信息被转变为物质,物质被转变为信息”⑩。他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再媒介”(remediation)概念——每一项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项媒介,所有之前媒介的形式将成为新媒介的内容。例如印刷媒介挪用了书写文化的形式、电话挪用了口语的形式、摄影挪用了绘画的形式、电影挪用了摄影的形式、电视挪用了广播的形式、网络则同时挪用了报纸、电视等各种媒介的形式。不过,在麦克卢汉那里,新媒介构成更真实、更全面的经验。基特勒则认为新媒介同时颠覆和构成了人类存在。例如光和声波的传播方式原本是截然不同的,但在计算机中,整体的数字化消除了媒体间的不同,声音与图像、说话和文本都融合成为表面现象(surface phenomena),最直观的就是计算机用户界面。当我们关闭计算机屏幕,仅仅让主机运行时,所有原先的媒介内容都成为二进制代码。“从书写或运算一直到成像或发声,任何东西都能够使用通用的二进制媒介进行编码、传输和存储”(11)。
四、话语网络:从技术观照人类历史
基特勒不仅意识到媒介技术的力量,更试图从媒介技术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知识考掘”。在《话语网络》中,他把话语网络界定为“技术和制度的网络,这让一个既定的文化进行选择、储存和推进相关数据”(12)。因此,话语网络是一种制度化权力和选择的话语。话语网络德语原词是Aufschreibesysteme(记录系统),这与弗洛伊德所分析过的疯子丹尼尔·施雷伯有关。通过使用记录系统,“疯子(如施雷伯)试图暗示说,在安全场所中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会马上被写来或者记录下来,没有人可以避免让其被记录下来,有时是从好的角度,有时是从坏的角度来记录”(13)。这恰是对话语网络的隐喻。
受福柯的影响,基特勒拒绝将历史看成是渐进的、进步的连续过程,强调断裂、打破、停顿。福柯认为,在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知识型,而每种知识型都有自己的确定性原则,并赋予某些特殊的科学知识以确实性。各种知识的历史是相互断裂的知识型不断变换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的考掘就是力图确定这些断裂发生的位置和年代。基特勒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认为新知识型产生的原因事实上是“中介物”(medial)的改变。在他看来,福柯的知识考掘还是局限于书写。福柯的“档案”基本等同于图书馆,一个文件的收藏地点。而书写文件绝对不是构成话语网络的唯一来源。技术促成了“一个全新的事物秩序”(14),而福柯却忽略了这点。伴随着技术媒介的兴起,书写和印刷对处理和储存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了,其他话语网络兴起。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考掘就不能仅通过传统话语分析完成,而需要用技术媒介分析。
基特勒的研究从1850年左右福柯研究结束时开始。在《话语网络》中,基特勒试图通过对人类读写的社会历史及物质状况的分析,挖掘出人类实践的基本结构。他分析了两个重要的话语网络。在1800年左右,新媒介技术(打字机、留声机)的发明,将所指的逻辑改变成能指的逻辑,把意义和文字打碎成字母。这时期最明显的艺术表现是前卫派和表现主义。1900年左右,文学和文化受到新的模拟技术的挑战,比如摄影、电影和留声机等,这些技术可存储动态的现实(如大海的奔腾),而不仅仅通过文字表征现实。因此,现代技术建构了“话语网络”。基特勒话语分析路径变化的核心是媒介观念本身的技术转化。技术媒介成为一个中心,围绕着这一中心,“知识型”得以被组织。技术中介物先验论取代了福柯的历史先验论,福柯相对抽象的“知识型”概念被发展成具象的“话语网络”。
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基特勒创造性地运用了拉康的辖域(register)概念来分析19世纪末给书写媒介带来挑战的新技术。拉康把人的生存戏剧分成三种表演辖域(register)——想象的(imaginary)、象征的(symbolic)和真实的(real)。它们代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三种力量——意象、能指和不可能之真(15)。基特勒认为,想象的、象征的和真实的辖域分别对应留声机、打字机和电影三种媒介。在基特勒看来,印刷媒介属于象征的辖域。不管是写作还是话语,都与符号的秩序紧密相连。在书写时代,人们仅仅可以写下象征辖域里已有的元素。写作就是在象征领域工作,“所有的数据流必须通过所指的瓶颈”(16)。而电子媒介技术则通过光的形状和声波来捕捉正式的物质踪迹。这毫无疑问是根本性的断裂,该断裂改变了表征的基础,也改变了我们对表征的期待。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人类超越了象征辖域,这种媒介让人可以精确地选择、存储、生产那些不能挤进所指瓶颈的东西。
与此相伴随,人类的时间经验改变了。人类开始使用技术实施对时间的管理。时间的不可逆转性曾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经验,但现在却日益受到技术的操纵。在技术时代,媒介技术可以存储真实时间,同时将其转化成一个技术时间。“数据处理成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顺序在一个特定的空间经验下可以被挪动甚至逆转”(17)。
五、结语
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学者发现了媒介技术的力量,但还是希望借助媒介技术帮助人们走向美妙卓越的理想宏愿。与他们不同,基特勒的媒介思想更具反乌托邦色彩。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参与到现实的建立中,它‘展现’现实,是原意上的真理”(18)。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基特勒不仅发现了媒介技术的自主性,更认识到媒介技术拥有改变、控制乃至建构社会的力量。在他看来,“媒介决定了我们的状况”(19),媒介技术不是社会生产的(马克思的观点)或者是主观上有意义的(韦伯的观点),相反正是技术使得社会和意义得以可能。
基特勒的后人文主义思想看起来似乎过于激进,但在技术越来越具有自主力量的当下社会里,他的思想无疑是具有意义的。它让我们重新检视技术和人类的关系,并始终保持警醒:我们未必是技术的主人,却可能处于技术的掌控之中。
注释:
①③⑧(16)(19) Kittler,F.Gramophone,Film,Typewrit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7,xx,xl-xli,4,xxxix.
② Holub,R.Crossing Borders:Reception Theory,Poststructuralism,Deconstruction,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2,p43.
④ Winthrop-Young,G.and Gane,N.Friedrich Kittler:An Introduction,Theory,Culture&Society,2006,23(7-8),pp 15-16.
⑤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⑥ McLuhan,M.&Fiore.Q.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An Inventory of Effects,New York:Bantam Books,1967,p26.
⑦ Kittler,F.Optical media:Berlin lectures 1999,Polity Press,2010,p21.
⑨(12)(14) Kittler,F.Discourse Networks,1800/1900,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96,369,352.
⑩(17) Kittler,F.Literature,Media,Information Systems:Critical Voices,Amsterdam:OAP,1997,p126,130-146.
(11) [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胡菊兰译,《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3) Armitage,J.From Discourse Networks to Cultural Mathematics:an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Kittler,Theory,Culture&Society,2006,23(7-8),pp 17-38.
(15)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页。
(18)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编辑)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