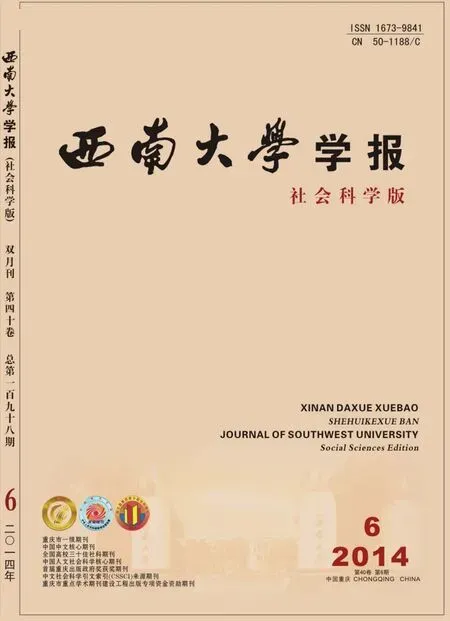运气之网与道德情感
——论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运气与伦理*
费 尚 军,徐 璐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江西 南昌 330031)
美国哲学家M.纳斯鲍姆在其长篇巨著《善的脆弱性》中,基于古希腊戏剧和哲学文献,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主题:“有多少运气的因素是古希腊思想家相信人类生活可以接受的?为了使我们的人类生活成为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人类生活,又有多少因素又是我们应该承担的?”[1]5而伯纳德·威廉斯更是在《道德运气》中断言:“道德毕竟仍然屈从于生成运气这个苦涩的真理。”[2]31显然,在使道德免于运气占据着我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解释传统中,伦理学家对这一主题的持续论争,又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道德与运气的关系问题。然而,多少让人奇怪的是,人们却较少论及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按照努德·哈孔森的说法,斯密正是“将道德解释为一种在有运气成分的世界里的外在行动的指南”[3]85。由此,本文拟在运气与道德关系的主题语境中,探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论及的“道德运气”问题的理论含蕴和伦理学意义,相信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抓住人类道德“本来的情形”,也将丰富道德运气问题的当代论争。
一、好生活的“脆弱性”与运气的解释难题
如果说,在伦理思想的解释传统中,既注重对理性自足性的热切追求,希望借助于理性的支配力量,使人类好生活之真善得以摆脱运气的左右,也承认运气对人类伦理生活产生了影响,那么亚里士多德似乎就是秉持了这一“折中”立场的阐释者。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指出,幸福就在于人的灵魂的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而“一个幸福的人就还需要身体的善、外在的善以及运气,这样,他的实现活动才不会由于缺乏而受到阻碍”[4]222。对人的幸福而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的影响?亚氏认为,首先要反对两种错误的观点:其一,就是认为幸福完全是运气或机运作用的结果,“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其二,“另一些人把它等同于德性”,认为运气根本没有力量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善,与幸福相关的一切因果要素都处在行为者的理性控制之中。
亚里士多德善于从过度与不及的两极中引出“中道”,在运气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也通过描述这两种极端的看法来彰显二者之间的张力。在拒斥运气至上论的同时,认同运气之所以影响伦理生活,就在于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容易为运气所打断或阻碍,重大而频繁的厄运可能由于其所带来的痛苦和对于活动所造成的障碍而毁灭幸福。不过,具有实践智慧和美德的人往往能够抵御这种损害,“在厄运中高尚[高贵]也闪着光辉”[4]29,面对不利环境,甚至也能够寻求一种高贵的行动方式。不过问题在于,否认运气影响的辩护立场在于,他们之所以拒斥运气的考虑,把运气排除在伦理生活之外而缩小“好生活”的范围,是因为承认只有那些具有最大的稳定性且不受偶然性影响的活动,才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对亚里士多德的回应而言,一方面,“好品质”与“好生活”之间由于运气影响而存在一个事实上的“裂缝”,不仅是其他外在善的构成性要素的缺乏,那些偶然的未受理性控制的事情也随时可能进入而妨碍德性实现活动;另一方面,尽管厄运影响了生活状态,但只要拥有了德性的稳定性,既不至于使其生活成为邪恶的或该受责备的,也不会影响到对行为者稳定和卓越品质的价值判断。[5]
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或许会更多援引康德那句著名的断言:“使一个人成为幸福的人,和使一个人成为善良的人决非一回事。”[6]62在道德价值与幸福原则的两分中,得以摆脱人之所处的偶然境遇与运气的作用。在这种理论的持续影响下,人们也似乎一直保持着一种使道德免于运气的伦理情结。然而正如伯纳德·威廉斯所质疑的,按照这个观点,“不管偶然性产生的东西是幸运还是不幸,它们都被认为不是道德评价的恰当对象,也不是决定道德评价的恰当因素。……在行动的领域中,在世界中实际上得到实现的东西不是变化,而是意图。”但是,“使道德免于受到运气的影响这一目的必定是一个很令人失望的目的。”[2]29-31就人们的日常经验和道德体验而言,运气对构成性的生活之善确实产生了影响,而与道德免于运气以使相应的道德价值判断“简化”的理路相比,认同运气对特定境遇中人们的行为和品质的道德评价产生影响,也必然会使相应的道德评价呈现出某种“复杂性”。亦如丹尼尔·斯塔特曼在引介内格尔关于运气影响道德的几种不同方式时指出的:“即使意志本身的行为不为先前的原因所决定,仍可能为是哪种类型的人所决定,即使不是这样,也会受到自己所处境况的运气的伤害,即使这种运气能够克服,个人的道德评价仍受到因实际行为结果完全不在个人控制之中的运气所支配。”[7]11因此,对人类生活与个体道德体验完整性的关注,使人们认识到运气之网存在的某种必然性,不仅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运气对道德评价所产生的影响,既指向行为者自身,也指向了其现实的实现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人们需要在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完整对应,以及在道德责任承担中弃除行为意愿的原因而完全归因于运气这两者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即使在“谁有道德责任”这一问题上获得共识,仍面对在特定境遇中,在何种条件下以及何种程度上承担相应道德责任,和对行为者以及他人作出公正道德评价的解释难题。[8]
二、运气之网与情感的“不规则性”
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同样为运气与道德的关系论题作出了一种具有阐释意义的理论努力。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就以“就行为的功或过,论运气对人类情感所产生的影响”为题而集中阐述了这一论题。其所作出的断言就在于:“行为好坏的结果,对造成这些结果的人和其他人的情感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这样,左右世人的命运就在我们最不愿意让它发生作用的地方施加它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产生有关自己和别人的品质和行为的情感。”[9]130诚然,如果把斯密的这一论述放在当代关于道德运气论争的语境中,按照内格尔所做的界定,如果“某人所做之事的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超出其所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仍然在这一方面把他看作是道德判断的对象,就称之为道德运气”[7]26,那么斯密所揭示的也就是其所述说的“结果运气”。就对某一特定行为的道德评价依据而言,尽管不像康德那样,认为即使人生不逢时或受自然的无情苛待,只要剩下了善良意志,“它仍然如一颗宝石—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6]9。斯密却强调了人们在作抽象思考时得到的这样一种理想化的主张,亦即,任何行为是应受赞扬还是该被谴责,最终都应当取决于行为者内在的意图和动机,也只有作为行为者意图的结果,才是其所应当承担责任的。因此,行为无论其偶然的、非意图的和意料之外的后果如何不同,功过判断唯一重要的条件,也应在于行为者原始行动背后的意图和动机。
运气影响了道德生活,通过人们的情感及其反应性态度为媒介而发生作用。由于某一行为产生的实际后果对我们关于行为的功过判断的情感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它总是加强或减弱我们的功过感。因此,尽管人们都承认应当以上述“公正准则”来调节我们的情感,在具体境遇中的实际情感却很少完全受这一准则控制,斯密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情感的不规则性”(irregularity of sentiment)。而要理解这种情感不规则性产生的原因及其与“结果运气”的关系,则首先需要在其对关于行为的功过感及其道德评价的整体分析框架下展开。斯密认为,在人们日常道德生活中,我们判断某人的行为和导致这种行为的情感时,往往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亦即它产生的原因或形成的动机,以及它希望达到的目的或试图引出的后果。正是某种特定后果所具有的有益或有害的性质,决定了行为的功过与应得的赏罚。而作出这种判分的基础,是感激和愤恨这两种激情,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情感能像它们那样直接地引起人们对他人苦乐的关切。因此,当某一行为作为合宜的感激或愤恨对象时,我们自然也就判断了行为的功过,相应的情感反应也指向了其所应得的报答或惩罚。不过值得注意,在斯密看来,功过感“好像是一种混合的情感”[9]91,从理想公正旁观者的立场出发,要作出正确的道德评价,并非仅仅只是把受者实际的感激或愤恨的情感作为唯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对受者感激或愤恨的间接同情,需要与对行为者情感和动机的直接同情或直接反感结合起来。由此,对某一特定行为的道德评价,最终需要诉诸对行为者意图和动机的合宜性判断。而由于“行动以及它的后果将会轻易地反过来干扰自己,并且会经常或多或少地窃取了这种外显的机会”[3]84,不论对于想象的公正旁观者自身,还是对于其他现实的旁观者而言,这种理想化立场在具体境遇中却总是出现某种程度的偏离。
问题在于,这种通过运气影响而产生的实际结果为什么会扭曲人们的合宜感,使相应的道德评价偏离理想的准则呢?斯密进而阐述了运气对人类情感与道德评价产生影响以及情感不规则性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无论痛苦和快乐的原因是什么,或它们是怎样产生的,都会激起人们感激和愤恨这两种激情。哪怕你在行走中偶然被一块石头碰伤,这种因为运气影响而非意图的结果,因其所引起的痛苦也时常令你感到愤怒,甚至想着要“惩罚”它,尽管不久就可能纠正自己而意识到石头不是合宜的报复对象。但法律的历史表明,即使是对这些无生命的存在物,人们也并不能够总是对其自然的感受进行纠正。事实上,它们也往往成为我们愤恨的对象。“在许多地方,特别在雅典人中间,伤害人命的剑或工具被看作嫌恶物,因而被毁掉。根据英格兰法律,如果一个人从一个房屋跌下殒命,那个房屋就按供神物律例被没收入官作为供神之用。”[10]159由此,“人们的判断甚至在其背后不可能有任何意图的无生命的事物的‘行动’时,也会如此彻底地偏颇,很难不去这样想像,在他们对他们同胞的判断里也存在着这样的因素。”[3]84其实,就理智健全的人作为一种完整而恰当的感激或愤恨对象而言,既能够成为快乐或痛苦的原因,也具有相应的感受苦乐的能力,由于各种境遇中以我们赞同或责难的方式有意图地产生的快乐和痛苦,也是激起人们感激和愤恨的“附加”的原因,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情感不规则性”的两种具体表现。因为尽管一个人的意图是如此恰当与仁慈,抑或不合宜与恶毒,但却没有产生作为意图结果的实际善行或罪恶,显然也就缺乏某种令人激动的原因;相反,虽然一个人的意图没有值得称赞的仁慈,或没有该受责备的恶意,但倘若他的行为带来大善或大恶的结果,这两种情形却又都产生了一种让人激动的原因。由此,感激和愤恨并非唯一针对行为者的意图而产生,实际结果产生的快乐和痛苦自发地激起了这两种情感,使人们的功过判断出现偏颇。而斯密断言,行为实际结果又处在运气的支配之下。
三、“结果运气”与道德评价的“偏见”
人是以某种道德的方式来接触和了解世界的。认识到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就会对某些品质和行为作出相应的道德评价,给它们打上光荣或耻辱、赞许或责难的印记,赞同并崇信善与恶以及应得报答或该受惩罚的两分法。然而,道德评价究竟应该立基于何处?不同的伦理学理论作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大多认可行为动机与道德评价的关系。在斯密看来,就我们对某一行为能够作出判断的依据而言,所针对的无非就这三个方面:“首先是针对产生这个行为的内心意图或感情的;其次是针对这种感情所引起的身体外部的行为或动作的;最后是针对这个行为所实际产生的或好或坏的后果的。”而由于“在最清白的行为和最可责备的行为中,身体外部的行为或动作往往是相同的”[9]114,行为外部动作相同,出于不同的动机我们可以对它们作出完全不同的道德评价,而取决于运气的实际后果更是无关褒贬,亦如内格尔所言:“人们会直觉地相信,在并非由人们的过错、抑或超出他们控制力因素引起的事情上,不能对人作道德上的评价。”[7]58由此看来,后两者本不应作为当然的依据。而通过情感不规则性的阐释,斯密却揭示了这样一个在日常道德生活中时常偏离了抽象准则的人类情感及其反应的客观事实:“任何行为愉快的和不幸的结果不仅会使我们对谨慎的行为给予一种或好或坏的评价,而且几乎总是极其强烈地激起我们的感激或愤恨之情以及对动机的优缺点的感觉。”[9]130不论是意图和动机还是作为运气影响的实际结果,实际上都确实作为激发我们的情感而作出相应判断的原因而起作用。如果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是仅由善的意志或恶的意志所造成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运气”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评价呢?
在“论运气产生影响的程度”的论题中,斯密认为,运气影响的结果将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人们的评价,并使之呈现出某种判断的“偏见”,而这不只是受行为结果直接影响的人能感觉到,甚至公正旁观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感觉。首先,当一些行为虽出于最值得赞扬或最该受谴责的意图,但运气影响而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它就会减弱我们对这些行为的功过感。就行为的直接结果所能引起的快乐和痛苦,将通过感激和愤恨的方式回溯到行为者的意图或动机而言,我们都能感觉到“人类是如此不公平”。当行善未果或好心无实际的善果时,旁观者会减弱对行为者出于意图而应有的感激,而行为者自身也会缺乏那种基于行善成功的功劳感。斯密举例说明:“假设在助人失败的朋友和助人成功的朋友中间——其它一切情况都一样——甚至在最高尚和最优秀的心灵之中,会存在偏爱助人成功的朋友的某些感情上的细微差异。”[9]121由此,无论是对于一位雄才大略而憾失战功的将军,还是一位有天才般谋划而未能付诸实践的设计师,由于各种运气和偶然因素的干扰,未能使才能化为光辉业绩而难以激起人们的赞赏。因此,“卓越的品德和才干并不会产生同卓越的业绩一样的效果,即使是对承认这种卓越品德和才干的人也不会产生同样效果。”[9]123这种判断的“偏见”也成为人类情感的真实体现。而那些由于运气影响而作恶未遂的人,同样也会由于缺乏实际的罪恶而减轻对其产生的罪过感。预谋作恶,无论证据多么确凿,从来不会像实际作恶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因而可以设想,一个用枪射击仇人却因运气影响而未能击中,与射击而致人死命的结果相比,尽管两种情况下的意图是同样的,但所有人的情感却存在着这种“偏见”:因为对遭致不幸的悲伤加剧了对他行为的愤恨,对幸免受害的愉悦却缓和了这种情感。由此,也相信“一切最文明的国家的法律同一切最野蛮的国家的法律一样,有一种必然的减刑条例”[9]125。
“结果运气”影响道德评价的第二种情形在于,当一些行为意外地引起特别的快乐或痛苦时,它会增强我们对这些行为的功过感,以至于超出仅仅依据行为由以产生的动机或情感所应得的评价。可以设想,当好心不幸酿成恶果,而无心却因偶然性而伴随重大善果时,尽管行为者意图可能没有任何该受责备或值得赞扬之处,但行为结果的愉悦与否,却时常会给行为者的功过投上某种“阴影”。如果说作为行为意图结果的某种真实的罪恶,自然地成为人们愤恨的合宜对象而应得惩罚,那么即使因为行为者无意或疏忽的原因,但运气影响的幸与不幸的结果之间,却同样存在着重要的情感差异。当一个人因疏忽而对他人造成某些无心的伤害时,只要我们同情受害者这种基于伤害而产生的愤恨,就会赞成对施害者所施加的惩罚,而这显然“大大超过那个没有因此带来这种不幸后果的冒犯者或许应该得到的惩罚”[9]127。对于那些运气影响而不在行为者控制之内所导致的恶果,也将因其所引起的愤恨而承担应受惩罚之责。就某种疏忽的严重程度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而言,如果是缺乏那种奠定正义和社会基础的尊重他人的意识,譬如无视他人生命安全的“高空抛物”而导致的某种不幸后果,则因其所引起的自然义愤而更需严惩。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种“严重的疏忽和恶毒的图谋几乎相等”[9]128。而如果是没有任何不正义的成分,无意侵害他人,却因疏忽、甚至仅仅缺乏那种过分谨慎或哪怕是细小疏忽而因运气引起对他人的某种伤害,人们的自然情感都会倾向于赞同对这种后果作出惩罚的法律裁决,行为者自己似乎也感到自己的过失应该受到责罚,而如果没有那些不幸的意外结果,人们就不会想到对他施加责罚。由此,愤恨作为对现实伤害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的情感反应,似乎总是确证着“一个人不应为他人的疏忽而受害”这一生活法则。如果某人因为“结果运气”而成为这一情感反应指向的对象,就成为负有一定责任的行为者。
四、自然智慧、运气与伦理学
与使道德免于运气的理论努力相反,亚当·斯密正是通过感激和愤恨的情感反应,以情感的不规则性揭示了“结果运气”对道德评价所产生的影响。运气好坏导致的幸与不幸的结果,不仅影响到对某人及其行为的道德评价,也影响到行为者对自己的评价。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以运气可能对德性的实现活动所造成的妨碍,来凸显出好生活的“脆弱性”,那么斯密却得出一个完全不同而多少令人惊异的结论:“当造物主在人们心中撒下这种情感变化无常的种子时,像在其它一切场合一样,她似乎已经想到了人类的幸福和完美。”[9]130-131因而在运气影响人类道德的问题上,这个为威廉斯所断言的“苦涩的真理”,在斯密的叙述中却似乎成为了促成人类“幸福的真理”。尽管人们历来抱怨世人都根据结果而不根据动机作出判断,然而人类道德情感的这种不规则性即使是人性的一种“弱点”,恰恰也是自然智慧的一种体现。应该说,就运气和道德的关系以及对特定行为的道德评价及其应得的赏罚而言,斯密首先认识到了理想化的“公正准则”与人类情感事实之间存在的“悖论”或冲突。因为理想的道德评价立场似乎就应当拒绝运气的考虑,“最终必定针对内心的意图或感情,必定针对行为的合宜与否,必定针对仁慈或不良的意图”。然而,“在某一具体情况下,我们的情感很少完全是受那种法则控制的”[9]115。运气影响的实际结果事实上总是给人们的功过判断投上某种阴影,因而不考虑“结果运气”,就与我们的情感体验和情境的道德直觉相悖。
如内格尔指出的:“把每一种行为削减到它道德上必要的核心,一种由动机和意图来评价的纯粹意志的内在行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倡这样一种观点,但指出了它与我们的实际判断背道而驰。”[7]63如果仅从动机评价道德行为而得以拒斥运气考虑过于理想化,斯密显然在要不要考虑后果的评价立场上,强调了后果作为激起我们判断的原因而起作用,认同运气会影响道德判断。不过,它也会与我们另一种思辨的道德直觉“相悖”,它“与这样一种观念相对立,亦即,一个人该受责备或尊敬的事情应当是受他控制的那个部分,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或者由于它们对他只能部分控制的结果的影响,而给予或免除对他的赞扬或责备,看来是不合理的”。[7]61这也是我们一直持守的一种责任观念,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似乎受谴责的也只能是由我们自己的原因所造成的那些恶果。斯密也认同这样一种理想的判定准则:“行为者可能对此负责的、或者他由此可能得到某种赞同或反对的唯一后果,就是那些这样或那样预期的后果。”[9]114-115然而造化弄人之处在于,人类道德情感的某种“严重失调”,即使是因为受到运气干扰而作为非意图或意外的不幸后果,也会给予实际的责备。由此,既让行为实际结果改变依据行为意图和情感的功过感,甚至也让行为者承受运气影响的意外之责。“结果运气”凸显了人性的弱点,也有违“公正准则”而常常使我们失去对美德的信心,在使道德评价中“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呈现的同时,究竟如何认识在抽象反思的“公正准则”与道德情感体验中不规则性之间所出现的“裂缝”?
如果认同“人是如此软弱和不完美的生灵”这一事实,认识到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某种不完整的自足性,人类在运气的影响下就会呈现出某种“脆弱性”,人类道德和生活条件都有向运气敞开的可能。斯密也坚信,我们所有自然的道德情感反应正是在这一原则下发生作用的。因此,真实的道德必须确认这种社会心理和情感的事实。不过他认为:“人类道德情感的这种巨大的失调,并非毫无用处。”[9]328这一最初看来不合理的“不规则性”的效用,首先产生了这一必要的正义法则,即人们只应为他们的行为而受到惩罚。这使我们免于仅因内心感情就施加惩罚这种“最粗野和残忍的暴行”,避免社会陷入相互猜忌和混乱,给感情和想法以内在自由之域;其次,它促使人们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善良的意图,以行动去增进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因为仅仅具有良善意愿的人是“不完美的”;再次,对因偶然而产生的愤恨之情来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正的,却也是自然的,因为它告诫人们,“正义的树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要尊重自己同胞的幸福,唯恐自己会做出任何可能伤害他们的事情,哪怕这是无意的”[9]133。显然,我们不能把这些间接的社会效用仅仅看作是补偿情感不规则性“缺点”的理由,毋宁相信,对促成人类幸福和生活秩序这一伟大目的来说,斯密仍信守着自然并没有把“达到这些目的的合适手段寄托于我们理性中缓慢而不确定的决断”,而是“赋予了人类一种直觉和本能”[9]95。情感不规则性的原因即有自然的苦乐原理。即使是人性的弱点,但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自然所赋予的目的和效用,也许意识到这只是实现世界的整体秩序和幸福的某种因果链中的一个必要环节。
与内格尔通过“自我控制”原则来解释道德运气的含义及其作用方式不同,斯密更多通过揭示理想的“公正准则”与情感不规则性之间的裂缝,来凸显“结果运气”对道德评价的影响。而与前者认为道德运气与“控制”原则相悖,却又“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相比[7]58,斯密更希望为运气和这种情感不规则性所引起的“裂缝”找到一种道德解。如果说,斯密要实现的是“一个极其非凡的结合,把一种关于意图的理想的伦理学与一种关于结果的实际的伦理学结合在一起”[3]85,那么承认运气影响的结果对功过判断的干扰,也并不意味着他对后果主义作出彻底让步。因为当现实的旁观者以“是什么”的评价尺度、以行为结果表达实际的赞扬或责备时,却并没有排除理想的公正旁观者以“应该是什么”、以值得赞扬或该受责备为依据,去矫正人性中那些不规则性变化的道德努力。如果说,前者使生活世界中总是有某些“不公平”,也时常有使一个人得到多于或少于其应得赏罚的某些“例外”出现,那么后者就与理想的公正和完美的合宜性最终相关。也许对他而言,伦理学与其一开始就在纯粹良善动机的形而上中寻求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和绝对公正,不如从人性和自然情感的事实出发,去探究前者“可能”接近后者的方式。不过,在这种立场上为运气与情感不规则性引起的裂缝提供一种道德辩护,重要的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公正报偿而保持赏罚应得的道德确信。因为如果判断的“偏见”在社会成员之间持续交流,当美德没有得到报答而无辜时被惩罚时,人们就会逐渐失去对法律和道德的尊重和信任,衍生为社会焦虑和悲观主义的来源。
参考文献:
[1] 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M].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 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M].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3] 努德·哈孔森.立法者的科学[M].赵立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孔扬.德国古典哲学外延逻辑批判的总线索[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44-51.
[6]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 Daniel Statman,ed., Moral Luck[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8] 张雷.精神世界中道德与自然的对立和谐考略[J].探索,2012(6):183-187.
[9]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 坎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