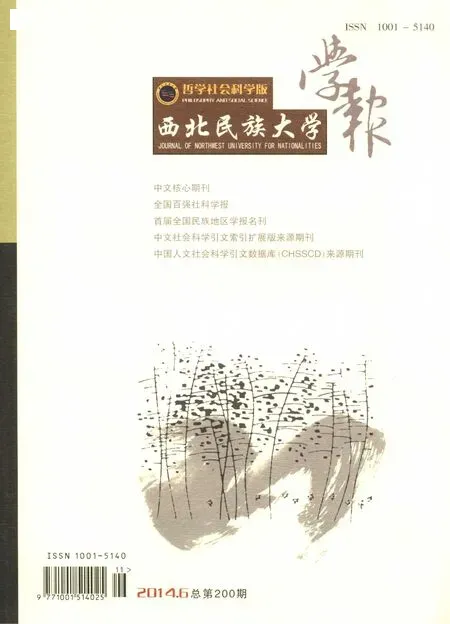表征与隐喻: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疾病书写探析
邱诗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苏珊·桑塔格认为:“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也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感到不正确的事物。”[1]疾病成为了一种隐喻,疾病的内涵就逾出了疾病本身的阈限,我们可以从中理解或阐释出某种道德、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文学作品里,疾病常常成了对社会中某种缺失状态的展示,或者是对这种缺失关系、根源的揭示,通过疾病的隐喻传达出作者的一种价值判断,同时也是读者对其的阅读使这种价值判断得到理解与再诠释,甚至进而产生共鸣。
疾病在文学里既是所指,又是能指,它成为了一个载体,已超越了具体的生理病象与医学意义。文学中的疾病描写和叙述不仅仅是对真实疾病的客观反映,而且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美学等方面的意义,也许正因此,学者叶舒宪才会说:“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2]因而,在文学中出现的疾病意象也拥有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承载了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功能性内涵。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有大量的对各种疾病和痼疾的叙述和描写,如张天翼《寻找刺激的人》里的皮肤病,鲁迅《药》里的华小栓得肺痨、《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得肺结核等,小说里写到的某种确切的疾病,其实作家的目的有时是直指民族的痼疾,是作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个总体的思考与探寻。
修辞学研究认为,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名称用来命名该事物,逐渐被提升为一种方式和世界观。当代隐喻理论把隐喻从单纯的语言现象提高到了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的高度。隐喻的思维就在于借助想象性事物,以相对熟识的方式思考和认识隐秘而陌生的事物。在文学上对疾病的叙写不只是对疾患的确指,而是具有了象征意义与隐喻功能,疾病往往与国家民族的痼疾和社会现实的颓然相关。
一、疾病意象:对文学功利性内涵的宣谕
中国人对身体的言说往往表现得不是很“客观”,常把身体看作文化象征意义上的“虚实体”,这样,身体也就成了不仅仅是能指的符号,同时还是所指的意义,也就如学者葛红兵和宋耕在其合著的《身体政治》里所说的:“‘身’和政治紧密结合着,它是政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的目标,同时也是政治的结果。‘身’在肉体论、躯体论、身份论三位一体意义上,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人类政治现象。或者说,‘革命’作为非常态的政治手段,它既是以身体(改造、消灭、新生)为目标,也以身体为工具,革命是身体政治最暴烈的手段,革命的文学家同时必然是治病救人的‘医生’。”[3]我们通过阅读鲁迅的小说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他的叙述中,中国人的身体和民族国家的文化机体常常是互文的。并且,在鲁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机体”已经病入膏肓,甚至无药可救,因此,他也就时时表露出绝望和愤激之情,这种无望是源于他对传统的否定,而对此的全盘否定也就注定了必定会有新生的诞生,改造国民性与社会改造就成了他的期盼,也是他的希望,这也就是学者汪晖所说的,“鲁迅对传统的否定性判断来源于对民族新生的期望”[4],即对“绝望的反抗”,绝望与希望就以一种悖论式的方式并存于鲁迅的世界中。而另一颇具特色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疾病叙事就呈现了与鲁迅不同的内涵,她的疾病叙述写出了在方生方死的暧昧纠结中,个人的不可救治与社会的渐趋颓势在相互的抗衡中彼此都沦落了。鲁迅与张爱玲的疾病描写都源于失望,但鲁迅从“绝望”“虚无”“黑暗”中看到“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与未来的“希望”,而张爱玲则在挽救中陷落、失望。
“‘疾病’作为隐喻日益弥漫在中国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之中,并转化为一种文化实践行为”[5]。从新文学产生的社会语境来看,文学被功利化为治病救人的工具,文学对社会、民族、人生与生命的疗救作用,是对现代启蒙所起的工具性作用的一种转喻,是对饱受列强侵略之难后的强国保种的民族使命意识的呼唤。正因如此,鲁迅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奠定了他的文艺的工具功能化效用,借助文艺来疗救国民精神的劣根性。因而,鲁迅除了关注文艺的本体性诉求之外,还自觉追求文学的工具性功用,在他的创作里呈现了大量的有关社会、国家、民族等的宏大叙述。
小说中的疾病意象,不仅是表达方式,更是思维手段,它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参与艺术层面的创造,深化了文本的内容。疾病作为象征,承载了小说的社会性价值与功利性作用,常常被用作思想启蒙的转喻。鲁迅常常将对疾病的叙述比照传统机体的病状与个体的精神缺陷进行描写,对身体症状的描写隐喻了社会与民族的病态存在,身体疾病便成为一种政治隐喻,以此表达作家对其的深刻反思与质询,这就恰如苏珊·桑塔格在其专著中所说的那样,“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6]。
文学里的疾病叙述中描写最多的要数肺结核了,并且,在所有的疾病中,肺结核也有它的独特之处。在西欧18世纪中叶,肺结核被指称能够引起浪漫主义的联想[7]。结核病的浪漫化书写在西欧和日本曾一度盛行,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创造社作家曾深受此影响。创造社代表作家郁达夫的小说几乎可以看作是“疾病大全”,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衰颓的美感,“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频繁地指涉疾病母题的,或许没有人能出其右”[8]。如《茫茫夜》中的吴迟生、《过去》中的李白时、《蜃楼》中的陈逸群和叶秋心以及《迟桂花》中的翁则生都是肺病患者。当结核神话得到广泛传播时,结核病被看成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9]。我们看到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出身书香门第又身患肺病的才子,脸色苍白、嘴唇灰白、身体清瘦、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等几乎是患者们共有的体貌特征,而且这些人物大多表现为敏感、纤细、才华横溢,在郁达夫那里,肺病也就几乎成了才子病,这就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10]。鲁迅的《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都是描写肺病的市镇小说,当然这些作品与上述结核病的浪漫风、才子气相去甚远,呈现了不同的内涵,鲁迅的作品里的疾病叙述更多地是表现了生命的沉重与价值询唤之意义。
詹姆逊说:“读者必须具有相应的经验,无论是身体的疾病或精神上的危机,亲身体验过我们无法从精神上逃脱的不幸异化了的现实世界,这样才能真正欣赏鲁迅所描绘的恶梦的极其恐怖。……那种不可言喻、难以名状的内心感情,其外部只能由像譬如疾病症状一类的外壳标志出来。”[11]这段话有助于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与对疾病的理解,指示我们要透过症状的表面直抵表征对象的内里与本质,鲁迅的疾病叙事与特定时期的民族、社会症候建立起了对应关系。
二、疾病表征:孤独的探寻与探寻者的命运
疾病叙事呈现了生命的时代诉求与价值关怀,正义无法承担生命的价值与人格尊严,是对探寻者现实境遇的关照,也是对其的生存关怀。《药》反映的是愚昧的个体与启蒙者的对立状态,是看客的冷漠与被看的悲哀,是愚昧与文明的冲突,是少数革命者与落后的大众之间的裂隙和鸿沟,舐噬革命者的鲜血无法治愈小栓的肺痨,也无法弥补相互间的沟壑,疾病表征了愚昧的顽固强大,形成了对启蒙与文明的消解。这里,疾病叙述就成了对启蒙与革命前途境遇的生动表达与探寻,暗示了革命的阻滞与沉重。如果革命没有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革命者最后的结局就是牺牲、革自己的命。革命的行动成了被看的内容而落得可悲的下场,未能唤醒民众的革命,革命者的振臂一呼只能是独鸣,而不是合奏,施助与被救间就因两者的距离,形成了即便在同一场域而依旧如陌路的存在。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认为,悲剧不仅表现失败,但更重要的是传达“解救”,夏瑜的牺牲,革命的失败,传达了革命者的“解救”之行动,但未被大众感知。华小栓患肺痨用夏瑜的鲜血治疗,这也表明了革命行动的徒劳与施救的无效。与其说夏瑜的杀身成仁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社会、民族的不幸。疾病隐喻了对世界合理性,乃至启蒙者自身合理性的双重质疑,革命的成果与意义被革命对象和被救者所解构和消解,被助者本来应是革命者的盟友、同志,而现在被异化为革命的他者,是革命得不到理解、支持的转喻,革命者被自己的革命行动所解构。疾病的政治隐喻内涵凸显了疾病与旧社会的历史同构关系,在身体症状的治理中建立起另一种意义构架,革命者的孤独就表明了群体的愚昧无知,众人处在昏沉中仍未被唤醒,个体流血的牺牲遭遇群体的价值评判标准,被群体所消解、所忽略,也就如鲁迅本人与友人谈到《药》时所诠释的:“《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12]《药》通过描述新旧碰撞、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锋以及对先觉个体与落后群体的相互对照叙述,身体疾病就与民族国家态势形成了互文关系。
学者汪晖说:“中国社会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高度一体化过程实际上不仅使政治伦理化,社会结构伦理化,同时也使伦理道德体系政治化、制度化、实体化。”[13]《药》中华小栓所患的“痨病”是对病态社会中形成的非正常人际关系的指代,代指中国传统文化所肯定的伦理道德就是群体本位,即群体掌握了“正确的”话语言说权力,这一规范的实质是群体对个体生命的遗弃,这种评价标准就喻示了正处病中的华小栓的命运,更是对以“药”的身份出现的革命者夏瑜牺牲价值的否定。这正是传统伦理的巨大力量,它显示了在群体掌握的话语权下,个体生命的卑微、启蒙感召的纤弱与先驱者的孤独。
《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曾受时代感召立志革新,反对旧家庭、反对封建礼教,被周围人称之为“新党”,当在反抗中受困遇挫后,就开始步步退守屈服,不得不向曾经所“反对的一切”复归。从他的历程来看,他于黑暗中奋膈振翅,是因有所期望去反抗绝望,面对强大、厚重的黑暗现实,一己之力撼不动腐朽的社会,他深感身陷围城无法突破,因此在得肺痨后精神自戕、拒绝治疗,他的病死就是对反抗的徒劳、救赎的绝望的表达。《孤独者》的疾病隐喻成了对《狂人日记》的另一个演绎,同为疾病叙事,两者相较,各有不同,那就是狂人因投降而致康复获“生”,魏连殳却因抗争导致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死亡。个体的魏连殳是为拯救群体而遭弃被疏离的,他在群体中呐喊之声的纤弱、拯救的乏力,就说明了群体对个体的放逐。小说批判了传统文化对“人”的忽略与压制,这也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之处。西方社会重视个体的利益诉求,而中国更重视群体的价值,而常常忽视了个体的存在意义。因此,鲁迅将“个体”作为关注对象,探寻个体在集体中的存在与命运,他通过对个体生存的描写,揭示以群体为本位的道德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他的“反抗绝望”的核心思想,也即对“个体”的深切关注与“立人”至“立国”的探寻,以“人”之价值标准来揭露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礼教制度等的“吃人”真相,病也就意味着是对当时社会秩序、体制制度、思想传统等之缺陷的表征,这就亦如谭光辉所说的,“当文学作品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语境而处于其中的时候,肉体就会在社会文化的巨大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身体符号则往往成为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14]。借对身体疾病的书写来隐喻社会性的思想主题,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我们不难发现,疾病呈现在个体上的症状是对群体的症候的书写。正如学者黄子平所认为的,病弱的身体在这些作品中成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现代作家们想象着自己的国家、民族以及赖以生存的文化就像病弱的身体一样急需救治,而把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身体想象成民族新生的符号,于是思想启蒙、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种“治疗”行为[15]。魏连殳的病是对传统文化之病态的隐喻,表征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指斥。
日本学者柄谷行认为:“‘政治与文学’不是什么古来对立的普遍性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的‘医学式’的思想。”[16]林淡秋的市镇小说《复活》里的章植农追求政治进步、参加革命运动,但他的行动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理解与同情。家境的贫寒、养家的责任,使他的行动既没有现实的基础,也不可能得到家人的支持。这里对疾病的叙述,既是对个人境遇的喟叹,也是对群体生存现状的不平;既是对愚昧落后的指斥,也是对社会混乱无序的控诉。因此文学里的疾病叙述就是对社会的发言,当构成对社会的批判的时候,便是对观念的呈现,也就是对意识形态的表达。约翰·奥尼尔认为,人的身体与社会机制是互相重构的,“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17]小说以疾病之躯来隐喻社会的混乱与政治的腐败,是作家对非正常形态的社会伦理规范的质疑与思考。小说《复活》最后写到,在家破人亡与异族入侵的形势下,植农最后得到周围人的支持走向革命、为国效力,这是对作家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感的传达。这正如作家成仿吾所说的:“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18]疾病叙事也可看作是作家的良知呈现与责任感的表达。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19]。蹇先艾的市镇小说《酷》写了因生病而住医院的晓英,看到医院里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医生对待病人态度冷漠恶劣,不但不及时救治病人,更是将病重未死的病人放置停尸间,以“我”生病住院看到的一切揭露医院丑陋的一角,暗示社会的黑暗腐败和医院的不人道行为,意在呼唤对生命的尊重与珍视。靳以的市镇小说《去路》里儿子虎儿的病弱隐喻社会的混乱无序和民族的危难。“我”将病弱幼儿托付给友人后,走向革命去寻求社会、民族解救之良方,为国家的未来找出路,以期弱国的自新图强。
作家经常将疾病的描写作为他们表达对外部事物的态度与观点,成了他们认知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亦即以对疾病的认知作为进入世界的一种途径。因此,文学里的种种症状,也就不仅仅是疾病本身,疾病也就成了载体,而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伦理的意义,疾病也就由此突破了一己的疼痛,上升为对世界的关怀、对存在的探寻,也就具有了某种普适的意义。
文学与疾病相联系,疾病被赋予了一种现代化的书写方式与现代性的思想内涵。疾病叙事关涉国家、民族、阶级、人性等多种叙事因素,构成了丰富复杂的文本内涵,既有对个体命运、生命存在的叙述,又有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述,在广阔的历史语境中不断扩建意义。从疾病这一独特的角度来思考妇女问题、生命问题、现代启蒙,乃至国家、民族问题等,因此疾病叙事显示出了超越时代语境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对疾病的叙述犹若建立起了一个关系网络,由个体而想到家庭与社会,进而想到民族与国家。文学里的疾病叙事常常作为象征符号和修辞手段,被用来对当时的现实社会、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进行隐喻化的阐释,附带有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政治的或者美学的含义。疾病叙事以身体的病变来映射一个社会群体的颓废,来表征个体与民族的非常态存在,疾病叙事也就呈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直指作家的情感倾向。
[1][6][10][19](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5,5,18,65.
[2]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98,(6):84-85.
[3]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0.
[4][1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7,65.
[5]杨念群.再造“病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
[7][9][16](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96,39-41,10.
[8]吴晓东.一片被蚀而斑斓的病叶——疾病的文学意义[J].书城,2003,(4):39-41.
[1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A].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6.
[12]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98.
[14]谭光辉.晚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J].中华文化论坛,2007,(2):82-87.
[15]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53-169.
[17](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0.
[18]成仿吾.新文学的使命[A].王立鹏.王统照的文学道路[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