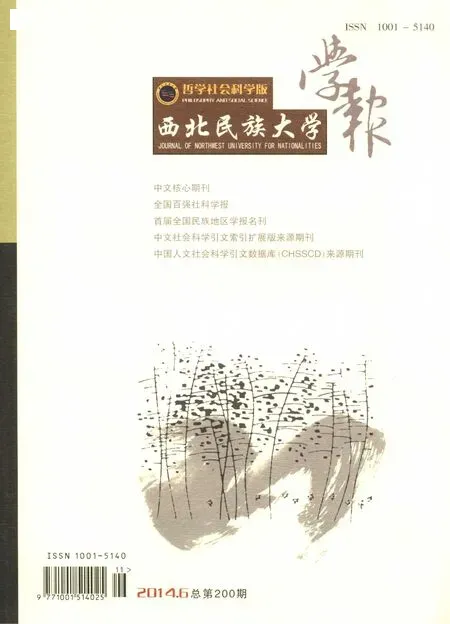中央支持民族地区政策体系的科学基础探寻
张冬梅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这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央支持民族地区政策体系(下文简称“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立足民族地区实际,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支持民族地区走各具特色的跨越式发展之路,为确保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民族地区发展具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双重约束,其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的综合推进过程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根本上讲要靠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仅仅依靠外部帮扶是不现实的;中央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十分关键的。政策体系是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系统,是一项针对民族意识与民族行为构建并不断进行完善的激励机制设计,是一项制度的顶层设计。因此,探寻从根源决定政策体系实施效果的科学基础成为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基于激励机制设计的政策体系更科学
中央支持政策的准确定位应在民族地区发展主体(政府、产业与民众)的“内在激励”上,换言之,政策更应该重视“给力”,而不仅仅是“给钱”。如何将中央支持政策转化为民族地区内在的动力源,进而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是激励机制设计者肩负的重要使命。
1.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目标激励相容是最优设计
中央支持政策的目标是促进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地发展,具体执行政策的是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方向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必须承认,民族地区利益与民族地区政府利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属于民族地区行政区中的各个主体(具体包括个人、各部门、各单位、各级政府)的共同利益;后者是民族地区的最大利益主体——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本应是地方共同利益的代表,然而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决策都是以个人的成本收益估算为基础的,政府行为由“人”决策和实施,政府的行为规则由“人”制定,而“人”是“经济人”,因此政府也是“经济人”。民族地区利益中包括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即政府人员的利益和政府机构的利益。这些利益的实现程度和实现方式对民族地区利益的影响客观存在。在中央支持政策安排中,民族地区政府作为利益主体接受中央政策,又作为调控主体在辖区范围内落实中央政策,这就存在民族地区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的问题。实际上中央支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过程,也是双方的博弈过程,这种博弈行为反映在事前、事中与事后。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机制设计是永恒的主题,这也恰是“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
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利奥尼德·赫维茨、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创立和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定义为: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合理机制(即制定什么样的方式、法则、政策条令、资源配置等规则),使得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相一致。政策体系要考虑激励相容的目标设计,即在民族地区特定资源环境下,研究如何设计一个政策机制,使得民族地区政府在自利行为驱动下采取行动,使得中央政策预定目标得以实现。简言之,“中央政府做什么,才能让民族地区政府做中央政府想做的事。”如果每个参与者真实报告其私人信息是占优策略,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因此,在制度或规则的设计者不了解所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设计者所要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所制定的机制能够给每个参与者一个激励,使参与者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所制定的目标,这就是机制设计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激励相容问题[1]。显然,只有民族地区政府选择中央政府所希望的行动得到的期望效用不小于选择其他行动得到的期望效用时,民族地区政府才会有积极选择中央政府所期望的行动。为提高中央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实现中央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求在信息分散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设计激励相容的政策体系。
2.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政府良性互动促进对称的信息传递
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显示原理表明:一个社会选择规则如果能够被一个特定机制的博弈均衡实现,那么它就是激励相容的[2]。如果假设人们是按照博弈论所刻画的方式行为的,并且设定按照社会选择理论对各种情形都有一个社会目标,那么机制设计就是考虑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这个博弈的均衡解就是这个社会目标,或者是落在社会目标集合里,或者是无限接近于这个社会目标。中央支持政策的最优设计依赖民族地区政府对称地显示真实信息,形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在现实经济环境中,未来是不确定的,且私人信息的存在致使博弈参与人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不完全的,博弈过程中充满了机会主义行为,广泛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民族地区政府的信息传递主要用来证明其具有的能力、特征等,如果民族地区政府对私人信息保密会获得更大的效用,那么他们就不情愿去披露私人信息。一方面,信息是有成本的,只有当信息公开会使民族地区政府的境况变得更好时,才会有积极性去传递反映其特征的信息;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政府会选择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竭力使中央政府降低对其自身信任的不完全程度,竭力显示诚实倾向、合作偏好及努力程度等。
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执行理论运用到政策体系,实际上重点是对政策机制运行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考察机制能否顺利运行,最值得关注的两个特征是信息和激励。机制的运行总是伴随着信息的传递,信息传递就成为影响机制运行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要使机制有效运行,最好的方式就是信息都是真实的,没有被扭曲,这既可以减少成本,又可以促使机制有效地运行。只有中央政府建立激励相容的政策安排,才能使地方政府的信息对称地显示与传递;只有地方政府的信息对称地显示与传递,中央政府才能建立激励相容的政策安排;因此,政策体系的完善是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政府长期动态的博弈过程。
二、基于民族文化价值观激励的政策体系更有效
价值观是人们在人生历程中所持的价值观念,包括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创造与实现;是判断是非曲直、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价值标准;是指人们在处理普遍性价值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是主体整合价值生活中具体经验事实的背景式价值意识,是主体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内在依据”[3]。价值观联系着人的直觉,影响着人的信念和选择的合理性,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投身其中的事业;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4];它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5]。人们在价值追求目标上抱有怎样的信念、信仰、理想便构成了价值观所持有的内容。“激励”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激励,少数民族对政府政策是否信任,是否会积极参与并选择行动的主要因素属于价值观范畴。
1.尊重与引导民族文化价值观是内在化的激励方式
价值观是文化层次中最核心的内容和范畴。民族文化决定少数民族特殊的偏好,如蒙古族草原的马奶酒、傣族的孔雀舞、回族的“花儿”、藏族的哈达等[6];民族偏好决定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民族行为。“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渗透在个体思维与心理的民族模式之中,是个体成员价值评判和行为选择的重要凭借……接受民族文化价值观熏陶和教化的个体,往往具有本民族特有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判断,以及鲜明的民族思维和民族定势。”[7]因此,在中央支持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考虑尊重民族文化价值观。
价值观源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个人修养及社会联系等,它是由复杂的历史、地理、心理、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超理性的现成的东西,而不是某种合乎理性的决策的结果,因此,价值观具有时代性、地区性、民族性等特点,任何社会的价值观都必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社会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变革都会引起价值观的改变;某种价值观在特定历史阶段是合理的,但是在进一步的历史发展中却可能成为一种习惯势力或惰性力量,从而影响和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内学者赵德兴等人专门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居民的价值观做调查,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的当代价值观相对传统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8],进而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中央支持政策制定的事实因素中,要在尊重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与培育一些代表社会正确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观念,从而使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得以有效协调,这是影响少数民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并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的激励方式;对核心价值观的承认、认可与赞同,可以消除少数民族在多元价值冲突中的迷失,形成更高社会信任的自我构建。①自我构建定义为“人们对自我与社会环境连结或分离程度的感知”。Markus,H.R.&Kitayama,S.“Culture and self: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emotion and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991,Vol.98,(April),pp.224-253.正如西蒙指出,在任何决策中均包含有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两个方面,前者就是制定一项决策所依据的外部客观事实,决策者依据这些信息去认识问题,进而找出问题的症结,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后者是指决策者在进行任何一项决策时不可能仅仅依据事实因素,在此过程中必定受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往往与伦理道德因素有关[9]。值得深思的是,这里的事实因素包括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在信息非对称情况下,中央政策决策者要考虑到其与自身价值观的差异,要在自身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价值观两方面相互影响的背景下产生最终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政策是特定制度的产物,是决策者在这个制度框架内综合平衡的结果,因此中央政策决策者对差异价值观的协调规定着政治进程和管理过程,并且是资源分配的指导原则的核心。
2.构建包容的制度环境确保少数民族积极参与政策实施
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表现为多元化,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文化价值观间的冲突也容易发生,因此,构建包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制度环境,提升社会信任,逐渐转变少数民族群众从“强调人际关系信任转向强调监督、预防和惩罚机制的制度信任”[10],增强少数民族自信,确保少数民族积极参与政策实施显得极为重要。价值观差异的影响渗透到中央支持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在政策实践中必然会反映人们内心不同的主观愿望及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看法。包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社会环境,更易消除少数民族被排斥的感觉,促进少数民族自信与社会信任的良性互动,社会良性互动是激发少数民族内在积极性与潜能的关键,积极参与、加入、收益,并有归属感,从族际文化间的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过程中领悟到文化的相通性、相融性与另变性。
包容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提升全社会的信任水平。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度量维度[11],与文化资本的核心要素文化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创新绩效的部分影响是通过社会信任因素起作用的[12],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已是继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后的对社会创新绩效产生巨大影响的资本形式。包容的制度环境是对不同民族、宗教及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开放的,是建立在所有人之间矛盾的观念、需求、价值观等多样性的基础上的,这并不威胁社会的稳定,相反正是社会灵活与开放的一面。开放的社会不再仅有一元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的凝聚力并不要求不同的团体融合为一个缺乏差异的实体,反而凝聚力能够通过不同团体的互动在多样性的社会中获得并加强,平等的原则指导互动,多维观念的认同、归属的多重感觉经常能够增加自信,使社会网络更稳定,从而更有利于提升国家创新绩效。
中国历史上文化取向的民族观以及“以和亲之”“因俗而治”的处理族际关系的方式,体现出中华文化对待族类上的品格、修养和高超的智慧;族际观念从封闭的、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善恶判断走向开放、圆融和富有智慧[13]。基于民族文化价值观激励的政策体系的目的是促进少数民族参与到所有政策层面,能够成为充分参与者参加到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发展中,构建一个合意的社会秩序。
三、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的政策体系更绿色
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民族地区要考虑本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绿色发展转型。
1.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要求民族地区走绿色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特殊地理区位决定的资源环境不仅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与约束,同时成为全国宏观经济发展规划与战略的重要问题。世界各国早已将稀缺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其价值日趋升高,经济学上将其称为“自然资本”。忽视资源再生产规律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实践证明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是得不偿失的急功近利行为,是与长期发展目标相矛盾的短期行为。
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全国的生态屏障,肩负保护全国生态环境的重要任务,且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域大多数位于民族地区,因此资源环境承载力无疑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约束之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民族地区重视资源环境保护,建设“两型”社会要求民族地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生态文明要求人们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坚持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高效益、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要在民族地区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增强危机意识,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更好地节约和管理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进而提高生态文明。
2.绿色发展要求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确保自然资本的总体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民族地区乃至全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需要。要摆脱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要求民族地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或曰拓展内生能力,实现内生增长,即区域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依靠区域经济系统内部作用获取经济增长的动力[14]。要实现绿色产业转型,民族地区要增强自身经济、社会、人力与自然资本的积累,从而激发绿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及民族地区外投资维持长期发展繁荣是不现实的。作为全国生态环境系统最脆弱、贫困问题最突出、民族文化差异最显著的民族地区,首先要考虑从国家政策创新引导并带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自然和社会资源优势,培育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地明确不同民族地区的绿色发展潜力,例如森林草原相关的生态产业、水电风电等相关的清洁能源产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文化资源旅游产业等,提升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制定差别化的绿色产业准入规则,避免其他地区的污染性行业转移到民族地区。政策体系要满足资源环境承载力这一重要约束条件,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四、基于整体福利增进的政策体系更和谐
福利经济学原理表明每个社会的目标都是追求其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政策体系旨在提高民族地区乃至全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1.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政策体系增进民族地区整体福利
福利经济学认为,“个人福利(individual welfare)被看做是个人的wellbeing(平安、健康、幸福、兴衰)”。一般情况下,个人福利可以用个人的效用来表示,假设个人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全社会的福利的大小取决于影响社会成员个人福利的所有因素,是经济福利、社会福利与生态福利的总和,即整体福利。在实际的现代社会中,增进经济福利是人们首先关注的福利目标,诚然,经济福利不能作为整体福利,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恰恰主要是经济因素这一点而非其他,影响了民族地区非经济福利,并因此又进一步影响了经济福利。
要增进民族地区整体福利,就要同步增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福利。首先,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福利水平。庇古的理论是分配影响福利,不同的制度对同一个人收益的影响是不同的,政府通过提供某些政策直接改变利益分配格局。如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多为资源性国有资产,国有产权安排是多方参与的利益共享,为确保民族地区经济利益,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等手段作用于市场经济运行,提高中央支持政策的经济效益。其次,提高民族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社会福利还取决于自由、公平、权利等方面。罗尔斯理论要求在最为广泛的基本自由平等的总制度中,每个人都要享有平等的权利,且应该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做出安排,要对最为不利的人产生最大收益[15]。诺兹克提出了所谓的应得权利理论,该理论不是从结果的角度,而是从程序上来评价分配公平(程序公平)[16],认为只要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尊重,就认为任何分配都是公平的。森的公平理论把对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17]。为了达到公平的最优效果,研究社会经济状态,提供政策体系的创新性安排,需要协调市场秩序与非市场秩序之间的关系,最大化地追求整个社会秩序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第三,提高民族地区生态福利水平。判断社会的福利标准更应该从长期来考察,所有人的福利水平都会由于生态福利的提高而提高,生态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水平,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态福利。生态福利影响经济福利,同时约束着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日益发展,人们对生态福利目标的要求越来越高。理论和实践证明,政策体系的有效安排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一个分配问题。
2.民族地区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函数确定后,最优的社会选择就是在满足社会面临的约束条件下追求福利函数的最优值。要想实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整体福利水平提升,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制度资源,既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政策的经济效益;又要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提高政策的社会效益;还要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政策的生态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牢牢把握和谐发展的原则,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综上,中央支持民族地区政策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这一政策系统的创新性安排要注意挖掘其积极因素,增强发展的后劲,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就要更加强调“激励”,充分调动民族地区政府、产业和民众的积极性,立足于在民族地区建立自我发展机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促进绿色发展,增进民族地区整体福利。
[1]Hurwicz I.On Informationally Decentralized System”[R].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1972,Results 1-10 of 67.
[2]Gibbard A..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s:A General Result[J].Economitrica,1973,Vol.41,No.4,pp.587-601.
[3]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1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242.
[4]Schwartz,S.H,and W.Bilsky.Toward a univers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Vol.53,No.3,pp.550-562.
[5]Schwartz,S.H.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2,Vol.25,pp.1-65.
[6]Harsany,J.C.Utilities,preferences,and substantive goods[J].Soc.Choice Welfare,1997,Vol.14,pp.133-135.
[7]詹小美,金素端.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化认同[J].青海社会科学,2013,(3).25.
[8]赵德兴等.社会转型期西北少数民族居民价值观嬗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2-428.
[9]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71.
[10]郭晓凌,张银龙.文化与信任:国家与个人双层面的实证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36.
[11]Stephen K.,KeeferP..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Vol.112,No.4,pp.1251-1288.
[12]李晓梅.社会信任与文化价值观对于国家创新绩效的作用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8):98.
[13]毕跃光.从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看民族观的形成[J].贵州民族研究,2003,(3):21.
[1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与发展政策研究报告.区域平衡与绿色发展[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81.
[15]Rawls,J..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3-62.
[16]Nozick,R..Anarchy.State and Utopia[M].New York:Basic Books,1974,pp.32-67.
[17]Sen,A.K..Description as a Choice[J].Oxford Economic Pap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Vol.32,No.3,pp.353-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