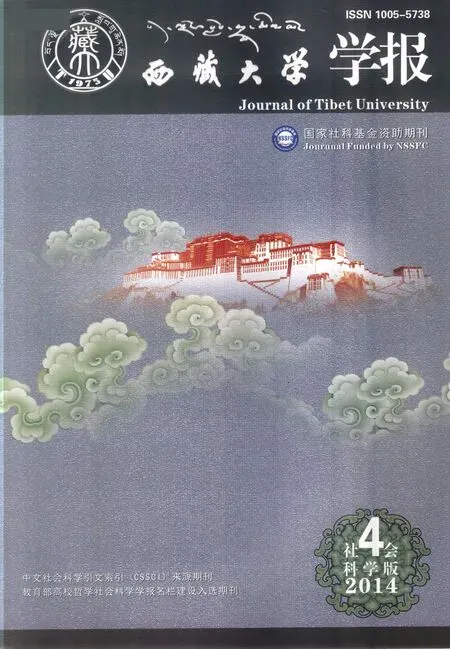从神话叙事到神性写作
——论19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的话语谱系
叶立文 游迎亚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从神话叙事到神性写作
——论19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的话语谱系
叶立文 游迎亚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代际嬗变始于启蒙叙事对十七年小说神话叙事的鼎力反拨,但启蒙叙事这一反神话叙事的话语方式,却逐步演化成了一种以道德神话为内核的新神话叙事。至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启蒙文学的暂时消歇,当代小说的叙事话语又转向了以欲望叙事为突出特征的世俗化叙事。此消彼长之下,世俗化叙事终以构筑身体神话的方式,取代之前的新神话叙事成为了当代小说的叙事主流。但在此历史进程中,启蒙叙事与世俗化叙事的话语博弈,又于90年代中后期催生出了神性写作这一新的小说叙事话语。从神话叙事到新神话叙事,再到世俗化叙事与神性写作,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发展流变,已然自成系统地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
神话叙事;启蒙叙事;世俗化叙事;神性写作
自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的每一次革新几乎都与社会思潮的嬗变息息相关:从1980年代感时忧国的启蒙文学,到1990年代欲望狂欢的世俗化书写,再到新世纪初承领苦难的神性写作,中国当代小说所发生的种种历史流变,莫不折射出时代风尚和社会变迁对于文学领域的深刻影响。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说,[1]庶几可解释当代小说的这种话语转型。然而,倘若论及当代小说在叙事话语层面的革故鼎新,却不可不言及一个与社会思潮内外有别的知识谱系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当代小说自成一格的叙事话语谱系,才在设定作家叙述理念和叙述方式的基础上,重塑了当代小说的发展面貌。较之社会思潮这一外部诱因,那些彼此传承、经纬交织的叙事话语,似乎更能影响当代小说的叙事主题与美学风格。有鉴于此,若能厘定和廓清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知识谱系,则有望在文学社会学的阐释思路之外,寻绎出当代小说在近三十余年来发展流变的内在原因。
一、十七年小说的神话叙事
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看,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代际嬗变始于中国作家对十七年小说神话叙事的鼎力反拨。1980年代小说创作中盛极一时的启蒙叙事,不仅颠覆和解构了此前以国家乌托邦主义为表征的神话叙事,而且还在以人学思想重构小说叙事的文学革命中,渐次演化成了一种以道德神话为内核的新神话叙事。至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启蒙文学的暂时消歇,当代小说的叙事话语又转向了以欲望叙事为突出特征的世俗化叙事。此消彼长之下,世俗化叙事终以构筑身体神话的方式,取代之前的新神话叙事成为了当代小说的叙事主流。但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作家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却并未随着世俗化时代的来临而全面隐退,反倒是在与世俗化叙事的话语博弈中,于90年代中后期催生出了神性写作这一新的小说叙事话语。从神话叙事到新神话叙事,再到世俗化叙事与神性写作,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发展流变,已然自成系统地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
但问题在于,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这一知识谱系,却并不完全呈现为新叙事话语对旧叙事话语的消解与置换,反倒是新旧叙事话语之间所展开的权力博弈,更能彰显这一知识谱系的复杂面貌。譬如说世俗化叙事中的欲望叙事,其实始自19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的启蒙叙事。若以进化论视角观之,以为世俗化叙事就是对于启蒙叙事的颠覆与解构,那么就会忽略“知识谱系”这一自在之物的历史复杂性——谱系之内经纬交织的话语权力,岂能被简单视为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历史沿革?[2]同样,90年代中后期神性写作的兴起,也并不完全依赖于对世俗化叙事的反拨,像张承志的《心灵史》这般以道德自圣为叙事本位的神性写作,同样与启蒙叙事的道德神话之间渊源颇深。由此可见,启蒙叙事对此前神话叙事的颠覆,世俗化叙事对启蒙叙事的解构,以及神性写作对世俗化叙事的反拨,都只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说,梳理当代小说从神话叙事到神性写作的话语谱系,实际上也是一个为后继话语类型提炼历史内因、寻其历史渊源的知识考古过程。换言之,惟有辨析出这一知识谱系内部两种异质话语之间的传承与博弈关系,那些促成当代小说发展流变的内在诱因,亦即通常所谓的“文学规律”也才能够自然显现。
如前所述,既然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变化始自中国作家对十七年小说神话叙事的颠覆与解构,那么就有必要首先阐明这一文学时段的神话叙事问题。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由于作家秉承了文学为政治服务,以及用小说反映现实的叙述理念,故而其叙事话语总是以揭示社会历史进程为己任。随着左倾文艺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十七年作家在小说叙事中倾向于展开对历史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文学阐释。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种历史之必然,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文学的任务就在于再现现实。在所谓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个体的生命印痕或是命运变故都得屈服于历史之永恒不变的铁血法则——此即为历史理性主义的思想核心。更为重要的是,为将乌托邦式的国家主义思想贯彻始终,十七年作家也常常会在看似客观的现实主义叙述中,将某些人为的历史错误表述为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诸如50年代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以及60年代的自然灾害等左倾错误,就往往被十七年作家出于“政治正确”的目的,在《创业史》、《青春之歌》和其它一些作品中叙述为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途中的历史必然。这种将人为的“历史决定”表述为无可更改的“自然法则”的话语形式,即为神话叙事。按罗兰·巴特的说法,所谓的神话学即是将“历史”表述为“自然”,对“历史”和“自然”的混淆,是一种“有待揭露的错觉、谬见”。[3]一旦历史决定被转换成自然法则,那么国人就只能以服膺历史规律的名义,无条件地接纳那些造成我们民族创伤的人为错误。就此而言,十七年小说的神话叙事不仅以推崇历史理性主义思想的方式让文学远离了人学,而且还在承载国家乌托邦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异化了文学自身。在嗣后的“文革”文学中,十七年小说的这种神话叙事更是趋于顶峰:像《虹南作战史》和《西沙儿女》这类“文革”小说,有意将保卫西沙群岛等历史事件叙述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这一“自然法则”背后的历史决定,亦即“四人帮”集团的政治阴谋等“历史决定”反倒被深深隐藏。在这样的一种神话叙事下,国人岂能借助理性之光去审视和批判历史真实?因此可以说,新时期之前小说创作中的神话叙事,实际上承担起了构建国人政治伦理、抹杀人之主体性的历史功能。
二、启蒙与神话叙事的话语博弈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高涨,十七年小说的这种神话叙事也遭到了启蒙叙事的全面解构。作为八十年代小说中最为重要的叙事话语,启蒙叙事的初衷,即为对小说创作中神话学色彩的祛魅与剔除:不论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小说,还是以个体生命感觉为旨归的先锋小说,皆以彰显人之主体性、表达文学对人的叙事关怀为己任。在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既往小说叙事的国家乌托邦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思想,正面临着以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为批判武器的启蒙叙事的全面挑战。譬如在八十年代初期王蒙等作家的“意识流”小说《蝴蝶》和《布礼》中,反讽式的修辞手法和自由联想的心理揭示,处处颠覆了既往小说叙述中的政治神话。[4]而先锋作家对人物个体生命感觉的深度叙述,则不仅让文学重归人学母题,同时更在历史批判的启蒙叙事中,解构了十七年小说神话叙事的政治色彩。[5]但较之这种颠覆与反抗,启蒙叙事对神话叙事的继承与改写却甚少引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所培育出来的神话叙事,固然在新时期遭到了启蒙叙事的全面解构,但启蒙运动本身所具有的民族国家想象特质,却依然为这种看似落伍的神话叙事提供了生存土壤。它不仅以宏大叙事的面貌存在于八十年代前期的人道主义小说之中,更以佯装为启蒙叙事的方式潜隐于知青小说和先锋小说之下。八十年代小说叙事话语的历史流变,也因此显得极为吊诡——原本以解构神话叙事为目标的启蒙叙事,却在其解构对象的潜在影响下,从启蒙思想的人道关怀渐次演化成为了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思想内核、以道德神话为表现形式的新神话叙事。有鉴于此,为廓清八十年代小说从神话叙事到启蒙叙事,再到启蒙叙事演化为新神话叙事的知识谱系,就有必要从神话叙事的存在方式谈起。
具体而言,尽管神话叙事在八十年代遭遇到了启蒙叙事的全面解构,但其流风余绪却依然隐含于八十年代前期的人道主义文学,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之中。在人道主义小说,尤其是知青小说中,神话叙事的国家乌托邦色彩业已全面淡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启蒙时代,重提集体主义的政治诉求显然已不合时宜。但神话叙事将历史决定表述为自然法则的叙述方式,却依然影响了知青作家的历史记忆。在知青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启蒙叙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叙事话语,他们对自己这一代人上山下乡经历的集体叙述,由于建构在对历史本身的警醒与反思之上,故而本身就可以纳入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文学的启蒙范畴。但出于对神话叙事蓄意制造历史记忆的叙述方式的反叛,知青作家又强调在启蒙叙事中历史记忆的多样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历史真实从来都不是神话叙事所讲述出来的以国家乌托邦主义为梦想的集体记忆,而是一个仅仅与自我经历和生命体验相关的个人记忆。换言之,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所谓普遍客观的历史真实并不存在。这一具有新历史主义特质的历史记忆方式,显然是启蒙叙事颠覆既往历史理性主义的思想产物。但知青小说这种反神话叙事的启蒙叙事,却在凭借个人记忆讲述出历史多样性的同时,并未完全脱困于神话叙事的话语模式。譬如在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中,知青为北大荒献身的悲壮故事,就被作家叙述成了知青群体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倾心归顺。在此叙述方式下,造成小说人物裴晓芸壮烈牺牲的客观原因,也不再是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悲剧本身,而是酷烈残暴的自然之力。由是观之,当梁晓声将知青运动这一悲剧肇因(历史决定)转换为北大荒的暴风烈雪(自然法则)之时,作家也就放弃了启蒙叙事所独有的历史批判精神。换言之,将历史决定表述为自然法则的神话叙事模式,有时依然会以佯装为启蒙叙事的面目存在于某些知青作家笔下。
至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先锋小说运动的持续发展,传统神话叙事的国家乌托邦主义也逐步褪去了宏大叙事的外衣。但这并不等于说,以书写人物异化境地、描摹自我生命感觉为目标的先锋小说,就会放弃中国作家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想象情结。对于先锋作家而言,讲述人物纯然属己的生命故事,寓言他们与异己力量之间的精神苦斗,都只不过是启蒙叙事弘扬人之主体性,将人从历史理性主义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叙事策略。但较之这种启蒙主义对人的解放,先锋作家的叙事动机却仍与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密切相关:譬如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不就是通过对国民原始生命力的发扬蹈厉,试图实践其民族再造与强国之梦的政治诉求?同样,余华在《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等作中对鲁迅启蒙文学的全面继承与改写,不也蕴藉着以国民性改造实现复兴之梦的国家想象?[6]韩少功在《爸爸爸》中所构筑的民族寓言,苏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所表达的历史记忆,以及残雪在《黄泥街》中对历史荒诞性的批判,又哪一样不与先锋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梦想息息相关?就此而言,即便是在以个体叙事为基调的先锋小说中,也存在着神话叙事与启蒙叙事这两类叙事话语。尽管神话叙事的国家主义业已被启蒙主义的民族国家想象所取代,但其对启蒙叙事的影响也依然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作家一方面以启蒙叙事讲述人物对历史理性主义的生命抗争,描摹其精神世界的绝对解放,但另一方面却又以神话叙事不自觉地工具化了这些人物——似乎人的解放,仅仅是为了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历史目标。说到底,启蒙叙事中所谓人的解放,不过又再次沦为了国家梦想的政治棋子。由此可见,先锋作家若想将自由个体的生命故事讲述下去,就必须更为彻底地解构神话叙事。但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启蒙叙事对神话叙事的这种深度解构,却令自身逐步发展成为了一种新神话叙事。
三、新神话叙事的形成
在80年代小说的启蒙叙事中,欲望叙事的出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学事件。从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小说,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和余华的《现实一种》等先锋小说,欲望叙事的崛起已然成为了启蒙叙事的突出表征。而对于传统的神话叙事来说,欲望叙事显然具有最为强大的颠覆功能:通过对人物暴力欲望、生之本能以及死之本能的细致书写,80年代的启蒙作家终能冲破神话叙事所织就的思想牢笼,从而在异己的历史理性之外,寻求到人之存在的本真面目。欲望叙事对人生命本能的发掘与弘扬,也因此在80年代具有了一种革命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欲望叙事对人生命本能的书写,应和的正是启蒙叙事中一个最为根本的思想理念,即人是宇宙万物的灵长,文学理应表达人的存在问题。尽管欲望叙事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传统的伦理思想,混淆人性的美丑和道德的善恶,但正因其叙事焦点完全置于人类自身,所以才能在一种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人性描写中,反抗神话叙事所表征的历史理性主义对人生命本能的强力压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张贤亮、王安忆、莫言和余华等作家,会始终致力于对欲望叙事的表达。隐含其后的人道关怀,以及对神话叙事的反拨,无疑唤起了80年代青年读者的情感共鸣。但问题却在于,随着先锋小说对欲望叙事的不断强化,这一原本具有革命功能的叙述话语却将启蒙叙事愈发推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藩篱。
一般而言,启蒙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潮流,它呼吁人的理性精神,尊重天赋人权,追求自由平等。但启蒙主义却并不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在启蒙主义的思想视域中,真正的理性精神势必会看到人存在的有限性。但在80年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欲望叙事的不断高涨,启蒙叙事本应具有的理性精神却渐渐付之阙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先锋作家笔下,他们认为人的主体性至高无上,人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主体意识去实现自我价值,由是也就逐步将启蒙叙事演化成了一种启蒙神话。受此影响,限制叙事往往成为先锋作家乐于采用的叙事视角。因为限制叙事,特别是第一人称叙事(“我”之叙事),可以充分讲述“我”纯然属己的生命故事,楬橥那些蜷缩于历史边缘的个人话语,进而在反抗历史规律的叙述进程中重新树立“我”之价值。因此,那些人之为人的本质,诸如欲望、梦想与记忆,便成为先锋作家不懈书写的客观对象。换言之,先锋作家采用限制视角的真正用意,无非是借助叙事者的心理体验,去张扬远比历史规律更为重要的人之主体性。在这一叙事实验中,先锋作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可谓是展露无遗。
更为重要的是,当欲望叙事将启蒙叙事转化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后,80年代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也似乎找到了一个更为坚实的思想平台。从历史上看,中国作家从来就不缺乏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只不过十七年小说神话叙事中的道德理想主义,更像是一种心怀天下的事功思想,比如柳青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描写,杨沫对革命新青年的塑造,表达的都是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而生的一种集体道德,其工具论色彩显然排斥了个人品行的自我修养。相形之下,80年代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由于建构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故而对道德修养和理想精神的倡扬,也就具有了一种活出人性尊严的存在内涵。这显然也是启蒙叙事对神话叙事压制个人存在的一种反抗方式。不过饶有意味的是,一旦80年代作家将道德理想主义情怀从神话叙事的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转化为启蒙叙事的人性尊严时,这一思想话语也因此逐步演化成为了一种道德神话:从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到张炜的《古船》等作,80年代的启蒙作家愈发将个人的道德理想视为了人物对抗异己力量的一种存在方式。由是所演化出来的自圣哲学,庶几可被视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极端表达。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神话:作为启蒙叙事主体的中国作家,越发将自己和具有国民劣根性的庸众对立了起来,他们对人性尊严的无限放大,已然达到了蔑视世俗伦理、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维度。从这个角度说,不论是欲望叙事对启蒙叙事的改造,还是启蒙叙事中道德神话的形成,都表明曾经一度为庸众忧心的启蒙作家,已越来越放弃了启蒙叙事的疗救功能,转而以道德自圣的存在方式日益远离了早年的启蒙说教。就此而言,在欲望叙事的影响下,八十年代的启蒙叙事已渐次演化成为了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思想内核、以道德神话为表现形式的新神话叙事。
四、启蒙与世俗化叙事的话语合流
从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小说领域的叙事话语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世俗化叙事取代启蒙叙事成为这一时期的话语主流。一般认为,世俗化叙事的兴起,是中国作家在市场化环境下所做出的一种历史选择,它对于启蒙叙事的颠覆与解构,不过是小说叙事话语自我进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正如前文所述,世俗化叙事与启蒙叙事的话语博弈,远非新叙事话语取代旧叙事话语这般简单。从某种程度上说,世俗化叙事虽然打着解构启蒙叙事,尤其是新神话叙事的幌子出现,但其知识谱系却依然可追溯到启蒙叙事之中。更准确地说,90年代世俗化叙事的话语谱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80年代小说中世俗化叙事话语的质变;其二是对启蒙叙事话语,尤其是欲望叙事的继承与解构。前者不难理解,因为早在80年代启蒙叙事独领风骚的历史时期,当代小说的世俗化叙事就已悄然勃兴。通俗文学中的金庸热、琼瑶热,虽未真正触及纯文学领域的话语递嬗,但其对读者市场的培养之功却不容小觑。一俟日后王朔和池莉等人的世俗化叙事出现之时,读者对其中文化祛魅功能的理解也自然是我心戚戚。像王朔对知识分子启蒙理想的解构、池莉和刘震云等新写实诸家对一地鸡毛式的烦恼人生的描画,均缘起于80年代通俗文学的浸润与滋养。至90年代初期,随着文学的市场化趋向愈发明显,以新生代、新状态、新市民命名的各种世俗化写作也毫无保留地承继了此前王朔等人的解构精神。与此同时,90年代世俗化叙事对启蒙神话中欲望叙事的解构与继承也同样引人瞩目。如果说80年代的王朔和池莉等人,将世俗化写作视为解构启蒙叙事这一新神话叙事的主要武器,那么90年代的世俗化叙事就更加彻底地剥离了这种革命精神。因为在90年代的世俗化叙事中,中国作家已将叙述焦点从对新神话叙事的革命性解构完全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合法性的证明。前者或多或少因其革命性而让世俗化叙事具有了一种启蒙特质,而后者就在放逐这种革命性解构功能的同时,也真正令世俗化叙事回归到了其日常叙事的话语本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的世俗化叙事中,欲望叙事依然是其核心内容。只不过较之此前启蒙叙事中的欲望叙事,世俗化叙事的欲望书写也已剥离了自身的革命功能。两者之间的复杂性就在于:一方面90年代的世俗化叙事继承了启蒙叙事中的欲望叙事,将叙述焦点仍然放在了对人物生命本能的发掘与张扬上;而另一方面,90年代的世俗化叙事在进行欲望书写时,却以身体崇拜的叙述姿态解构了启蒙叙事中欲望叙事对于神话叙事的解构功能。以80年代的余华和90年代的卫慧为例,前者的暴力叙述在批判锋芒上无一不指向了种种压制人的异己力量,但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有关身体的种种欲望书写,却已然将余华笔下的启蒙神话转换为了一种身体神话。对身体的迷恋与崇拜,对自我生命感觉的把玩,以及对自我内心欲望合法性的证明,业已成为90年代世俗化叙事的核心内容。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启蒙叙事的欲望叙事因其对神话叙事的解构功能从而具有了一种工具论色彩的话,那么世俗化叙事中的欲望叙事就以展示人的本能欲望、证明其现实合法性为己任,在描写自恋、身体和暴力等禁忌话语的同时,迎合着读者的生理及心理需要。这显然是文学市场化之后当代小说的一次彻底转向。而从小说叙事的文体结构来看,80年代小说的启蒙叙事本身也包含着某些世俗化叙事的话语形式,如先锋作家余华对于通俗小说的文体戏仿就是一个突出例证,《鲜血梅花》之于武侠小说,《古典爱情》之于言情小说,《河边的错误》之于侦探小说等等,皆预示着启蒙叙事与世俗化叙事之间日趋模糊的话语界限。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此,由于90年代世俗化叙事中的欲望叙事本身就来自于80年代的启蒙叙事,兼之中国作家对自身启蒙情结的无时或忘,故而在世俗化叙事与启蒙叙事这两类话语模式之间,就于90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难分彼此的权力博弈,其突出表征就是启蒙叙事对于世俗化叙事的话语兼容。
按照文学史的一般叙述,90年代文学中的启蒙叙事,主要是为了反拨日益流行的世俗化叙事而生。[7]但从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却颇能见到两种话语模式日益合流的发展趋向。在90年代小说的启蒙叙事中,当代作家不仅继承了早年启蒙文学的国民性改造主题,更在具体的叙述实践中广泛吸纳了世俗化叙事的种种叙事策略。诸如身体叙事、欲望狂欢等世俗化叙事的基本元素,皆在90年代小说的启蒙叙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以林白、陈染的女性写作为例,这两位作家对女性人物生命感觉的书写,对男权社会权力话语的鼎力反抗,都明显接续了80年代小说的启蒙叙事传统。但在描写女性人物的异化境地时,这两位女性作家却在《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等作中,集中笔力书写了女性人物的身体及心理创伤。对身体叙事的迷恋,使得林白和陈染的作品也沾染了一定的商业化色彩。但有心读者不难发现,这两位女作家对身体的叙事过程,却充满着启蒙叙事的颠覆与解构之力。比起更为年轻一代的女性作家,比如卫慧和棉棉等新生代,林白与陈染的女性写作更迹近于启蒙叙事中的女性主义。她们对女性隐秘创伤的直白表达,对男权社会的异己力量,均进行了解构主义式的启蒙言说。从这一点来看,90年代小说中启蒙叙事对于世俗化叙事的话语兼容,显然立足于对欲望叙事的承续与改造之上。
除此之外,在其他的一些启蒙作家,比如王小波、莫言、贾平凹甚至是陈忠实笔下,世俗化叙事的某些叙事策略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以王小波这位典型的启蒙作家为例,他的时代三部曲、《红拂夜奔》和《革命时期的爱情》等作品,虽然主旨仍在于对个人异化境地的表达和对自由之境的向往,但其黑色幽默中比比皆是的戏仿与嘲弄,却恰如其分地契合了90年代的世俗化语境。可以这样理解,王小波实际上用一种后现代式的世俗化叙事形式,深刻表达了国人在历史权力重压之下的屈辱和卑微。隐含其中的自嘲与无奈,显然在反映小人物不屈的抗争之情时,传达了一代国民的历史记忆。就此而言,王小波这位启蒙作家,正是因为广泛运用了世俗化叙事中的戏仿与自嘲精神,才会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情境中,得以让当代小说的启蒙传统薪火相传。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莫言和贾平凹等作家笔下,不论《丰乳肥臀》还是《废都》等作,都集中表达了这两位作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讽喻之情。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欲望叙事,莫不传递着他们的历史忧思。就此而言,九十年代小说中世俗化叙事与启蒙叙事的话语博弈,虽然起步于世俗化叙事对启蒙叙事这一新神话叙事的解构,但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却发生了明显的历史合流。
五、神性写作的思想价值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新世纪,当代小说中又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世俗化叙事与启蒙叙事的新型话语方式,这一叙事话语即为神性写作。张承志的《心灵史》、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等长篇小说,皆可被视为这一叙事方式的话语实践。如果以文学史视角观之,当代小说的这一叙事话语可谓是其来有自:早于80年代中期,就有北村以《施洗的河》一作率先揭开了当代小说的神性叙事。但在中国大陆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类似于北村这般以基督徒身份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可谓是凤毛麟角。神性写作对自我生命迷途的奉献、对此世存在苦难的承领,以及对彼岸神圣价值的倾心,似乎永远与实用理性精神至上的中国作家格格不入。因而在80年代的文学主潮中,鲜少有中国作家致力于神性写作的小说叙事。不过这一状况在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却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心灵史》和《务虚笔记》等作品的横空出世,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了神性写作对于当代小说叙事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如果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看,90年代中期小说叙事中神性写作的出现,主要与当代作家对于世俗化叙事和启蒙叙事这一新神话叙事的双重反拨密切相关。就反拨世俗化叙事这一层面而言,神性写作所具有的思想价值毋庸讳言。在一个缺乏信仰的世俗化时代,借助神性写作的思想言说,不仅可以疗救无处不在的虚无主义,而且也能在敬畏神圣价值、正视现世苦难的前提下,鞭策国人踏上拯救之途。相较之下,神性写作对于启蒙叙事这一新神话叙事的反拨则显得十分复杂。可以这样理解,当启蒙叙事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泥潭之后,当启蒙作家以道德自圣的存在面目示人之时,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也已丧失殆尽,彷佛只剩下了一种盲目自大的主体信念:所谓人定胜天的启蒙理想,只不过是我们无视人之存在有限性的狂妄与无知。针对这样的一种新神话叙事,史铁生这位曾经的启蒙作家率先走出了启蒙的迷途。
进入90年代以后,史铁生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获得了这样一种认知,即启蒙哲学所倡导的对人之有限性的克服与超越,实则深深受制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藩篱。由于人对自身主体性力量的盲目崇信,反而会无视人之有限性本身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倘若结合史铁生在90年代以来所写下的长篇小说,当能明了他对人之有限性的理解,其实并非克服与超越,而是接纳与臣服。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能够真正体会人的这种有限性,那么就有可能使其成为我们承领上帝之恩泽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史铁生才会在后来的《病隙碎笔》中如是说:“你在你的时空之维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地观察呀,实验呀,猜想呵,思辨呀”,却不知“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8]所谓的“迷途”一语,在此便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指启蒙神话对人之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业已成为阻碍人获得神恩救赎的思想牢笼;二是指在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启蒙时代,人理应去接纳自己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接纳与臣服中,将自己的生命迷途呈现于世人面前。唯有如此,人方有可能承领上帝的恩泽。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中,史铁生讲述了一个身魂分离的故事。他试图以宗教哲学的神性维度,揭示“我”这一生命个体的在世意义。在他看来,“我”其实就是上帝的仆人亚当,在无法抵御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从此便与夏娃天各一方,而“我”的生命意义,也因此全系于对夏娃芳踪的苦苦寻觅——惟有和夏娃这样的一个“你”的重逢,“我”才有可能实践那生命原初的伊甸盟约。因为这一盟约,是上帝对世人的殷切嘱托,只有实践了这一盟约,人才能以承领上帝恩泽的形式圆满自我。对于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史铁生来说,寻找夏娃就是生命个体追求自我认识,活出人生意义的终极事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史铁生笔下,爱情总是沐浴着神性光辉的原因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其实通过亚当寻找夏娃的故事,解答了“我”如何承领上帝神恩的皈依之途。
不过较之史铁生对新神话叙事的反拨,另外一位同样以神性写作名世的当代作家张承志,却在《心灵史》这部作品中呈现出了一份更为复杂的思想风貌。这一复杂性就在于,《心灵史》固然是一种解构启蒙叙事的神性写作,但在张承志壮怀激烈的神性启示和暴躁凌厉的美学风格下,却隐含着一种《黑骏马》式的道德神话。以反拨启蒙叙事这一新神话叙事为创作主旨的神性写作,却依然在话语实践中兼容了它自身的解构对象。作为一部宣讲伊斯兰哲合忍耶的鸿篇巨制,《心灵史》首先从反智主义的思想表达起步,在嘲笑知识和理性的解构叙述中,倡扬了信仰和牺牲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心灵史》无疑是一部绝对意义上的神性写作,因为它不求理解,只求皈依的言说方式,真正超越了以理解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这一类启蒙话语。但极具吊诡意味的是,张承志在这部作品中的叙述焦点,却并不是对哲合忍耶教义思想的宣扬,也不是对信仰本身的阐释,而是对哲合忍耶教徒牺牲奉献精神的赞颂。作品中的各色人物,不论是穆宪章、苏四十三,还是其他任何一位信众,都展现出了为信仰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他们为护教和世俗政权所展开的殊死搏斗,构成了作品真正的叙事焦点。换言之,张承志对哲合忍耶教义思想的宣讲,显然远逊于他对信众奉献精神的赞颂。这意味着《心灵史》其实仍是一部以人为叙事核心的作品。张承志对底层人民道德力量的膜拜,对苦难和牺牲精神的推崇,无一不让《黑骏马》式的道德理想复现于今日。因此也可以说,像《心灵史》这般以道德自圣为叙事本位的神性写作,同样接续了此前启蒙叙事的道德神话。
综上所述,自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叙事从反神话叙事的启蒙叙事起步,在经历了新神话叙事的发展后,至90年代终于形成了世俗化叙事、启蒙叙事与神性写作三足鼎立的叙事格局。而在此话语谱系内,各类叙事话语之间的彼此融合与权力博弈,也令当代小说的发展流变从此愈发显得绚丽多姿。
[1]刘勰.文心雕龙·时序[M].
[2][7]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224.
[3]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初版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
[4]叶立文.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J].天津社会科学,2004(6).
[5]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6]叶立文.颠覆历史理性——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J].小说评论,2004(4).
[8]史铁生.病隙碎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
From the Mythic Narration to Divinity Writing——On the discourse development of novels’narration since the 1980's
Ye Li-wen You Ying-ya
(College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The discours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novels’narration started 17 years ago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mythic narration by enlightening narration,but enlightening narration,the anti-mythic narrative discourse,later evolved into a new mythic narration with moral myths as its core.In early 1990’s,with the temporary science of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contemporary novels’narration turned to secularized narration highlighting desires,and secularized narration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contemporary novels.But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the result of the competition of secularized narration and enlightening narra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divinity writing in the late 1990’s.From the old mythic narration to a new mythic narrative,then to secularized narration to the last,divinity writing,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novels’narrative discourse has already construct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mythic narration;enlightening narration;secularized narration;divinity writing
I106.4
A
1005-5738(2014)04-158-08
[责任编辑:周晓艳]
2014-06-18
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史铁生评传》”(项目号:11CZW066),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的文学批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号:13&ZD128)阶段性成果。
叶立文,男,汉族,甘肃陇南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