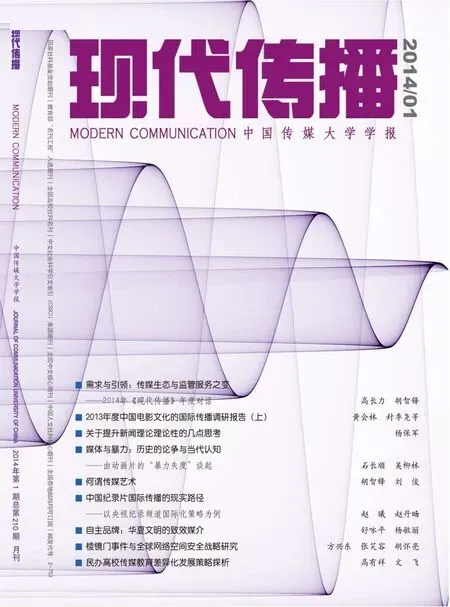国产动画高等教育现状及其变革视角*
■ 张启忠
美、日动画电影借助文化工业,吸纳整合东西方文化质素后在世界市场强劲流转。这种视觉文化某种程度上侵蚀和驯服中国的日常文化。①对此,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大力扶持具有文化生产力属性的动漫产业。但中国动漫业多年呈现“产量剧增、精品难产”的态势。不仅如此,教育部阳光高考网站2010年10月27日将高校动画专业列为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的20个“红牌”专业之一。本文着眼于作为文化生产力的动画产业期求,以美日动画电影的成功设计为例,对国内动画高等教育的变革予以探询。
一、现状:文化符号的贴附
美国的《功夫熊猫1》 (2008年)、《花木兰》 (2009年)、《功夫熊猫2》(2011年)曾引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热议。自《宝莲灯》(1999年)始,民族文化在国产动画电影中仅为“贴附”状态,即多借用美日动画电影的美术技法,而角色造型与性格缺乏中国文化的骨感。而且,当前饱受诟病的国产动画高等教育现状也有“贴附”的问题。
其一,重技术而缺乏文化底蕴。漫画家、动画艺术家张光宇的漫画魅力来自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如古典文学、书法、舞台美术、电影美术、现代绘画、墨西哥壁画、前苏联版画等。他虽然受过墨西哥弗珂罗皮斯的一些影响,但他民族艺术根基深厚,很快就“民族化”了。②而国内一些高校动画专业却偏于动画技术的传递,很少设置诸如艺术史 (中外美术史、建筑史、音乐史、雕塑史等)、中西方文学史、民俗学、宗教学等,至于纺织、印染、天文、机械等边缘学科更无从谈及。缺乏对动画专业学生的“美术”思维进行“震碎”与型塑功能的文化学养,仅倾力于动画技术的训练,虽有助于学生使造型“动起来”,但无法深入解决“如何动”“为什么动”的深层命理和问题。
其二,动画教育中美术环节的思维剥离。一些高校动画专业的美术环节多以西方写实造型技法课程为主。其实,这种理念在新中国美术教育中留有历史缺憾。自“五·四”以来,中国画坛就萌生了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潮。保守主义无视历史发展,只临摹古人画稿与技法;虚无主义视水墨技法相对三维透视而言为不科学,认为中国画无法表现迅速变革的新生活。1954年爆发了关于中国画问题的大讨论。20世纪50、60年代的美术教育开始仿照苏联美术教育体系,而倡导一切美术以写实造型为主,但这戕害了以中国书法为根基的中国水墨画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之后进行了求索,例如中国水墨人物画方面,以中国画院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卢沉的《清明》,以及二人合作的《矿工图》系列作品表明,中国水墨人物画在消化西方艺术思潮的同时,采用移植拼贴、多空间平面组合等手法探索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空间。这是在徐悲鸿、蒋兆和等先辈开拓的水墨人物画现代化基础上的嬗变。
但当今动画教育中的美术环节延续着中国美术教育曾经的错位,只是形态由“排挤”转为单一或并列。那么,未来国产动画业者,在造型思维上如何形成“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知识框架并活络于鲜活灵异的造型设计呢?
其三,传统艺术样式训练的单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为代表的艺术家,弘扬了张光宇等创见的“大美术”概念,即打破传统的“纯美术”与工艺美术、装饰美术、工业美术之间的隔膜,形成从“道”向“技”的转化与应用的向度,意在美术门类内各子类之间的借鉴与激活。
相形之下,当前国内高等动画教育中的美术环节,多传递书画或民间美术等。中国美术历史演进包括中国早期先民的彩陶玉雕、三代的青铜鼎彝、战国的漆器、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南北朝隋唐的佛教造像,以及绘画、书法等;工艺美术类别有中国有雕镌、编扎、髹饰、陶埏、琢玉、画绘、作金、绣织等。上述各个类别、各个系统在不同的时空、地域中孕育了不同的体裁、样式与流派,形成了不同的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艺术样式都存在新陈代谢的层积与变异。它们与中国传统艺术样式包括神话传说、民谣、歌舞、京剧以及相关的地方戏剧、民乐、皮影、园林建筑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和理念。对这些艺术样式的学习,可以增进动画创作者想象元素与审美认知的感知与陶铸,进而形成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血脉相通的创意源泉。
其四,缺乏博物学的视野。2010年底,美国电影《阿凡达》登陆中国院线时,曾引发了该片应归于科幻电影还是动画电影的争议。其实,议论本身就是中国当前高中“文理分科”思维的体现。该片中圣母之树的周围,巨大拱形的、宛若天桥的岩石石头桥是按照磁力线分布的;巨大山石漂浮于空的原因与磁悬浮列车原理相通,不受磁场作用的水依然形成飞流直下的瀑布;作为潘多拉空中的霸主,“伊克兰”和“魅影”都形似人们想象中的“飞龙”,与今天生物界中悬栖于房梁的、用类似“翼膜”的结构飞行的蝙蝠相似。可见,卡梅隆设计的潘多拉星球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科学知识之后的模拟,这是该片赢得世界美誉的内在功力。
而国内高中文理分科致使动画学子缺乏天文、地理、生物、植物、文史等知识。当前高校的动画教育,对自然学科更是荒疏。
上述的断裂与空白致使未来的动画业者仅能剪贴民族文化的碎片,遑论深入理解碎片的衍生场域及文化生命语义。
二、变革:文化符号的复活与再生
现在国内动画界的部分业者,不仅没有深入生活来体悟民间艺术符号,甚至没有观摩博物馆中作品残留的音韵。这是当前国内动画造型缺乏生机活力的症结之一。而反观日本动画电影角色设计,在引用日本传统文化符号同时,将物哀、茶道、俳句等文化艺术生活的各种景观,有机地融汇在作品中,形成了融合日本文化肌理与跃动的造型设计。且日本动画电影还运用了当下的民俗。如其中的主人公报恩情结设计与当下的“针供养”习俗有关。即每年的年终,类似缝纫协会之类的组织,会把一年当中用过的、折断的残针收集后送到神社供奉后再销毁,以感谢一枚细细缝纫针一年的辛劳。这种感恩万物福报的情怀,与日本人“虽饱犹带三分饥”的爱惜粮食的习惯一脉相承。日本动画电影往往来自创作者自己的文化体验、民俗思考,并撷取各种鲜活的艺术形式和生活场景来表达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无生命的拼贴。
首先,历史图景中的细节与真实。宫崎骏在评述剧本《合战》时,认为:“无论是描绘长筱之战,或是真田与伊达在大阪之阵的对战——子弹射向没有配枪的真田军,将士们的铠甲发出声响,士兵用同胞的尸体来当做盾牌——这是多么逼真的情景。虽然它不像冲锋的重骑队那样发出隆隆的马蹄声,但战况的激烈却在眼前。”③此场景在宫崎骏《风之谷》的战争场景中做了部分动画的迁用。当然,让腰中的剑晃几下,就做了很大的工作量,要描绘甲胄的威严感,更是剧组力所不逮了。但是,正是因为史料才激发了宫崎骏对战斗场景的勾画与设计。而一些院校动画专业并未认识到历史文化对于动画设计的价值。其实,历史描述的社会生活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其次,文化符号的历史生存。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剪纸实物,是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址北朝墓葬中出土的以动物、花卉和几何图形为题材的团花剪纸。其功能之一就是祭奠鬼神、慰藉亡灵。南北朝以后,出现了立春、人日节等节日剪纸,用于祭祀招魂的风俗盛行一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剪纸的祭祀功能逐渐让位于日常生活的装饰以至变成世俗化的商品。到了近代,剪纸成为寻常百姓尤其是农家妇女谋生、装饰生活的一种手段。
可见,动画作者构思动画角色时,若仅是一些片段式样的“知”和臆想的“识”作为角色生命活力的源泉,怎能期求观众的赞许呢?在视觉文化洪流滚滚的全球化语境中,以漂浮着传统文化碎絮的动画造型,却自诩张扬着民族文化,必然言过其实。
在动画教育中提倡文化符号的复活,目的在于拓深文化符号存活其中的历史、民俗、社会、自然的文化生态,探求其生命活力的源泉,这是动画设计的起点。在创意阶段,则提倡文化符号的再生。
作为“软实力”文化产业对世界市场的开拓,致使动画电影不可能是单一的民族文化,而是融合世界各国文化元素之后的本土文化的再生与传播。
如日本的《幽灵公主》中的黑帽子夫人形象是集宫泽贤治的“土神”、民俗学中的“金屋子神”和日耳曼的“女神布里可特”这三神为一体。在《风之谷》中,角色设计、情节编织也演绎了阴阳五行思想。以这种源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维作为角色肌理,赢得了国人的亲近;同时,这种原始思维色彩的思想以玄理的神秘而博得的西方观的关注。
同样,美国动画电影也依托自身哲理融合了西方文化元素。如《冰河世纪》 《怪物史莱克1》等出现了驴子形象,有西方民俗意味。历史上在教堂管辖区附近举行的“驴的盛宴节”仪式,本是庆祝圣母玛利亚和婴儿耶稣一起来到埃及这件事,而该故事主角却是一只驴,周围滑稽地表演的人们用驴叫伴唱。可见,具有悠远历史文化丑角的驴子,在当今动画喜剧中得以复活。
在同东方文化的转换上,美国动画电影也注意到了形神的转化。例如《功夫熊猫1》中采用了很多中国元素,诸如形意拳等。在自然山水方面,仿制了丽江的小桥等。这些还只是表层文化符号的运用,真正激活这些元素的是知天命、铁肩担道义、父慈子孝等中国文化理念。再者,《怪物史莱克》中史莱克的造型一般认为是美国动画设计师的独造,其实,该角色造型与中国墓葬所生产的“明器”——唐墓地三彩神王的造型很相似,也许这种吻合具有偶然性,但中国观众因不知其与中国古代墓葬明器形象相近而没有禁忌,反而因其暗含的审美意味而受到欢迎。鉴于此,国内的动画教育在传递民族文化符号的同时,更应该传递文化符号的内在哲学命理。
当前的动画高等教育除了传递动画技术,更应该传递动画造型所需的文化符号的历史生存境遇,及其内在哲理与生命理念,建构一个文化形神流通“自养”知识架构。以此类推,立足于民族文化再生思维的国产动画电影,才能真正复兴有日。
注释:
① [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消解文化》,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② 张仃:《它山画语》,李兆忠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③ [日]宫崎骏:《出发点 (1979——1996)》,台湾东贩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