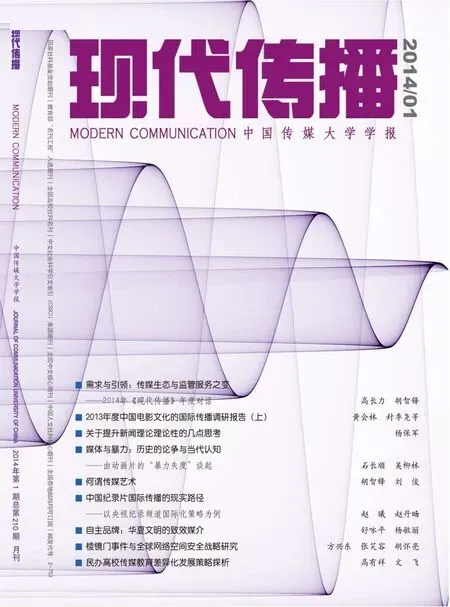评价与被评价:当下学术期刊学术功能异化的一个视角
■ 陈 颖
对学术期刊而言,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学术功能,即为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发表的平台,犹如汽车最重要的功能是运输人或货物一样,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否认,在当今中国,社科类学术期刊多少附带着政治宣传的功能,但这不是学术期刊的本体功能,因此本文对此不多加讨论。这里,笔者关注的是当下中国学术期刊界正在蔓延的一种“病态”现象,即为数不少的学术期刊似乎正不由自主地被一种非学术或超学术的评价功能搅得六神无主,乃至神经错乱,导致它们或高高在上自我膨胀,或自轻自贱、唯利是图。学术期刊于“癫狂”状态的不是什么超凡的秘密武器,而是学界所熟知的所谓“评价”与“被评价”之常规武器。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评价他人或被他人评价,学术期刊同样如此。当其作为评价主体的时候,其刊发或不刊发某篇文章,实际上就带有评价学术的功能;而当它作为评价客体时,其水平质量又无可避免要被读者所评价,这种评价和被评价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本文之所以要拿学术期刊的评价和被评价说事,乃因为近20多年来,我国学术期刊源自天然的学术评价和被评价已严重地人为扭曲,到了必须深刻反思回归自然的时候。
一、学术传播与学术评价:学术期刊功能透视
众所周知,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传播需要借助一定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之一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因此,学术期刊首先是一种传播学术的媒体,具有学术传播的功能。其次,面对数量浩瀚、鱼龙混杂的学术或伪学术成果,学术期刊选择传播内容本身便是一种学术价值判断的过程,即学术评价。学术传播与学术评价因此构成了学术期刊的两大基本功能。从学术传播的功能看,传统纸质媒介的学术期刊,无论传播形式、传播对象,还是传播渠道,基本大同小异,并无本质区别。而从学术评价功能看,则彼此间形式、过程和结果均差异巨大。如果我们把前者视为学术期刊的显功能,则后者便可以视为学术期刊的潜功能。所谓“显”,即浮在面上,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们通过阅读纸本学术刊物,了解其所刊载的学术研究内容,从而实现了学术传播的目的,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学术期刊的这种显在功能,堪称为与生俱来的基本功能,也是其主要价值所在。然而,当下中国的学术期刊,由于其学术传播功能已经被太多非学术的功利目的所扭曲,以至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于学术期刊的所谓体制改革举措亦从这种被扭曲的价值判断出发,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忧虑。因此,我们需要从源头上厘清学术研究与学术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从本质上说,学术研究是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现象的超功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社会进步和生活幸福。学术研究成果应该造福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因此,学术研究从本源意义上是一种无功利或超功利的高尚的创造性活动。学术期刊被赋予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使命,是整个学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既然学术研究是无功利或超功利的,那么,传播学术当然不应有功利。所谓“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学术的优良传统,从四书五经到宋明理学,浩瀚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造就了一个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度,其价值和影响难以估量。但这些学术思想的开创者却大多并未从中谋到多少功利,有的甚至穷困潦倒。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多年,学术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被种种政治禁区所困扰,也被加载了许多政治目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几近空白。学者们被体制严重钳制,发表了一些迎合极“左”政治的违心之论,他们多为生存和环境所迫,实为无奈之举。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功利考量,那么,今天中国的功利学术大约由此开始滥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事业通过拨乱反正逐渐走向正常化轨道,但体制对于学术的规划和管理却有增无减,只是改变了过去单纯从政治和思想内容上强加限制的落后方式,转而通过建立各种名目的基金项目、人才计划、建设工程等引导各类学术研究朝既定的国策方针开展,加上政府有意无意通过行政化手段采取量化方式对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等进行科研业绩考核,并据此从政策、经费、人员等方面影响被考核对象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或被迫无奈或主动迎合,对各类专业人员采取量化考核办法,据此决定人员的升迁去留。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带有极强功利色彩的量化考核办法对学术研究带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其对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戕害更甚。试想,当充满创造精神且需耐住寂寞潜心面壁的学术研究成为在规定期限内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时,能有多少富有创新价值的成果问世。更不用说一些“学阀”俨然已经成为学术包工头,其承包下的“学术课题”或“学术工程”经过层层分包,最终能有多少“干货”问世令人怀疑。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如果处于道德高地、代表社会良心的学者都无视良知耐不住寂寞一窝蜂奔着功利学术而去,这个社会肌体能够健康吗?置身于如此功利化的学术环境中,以传播学术为使命的学术期刊怎能不受侵蚀?
大量经费不菲的基金课题制造出来的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急于寻找发表渠道以完成科研考核任务,学术期刊就是他们绕不过的一道坎。于是,一些学术期刊抱着分一杯羹的心理,以出卖版面换取眼前实惠,久而久之蔓延开来,竟成为今天学术期刊界的一种潜规则。固然,这种表面上看似合情合理或曰符合市场化利益交换原则的学术传播潜规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学术期刊的学术传播功能,但是它却或多或少损害了学术期刊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即学术评价功能。在纸媒仍居学术期刊主体的今天,任何一家学术刊物的版面容量都是有限的,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发表,其决定权在刊物。换言之,学术期刊只有通过科学和公正的学术评价,才能实现向社会传播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的使命。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不少学术期刊抗不住诱惑,早已趟入功利学术的浑水中心安理得地“摸鱼”了,使其失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功能。我不知道,大量为“学俗”服务的学术期刊还能有多少学术含金量,对学术的进步又能起多少促进作用?最悲哀的是,由于一些学术期刊的唯利是图让社会上那些伪学术期刊钻了空子——眼看学术期刊通过收取版面费就能一本万利,许多非学术和伪学术期刊纷纷“越界”行动,干起收费刊发论文的勾当,使本已声名不佳的学术和学术期刊界更加雪上加霜。近几年,媒体上充斥大量“学术垃圾”论,其批评锋芒直指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界,虽然其中不无误解和偏见,但确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学术研究及其传播急功近利的现状,这应当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警醒。
二、学术期刊的非学术追求:缘于被评价
应当说,无论评价还是被评价都是一种对人或事必要的督促,是一个机制健全的社会里必不可少的激励手段。因此,评价和被评价作为一种选优汰劣的手段无可厚非。然而,基于功利目的且政出多头、标准混乱的众多评价机构的存在并非好事。当下中国学术期刊面对的评价机构之多、受影响之大,已经让学术精神、学术勇气乃至学术道德濒临崩溃。回首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学术期刊发展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用各种量化指标来评价学术期刊及其所承载的学术内容。本来,一家学术期刊的社会声誉、学术影响力是靠读者和业内同行、专家的社会评价自然形成的。这种自然形成的学术期刊评价不一定十分准确,但至少不会扰乱学术期刊健全的学术神经,更不至于使它们纷纷陷入畸形的排行榜中而倍感疲惫。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更好服务读者,先后参照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的“文献离散定律”和美国著名文献学家加菲尔德的“引文分析理论”,尝试对中国的学术期刊进行核心和非核心排列的时候,当时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学术期刊对此还了解不多,且由于当时功利学术处于萌芽状态,科研“GDP”崇拜也未抬头,因此,学术期刊的竞争还处于相对自然和良性的状态,人们对于核心期刊的排行榜并不十分在乎。随后,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先后跟进,尤其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中文社科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的异军突起,武汉大学中国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的“凑热闹”,逐渐把核心期刊概念炒热,尽管这些以图书馆为基地的各家评价中心纷纷声明他们的核心期刊排行主要是为读者订阅期刊而服务,并不能作为学术期刊质量水平的评价依据,但当众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纷纷把这些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与教师科研人员的职称晋升、科研奖励、课题申请以及职级待遇相挂钩的时候,核心期刊的功能和价值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人们开始回过神来,逐渐意识到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机构和个人利益攸关的时候,各种期刊评价机构已经水到渠成织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大网,所有学术期刊都被这张无形的大网罩住,无以挣脱。
固然,我们不能否认现今被遴选进入上述各种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学术刊物,绝大多数是高水平高质量的,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由于评价指标的不完善不科学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不完全适用,使得核心期刊遴选的负面效应逐渐浮出水面,一些期刊为提高影响因子挤进核心期刊行列,无视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在被引指标、下载频次等方面搞小动作,拉帮结盟互引互惠。一些期刊更是在选稿、用稿和编辑规范等方面迎合核心期刊评选的需要而逐渐丧失了学术个性和学术活力。
最可怜的是,那些出生“低贱”的学术刊物(如地方高校学报)由于“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即使刊物主编、编辑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与核心期刊结缘。又由于“箭垛效应”的作用,一家学术期刊一旦入榜核心或来源之列,则稿源充沛,主编和编辑可以在数量浩瀚的来稿中精挑细选,作者趋之若鹜,编者高枕无忧;而众多非核心期刊则优质稿源日渐枯竭,陷入了“好米难求”甚至“无米可炊”的恶性循环中。许多学术刊物既难圆“核心梦”,索性“破罐破摔”,或降格刊稿以求勉强生存,或出卖版面谋取眼前实利。笔者不知道,这种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在稿源、吸引作者和读者、学术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两极分化现象,对学术期刊的竞争和学术生态的发展究竟是好事还是孬事?也许只有时间能为我们答疑解惑。
三、数字化和集约化:学术期刊评价的因应之道
虽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传播的良好平台将依然保持刊自为阵的总体格局,因此,各家学术期刊还免不了被期刊评价机构呼来唤去,但是,网络化、数字化的日新月异必将深刻改变当下学术期刊的个体面貌和整体命运,也必然对期刊评价制度的科学完善不断提出挑战。
吊诡的是,近20多年,以核心期刊为主要标志的学术期刊评价制度之所以盛行,正是网络化、数字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电脑的计算固然迅速精确,拿它来判断学术期刊的传播范围尚可,而机械地搬用它来评判具有一定模糊性思辨性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水平质量,似乎不大靠谱。在我看来,人文社科类文章的引文、注释等其实很多时候不能说明文章的水平质量,同行学者专家的阅读和直观判断倒更准确和令人信服。
如果我们对被引和下载频次高的文章细加考察,会发现其大体不外三种情况:一是所谓热门话题或曰学术前沿问题,二是学术水平领先的创新观点,三是学术观点错误遭学界挞伐的。由于学科差异,有些学术前沿问题在一定学科范围内颇受重视,但它的绝对影响力可能不如另一些热门的学科,如果单凭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指标来判定,则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肯定远远不如政治、经济、教育、法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所以,为了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近年来,一些综合类社科期刊有意无意地扬社会科学论文抑人文学科论文,加剧了文史哲等传统学科走向边缘的趋势。这里笔者无意全盘否定以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遴选为主要标志的现行学术期刊评价制度,毕竟,它比完全人为操控的转载、摘登、评奖等评价手段相对靠谱些。在学术道德水准严重下滑、学术功利化状态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那些完全靠人为因素起作用的评价方法,其科学性和公正性不免使人怀疑。
归根结底,要让学术期刊的评价与被评价回归学术,终究要寄希望于当今中国社会整体学术评价制度早日摆脱急功近利的行政化窠臼。然而,前景似乎未可乐观,功利化的学术不但未见收敛,反倒有强化的趋势。君不见,在核心期刊和国家期刊奖之外,新近,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评选,又把我们本已脆弱的敏感神经再次撩拨起来——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诱人“利益”啊,谁不向往?
其实,学界对于现行期刊评价制度的质疑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炮声隆隆,但批评者多为被核心期刊边缘化的所谓“第三世界”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辑们。许多大刊名刊的主编、编辑并未对此感到不适,有的甚至还撰文为核心期刊的合理性辩护。笔者虽为一家核心期刊的主编,算得上是现行期刊评价制度的“受益者”,但在十多年前即已对核心期刊评选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①。不过,话说回来,在没有更好的期刊评价制度产生之前,现行期刊评价方法尽管漏洞百出,但多少可以弥补纯定性评价的缺憾。作为一种民间性的评价,所谓核心期刊排行榜本可以置之不理,然而众多机构却以它作为学术评判的重要依据,这就使问题变得严峻和复杂起来。既然现行期刊评价制度的存在非学术期刊界所能左右,则我们只有正视现实,另辟蹊径,寻找应对良策。笔者以为,学术期刊界应当充分利用网络化、数字化的手段,通过集约化途径,避免因小而全的分散“经营”被“各个击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将高校学报分散的内容以专业化方式重组,借助中国知网这一目前国内最大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以集约化数字化的整体形象二度面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评价机构对各刊的单独评价,也有益于克服纸质期刊传播渠道受限的先天不足,使优秀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利用,这是克服学术期刊学术功能异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当个体的纸本学术期刊逐渐萎缩淡出,数字化集约化的期刊集群日益强大的时候,也意味着所谓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存在意义在逐渐丧失。
当下,特别值得业界注意的是,传统的纸媒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传播平台的权威性正面临着数字化的严峻挑战,一旦纯数字化学术传播平台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认同,学术论文发表渠道的多元化成为现实,那么,传统小作坊式经营的学术期刊必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行的学术评价制度将面临重大变革。这一天的到来恐怕为时不远。这已逸出本文的论述主题,恕不展开。
注释:
① 参见陈颖:《谁来评选“核心期刊”》,《中国出版》,2001年第6期;陈颖:《“核心期刊”现象透视》,《中国新闻出版报》,2001年4月27日 (第3版);陈颖:《现象扫描:学术期刊等级划分中的谬误》,《出版广场》,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