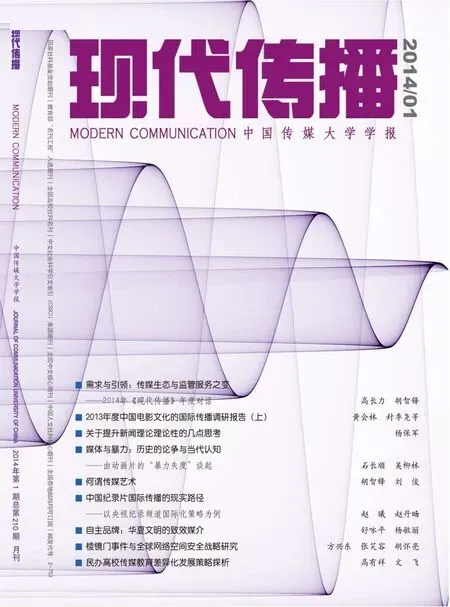论当代媒介环境中的“城管之殇”
■ 彭华新
在当代大众媒介中,“城管”一词的含义与“城市管理”渐行渐远,经过众多城管事件的洗礼与媒介话语的洗劫,“城管”包含了太多的负面情绪,“网骂”之声不绝于耳。“城管”还是那个“城管”,缘何与传统媒介时代相较,境遇如此不堪,用媒介环境学的话语来说, “鱼”没有变,是“鱼”周边的“水”发生了改变。昔日城管遇到今天的媒体,环境的不适制造出了一个喧闹的空间。当代媒介环境,指的是以手机、网络、高清视频、无线SNG等当代技术为物质基础,以随地可及的记录、随时可触的传播、随处可即的信息为特征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氛围。
一、媒介事件:城管“乱象”的现场直播
1.关于城管的“媒介事件”生成路径
“媒介事件”是历史的现场直播,它让人们不断在媒介真实、符号真实与客观真实三者之间徘徊。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特别是公民记者的普遍出现以后,“媒介事件”已经超出了戴扬和卡茨在90年代对其作出的界定:“媒介事件都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①随着网络社会的演绎,世界已经分裂为“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两个空间,在“想象世界”空间,人们能动性地推动事件朝其愿望、担忧或恐惧的方向发展。2007年,卡茨也承认了媒介事件关注重心的转移:“仪式性的媒介事件其重要性似乎在减弱,甚至频率也在降低,而破坏性事件的现场直播,比如灾难、恐怖和战争,则进入中央舞台。”②关注重心的偏移,媒介事件的生成路径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变更,即由“新闻策划→执行者与媒体合谋→伪事件 (pseudo-events)”转变为“自然发生的事件(spontaneous-events)→公民记者偶遇→网络发酵→传统媒体追问→当事者回应”,前者注重一致性、仪式性,从而制造出一道道绮丽的“媒介奇观”(media spectacle),后者注重创伤性和冲突性,因而润含更多的情节围观、文化消费和社会反思。
纵观2013年以来发生的与城管有关的“媒介事件”,经过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共同发酵,有三件大事是无法绕开的:1.广州城管围殴女贩。2013年3月7日,新浪微博、天涯论坛等新媒体传播平台疯传一则消息:广州市海珠区城管队员与女性小贩发生冲突,从跟帖的图片中可以看到,虎背熊腰的城管队员手掐女性小贩的脖子,旁边站着女贩的三岁女儿正在嚎啕大哭。最后的一张图片更加煽情:女贩被反剪双手蹲在执法车边,女儿抱着妈妈的头,图片配的字幕是:“孩子,对不起,妈妈这次不能抱你”。2.延安城管跳踩市民头部。2013年6月3日,网上公开的一段视频显示:一群身着城管制服的人群围殴一名男子,男子被击中倒地之后,城管仍未善罢甘休,其中一人双腿跃起,腾空踩向男子头部。3.临武城管被质疑秤砣砸死瓜农。2013年7月17日,临武县瓜农邓正加在贩卖西瓜时与城管发生冲突,网上热议其死因可能为秤砣击中头部,配图是邓正加倒在血泊之中。
在生成路径上,这几起事件的关节点几乎一致:1.均起因于城管与小贩 (市民)的冲突,非刻意策划或有意安排,因此属于自然发生。2.均由公民记者记录以及在网上发布,这些公民记者不仅仅具有拍摄工具和网络发布能力,而且在文字、图片和视频的编辑中,能掌握导向性,在叙事情节和议程设置中,将舆论高地选择性地向小贩 (市民)倾斜。比如在广州城管手掐小贩一系列图片中,特意隐去小贩用番石榴砸城管情节;在延安城管跳踩市民的视频中,刻意突出跳起落下这一极具冲击力的镜头;在临武瓜农案例的照片中,将躺在血泊中的邓正加照片与秤砣照片并列,产生蒙太奇逻辑效果。3.均经过网络发酵过程。与电视时代的媒介事件不同,当代媒介环境下媒介事件最大的特点即受众的参与性,受众以媒介信息为前提,依据自身知识背景和社会经验,参与对事件的是非判断、社会评价、发展预测等,这些行为直接影响事件的发展轨迹,而在电视时代的媒介事件中,围观者只能赞叹仪式的威严,以及沉醉于事件的协同性、规模性和权威性所带来的愉悦感之中。4.均有传统媒体的随后介入,加速事件的发展进程。广州城管与女贩冲突发生后,这一事件成为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盛宴,延安城管跳踩市民事件更是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的视野,事情发生后半个月,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延安城管打人事件调查》,追叙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追问了城管功能与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城管与瓜农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媒体涌入邓正加家中,深入挖掘事件的各种因素。
2.“媒介事件”衍生下的城管“乱象”
近几年城管成为网络新闻的热门话题,只要是涉及城管的事件,几天之内即可孵化成为“媒介事件”,而“媒介事件”的完成并没有给城管困境画上句号,而是衍生出一系列后遗症。综合分析各类城管案例,后遗症的衍生过程基本遵循这一规律:“媒介事件 (源头)→舆论焦点 (发酵)→社会公敌 (身份)→四面楚歌 (境遇)”。后遗症的衍生过程,既是城管“乱象”的描述过程,也是城管“乱象”的阐释过程,呈现了“乱象”的内部根源与外部作用力的关系。
当代媒介环境下,现场直播的记录者和传播者无处不在,当一个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之后,媒介的嗜血欲望又在诱使它寻找新的关于城管的媒介事件,继续着尚有余温的媒介狂欢和文化消费,从而使得“城管话题”形成一个独特的舆论矩阵,绵延不断地供人消遣。也就是说,此时的记录者是有偏向的,启动“议程设置”功能,在海量的社会信息中,专注于城管与小贩的“战争”,使其形成长期的舆论焦点,在网络平台展开叙事的开场白经常为“又是城管”“又见城管打人”等等,以此勾起人们的围观欲。聚焦城管的消息从未在网络上消失,几乎每一条消息都能引发大量的网络唾沫和网络暴力,即使实际的社会危害并不大的事件也被推至舆论浪尖,如重庆城管躺执法车中请人擦鞋,武汉城管下班时间“摆地摊”。
社会聚焦给城管形塑了一种无法自辩的身份——公敌。虽然在媒介视野中,城管执法与社会存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小贩”身上,但此时“小贩”的身份认同已经在网络叙事过程中符号化和形象化,他的语义被无限量扩大,乃至于在潜意识中代表了公民权利,成为正义的化身,而与“小贩”冲突的“城管”,无疑被推至公众对立面。在这种境遇下,即使城管遭遇不公平,仍然难以取得谅解,如2013年3月广州天河区一名城管队员遭小贩连砍七刀,社会舆论却倾向于同情小贩,而对受伤城管的评论多为“活该”。传统媒体对这起事件的追踪力度和报道热度也完全比不上“城管打人” “城管群殴小贩”等血性事件。
3.“战场”的迁徙:城管们难以回避的媒介之役
至此,城管与小贩的“战争”,已经演化成为城管与媒介的“战争”。在传统媒介环境中,城管作为一种权力机构而存在,它们与新闻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敌对状态是被限定于一定的框架之内的,这一框架有力地支持了权力机构对媒介的控制和疏导,在这一大背景下,媒介看似是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其实是建构现实,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通过对各种文化形式和受众解码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媒介依靠生产出凝结社会的霸权符码而发挥作用。在法兰克福学派视野中亦是如此,无论是“媒介的被控制”,还是“媒介的控制”,皆是媒介对权力的屈服。“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媒介的控制,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前者是国家对媒介的控制,后者是国家通过媒介对社会的控制。”③
然而,传统的媒介身份已经随着技术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当代媒介现场直播的随意性取代了传统媒介现场直播的适时性,从而在结构上解放了媒介对权力的附庸,消解了权力赋予的解释霸权,也颠覆了其解释世界的话语方式。正是这一语境的变更,为城管与媒介布置了“战场”,昔日权力对媒介的征服与媒介对权力的谄媚已日渐稀薄。城管与当代媒介的“战争”,并非与媒介的控制者的“战争”,而是与媒介中的表达者的“战争”,表达者的分散化、随性化和多元化,注定了城管是在面对一场不可回避,而又难以战胜之役。无怪乎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指责时,透露出了对这场无休止之战的焦躁和厌恶:“我们强力管理,被指责暴力,我们采取眼神、鲜花、体验执法,被质疑作秀,到底要我们怎么做。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我们奖励1万元。”④
二、媒介环境:城管拟像中的适者生存
1992年,媒介环境学的第二代传人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直呼“狼来了”,忧心忡忡于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对现实的危害。对于今天的城管来说,“狼”真的来了,他们之所以悸惧当代媒介这匹“狼”,并非缘于它制造事端,而在于它的四处吟唱。
1.现实与想象:拟态环境下的公共形象
众所周知,城管的主要职能在于实施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在现实生活中,城管也主要是履行这一看似光鲜,而且附着些许权力的职责。但是,在当代媒介营造的舆论氛围中,城管却有着不堪的公共形象,比如暴力使用者、临时工等等。此处暂且不对城管行为和小贩行为进行道德评判,仅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公平分析城管在公众意见中的公共形象。
公众对城管的认知,总是在“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中纠结,在“现实世界”中需要城管,比如遇到乱摆卖导致的脏乱差、噪音污染和交通堵塞,他们向城管投诉;而当城管执法与小贩生存二者产生矛盾之时,他们又走向“想象世界”中声援小贩,谴责城管,把自己想象成为正义的护卫者,而城管则成为十恶难赦的撒旦。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了媒介在介入认知过程之后,引发了公众舆论的两种分裂,第一种是公开的、庄严的,第二种是私下的、人性的。这种分裂的直接后果即产生“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对立。现实的需要和想象的尊严,正是拟态环境存在的合理性,对城管的成见,也发端于此。“问题出在成见的性质和我们运用成见时的那种轻信。而这些东西最终要取决于构成我们生活哲学的各种样板。如果我们的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某种法则去运行,那我们就很可能会喋喋不休地根据我们的法则去描绘世界。”⑤长期对暴力突发事件的传播,遮蔽城市管理中的现实问题,给城管的公共形象制造了刻板印象,“刻板形象通常是指在掌握有限的信息的情况下,对某个群体的人进行形象或概念上的标准化。”⑥公众认知从“现实世界”偏向于“想象世界”,摒弃具体的问题讨论,而倾向于抽象的道德评判,使得整个公众舆论进入一种神话叙事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城管的“刻板印象”虽然起源于公众的精神乌托邦,但并非停留于此,公众反之又将这一成见带回至“现实世界”,作为社会行为的依据。
2.正义与邪恶:受众环境中人文困惑
媒介环境起因于技术,作用于受众。技术本身没有道德判断规则,没有正义与邪恶标准,但技术灌输给受众的信息,却时不时引发人们对正义与邪恶的人文追问。尼尔·波兹曼针对技术与受众的关系,提出了四条人文主义原则:“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损害了我们的道德感和我们向善的能力?”⑦这四条原则看似在发问,实则是在质问。从今天我国情形来看,当代媒介对受众环境的培育,体现在角色蜕变、态度渐变和行为衍变三个方面。
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的角色仅是信息的接收体,极端的如“魔弹论”宣扬:受众如同靶子,对方发出什么信号就接受什么信号。而在当代媒介语境中,受众随时都可以蜕变为信息的发布方,比如城管事件频发的当下,小贩们都自觉配备有摄像功能的手机,遇到城管执法时娴熟完成“录制视频—发布消息—文字评论”这一传播过程。作为受众的小贩在前期信息和经验中已经积累了应对方法,在与自身利益相关时立即启动角色蜕变,变为信息源。公众的积极参与也成为信息源的累加,他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对邪恶的谴责就是对正义的声张。
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在态度上屈从于所谓的权威信息和优势意见。1980年,德国传播学家诺力·纽曼总结出一个舆论规律:“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其中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⑧这一规律被称为“沉默的螺旋”,视为受众接受信息的必然心态,个人对社会孤立的恐惧感,让他们不得不服从于权威和优势信息源。“沉默的螺旋”奏效需三个条件:“1.少数缺乏社会主体意识而又缺乏主见的人,轻易地把媒介意见视为真理……2.媒介在设置议程方面一旦巧妙到难以被人发现其荒谬之处,或者受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就会盲目地追随媒介……3.媒介的意见符合绝大多数受众的价值观、利益和见解,同民意达到一体化,沉默的螺旋开始生效。”⑨然而,在新媒体的意见表达中,优势意见的这三个条件基本很难实现,网络社会从不缺乏有主见的人,知情权也从未离席。在这种境地中,优势与劣势发生了倒置,原本被认为是官方、权威的和具有压倒性的信息源,被散状的、独立的信息接收体分解,匿名的受众不再恐惧孤立与边缘化,“意见倒流”使得原本处于劣势的意见团体逐渐壮大,最终转化为优势,在媒介视野中,正义与邪恶的界线似乎更加清晰。
新媒体技术营造下的当代媒介环境也导致了受众行为的衍变。接收信息的单一行为,转化为围观、戏谑和暴力等多元行为,“沉默的螺旋”不再沉默,参与对事件的舆论营造和态度引导,直接决定了事件的发展轨迹。比如,受众参与的戏谑语言,其实是在解构城管的公共权力与社会功能,“借我三千城管,一周收回钓鱼岛” “拳王泰森在微博上被城管震慑”,城管在此类的幽默语境中既没有对话平台,更无对战平台。至此,受众被卷入了正义与邪恶的无休止追问当中。
3.纵适与拘囿:媒介之水中的这条大鱼
为什么是城管?众多的权力机构中,偏偏城管被卷入舆论漩涡?答案很明显,如果将媒介环境视为水,城管事件的种种秉性皆顺应了这个漩涡的水纹。
当代媒介具有三个偏好:嗜血、抗权和援弱。嗜血体现了冲突本性,抗权彰显了公共追求,援弱则凸出了道德关怀。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正好契合了这三层关系。这些城管事件通过媒介的故事演绎和情节叙事,成为当今一道夺目的视觉盛宴。
冲突本性如前文所说的“媒介事件”转向,从仪式性事件转为创伤性和破坏性事件,城管事件无不与此有关,以强凌弱的肢体暴力所带来的血腥味刺激了人们的感知味蕾;公共追求与整体性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相关,当小贩在媒介事件中成为公众利益与公共权利代言人之时,受众的“义愤填膺”就成为了一种公共追求;道德关怀是当代媒介中民间舆论空间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民间心理的传统性依赖,其具体行为表现为“援弱”。在城管与小贩的“战争”中,小贩虽然占据道德优势,却无疑居于体力弱势,对弱者的声援意味着对生存权的争夺。这种传播行为的叙事魅力在于,它将传说式的社会争端现实化,勾起人们对侠客文化的召唤,在传说世界中,侠客们惩恶扬善、锄暴扶弱,而在当代媒介世界中,一个个网络侠客用独特的方式“行侠仗义”,围观的人们既可津津有味地咀嚼侠义文化,又可津津乐道地传播公共事件。可见,城管在当代媒介之“水”中,只是一尾供人消费之“鱼”,城管事件的暴力倾向和欺弱特征,决定了它与“水”之不适,卷入漩涡,在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之下,城管处处受制,时时拘囿,又怎能纵适酣游?
三、媒介突围:净化环境还是增强抗体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技术对人类传播的解放力度越来越大,城管与媒介之间的“战争”也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处于被动境地的城管无法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如何走出这个漩涡,更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服务,真正实现城市管理的功能,不仅是一个媒介素养的提高过程,更是一个媒介环境的适应过程,存在于暴力、表演和理想三个阶段之中。
1.暴力:城管与媒介环境的对抗之旅
自从21世纪初期民生新闻兴起以来,城管便视媒介为敌,近几年新媒体的全面席卷,更是给城管制造了压顶之势。因此,城管对媒介环境的对抗,有一定的心理基础。目前有两种对抗方式:第一,“抢手机”是城管的典型对抗心理,出于对进入媒介视野的恐惧,以及对社会评价的不自信,因而从传播的起点着手对抗,试图剥夺对方的传播权利。仅以2013年为例,城管“抢手机”案例一直存在于网络话题中。2013年1月15日,河南济源市民路遇城管工作,本打算拍照片夸城管辛苦,不料手机竟被城管队员迅速夺走;6月6日,洛商某技校学生欲拍摄城管没收老人摆摊的水果,招来城管抢手机;7月26日,徐州市民上班路上看到城管打人,拿手机拍照,结果手机被砸,人也挨揍。这种对抗方式让城管身份与媒介环境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状态,本来是为了切断传播源头,最终却又招致了众多非议,“抢的是手机,丢的是形象”“猛如过山之虎,虚若惊弓之鸟”,城管又被推入道德低谷。第二,“配相机”也是城管对抗媒介环境的一种方式,即每次执法过程皆有专职摄像跟踪,看起来似乎是对舆论的参与,对媒介的合作,对环境的顺应,但其根本也是对抗,即争夺对话的主动权和争辩的证据,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城管的选择性拍摄也遭到众多质疑,对城管有利的片段开机,不利的则关机,如此一来,城管摄制的视频无法融入整个媒介环境。
2.表演:城管对媒介环境的妥协尝试
鉴于与媒介的对抗所带来的惨烈教训,城管也曾尝试向媒介妥协,利用媒介对城管的关注,刻意制造媒介话题,比如敬礼执法、围观执法、鲜花执法等等,其原理是将破坏性、创伤性的“媒介事件”回归至仪式话语当中来,戴扬和卡茨在上世纪90年代对“媒介事件”的界定是基于电视时代的媒介理解,认为“媒介事件”必须要经过事先的策划和宣传,而在新媒体盛行的当代媒介环境中,“媒介事件”已发生语义学转向,随时随地的现场直播和招之即来的拥趸围观,足以实现电视时代现场直播的仪式功能,因此可见,城管的表演,亦是一次自讨无趣的媒介尝试。2007年成都城管开展敬礼执法,执法之前先敬礼,但是敬礼并没有带来城管与小贩的和谐,2012年南京城管开始围观执法,众城管不动手只动眼,盯走小贩,亦被斥为冷暴力;2012年武汉城管试行鲜花执法,即在处理完各种违规经营的商户以后,给对方送上一束鲜花,寓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一类温柔执法与前述的对抗执法已是进步,但是,制造此类仪式化的媒介事件却是一种倒退,符合电视时代的“伪事件” (pseudo-events)在网络时代随时被“揭穿”,在电视中,“伪事件”的表述语言是超越真伪的,视觉的刺激和情节的荒诞可能使它比真事件更具吸引力,但在网络中,这一优势随即被散状的受众所消解,不再受到关注,也无法制造宏大、规模化的媒介氛围,“伪事件”只被看作一种表演。
3.理想:城管与媒介环境的协调共存
媒介聚焦的是城管执法权与小贩生存权之间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媒介 (其实是运用媒介进行传播的人)被推至道德制高点,对城管的执法权进行批判,而为小贩的生存权呐喊。因此,如何终结这场战争,让城管回归到社会服务的正常功能中来,唯有抓住道德批判这一节点,在有序的条件下保障小贩等基层民众的生存权才是根本出路,如此一来,当代媒介的三个偏好——嗜血、抗权、援弱——均能生成可供大众消费的媒介事件。以下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2013年7月底,新浪微博上流传着一条同样以“城管与瓜农”为出发点的新闻:《南方农村报》发出微博,长沙望城区瓜农摆摊占道,多次引发交通事故,上级要求取缔,瓜农不肯走,怎么办?一位80后城管多次与领导沟通,最后决定由政府出资,帮瓜农搭棚卖瓜。城管对瓜农们说“叔伯们,进棚里卖瓜吧”。这条微博当天的转发量即超过一万次。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当代媒介并非城管的天敌,而是某些暴力事件契合了当代媒介的嗜好,在当代媒介的酝酿下,这些暴力事件又代表了整个城管形象。邓正加的“秤砣案”已成为全国瞩目的媒介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城管与瓜农”可看作暴力执法的符号,但长沙城管运用“城管与瓜农”这一契机,在媒介之“水”中取得主动权,为城管与媒介建构了协调共进的双向关系。
四、结语
当代媒介现场直播的随意性取代了传统媒介现场直播的适时性,从而颠覆了电视时代“媒介事件”的语义,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城管的媒介事件层出不穷,城管的公共权力的暴力倾向与社会功能的欺弱特征,契合了当代媒介的偏好,城管在此种“水纹”中陷入漩涡,四面楚歌,处处受制。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城管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暴力倾向越来越明显,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实现了社会矫正功能;第二,当代媒介的传播与叙事已为城管构建了难以洗脱的“刻板印象”,然而,当代媒介可以说是城管的劲敌,但不是天敌,城管也并非是天然的社会公敌,城管只有重新理解媒介事件,祛除暴力化、对抗化和表演化,彰显人性关怀,才能适应当代媒介环境,让城管回归至正常的社会服务中来。
注释:
① [美]丹尼尔·戴扬、[美]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② Katz,E.,Liebes,T.,“No More Peace!”:How Disaster,Terror and War Have Upstaged Media Even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
③ 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④ 《武汉城管委抱怨被说作秀悬赏1万征集工作办法》,《新京报》,2013年6月19日。
⑤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4页。
⑥ [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靖、黄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⑦ [美]尼尔·波斯曼著:《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译者前言,第4页。
⑧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1页。
⑨ 刘建明:《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式》,《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