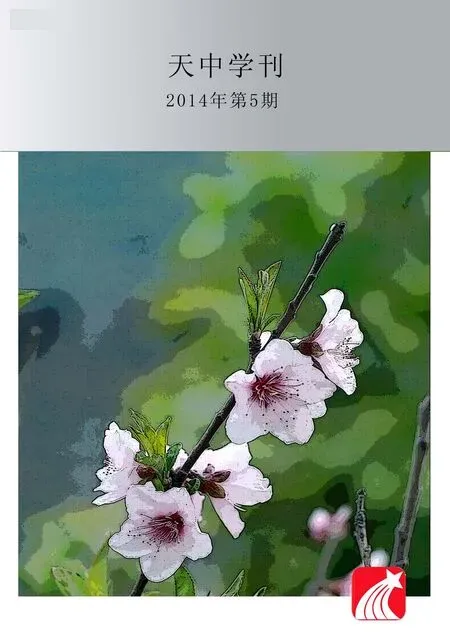论文学作品的意义与时间性
惠帅
论文学作品的意义与时间性
惠帅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对“一件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向来有诸种回答,如作者意图、读者理解、文本自身等,而这些回答显然都有一定的问题。通过分析理解以及对作品的存在及其意义时间性的探析,我们看到了这个文学作品意义的问题本身所具有的不合理性,进而从文学作品意义“到时”角度看到了以上诸种回答的问题所在,进一步揭示了作品意义的时间性。
文学作品;意义;时间性;到时
20世纪80年代初,伊格尔顿曾指出,随着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诞生,使我们接触到一些一直使现代文学理论感到头疼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什么?作者的意图与这一意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关?我们能够希望理解那些在文化上与历史上对我们都很陌生的作品吗?‘客观的’理解是否可能?还是一切理解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处境相联?”[1]65此类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文学理论家,并随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理解”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人们对文学作品意义的不懈探寻逐渐显现出来。海德格尔哲学彰显了“理解”和“意义”的存在论维度,“意义”从根本上说并非外在于人的对象性存在,而是作为已经处于“领会”或“理解”之中的人的固有“姿态”或“关联”。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艺术作品存在的“同时性”与其意义构成的时间性,将作品置于作者、读者、文本之间的间性领域,强调作品意义的不断构成和开放的本性。这些无疑从根基处冲击了“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
一、文学作品意义问题
文学作品意义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意义本身的多层性。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曾指出,意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字的意义、一段语言的意义以及一个文本的意义。文学作品的意义显现于读者的阅读理解过程,而意义的各层面也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且又在不同程度上交织于读者的理解中,影响着文学作品意义的构成。
传统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文学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现实的问题。在这种观念下,文学作品的意义就被理解为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即作者意图。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一般首先考虑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次追寻作者的生平生活经历,最后再通过作品去寻找作者寄寓于作品中的原意。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掺杂作者的原意或受其意图影响,但简单地将文学作品的意义视为作者的意图或本义,无疑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作者的意图或原意是读者无法完全准确把握的。作品一旦完成,随同作品创作产生的与作者相关的由情感活动、时下语境、灵感神思等所构成的创造“场域”,除部分转化为文字留诸纸面以外,其余部分已经不可寻了。读者面对时间的距离、语境的差异和冰冷的文字,很难完全准确追寻到作者的意图或原意,这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无法做到。其次,文学文本本身的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存在差异的。“一个作者要表达某个特定含义的意图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会实现该意图……文本中所存在只是作者实际所达到的效果。”[2]20再次,忽略了读者作为意义构成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仅仅把读者当作一块“白板”或设想为“理想读者”去发现作者的原意,但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何况即便作者面对自己的作品时亦是一个读者。总之,简单地将文学作品的意义视为作者的意图是存在诸多问题的。
与作者意图论相对的是读者中心论,这种理论将作品的解释权授予读者,肯定作品意义在作者创作之后的未完成性和作品本身的不定性与空白状态,认为读者是作品意义的创造者。这种观点在接受美学中有突出表现。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认为,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总处于一种前在的理解和阅读期待之中,文学接受过程就是读者不断建立、修正与再建立期待视野的过程。接受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伊瑟尔则提出,文学语言是一种“描写性语言”,包含许多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正是作品的不确定性和空白使读者能够参与意义的构成。这种批评观念赋予读者充分的自由和创造空间,利于读者积极参与到文本或作者的意义生发对话中。但过于强调读者的地位,将话语权完全交予读者显然容易造成解释的混乱,读者由于自身处境各异会造成无数种的作品意义。另外,这种观点显然也忽视了作者对于作品意义构成的必然影响和作品本身的自律性。
与强调作者与读者作用不同的另一种理论,突出强调文学作品自身的决定意义,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字词、结构、形式及语言等因素。这种观念主要体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叙事学等理论中。它们大体上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将文学视为一种自为、自律的独立存在,认为形式决定包括作品意义在内的整个艺术活动,强调在形式中发现决定作品意义的自在结构。虽然这种将文学作品脱离作者、读者及社会历史的孤立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把一件文学作品的意义完全归于文本本身的探索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意义并不是一个去直观一头洋葱的普遍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个人之间的不断变化着实际往来的问题”[1]59。意义的产生与理解从根基上就离不开人与社会,独立自持文学作品作为某一“物”的现象是存在的,但独立自持、不假外界的作品意义是不存在的,因而作者、读者及社会历史环境等对文学作品意义构成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乔纳森·卡勒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是由语境限定的,“因为语境包括语言规则、作者和读者的背景,以及任何其他能想象得出的相关的东西”。但是,“语境是没有限定的:没有什么可以预先决定哪些是相关的,也不能决定什么样的语境扩展可能会改变我们认定的文本的意义。”[3]71乔纳森·卡勒的文学作品意义的语境决定说看起来比上述观点更具合理性,不仅肯定了影响作品意义构成的作者、文本、读者等各方面因素的作用,还由于不对语境进行强制限定而彰显和肯定意义构成的历史性。但是,用一个本身就极具开放性而又不加以限定的范畴——“语境”来解释文学作品的意义,显然难以对文学作品意义及其生成进行有效的解释。
作者、读者、文本自身、语境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影响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因此文学作品意义的来源就富有多样性、多维度,不能将决定权仅授予任何一个维度。可是通过对上述学说的分析,对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我们依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倒是清晰地看到对这个问题回答所形成的种种错乱。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是否存有问题呢?
二、文学作品、理解和意义的时间性
“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本身,如同在美学中一直追问“美是什么”一样,包含着不合理性。意义的存在方式如同美一样并非是一种客体式对象性的存在,两者都存在于人的世界中,都极具生成性,而追问两者是什么显然已经无意识地将它们固化为某一有待发掘或认识的客体存在物。于是,这样就容易出现诸多的具有合理性而非准确的答案。事实上,这样的追问最后至多只能探寻一些影响意义构成的相关因素。那么这个问题的不合理性或难以回答的根源在哪儿呢?
海德格尔从存在之无蔽或存在之真理来思考艺术作品的本源和作品的存在,提出了作品保存论,认为伟大的作品将我们从寻常平庸的状态移入存在者的敞开性之中,它抑制我们的“一般流行的行为和评价,认识和观看”,让我们逗留于作品发生的真理中,如此才能让作品得以“保存”。只要作品被保存,就必然与保存者相关涉,而没有保存者,被创作的东西将不能存在。“因为只有当我们本身摆脱了我们的惯常性而进入作品所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从而使得我们的本质置身于存在者之真理中时,一个作品才是一个现实的作品”[4]295。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现实性”的考察显现出了艺术作品存在的非对象性、非客体化特性,而这在伽达默尔对艺术作品的时间性探索中被阐释得更加形象。
伽达默尔通过分析“节日”来说明艺术作品的时间性。节日首要的时间性特征是它的重复性,节日总是要在某个被人们庆祝的时刻重返,但由于时代不同,参与庆祝的人不同,对节日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而不同的人赋予所庆祝节日以不同的内涵,于是它一方面不断变迁和生成,另一方面节日又在变迁中不断返回自身,保持为同一个节日。艺术如同节日一样,艺术作品作为游戏是以其自我表现形式存在的,它的每次自我表现都由于游戏者的不同以及游戏者时代境遇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艺术作品在自我表现中发生多少变化,只要这种变化出于自我表现,艺术作品仍然是自我同一的,这就是艺术作品的“同时性”。“同时性是指,某个向我们呈现的单一事物,即使它的起源是如此遥远,但在其表现中却赢得了完全的现在性。”[5]165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同样有这种时间结构。它在一次次被阅读和被理解中赢获自己的现实存在。而在这种强调文学作品存在的时间性的理论中,实际被彰显的正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作品的每次现实存在的实现是作品意义世界的展开。在此,作品意义的时间性就随着作品存在的独特性浮出水面。
意义总在理解中获得现实存在,考察文学作品意义的时间性要从理解着手。海德格尔基于其“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思想之上的解释学的研究主题乃是每一“本己的此在”,而“此在”“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6]49“此在”没有任何现成的本性,而总活在一种要“去……”超越性的“势能域”之中,因此他认为解释学并不是要获得“知识”,而是要达到一种“生存状态”的认识。“在解释学中,对于此在来说所发展的是一种以它自己的理解方式自为地生成和存在的可能性”[7]。在此,理解不是对另一个生命作认知态度上的理解,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指向……的态度”,而是此在本身的一种“如何”,也即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理解所针对的不是任何外在于人的对象性客体存在,而是此在所筹划的可能性,是人生命中的固有“姿态”,即“意蕴”。这是具有根基性的意义,是意义存在论层面的含义。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对“理解”和“意蕴”解释所开辟的道路,在对理解的历史性及解释学应用问题的阐释中,通过“前理解”“视域融合”及“效果历史原则”等进一步具体地解释了理解现象,揭示了文本意义存在的时间性及其因而具有的间性、生成性及开放性等特点。
追究文学作品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的时间性特点能让我们看到文学作品及其意义的存在与人的亲密性,发掘其存在论层面的内涵。从这里,再回过头来看“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能更清晰地看出文学文本的意义绝不是某一现成存在物。这里我们并非仅仅是在追究文学作品意义问题的不合理性或难以回答的根源,也不是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理解事件及意义存在的时间性而将文学作品的意义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要尝试能否从另一个角度(时间或时间性)对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做出积极的阐释。
三、文学作品意义的“到时”
传统时间观以现在为基点,认为过去是不再存在的现在,将来是即将到来的现在,而现在似乎才是现实存在的,这就将时间表象为一种过去、现在、将来的线性“一维体”。传统时间观的这种线性思维实质上就是其内在二元对立思想或思维方式的体现。二元对立思维满足叠加原理,具有加和性,体现了线性的因果单值对应,否定了随机性、不确定性。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所必须的“视野”,他认为“先行”使“此在”本真地是将来的,充满非现成性和纯趋势性的“将来”占据着核心位置,“曾在源自将来,其情况是:曾在的(更好的说法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6]372。时间性并非某一现成的存在者,它不存在而是“到(其)时(机)”(Zeitigen),它是原始的、自在自为的“处理自身”本身,将来、曾在和当前是时间性的“绽出”,时间性的本质就是在诸种“绽出”的统一中“到时”。
首先,按照海德格尔这种“到时”的时间观,我们看到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在“到时”中成为纯原发构成的“现象”,具有时间性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么一种非现成实存的东西。当然,这并非就是将作品的意义视为一种纯粹动态的无形似的存在,而是试图从文学作品及其意义的时间性揭示它们存在论层面的内涵。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从不缺乏文学作品意义的现成形态或将其视为现成的这种现象。
通过海德格尔揭示的时间性的“到时”,我们还要尝试分析前述几种关于作品意义问题的回答存在问题的症结,并进一步揭示作品的意义生成的时间性。作者意图理论将文学作品的意义视为已经过去了的作者意图,事实上如果以文学作品产生的时间为界点,作者总是已经过去了的,且作为过去了的作者注定已丧失了对作品的“生杀大权”。从时间性的角度看,作者意图理论者的问题就在于将作品意义完全地封闭于时间的过去维度,看不到作品意义总会指向将来的时间维度,总是会活生生地存在于当前化的读者理解之中。事实上,将作品意义推向时间过去维度的最极致者,应该是从作者创作的角度出发,将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几乎完全交付于文学传统或过去作家的英国著名诗人与批评家T. S. 艾略特。但仅从作者创作角度看,艾略特的理论显然因看到了曾在是将来的当前化而切中了创作的时间性,显现出其理论一定的合理性。虽然阅读或理解会是当前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将读者中心论视为是将作品意义交予未来读者的阅读或理解。这不仅是因为以文学作品产生时间的界点来看,读者是未来的,从宏观的阅读或理解的角度看,读者也总是未来的,是被作品召唤着的。在海德格尔前期的时间观中,时间的“将来”维度具有优先地位,而在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中可以说代表“将来”维度的读者也极具重要性,这点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中都得到了凸显。作为“保存者”的读者,不仅使文学作品获得了现实性的存在,更是在作品意义的构成中最具活跃性的因素。但是,将文学作品的意义仅归于时间的未来一维,显然既使其完全丧失了历史性根基又使其指向不明、不确定,毕竟读者的阅读或理解最终也要成为过去,而作品将迎来的读者又是形形色色、数无可数的。最后,认为作品的意义仅取决于作品文本自身(形式结构因素)的理论,可以说将作品意义推向不变的当前。文本自身不仅残存有在其被创作时的当前因素,而且在每一次被阅读或理解中又成为绝对当前的。恰是这种绝对的当前将作品的意义归于绝对固化的形态,割断了作品的历史性联系,使作品意义的领会或构成从在世之“此在”中脱离了,从“此在”的时间性中脱离了。这样的意义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
总之,将文学作品意义推向时间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存在一种固化意义的倾向,都没能看到作品意义的时间性。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或领会就是时间的诸种“绽出”现象(将来、曾在和当前)统一的“到时”(时机成熟),在时间的过去、当前与未来三个维度中影响着文学作品意义的诸因素(包括作者、读者、文本自身、语境等),在达成一定的协调统一时即时机成熟时(“到时”)就使得意义显现出来。而这样意义也不会是唯一的,因为影响文学作品意义的诸因素显然在每一次的“到时”中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意义的“到时”或许仍很难详尽准确地回答关于作品意义的各种复杂问题,但它无疑让我们更具体地看到了文学作品意义的时间性。
[1]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德]赫施.解释的有效性[M].王才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3]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6.
[5]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7] [德]海德格尔.本体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节译)[J].何卫平,译.世界哲学,2009(1).
〔责任编辑 杨宁〕
On the Meaning and Temporality of Literature Texts
HUI Shuai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There are all along many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 literary text, such as author’s intention, reader’s reading, the text itself and so on but they all have some problems to some extent.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temporality and the meaning of being a text, it is clear that the quest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a literary text has inherent unreasonableness, which will be clea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emporality.
literary text; meaning; temporality; time up
I0
A
1006−5261(2014)05−0048−04
2014-01-21
惠帅(1989―),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