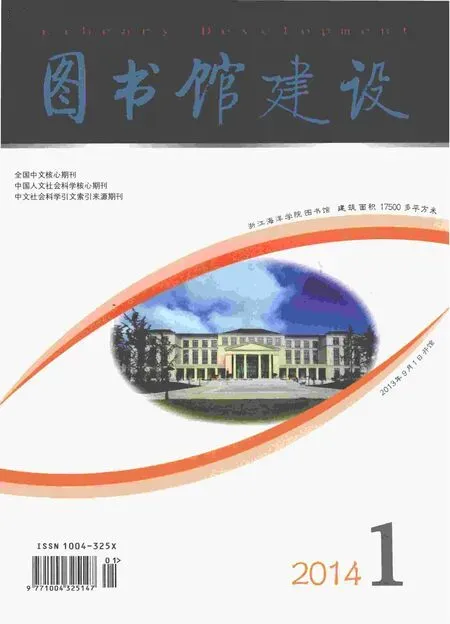我国图书馆“孤儿作品”利用中的版权问题分析
秦 珂 (新乡学院图书馆 河南 新乡 453003)
在现实中,存在有这样一类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其版权人身份不明或版权人身份确定但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参照日常生活中“孤儿”的概念,学术界通常称此类作品为“孤儿作品”(orphan work)[1]。近10年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孤儿作品”的版权问题日渐凸现。目前英国、匈牙利、加拿大、日本和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等国家与地区已经为“孤儿作品”立法,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简称IFLA)和国际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IPA)也在2007年7月联合提出了被认为是对国际“孤儿作品”论战有重要贡献的《孤儿作品使用原则》[2]。与“孤儿作品”相关的版权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制约我国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3]。例如,2012年,在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牵头启动的以抢救、保护濒临毁损的珍贵历史文献为目的的“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无论是数字化还是影印出版,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孤儿作品”的复制和利用问题[4]。美国版权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孤儿作品”是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孤儿作品”的存在,而且每个国家都迟早要被促使去思考解决该问题的方案[5]。然而,我国法律制度迄今为止尚未对“孤儿作品”的认定程序、授权规则、补偿标准、侵权救济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得图书馆对“孤儿作品”的版权管理,尤其是数字化开发利用受阻于法律滞后的现实立法环境。
1 “孤儿作品”的概念、特征、范围与产生原因
1.1 “孤儿作品”的概念与版权特征
“孤儿作品”的概念首创于2006年美国《孤儿作品法案》,指使用者利用版权作品并且需要得到授权时,该作品版权人的身份无法定义、界定或者无法与其取得联系[1]。随后,IFLA与IPA在《孤儿作品使用原则》、欧盟在《孤儿作品指令》中对“孤儿作品”做了不尽相同的解释。“孤儿作品”的主要版权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其一,版权人身份不确定,即便确定,使用者经过勤勉查找①仍然无法得知其下落以取得联系。其二,“孤儿作品”是版权客体,在版权保护期限内,属于非公有领域资源。其三,使用者利用作品的方式不能满足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的条件。其四,“孤儿作品”的版权状态并非绝对不变,具有不稳定性,版权人存在主动现身或者被找到的可能。
1.2 “孤儿作品”的范围与产生原因
“孤儿作品”版权问题的核心是“利用”,最大的法律障碍是使用者无法与版权人取得联系,无论是“版权人身份无法确定而找不到版权人”,还是“版权人身份确定无法找到版权人”的作品都应该被纳入“孤儿作品”的范畴。“无法与版权人取得联系”只能从主观角度进行判断,考量标准要具有“合理性”。例如,不能要求使用者采用类似刑事侦察的技术手段去查找版权人。所以,只要使用者查找版权人的行为符合了“勤勉”的法定标准,则可认为相关作品就是“孤儿作品”。有学者认为,“孤儿作品”的特征之一是版权人行使了发表权,作品已经公开发表[6]。这种观点把“未发表作品”排除在“孤儿作品”之外。对此问题,国际上存在不同的立法或立法倾向。例如,日本、加拿大的与版权相关的法律规定“孤儿作品”只限于发表的作品,美国《孤儿作品法案》则将未发表作品涵盖其中。导致“孤儿作品”大量存在的背景因素相当复杂:由于版权施行“自动保护原则”,使得版权登记丧失了对版权人的强制性,给版权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平台建设造成了困难;作者以假名、笔名,甚至匿名等方式行使署名权;作者通讯地址、联系方法变更;自然人去世,或法人及其他组织合并、重组、分立、破产、撤销后,版权无继承者;网络作品的版权信息被篡改、替换、丢失或者失真;报刊转载、摘编作品时,版权信息有意或无意地编造、隐瞒、改头换面;作者对摄影作品、美术作品等特定类型作品署名权的行使受到限制等。
2 我国图书馆利用“孤儿作品”的版权障碍
2.1 “孤儿作品”版权问题的由来与国际相关立法
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简称OCLC)的World Cat联合编目库统计,在3 200万种图书中,75%是版权人不详的“孤儿作品”[7]。IFLA的独立调研结果显示,其调研样本中某一组织拥有超过750万册的“孤儿作品”无法处理[3]。考虑其总量为503个调研样本,“孤儿作品”的总量可能超过5 000万册[3]。按照英国国家图书馆的统计,在其1.5亿份馆藏中,有40%属于“孤儿作品”[1]。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图书馆曾随机抽查了316册图书,其中,22册图书的版权人地址完全无法找到,向另外278册图书的版权人发出数字化请求,又有11%反馈“查无此人”,更有30%的请求杳无音信[8]。在特定类型的作品中,“孤儿作品”的比例相当高。例如,欧洲电影作品中“孤儿作品”占20%,实际数量达到22.5万部。英国摄影作品中“孤儿作品”的比例高达90%,约1 700万部[3]。可见,“孤儿作品”数量巨大、类型丰富,是图书馆的重要馆藏资源。
欧美各国对“孤儿作品”版权问题的关注源于数字图书馆建设[9]。正如2008年欧盟在《知识经济中的版权》(绿皮书)中指出的,“孤儿作品”现象是大规模的数字化活动引发的[10]。这一切都肇始自2004年Google公司实施的“阿波罗项目”(即“数字图书馆计划”)。 据统计,“阿波罗项目”已经扫描的图书中有70%是“孤儿作品”[11]。2011年3月,美国法官Denny Chin否决了Google与美国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家协会达成的“和解协议修订本”(Amended Settlement Agreement,简称ASA),其中“孤儿作品”是个关键问题。Denny Chin认为, Google的“和解协议”(包括原始和解协议与和解协议修订本)针对“孤儿作品”提出的“选择退出”(opt-out)机制不符合版权规则,而且存在限制“孤儿作品”搜索市场竞争的违背反垄断法的问题[7]。部分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之所以卷入“阿波罗项目”版权风波,是因为其向Google提供了被扫描的馆藏图书,图书馆本身还是图书电子副本的保存和使用者之一。这是发生在图书馆界的全球首场“‘孤儿作品’战争”[12]。2011年4月,美国作家协会起诉HathiTrust,指控其“孤儿作品计划”(orphan works project),共同被告还包括向Google提供了“孤儿作品”的密西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图书馆。原告还认为, HathiTrust和涉案图书馆的行为不符合美国《版权法》第108条(图书馆例外权利)和107条(合理使用权)的规定,图书馆对电子副本的保存有安全隐患,可能导致流失,造成版权损害。
在版权羁绊面前,图书馆对“孤儿作品”的数字化开发、利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欧盟委员会认为,传统图书馆对“孤儿作品”的数字化利用面临巨大的挑战,大规模的文献数字化使“孤儿作品”版权问题愈加突出[13]。IFLA和IPA的联合筹划指导小组主席Claudia Lux认为,“孤儿作品”对图书管理员、信息利用者是一件坏事,太多的无法追溯版权人的作品被尘封,将阻碍创造性和进步[2]。Google的数字图书馆梦想掀起了“孤儿作品”版权问题的“盖头”,印证了法律的缺失,推动了立法的变革,国际社会对“孤儿作品”的立法从此驶入快车道,立法模式包括侵权责任、中介许可、强制许可、法定许可、折衷许可等,多路径的法律选择不仅映射出权利博弈的激烈性、复杂性,而且体现出法律的不成熟性、不协调性。版权制度已经举起了保护“孤儿作品”的旗帜,其效果怎样,尚需版权实践的检验。
在相关立法与法案中,不乏专门针对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规定。按照2006年美国《孤儿作品法案》的规定,如果“孤儿作品”的侵权者是非营利性的图书馆、教育机构等,可免予对版权人的经济补偿,即所谓的“公益性免责”[3]。根据欧洲“数字图书馆高级专家组”的意见,欧盟委员会在2011年5月提出了《允许适当使用孤儿作品指令的提案》(即后来的《孤儿作品指令》),把使用“孤儿作品”的“特权”限定于赋有“公共利益使命”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3]。按照芬兰《版权法》第16d条、丹麦《版权法》第16b条的规定,图书馆可以通过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达成扩张性许可协议利用“孤儿作品”[4]。日本《版权法》第67条规定,对于已发表的经过相关程序和机构认定的“孤儿作品”,文化委员会可强行授权图书馆使用[8]。2007年7月,IFLA和IPA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孤儿作品使用原则》。
2.2 我国图书馆利用“孤儿作品”中的版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未涉及“孤儿作品”,只是对诸如“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和“没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作品进行了零星的规定。这些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孤儿作品”的使用困境,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孤儿作品”的利用问题[14]。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我国图书馆利用“孤儿作品”(主要指数字化利用)将遇到下列版权问题。
2.2.1 对“孤儿作品”的利用缺乏法律根据
我国法律制度中与“孤儿作品”版权保护相关的条款是《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3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下文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但是并没有就“孤儿作品”的范围、认定标准和授权程序使用性质与规则,以及对经济补偿和法律责任限制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总体上缺乏法律规范。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除去合理使用(《著作权法》第22条第8款、《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法定许可(符合法定条件的图书馆可以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8条“义务教育法定许可”、第9条“扶贫法定许可”的规定)等情形,图书馆对作品的数字化利用应遵循“先授权,后使用”的原则。但是,由于“孤儿作品”的版权人身份无法确定,或者确定却无法取得联系造成的“授权不能”,使图书馆不得不囿于版权的藩蓠,放弃对作品的利用,这既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也极大地降低了数字化项目的质量。欧盟委员会指出,图书馆因授权障碍而远离“孤儿作品”,将形成“资源黑洞”[13]。我国有学者认为,由于“孤儿作品”在信息资源中占据的比例相当大,抛弃此类作品意味着图书馆的数字化构建将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可能就此搁浅[15]。
2.2.2 对“孤儿作品”利用的可操作性较低
《著作权法》第19条、《继承法》第32条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尽管与“孤儿作品”有关,但是极不完善,图书馆据此利用“孤儿作品”会遇到可操作性低的问题。例如,《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规定,作品原件的持有人可以行使“作者身份无法确定”的作品的版权[16],但是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原件”的概念和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图书馆面对持有相同“数字原件”的两位以上的都声称对作品享有权利的人,该如何断判谁是真正的权利主体,又该与谁谈判取得授权呢?又如,该条款只规定了“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的权利行使问题[16],那么图书馆在利用“作者身份明确但找不到版权人”的“孤儿作品”时,谁又是权利的主体呢?再如,《著作权法》第19条[16]、《继承法》第32条[17]规定,没有版权继承者的作品,其版权归国家享有。既然版权由“国家享有”,那么这类作品就不属于“孤儿作品”。问题在于我国法律从未对“国家享有版权”的主体予以明确,其性质、职责更是无从定位,使得“国家版权”的主体虚化。这种规定也模糊了“孤儿作品”与“国家享有版权”的作品的界限,由于没有对“国家享有版权”的作品的登记与版权公示制度,图书馆对这两种情形的作品的确是难以区分。图书馆即便能够厘清、判明,也不知道该向哪个组织递交使用“国家享有版权”的作品的申请书。
2.2.3 版权利益纠纷隐患和法律风险增加
法律的缺失和不完善为图书馆利用“孤儿作品”中的版权纠纷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例如,图书馆对“孤儿作品”的利用并非只限于陈列、保存意义的数字化复制,或者只在有限范围内的传播,而是可能在“孤儿作品”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附加了版权价值的衍生作品,如多媒体、数据库等。如果版权人现身后向图书馆主张权利,那么这些衍生作品的权利归属就可能成为争议的焦点问题。如果版权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颁布禁令要求图书馆停止使用“孤儿作品”,那么图书馆在开发“孤儿作品”中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都将付之东流。正如有学者指出,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的不断加强,使“孤儿作品”版权的制度瓶颈愈加突出,将引发诸多纠纷[18]。图书馆使用“孤儿作品”的法律风险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与美国等国家的立法不同,我国《著作权法》没有赋予图书馆享有“善意合理使用抗辩权”,图书馆如果侵害了著作权,造成版权人利益损失,则无论图书馆是否具有善意,无论版权人的实际损失是否可以计算,都将同其他主体一样承担赔偿责任[19]。加之,我国立法存在着提高版权损害赔偿金的趋势[20]。这些都使图书馆在法律不健全的条件下使用“孤儿作品”的风险增加。另外,从国际立法看,规范“孤儿作品”的法律规则通常都较为复杂,缺乏版权专业管理人才的图书馆很难在具体的作品利用行为中正确、恰如其分地把握相关的法律界限,由此也会增加法律风险。
为了弥补我国对“孤儿作品”立法的缺陷,2012年7月国家版权局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第25条中对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著作权法》第19条和《继承法》第32条的内容作了归纳表述,在第26条对 “无法联系版权人”的作品采取了“强制许可+事先提存使用费”的立法模式,这实属是对“孤儿作品”立法的突破[21]。但是,相关规定的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不足。国际知识产权联盟针对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第26条指出,“前款具体事项,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另行规定”的说法,使人们觉得关于“孤儿作品”条款的实施尚待时日,令我们深感关切[22]。
3 我国图书馆利用“孤儿作品”的策略思考
3.1 Google公司“阿波罗项目”的启示意义
图书馆究竟是继续困守于“孤儿作品”的版权“围城”,还是主动寻求“自我救赎”路径呢?或许,“阿波罗项目”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阿波罗项目”尽管挑战了法律的底线,然而其积极意义可圈可点。例如,有学者认为,“阿波罗项目”探索了在版权专有与垄断的立法之下破解“孤儿作品”版权困惑的道路,挖掘了巨大的文化财富,使全社会受益,是当前唯一能够救“孤儿作品”于水火的办法[23]。但是,“阿波罗项目”的版权政策是有其致命缺陷的,笔者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采取“选择退出”机制,而是在该机制基础上作品被不合理地大范围传播,因为众多单个用户使用行为的集成化效应明显地减损了“孤儿作品”的市场价值。
如果图书馆能在欣赏Google与版权制度抗争的勇气的同时,又不失于“鲁莽”,认真汲取“阿波罗项目”的教训,采用适度、有节制的、不致对版权利益平衡机制造成太大扰动的“孤儿作品”版权数字化利用策略,版权人应当乐于接受。这既有助于增强作品的“可见度”,使版权人能够识别、找到使用者,通过授权活动实现其权益,也是图书馆逐步积累证据,向立法机关反映诉求的一种重要方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Google的“和解协议”(包括原始和解协议与和解协议修订本)为立法机关修改版权规则提供了新的思路[11]。实际上,图书馆采用适度、有节制的版权利用方法并非鲜见,尽管某些做法与法律的规定有所出入。例如,按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的规定[24],图书馆对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的传播应仅限于物理馆舍的“局域网”内,现实情况却是几乎所有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都实现了“校园网”(而非图书馆“局域网”)范围的传播利用,而绝大多数的数字资源供应商对此并无疑义,并且会在许可协议中主动授予图书馆这项权利。
3.2 现行法律框架下我国图书馆利用“孤儿作品”的方法探析
笔者认为,我国图书馆对“孤儿作品”适度、有节制的数字化利用主要应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勤勉搜索”版权人。国际社会对“孤儿作品”的立法,无论是采取法定许可、强制许可模式,抑或采取侵权救济等模式,大都把“勤勉搜索”当成使用者利用“孤儿作品”之前必须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来对待。例如,欧盟《孤儿作品指令》就明确要求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必须勤勉地查询版权人的下落[3]。IFLA和IPA提出的《孤儿作品利用原则》也将“勤免搜索版权人”列为第一原则[2]。至于如何判断使用者是否进行了“勤勉搜索”,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版权局提出了“最佳行规”(best practices)的概念,美国《孤儿作品法案》、加拿大《版权法》等都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结合国际立法与我国版权授权机制建设现状,图书馆可以通过下列途径开展“勤勉搜索”:直接联系版权人或者作品出版单位,或搜索图书馆网站和其他相关网站已经公布的图书馆拟使用“孤儿作品”的信息;向版权信息库提出查询版权人的申请;通过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版权代理公司、版权登记机关,以及国家版权行政管理机关或其授权机构查询版权人;在全国性报刊上登载查找版权人的公告。
第二,建立作品利用规则。除非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情形,我国图书馆非经授权使用“孤儿作品”是一件需要“越雷池”的带有一定程度法律风险的事情。作品利用规则的制定与严格执行对图书馆化解风险至关重要。其一,坚持非营利性的善意使用。其二,“孤儿作品”要具有“不可替代性”,即如果放弃对该作品的使用,图书馆的业务活动将达不到目的。其三,传播范围限于图书馆物理馆舍内的局域网(这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因为将不具备合理使用条件的“孤儿作品”也纳入了局域网传播的范围)。其四,使用“孤儿作品”时要附带版权信息标识。其五,如果版权人出现,无论其是否向图书馆主张权利,图书馆都应立即停止使用,在与版权人沟通协商后决定是否继续使用作品。我国图书馆对“孤儿作品”的版权问题十分陌生,因此笔者建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制定行业性的版权指导政策。
3.3 基于图书馆视角的立法建议
“孤儿作品”的版权问题终究要靠立法的健全与完善来解决,有必要从图书馆角度向立法机关反映诉求。其一,借鉴欧盟《孤儿作品指令》的规定,把“孤儿作品”的利用主体限定于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范围之内。其二,避免“勤勉搜索”标准的严苛性与程序的复杂性,降低图书馆“勤勉搜索”的时间成本。据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简称JISC)2009年4月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在欧洲每部“孤儿作品”的版权查证通常需要12个小时[4]。在数字版权管理系统较为发达的欧洲尚且如此,那么在我国查证一部“孤儿作品”版权情况的平均时间或许更长。我国可以研究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的法律,建立扩展性(延伸性)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使图书馆能够通过中介机制使用“孤儿作品”,提高效率。其三,学习美国《孤儿作品法案》的做法,赋予图书馆等非营利机构享有公益性使用“孤儿作品”的经济补偿豁免权,即便要求图书馆向“孤儿作品”的版权人支付补偿金,也应从图书馆的主体性质与社会职能出发,合理制定补偿标准,使图书馆不致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例如,奥地利一所大学图书馆耗资15万欧元将1925—1988年间完成的博士论文数字化,但因无法承担高昂的版权交易费(约为数字化的20~50倍),至今无法提供在线获取[4]。数十年前的作品的版权交易费都如此之高,近些年的版权交易成本就可想而知了[4]。又如,2013年初,由于《商务和企业改革法案》被否决,使得英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不得不预先花费累积数额庞大的资金为“孤儿作品”的使用权买单。英国国家图书馆董事会会长泰莎·布莱克斯通(Tessa Blackstone)认为,这种决策对图书馆是“极具毁灭性的”[25]。立法机关可以按照“孤儿作品”的不同类型,及其对图书馆公益性服务的影响程度,分别制定合理的补偿金标准[26]。其四,对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进行修订,拓宽图书馆对“孤儿作品”的数字化合理使用权限。
注 释:
①勤勉查找指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法,作品利用者对版权人进行了查找。
[1]王 迁.“ 孤儿作品”制度设计简论[J]. 中国版权, 2013(1):30-33.
[2]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国际出版者协会和国际图书馆协会确立孤儿作品使用原则[EB/OL]. [2013-05-12]. http://www. lawtime. cn/info/zscq/gwzscqdt/201103.html.
[3]赵 力. 孤儿作品法理问题研究:中国视野下的西方经验[J]. 河北法学, 2012(5):149-155.
[4]翟建雄, 邓 茜. 孤儿作品的数字化利用:欧洲的立法与实践[EB/OL]. [2013-06-11]. http://www. chinacourt. org/article/detai/2013/01/id1813216.shtml.
[5]董慧娟. 孤儿作品的利用困境与现行规则评析[J]. 中国出版, 2010(9):36-39.
[6]张 雪. 从国际角度看我国的孤儿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EB/OL].[2013-05-12]. http://www. docin. com/p-386180437.html.
[7]杜铂伦, 黄光辉. 孤儿作品的保护与利用危机及其解决方案刍议[J].电子知识产权, 2013(3):83-88.
[8]马海群, 高思静. 孤儿作品的版权困境及解决路径[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9):87-91, 143.
[9]杨佩霞. 论版权制度下孤儿作品的保护[J]. 中国版权, 2012(3):44-47.
[10]周艳敏, 宋慧献. 版权制度下的“孤儿作品”问题[J]. 出版发行研究, 2009(6):66-68.
[11]肖冬梅. 谷歌数字图书馆计划之版权壁垒透视[J]. 图书馆论坛,2011(6):282-288.
[12]愈演愈烈的“孤儿作品”之战[EB/OL]. [2013-05-09]. http://www.dajianet. com/world/2011/0926/171090. shtml.
[13]孟兆平. 互联网时代孤儿作品的利用困境及其解决机制[J]. 电子知识产权, 2013(7):27-33.
[14]刘 宁. 试论我国孤儿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保护[J]. 电子知识产权, 2013(7):20-26.
[15]金泳锋, 彭 婧. 孤儿作品保护大陆与香港之比较研究[J]. 电子知识产权, 2011(3):69-71, 75.
[16]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EB/OL]. [2013-05-11]. http://wenku.baidu. com/view/17687f5b312b3169a45la4c6.html.
[17]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EB/OL]. [2013-05-11]. http://news.xinhuanet.c om/lrgal/21/content.html.
[18]赵 锐. 论孤儿作品的版权利用[J]. 知识产权, 2012(6):58-62.
[19]王 清, 陈凌云. 中美版权法之公益图书馆豁免制度比较[J]. 图书馆杂志, 2008(9):2-5.
[20]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EB/OL]. [2012-09-07]. http://www. law-lib.com.
[21]黄浩杰. 试析“孤儿作品”的国内立法保护[J]. 法制博览, 2013(1):40-41.
[22]Schlesinger M.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对《著作权法》修改及最高人民法院网络著作权保护司法解释的建议[J]. 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译.中国版权, 2012(5):17-18.
[23]练小川. 谷歌图书扫描与“孤儿图书”[J]. 出版参考, 2009(12):42-43.
[24]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EB/OL]. [2013-05-11]. http://baike.baidu. com/link?url=wzyrQyzwlwRincGm YQBQcUVR2GPCSR HBDgCe.
[25]英新规迫使博物馆等为孤儿作品使用权买单[EB/OL]. [2013-06-08]. http://www. cnarts. net/Cweb/news/read%asp?id=252378&kind=%3F.
[26]黄丽萍. 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制度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1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