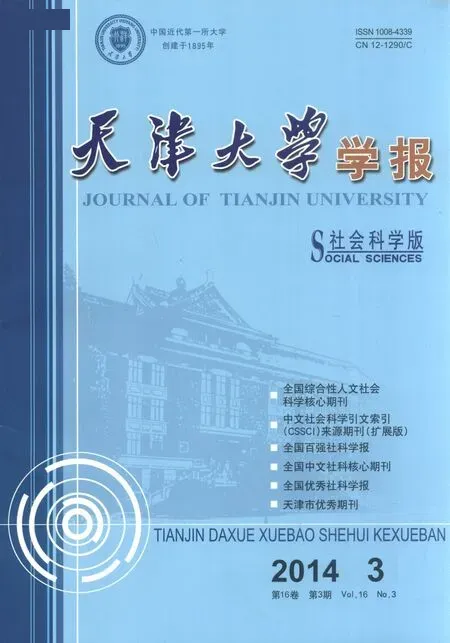人情味的缺乏:约翰逊论弥尔顿人格与作品的缺憾
叶丽贤
(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2.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9)
塞缪尔·约翰逊是英国18世纪成就斐然的词典编撰学家、文学评论家和传记作家。1777年,已著作等身,年近七旬的约翰逊受部分伦敦书商的委托,为将要联合出版的《英国诗人作品集》撰写前序,包括对每位诗人的生平介绍和作品点评。约翰逊历时4年才最终完成这项工程。最早这些序言与各自评介的诗人作品合在一起出版,后来集结成4册以新名单独发行,评论界约定俗成称作《诗人传》。《弥尔顿传》写于1778年,发表于次年,是这系列传记中最具举足轻重,也最饱含争议的一篇。约翰逊的政治态度和他对弥尔顿诗歌艺术的评价,成为当时很多文人作家炮轰的对象。不过,现今学者已倾向于认为约翰逊评述诗人,能谨慎地将“文品”与“人品”区分开来,即使有些诗人私德败坏(如沃勒)或与他政见不同(如弥尔顿),却并不影响约翰逊对他们艺术成就的评价。
《诗人传》中一些较长的篇章,如《德莱顿传》和《蒲柏传》,通常是由“诗人生平”、“人物素描”和“作品评介”3部分组成。约翰逊常以“人物素描”为过渡,把“诗人生平”与“作品评介”一条隐秘线索贯穿到一起。这条线索便是作家的人格形象(包括性格、心智或才华)与其诗歌风貌之间的关系。格列格·克林汉姆曾以《德莱顿传》的“人物素描”为核心,尤其是以诗人的敏博才情为关键,来检视它如何贯穿在诗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中[1]。斯蒂文·菲克斯也曾详细分析在《弥尔顿传》中约翰逊如何使弥尔顿诗歌的美学风格与其孤傲的人格形象相互呼应,共成一体[2]。但菲克斯的文章着眼点在于弥尔顿的诗歌优点、成就与诗人人格之间的关系,而且并未将约翰逊的评点放在弥尔顿的批评传统中来考量。本文拟将《弥尔顿传》放在18世纪以及后世的批评历史中,着重考察约翰逊如何评价弥尔顿这位经典诗人的美学风格的缺陷,并借助菲克斯对约翰逊笔下的弥尔顿形象的归纳,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菲克斯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弥尔顿的人格特征与诗歌创作
《弥尔顿传》刚开篇没多久,约翰逊就对弥尔顿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人格形象作了简单勾勒:“似乎在所有的作品里,他都显露出高才硕学通常会有的品质,即坚定的高度自信,也许还带点对他人的不屑”[3]。在这篇传记中,但凡涉及弥尔顿对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约翰逊的行文都可以说是万变不离一宗。弥尔顿才学惊世,但是性情孤傲,以自我为中心,以私见评判是非,不屑与平庸之辈相往来,致使自己与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相隔绝。菲克斯对与弥尔顿强大、孤傲的生平细节作了详尽归纳。在教育思想上,弥尔顿不屑教授“中小学的普通知识”,如宗教和道德,偏喜爱传授高深的天文地理知识[3]248;在政治上,他信奉共和思想,但这种思想“所植根的基础,恐怕是对‘伟大’的艳羡与妒恨,对‘独立’的病态渴望,是急于操控他者的爆脾气,是鄙视居上位者的自尊心”[3]276;在宗教上,他几乎不出入教堂做礼拜,也很少单独或与家人一同祈祷,他似乎相信“人可以靠对自我的嘉许来生活,向自我辩护自身的行为”[3]276;在夫妻关系和友谊的问题上,弥尔顿也表现出难以合群并享受其间乐趣的特点,与培护伦理关系相比,他似乎更关心个人学问的精进。综合可见,约翰逊展现给读者的弥尔顿,确实是一个落落寡合,矫矫不群的孤傲人物,有别于《诗人传》中取媚俗众的德莱顿和处事圆滑的蒲柏,也有别于喜欢流连于酒馆茶肆,与众友高谈阔论的约翰逊。
弥尔顿的这种人格特征进而决定了个人的诗歌创作特色,即更擅长表现非现实主义的题材或遗世独立者的思想情感,很少创作偏重俗世情感交流和往来的作品。《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就属于这类以宗教故事为题材的非现实主义作品。约翰逊高度赞扬了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所展现的具有原创性的诗意想象。这种无需取法于先人的“原创性”,是约翰逊给予弥尔顿的才华及作品的最高礼赞,它与诗人独立自主、恃才自负的人格之间存在一种深层的联系。传记最后一段,约翰逊将这层联系明确地揭示了出来:“在所有借鉴了荷马的诗人中,弥尔顿也许是最无需对他感恩戴德的。弥尔顿天生就是独立的思想者,对自身的才能充满自信,不屑于他人的扶助或阻扰,他并不能拒绝接受前人的思想和意象,却从未刻意去追寻二者。他并未从同时代人那里寻求过帮助,也从未接受过他们的帮助;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任何东西能满足其他诗人的自尊或虏获他们的青睐;没有相互的恭维,也没有乞求他人的扶持。他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在困窘和失明的状况下写就的;他是为艰巨的伟业而生;《失乐园》不是最伟大的英雄史诗,只因为它不是第一部。”[3]294-295由此可见,就创作的现实环境而言,弥尔顿因眼睛失明和王朝复辟,陷入孤立隔绝的状态。就面对的文学资源而言,诗人也处于同样的境地,但与前者不同,这是他有意而为的结果。不管是何种情形,都可以反映或烘托出弥尔顿独立自信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恰恰构成了弥尔顿的卓绝想象和作品原创性的生平基础。除此以外,弥尔顿的原创性还体现在他在诗歌中所使用的前所未有的独特、怪异的英语[3]293。约翰逊认为弥尔顿在早期作品中就呈现出一种能反映他特立独行的性格的语言特征:“独立自创和不求假借的风姿”[3]278。所有这些表述都以一种有机的方式将《失乐园》的作品风貌与人格特征联系了起来。
弥尔顿不仅擅长处理需要超越现世生活进行虚构的题材,他也善于传达像《欢乐颂》和《沉思颂》这类诗作中孤独者的思想情感。这两首诗所表现的“欢乐”和“忧愁”都不是在大庭广众或亲朋好友之间集体抒泄的情感。相反,约翰逊说它们“孤独而沉默地寓居于人的心胸中,既不向外敞开,吐露心声,也不接纳他人的情意。所以诗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位智慧的朋友或愉悦的同伴”[3]280。虽然《欢乐颂》描绘了欢闹热腾的集会和婚礼场面,但说话者“仅是一个旁观者”[3]280,与众人始终保持疏离的态度。《欢乐颂》和《沉思颂》是弥尔顿小诗中约翰逊评价最高的两首,约翰逊说它们是“想象的宏伟之作”[3]280,其实是在暗示孤傲的性情使弥尔顿能充分想象离群索居者的心境以及他们眼中的世界,甚至使歌颂欢乐女神的作品也蒙上一层忧郁的色彩。《欢乐颂》和《沉思颂》中的心灵景象及《失乐园》天马行空的想象,都在约翰逊的点拨下,与弥尔顿的生活体验和性格产生了微妙的呼应。
约翰逊对弥尔顿的诗才和成就其实评价很高,他认可17、18世纪的批评家给弥尔顿的经典地位所贴的“崇高”(the sublime)标签,认为“崇高”是主导弥尔顿的心智和作品(尤其是《失乐园》)的力量或风格[4]。“崇高”作为文艺理论术语,源起于希腊修辞学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后来经17世纪法国批评家布瓦洛和18世纪英国批评家的译介和阐发,逐渐在18世纪中后期由修辞技艺转变为美学概念。在文艺创作领域,它可用以概括创作者的心智才华,形容作品的风格和思想,还可用以描述读者的情感反应。18世纪英国批评家约翰·丹尼斯认为崇高和普通的诗歌在读者心中所引发的“激情”是不同的。后者所触发的是“俗常的激情”,即由眼前的事物、日常生活中的观念所引发的情感;而前者所触动的是“高扬的激情”,即宏大的观念经过心智反思后所产生的剧烈反应[5]。这种反应常表现为令人心魂俱与、不可自控的惊奇、恐惧、愁苦等激情。埃德蒙·伯克将“优美”视为“崇高”的对立面,认为“优美”产生于“社会交往”的本能,与爱以及类似情感有关联。由此可知,在伯克心目中,“崇高”多与孤独、内省相关,它绝不同于人在俗世生活中所互存的友爱之情。另外,艾迪生把史诗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分为“自然型”(即凡夫俗子所拥有的令人愉悦、着迷的情感)和“崇高型”[4]156。约翰·贝利认为能引发崇高感的自然景象除了具有宏大、均质的特点外,还要“非同寻常”[5]90。所有这些比照或观点都暗示“崇高”有与普通人的往来和情感相脱离,追求宏大和高远,不流于俗常的意味。约翰逊塑造弥尔顿的人格形象和评判他的诗歌,也沿用了这些批评家的区分,突出了“崇高”与“俗常”的比照。
在约翰逊看来,弥尔顿正是凭借个人的崇高才华才能创作出《失乐园》这样一部脱离人间俗世,题材宏大、主旨高瞻,能震人心胆的史诗巨著。弥尔顿有如此崇高的才情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与他傲岸独立、卓尔不群的性格或精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约翰逊在肯定弥尔顿的性格和才情给创作带来独一无二的优势的同时,又看到这种人格特征导致他的诗歌存在一个重大缺憾,即“人情味的缺乏”(the want of human interest)[3]290。引用菲克斯的话说,弥尔顿的诗歌“也具有自我中心主义,与现实经验脱离,与普通人的兴趣没有关联”[2]252。这句评断呼应了约翰逊阅读完《失乐园》后不由自主产生的直觉感受:这部作品没有人的情味。
二、约翰逊对弥尔顿诗歌的批判
约翰逊本来是用“人情味的缺乏”这个短语来描述《失乐园》“与生俱有的缺陷”(original deficiency)[3]290。所谓“与生俱来的缺陷”,指的是《失乐园》题材的选择、寓意的确立、情节的虚构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观念所必然导致的作品缺憾。约翰逊其实是将“人情味的缺乏”视为弥尔顿诗歌缺憾的整体表征。论及《失乐园》,约翰逊明确指出,这部史诗极少有关于“道德教诲”和“审慎原则”[3]286的精彩片段,它“既不含有世人的行为,也不含有人世的风尚”[3]289。虽然约翰逊在传记稍前部分承认《失乐园》的堕落和救赎主题、亚当夏娃身上的善与恶,能与所有人永远产生利害攸关的联系[3]285,但约翰逊后来又依据自己作为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推翻了前面的看法。他指出现世的读者无法以想象的方式参与到《失乐园》所发生的事件中,去体味人类始祖的纯真状态以及因堕落而受的惩罚,所以“几乎不会产生天然的好奇心和同情感”[3]290,必然与作品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隔阂。
虽然弥尔顿善于“展现宏阔的气象,昭显壮观的气派,增强威严的气度,使阴郁的气质更暗淡,使恐怖的气氛更惊悚”[3]286,令读者胆颤心惊,无法自持,但其间所蕴含的善与恶、罪与罚的观念,其间所传递的审美效果,约翰逊认为,最终只会让读者唯恐避之不及。“那些观念,有一些我们会因崇敬远而避之,只有在需要联想起它们的具体时刻,才会去接纳它们。有一些我们会因恐惧退避三舍,只把它们当作有益的惩罚,用以抵抗利益与激情对自我的影响。这样的观念,只会阻碍而非激发奔腾的想象。”[3]289也就是说,弥尔顿靠磅礴大气的想象所传达的宗教观念以及艺术效果,因过于庄重和严肃,只会让那些为审美愉悦而阅读的读者感到无心忍受,无力应对。“与永生攸关的善恶观念,对才智的翅翼而言,太过沉重;才智受到它们的重压,处于消极无助的状态,只好满足于温和的信仰与谦卑的仰慕”[3]289。约翰逊用了“沉重”、“重压”、“谦卑”这些词语来表明读者在弥尔顿的想象牵引下,非但不能随其扶摇直上,反而处于下坠和低伏的状态。同情的想象最终无法在普通读者与《失乐园》之间产生,横亘在中间的是“崇高”与“俗常”的壁垒。
约翰逊的评判迥然有别于之前的18世纪批评家的观点。例如,弥尔顿的传记作者乔纳森·理查生认为《失乐园》的思想是“以最有效、最迷人的方式传达给读者。读者的心智被愉悦所缓和,被调制,吸引,诱惑,唤醒,激活,接受了诗人意欲传给它的印象”[6]。理查生对阅读《失乐园》的体验的描述,只是一味的赞美,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可以说代表了17世纪末、18世纪早中期受众的态度。到18世纪中后期,随着小说体裁的兴起和阅读品味世俗化的加强,英国学者休·布莱尔开始承认,如果弥尔顿选择一个更贴近世人生活,而非关乎神学义理的题材,展现更多类型的人物和情感,他的诗作会更“令人愉悦和着迷”,但他仍然认为弥尔顿的作品“总体基调”是“引人兴趣”的[4]246。约翰逊与布莱尔不同,他坚定声称《失乐园》难以满足普通读者的个人趣味。约翰逊这么总结阅读完《失乐园》的心里感受:这部诗没有人的情味,这是“一本读者尊崇,但一旦释手就不会记得捧起的书”,“阅读它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件乐事”[3]290。约翰逊还向读者坦白道:“我们读弥尔顿是为了教诲,我们离去的时候,感到心神不安,心情沉重,只能去它地另寻消遣;我们抛弃了导师,去寻找自己的同伴”[3]290。弥尔顿的心灵境界,远非普通人所能企及,他的文学作品虽好,但人们无法从中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得到心灵的慰藉。
从约翰逊的评判,可以窥见他对宗教题材入诗的总体态度。18世纪早期的批评家,以约翰·丹尼斯为代表,倾向于认为宗教观念或神圣题材适合创作为诗歌,因为它们最能有效地激起人的崇高情感。在18世纪的英国,宗教常与“崇高”联系在一起。在神学家和批评家的推动下,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圣经》文本的崇高性,并将它视为崇高的典范。他们认为这种崇高性不仅源自于《圣经》简单朴素的语言,也源自于蕴含在经文中的公正、伟大而神奇的思想,它是受神启示的结果[7]。所以,18世纪不少文人学者提倡让神圣题材入诗以产生崇高效果,利用崇高达到灵修的目的。丹尼斯就曾声言现代诗人应将基督教神学与诗歌的构思结合起来,以获得高于古人的优势[4]127。正如戴维·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活跃在18世纪早期的诗人,像理查德·布莱克默爵士、伊萨克·沃茨、亚伦·希尔,甚至倡议用《圣经》的题材和希伯来诗歌改造当时英国的诗歌创作[8]。与这些诗人学者不同,约翰逊认为宗教默想或神学教义未必能勾起读者的审美反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人将全能的神直接作为叙述、歌咏或敬献的对象,其实并没有可进行艺术加工的余地。正如约翰逊在《沃勒传》中说:“凡是伟大的、理想的、宏贯的,都集合在最高者的名下。‘全能’难再有提升;‘无限’难再有扩展;‘完美’难再有增进”[3]53。诗人无法通过创造给读者带去文学作品应当要产生的“奇妙和喜悦之感”,读者从这类诗作中所能体验到的只是诗人孤独、虔诚、崇高的宗教默想。就像《失乐园》这样的作品,虽然充盈着诗人的崇高想象,但它指向的宗教寓意和义务,却对读者的审美体验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制和阻碍的效果。
约翰逊对戏剧《力士参孙》的评判,与史诗《失乐园》相近,一样缺乏人的趣味:“弥尔顿在戏剧方面并不出类拔萃,他对人性知而不详,从未细察个性之间有何细微差别,也从未细察激情投合时所起的作用,或激情相抵触所引发的迷乱。他博览群书,深谙书中教导;但涉世不深,阅历不足,所以缺乏相应的知识。”[3]293在约翰逊看来,弥尔顿的戏剧缺乏对人性、个性、激情、人世的深刻体味。如果将约翰逊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与这段文字比照,就会发现实际上他是以莎士比亚作参照来评价弥尔顿的作品,用的是“自然”(nature)和“触情”(pathetic)这两大相联的标准。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才会充满了实用的真理和家常的智慧……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搜罗到一整套关于细谨持家,勤谨治国的箴言”[9]。“形象丰满并具有普遍性的人物,要使他们相互有别并长存于世并不容易,不过迄今还没有诗人会比莎士比亚更能塑造截然不同的人物”[9]331。“遁世隐居的人从中可以学到对人间事务的判断,聆听忏悔的神父从中可以预知七情六欲的走向,观览剧中的景象,体味富含人性的语言中人的思想,读者也许就能治好对幻想的狂热与痴迷”[9]332。这些论断说明莎翁的才赋在于擅长塑造具有普遍性但又极具个性的人物,表现人的七情六欲和俗世的景象,与弥尔顿形成鲜明反差。约翰逊认为莎剧是一面反映“自然”(包括大自然、社会、人性、激情等)的镜子,它能产生“触情”的效果(依据约翰逊的定义,它指的是“触动人的激情;富有激情;令人感动”[10])。与此相反,弥尔顿的作品优长不在于描摹自然,而在于对人间之外的故事的虚构,因此也就难以触动普通人心中的喜怒哀乐。这迥然有别于观众观看莎剧时的反应:“不管是逗观众开心,还是使观众感伤,或者只是通过熟悉流畅的对白,不动声色、平平淡淡地把故事展开,他都能轻易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一旦被他所掌控,就只能高声大笑或者黯然伤怀,又或者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满怀期望地等待”[9]337。总之,虽然《失乐园》的崇高性能震撼人的心魄,甚至令人胆战心惊,但是这并不等于莎剧中那种更贴近于俗世生活的“激情”。
在约翰逊的术语体系中,“激情”一词,较接近于丹尼斯的“俗常的激情”,而“崇高”产生的心理效果,则大抵相当“高扬的激情”。约翰逊在根本上将弥尔顿作品中“激情”的缺失归结为诗人狂傲独尊,睥睨天下的人格。当然,这种缺失对诗人作品的艺术品格的影响并不相同。以《复乐园》和《力士参孙》为例,约翰逊对前者的评价要稍高于后者,部分是因为他认为前人过于贬低《复乐园》,抬高《力士参孙》,自己有必要作一纠正。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俗世激情的缺失对不同题材的创作的影响不尽相同。约翰逊暗示《复乐园》和《失乐园》一样,也具有“丰沛大气的想象和崇高的智慧理念”[3]292。这是肯定弥尔顿的心智脱离了俗常现实和人世激情的束缚,对诗歌创作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但评论《力士参孙》,约翰逊偏向于强调这种脱离可能引向的另一潜在极端:自闭于书斋之中;专注于宏大的政治、宗教问题;疏远日常生活的人和事;必然会缩小作家的写作空间。既然诗人描摹不出现实生活中微妙复杂的人性,也就难以创作出吸引读者兴趣的戏剧作品。约翰逊显然认为《力士参孙》不受好评,不应归咎于读者的素质不高,这其实等于否定了威廉·梅森在1753年的观点[4]225-226。
当约翰逊说弥尔顿其人其作缺乏人情味的时候,他其实也在谈论作家应如何处理文学写作与人生体验的关系。约翰逊的态度可以用《漫游者》第4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作家“除了应具备可从书本获取的学识以外,还需走出闭门造车的状态,从广结知交,人事往来中获取人生的阅历,并学会精细入微地观察世事”[9]20-21。这就是他对很多作家的罗曼司和田园诗感到不满的缘故:这些作家都表现出了“对自然一无所知,对生活一窍不通”[9]20,经常让体裁所规定的套路替代了真情的表达和对现实的模仿。约翰逊在《漫游者》第37篇中指出了田园诗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只要情境有所需要,诗人们就会急不可耐地口诉悲情、口吐欢言;荒唐的事自然总是前后相连,前仆后继,到最后作品完全不顾生活与自然的原状,充斥着神话典故、惊人的虚构和……不受激情或理性左右的情感”[9]244-245。这就是为什么约翰逊会断言弥尔顿的田园挽诗《利西达斯》不是“真实激情的流露,因为怀有真情,就不会追逐生僻的典故和晦涩的意思”,“这首诗里没有真实,也就没有自然”[3]278,悲悼的方式“无法引人共鸣”[3]279。约翰逊认为,弥尔顿既是在现代语境中写悼念少年同学的诗歌,就应注重表现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但是《利西达斯》显然套路多于真情。菲克斯指出,弥尔顿采用田园挽歌的体裁以及造作的技巧,可能是他一向对其他个体兴趣寡淡的表现,目的是要让自我及诗才在读者意识中凸显出来,这对写过《悼念罗伯特·莱维特医生之死》这样一首重在回顾好友生前美德的约翰逊而言,实在是难以接受的[2]254。
弥尔顿唯我独大的心理和崇高才智造成他作品中人情味的欠缺,这继而影响到了诗人在《利西达斯》这类小诗上的总体表现。约翰逊将弥尔顿比作一头不擅长与幼狮戏耍的威猛雄狮:“弥尔顿从没学会把小事做得漂亮;他看不上温文圆融这类较温和的品质;他是一头巨狮,笨手笨脚,不知怎么哄弄幼崽”[3]278。约翰逊的比喻暗示弥尔顿心气高傲,才气高迈,独立于一时,虽肯纡尊降贵烹制小诗,却不知如何把握力道,做得圆融漂亮。弥尔顿这头“文学巨狮”没有“哄弄”好的作品,至少包括《利西达斯》和十四行诗等小作品。约翰逊说弥尔顿的十四行诗不值得费笔墨去评论,因为“其中最好的,也只能说是不坏”[3]282。约翰逊其实要纠正的是18世纪批评家,如约瑟夫·沃顿[4]232-233,因为爱屋及乌过高地肯定除了《失乐园》以外的作品的现象。约翰逊在传记中指出,那些欣赏弥尔顿才华的人,往往“曲解自己的判断,去错误地嘉许他的小作品”[3]278。在评论《利西达斯》时,约翰逊声言,“要是不知道出自谁笔下,大概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读《利西达斯》时很愉快”[3]279。其中的潜台词是如今的读者会喜欢读这首诗,高捧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出自《失乐园》的作者的笔下。论及《复乐园》,约翰逊也说,如果这部诗“不是弥尔顿,而是某位模仿者所作,它理应获得并且能获得全世界的称赞”[3]292。换句话说,这部诗出自弥尔顿这样的大诗人之手,就不值得惊叹了。
三、后世批评家的呼应
约翰逊对弥尔顿诗歌和人格缺憾的评判,虽然受到很多18世纪评论家的抨击[11],但是仍然被19、20世纪的重要批评家、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例如,约翰逊总结《失乐园》的阅读感受时,指出这部诗给人一种欲离其而去,离去后又不愿再复返的隔阂感和沉重感。这种感受预示着19世纪的读者在思想情感上与这部作品渐行渐远的趋势。维多利亚时期的牧师兼作家马克·帕蒂森就曾在1879年专论弥尔顿的册子中,总结了19世纪末英国人阅读《失乐园》时的直觉感受:“如果说作为诗歌语言的宝库,《失乐园》的魅力与日俱增的话,作为神圣真理的仓库,它的影响则已大幅下降……这部诗所蕴含的生命力之所以衰败,说来奇怪,恰恰是与弥尔顿为确保永传不朽而选择的题材有关。不满足于成为凡人的诗人,不满足于描摹人类的激情和日常的事件,弥尔顿渴望要呈现整个人类的命运,讲述创世的故事,展现天堂与地狱的大会……犹太人的经书对英国男男女女的想象的影响竟有衰弱的一日,对弥尔顿而言,实在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个进程确实已经开始了。”[12]帕蒂森在书中其他地方还指出,俗世人的欲望、激情、善恶、雄心抱负,是比任何神学体系都更稳固的创作基础[12]200。由此可见,在帕蒂森看来,弥尔顿成为鲜有人问津的作家,与他作品的题材脱离世俗生活,神学思想与现代人存在隔阂密切相关。如果说约翰逊认为阅读《失乐园》是一种需要去承担、却并不好忍受的义务,那么100年后帕蒂森则声称他同时代的人已经抛弃了这种义务;如果说约翰逊的行文透露出离开导师后虽得解脱却仍想回来的意思,帕蒂森则坦言维多利亚人为寻找自己的亲密同伴已经一去不复返。约翰逊关于《失乐园》作品缺憾的直觉感受和批评意见,指向了19世纪英国读者大众对弥尔顿的态度将要逐渐发生的转变。
约翰逊对《力士参孙》的批评也得到了20世纪批评家T·S·艾略特的呼应。艾略特在文章中含蓄指出,力士参孙的题材与弥尔顿的才情十分相宜,却没有在他的手下变成一部杰作,与弥尔顿对“人类的个体兴趣索然,且缺少了解”有关系[13]。但这样的问题是弥尔顿在创作《失乐园》时所无需面对的:像亚当和夏娃这类的角色,虽然不乏世上男女的心理特征,但他们却不能算是“普通的俗子”,他们属于某种“原型”[13]322;描摹他们,不需要那种“对人类的兴趣”,那种“源自于对世上男女充满爱意的体察的理解”[13]321;相对而言,弥尔顿更擅长呈现摩洛克、彼勒、玛门这类代表不同“癖性”(humor)的角色[13]322。艾略特的这些论断显然是对约翰逊的观点的重新表述,弥尔顿“对人性知而不详,从未细察个性之间有何细微差别,也从未细察激情投合时所起的作用,或激情相抵触所引发的迷乱”[3]293。可以说艾略特对弥尔顿性情、才情以及诗歌局限的评判,很大程度受到了约翰逊的影响。
四、结 语
约翰逊评判弥尔顿的诗歌作品,常会引用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法则和模式。他检视《失乐园》就运用了勒·博叙的史诗理论框架,与艾迪生在《旁观者》系列文章中的立论框架一致,大体按“寓意”、“故事情节”、“人物”、“思想情感”、“语言”等范畴进行评判[14]。但在此过程中,约翰逊的身份经常会从手持批评戒尺、文化素养很高的评论家转变为更看重直觉感受和个人兴味的普通读者。他批判弥尔顿的诗歌作品缺乏人的情味,就是这种普通读者立场的体现。约翰逊所谓的“普通读者”,并不完全等同于他那个时代所有消费书籍的读者的总和,而是他有选择、有目的进行塑造后的群体。正如阿尔文·柯南所说,这个群体是经过启蒙的、充满理性的世界人,他们浓缩了广大读者最优秀的品质,如“良好的判断力、基本的人性、对永恒的社会与经验真理的意识”[15]。正是对普通读者意识的强调,使约翰逊的评判带有可令人亲近和相信的真诚态度。而正因为这样的真诚,他的批评才超越了之前18世纪新古典主义批评家,并得到了包括艾略特在内的后世批评家的认同和接受。
[1]Clingham G.Another and the same:Johnson's dryden[G]//Earl Miner.Literary Transmission and Authorit y:Dryden and Other Writ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21-159.
[2]Fix S.Distant genius:Johnson and the art of milton's life[J].Modern Philology,1984,81(3):244-264.
[3]Johnson S.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English Poets[M].Oxford:Clarendon Press,2006:246.
[4]John T S.The Critical Heritage:John Milton[M].London:Routlege,1995.
[5]Ashfield A,Peter B.The Sublime:AReader in British Eighteenth-Century Aesthetic Theo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35.
[6]Thorpe J.Milton Criticism:Selections from Four Centuries[M].New York:Octagon Books Inc.,1950:62.
[7]Monk SH.The Sublime:AStudy of Critical Theories in XVIII-Century England[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78-80.
[8]Morris D B.The Religious Sublime:Christian Poet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in 18thCentury England[M].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2:82-85.
[9]Johnson S.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M].New York:Prafraets Press Troy,1903:329.
[10]Johnson S.A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Heidelberg:Joseph Engelmann,1828:168.
[11]Boulton JT.Samuel Johnson:The Critical Heritage[M].London:Routledge,1971:253-269.
[12]Pattison M.Milt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99-200.
[13]Eliot T S.Selected Essays[M].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32:321.
[14]Addison J.Addison's Criticisms on Paradise Lost[M].New York:G.E.Stechert& Co.,1926:1-28.
[15]Kernan A.Samuel Johnson and the Impact of Print[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