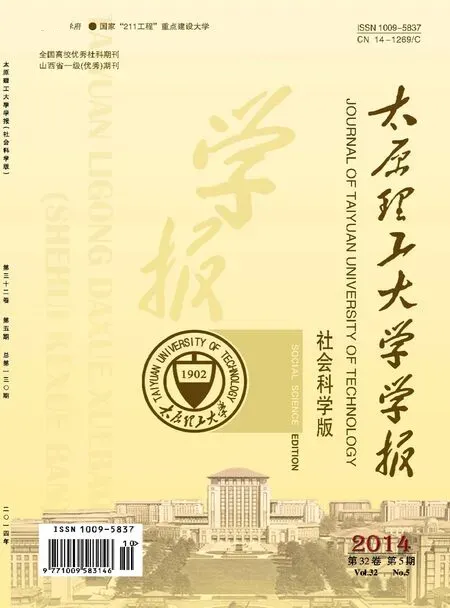罪刑法定原则的扭曲与再启蒙
蔡淮涛
(1.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安阳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一、中国语境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扭曲
罪刑法定不仅仅是一项刑法铁则,也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当然也是刑法学充满魅力的永恒课题。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罪刑法定的立法化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的现实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与法律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总有一定的差异。罪刑法定原则虽然被视作刑法领域的普适原则,但其在不同国家的命运却有所不同。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为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1]。 三权分立学说的核心观点是:三权分立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只有划分国家权力,国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才能得到保障。根据三权分立学说,立法机关依照正当的立法程序制定法律,这种法律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普遍的约束力;司法机关必须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合法的判决;行政机关必须认真执行司法机关作出的最后判决,不得非法变更。被称为现代刑法学之父的费尔巴哈在其提出的著名的心理强制说的基础上,于1801年将罪刑法定主义简洁地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根据费氏的主张,必须事先以法律明文规定犯罪的法律后果,使理性的人们能够预测犯罪后所受到的刑罚处罚,从而形成心理上的强制,才能够预防犯罪。很显然,费尔巴哈的以心理强制说为基础的罪刑法定主义之所以能够保障国民的自由,就在于其实质上隐含了预测可能性的思想。
由于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不能令人信服地得出罪刑法定的必然结论,所以学者们认为其只具有理论上的沿革意义,而不具有现实意义。现在刑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是比较妥当的。罪刑法定原则是针对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断而提出来的。针对封建时代罪刑擅断、国民随时可能遭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的事实,启蒙思想家们挖空心思地提出了种种理论假设。启蒙思想家们敏锐地认识到罪刑擅断给国民造成的痛苦最为严厉,因此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保障国民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罪刑法定,禁止罪刑擅断。没有罪刑法定原则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法治概念[2]。 由此可见,罪刑法定原则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是为了防止罪刑擅断而用来保障人权的。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几百年来,可以说,在绝大多数国家罪刑法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3]。
相较之下,由于我国长久缺乏法治的传统,加之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时间比较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司法人员较低素质的制约,导致尽管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在立法中还是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之中,都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相当程度的扭曲。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扭曲。
(一)对《刑法》第3条的扭曲解读
在经过一番艰难的选择后,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我国有些刑法学者在承认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刑法》第3条作出了独特的解读。例如,有学者将有中国特色的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前半段称为积极的罪刑法定主义,将后半段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主义,认为积极的罪刑法定主义从积极方面要求正确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并且认为这种二元统一的罪刑法定主义既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4]。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背离罪刑法定主义基本精神的扭曲解读,尽管《刑法》第3条的表述不同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但并不能就据此认为我国刑法存在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主义与消极的罪刑法定主义之分,实质上,《刑法》第3条的规定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对此,我国的立法机关曾经明确指出:第3条前半段的含义是只有法律将某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5]。 很显然,如果对此作反对解释的话,则《刑法》第3条前半段应该理解为: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行为的,不能定罪判刑,这和《刑法》第3条后半段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作出这种扭曲解读的一个潜在危险是,会不适当地夸大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有意无意地忽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而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根本的价值蕴涵在于强调对人权的保障。所以,我们要避免作出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基本精神的扭曲解读。
(二)类推解释以隐秘的方式施行且难以杜绝
刑法理论上,曾经有学者反对对刑法进行解释,比如,贝卡利亚就曾经异常鲜明地提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诚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固然是最为理想的,但任何刑法都有解释的必要,甚至若不解释,刑法就根本无法适用。在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于刑法的适用而言,进行刑法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对刑法进行恣意的解释。否则就会出现贝卡利亚所言:“不幸者的生活和自由成了荒谬推理的牺牲品,或者成了某个法官情绪冲动的牺牲品。”[6]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价值蕴涵角度看,是坚决反对进行类推解释的,但是,在我国刑法学界仍有少数学者对类推解释情有独钟。如有学者认为:“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是相通的。”刑法不仅具有保障功能,也具有保护功能,刑法的保护功能“使类推解释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该学者进而认为:“类推解释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实与援引的条文的明文规定具有类似性为前提的。该类似性反映到犯罪构成上,就是其构成要件在总体上相类似。因此,类推解释是依据立法精神和原则对犯罪构成要件,即法律的明文规定作实质判断的结果。这一结果虽然超出刑法某一条文的意思范围,但并不违背立法的总的精神。”[7]还有学者别出心裁地提出,在刑法中明文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之后,应禁止司法性质的类推解释,严格限制立法性质的类推解释[8]。 在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后,尽管没有学者再公开鼓吹类推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另一种扭曲的适用,类推解释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施行,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类推解释时有出现。例如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肖永灵投寄虚假危险物品案就很典型*案例来源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132号。。 该判决适用的是我国《刑法》第114条的规定。对于这个案件,我国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的炭疽杆菌”一案中,法院将“投寄虚假的炭疽杆菌”行为解释为《刑法》第114条中的危险方法,这既不符合此种行为的性质,也不符合《刑法》第114条的立法旨趣,已经超越了合理解释的界限,而具有明显的类推适用刑法的性质[9]。 陈兴良教授也指出:“投放虚假炭疽杆菌的行为在客观上根本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它与投寄炭疽杆菌行为的性质根本不同,连类似关系都不存在,称之为类推适用已经是一种客气的说法。”[10]
显而易见,肖永灵案的判决是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后来的《刑法修正案(三)》的立法补充规定充分说明这个判决是错误的[5]。 由此可见,尽管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罪刑法定的司法化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罪刑法定司法化之路途还很遥远,类推解释还阴魂不散地困扰着司法实践,也严重扭曲着罪刑法定原则。
(三)错误地理解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
明确性是这样一种基本要求,“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11]。 理论上一般认为,将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原则实质的侧面,源于美国的“因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因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不仅仅在美国得到了承认,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确认。
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和国民自由的角度而论,刑法规定得越明确越有利于保障国民自由。但是,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又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明确,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明确。因为“刑事立法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明确,要求极度明确的刑法只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动辄对刑法不明确提出批评是值得反思的”[12]。 在刑法中贯彻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扭曲理解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现象,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法官常常将明确性视为立法者的任务,并常常以立法不明确为借口而不敢解释刑法,僵硬司法。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2年9月25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80条第2款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1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此,张明楷教授认为:“之所以作出这种司法解释,是因为解释者认为,诉讼诈骗行为并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为,这是解释能力低下的表现,而不是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表现”。我们认为,张明楷教授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司法解释,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者扭曲地理解明确性原则,认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规定的不明确,因而对于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只能求助于立法或司法解释,法官不敢主动解释刑法,导致司法僵化。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再启蒙
“启蒙”是近代反对那些把一切都混淆成一团迷雾的模糊观念的斗争观念。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我解释涉及一种被比喻为光的理性,这种理性主动“照亮”了世界。康德在《70年代人类学讲座》的草稿中写道:“一个被照亮的(经过启蒙的,需要清晰观念的)时代,一个清晰的(经过启蒙的)头脑。”[13]由此可见,启蒙就是一种从思想上的混沌状态得以廓清的过程。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需要对罪刑法定原则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再启蒙。
(一)应该牢固树立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保障人权的观念
在我国,罪刑法定的立法化任务已经完成,但是罪刑法定主义并未深入人们的内心,尽管就刑法规范的性质至今在理论上还存有不小的争议,但现今多数学者认为刑法规范一方面是行为规范,具有约束公民行为的机能;另一方面,刑法规范又是裁判规范,是司法机关据以定罪量刑不可逾越的准则。司法机关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对一个犯罪行为如何处罚,都应当并且只能以刑法规范为准绳。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是否把人权保障放在首要位置,是法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刑罚的根本区别之所在[10]。 在我国,当前应更加注重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功能,令人欣喜的是我国已把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宪法,因此我们应理所当然地把保障人权作为刑法的第一要义,牢固树立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保障人权的观念。相应的对于我国《刑法》第3条的理解也应认为其仅仅具有消极限制的机能而不兼具积极促进机能,更不能把《刑法》第3条视为有中国特色的规定,把其理解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和消极的罪刑法定的二元统一。
既然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保护人权,而要真正实现对人权的有效保障,避免刑罚的恣意,就必须树立罪刑法定原则既约束立法权又约束司法权的观念。根据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原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要求刑事立法采用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同样的,基于国民预测可能性原理,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也就理所当然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的要求。刑罚法规只能将具有实质的处罚根据或者说值得处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的基本要求。实行法治并不是说一切琐细的事都由法律来处理,更不意味着琐细之事要由刑法来处理,西方法律格言“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就暗合了这个意思。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独立品性,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发挥最后一道屏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刑法要具有补充性,只有当穷尽其他手段尚不能充分抑制某种法益侵害行为时,才能动用刑法。换言之,刑法谦抑性包含了补充性、不完整性和宽容性。根据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立法者要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只能把严重侵害法益的值得用刑罚处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二)严格禁止类推解释,合理界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要求来看,要求禁止一切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因为类推解释的基础在于事物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任何事物之间总有某些程度的相同之处,有相同之处,我们就说它们之间具有相似性,如此来看,则任何行为都会有与刑法规定的行为的某些相似之处,都有招致刑罚处罚的风险。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要求来看,也应禁止类推解释,刑法是通过文字的形式形成刑罚规范来指引人们的行为的,而根据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原理,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内作出解释,才不会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而类推解释的本质就在于对刑法用语的解释超出了字面的可能含义范围,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这样就会出现要么造成行为萎缩的后果,要么造成公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也会招致刑罚处罚的后果。由此以观,无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还是实质侧面,都天然地排斥类推解释。
在民法等其他法领域,类推被认为是一种正当的法律制度,类推对民法等能起到补充的作用,有助于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但刑法却不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就必然地要排斥类推解释,这是由刑法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刑法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的限制或剥夺,如果允许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通过类推的方法而适用的话,将使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处于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但令人遗憾的是,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类推解释。例如,德国学者考夫曼就认为类推解释并不必然与罪刑法定主义相违背[14]。 我国在1997年《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尽管没有学者公然支持类推解释,但类推解释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销声匿迹,这是值得我们加以警惕的。
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要正确的界分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防止以扩大解释之名行类推解释之实。理论上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尽管严格禁止类推解释,但并不禁止扩大解释。如何区分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是一道摆在刑罚学者面前的世界性难题。有学者认为,“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的区别是毫厘之差,其区别的标准其实也就是想法的不同”[15]。也有学者认为,“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在说明原理上二者甚至可以互换”[16]。 我们不认可上述学者的论断,因为如果真如这些学者所言,那么区分出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不过是“近代法治的一个美丽谎言”[17]。 果如是刑法上禁止类推解释而允许扩大解释,也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已。冯军教授认为:“在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上,中国刑法学者还面临着独自的困境。”[18]尽管合理地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存在相当的难度,但只要我们认真廓清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的含义,以理性的态度,根据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是可以符合目的地区分二者的。我们原则上赞同冯军教授所提出来的合理区分二者的操作路径[18]。
(三)正确地理解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
不明确的法律是非正义的法律。应当承认,中国1997年《刑法》为实现刑法的明确性作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中国特有的刑法立法方式,不可能对犯罪的规定做到完全的明确。另外,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刑法明确性,作为一种立法和司法适用原则,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明确性。事实上,从多数主张明确性原则的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以刑罚法规规定的不明确为理由而判定其无效的情况并不多,在多数情况下,法院是通过解释使被认为不明确的规定变得明确起来的[19]。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理解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不能要求立法者对刑罚法规规定的绝对明确,因为要求刑法明确到无需解释的程度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法律使用明确的概念的情形,而且真正明确的,不需要解释、也根本不能解释的只是数字概念”[20]。 一味地要求刑罚法规的绝对的明确性,在我国还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弊端,那就是导致法官借口刑罚法规规定的不明确而不敢合理的解释刑法。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司法僵化,法官的解释和创造能力低下。我们认为,刑法的适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释刑法的过程,而解释刑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刑法明确,实现刑法的明确性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共同任务。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都要善于运用各种刑法解释方法,通过解释使相对不明确的刑法规定变得明确,当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三、 结语
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今世界各国几乎都被奉为一项神圣的法治原则,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在于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因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由法律以文字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就万事大吉,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首先需要对它有正确的解读。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但刑法施行十几年来,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却不太尽人意,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不少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扭曲与误读,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认为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既包含了积极的罪行法定也包含了消极的罪刑法定,从而有意无意地弱化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功能;背离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类推解释远未绝迹,反而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出现;错误地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仅仅是对刑事司法的要求而不包含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对刑法的明确性原则的错误理解。正是由于存在诸多扭曲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才导致罪刑法定原则保障国民自由和人权的功能大打折扣,为了更好地发挥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功能,尤其是更好地保障人权,需要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再启蒙,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观念,对《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作出正确的解读;坚决摒弃类推解释,合理界分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要求的明确性原则有正确的认识,要善于通过合理的刑法解释使不明确的刑法规定变得明确。
参考文献:
[1]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东京:有斐阁,1997:56.
[2] 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0.
[4] 何秉松.刑法学教科书:上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7.
[5] 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604.
[6]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 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3.
[7] 薛瑞麟.论刑法中的类推解释[J].中国法学,1995(3):77.
[8] 陈泽宪.刑法修改中的罪行法定问题[J].法学研究,1996(6):84-90.
[9] 周少华.罪刑法定在刑事司法中的命运——由一则案例引出的法律思考[J].法学研究,2003(2):82-103.
[10] 陈兴良.罪行法定主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8,41.
[11]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4.
[12] 杨剑波.刑法明确性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72.
[13] [德]曼弗雷德·盖尔.康德的世界[M].黄文前,张红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78.
[14] [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4.
[15] [日]木村鬼二.刑法学词典[M].顾肖荣,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83.
[16] 黎 宏.禁止类推解释之质疑[J].法学评论,2008(5):45-50.
[17] 吴丙新.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近代法治的一个美丽谎言[J].当代法学,2008(6):48-53.
[18] 梁根林.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7,166-170.
[19] 黎 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0.
[20]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