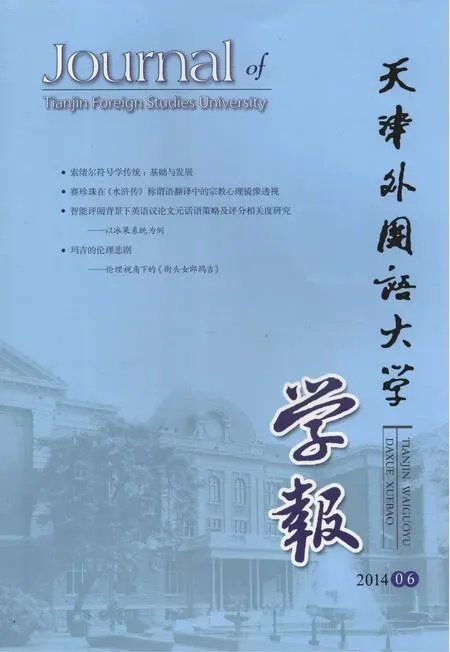玛吉的伦理悲剧——伦理视角下的《街头女郎玛吉》
陈向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16)
一、引言
19世纪末美国文坛“金童子”斯蒂芬·克莱恩的代表作之一《街头女郎玛吉》(以下简称《玛吉》),描述一位城市贫民窟的少女被迫沦落街头为妓并最终自尽的悲惨故事。以往研究对此悲剧说法各异,但基本没有超出自然主义生存论和决定论的框架,玛吉的命运被归结为“生理遗传”和贫民窟环境。作者本人的话常被用来作为论证材料:“《玛吉》企图说明,在世界上,环境是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不顾人们的愿望,决定着人们的命运。”(Katz,1979:1)实际上,克莱恩虽然把玛吉定位于贫民窟,却未按照环境决定论观念描述她。换言之,发生悲剧的环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物质生活环境。伦理道德层面的解读,应更能准确把握玛吉悲剧的实质。有知名学者提到小说的道德因素,如布雷南(Brennan,1972:323)提到贫民窟环境中的道德缺失,拉弗朗(LaFrance, 1972:35)指出,玛吉的悲剧命运源于其他人物道德上的怯懦和不诚实。著名评论家派泽(Pizer,1972:335)也谈到决定人物命运的力量并非环境,而是错误的道德理念以及自欺欺人的价值观。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对作品中的道德倾向进行单一的价值判断,没有对其中的道德现象作系统的分析、阐释。本文借鉴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对该小说进行重新解读,认为玛吉悲剧是家庭伦理、社会人际伦理、爱情伦理嬗变带来的结果,本质上是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天性与生活中的伦理枷锁发生冲突造成的伦理悲剧。通过再现19世纪末美国转型时期社会伦理关系状况,作者意在引发人们反思社会伦理道德现状,思考如何构建和谐平衡的社会伦理环境。
二、伦理冲突与伦理悲剧
小说《玛吉》主人公走向悲剧命运的核心事件是她的未婚同居、丧失贞洁等伦理失范行为。从小说叙述结构看,该事件出现在位于中间的第九、十章,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从小说人物命运看,该事件充当着转折作用,使玛吉生活每况愈下,遭受非议谴责,被家庭和社会抛弃,最终毁灭。伦理秩序的破坏者遭到惩罚不足为怪,但玛吉为何触犯伦理禁忌却不应该忽略不计。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运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倾向于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聂珍钊,2006:16)。因此,只有返回玛吉所处的伦理语境中,审视其动机和目的,才能从道德层面对其行为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
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那里的人们伦理意识淡漠,道德亏空、人性蜕变,但玛吉仍然保有强烈的道德理想和追求。克莱恩以细腻、客观的记录手法描述了贫民窟环境,但他刻意突出的不是物质环境,而是伦理道德环境。小说以孩子们叫骂、打斗场面开始就预示着这里罪恶横生,如酗酒、斗殴、诱骗、卖淫等,人们行为任凭本能欲望驱使,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玛吉的家里“拳头说了算”,是贫民窟的缩影,从父母兄弟那儿得不到丁点儿温暖,找不到自尊,物质保障和情感依托都只是奢望。虽成长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她并未受家人、社会暴力倾向和颓废人生的影响。克莱恩(1999:15)将她描述为“在泥潭里长成了一朵花”,“成为公寓区一个极其罕见的奇迹”,“朗姆巷的污垢似乎与她是绝缘的。”实际上,她即便沦落街头为妓时也没有堕落,成为像内尔那样无所顾忌的妓女,仍有着很强的羞耻、内疚感,甚至寻求像牧师那样高尚者的帮助,也正是这份道德内疚感使她最终选择了自尽。派泽(Pizer,1966:121)认为:“玛吉本身的角色几乎是一个没有受外界邪恶势力污染的内心纯净的表现主义的象征符号。”作者意在表明生活环境没有使她自然地堕落,相反,她的身上依然澎湃着生命的激情,内心充满着自由幸福生活的理想和向善求善的道德追求。
与皮特交往正体现出她身上追求爱情、追求生命的自在意志和不屈精神,也应该是提升道德的一种表现。花季少女情窦初开,渴望真挚的爱情,主观上受自然情欲的驱使,希望与皮特发展正常恋情,托付终身,获得稳定的情感和物质依靠,这种自然情爱的需求应该是纯洁真诚的,是对快乐幸福生活的追求。按照费尔巴哈(1984:433)的观点,“道德的原则是幸福”,“善就是肯定追求幸福的愿望”。“爱情是一种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感,它使人上升到新的道德高度,使人更强烈地意识到生活的美好和自己的责任感。”(罗国杰,1989:292)这种追求本无可非议,更谈不上与触犯伦理的不道德行为相系。
然而,生活在社会伦理之中的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伦理和道德的约束和影响。著名伦理学学者诺兰(1988:19)认为:“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内,道德选择的范围是狭窄的。多数个人可以进行的选择是有限的,他们的观念是命定的。”对玛吉而言,在家恪守世俗伦理规范,依靠家庭实现自己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就只剩下爱情婚姻了。在残酷现实和自由梦想的撕扯下,玛吉焦虑、挣扎、内心充满矛盾、痛苦,深陷伦理困境。在目睹母兄打斗留下的满屋家具残骸,面对着无情辱骂自己的母亲,她“忧心忡忡”,“久久地望着母亲”,但最终内心强烈的理想生活欲求超越了伦理的限制,使她走出了家庭,选择与情人同居,因此触犯禁忌,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克莱恩在描述这一过程时对玛吉未有丝毫的苛责,而且竭力突出她的无助无望无奈感,意在使读者意识到正是她追求自由幸福的天性与生活中的伦理枷锁发生冲突引发了她的悲剧。悲剧的一面是生命本能的合理要求,一面是强大无形的伦理力量,它反映了个体生命自由与理性伦理文明发生冲突的人类永恒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19世纪末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特定的伦理道德情境。玛吉追求爱情、自由,她的行为绝没有给他人带来任何痛苦和不幸,无疑体现出善的意志,但这种善意没有结善果,相反却结出恶果,遭到了惩罚。读者在对主人公身处逆境仍然求索的不屈精神发出赞叹,为她的不幸扼腕之时,不免会谴责她所处伦理环境的罪恶、质疑当时伦理规范的合理性、正当性。
三、伦理嬗变与伦理悲剧
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伦理“主要指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和“在这种秩序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规范”(聂珍钊,2010:17)。可将其分为两层含义:一指客观的伦理关系和秩序或伦理之实然,即指人与人之间的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上下尊卑的秩序结构;二指主观的伦理德性或伦理之应然,指为维护上述既定的伦理关系和秩序,人们所应持守的以一定价值信念为核心的伦理理则、道德规约、情感义务等,亦即狭义上的道德。道德有时与伦理关系和秩序的客观要求相符,有时与其相悖,从而导致既定伦理秩序的打破和超越,形成新的伦理体系和结构。克莱恩主要采用视角(人物视角和叙述人视角)对照的叙事手法展示人物的道德感知,描述他们的道德行为和具体情境中的道德选择,通过视角反差揭示人物的道德感知与所处伦理现实的偏离,心性操守与外在的道德规范悖谬,表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几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嬗变,并引发严重的道德危机,造成主人公的悲剧。
1 爱的缺乏——家庭伦理关系的疏离和异化
玛吉的悲剧首先源于缺乏爱的家庭伦理环境。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每个人的伦理之源都始于家庭。家庭伦理主要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爱是维系家庭伦理的纽带。然而,玛吉家中因爱的缺失,成员关系疏离、冷漠,形成悲剧的土壤。
黑格尔(1982:177)指出:“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 玛吉父母的婚姻显然是缺乏爱的,他们之间连正常的沟通交流都难以进行,更谈不上夫妻之道,即相互尊重、理解、包容等。克莱恩通过夫妻间诅咒式对话和粗暴打斗场景来呈现他们的关系。无休止的吵骂和厮打,酗酒成性,粗暴野蛮,体现更多的是兽性原欲而非人性理智。这样的夫妻关系只能造就 地狱,正如玛吉父亲在酒吧向人倾诉时说:“我家简直是座活地狱!我干啥来这里喝酒?就因为我家里是座活地狱!”(克莱恩,1999:10)家成了暴力的温床,远非避风的港湾,无法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正常环境。
亲子关系的畸变使子女陷入不同的悲剧命运。父母子女间是一种天然的血亲关系,父母爱孩子天经地义,是一种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但玛吉父母的这种伦理意识十分淡漠,缺乏对孩子起码的关爱和亲情。克莱恩通过叙述者客观的口吻描述了母亲疯狂的意欲毁灭一切的暴力行径和孩子们对她产生的极度恐惧感,反映出他们畸变的亲子关系。在玛吉及其兄弟幼小的心灵里,母亲成了邪恶的化身,是恶棍、魔鬼、洪水猛兽,他们也因此遭遇了不同厄运。最小的汤米早夭,吉米由于深受父母不良习性的影响,成年后同样崇尚暴力,并酗酒滋事,引诱女人,成了与警察监狱打交道的常客。“对于这个世界,他从来未怀过敬意,因为他自小开始,委实不曾有过任何幻想,一切幻想早被现实敲得粉碎了。”(同上:12)玛吉虽竭尽全力寻找出路,追求幸福,但悲剧终未幸免。
母亲对传统道德信条的盲从将玛吉逼上了绝路。玛吉母亲一方面行为任凭本能驱使,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显现出她真实的兽性;另一方面盲目跟随周围人,遵循那些不切实际的传统道德信条,扮演着伪道士的角色,尽露其虚伪的人性。当遭皮特抛弃的玛吉回家寻求保护时,母亲超然事外,认为玛吉未婚同居丢人现眼,并当着围观街坊邻居的面,“活像个油嘴滑舌的讲解员”,对女儿极尽羞辱和嘲弄,不顾及母女之情,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同情心。在获知玛吉死讯时,她表现得异常冷漠,竟认为玛吉本就该死:“她的生活就是祸根,她的行为令人羞耻……她的罪恶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她应该死。”(克莱恩,1999:63)这位母亲的话语充满道德的说教,但叙述者强烈的反讽语调揭示了她的道德感知严重偏离事实。女儿当初离家出走,她是直接的责任人,她的所作所为本身已破坏最基本的人伦。因此,她的道德只是一种装腔作势,正是这种伪善迫使玛吉一步步走上了不归路。
玛吉和吉米兄妹关系经历了从正常走向异化的过程。儿时玛吉照顾吉米和后来夭折的汤米,关爱他们。在父母争吵打架时,玛吉常常是唯一关心哥哥的人。吉米尽管对妹妹比较粗暴,但还能和妹妹相依为命,共同驱赶母亲造成的恐惧感。成年后的吉米深受周围伦理环境的影响,人性一步步堕落,对妹妹越来越疏远,以致冷漠无情。在遭弃回家的玛吉求助于他时,吉米竟也充当起正人君子,道貌岸然,认为妹妹有辱家风。“‘嗯,你是什么东西?’他说,鄙夷地撅着嘴唇。他的眉梢露出尊道崇德的光芒,两手摆来摆去,表示他生怕被玷污。”(同上:52)叙述人讽刺的声音和吉米话语中透出的自以为是形成巨大的张力,张力之下是人物真性的暴露。和母亲一样抱着虚幻道德观的吉米丝毫不顾念兄妹手足之情,间接地成为妹妹悲剧的帮凶。
在玛吉生活的家中,家的内涵发生了质变,缺乏温存和关爱,有的只是暴力酒精滋生的窳败、堕落和伪道学铸成的铁石心肠。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紧张对立,亲情之爱剥离、扭曲,家庭伦理异化。玛吉无法享受人伦之欢、天伦之乐,也容不下她追求幸福生活的夙愿。
2 真的丧失——社会伦理关系的冷漠和虚假
家庭伦理关系固然是导致玛吉悲剧的重要原因,但社会伦理环境的恶化也难辞其咎。人是群居动物,身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真诚友善地对待他周围的人,他与周围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利互惠而不是虚假、敌对的关系,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伦理。但在包尔瑞贫民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却背离这一基本伦理。
邻里关系冷漠紧张,甚至幸灾乐祸。克莱恩为表现这种关系,一方面用战场和监狱两个主要形象来描绘包儿瑞贫民窟,但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与道德相差甚远,另一方面大量着墨于围观人群。小说伊始,贫民窟里两个街道的孩子们在一起野蛮地战斗,此时公寓周围的大人们却当起了看客,有从公寓窗口探出身子的好奇女人,有停下手中活观战的码头工人。他们中竟没有人出面来阻止孩子们的战斗,只是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好不自在地将其当成乐子。当玛吉家中发生任何事件时,都少不了这些围观的邻居。邻里本应互相关心照顾,和睦相处,而他们却充当着看客,对他人的痛苦甚至死亡漠不关心,还幸灾乐祸,这根本是一种心理上的麻木不仁及伦理道德感的严重缺失。大量“冷静沉着”的围观者本身说明社会充满了暴力、冲突和犯罪,人们已司空见惯,社会已远离理性与道德。
人们彼此虚情假意,缺乏真诚关怀。克莱恩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对玛吉出走和最后自尽的反应。玛吉出走后,他们私底下嘁嘁喳喳,自鸣得意地评头论足,说玛吉生性不正经,勾引男人,伤风败俗等,表面上却又故作关心她,去她家问长问短,打听玛吉的下落,在玛吉事件上推波助澜,对她家人形成道德舆论压力。在他们得知玛吉自尽后,竟都表现出大慈大悲的样子,陪着玛吉的母亲或呻吟悲泣,或“像刀扎似的”号啕大哭。其中一个穿黑袍的女人一边啜泣一边安慰道:“你那误入歧途的可怜孩子离开人世了,玛丽,但愿这是最好的结局。你得宽恕她,亲爱的,你说是吗?宽恕她不听话,宽恕她对做妈的不孝顺,宽恕她缺德丢人。她犯了弥天大罪,如今走了,去受审判啦。”(同上:63)人物的视角使他们自身能站在道德的制高地,自以为品德高尚,行端止正,是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但叙述者充满反讽的叙述则揭露了其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真相。他们拿传统伦理来说事,并非真正相信其合理正当性,只是将其作为抽象的信条,不考虑具体情境而盲目使用。道德是以善为目的,珍视人的生命无疑为大善,为了某些所谓的道德信条而放弃这种大善,显然偏离了道德的正轨,故他们所持的道德正义只是虚假的关于善的想象,实质已经被掏空了。他们已丧失了本真之德,对他人的命运无动于衷,缺乏真诚的关心,甚至没有最起码的怜悯之心。
虚假仁义为表象、情感冷漠为实质的社会让人要么随波逐流,泯灭个性,给他人带来灾难,成为别人悲剧的根源;要么拒绝屈服,艰难抗争,但很可能难逃悲剧命运。在如此恶劣的社会伦理环境中生存,玛吉纵使能逃得出家的小牢笼,也无法逃脱社会的大牢笼。
3 诚的消逝——爱情伦理关系的多变和脆弱
追求爱情幸福是驱使玛吉触犯伦理禁忌的主要动力,爱情伦理的变质是她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青年男女之间相互吸引而真情流露,由此结成的爱情伦理关系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具有感性、激情、欲望的特点,但同时更应该具有理性的本质。弗洛伊德 (1987:223)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凡健康正常的爱情,需依靠两种感情的结合,一是温柔而执著的情,另一种是肉感的欲。”前者显然关涉理性道德性,即爱情内含道德性。爱情之所以具有道德性,在恋爱双方的伦理关系层次上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爱情自身蕴含着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索取与奉献等道德内容,二是爱情关系需要良好的道德情操的维护,忠诚、信任、宽容、尊重等都是爱情不可缺少的道德品质。但小说中的爱情关系则出现明显的本能欲望和道德理性的冲突,其中本能欲望总是冲破理性的防线,占据主导地位。缺乏理性之维的爱情因此变得盲目、脆弱和短暂。
首先,肉欲为主、道德维护不足的爱情必然生变。小说中的恋爱关系具有明显的肉欲倾向。皮特开始与玛吉交往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关注其外在体貌而非性情品格。他对玛吉的言语是轻浮的、挑逗性的。“喂,麦格,我给你的模样迷住了,漂亮死了。”(克莱恩,1999:18)“看在带你去看节目的份上,亲我一下好吗?”(同上:24)皮特恋爱动机不纯,和玛吉在一起只是为了满足肉体欲望,并非为了正常的缔结婚姻。他们的爱情是缺乏道德维护的,皮特引诱玛吉与己同居,事前事后没有丝毫的道德责任感。但两性关系始终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性关系可以直接地看作是基本的道德关系,看作是道德的基础”(费尔巴哈,1984:572)。事前皮特明知自己的不良企图却仍故意为之,事后的所作所为也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受任何伦理道德规范的羁绊。他将早先对玛吉的虚情假义抛之脑后,当玛吉来找他时,他竟寡廉鲜耻地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反倒是她与他过不去,让他丢掉体面。玛吉提醒皮特以前的承诺时,他恼怒不堪,“就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似的”。玛吉说到自己无处可去时,他又“勃然大怒,忍无可忍,认定这是想让他对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情承担责任”(克莱恩,1999:55),最终绝情地关上了门,彻底地摆脱了可怜的玛吉。吉米与哈蒂的恋爱也如出一辙。皮特和吉米之流自私自利、卑鄙无耻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这是一个人伦理道德堕落的赤裸表现。此处情境反讽的使用既传达了作者无声的愤怒,又揭示了爱情的真谛,即建立在外在体貌和肉欲满足基础上的爱情没有道德品性的维护,无根无基,必然多变,不能持久。
其次,情欲失度、理性不足的爱情注定盲目、不可靠。贫穷的物质生活和浅薄的阅历使玛吉对外面的世界缺乏真知灼见。皮特华丽的衣着、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等为玛吉打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满足了怀春少女的浪漫渴望,加之冷漠的家庭造成爱的匮乏,使她很容易陷入情网,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因此,恋爱中的玛吉对对方甚至怀有崇拜心理,过分信任皮特,认为他顶天立地,“简直是个骑士”,“犹如金色的太阳”,相信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正人君子。爱情当然需要以信任为滋养,彼此信任是爱情成长的土壤。但玛吉的信任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缺乏对对方真实个性的理性认知,根本不了解对方是个无耻之徒。实际上,这是痴迷的情欲蒙蔽了清醒的理智,在爱情光环的遮蔽下,理性难辨真伪善恶,对爱人过于信任盲从,看不到他们身上的危险品格,陷入爱情骗局而遭不幸。
小说中的爱情伦理已偏出正常的轨道,最终以离散甚至悲剧收场。归根结底,他们的爱情都缺少了道德的核心内涵——诚之德,即恋人之间对彼此的真心实意、真情实感,表现为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尤其强调实际行动表现出的诚挚、诚心。心与心的沟通需要一道真诚的桥梁,他们的爱情缺少的正是诚之桥梁——真情。
克莱恩通过对贫民窟人物的话语模仿和自己的叙述话语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域来展现玛吉悲剧这一伦理事件,旨在传达他对所处时代变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演变的伦理思考,即亲情、友情、爱情本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却成了一片荒漠。取而代之的是在人的本能、隐蔽的欲望和残酷的行为中,道德遭到了漠视,走向虚无化,社会浸透了伪善。在这种伪善的社会里人们看不到道德、信仰和希望,到处都是巨大而无情的力量,玛吉最终的毁灭是必然的。
四、伦理环境与伦理悲剧
“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归属于她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聂珍钊,2010:19)《玛吉》创作于19世纪末,要深入理解主人公悲剧的根源,还须返回这一特定时期的伦理环境与语境。
社会转型引发的道德危机使玛吉悲剧的发生具有社会必然性。19和20 世纪之交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社会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也标志着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伦理观念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任何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波动甚至混乱。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当时美国社会贫困人数急剧增加,出现大量的贫民窟,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对于这些无法实现基本生命欲求的穷人,求生本能难免触发道德越界,道德会失去其有效性。社会变革在价值取向上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的式微与解体,新的价值体系的萌生与建立需要一个过程。美国农业文明的传统伦理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适应城市文明的新道德规范尚未建立,旧规范与新价值交错并立,常伴有新规则暂时缺位而出现价值失范的局面,人们难免迷茫、惶惑。这种新旧犬牙交错的现状常使得是非不清,善恶难辨,作恶的人未必受到惩罚,善良的人也未必幸福,道德危机也由此而生。道德权威弱化,道德约束机制脆弱,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这样的社会必然充满悲剧,玛吉的遭遇如此悲剧化乃时代必然。
世纪末盛行于美国的自然主义思潮对《玛吉》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克莱恩受其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是批评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玛吉》也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完完全全的自然主义小说”(Cargill,1941:85)。自然主义者强调人的动物本性,否定人的理性、精神性,认为生存是人类活动的最高目标,人的行为无所谓善恶,传统道德在社会中的地位已被非道德力量取代,宣扬道德地位的无意义性。克莱恩对传统伦理道德向来持批判的态度,他的个人生活也可以为证,如虽出生在宗教家庭,却从不相信宗教,在学生时代就染上了抽烟、酗酒甚至吸毒的恶习,在纽约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与声名不佳的离异妇女科拉·霍恩同居等。他在创作中融入了这些思想,小说大量描绘人们漠视道德的行为,并展现传统道德规范的不合理性。著名批评家沃尔卡特认为,克莱恩 “通过自然主义的再现方式不断地抨击传统价值,说明传统社会道德的概念都是虚假的,因此产生的人类动机都是一种伪装。……他否定体验的整体性,承认感觉的无序性,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旧道德中的秩序观念以及传统道德中的奖惩过程。”(方成,2007:165)玛吉悲剧的刻画是克莱恩的自然主义伦理观使然。
玛吉悲剧的描写离不开克莱恩在纽约时的生活体验、考察和记者经历。在创作该小说之前克莱恩本人曾在纽约贫民窟生活过几年,对那里进行过认真的考察,曼哈顿区南部的贫民区域就是他观察的中心(常耀信,1998:551)。他观察街上形形色色的川流不息的人群、破旧公寓房吵闹的酒徒、面包房前的长队,还有乞丐、警察、街车等。他自己潦倒时去排队领取过救济食品,在下等旅店中过夜。他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在贫民窟的世界里,人们不仅受困于贫乏的物质生活,更为严重的是道德理想丧失,精神颓废堕落。他的短篇甚至中长篇小说均反映了这座城市贫民的生活现状,这在《痛苦的尝试》、《不祥的孩子》、《暴风雨中的人们》等作品中有明显的呈现。他还做过记者,广泛接触到社会的真实面,发现违背伦理道德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并且深刻认识到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过时,它不仅不能阻止日益滋长的不良风气,还极有可能给原本善良的人带来噩耗。克莱恩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说:“我感到,一个作家越接近生活,他就越能够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家。”(Holton, 1972:55)克莱恩深入生活,从社会底层看起,洞察了城市文明背后深刻的道德危机,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中他成功地再现了真实的社会伦理状况,《玛吉》是一幅社会伦理环境的艺术缩影。
五、结语
小说通过对转型时期玛吉这样一个社会底层人物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揭露了社会生活的残酷、伦理价值观的虚伪,唤起人们对现实社会中伦理道德现状的思考,表达了作者对迷失于伦理困境的人们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作家的伦理态度决定了作品的伦理精神。克莱恩在刻画玛吉这个人物时始终充满同情,他正是想借玛吉的经历呼吁人们应拥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灵,去营造更富有人情和人伦的情感空间,期待建立新的合人性、合生命的道德标准,创造和谐的伦理关系,构建平衡的社会伦理环境。“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2010: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玛吉》是一部深刻的伦理小说。
[1] Brennan, J. Ironic and Symbolic Structure in Crane’s Maggie [A]. In T. Gullason (ed.) Stephen Crane’s Career: Perspectives and Evaluations[C].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2.
[2] Cargill, O. Intellectual America: Ideas on the March [M]. New York: Macmillan, 1941.
[3] Holton, M. Cylinder of Vision: The Fiction and Journalistic Writing of Stephen Crane[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Katz, J. The Portable Stephen Crane [M]. New York: Penguine Books, 1979.
[5] LaFrance, M. George’s Mother and the Other Half of Maggie [A]. In J. Katz (ed.) Stephen Crane in Transition[C].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2.
[6] Pizer, D. Realism and Naturalism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6.
[7] Pizer, D. Stephen Crane’s Maggie and American Naturalism[C]. In T. Gullason (ed.) Stephen Crane’s Career: Perspectives and Evaluations[C].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2.
[8] 常耀信. 美国文学史(上册)[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9] 方成. 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化建构与价值传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10]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1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12] 罗国杰.伦理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13]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 2010, (1).
[1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 2006, (2).
[15] 诺兰, R. T.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M]. 姚新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16] 斯蒂芬·克莱恩. 街头女郎玛吉[M]. 孙致礼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1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性爱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