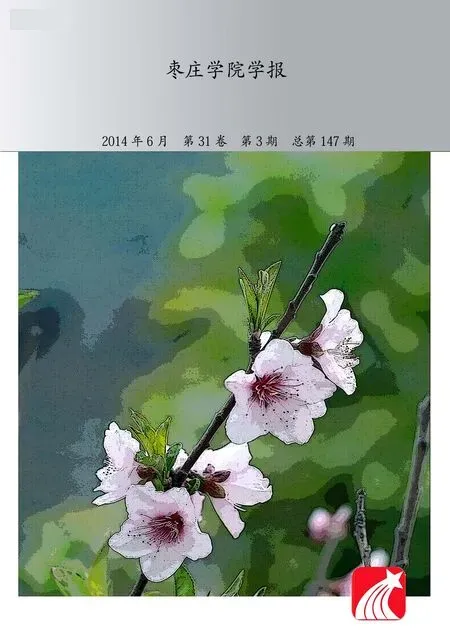《哥儿》与《围城》主人公形象比较
赵珂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1906年,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发表其名作《哥儿》,40余年后的1947年,在中国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发表了代表作——长篇小说《围城》。两部作品出现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国度,却都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展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下,知识青年在性格、事业方面的相似性。同时由于作者本身的思想取向、人生经历等原因,这两部作品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一、性格方面
《哥儿》与《围城》是以哥儿和方鸿渐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展开的。这两个主人公在性格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是富有正义感、同情心、善良正直的人。哥儿的这种性格在他幼年的时候已经有所显现,比如他很喜欢吃栗子,却也仅仅只是拾掉到地上的带到学校里受用。发现勘太郎偷栗子之后,就躲在暗处要抓住他,以示惩戒。长大后的哥儿在四国地区的学校教书,这种性格更加凸显。对于被“红衬衫”夺走未婚妻并遭到陷害的古贺报以极大的同情。为了惩罚“红衬衫”这伙坏人,堀田提出对他们“只能靠拳头解决问题”[1](P247),最后哥儿与堀田联合起来,抓住“红衬衫”和“蹩脚帮”嫖妓之机,把二人狠狠揍了一顿。哥儿和方鸿渐始终坚守着那份宝贵的正义感。对于从小就照顾自己的阿清婆婆,哥儿一直十分牵挂与惦记,从来不忘婆婆的恩情,经常给阿清婆婆写信,述说自己的近况,和绝大多数出家在外的人一样报喜不报忧,只说好的一面,以免婆婆担心,透过这些细节,哥儿无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方鸿渐同样,说他正直是因为他不愿意向虚伪狡猾的高松年乞求教授职位和续聘的恩赐,更不会像韩学愈那样,拿着假文聘四处炫耀,抬高自己身价,宣扬克莱登大学是一所非常好、严格并且正规的学校,一般人是不能入学的。方鸿渐说“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用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2](P195),这也不难看出方鸿渐心中还是有一种道德标准的,他的内心依旧正义,有良知。同时在文章快结尾处方鸿渐遇见了那个衣衫褴褛卖笨朴玩具的老头儿,不禁联想到自己找工作的困难,掏出两张钞票给他,表现出了对那位老人和自己的同情,再看自身目前状况,不禁哀叹与无奈。
其次,哥儿和方鸿渐身上都有一种不愿意和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傲然之气。哥儿在教书期间看不惯学校腐败黑暗,阿谀奉承,奸诈伪善的风气。喜欢和性格爽朗正直的堀田君交往,不愿意和那群乌合之众为伍,拒绝“加薪”、“提拔”的诱惑,毅然决然地辞职离开了那个污秽之地。在四国学校教书时,第一次值班就遇到了学生的百般刁难,一会儿是放在哥儿床上的蝗虫,一会儿又是在哥儿睡觉的二楼,“咚、咚、咚,有节奏的猛踏地板的声响,弄得二楼像要塌落下来”[1](P202),哥儿准备搜查宿舍,所有的宿舍门都被学生从里面反锁了,“垒壁森严”[1](P203),“推 也 罢,撞 也 罢,纹 丝 不动”[1](P203),哥儿拿这些学生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全然不知所措,但是他说“我绝不因此认输”[1](P204),一个充满傲气的形象跃然纸上。《围城》中的方鸿渐准备搬离周家之前,岳父周经理说他可以自由上下班,薪水照支,送给方鸿渐四个月的薪水当作他旅行的费用,不必向方老爷去筹了,方鸿渐很果断的拒绝了,说“我不要钱,我有钱”[2](P108)。这时的他很气愤,仿佛“国力大银行的钱全在他随身的口袋里”[2](P108),他不接受周经理施舍般的给予,他希望让人们看见他高大的背影,一种傲气的姿态,于是转身走了。曹元朗觉得出国留学很了不起,念念不忘自己是留过学的,经常把牛津剑桥的留学经历挂在嘴边到处炫耀,可是方鸿渐却认蜗为出洋就是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只有这样,面对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才有抵抗力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该把出痘的事忘了,留学生也应该把留学这事像出痘是一样忘了。方鸿渐认为这是不足挂齿的事情,这也不难看出方鸿渐骨子里还是有种傲气的。
第三,哥儿身上具有一种来自大都市东京的“江户之子”的优越感,这与方鸿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气质不谋而合。哥儿来到学校教书,第一次登上讲台,缺乏胆量,被同学们“老师”一声高呼,令他胆战心惊。第二节课,想到自己是东京人,立刻有了勇气,不要让那些“乡巴佬”的同学看出他自己无能,“于是尽可能放开嗓门,用略快且重的声调讲了起来”[1](P191)。《围城》中的方鸿渐留学回乡的时候,在火车站受到众多人的迎接,连报社的记者也来报道。方鸿渐虽然嫌弃两位记者一直叫“方博士”,但是看见记者竟这般恭维自己,不由得身心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2](P30),知道住在这种乡村小地方也是有好处的,此时的方鸿渐优越感油然而生,“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那根手杖”[2](P30),“照相怕不会好”[2](P30)。岳母周太太给方鸿渐介绍相亲对象是买办张先生的女儿,显然他对于岳母“这般好心”并不领情,觉得连相亲也得岳母做主,这时的方鸿渐也不乏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意和这位张小姐相处,更不愿意和说话夹杂蹩脚英文的张先生相识。
最后,哥儿也是个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虽然没有方鸿渐留学的经历,但是他们对于那些崇洋媚外的人根本瞧不起,比如哥儿和“红衬衫”及“二流子”一起钓鱼,谈话中不时听见两人说透纳、拉斐尔、玛利亚、高尔基这些西方人物的名字,以示自己很有文化知识和内涵,哥儿对于这些很是反感,他很不屑而且不愉快地说“这是红衬衫的坏毛病,一见眼前有个人,便罗列出一大堆诘屈聱牙的外国人名字”[1](P209)。方鸿渐对于曹元朗他也是打心眼里鄙夷的。尤其是对曹元朗那首中文中夹杂英文的小诗《拼盘姘伴》更是嗤之以鼻。
虽然哥儿和方鸿渐在性格上有某种相似,但是作为作家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二者存在自身独特的个性。哥儿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从哥哥那里得到了六百元钱之后,思考自己的未来,他选择了继续求学,选择毕业之后去教书,在学校,遇见的事情和人,他有着自己鲜明的爱憎和是非观念,从不依附别人,是一个非常富有个性主见的人。而方鸿渐总是一种依附别人,优柔寡断的状态,用岳父资助的资金出国留学,回国后,在岳父家里生活,又凭借岳父的关系谋得银行的工作,看着岳父一家的脸色,小心翼翼的行事。而后,方鸿渐的工作都是靠赵辛楣获得的。在与女博士苏文纨的交往中,明知自己与她“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不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始终合不拢成为一体”[2](P23)。但却在苏文纨的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中犹豫不决,迟迟不敢表明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同样因为懦弱,他从来没有驾驭爱情的能力,造成了他一直被困在情感的“围城”中。
二、事业方面
哥儿和方鸿渐都从事过教师这个职业,但是对于这份工作,两位主人公并非乐意为之,实属无奈之选。哥儿之所以选择教师这种职业,漱石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说实话,我虽然也吃了三年寒窗苦,但压根儿就没想过当什么教师,去什么乡下。当然,也没有考虑过教师以外的任何职业。因此,当校长问到我头上,便当场回答愿去。”[1](P183)。留学归来的方鸿渐在岳父的点金银行里上班,暂时不用为生计发愁。由于方鸿渐的优柔寡断,苏文纨的从中挑唆,使得自己和真正喜欢的周小姐就此错过,陷入失恋的痛苦,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为了在岳父面前逞强,逃避岳母的盘问和教训,最重要的是希望远离上海这个伤心之地,宽慰自己受伤的心,于是“三闾大学的电报自动冒到他的记忆面上来,他叹口气,毫无愿力地复电应允了”[2](P106)。哥儿和方鸿渐在学校的经历同样颇为相似,他们厌恶学校里的腐败营私、尔虞我诈,营党结社。令人欣慰的是两位主角依然坚持本心,希望做那枝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可是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学校受到别人的排挤,最后毅然决然地辞职离开了学校,更令人气愤的是坏人依旧存在,这是一种社会的悲哀。哥儿在学校遭到“红衬衫”一党制造的“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的羞辱与作弄,并没有使哥儿屈服于他们的统治,哥儿不屑于威胁,依旧勇敢地保持自我。联合堀田,抓住了“红衬衫”和“二流子”嫖妓,将二人教训了一顿,离开了那座小城,回到东京后经人帮忙,在铁路公司做技术员,和阿清婆婆简单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也算得上比较圆满的结局。不幸的方鸿渐比哥儿在事业上经历了更多的不如意,留学期间荒废时光,一无所成,花钱购得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充数,糊弄父亲和资助自己留学的岳父。回国到达三闾大学之后,狡猾的校长高松年、外表诚实内心虚伪的韩学愈、学校各个派系之争,方鸿渐又是牺牲品,离开三闾大学的路上接到高松年的不是聘约,而是书信及送给方鸿渐结婚的礼券,他异常愤怒,准备回信责骂高松年,并退回礼券,可是在孙柔嘉的劝说下,他放弃了,把高松年的信件“团作球状,扔在田岸旁的水潭里”[2](P268),不了了之。“他能看看穿恶劣的环境而不能自拔,虽然嘴上机敏但内心怯懦无能”[3](P386),方鸿渐从耻与和高松年之流为伍到希望和他们和睦相处而不得,这样的一种过程中,他并没有像哥儿那样实际的反抗,有的只是嘴上与头脑里的愤恨。
三、原因析探
作者的经历、价值取向、作品中主人公所处的时代等等的原因,使得这两部作品同中有异。首先造成两部作品相同的原因有:两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相似。《哥儿》成书于1906年,日本正在实行“文明开化”政策,但封建制度一直阻碍着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围城》发表于1946年,中国正与日本交战,虽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依旧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夏目漱石和钱钟书两人都生活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年代,封建制度和近代文明无可避免的发生碰撞,东西方文化在各自的国家不断的融合交汇。同时两人都深爱并有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积淀,幼年的夏目漱石在养父家中,受到了严格的汉文化教育。使用“漱石”为笔名,这个颇具汉学内涵的名字,据说其典故取自于中国的《晋书·孙楚传》。钱钟书出生于书香世家,在伯父和父亲的教导下,让他对本土的文化了如指掌,两人都有留学的经历,出国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钱钟书曾经说过“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些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4]。夏目漱石写作《文学论》的初衷也“在于反对日本盲目崇拜西欧的风潮”[5](P49),这不难窥见漱石和钱钟书二人对于西方文化有着清醒的头脑,在东方古老文明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西方近代文化。二人又都为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所属的群体,了解得具体而又深刻,清楚这种时代下的知识分子性格的缺憾以及生存的困惑。在作品的艺术表现层次上,两位作家同时选择了讽刺这一表现手法,在看似简单平淡的叙述与描写中,批露了当时的人与事。作家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哥儿和方鸿渐安排的年代也是一个各种文化交融的时期,主人公们也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分子,有着一定的追求与理想。以上的原因,使得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像。
其次,两部作品不同的原因也不少。第一,1905-1906年,可以视为夏目漱石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哥儿》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时的漱石被人称为“愤怒的漱石”,当时的夏目漱石只是反对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作品也是一味的揭露与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他的锋芒指向明治以来的日本所走的道路,揭发资本主义社会及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本质。虽然自己身为知识分子,但是这时夏目漱石的思想还没有成熟确立,所以《哥儿》没有《围城》那样细腻、深刻的描写人物内心的变化。但是在他后期作品《三四郎》、《从今以后》、《门》中,不难看出,漱石已从单纯的批判社会,转向知识分子内心道德伦理问题的紧张剖析。第二,夏目漱石幼年当养子的经历,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他对亲情极为淡薄,不像钱钟书,虽然也是养子,可是伯父和父亲在严格的教育中,他依旧可以感受到来自亲情的温暖。这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中表现的很明显,哥儿对于自己的父母没有什么感情可言,父母的去世也没有给他带来情感上的起伏,哥儿从小我行我素,具有独立的人格。在漱石的其他的作品中,对主人公父母的描写也很少,有的甚至没有交代。第三,《哥儿》是日本战胜俄罗斯时所写,夏目漱石对于这场战争也是支持的,欢呼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他希望这场战争的胜利能使“日本人抬起头来,不要甘心做西方人的奴隶,尤其希望日本人在文学方面抬起头来,创作出不劣于西方甚至超出西方的文学作品”[5](P57),所以文中并没有过多的哀伤,哥儿也是非常勇敢无畏的,而《围城》产生的时代,中国被列强侵略了一百多年,从天朝上国到满目疮痍的状态,中国人无不感觉世态炎凉,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以其敏感小心自负虚荣的状态生活着,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中庸自保之道,造成了方鸿渐的退缩与懦弱,也是一个时代真实的写照。书中的方鸿渐比哥儿的生活条件要优越很多,这就使他身上更多了一些依附别人、玩世不恭贵公子的气息。第四,《哥儿》是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故事,能使读者产生一种真实、亲切的感觉,更便于直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所写的内容不能超过“哥儿”耳闻目睹的范围,所以不便于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围城》却是用的第三人称的叙述,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灵活地反映客观内容。运用旁观者的立场进行叙述,可以了解过去、未来、对于每个人物都可以进行心灵深处的挖掘。
总之,哥儿是一个性格直率勇敢、嫉恶如仇的善良知识青年,方鸿渐是一个“不讨厌,却全无用处”,不够积极却还是有道德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两者个性鲜明却又复杂多变,在性格、事业、爱情方面众多相似的情况下,演绎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哥儿》和《围城》吸引了中日乃至世界各国众多读者,两部作品也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征服了世人,钱钟书先生是否读过《哥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两位大师留下了各自的文学的结晶,提供了我们世人交流研究的基础,在存在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吸收和借鉴,展现着东方独特的文化魅力。
[1]夏目漱石著,林少华译.心[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2]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罗新河.钱钟书文艺思想生成的历史语境[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1).
[5]何乃英.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方鸿渐和他的红粉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