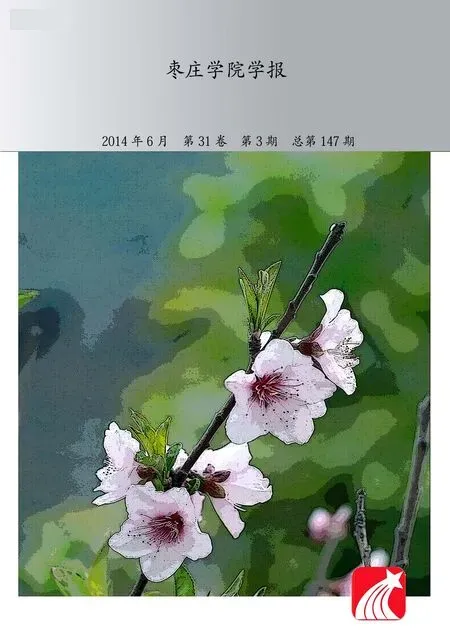仪式与公共记忆的制造
张春田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在清末革命思潮的传播中,南社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宣传革命的贡献,并不主要体现在理论论述上,而更多是通过一些文化实践行动影响社会风潮。哭祭就是他们常用的一种的仪式行为。大概言之,哭祭主要是指南社人寻访历史遗迹,凭吊前朝英烈的活动。哭祭在南社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革命者藉此重构了自身的认知框架与情感结构,催生了新的社会和政治能量,同时也改变了权力关系的配置。
在南社筹备成立的过程中,哭祭活动比较频繁,有文字记载的重要活动有如下八次。
第一次是1903年11月19日进行的狮子山招“国魂”,参加者为朱锡梁和包天笑等。这一天是夏历十月一日,他们和十几名青年一起,来到苏州狮子山。准备了一幅白布幡,上面印有雄狮,以这样的形式呼唤“国魂”的归来。范烟桥在《茶烟歇》里对之有详细记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朔,关中梁柚隐,吴县胡友白,杨韫玉、朱梁任、包天笑等若干人,登苏州郊外狮子山,为诗文以招国魂。其事甚秘,而当时文人革命思想之活跃,此见其端。朱梁任先生最激烈,书年曰:“共和纪元第四十六癸卯十月辛亥朔”,而署名曰:“皇帝之曾曾小子。”……若为当局所发觉,必难免身殉。……复有《题招魂幡》云:“归去来兮我国魂,中原依旧属公孙。扫清膻雨腥风日,记取当时一片幡。”幡为一白布,上绘雄狮狰狞状,意谓睡狮已醒,将一吼惊人也。前年陈佩忍丈主江苏革命博物馆,梁任先生曾语及幡,佩忍丈戏谓之曰:“招魂之幡,至今犹藏诸箧衍,其价值在革命博物馆所列者之上。盖三十余年前,冒死以为此,其敢胆不弱于烈士之怀刃掷弹也。”①
这里记述的不完全准确。所引两首诗,都刊于《江苏》杂志第九、十期合刊。一首是朱锡梁署名君仇所作的《题招魂幡》,直言“归去来兮我国魂”;而“黄帝之曾曾小子”是包天笑的署名,他写下《狮子山赋》:“纵有胡儿登大宝,岂无豪杰复中原。今朝灌酒狮山顶,要洗腥膻宿世怨。”②无论从署名还是诗的内容来看,都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意愿。因为这毕竟是十几个青年经过策划和安排的一次集体行动,在仪式中也非常讲究,整个过程充满了严肃的象征意义。同时这次活动又留下了两首诗,登载于杂志上,作为一种有意的宣称,使这个原本较为私密的行动呈现在公开领域。他们所说的“国魂”,在这里既代表一种文化上的权威,也代表正义的道德原则。以“国魂”而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作为召唤的对象,这已经是新的民族国家意识萌发的征兆和结果。
第二次是祭扫张煌言墓。先是1905年5月,高燮访张煌言墓并赋诗,后来,陈去病、高旭、刘三、黄节等在几年之间都陆续前去祭扫。张煌言,号苍水,曾任南明的兵部尚书。南京失守后,仍然坚持抗清斗争二十多年,后被清军杀害。高燮在《谒张苍水墓》中一面歌颂张煌言“为国岂爱死,深入奚敢辞”的舍生取义的精神,一面记叙自己前来寻墓的行动与心情:“峨峨南屏峰,草没长松枝。远来寻公墓,哭公泪如丝。凤凰好山色,长系后人思。伪廷谬褒荣,对此益生悲。”③直说张煌言的墓隐没在深山之中,暗指他的抗清精神已经被遗忘,人们在异族统治下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而痛哭更是一个重要的行动。既是惋惜张煌言当年壮志未酬,赍志以殁,更是一抒作为知识人面对当代内忧外患的愤懑之情。据说张煌言被杀害时,曾望凤凰山而叹“好山色”。历史已经在自然山色上打下了烙印,“凤凰好山色”一句即是说张煌言的精神一直存留在知识者心中激励他们。而最后一句,是指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曾为张煌言加祀“忠烈”一事。但在高燮看来,这更加刺激了自己的感情,因为作为反清的英雄,他的志向没有实现,却重新被清廷在文化统治上加以利用。作为后人,不能恢复河山,只能愧对前贤。所以这里的“悲”包含了深层的感慨。
第三次是1907年4月6日,陈去病、高旭、朱少屏、刘三、沈砺五人自上海赴苏州,谒虎丘张国维祠。张国维曾任兵部尚书,拥鲁王朱以海监国,领导抗清运动;后知事不可为,投水殉国。他在苏州担任巡抚时,曾大兴水利,苏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为他修了生祠。陈去病先前自己已来过一次,但是没能进入,“瓣香清酒,怊怅难陈嘉俎”④。几天后,又与朋友一起重访。两次到来,表明在陈去病心中这是一定要完成的一种纪念。这次重谒,陈去病作了《天仙子·重谒张东阳祠》:“短艇轻桡随处舣,又到中臣香火地。神鸦社鼓不成声,哀欲死,无生气,入门撮土为公祭。痛饮黄龙今已矣,亮节孤忠空赍志。满园花木又凋零,余碧水,向东逝,盈盈酷似伤心泪。”⑤他看到祠堂里一片寥落景象,感到伤感。最后把水比作“伤心泪”,就既是源于张国维的身后寂寞,也是自己对时局的一种悲观。参与拜谒的高旭也作了一首词,同样感慨“龙虎无堆,鸡豚有社,千古齐挥涕”。但他更指出作为“来者”,应该要继承张国维匡济时局的精神:“十载提戈,一篇负国,来者须能继。楚氛甚恶,鬼雄上诉天帝。”⑥“楚氛”喻指满清的压制。他希望借助天帝的正义力量,同时也相信“忠魂不死”,会帮助“来者”扭转“华夷倒置”的局面。柳亚子虽然没有参加,但读了他们的作品后,也和了一首《题吴门纪游·和谒张国维祠》:“头颅昔日悬胡阙,魂魄今尤恋汉州。一水西陵松柏渡,吴山越水怒潮秋。”⑦柳亚子也强调英雄魂魄长存,并且这种存在可以激励现实中的抗清“怒潮”。
第四次是1908年4月19日,时在绍兴的陈去病祭扫宋高宗、孝宗等六陵,仍然伴随“歌哭”的举动。他在诗中说:“桥山弓箭杳无存,谁向昌平奠一尊。只是六陵齐在望,不嫌歌哭吊湘魂。”⑧陈去病在诗中详细描述了他祭陵的情况。这是暮春时节,他亲自带着祭品来到陵墓前,周围开满了杜鹃花,此情此景下也染上了悲情:“却有满山红踯躅,血痕狼藉惹人怜。”他由宋亡联想到了明亡,“未信百年遗恨在,阖宫同殉有煤山。”不仅悼念崇祯,而且进一步联想到南明的永历帝。比起崇祯,永历帝更是连陵墓也没有:“脉脉九龙池畔路,天南遗老至今哀。”⑨借悼宋陵而哀亡明,这种祭祀的对象本身并不是那么确定,更多是借助于祭祀的形式来宣示自己的态度,并且把这种祭祀当成一种微观的反抗方式。
第五次是1908年5月24日(夏历四月二十五日),陈去病与刘三在杭州祭扫张煌言墓,并吊南明永历帝。这一天是永历帝殉国的忌辰。他在事前给高旭的信中说:“四月二十五大纪念,为汉族最惨苦、最伤痛之一日。盖永历英主生为俘囚亦既已矣,而身受绞杀,死后更遭扬灰之戚,较诸杨琏真珈捣毁宋六陵,取理宗顶骨为饮器,其残忍为甚。……故特告君及安如,务必来西湖向苍水墓上一哭,以泄吾无穷之悲。”而刘三愿意为东道主。陈去病在信中还抄录了刘三的一首诗:“几经无浊阏天才,零落栖迟骨未灰。为扫南屏苍水墓,几人豪哭过江来。”⑩刘三和陈去病特意选择这个日子去祭扫,显然是将之视作为亡国纪念日的纪念。陈去病在《四月二十五日偕刘三谒苍水张公墓并吊永历帝》诗中写道:“大好河山日欲斜,登高揽胜兴何赊。苍天逆行黄天死,只向秋原哭桂花。”面对“大好河山”却无心“登高揽胜”,“哭”字再次出现。“苍天”/“黄天”的对比,不仅具有高度人格化的力量,而且也有现实影射。他在这一天所写的《永明皇帝殉国实纪》中说,历史上的这一天是“吾皇汉民族永堕于奴隶牛马之第一日也”。而在现实中,革命党人现在已经在云南发动的起义:“一剥而不复者,终古无是理也;有因而弗革者,吾又未之闻也。是以一发千钧,卜生机于硕果,普天同愤,须有待于今时。爰纪确闻,以告同志,庶几勖励,用报大仇。……而我今国民军政府之进攻云南者,当共见有彩幢羽葆,立云中指麾,而益鼓动震奋以杀贼也,必矣。”陈去病相信天道的循环往复本身将为“革”提供便利。有意思的是,一年多以后,陈去病在苏州得到永历币一枚,他认定这是上天对他“尽精力于帝”的一种回报。高旭作了一篇《百字令》,题注云:“巢南见示永历钱,索题,且云:‘仆尽精力于帝,至矣。此殆天阴有以报我耶?’其言可哀也。”表达了强烈的共鸣:“何物迂儒,瞿、张殉后,努力如公少。老天有眼,殷勤贻以相报。”更以“伤心帝子,精魂那日归了”作结。不仅编织了一个天道报应的完整故事,而且暗示这种自然力量,为他们的政治意图的最终实现提供了保证。
而与陈去病一同扫墓的刘三也赋诗曰:“我马乌骓君马黄,墓行相对忽淋浪。绝同南内荒凉后,白发宫娥说上皇。”他把伺墓老妪跟他们的谈话,逆想为“白头宫女”追忆玄宗之事,从心理认知上他们自己就此顺利地扮演了“遗民”的角色。这一点对于柳亚子也同样适用。他写了《四月二十五日》一诗,自称是明朝“遗民”:“伤心今日是何日,忍死遗民泪眼枯。”他以为云南起义一定因为发生在“旧帝乡”而能够得到更多的庇佑。而将来一旦胜利,也要告慰明朝历代皇帝的英灵:“好待收京传露布,十三陵畔奠先皇。”再次利用了对英雄先烈的信仰,为现实行动提供精神的支撑或情感上的感染。
此后数年,黄节、高旭等也来张煌言墓上拜谒过。黄节作《南屏谒张苍水墓》,“心伤湖水哭先生”,把他的墓与岳飞的墓相提并论。高旭来拜谒时,也深有感触:“我来此地觇遗影,慨想当年尺涕横。”历史没有提供机会,“天未厌胡骄铁骑,地堪埋骨哭铜驼。”面对“凄绝东南好山色”,他想到的是英雄的遗恨:“英雄至竟恨如何。”在两人诗中都有“哭”出现,可见这种感伤情调的普及。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字,他们让这种行动进一步“可见化”。
第六次是1908年下半年陈去病南游时的祭奠活动。9月22日,陈去病在隆武帝后忌辰那一天,登别岛祭悼。跟以前一样,也以诗纪之。写自己“扁舟独泛沧溟阔,穷岛来寻越鸟巢”,“登高宁识林峦趣,摅愤空凭子午潮”,寻寻觅觅,希望招回“帝魂”。陈去病把这首诗寄给了朋友,把个人性的活动变成了一个群体可分享的文化行为。柳亚子读后,和了一首:“一纸新诗涕泪涟,桥山弓箭至今传。魂归沧海怜精卫,人向空山拜杜鹃。抔土难埋龙凤骨,冬青休问犬羊年。尼山笔削分明在,谁识《春秋》内外编(是日即孔诞)?”他以这样的方式参与着祭悼活动,并且感叹《春秋》大义的中断,这就重新赋予了文字符号以塑造认同的政治性功能。
11月,陈去病途经新会县厓门,对陈去病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陈去病作了《厓门四律》,小注中交代:“新会县南之厓门,宋陆丞相负少帝蹈海处也。余于仲冬七日,自江门独游至此,宿全节庙,一夕而去,风雨四合,阴森怖人,赋此志哀”。其中有一律是这样的:“淙淙遥夜雨声多,独哭荒祠泪似波。若有人兮留劲节,自今谁与共丘阿。挑灯快读残碑字,危坐频吟正气歌。一事只防山鬼笑,楚囚胡服竟如何。”陈去病特意强调夜宿的地点,并营造出一种隐约幽微的氛围,好像“若有人兮”。他又是读残碑,又是吟诵《正气歌》,所做的都是很有象征性的行动,让自己的身影也迭印在前辈英雄的身影之上。但是最后一句又显示了作者对自己的警醒,把羞耻感表露得再明白不过了。
第七次是1909年10月12日,高旭、姚光、蔡守、苏曼殊等相约游杭州,蔡、苏爽约,高、姚谒岳飞庙。高旭《谒岳鄂王墓》说:“墓门一抹云如墨,我来对此三太息。阴森宰柏尚排胡,叶叶枝枝不向北。天荒地老陵谷沉,万古难消忠义心。岳王冤死已千载,白骨永避蛟龙侵。半壁湖山宋南渡,人自亡之岂天数。为伤眼底无英雄,一瓣心香拜公墓。”他所发的三个“太息”,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感应现象。高旭列出这些心物交感的可能性,是为了证实抽象的天道的能动作用。1910年夏,柳亚子也曾和了高旭一诗《寄题西湖岳王冢同慧云作》,呼应高旭“人自亡之”之意,慨叹清政府“自坏长城”,“无愁天子朝廷小,痛哭遗民涕泪多。”又把秋瑾殉难事引入,“秋坟一例沉冤狱,可许长松附女萝。”与其说表明申诉秋瑾的遭受不白之冤,毋宁说是将之作为后来者行动的激励。
第八次是1910年重九,高燮、高旭、姚光、高均、蔡守等结伴游南京,与周实、周伟等一起凭吊明故宫、明孝陵等地。姚光的《庚戌重九金陵游记》,以散文的形式记叙他们的游踪:
于重九节登北极阁,造其巅。纵目四望,……全城形胜历历如指诸掌。呜呼!何其壮也。题名而下。折而东,至明故宫,为太祖之所宅。有驰道,直达紫禁城之西安门。城已无有存者,惟东西安门暨正中之五朝门巍然独峙,然亦颓废零落,近方鸠工拆毁,车载驴负以去。可慨也夫!……故宫之西北为方正学祠,祠之东隅有血迹碑亭,巨石翼然,赤痕缕缕,摩挲不忍去。……折而东,北行三里许,抵明孝陵前,……登祭坛凭吊久之,然后唏嘘而出。时则残山一角,落日苍茫,驴背沉吟,不堪回顾矣!吾因之忆去年今日,方在武林于雨丝风片之中,拜张公苍水墓;今年此日,复来建业,于疎柳残阳之外,谒胜朝太祖陵。如此重阳,其真百无聊赖矣。
姚光把这次金陵之行与上一年拜谒张煌言墓联系在一起,显示出这是他们有计划的参拜,是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下设计的身体行动。而他们所拜谒的地方也都经过精心选择。南京曾是明朝的首都,而明故宫、明孝陵等地,更是曾经的政治权力的象征。古迹在岁月冲刷下的衰败景况,正配合了他们自我塑造的“遗民”身份:“付遗民,凭吊伤怀否?”这一群“扮演”的遗民,相率伤悼前朝命运:“相见我侪啼哭处,剧悲歌,肝胆应如斗。心头血,杯中酒。”
他们写了不少诗词,记叙这次南京之行。高旭的《登北极阁》继承文人登高抒怀的传统,同时总结历史教训:“乱世骚人空说剑,百年壮士几登台。心知江左非王业,(用宋梁栋句)玉树歌终付劫灰。”另一首《血迹亭题壁》悼念方孝孺,“此是读书真种子,入石不磨称精忠。”高旭认为方之可贵在于坚持纯粹道德。“正学何如先正心”,应是针对现实中那些投身清朝的读书人的讽刺。在《过明故宫感赋》中,他“宫墙踏遍痴如许”,思索“此中王气消磨未”。在《谒孝陵》中,他一方面称赞明太祖“恢复旧物追前踪”,另一方面也批评他的政治专制:“惜哉政治何专制,宰戮勋臣任私意。朕即国家奚畏为,颠倒干纲太无忌。”他提醒那些要恢复汉族政权的后来者,不应效法朱元璋,“牧羊政体久绝迹,大权独揽非其时。时移势迁今殊昔,石头虎踞秋瑟瑟。”这在所有关于遗迹的书写中显得非常特别。高旭日渐形成的共和民主观念,使得他没有沉迷在恢复明朝的政治想象之中,提醒革命者应该与时俱进,推动民主政体的建立。
但高旭仍然有浓重的历史怀旧情结,孝陵的残瓦剩砖也让他痴迷,他仔细端详孝陵瓦:“吁嗟此物六百年,国亡片瓦空流传。钝剑抚之涕泪涟。”又得了一方孝陵砖,他将之斫为“日月重光砚”。感叹只有这块砖保留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太息衣冠尽变迁,不变迁者惟此砖。”他把砚台作为一个象征物,“对砚如对我高皇”。要留这个砚台作为见证,等待“天下大明”。参拜遗迹本来就依靠现实的各种物质存在来激发感情,无怪乎他们对物质性的如此关注。原来普通的孝陵瓦、砖也成为了跨越时间阻隔的精神的象征物。
高燮《谒明孝陵》一诗,对他们一行谒明孝陵的过程记载甚详:“驱车出朝阳,山色凝空蒙。舍车聊步行,满路吟秋虫。……翁仲近十余,石马犹纠雄。依然数里外,拱护榛莽丛。凄恻达明楼,徘徊再拜恭。郁纡枕岩冈,马鬛万古封。”高燮也从凭吊中,思索历史教训:“兴废有乘数,抔土终相同。请君付达观,万事江流东。”相对于高旭感慨兴奋但依然砥砺志向,高燮则有些历史虚无主义,似乎把一切功业兴废都给取消了。
事后,周实将这些诗词辑为《白门悲秋集》。他在序中说:“取名《悲秋集》,以其为《九辩》之遗音也。”即强调同人内心对国家危亡的担忧和愤懑。而这种“伤时念乱”正是针对时局而发:“天不可知,世方多难,国亡族灭之祸,岌岌焉悬于眉睫间。一二在上位者,犹复揽权怙恃,恬然于危堂沸釜之中;而晚近少年,又从事于锦衣玉食,金鞍白马,酣歌恒舞,而不知休。……则吾侪本古诗人伤时念乱之义,以此为周顗新亭之泪,阮籍空山之哭,不犹贤乎。”通过《白门悲秋集》这样公开发行的印刷文本形式,本来是一个同人圈子内的诗歌唱和,获得了更多公众阅读的可能。从而,不仅使拜谒古迹的仪式凝定成文字,可以进一步地传递和交流,更能利用这些公共符号,激发民众情感。
综合来看上面列举的南社人这些哭祭活动,我们发现,第一,这些活动是行动者有着高度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渗透着强烈的主体意愿,特别是通过文字书写,他们更让这种主体意愿在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可见化”。第二,这些活动在时间、地点、对象的选择上,都非常有讲究,本身也是充满程序化的操演,比如“哭”的行动几乎次次都有。第三,德里达曾经提到过革命所面临的“鬼魂缠绕”的状态。我们在南社的这些哭祭活动中正可以看到一种关于英灵的“魂在论”(hauntology)思想的宣扬,行动者在行动与文字上造神,把鬼魅作为社会文化生产中有意义的现象。革命本身内在包含着时间上的“他者”。拜祭先烈,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单纯表达对于英雄的崇拜的活动,更是一种象征符号的编码。通过在心灵和语言上对英雄灵魂的认定与召唤,想象并建构着诗性正义的可能性。第四,在这些活动中,主要利用和挪用了传统王朝/君臣的政治观和“遗民”文化,华夷与忠奸意识得到强化。但同时,新的替代叙事也开始在这些活动及其表述中浮现出来,比如民族主义、民主共和,等等。在南社人的唱和与发表中,原本是个人性的“哭祭”行为,最后也变成了一个群体参与的“表演”。
正如郑勇所说:“陈去病至浙江访宋遗民谢翱西台恸哭处,在绍兴祭扫宋高宗、孝宗六陵,杭州祭扫张煌言墓,至广东则凭吊陆秀夫背负宋少帝投海处,在汕头祭悼南明隆武帝,而且每每行之诗文,向社友索和,由酬唱和迭行为使‘独哭荒祠’式的个人行动变成群体参与。1910年,高燮、高旭、姚光、蔡守等会同周实、周伟同时凭吊明故宫、孝陵时,‘本古诗人伤时念乱之义,以此为周凯新亭之泪,阮籍空山之哭’,便不无‘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誓师北伐的豪壮。”南社人不仅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意义交流,更尽力使其带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具体说就是广义上的“革命”。
注释
①范烟桥:《茶烟歇》,转引自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5-6.
②均载《江苏》第九、十期合刊,1904年3月.
③高燮:《谒张苍水墓》,高铦、高锌、谷文娟编:《高燮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463.
④陈去病:《念奴娇(丁未清明,虎阜谒张东阳祠,不果)》,张夷编:《陈去病全集》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271.
⑤陈去病:《天仙子·重谒张东阳祠》,《陈去病全集》第一册,页271.
⑥高旭:《百字令·绿水湾谒张国维中臣祠》,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288.
⑦人权(柳亚子):《题吴门纪游·和谒张公国维祠》,《磨剑室诗词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2.
⑧陈去病:《戊申三月十九日有事于宋之高、孝、光、宁、理、度六陵》,《陈去病全集》第一册,页67.
⑨同上注.
⑩陈去病:《寄天梅书》,《陈去病全集》第一册,页359-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