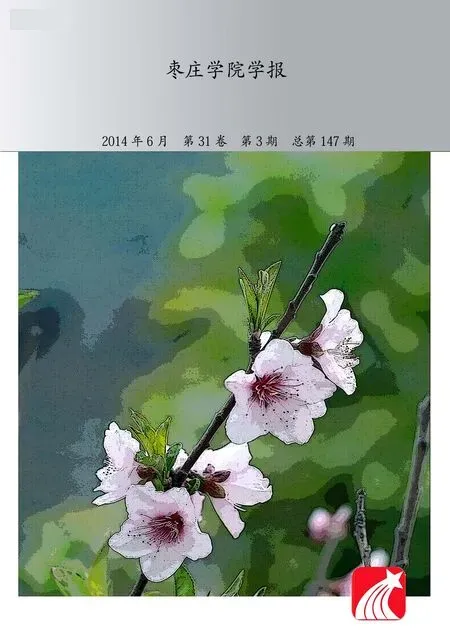“女性谱系”的建构
——论林白的小说《回廊之椅》
邓如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文学院,北京 100029)
林白,当代中国大陆最激进的女性主义文学文本的创造者之一,她的写作总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书写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状态。林白的创作丰富,其中最能代表她的写作风格和水准的是《回廊之椅》。在这部作品中,林白试图建设一个自尊自足的“女性谱系”,以此来抗拒“宏大叙事”中的男性权力。
一、边陲女性的追寻与传承
林白是独一无二的,她的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小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或明丽、或冶艳、或凄绝。她是广西省北流县人,这一边陲女子的身份在她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的女主人公大都是边陲女子,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丰富的内心。《回廊之椅》延续了林白一贯擅长的故事模式:在一个边远而神秘的小镇,发生了一些关于女性的奇特的故事。这样的小镇出现在林白的多部小说中,具有浓郁的南方边陲地区的特有的风情,构成元素也充满特殊的情调:深邃的丛林(远古的、神秘的)、常年的雨季(潮湿的、闷热的)、长长的天井(封闭的、幽暗的)、厚厚的青苔(古旧的、落寞的)、暗红的指甲花(美艳的、凄绝的),这一切使得小镇散发出久远而神秘的气息。
《回廊之椅》中的小镇水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女主人公居住的庭院周围植物繁茂,弥漫着原始的、野性的生命之气,而庭院本身典雅深阔、年代久远,朱红色的楼廊三重四叠,“有一种幽深、干净、拒人千里的感觉”,空旷的回廊有着“无边的寂静”,一只似乎有人用过的杯盖斜盖着的茶杯静静地放在廊椅上,穿过幽暗的时间隧道向“我”虎视眈眈。“我”是一个年轻的现代的来访者。“我”来到了小镇水磨,偶然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庭院“章宅”,遇见了一个年事已高的女人七叶,听她讲述章宅曾经的女主人朱凉的故事,“我”被朱凉深深吸引,不由自主地一再进入庭院,无法拒绝,仿佛梦魇。
很明显,小说有一个“探险故事”的框架,“我”是一个叙述者,通过“我”的视角,读者也可以充分感受到一种“探险”的快乐、神奇、甚至是惊悚。然而,“我”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叙事学意义的“叙述者”,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我”的意义,更在于形成了一个“女性谱系”:“我”的一次偶然探访,造成了“我”对朱凉的魂牵梦萦般的探索,这探索并不是对往事的猎奇,而是“我”与“她”之间冥冥之中的牵挂、理解和慰藉,“我们”之间是精神相通的。“我”——七叶——朱凉,三个女性构成了一个别具意味的“女性团体”,她们在有着回廊的房间里相遇,这个房间是独属于她们的,有着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自己的房间”[1]的意义。尽管她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但后辈却不停地寻找、追随着前辈。正是在“探访、追寻、继承”这些含义上,《回廊之椅》形成了一个具有传承关系的“女性谱系”。
二、“男性史”的暴力逻辑
在《回廊之椅》中,男性也自有他们的历史逻辑。事实上,小说正是在一个“男性史”的对照之下来建构“女性谱系”的。在林白的笔下,“男性史”是怎样的呢?革命、暴动、冲突、审讯、屠杀……一切“正史”中的元素都包含其中——毕竟,在我们的思维中,“正史”几乎约等于“男性史”。正如阿德里安·里奇所说,父权制在正史中起到统治性的作用,“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2]
在《回廊之椅》里,“男性史”充斥着令人不齿的嫉妒、告密、手足相残、公报私仇等无数龌龊不堪的东西。里面的男性没有一位是让人钦佩的,朱凉的丈夫章孟达追求革命,不过是为了赶上“世界的潮流”,领略“冒险的乐趣”,同时杀二弟章希达的威风;希达是个白面书生,满嘴的“主义”,然而他在被审讯时却相当“缺乏英雄气概”,为了活命告发哥哥章孟达密谋暴动,枪决前“一泡尿从腿根一直流到鞋底”;审讯科长陈农内心龌龊,长期吃开水泡饭的他憎恨地主章孟达,“恨他有三房太太”,“恨他被关起来还有人给他送米饭煎鱼”,“恨他连使女都这样不卑不亢”。他利用手中的职权以肃清暴动的名义枪决了章家兄弟,渴望趁机得到觊觎已久的美丽的三姨太朱凉。
在充满“宏大叙事”的“男性史”中,最触目惊心的组成元素是“暴力”。暴力既包括审讯、刑罚、枪决等血淋淋的场面,也体现在对人性的玩弄和践踏之中。小说中的一段很长的关于杀猪的描绘是极具隐喻性的,是暴力的残酷和暴力的恐怖的具体写照:陈农等“革命群众”闯入章孟达的庭院,在他家的天井之中、在四楼的朱凉和七叶的眼皮底下肆意杀猪,以一种“兴奋、富有弹性、喜气洋洋、幸灾乐祸”的声音和心态进行着暴力的宣泄:“他将这桶滚烫的水举起来,哗的一下倒在猪身上,浓白的水汽腾地一下铺天盖地升起来,这些水汽在锅里被一再加热,它们憋足了劲,鼓足了热情,它们是水中的热情分子,现在它们被释放了出来,它们迫不及待地奔涌而出,它们舞蹈、歌唱、扭动、喊叫、蔚为壮观,在铅灰色的雨意中,这一大片白色的水汽既辉煌又恐怖。”
这场杀猪的闹剧之所以如此喧闹和低俗,原因之一是男人们对楼上的女性的性幻想,这一原本隐秘的淫念在“革命”的外衣之下变得公开起来,并借助男人们颇具含义的大笑声得到不断的放大,公然地冒犯着、侮辱着两个美丽的弱女子,“杀猪的声音……从七叶体内曲折而快速地奔走,然后从她狭窄的喉咙再度冲出,夸张而变形,它们声势浩大,一次比一次强大而真实,一次比一次恐怖。”
充斥暴力的“男性史”令周遭的女性不寒而栗。在《回廊之椅》以及林白其他的作品中,她,林白要建立的,是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女性谱系”。
三、“女性谱系”的温暖与爱
与男性世界充斥的暴力、肮脏、低俗相比,女性的世界则是一个温暖的夏娃乐园。林白要建构的,正是一个与充满“宏大叙事”的“男性史”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一种“边缘性”的历史,这历史由女性创造,具有女性特质,它并不“宏大”,细腻而琐碎,不一定被“正史”接纳,但却真实地显示着女性的温暖、哀乐与爱。
林白笔下的女性都是美的。朱凉是《回廊之椅》中美丽而神秘的女性。事实上,小说自始至终朱凉本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关于她一切都是由使女七叶转述而来的。七叶的转述加上“我”的想象,构成了一个“虚拟”的朱凉的形象,“我”从未见过她,却时时感到她的无处不在。这种写法,颇似英国著名小说《蝴蝶梦》,带来的效果也是与《蝴蝶梦》类似的:浪漫、神秘,兼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只见过朱凉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人穿着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开叉至大腿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艳。这明艳像一束永恒的光,自顶至踵笼罩着朱凉的青春岁月,使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向我凝视。”
在小说中,“我”毫无保留地赞美着朱凉的无与伦比的美,她用过的茶杯、她留下的被面、一切与她有关的事物都激发起“我”的强烈的兴趣,“我”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地被吸引进她曾经居住过的古老庭院,在回旋而上的楼廊上一遍又一遍追随她的足迹,怀想她的眼神、她的姿态、她的身体的香气。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白在这篇小说里建筑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女性的“私人领地”,美丽的女主人公朱凉就住在这样的一块领地里:庭院深深,屏风挡住了前庭到后院的通道(亦挡住了男性世界通往女性世界的通道);后院寂静的四层小楼是她的居室,“有一种幽深、安静、拒人千里的感觉”(一种自我保护、独善其身的感觉);室内帘幕低垂,挡住了肮脏龌龊的“革命干部”陈农(一个有权力的男性)从窗口窥视朱凉的视线(窗口正是最好的窥视和入侵的入口),陈农“终于未能看清窗内”。一些女性的事物——窗帘、屏风和阁楼将朱凉完美地保存了下来,使她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中免受侵犯,保全了女性的尊严。这个时候,她是自在的、放松的、欢愉的、真实的,她因为身和心都达到了完全的自由而与自然合一,她的美也因为自然的光辉而具有了某种神性:
“落日的暗红颜色停留在她湿淋淋而闪亮的裸体上,像上了一层绝妙的油彩。……这暗红色的落日余晖经过漫长的夏日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它顺应了某种魔力,将它全部的光辉照亮了这个人,它用尽了沉落之前的最后力量,将它最最丰富最最微妙的光统统洒落在她的身上。”
“私人领地”是属于女性的,它是置于男性的控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它幽暗不明,深不可测,男性在这个世界里是“缺席者”。这片领地类似于美国女性主义者吉伯特和古芭的笔下《阁楼中的疯女人》的“阁楼”[3],一方面隐藏着女性的“忧虑和愤怒”,另一方面,也是只属于她们的温暖之地。
“我”与朱凉之间的神秘联系,已经凸显出了林白要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姐妹情谊”——女性之间的精神相通、相互牵挂和庇护。当然,《回廊之椅》对“姐妹情谊”的表现重点放在七叶和朱凉这两个女子身上。
七叶与朱凉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她们组成一个情感自足的世界,抵抗着外界一切的危险,不管世界怎样变化,她们的“姐妹情谊”延续至死。七叶对朱凉的忠诚和欣赏已经超出了普通人想象的“主仆情谊”,其中婉转的情感、暧昧的情调让小说变得质地丰富起来。七叶在谈及朱凉时,“她的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怀旧和眷恋之意,就象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怀念他年轻时代的铭心刻骨的爱情。”因为“我”的眼睛与朱凉长得相似,七叶对“我”也产生极大的兴趣,对我说话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一种动人的申请,使我感觉到某种遥远的东西。”而“我——七叶——朱凉”之间也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欣赏,这种奇妙的情感胜过友谊,接近爱情,又超乎肉欲,婉转妙曼,时隐时现,“姐妹情谊”得到了诗意的表达。这正是林白小说中最具魅惑性的一笔。
[1]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房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阿德里安·里奇.生来是女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吉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