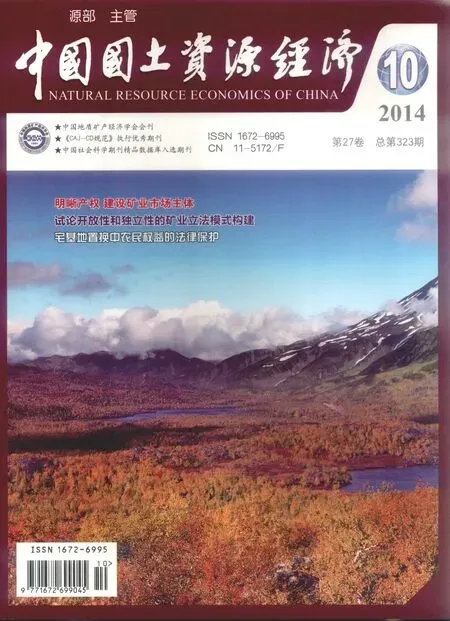试论开放性和独立性的矿业立法模式构建
■ 李显冬/谢 涛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试论开放性和独立性的矿业立法模式构建
■ 李显冬/谢 涛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我国矿业立法的困境逼迫着我们寻找一条新路以探求矿业立法所应当遵循的立法模式。以系统哲学理论作为统筹,以系统哲学理论为基点阐发一部具有整体性或是融贯性的法律所应当具备的开放性和独立性。持开放性而得以祛除狭隘理论争议之弊且得以与外界有益互动;持独立性而得以立法内部结构之完整。此外,基于实践活动的客观现实性,探讨开放性和独立性所应当立足的法学理论的客观规律和矿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法学理论的客观规律要求立法所涉及之体系、概念等应当摆脱于无益的理论争议而着眼于切实之立法需要;矿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立法应忠实于其调整之社会关系所蕴含的产业发展规律。
矿业立法;系统理论;开放性;独立性;客观规律
0 引言
我国目前尚无独立的矿业法,只有1996年制定的《矿产资源法》。作为初步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现行《矿产资源法》承载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期间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勘查、开采秩序的特定历史重任。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让现行《矿产资源法》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已无法承担起保证矿业作为一个行业能够科学发展的新的历史重任。笔者认为现行《矿产资源法》在其功能定位、调整范围、调整方式……上出现的种种困境都可归咎于违背了立法所应当遵循的法学理论的客观规律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在探寻构建矿业立法新模式的当下应当立足于立法的客观规律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除对作为基础的客观规律的寻找之外,我们似乎还应当对在这一基础之上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矿业立法模式做一描摹。一部理想状态中的矿业立法应当具有怎样的特质以及这些特质深含着的客观规律是什么是本文重点阐述的内容。
1 系统哲学理论对矿业立法的导向价值
实践的科学性在于其遵循了客观规律。对于立法而言,其实践的科学性在遵循法学理论的客观规律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或手段,其创立自是一种主观加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而统合法学理论的客观规律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产业立法又必将借助于具有最为普遍性和根本性的方法论作为认识的指导工具。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都必将吸收和兼顾其他学科的知识。系统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本文将借助系统哲学理论作为指导,尝试提出构建矿业立法模式的合理路径。钱学森指出:“把极其复杂的研制对象称为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他们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1]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2]恩格斯对系统也早有论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务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由此可以得出系统所具有的全局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预决性等特点。
系统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理论成就,以客观系统物质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的科学。系统哲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补充、丰富、完善和发展,是对传统哲学范式的一种超越,是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形态[4]。系统哲学是综合时代的思想结晶,其首要的思想和基本原则是“整体性”。一般系统论就是对“整体”和“整体性”的科学探索[5]。引入系统哲学理论是需要借助于整体性思维以构建合理而完善的矿业立法模式。矿业立法作为国家对一产业发展的立法规划,其法律理论客观规律的规定性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规定性决定了其合理性必将基于其能充分与社会的其他子系统相互配合与衔接,并处于合理的架构当中,以及自身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衔接。整体性思维落实到矿业立法当中,就是希望制定出来的矿业法一是能够与其他法律或规范之间能够相互配合与衔接;二是能与其他法律或规范处于一个合理的架构当中;三是其内部各组成部分自成系统且能相互配合与衔接;四是前三项在动态的时序当中能够自我调整以维持长久。
上述由系统哲学理论所引发的四项涉及立法构建模式的目标是处于理想状态当中作为相对独立系统的立法应当具有的特质。这四项目标中的第一、二、四项目标可以简化为立法所应当具备的开放性。具体而言,第一、二项可以归结为空间上的开放性;第四项可以归结为时间上的开放性。而第三项目标或许可以用立法的独立性代称之。因为一个内部各要素自成系统且能相互配合与衔接的系统单元必须具备相当的独立性以实现其内部系统的有效运行。正如上文所言,矿业立法的合理性受制于其法学理论客观规律的规定性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规定性。所以,上述所言一部法律所应当具有的开放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也可以从法学理论客观规律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上进行探寻。
2 矿业立法开放性的基础
2.1 于法学理论客观规律之上的探寻
矿业立法的开放性的探讨涉及到法的类别属性的开放性、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以及法律概念的开放性。法律的类别属性、法律体系和法律概念在法学理论上常常作为界定的对象。法律的明确性要求规定了任何一种界定都是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以将其作为判断非此即彼的依据。然而,因为每一次界定都会造成法律的僵硬性和滞后性,故而,任何一次界定的尝试都是一次似乎是无可奈何但又牵涉甚广、关系重大的举动。至于矿业立法,我们可能需要去界定矿业法的公私法属性、部门法属性以及其中诸如矿业权、矿业用地、权利金等各种需要明确的名词。在法学理论客观规律基础上探寻矿业立法的开放性就是一个对上述所言的“对象”有无必要进行界定以及如何进行界定的问题。
对于法律的类别属性而言,在传统公、私法二分的背景下,矿业法的归属似乎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不过,这也正是社会发展及其引发的有关公、私法相互融合渗透的一个例证。在众多学者费尽笔墨探讨矿业立法的公、私法属性的时候,我们似乎应当去思考公、私法属性探讨的现实必要性。或者说在公、私二分法理上的绝对权威下,牵强附会式地开辟一个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的社会法领域以化解困境的做法有无合理性。在对公私法划分理论持怀疑论者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狄冀和凯尔森。
狄冀通过其“社会连带学说”揭示了法的真正基础:当群众的个人自觉意识了解规则必须具有一种社会制裁的时候,这种规则便是法律规则,就是社会连带的感觉和公平的感觉使法律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也使组成法律规范实施的习惯或成文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法律规则只是因为有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6]。狄冀根据其实证主义哲学认为,有关国家起源的试图通过超尘世力量的世俗介入来解释政治权力并使其合法化的神权政治学说,所有将政治权力来源归结于社会公众的意志并因这种来源获得其合法性的民主政治学说,都是虚幻无用的[6]。他认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将公法与私法绝对割裂开来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不可接受的;基于其社会关联性理论,他认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一样,也处于社会相互依存性的控制下,像所有社会成员一样,也要遵守立足于该相互关联性基础之上的法律规则。这种法律规则同时约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被统治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有而且只有一条永远相同的法律规则,即服从于社会相互关联性,公法与私法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6]。由此,狄冀以公私法存在的共同基础否定公私法划分的合理性。
此外,凯尔森认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由法律应然地确立的,而是由国家对公民事实上的支配的现实确定的。而公、私法的区别却又是立足于应然状态下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以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为内容的法律关系。他认为,区别公法与私法的主张,全是以国家与人民间的关系为无限制的权力关系,作为与私人相互间的关系完全不同性质之专制时代的遗物,在法治主义时代,是早已不能维持了的[6]。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如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具有特殊性,并以此作为否定公、私法划分的理由。
尽管上述有狄冀和凯尔森否定公、私法划分的论点作为反对的理论支撑,但笔者认为,公、私法划分的仍有其合理性,我们可以不囿于探讨矿业立法整体的公、私法的准确定性,但至少可以借助于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在个别条款或是个案当中用以界定政府公权力和公民个人自由的界限。也就是说,公、私法划分理论可以不作为立法创制的前提设想,只是将其作为个案权衡的理论工具。至于所创制的矿业立法的公、私法属性并不需要太多思考或定义附加其上。一部法律的合理性并不一定是基于其公法或是私法的准确定位之上的,笔者认为借助于立法原则完全可以予以保障以实现所制定法的合理性。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最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的中国立法基本原则有四项:一是宪法原则;二是法治原则;三是民主原则;四是科学原则[7]。严格遵循这四项制定出来的矿业立法的公、私法属性的确定对于我们而言已然是不重要了。
对于部门法属性而言,部门法的划分也是形式理性的产物。依据通说,法律体系即为部门法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一般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的理论归整,在其依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于法律部门的分类和组合中,亦在依据归纳——演绎的逻辑链条梳理着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而,对于法律的创制、适用和完善具有指导意义法律体系,指示法律思维和法律技术的理性化和自觉化,标志着社会关系和立法的成熟程度[8]。这是以部门法为基本单元的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概念或是本体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正基于此,我们似乎惯常性地把每一部法律分门别类予以规整。然而,既已确定的部门法体系是否能够容纳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制定出来的各种法律法规是部门法体系理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初步建立,这一法律体系是指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由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统一整体。部门法体系划分的首要标准是调整对象的不同。而作为调整对象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此与彼的划分似乎也不能做到泾渭分明。这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必有其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并且这种特殊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决定是否把其纳入到某一个法律部门。正确把握这个特殊性的“度”就很关键,如果不够“度”,就不能反映出部门法调整对象的全部特殊性,从而把应由别的部门法调整的利益关系也包括进来了,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过“度”了,它就没有反映出部门法调整对象的全部共性,也就不能把应由该部门法调整的全部利益关系包括在其中[9]。然而,以特定社会关系为划分标准的部门法体系的科学性是建立在首先其能统摄所有的可以据以确定权利和义务以及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其次是划入相应的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相对其他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以此来审视我国目前的部门法体系便可对其科学性管窥一二了。
对于第一项标准,现行的部门法体系就似乎稍显力不从心。因为据以确定权利和义务以及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并不局限于法律条文,而现行部门法体系最小的构成单元就是以法律条文为表现形式的法律规范。基于此,刘作翔教授提出以“规范体系”代“法律体系”之用以避短扬长。法律体系解决的是立法性产品,立法性产品可以放进去,而司法解释不是立法性产品。但国家政策、习惯已经被法律明确规定为在特定情况下即法律缺位时的行为依据和裁决依据,司法解释更是作为一种法定的裁决依据[10]。规范体系可以把发展变化的新的规范类型吸收进去,它以规范类型作为其组成单元,而不是以法律部门,因为法律部门很严格,必须是法律才能放进去,不是法律的就放不进去[10]。由此,在规范体系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包含有调整矿业法律关系的实质规范都可以纳入到矿业立法的规范系统当中。即便是未来较为系统而完善的《矿业法》的制定出台,也不能否定除法律之外的规范类型所具有的规范效力。以这种开放性的视角看待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有利于减少基于有限理性之上的立法再因有限理性的体系整合而丧失的作为一个系统应当具有的内外部融贯和顺应社会发展的功能特质。
对于法律概念而言,法律概念可以被视为是用来以一种简略的方式辨识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的工作性工具[11]。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易懂明了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给他人,如果我们试图完全摒弃概念,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化为灰烬[12]。法律规范是个开放系统,社会的发展,人的认识发展,也要求人的理性程度必须同步发展。唯有如此,才可以从“法”的理据性原则和通用性原则出发,真正完善确立法律概念的确定性,使之在新事物出现后不会出现法律空白,并且在“共同标准”的普遍适用性问题上,不被人任意理解[13]。然而,或许我们还应当看到任何概念的定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与真正的事实存在发生偏离。我们语言的丰富程度和精妙程度还不足以反映自然现象在种类上的无限性、自然要素的组合与变化,以及一个事物向另一个事物的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些演变则具有着如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客观现实的特性[14]。也正是如此,任何法律概念的界定都不免是一次冒险。正如法官卡多佐所言:“当概念被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全然无视后果的方式被发展到其逻辑的极限时,概念就不再是仆人而是暴君了。”[15]所以,法律概念的确定性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度”以达到法律概念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统一。法律概念的模糊性是指涵十分确定的法律概念,存在着外延边缘上的模糊性问题,即使一个人们认为十分确切的概念,如果深究下去,它也存在着外延的模糊性问题。所谓概念外延边缘的模糊性,就是指客观对象中存在有难以界定是否属于某个概念外延的两可情形[16]。那么在把握法律概念的确定性的时候应当注意回避两可情形。两可情形的法律适用可以交由法律适用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明确法律概念在适用个案时的具体含义。这样一种确定性与模糊性有机统一的法律概念确定技术有助于缓解法律的僵硬性和滞后性。
此外,法律概念作为法律的最小单元,有时也是整部法律的理论基础。诸如“矿业权”概念的确定,在矿业法当中对其概念或者对“矿业权的取得”概念所作的明确定义是立法者对矿业权性质的认识的直接反映。再如对“权利金”、“资源税”等概念的界定是把握国家矿产资源收益体系的基础,而国家取得矿产资源收益的根据又与矿业权的性质息息相关。由此,笔者认为在界定法律概念的时候,涉及到整部法律的理论基础的法律概念,其概念的确定性或者是周延性应当达到足以支持其作为法律推理的前提的程度。
2.2 于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之上的探寻
一个产业的发展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是产业立法的调整对象,所以针对产业立法模式选择的探讨还需落实到对以各产业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兼论的是矿业立法的立法模式选择,是把矿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来看待的,另言之,矿业立法将不再局限于现行矿产资源立法的立法模式结构和内容。这也是矿业立法功能定位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作出的有别于以往和现行矿业资源立法的正确选择。谓之正确,是因为矿业发展的基础和功能都愈加地趋近于一个完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以及其所应当负担的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时代重任。
以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待矿业立法的开放性,是指矿业立法应当能够与其他在产业发展上相关的立法相互衔接,并且矿业立法在能够保证矿业作为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产业格局当中处于恰当的位置。一些以采矿业为第一支柱产业的城市为避免“矿竭城衰”不得不采取“城市转型”的发展方针,以及将矿业作为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支柱产业的政策方针就是矿业作为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产业格局中位置失当的一个缩影和例证。
此外,我国对矿业的产业定位也不尽合理。只有当某种市场需求在普遍性和持续性都达到相当程度时,才可能赢得人们对它的先行投资,从而建立起相应的产业来[17]。唯有抓住决定着不同产业发生发展的根本因素,即以人们对特定产品使用价值的相对丛集性和持续性市场需求为产业类型的划分标准,方才能够使划分的对象涵盖面达到完整的外延范围,从而避免不停地抛弃旧的划分标准并寻找新的划分标准,以将新的产业类型包含进来的被动和盲从局面[17]。由此,笔者引用决定产业发生发展的根本因素即人们对特定产品使用价值的相对丛集性和持续性市场需求作为产业类别划分的依据。这种开放式的划分依据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有利于保证产业类别划分的科学性。根据“需求标准划分法”,姑且可以把产业二分为基本需求产业和可变需求产业。基本需求产业是指依据人们在相当时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市场需求而设立的产业[17],如农业、能源矿产业等。故此,可以将我国的采矿业和探矿业与农业归入为同一产业。如此而为的原因在于矿业同农业一样都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直接从自然界取得物质和能量的产业。从而,其同农业一样均处于人类生产活动的最初阶段。既然与农业为同一产业,那么就必然要发挥其同农业一样的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功能。矿业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为下游产业创造附加值提供物质载体。至于作为探矿业和采矿业下游产业的矿产品加工业则不应当纳入到矿业的范畴之中。所以,矿业立法所应调整和确立的矿业法律关系的范畴应只包括探矿业法律关系和采矿业法律关系。
基于前文有关矿业的产业定位分析,作为基础产业的矿业,其产业功能并不在于为国家直接创造财富。这一定性对于矿业的发展以及其立法的具体制度构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对于矿业的发展而言,也正如上文所述,作为基础产业的矿业就不能承担起支柱产业的时代重任以及超出其基本功能之外的社会经济功能。矿业所具有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功能也决定了矿业必需要和其他产业,尤其是下游以及同级配套产业进行合理衔接。
其次对于矿业立法的具体制度构建而言,矿业的基础产业定位以及由其决定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功能,决定了矿业权的性质以及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实现的性质和方式。因为,作为基础产业的探矿业和采矿业并不承担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发展重任,所以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现应当淡化其收益功能并同时强化其投资补偿功能和代际补偿功能。投资补偿功能集中体现为取得由国家出资勘查探明的矿产地上的探矿权、采矿权应当支付的矿业权价款。因为矿业权价款就是为了收回国家的勘查投入;而代际补偿功能集中体现为权利金和资源税。因为权利金和资源税其本质是对因开采而消耗的矿产资源需要对国家支付的补偿金。名义上是对国家支付的补偿费,但其实质是因资源总量的减少而向后代支付的补偿费。
此外,作为抽象所有权主体的国家是不能参与生产活动的最初阶段的。由此,矿业的基础产业定位以及其作为生产活动的最初阶段的特性,也决定了矿业权应当具备由特定的经营性组织代国家行使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特定功能。这种特定功能也就决定了矿业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因为国家作为抽象的所有权人,其不能自行行使权利的各项权能,但其可以将部分权能让与特定实体以间接地实现其权利的价值。部分权能的让与形成了定限物权,而定限物权中的担保物权又因其从属性而难当大任。由此,确定矿业权以用益物权的性质是发挥其上述特定功能的逻辑推演。
3 矿业立法独立性的基础
立法的独立性是指立法这一系统的内部各组成部分自成系统且能相互配合与衔接。据此可知,矿业立法的独立性是指矿业立法内部各组成要素能相互融贯并能自行维持一部法律的正常运行。作为矿业立法的独立性基础的法学理论客观规律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相互交融而须臾不可分离,这是由一个独立的系统所具有的融贯性决定的。如前文所述,如果一部法律内部诸要素的组合不能促成其特定立法目的和功能的实现而需要依赖其他法律,则不能称其为一个系统。
矿业立法的独立性表现为矿业立法作为一个系统涵盖了一个产业健康发展所需的全部关键要素,并且相互之间在功能上和逻辑结构上均能达致融贯。这一部分的探寻直接涉及到矿业立法的具体制度设计,基于本文旨在提供一种立法模式的构建路径之由,笔者在此淡化有关具体制度设计的笔墨而重点探讨确定各关键要素及其组合的方法。
在此需要区分两个领域:政府管制领域和市场支配领域。如同上文有关公、私法划分一般,政府和市场关系在立法当中也是一道不得不逾越的障碍。然则,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确定还得落实于对于作为基础产业的矿业而言所应当承载的政府管制该如何界定。对于基础产业而言,产业的发展关系国计民生,所以笔者认为政府管制在产业的准入、过程以及退出方面应当有所体现。产业的准入和退出当中的政府管制存在的必要性无需多言,然,对于“过程”当中的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则因其复杂性而不得不详细探讨。“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法律关系有:矿业权人和作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之间的关系,矿业权人和非矿业权人之间的关系,非矿业权人和作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上四对法律关系中可能涉及公权力行使的有矿业权人和作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非矿业权人和作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对法律关系当中的前者是指作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人的国家基于其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对矿业权人矿业权的行使进行监督管理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后者是作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人的国家基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中的排除妨碍权能对非矿业权人进行监督管理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前者可具体化为矿产资源规划制度;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制度;勘查技术标准、规程管理制度;勘查报告管理制度;地质调查管理制度;最低勘查投入管理制度;探矿权和采矿权衔接管理制度;开采方式管理制度;开采总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矿产品流通和分配管理制度;矿业用地管理制度;矿区环境保护和修复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执法管理制度和行政责任制度。这些制度是根据维持矿业活动进行所需的正常秩序而确定的政府管制。而后者可以具体化为相应的行政责任制度。
确定好政府管制领域之后,市场支配领域又应当确立哪些制度呢?笔者认为,一个健全的矿业权市场应当具备两个要素:一为完善的产权制度,这里包括矿产资源所有权与矿业权的关系制度和矿业权取得、变更、转让与消灭制度;二为完善的民事责任制度,这里主要是指因侵权而引发的民事责任制度。
4 结语
矿业立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应当具有由其整体性所阐发的开放性和独立性。然而,矿业立法作为一项产业立法,更是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其必须遵循相应的法律理论的客观规律和矿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将其作为矿业立法的开放性和独立性的基础。构建一部理想状态中的法律,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其都能发挥一个系统所应当有的生命力。上文所述就是基于这个理想目标所应当具有的状态所做的描摹并对每一笔的描摹阐述其理论根据。本文意在为构建兼具开放性和独立性的立法模式提出作者的看法,并希望以此作为未来矿业立法模式的一种有益借鉴。
[1]钱学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221.
[2](奥)路德维希·冯·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M].秋同,袁嘉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4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4.
[4]乌杰.系统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5]李诗和.系统哲学与整体性思维方式[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2):25-28.
[6]曹治国.公法与私法划分否认说及其评价——兼论公私法划分的必要性[J].法治研究, 2007(4):74-80.
[7]周旺生.论中国立法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J].法学论坛,2003(3):29-36.
[8]马新福.法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21.
[9]颜俊.论法的规范体系[J].当代法学,1991(4):18-23,27.
[10]刘作翔.规范体系:一个新体系结构的思考[J].东方法学,2013 (1):64-76.
[1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01.
[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04.
[13]张晓芒.法律概念与开放系统[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5-10.
[1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03.
[15]Benjamin N.Cardozo.The Paradoxes of Legal Science[M]. New York:Lawbook Exchange,1928:61.
[16]张静.论法律概念的特征[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3):54-57.
[17]杨达.现代社会产业类型划分方法[J].企业经济,1998(6):14-17.
Building Opening and Independent Legislation Model in Mining Industry
LI Xiandong, XIE Tao
(Civial,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the dilemma we face in mining legisl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business, and we must seek a new path so as to pursue the legislation model that we must follow in mining legisl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y of system philosophy must be the whole and basis of our efforts to elucidate the openness and independence that a law with wholeness or coherent should have. With openness to mining legislation model, narrow theoretical controversy can be eliminated and the beneficial interaction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can be allowed. And the integrity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legislation can be maintained with independenc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bjective law of legal theory and the objective law of mining development what the openness and independen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objective law of legal theory means that with regard to the system and concept which legislated, the useless theoretical controversy should be got rid of and focusing on real legislation requirements. The objective law of mining development means that legislation should be faithful to the law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hind the social relations that are adjusted by the legislation.
mining legislation; system theory; open; independence; objective laws
F407.1 ;DF01
C
1672-6995(2014)10-0010-06
2014-09-10;
2014-10-07
李显冬(1951-),男,山西省太谷县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国土资源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矿业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