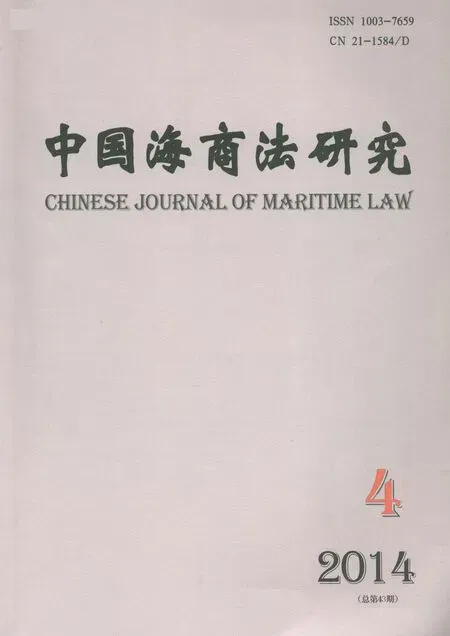论凭单放货要求对记名提单的直接适用性
董金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记名提单无单放货纠纷在中国海事诉讼当中较为常见,尤其表现为承运人在未获得正本提单的情形下向该记名提单载明的收货人放货。该问题的法律适用一度引起理论界的热议。此类案件审理的难点不在于案情的复杂,而是如何看待中国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的性质。如果将之视为直接适用的法*此类规范还被称为超越一切的制定法(overriding statutes)、自我限定的规则(self-limited rule)、公序法(lois de police)、干预规范(eingriffsnormen)、专属规范(exclusivnormen)。,则可以优于提单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或在没有选择时根据最密切联系指引的外国准据法。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法律适用法》)第4条首次设置了直接适用的法制度*《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使得这一命题更具有实践价值,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对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的要求是否构成《法律适用法》下的直接适用的法。着眼于司法实践对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能否直接适用的争议,笔者从实体法、冲突法以及比较法层面探讨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的直接适用性质,希望对该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一、司法实践关于凭单放货要求能否直接适用于记名提单的争议
(一)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构成直接适用的法的司法实践
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是否构成无须冲突规范指引的直接适用的法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争议。早在《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就有判决认为凭单放货要求构成直接适用的法。在江苏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夏货运有限公司无单放货纠纷案*参见上海海事法院(2003)沪海法商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书。中,二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提单背面条款所载明的《1936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及其指向的美国提单法中关于记名提单可以无单放货的规定*《1936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没有规定记名提单,而其指向的《1916年美国联邦提单法》即1994年修订后的《美国法典》第四十九卷第八百零一章第80 110条第2款规定承运人可以向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提单)所载明的收货人无单放货。,违反了《海商法》第四章第44条和第71条的强制性规定,故提单的法律选择条款无效。此种能够导致当事人选择法律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即构成直接适用的法。
(二)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不构成直接适用的法的司法实践
在类似的案件中,法院却肯定此种争议的当事人选择的或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引的外国法的适用。如在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与菲达电器厂、菲利公司、长城公司无单放货纠纷再审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8)交提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可了提单首要条款规定的《1936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及其指引的美国提单法的效力;在江苏轻工诉江苏环球、美国博联公司无单放货案*参见武汉海事法院(1999)武海法宁商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中,武汉海事法院认为,鉴于提单的首要条款约定的《1936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对正本提单无单放货没有规定,故此应该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最密切联系应考虑与案件的特定争议有关的连结因素。本案的争议在于承运人交货行为引发的法律后果,而交货行为直接受交货行为地法律约束,故交货地(美国)而非签订地或始发地(中国)与该问题存在实质性联系。武汉海事法院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7-303条第1款c项的规定*除非提单另有规定,承运人在接到不可流通提单的收货人的指示后,只要发货人未有相反指示,且货物已到达提单所注明的目的地或收货人已占有提单,可以依指示将货物交付非提单注明的人、目的地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货物。,免除了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向记名收货人放货的责任。
(三)该问题在《法律适用法》生效后的状况
上述案件的共同点在于,法院认为无单放货纠纷应定性为合同纠纷,从而根据一般的冲突规范寻找合同准据法,特别承认提单条款对外国法的选择。然而不同的案件结果却是因为中国的凭单放货要求是否能替代允许记名提单无单放货的外国准据法特别是美国法的规定。就各地的做法而言,至少上海法院长期坚持作为强制性规定的中国法中关于记名提单的凭单放货要求应当直接适用*参见上海海事法院(2009)沪海法商初字第932号民事判决书。。由于《法律适用法》生效时间尚短,尚无判决表证明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的态度发生何种改变。不过,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倾向于认为《海商法》第四章的内容不属于《法律适用法》第4条下的可直接适用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的法律。[1]无论此种看法是否正确,对各地法院能否产生约束,都存在说理不充分的缺陷。
二、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的实体法分析
任意规范不构成一国基本政策的表达,没有理由认为可优先于准据法而适用。[2]故直接适用的法必须首先是不为当事人排除的国内意义的强制规范。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是否构成强制规范必须从实体法的角度寻求答案。
(一)现行法对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的规定
关于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首先可以从《海商法》“提单定义”中推导。仿效《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而《海商法》第44条第1款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似乎可以认为这一要求是强制性的,不得通过合同条款排除。
就此问题,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第1条,无单放货下的提单情形包括记名提单、指示提单和不记名提单三种形式,从而明确记名提单同样需要凭单放货。不过,记名提单在中国法下不可转让*与《1916年美国联邦提单法》不同,根据《海商法》第79条,即使记名提单未注明不可转让,也不得转让。,不能流通,无须像空白提单或指示提单那样对提单持有人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此时提单所表彰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除了作为当事人的承运人和托运人之外,还存在收货人这一关系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十七章第三节货运合同的规定类似,记名提单下收货人的权利地位为托运人和承运人缔结的运输合同所赋予,在交付之前自然可以为当事人撤销或解除。[3]故《规定》第9条认为,承运人按照记名提单托运人的要求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持有记名提单的收货人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含义的正确解释
在记名提单的情形下,承运人按照托运人的指示可以向持有正本提单的收货人之外的人放货,构成凭单放货的例外。然而《规定》没有对承运人对记名提单的收货人无单放货的情形作出特别规定,这能否说明承运人在此时无一例外地要承担责任?由于记名提单无须考虑维护托运人、承运人和记名收货人之外的人的利益。如前所述,此时记名收货人的权利纯粹是托运人和承运人约定的结果,当事人可以变更。能否向记名提单的收货人无单放货,仅仅与托运人和承运人的利益相关。
合同法的规定主要为了补充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不足,故多为任意性规范。设置强制性规定无非出于以下目的: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保护与合同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平衡合同当事人的权益。从海上货物运输的实践看,格式合同的广泛运用导致了承运人缔约地位的强势。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即使是强制的,也仅仅在于平衡托运人和承运人的利益,即给予弱势一方的托运人以特别保护。在托运人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即提单背后条款列明,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可以由其预先处分,以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流程的快捷、高效。不应该将当事人另行选择法律当中的许可条款视为托运人对记名提单无单放货的明确认可。《海商法》第44条的约定无效仅仅针对当事人实体法层面的约定,并不具有冲突法价值。同样,托运人预先处分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的例外情形,也不应包括外国准据法当中的许可规定。
由此,《海商法》第71条在实体法下的正确解释应该是,承运人不得向记名提单的收货人无单放货,但托运人明确许可的除外。此类规范不同于任意性规范,在学理上被称为补充性处置性规范,即首先提出了行为人不得违反的强制性规范,然后指出除非行为人另有约定,此时只有行为人排除才不适用法律规定。[4]因此,第71条虽然存在例外规定,但仍具有部分强制性。从中可以看出其具有保护托运人利益的倾向,不同于纯粹由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情形。这使得进一步探讨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的直接适用性成为可能。
三、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与直接适用的法的判断标准
直接适用的法,是指维护一国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公共利益,无须多边冲突规范的指引,直接适用于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实体强制性规范。[5]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虽然构成国内意义的强制规范,但在冲突法层面直接适用还要看直接适用的法的判断标准。综合2008年欧盟《罗马条例I》*《罗马条例I》第9条第1款规定:“超越一切的强制性条款是指对一国维护该国的公共利益,尤其是维护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至关重要而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条款,以至于对属于其适用范围的所有情况,不论根据本条例指引的合同准据法为何都必须适用。”以及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三)涉及环境安全的;(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直接适用的法需要满足冲突法和实体法两重要求,即同时符合超越标准(overriding criterion)和公益标准(public interest criterion)。[6]
(一)超越标准
超越标准是指规范的适用与否由自身决定。该标准能直接反映直接适用的法的性质。有观点认为无须冲突规范指引是由于规范自身包含单边冲突规范。[7]如此一来,直接适用的法也需要冲突规范的指引。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萨维尼式的选法体系建立在对法律关系系统分类的基础上,用以确定一类规则的适用,即使单边冲突规范也采取立法演绎的方式;而直接适用的法是从具体规范出发,根据其意图确立适用范围,需要司法的归纳。
从裁判的角度来看,超越标准对强制规范或所在法律文件就适用范围规定的用语进行审查。用语分析是判断规范性质的常用方式。如果从文义上确切无误地得出强制规范具有超越冲突规范适用的地位,即构成直接适用的法。这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明确规定不顾当事人的选法或合同准据法而适用。如《1996年英国雇佣权利法》第204条“雇佣准据法”第1款规定:“为本法之目的,适用于雇佣的法律是否是英国或英国某一区域的法律无关紧要”;又如《1976年联邦德国标准条款法》第12条第2项规定:“当合同适用外国法时,如果一方当事人于缔约时在本法有效的区域内拥有住所、经常居所或作出接受的承诺,本法仍应适用”;二是制定单独的适用范围条款或强制规范自身表述该法的适用范围,但并未说明同冲突规范的关系。如《1977年苏格兰婚姻法令》第1条第1款关于不满16周岁的苏格兰居民不得结婚的规定,就采用了“居民”这一属人联系表示其国际强制性。但此种情形毕竟没有明确不顾冲突规范的指引,必要时仍需要结合规范的目的、意图加以判断。《〈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也采用超越标准,认为“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
就超越标准在海商法领域的表现,法国1966年6月18日颁布的《有关租船和海上运输的法律》第16条第1款规定:“本章适用于装运港或目的港为法国港口的运输。这被认为是可直接适用的法国公序法的重要表现。”[8]《1936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3条规定:“本法应适用于启运港和目的港为美国港口的任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该法的适用同样无须冲突规范的指引。”《海商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海上运输,是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客运输,包括海江之间、江海之间的直达运输。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从形式上,《海商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规定的适用范围与通行的国际做法不同。第2条仅仅针对中国港口和外国港口之间以及外国港口之间的运输,而非国内海上运输,并未强调其必须适用于装运港或目的港在中国的所有海上货物运输。退一步讲,即使《海商法》存在适用范围的规定,也不能表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构成直接适用的法。因为此类条款往往构成立法对适用范围的自我限定,没有考虑与冲突规范的关系。因此就超越标准而言,中国凭单放货要求并无构成直接适用的法的充分依据。
(二)公益标准
公益标准作为实体法上的标准,根据《罗马条例I》,是指直接适用的法应对保护其所属国诸如政治、社会或经济运行之类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维护公共利益的要求在学理上一直作为直接适用的法的判断标准。如梅耶认为,公序法不仅关乎公共政策,而是反映如此重要的公共政策,以至于它们必须适用;[9]哈特雷认为,狭义强制规范必须能实现其所隶属法律体系中特别重要的具体目标,即通常出于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10]受《罗马条例I》的影响,《〈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0条也确立了公益标准,即必须“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从而顺应了冲突法立法的潮流。
公益标准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那些能够强烈地体现出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意图的诸如外汇管制、外贸管制、反垄断等公法强制规范,无疑构成直接适用的法。而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性强制规范能否直接适用存在争议。[11]对此,作为条例前身的1980年《罗马公约》没有给予明确答复,欧盟法院也未加以解释,缔约国的做法大相径庭。法国法院通常将保护弱者利益的规定视为直接适用的法,而德国法院则更严格地解释公益标准。[12]《罗马条例I》第9条第1款虽然予以定义,但问题并未解决。从表面上看,至关重要公益的规定更接近德国的做法,但公益和私益本身没有明确的界限,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国家利益。为弱势群体制定的法律带有一定的公益考量,且有利于竞争秩序的形成。故成员国的传统司法实践仍大致得以延续。
首先,《〈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0条明确列举了劳动者保护,故可认为中国倾向于将保护性强制规范纳入直接适用的法的范畴。然而旨在保护托运人的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却很难构成直接适用的法。即使将保护消费者、劳动者之类的强制规范视为直接适用的法的范畴,主要针对法人而非自然人的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也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更何况各国并未就此种保护达成共识,实践中的做法十分混乱。[13]其次,《〈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0条将《法律适用法》第4条下的强制性规定限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而与公法进入私法渠道的《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的强制性规定的位阶一致。这说明直接适用的法主要是那些能作用于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该概念参见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重大公益需要绝对排除当事人的意愿而给予整个合同以否定评价。而《海商法》第44条第1款虽然认为违反本章规定的条款无效,但特别强调此类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另外从冲突法的角度,与《罗马条例I》第6条第2款和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不得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和受雇者依照没有选择时应适用的法律中的强制规范的保护不同,《罗马条例I》第5条第1款仍肯定了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具有选择准据法的自由。这一切无不反映该要求难以构成一国重大公益。
除此之外,中国台湾地区的“海商法”第77条*载货证券之装载港或卸货港为台湾港口者,载货证券之法律关系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所定应适用法律。但依本法台湾收货人或托运人保护较优者,应适用本法之规定。独具特色——在允许提单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同时,赋予“海商法”保护本地收货人或托运人的强制规范的效力。但这不属于笔者讨论的范围。台湾地区“民法典”第628条规定,除非有禁止背书的记载,否则记名提单仍可背书转让。故记名提单在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须凭单放货的原因在于此类提单具有流通性;而根据《1916年美国联邦提单法》的规定,可向收货人无单放货的记名提单必须注明“不可转让”字样。由此台湾地区的规定和美国法不存在明显的冲突,无直接适用的需要。
四、来自比较法的启示——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条款的直接适用
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能否直接适用,除了从实体法层面和直接适用的法的一般理论出发,还可以从比较法的实践中寻求答案。目前此类争议主要集中于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条款能否排除当事人另行选择法律的规定而直接适用。
(一)The Hollandia案
在TheHollandia案*参见The Hollandia,[1983] 1 AC 565 HL。中,原告托运人和被告承运人签订一份从英国运至荷属西印度群岛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约定适用荷兰法。货物在运输途中受到的损失高于荷兰法规定的承运人的责任限额,原告就此在英国提起诉讼。与荷兰适用《海牙规则》不同,这时英国已经是《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合同的责任限制条款根据实施《海牙—维斯比规则》的《1971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第8条的规定无效,而根据《海牙规则》则有效。同时,本案满足该法第5条关于适用所有启运自英国港口的海上运输的条件。英国上议院认为《1971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应当直接适用,当事人选择另一国法的适用有损《海牙—维斯比规则》的效力。
关于该案的判决结果,英国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里斯和曼恩曾发生激烈的争执。[14]本质上,《1971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在该案的适用,并非是法院认定该法构成国际私法层面的直接适用的法。条约为统一法之目的,专设条文加以规定其适用范围,不受冲突规范的影响。无论是通过转化还是纳入的方式,缔约国都要善意履行国际义务。[15]因此,英国法院不顾当事人的选法适用《1971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与其他缔约国优先适用《海牙—维斯比规则》类似,属于统一实体规范作用的范畴。至于此类强制性规则的目的、宗旨是否对一国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存在未知之数。
(二)Van Nievelt, Goudriaan and Co’s Stoomvaartmij NV v. NV Hollandsche Assurantie Societeit案
VanNievelt,GoudriaanandCo’sStoomvaartmijNVv.NVHollandscheAssurantieSocieteit案*《罗马条例I》第9条第1款规定:“超越一切的强制性条款是指对一国维护该国的公共利益,尤其是维护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至关重要而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条款,以至于对属于其适用范围的所有情况,不论根据本条例指引的合同准据法为何都必须适用。”参见Van Nievelt, Goudriaan & Co’s Stoomvaartmij N. V. v. N. V. Hollandsche Assurantie Societieit,Hoge Raad 13. 5. 1966。涉及将一批马铃薯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运至巴西里约热内卢港的海上运输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承运人无须就货物运输途中发生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并适用荷兰法。后来因故发生货损,托运人的保险人在荷兰对承运人提起诉讼。本案的争议在于法律适用问题。由于比利时在案件发生时加入了《海牙规则》,并通过《比利时商法典》予以实施,而且《海牙规则》适用于起运港在缔约国的海上运输所签发的提单,本案的提单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签发,故损害赔偿问题适用《海牙规则》的规定。在本案合同订立时,荷兰尚未加入《海牙规则》,当事人选择的荷兰法不包括公约对承运人责任限制的规定。
荷兰最高法院认为,国际合同的当事人原则上可以选择准据法,甚至可以排除包括强制规范在内的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只要这样做不违反荷兰的强行法以及不允许法律选择的冲突规范即可。但就本案讨论的合同而言,如果其他国家对在其领土外遵循特定强制规范拥有如此重要的利益以至于荷兰法院必须考虑,则法院应予以适用。比利时法虽然构成没有选择时应适用的法律,但不能体现比利时的重大利益,不具有优于当事人选择的荷兰法的性质。故荷兰最高法院更强调规范的重大利益属性,即并非所有的强制规范都具有潜在的直接适用资格,有关海上承运人强制责任的规定不满足重大利益的要求,无法排除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而直接适用。
(三)评价
TheHollandia案看似构成海上货物运输法当中的强制规范特别是承运人责任限制条款直接适用的依据,但实质上仅仅是条约在缔约国强制适用的结果。首先,《1971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海牙—维斯比规则》的条款具有法律的效力。其次,根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10条对适用范围的规定,当提单在某一缔约国签发或起运港位于缔约国,公约必须适用。二者都说明该法不受当事人意思的影响。审理VanNievelt,GoudriaanandCo’sStoomvaartmijNVv.NVHollandscheAssurantieSocieteit案的荷兰法院探讨国际私法层面的外国直接适用的法,这是有史以来司法实践首次明确赋予外国强制规范以直接适用的资格。该案最终以此类海事强制规范的公益性质不足为由拒绝适用。故虽然作为起草《罗马公约》工作组成员评述的《〈罗马公约〉报告》认为直接适用的法包括有关运输的强制规范,[16]但至少就保护托运人利益的记名提单的凭单放货要求而言,此种见解在比较法上难以获得支持。
五、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中国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在实体法层面只具有部分强制性。虽然原则上须凭单放货,但在托运人许可的情况下,承运人可以向记名收货人无单放货。这只能以明示的方式为之,而不包括当事人选择外国准据法当中存在许可规范的情形;其次,出于保护托运人利益的考虑,该要求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在冲突法层面并不满足直接适用的法通行的判断标准,既没有明确规定其必须适用,也不能反映国家的重大公益;最后,在比较法层面,虽然有观点支持直接适用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条款的判决,但这更多的是缔约国实施统一提单条约的结果,而且司法实践倾向于否定外国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条款构成直接适用的法。总之,记名提单的凭单放货要求不宜视为中国的直接适用的法,当事人选择美国法等域外法的效力在原则上应该予以承认。
为了防止记名提单下无单放货法律适用争议的发生,对托运人而言,在收回货款存在风险时,应谨慎选用记名提单。如需要签发记名提单且希望凭单放货,应效仿《鹿特丹规则》第46条在提单正面特别注明;[17]对承运人而言,宜在提单背面规定,除非托运人另有指示,否则签发记名提单的承运人可以在目的港验证记名提单收货人的身份后无单放货。根据上述分析,这与美国法的规定相一致,同时也不违反《海商法》第71条保护托运人的法律意图。承认该条款的合法效力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又能够达到公正的结果,可避免司法实践中对提单准据法的确立所发生的争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刘贵祥.在全国海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EB/OL].(2012-12-26)[2014-07-02].http://www.court.gov.cn/spyw/mssp/201212/t20121226_181432.htm.
LIU Gui-xiang.Summary speech at the working conference on national maritime trial[EB/OL].(2012-12-26)[2014-07-02].http://www.court.gov.cn/spyw/mssp/201212/t20121226_181432.htm.(in Chinese)
[2]BONOMI A.Mandatory ru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 quest for uniformity of decisions in a global environment[J].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999(1):223.
[3]吴文嫔.第三人利益合同原理与制度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45-150.
WU Wen-pin.On the theory and regime of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contract[M].Beijing:Law Press,2009:145-150.(in Chinese)
[4]许中缘.论任意性规范——一种比较法的视角[J].政治与法律,2008(11):64.
XU Zhong-yuan.On the default rul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J].Politics and Law,2008(11):64. (in Chinese)
[5]肖永平,龙威狄.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107.
XIAO Yong-ping,LONG Wei-di.On the internationally mandatory rules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China[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2(10):107.(in Chinese)
[6]KUNDA I.Defining internationally mandatory rules in European contract conflict of laws[J].Zeitschrift für das Privatrecht der Europ ischen Union,2007(5):210-222.
[8]QTAISHAT K S.Le role de l'ordre public et des lois de police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rivees[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0(2):11.
QTAISHAT K S.The role of public order and the rules of immediate appl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rivate relations[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10(2):11.(in French)
[9]MAYER P.Mandatory rules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J].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1986(4):275.
[10]HARTLEY T C.Mandatory rule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the common law approach[J].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1997(266):345-346.
[11]VISCHER F.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1992(232):158-159.
[12]PLENDER R.The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obligation[M].London:Sweet & Maxwell,2009:351-353.
[13]李小年.《鹿特丹规则》对不可流通运输单证的法律协调[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1):42.
LI Xiao-nian.Harmonization of non-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s in theRotterdamRules[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10(1):42.(in Chinese)
[14]COLLIER J G.Conflict of laws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Hague-VisbyRules—contracting out[J].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1982(2):253-255.
[15]董金鑫.论英国法上超越一切的制定法[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6.
DONG Jin-xin.On the overriding statutes in English law[J].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3(3):46.(in Chinese)
[16]GIULIANO M,LAGARDE P.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EB/OL].(1980-10-31)[2014-07-02].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1980Y1031(01):EN:HTML.
[17]王堉苓.简评《鹿特丹规则》对无单放货之规定[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3):14.
WANG Yu-ling.Brief comments o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relating to releasing cargo without production of B/L under theRotterdamRules[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09(3):14.(in Chinese)
——以交付的“可能”与“现实”为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