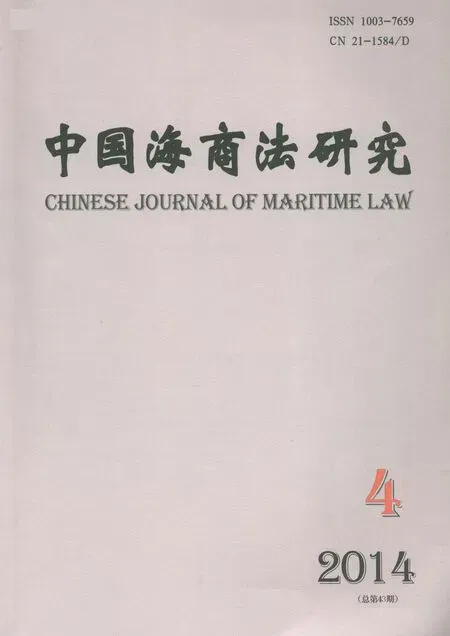《纽约公约》中“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①
——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8起案件为样本
徐春龙,李立菲
(广州海事法院 深圳法庭,广东 深圳 518081)
无论仲裁的性质是法官替代论、契约论、意思自治论还是民间论,现代世界各国对仲裁的尊重均系常态。但仲裁仍要接受司法监督,某种意义上,司法仍是仲裁的终局裁判者。但这种终局裁判,无疑应是审慎的。因此,各国立法都为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限定了诸多条件。为进一步规范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1958年6月10日,有关缔约国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国际商业仲裁会议上签署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该公约仅在第5条第2款规定了不予承认与执行公约项下仲裁裁决的情形,且区分了依申请人申请和依法院审查两种情形,对于依申请人申请者,若无当事人抗辩,则法院不可依职权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也明确了此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麦考·奈浦敦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2001年4月23日,法民二[2001]32号)第3条。。由此,奠定了《纽约公约》“支持仲裁”的大原则,以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为原则,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为例外。而在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中,最难把握的就是《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的“公共政策”。因《纽约公约》并没有采取列明的方式规定何为“公共政策”,各缔约国理解与适用并不完全一致。有学者曾言,“公共政策好比一匹难以驾驭之马,一旦跨上去,就根本不知道它会将你带向何方。”[1-2]虽说有些夸大之嫌,但从侧面亦可知公共政策的理解和适用着实是一个难题。而如何准确把握和理解公共政策的内涵及外延,履行公约义务,也就成了中国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中一项重要课题。
一、“公共政策”司法审查的“差异化”
为加强对《纽约公约》项下仲裁裁决的审慎司法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两次发文*具体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第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28号)第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和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2000]51号)第3条。明确对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实行内部个案逐级报批制度,地方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前,不得制发裁定。从司法实践看,在涉及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法院存在明显差异。
笔者选取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8起涉及《纽约公约》项下公共政策司法审查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查与适用公共政策的具体个案情况见文尾表1。对中国各级法院对《纽约公约》项下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进行评析。这8起案件分别为: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案、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案、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案、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案、GRD Minproc有限公司案、天瑞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案、路易达孚商品亚洲有限公司案、韦斯瓦克公司案。根据统计,8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只认定了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案中存在需援引公共政策的情形,其余7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均未予认定。缘何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笔者从认识对象的概念明确性、主体认知的差异以及主体考量利益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公共政策”概念模糊不定。中国国内立法并无“公共政策”这一语词,使用与其较为接近的语词是“社会公共利益”*参见:程序类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08条、第237条、第274条、第276条、第28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条;实体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7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条、第52条、第12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条、第14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等。,上述8起案件中个别地方法院使用的语词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政策本是一个国际私法概念,为普通法系国家广泛应用,英译为:public policy。在大陆法系与其具有内涵等同意义的语词是“公共秩序”,一般译为order public或public order。[3]无论《纽约公约》,还是中国法律,对“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共利益”都没有明确界定其具体涵义及适用边界。因此,认知客体概念的模糊不定造成了各级法院对公共政策的不同理解。GRD Minproc有限公司案、路易达孚商品亚洲有限公司案及韦斯瓦克公司案中,地方法院将仲裁结果的不公正及仲裁员对执行地国法律误读等侵害内国局部公共利益的事项解读为《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而最高人民法院则将《纽约公约》的公共政策范围限定在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第二,主体认知能力不同。单纯从《纽约公约》文本来看,关于“公共政策”的规定似乎是保证和实现司法对仲裁的监督,使“公共政策”作为阻却仲裁裁决发生实际效力的“安全阀”。但笔者认为这是对《纽约公约》的误读。从《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明确列明的5种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来看,只有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时方可依申请而为审查(不申请者司法不介入),而出于对仲裁的尊重,对于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并不作为不予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之理由。第5条第2款关于不可仲裁性和公共政策的规定,虽然保留了法院依职权监督仲裁的形式权利,但更希望达致的是提醒各缔约国限制依职权适用上述2个条款。在《纽约公约》项下“公共政策”的理解层面,地方法院更倾向于选择司法对仲裁的监督,从区域本位主义出发界定公共政策范围,将一主体、一地、一法律的利益界定为“社会公共利益”,并将之上升为《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案、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案及天瑞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案将一些内国强制性规范解读为“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则坚持尊重公约主旨精神、支持和鼓励仲裁,在司法审查时,注意区分内国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注重考察其他缔约国的普遍做法,并不单纯受制于区域功利主义,将司法审查范围严格限定在仲裁裁决是否存在侵犯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公认的公共政策事宜。
第三,裁判主体考量利益不同。地方法院经费及人员独立性差,在涉及某些重大的区域利益之时,只能从区域功利主义来界定“公共政策”。上海两级法院在GRD Minproc有限公司案中面对的现实是:在对系争设备进行调试生产时有5名人员因发生铅中毒而住院,且申请方飞轮公司先后通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个人,以及公司所属职工联名的方式,向市人大、市政府相关领导反映系争设备运行的污染情况及其对该公司造成的恶果,有关媒体也有相应的报道。因此对地方法院而言,保障地方公共利益也就是保障自身的利益,援引公共政策拒绝执行仲裁裁决,既可缓解地方现实压力,也可体现司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且因内部报批案件并不列为考核指标,还免除指标考核压力。而最高人民法院地位相对地方法院而言,更为“超然”,受地方利益的牵制小,而易于从尊重公约、理解公约以及国家整体主义的角度去考量公共政策问题。
二、“公共政策”适用理念、内涵及外延的“趋同化”
截至2014年11月,《纽约公约》已经有153个缔约国,中国作为成员国之一,在理解与适用公共政策时,应关注其他缔约国的新近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的最新进展。从笔者考察的情况看,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实务界与理论界在公共政策适用的理念、公共政策的内涵与外延等层面的理解日益趋同。
(一)限制解释与适用
各缔约国以限缩解释公共政策、限制适用公共政策为大原则。有学者对140多件援引公共政策抗辩的案件进行统计,其中仅有5件最终以公共政策为由阻却了仲裁裁决的执行。[4-5]传统的内国法的强制性规则、缔约国的局部利益、仲裁人员的过失等已经被排除在公共政策范围之外。NationalOilCorp.v.LibyanSunOilCorp.案*参见National Oil Corp. v. Libyan Sun Oil Corp.,733 F. Supra. 800 at 819(Del.,1990)。中,美国法院认为,“将公共政策理解为保护本国政治利益的狭隘工具将会严重贬损《纽约公约》的价值,该条款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国际政治的问题在‘公共政策’上大作文章。”[6]85WestacreInvestmentsInc.v.Jugoimport-SDPRHoldingCo.Ltd.案*参见[1998] 2 Lloyd’s Report 111。中,[7]科尔曼(Colman)法官认为,尽量尊重裁决的终局性的公共政策显然压倒了防止国际交易中贪污受贿的公共政策。他还指出,本案判决并不是对某些行贿行为视而不见,而是表明法庭对国际商会仲裁庭的信心;印度最高法院在1994年审理的一个案件中指出,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外国裁决仅有违反印度法的事实是不足够的,而必须是与印度法律的根本原则、印度的国家利益和印度的公序良俗相抵触*参见Inter Maritime Management SA v. Russin & Vecchi,9 January 1995,reprinted in (1997) XXII Yearbook 789。;[6]87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1995年审理的一个案件中认为,当外国法的规定与瑞士的强行性的法规不同时,并不必然实质性地违反公共政策。[6]87
(二)指向国家根本利益与价值
欧盟法院在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对公共政策适用较窄的标准,在Krombachv.Bamberski案中,欧盟法院称,“只有当在其他成员国承认和执行该判决会违反执行地国的基本原则、违反该国的法律秩序到难以接受的地步时,适用才是合理的。……这种违反必须是能够明显地对被视为执行地国的法律秩序的根本法治的违反,或者是对被执行地国的法律秩序视为基本权利的违反”;[6]95加拿大上诉法院在SocietyofLloyd’sv.Saunders案中指出,“公共政策”只涉及一国的根本正义或道德,适用范围很窄;承认和执行违反加拿大某些强制性规则(mandatory rules)的判决并不一定违反加拿大的“公共政策”;[7]卢(Lew)教授认为,虽然永远无法对公共政策提出一个全面的、深刻的定义,但是它应该能反映每个国家或者国际社会的基本的经济、法律、道德、政治、宗教以及社会准则;[8-9]福查德(Fouchard)等也指出,“并非所有违反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强制性规范的情形都能构成拒绝承认或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的合理理由;只有裁决违反了反映该国的根本信仰或者具有绝对意义的普世价值原则,拒绝承认或执行此项裁决才具备合理性”。[10]64
(三)指向范围更狭窄的“国际公共政策”
1999年非洲统一商事法组织的《统一仲裁法》中明确规定了“国际公共政策”;法国、葡萄牙等国国内立法中也采用了“国际公共政策”概念;大多数国家虽然没有规定“国际公共政策”,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明确区分了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艾伯特(Albert Jan van den Berg)在《2008年“新纽约公约”学者设想草案》第5条第(h)项指出,“执行裁决将违反被请求执行国通行的国际公共政策”;[11]国际法协会的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2002年在新德里提出了《关于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最终报告》(简称《最终报告》),明确提出了“国际公共政策”概念,并在第1(b)中建议,“只有在国际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违反国际公共政策时,才能认为存在此种例外情况”;[12]《最终报告》将“国际公共政策”限定为下列三种情形:一是与一国希望保护的与公正或道德相关的基本原则,即使它并未直接涉及;二是专门为一国根本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利益服务的规则;它们也是广为人知的“警察法”或公共政策规范;三是该国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所应承担的义务。并从实体、程序、公共政策规范、国际义务层面具体列明了一些属于国际公共政策的事项。
三、“公共政策”司法审查的“统一化”
“公共政策”具有灵活性、无法“定型化”的属性已是普遍共识。韦斯特莱克曾言,“给公共秩序保留规定范围的企图从未取得成功……只能由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论是通过立法机关还是通过法院,去决定他的哪一些政策是紧迫到必须援引。”[13-14]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政策”是体现了一定价值标准的规范性概念,这种规范性概念要求法律适用者自己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其判断标准又显然存在于法律秩序之外。[15]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政策系“立法计划安排的缺陷”。它赋予了司法审查主体某种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裁量并不是任意的,其应以正确的理念导引,并采取一系列较为合理、正当的审查原则,努力实现维护和保障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的根本价值、利益与履行公约义务、促进仲裁发展的平衡。一国之内的司法机关在审查公共政策之时,要尽量体现司法体系内的一致性,让一国的司法行为可以准确预测,以此彰明一国司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这同时也是履行《纽约公约》义务所需要的。
(一)理念层面,支持仲裁,限制解释与适用公共政策
《纽约公约》秉承的是“支持仲裁”的理念,其亦因受此理念之启发而被缔结。[10]57,[16]《纽约公约》第5条将拒绝承认与执行的理由以穷举的方式列明,并且这些理由皆受到严格的解释。在进行个案司法审查时,要对《纽约公约》的背景、主旨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要关注国际通行的司法实践,从支持和鼓励仲裁的视角认识到公共政策只是一种“例外”,而非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6]139援引公共政策应审慎、合理、正当地进行,不能不用,但绝不能滥用。
(二)审查分类层面,区别对待,准确适用法律依据
要明确区分一项申请执行的仲裁裁决是国内仲裁、非《纽约公约》项下的涉外仲裁还是《纽约公约》项下的仲裁,坚持不同的审查原则与标准。对国内仲裁的司法审查系中国内部事务,某种意义上并不需要考虑国际影响和公约义务之履行;对于非《纽约公约》项下的仲裁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对于《纽约公约》项下的仲裁裁决,依照《纽约公约》进行审查。
(三)界定标准层面,本土化兼顾国际化
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同法院地的社会有密切联系,不能超越特定社会的法律秩序而存在,而且,在当前要贯彻国际协调主义尚有困难。所以,从保留条款具有例外的、消极的性质这一点来看,原则上应理解为是一种内国的观念,较为妥当。”[17]《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也系以执行法院地国的标准来界定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运用公共政策时应当避免以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或狭隘的国家主义歪曲公共政策本意,因为目光短浅的现代民族主义会严重损害国际私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的价值。[18]中国作为《纽约公约》缔约国,作为仲裁事业日益发展、经济日益繁荣的国际大国,负有维护和促进实现国际民商事交往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的应然义务。虽然公共政策界定仍然以法院地法为基准,但必须明确的是:以法院地法为标准并不等同于将国内仲裁的公共利益问题等同于《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在考察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政策之时,正如国际法协会的国际海事仲裁委员会《最终报告》中建议的那样,应该考虑到其他缔约国法院的做法、学者的论著及其他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指的并不是单纯为某一国强制性规则所确定的公共政策,其更关注于本土与其他缔约国或国际上通行的公共政策的一致性部分,更强调这种认定的做出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持一致,因而在认定原则上与单纯的国内公共政策有本质的区别。
(四)基本内容层面,只包括违反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
虽然中国对《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具体指向哪些事项没有专门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个案批复中还是从正、反两个维度指明了公共政策的一些内容。从正包含维度看,明确“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被认定为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明确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归属于公共政策范围。从反面排除维度讲,明确指出了违反中国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仲裁实体结果不公平、仲裁员对中国法律的错误认识等不属于公共政策。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案批复只能解决个案事项或指明一定方向,但就具体内容而言,其对繁杂事项的涵盖性明显不足,这就要求司法审查主体不能单纯地依赖于一文一事,而需要在正确理念导引下借助可利用的其他资源。结合有关学者的论述并参考国际法协会的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最终报告》,笔者认为,下列事项可被认定为《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
第一,实体性公共政策:中国的宪法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原则(如合约信守,诚实信用,禁止滥用权利,禁止无偿征用,反对种族歧视与灭绝,禁止海盗、贩毒、走私、洗钱,禁止恐怖主义),社会基本道德(如赌博牟利、未成年人性交易、卖淫嫖娼等社会公认的普遍的善良风俗),国家的主权和领域安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涉及全国的社会公共安全等。
第二,程序性公共政策:仲裁庭(员)欺诈、腐败作出的裁决,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与中国有既判力的判决或者仲裁裁决不一致,但不宜包括仲裁员非因欺诈或腐败原因明显地无视事实和法律。
第三,公共利益强制规范:违背中国反垄断法、反倾销法、涉及国家根本经济利益的货币管制规则、价格管制规则、环境保护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障类法律),违反中国禁运、封锁、联合抵制等措施,但应注意中国行政法规和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则只有涉及到中国的根本利益时才可被识别为公共利益规则。
第四,国际性义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强行制裁决议、违反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违反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承担的义务等。
(五)技术选择层面,少援引、多说理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尊重已成主流,对《纽约公约》项下的公共政策范围应尽量做限缩界定,尽量少援引。在涉及拒绝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项下的仲裁裁决之时,如果存在其他事项已足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无需援引公共政策。如对于仲裁协议无效、严重仲裁程序瑕疵、超裁、有违执行地国既判力原则的,依当事人申请查明后,直接援引《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列明的5种情形拒绝承认和执行;对于可仲裁性问题,依据《仲裁法》第2条、第3条进行审查并综合考察其他缔约国关于可仲裁性问题的通行做法后,直接以仲裁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但仲裁裁决确实存在侵犯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最根本利益以及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及根本道德的,也应果断援引公共政策,但必须详细阐明某事项之所以被识别为违背中国公共政策的理由,要注重逻辑论证与说理,尽可能体现识别与适用过程中对国际通行做法的考量,对于仲裁裁决为何侵害中国基本法律原则或根本利益以及该法律原则及根本利益在国内与国际的正当性、合理性也要阐释明晰。
四、结语
《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作为阻却仲裁裁决发生效力的“最后一道屏障”,系可供各缔约国法院使用的“剩余条款”。但应认识到,《纽约公约》的基本主旨是“支持仲裁”,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作为《纽约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在对《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进行审查时,应本着支持仲裁的理念,破除地方利益本位主义,密切关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动态变化和各缔约国关于公共政策审查的好做法,做到既维护好中国根本利益,又兼顾公约义务。

表1 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法院公共政策审查情况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ARFAZADEH H.In the shadow of the unruly horse: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J].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2002(13):56-57.
[2]张艾清.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07(6):100.
ZHANG Ai-qing.Study on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J].Law Review,2007(6):100.(in Chinese)
[3]黄进,郭华成.再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问题——兼谈澳门国际私法的有关理论与实践[J].河北法学,1998(2):15.
HUANG Jin,Guo Hua-cheng.The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ca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Hebei Law Science,1998(2):15.(in Chinese)
[4]BERG A J.TheNewYorkArbitrationConventionof1958[M].London: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1:366-367.
[5]李沣桦.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在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适用研究[J].北京仲裁,2009(2):74.
LI Feng-hua.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ndatory rules and public policy i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J].Beijing Arbitration,2009(2):74.(in Chinese)
[6]高晓力.论国际私法上的公共政策之运用[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
GAO Xiao-li.Study on practice of public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D].Beijing: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2005.(in Chinese)
[7]张宪初.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中“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M]//韩健.涉外仲裁司法审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59-395.
ZHANG Xian-chu.The new development in judicial review of foreig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from view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policy[M]//HAN Jian.The Juridical Review of Foreign Commercial Arbitration.Beijing:Law Press,2006:359-395.(in Chinese)
[8]LEW J D M.Applicable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M].New York:Oceana Pub.,Inc,1978:532.
[9]徐琳.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J].河北法学,2009(7):17.
XU Lin.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public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J].Hebei Law Science,2009(7):17.(in Chinese)
[10]HANOTIAU B,CAPARASSE O.《纽约公约》第5条下的可仲裁性、正当程序以及公共政策——以法国与比利时为视角(上)[J].傅攀峰,译.仲裁研究,2013(4).
HANOTIAU B,CAPARASSE O.Arbitrability,due process,and public policy under Article V of theNewYorkConvention—Belgian and French[J].translated by FU Pan-feng.Arbitration Study,2013(4).(in Chinese)
[11]BERG A J.1958年《纽约公约》的现代化——2008年“新纽约公约”译释[J].黄伟,鲍冠艺,译释.仲裁研究,2010(1):76.
BERG A J.The modernization of theNewYorkConvention1958—a closer look at the proposed new“NewYorkConvention2008”[J].translated by HUANG Wei,BAO Guan-yi.Arbitration Study,2010(1):76.(in Chinese)
[12]朱伟东.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中的公共政策问题[J].河北法学,2007(5):133.
ZHU Wei-dong.The public policy issue i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J].Hebei Law Science,2007(5):133.(in Chinese)
[13]WESTLAKE J.A treati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M].7th ed.London:Sweet & Maxwell,1925:51.
[14]肖永平.肖永平论冲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91.
XIAO Yong-ping.XIAO Yong-ping theory of conflict of laws[M].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02:91.(in Chinese)
[15]杨弘磊.中国内地司法实践视角下的《纽约公约》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211.
YANG Hong-lei.Study onNewYorkConventionon basis of juridical practices in China[D].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06:211.(in Chinese)
[16]PAULSSON J.May or must under theNewYorkConvention:an exercise in syntax and linguistics[J].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1998(2):227-230.
[17]北胁敏一.国际私法——国际关系法II[M].姚梅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67.
MICHI K.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relation law II[M].translated by YAO Mei-zhen.Beijing:Law Press,1989:67.(in Chinese)
[18]李双元,金彭年,张茂,欧福勇.中国国际私法通论[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2.
LI Shuang-yuan,JIN Peng-nian,ZHANG Mao,OU Fu-yong.The general theory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M].2nd ed.Beijing:Law Press,2003:182.(in Chinese)